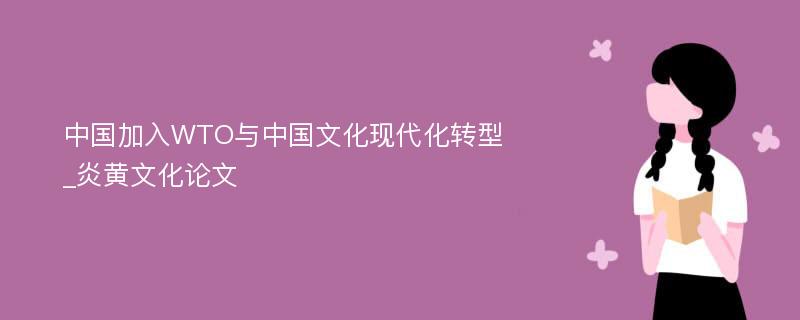
入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2)04-0023-05
一、流动的文化
有人说,中国“入世”是经济方面的事,与文化无关。这种看法失之片面。
文化是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胞中的,任何经济活动都充分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因此,古往今来国家间的贸易经济往来,都伴随着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谁能说希腊文化蔓延全世界与它的海上贸易无关?经济是文化的载体,经济活动中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必然会发生碰撞、冲突,其中就会有变异、融合。WTO经济走进我们,更不是一个孤立的事实,它与价值观俱来,它与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俱来,与人俱来。例如世界贸易组织中商品的交换流动是讲究严格的规则的,这些规则讲究公平、自由、透明,讲究法律公开,强调保护私人财产,强调时间和效率……它适用于所有入世国,所有入世国都将分享它的利益,也都将受到它的规范和约束,违反者还将受到它严厉的惩罚。它的“互惠”原则、“非歧视性”原则、它的“国民待遇”原则、它的“普遍适应性”,说的就是这些道理。它的原则与荒谬的政治,与封建专制和官本位,与权力经济,与暗箱操作和权力腐败等等都是格格不入的。WTO原则要求消解140多个入世国因所有制不同带来的差别政策以及身份等级观念等等,要求入世国都建立完善起一套符合WTO规则的社会管理运行的体制;它的原则,将会有效地规范人的行为方式,进而逐步改变人的陈旧的惯性的思维方式。那种只想拥有现代化的电脑设备和生产流水线、只想拥有现代化的吃穿住行等物美价廉的商品,而拒绝现代生产的管理体制和先进的商品理念的做法,已成为不可能。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那种市场经济与权力经济并行运作所形成的颇具中国特色的“准市场”行为——企业家一只眼盯市场,另一只眼盯官场的现象,已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
再者,从商品消费来说,商品生产者利用品牌、包装、广告等连环套似的各种手段,吊起消费者的胃口,诱惑消费者的欲望,千方百计地迎合消费者诸如身份、地位、归属、炫耀等心理,目的自然是促销以获取最大利润,但这些宣传实际上也是在创造一种文化——消费文化,它们在潜移默化地引导着人们的价值取向。而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也不再单单为了有屋住有饭吃有衣穿有自行车骑,不再单单为了简单的使用价值,而是伴随着钱袋子的鼓胀而萌生出更高的精神和心理上的需求。例如,消费者购进一部“奔驰”汽车,他不仅仅是为了结实耐用跑得快,更重要的是他在寻求一种心理精神上的满足,他在购车的同时,也购买了一种气派、风度、时尚,购买了他认同的一种文化。消费者无形之中接受了商家宣传的价值观。可以说,生产者和消费者不仅仅是商品买卖的经济关系,他们之间也发生了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况且,而今的商品交流,早已不是丝绸之路上驼队艰难的跋涉抑或一只满载国贷的大船漂洋过海去换点洋货了;商品交流的迅速及时和文化影响早已千百倍于历史。电影、电视、广播尤其是互联网的问世,更使“商品交易”这个概念不再仅仅是“物质交换”了。影视作品是商品,更是文化产品,精神产品。这种文化商品不同于一般的日用百货家电汽车,它直接承载着制作人的思想理念、价值标准,当我们也来分享好莱坞电影带来的快乐的同时,谁能说它所表现的思维模式不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
文化是流动的,而文化流动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水往低处流”,也就是发达国家的文化向欠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的文化,依托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已经形成了一种自我扩张自我增强的体制。“一个国家文化辐射力的强弱,受制于整体国力。整体国力强,辐射力就强;反之则弱。”[4]我们中华民族也有过令全世界瞩目的辉煌的历史,人们常常怀念大唐气象,那时的文化可谓是盛世文化,唐文化的流动辐射遍及东南亚,乃至全世界,至今世界各地都有生意兴隆的唐人街,就是明证。再如中国的17、18世纪,也属盛世,那时的德国就弥漫着“中国热”,大作家歌德家的客厅里就摆放着中国式的描金红漆家具,悬挂着印有中国图案的蜡染壁帔,客厅的名字就叫“北京厅”。歌德曾阅读了大量的中国书籍,把元杂剧中的《赵氏孤儿》改编成悲剧《哀兰伯诺》,还创造了著名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被称为“魏玛的孔夫子”。那时中国文化属于盛世文化,那时的文化流向是由东向西,德国人知道中国的四书五经等作品,而中国对他们却不甚了解,后来中国逐渐衰落,西方强大起来,文化交流的主要流向则变成了由西向东,我们知道歌德乃至茨威格、史托姆、伯尔,而他们却连鲁迅、郭沫若、茅盾都不知道。[4]试看当今中国的电影市场,我们虽然为了保证民族电影业的发展尽量控制外国影片的进口量,但美国好莱坞影片还是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占尽了风头,而我国影视界却很难拿出同量的大片推向西方。
中国入世,我们加入的是在发达的工业文明背景下西方社会经济基础上制定的WTO,而不是加入的欠发达的农业文明背景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上制定的WTO,这很清楚,中国入世,是要求我们适应世界,而不是要求世界迁就我们。显然,入世之后,西方的文化之流将更加顺畅地流向中国。中国文化必须作出与之相适应的调整与转化,才能与世界同步而不致于再次落伍。
二、文化的稳定性
那么,中国文化会被全球化同化掉吗?有的学者为此深深担忧。其实,入世并非统一全球的文化,并非排斥个性的文化。世界文化的丰富性源于多国多民族的文化个性。世界上的每一种文化都与其国家民族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各种不同的文化可以互相借鉴、融合,却不可以强行取代。WTO的规则之一就是对于个性的尊重。可以肯定地说,入世之后,中国特色的文化只会被优化,而不会被同化。理由有三:
其一,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本民族文化的根基,汉字汉语的独特性更注定了它的不可替代性。不要以为汉语中多了一些洋文的词汇和修辞方式就是同化。尽管当今中国不属于强势文化,尽管西方文化之流澎湃而来,但不可能动摇我们的根基,相反,倒是给了我们新的丰富的滋养,使中国文化之树绽出新绿。
其二,中国文化的根是很深的,有很强的稳定性。中国13亿人口,有10亿多农民,农民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是地域广大的农村,活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收藏在博物馆里,不是摆放在书架上,而是活在这地域广大的农村,在古泽遗韵里,在民俗风情里,在繁文缛节里,在祖祖辈辈绵延繁衍生生不息越来越多的人群里。传统的美德在这里,传统的陋习也在这里。这种内部文化的变革比起外部法律设施、经济体制、社会管理形式的变革来要艰难得多。但外部的变革会为文化的逐渐变革提供优化的条件,如今我们已经看到了农村的逐步城镇化和农业逐步工业化所带来的新的文化气象。
其三,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包容性。它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再生能力。中国的香港、澳门分别被英国人和葡萄牙人统治了若干年,但香港文化没有变成英国文化,澳门文化也没有变成葡萄牙文化。中国文化不排斥异质文化,而是在接受了异质文化之后,又会创化出中国的特色。例如,古印度的佛教传到了中国,就成了中国的禅宗。西餐传到中国,吃起来就有了中国的风味,当代著名作家王蒙讲过一个中国人喝美国的可口可乐的故事,很耐人寻味。他说,可口可乐一开始进入中国并不成功,美国人用了很多办法促销,慢慢才流行开来,孩子们特别喜欢喝,但家长们不让喝太多,担心里面有咖啡因。但不久,王蒙就发现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喝法而不和美国人一样地喝。中国人用美国可口可乐饮料煮姜末当感冒冲剂来喝治疗感冒。按中医的说法,可口可乐可以起发散的作用。它这点咖啡因对受感冒折磨的人来说可以让他提点精神。可口可乐到中国喝法发生了变化,XO到中国喝法也发生了变化。王蒙讲的这个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我们中国人对异质文化的改造创化。中国人到了美国,有的入了美国籍,甚至有了第二代第三代,也还是没有被外国文化同化,他们可能似浮萍般漂泊,但他们的文化之根仍然在中国,他们仍然在家里说汉语,喜欢吃水饺,很看重过春节。“洋装虽然穿在身,心依然是中国心。”他们精神建构的材料更多的还是中国的文化,他们的思想资料,更多的还是来自孔孟之道、老庄哲学,甚至是毛泽东思想。
中国文化的稳固性特征,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但是,也正是因为中国文化的超稳定性,所以文化的“优根”易于保存,文化的“劣根”也难于革除,这种劣根甚至还会借助开放自由的环境而滋生蔓延。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文化中一些封建腐朽的东西正与金钱联姻借助自由经济之势为自己寻找市场,从而阻碍社会的进步。近年来著名学者张志忠教授痛惜“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失落,不断著文抨击世纪末封建文化的全面回潮现象,但回应者寥寥,封建文化仍然是载歌载舞烟雾缭绕。这是值得警惕的文化现象。中国加入WTO,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真可谓天赐良机,积极促动中国文化尽快向现代化转型,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三、文化的冲突
日本著名学者丸山真男把近代世界各国的文化成长与转型,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成长”型,一类是“目的意识”型,并且,他对这样一种文化现象作过深刻的分析:……如果用列宁用语“自然成长性”和“目的意识性”来表达,那么,相对“后进”的国家的近代化可以称作“目的意识性”的近代化。这一点,是与相对“先进”的国家的不同之处。比如说,在某种意义上,英国是“自然成长”的近代化的典型。在那里,近代化不是“目的意识性”的。也就是说,不是按实现近代化的愿望去推进近代化的,其近代化是作为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而出现的。正因为如此,他们保留了一些落后的东西,例如残存着身份制等等。……越是“后进”的国家,越具有“目的意识性”,因为在那里,事先有了近代化的模式。只是以其为目标来推进近代化。由于是“目的意识性”的,所以当然会带上较强的意识形态性格,也就是某种意识形态指导下的近代化。同是在西方,美国独立革命比英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性强,法国革命比美国的意识形态性更强。其理由就在于此。所以在这样的国家作为异质文明传播者的知识分子的任务,自然也受到“目的意识”的近代化要求的制约。[1](P17)
按照这种分析,中国的近代化自然是典型的“目的意识性”的。因为中国虽然有过值得骄傲的古代文明,但到了近代,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崛起,仍滞留于封建王朝的中国成了落后于时代的“老朽”。为了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为了国家民族的强盛,百余年来,先驱们不得不以外部世界为参照,以西方先进的国家模式为榜样,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变革运动。可以说,从效法英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到摹仿美利坚和法兰西的民主革命,从以俄国十月革命为师所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到今天我们正在进行中的改革开放,都是中国的有识之士以外部世界为参照主动地推进中国社会转型的壮举。因此也可以说,中国近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地进行“目的意识性”非常明确的一系列文化选择的过程。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华民族百年来的艰苦奋斗并没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以致到了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仁人志士强烈地感觉到中国有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所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与中国的近代化的努力有异曲同工之处,即都是在现代化愿望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主动走向世界,并把世界引入中国,加快中国现代化进程的。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乃至加入WTO,都是中国人民具有“目的意识性”的文化选择。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自然也会带有相当强的意识形态品格。
在现代化“自然成长性”的国家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是大致和谐的,社会进步与文化转型是同步相伴的,而像我们中国这种发展中的“目的意识性”很强的国家,是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先行,并以思想文化为杠杆去跃动推进社会的全面改革和进步的,所以,这样的国家某一方面可能会发展较快,某一方面却可能严重滞后,由此,异质文明和本土草根文化的冲突会特别的激烈,文化的震荡和失衡也会特别突出。
WTO的规则是一种科学的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则,它所传递的工业文明的理念精神与中国农业文明中所孕育出的传统文化就有着明显的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自西汉开始,“独尊儒术”的社会政策,就使原始状态的“学术儒家”成为“政治儒教”,绵延到中国近现代,它一直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这种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风化流行,儒家思想已经沉淀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而化作民众行为的忠诚、孝道、节操、义气、信用、仁爱、礼仪等伦理道德风尚。儒家学说的原始状态与儒家思想在民间的流行并不完全吻合,而是一种折射的关系。中国伦理道德的本质就是强调个人对他人的义务,观念上“无我”,践履上“苦行”,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颇有特色的“群”文化,与西方的“己”文化恰成鲜明的对照。以“群体”为本位的文化对封建政权的稳固是有利的,但在此基础上,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经营方式是个体的、分散的,人与人之间在事业上是极少合作的,所以合作精神比较淡薄。经济与文化的交织在社会结构方面的表现则是“形聚而实散”。即表面上看来是群聚簇居比邻相望,实际上产业之间并没有多少有机的联系。张景芬教授在诸多论述中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文化特点。我觉得中国古代那个“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是很形象地说明我们民族精神文化上某些缺陷的。
中国传统的世俗儒风、儒家思想与WTO规则下的商品经济文化精神有着明显的矛盾和冲突。世俗儒风在农业经济和计划经济时代,使社会维持在低效稳定的统一体中,但进入商品经济时代,则与社会发展的种种要求相冲突了。农业经济与计划经济不是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它的精神指向或道德要求是“无私奉献”,这和儒家以“群体”为本位的文化是吻合的。但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通过交换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是商品的天然本性;相应的商品生产者的价值观或精神导向是“自我实现”。这种以“个己”为本位的文化观念与儒家思想是相矛盾的。儒家的许多东西与商品经济的种种矛盾的确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例如,儒家文化讲伦理,商品经济讲功利;儒家文化讲中庸,商品经济讲竞争;儒家文化讲等级,商品经济讲平等;儒家文化讲人治,商品经济讲法治;儒家文化传递宗法观念,商品经济倡扬科学民主;儒家文化维持“天”和共性,商品经济解放“人”和个性;儒家文化重传统,商品经济尚革新……这种文化观念的冲突和较量将会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WTO文化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撞,将成为当今时代最深刻的主题之一。
四、文化的选择
在与WTO原则的冲突与较量中,儒家文化中不适应现代化的成份必然被淘汰。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消亡。相反,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将在这场冲撞中经历扬弃、死灭和再生,中国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生将得益于可以预见到的两大变化:第一,中国的工业发展将完成从初级到高级的深度跃迁,真正“摆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社会联系呈有机网络。20多年的改革,在现代化的猛烈冲击之下,中国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处在了“前工业社会”阶段,换句话说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入世”,更带来了新的机遇,农业将会加快工业化,乡村将会加快城市化,旧的道德信条将会加速瓦解。工业文明在华夏大地的崛起必将改造和提升传统的地方文化。第二,包容市场经济工业机制的社会管理体制将完成深度改革。过去20多年在这方面的改革已初见成效。WTO的规则运作将为深度改革提供机遇和外部推动力,现代企业的迅速发展将为深度改革储备实力提供活力。这一切必将催生新的社会管理形式,催生出新的思维方式,从而为文化精神的再生提供制度保证和物质前提。
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生最重要的是儒家文化中宝贵的“和”的文化因子的重生。
也许先哲们深知华夏子孙积蓄了太多的恩怨和仇恨,深知我们民族“斗”的残酷与“和”的艰难,所以孔子把中国人际关系的和谐作为最高目标,谆谆告诫后人“和为贵”。时至当代,“和”的步伐仍是步履维艰。长期以来,我们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大搞“窝里斗”,就是我们跟别人过不去,划分出若干个“阵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我们的内部环境不得安宁,外部环境也十分紧张,既有内忧也有外患。整个20世纪可谓“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早在19世纪初德国的伟大诗人席勒曾预言:你们互相敌对吧,联合起来还太早!你们分头去找,真理才会找到。今天,经过20世纪百年的对立和寻找,在21世纪到来的春天,人们把分头找来的真理加在一起,形成了多元共处而走向了“和”。WTO世界就是一个具有共同规则而又共同守约的“和”的世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发展。今天这个“和”的环境,不同于以往那个“斗”的环境。这种“和”的环境,需要培养起崭新的合作精神,摒弃过去的“斗争哲学”,“志同道合者我们合作,志同道不合者或道合志不同者我们也合作,即使志不同道也不同者仍可在许多领域中的具体事情上合作。”[2](P31)人,是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的人,关系和谐,人的身心愉悦,事情才能做得好;“和”则进,不“和”则退。合作,能够软化心灵优化人性完善人格,也能营造“和”的国际环境。半个多世纪以前冯友兰先生在美国宾夕凡尼亚大学曾向西方人这样讲解中国文化的奥妙:
和是调和不同以达到和谐的统一。《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子(卒于公元前493年)一段话,其中区分了“和”与“同”。他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由这些作料产生了一种新的滋味,它既不是醯(醋)的味,也不是醢(酱)的味。另一方面,同,“若以水济水”,“若琴瑟之专一”,没有产生任何新的东西。同,与异是不相容的。和与异不是不相容的,相反,只有几种异合在一起形成统一时才有和。但是要达到和,合在一起的各种异都要按适当的比例,这就是中。所以中的作用是达到和。
一个组织得很好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统一,在其中,各种才能、各种职业的人都有适当的位置,发挥适当的作用,人人都同样地感到满意,彼此没有冲突,《中庸》说: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第三十章)
这种和,若不只是包括人类社会,而且弥漫全宇宙,就叫做“太和”。易乾卦《爻辞》说:“大哉乾元!……保合太和,乃利贞。”[3](P150-151)
冯先生对于“和”的阐释可谓启人心智。当今世界这个大天地,正是由于世界多国都处在一个世贸组织中,这就使东西方各种异质文化共处在了一个统一体中,长此以往就有可能诞生出一种属于全世界的崭新的文化来。与WTO原则相契合的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和”因子,将伴随着中国的入世,伴随着世界一体化市场经济的弥漫而获得新生!
从本质上看,这次入世带来的文化转型其实也是上世纪之初文化先驱们所倡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因为WTO原则的精神实质,正是“五四”所倡导的科学民主精神。20世纪接连不断的战乱和政治动荡,使中国人来不及进行扎扎实实的文化重建,先是“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后是运动排挤了启蒙,以致“五四”精神的弘扬时断时续。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解放了“人”。今天,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强化,人的价值观念得到了更新,改革已经呼唤出人们变革现实完善人生存环境的热情,为民主科学精神的生长培养了新的土壤。而今中国入世,又为民主科学精神在中国国土上扎根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更可喜的是,如果说“五四”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呐喊启蒙,那么这次转型则是顺应民意的政府领导全民的行动;如果说“五四”是停留在文化界的著书立说上,那么这次转型则是将现代经济文化的规则法制化地落实在具体的实践中。这次转型虽没有“五四”那般猛烈的摧枯拉朽的火药味,但它却比“五四”来得更深刻、更彻底、更有效。我们可以感受到,“被思想理论界热切呼唤的文化启蒙和‘五四’精神正在变成一场不动声色的深层文化观念变革的全社会的行动,行动本身正在消解着‘顽疾’,正在落实着‘五四’启蒙的任务和民主科学的精神”。[2](P31)“五四”所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与儒家的“和”的文化因子,必将创生出中国崭新的时代文化。
然而,“中国改革面对的是患了慢性‘顽疾’的社会,故需用‘中医缓药’。我们需用充分的耐心,需用百倍的努力,去克服一个一个具体的困难,去解决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2](P31)对内促转型,对外促互动,面对全球化的市场和文化的流动之势,中国文化人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就是加快文化的互动,努力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方面我们还作得十分被动。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俄亥俄大学等图书馆我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图书往往多于中国大陆的图书。在法国也是如此,中国的书很少,现代作家鲁迅和茅盾的书只有几本,当代作家的书也只有莫言、余华的。我觉得,这种只等洋人来取经学习,而不去主动输送的消极姿态背后,表现着古老文明大国的“有麝自来香”、“好酒不怕巷子深”自大风度,隐藏的却依然是农业文明社会小生产者的保守心理。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理应行动起来,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