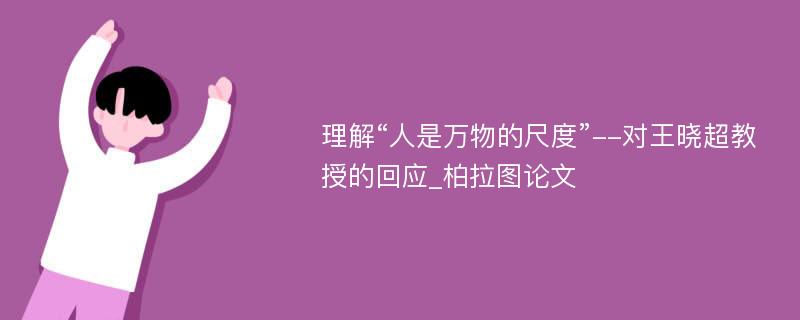
理解“人是万物的尺度”——回应王晓朝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是论文,尺度论文,万物论文,教授论文,王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2.232
文献标识码:A
去年我出了《读不懂的西方哲学》一书(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王书》”,引文只注页码),进一步论述了我自己主张的观点:在西方哲学研究中,应该把being翻译和理解为“是”,并且把这种翻译和理解贯彻始终。该书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的中译著作中选了一些论述,通过分析指出,由于把being翻译为“存在”,因而使理解他们的思想产生问题,使本来可以读懂的地方反而读不懂了。柏拉图的著作我选的是《泰阿泰德篇》中与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相关的一段文字。我认为,柏拉图的著作是名篇,“人是万物的尺度”又是著名论题,围绕它们进行讨论,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应该在“是”的意义上理解being,而且也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著名哲学问题。
《泰阿泰德篇》一文中译者王晓朝教授在本刊2012年第2期撰文《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再读》(以下简称“《朝文》”,引文只注页码),对我的讨论做出批评。感谢他的讨论和批评!但是我无法赞同他的许多论述。在他看来,“王路教授中了他自己制造的‘圈套’,落入了他自己造成的‘语言困境’,犯了‘词义漂移’的毛病”(第144页)。这三个加引号的贬义词是《朝文》在文末结合贝克莱、马赫、孟子、王守仁的话使用的。“圈套”有阴谋论的含义,可以不予理会。“‘语义漂移’的毛病”由于不是从分析《王书》得出的,因此也可以不予理会。“语言困境”倒是哲学讨论中常用的说法,因此,尽管这是《朝文》推论出来的,也还是可以认真对待的。比如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批评来思考,《王书》对文本的解读和分析是不是会制造语言困境?坚持我的上述观点是不是会制造和陷入语言困境?
一、几个明显的问题
首先我想说一说《朝文》几个比较明显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王书》关于柏拉图的讨论主要围绕着“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论题。《朝文》认为对它的“理解和翻译是我们讨论这节对话的关键”(第141页)。它讨论了自己的理解,也提到王路“一是到底”的观点。它说:王路在批评“存在”译法时“一般会给出他自己的译文,但对普罗泰戈拉的这个哲学命题我没有看到他给出的译文”(第142页),由此《朝文》进一步对王路提出意见和批评。
《王书》给出《泰阿泰德篇》的十段中译文,在分析了其中读不懂的问题之后,分别给出了它们的修正译文,然后又根据修正译文讨论了对柏拉图的理解,以及修正译文如何可以消除原中译文所存在的问题①。也就是说,《王书》明明给出了该论题的修正译文(第26页),《朝文》却说没有看到,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
第二个问题。《朝文》引了王路一段话,其中说到“einai这个词有时候表示的意思是存在,甚至可以说,它的有些用法我们只能用‘存在’表示或表示存在的词来翻译才合适”,然后《朝文》说:“王路教授在断言柏拉图的这节对话所包含的例子根本不含‘存在’一词的时候,要么是他忘了自己以前说过的话,要么是他想通过强调西方语言与中国语言的差别来误导读者,以证明中译文的理解和翻译是错误的,应负妨碍中国人正确理解柏拉图之责。”(第140页)
《朝文》所引是王路说过的话不假,但那不是在《王书》中,而是在其他地方。确切地说,那是王路在《是与真》一书中介绍了卡恩关于希腊文einai一词的三种用法(系词、存在、断真)之后,进一步探讨该问题时的论述。与《朝文》引语相关,王路在它之前说“系词用法和断真用法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唯一有变化的是存在用法”,而在它之后则探讨了与einai的存在用法相关的几种表达,包括法语的il y a,德语的es gibt和英语的there is②。这表明,王路对being一词的存在含义是非常重视的。《朝文》所说《王书》断言柏拉图的例子中不含“存在”一词也是真的。但是,柏拉图在例子中使用“是”而没有使用“存在”一词,乃是中译文告诉我们的,而不是《王书》修正后的译文告诉我们的。因此,《王书》只是照本宣科,陈述了一个事实而已。这与此前说过什么,包括是不是“忘记”了什么,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误导读者”之说更是无从谈起。
第三个问题。《朝文》在探讨“感觉能不能说明存在”一节中反复强调说:“王路教授认为,柏拉图和普罗泰戈拉不是在用感觉(风是冷的)说明存在,因为感觉不能说明存在,只能说明‘是’”(第144页,参见第143页)。并基于这种看法对《王书》进行了批评。
感觉是不是能够说明存在,无疑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是,“感觉不能说明存在,只能说明‘是’”,这究竟是谁的观点?《王书》没有这样的论述,《朝文》在这样说的时候也没有引文注释,因此,这不是《王书》的,而是《朝文》推论出来的。《朝文》多次引用的《王书》相关质疑是:“以人感觉到风是冷的或不是冷的为例怎么能够说明人是存在的事物存在和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呢?”(第139、143页)这话很明确,如果说《王书》以疑问的方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那么字面上也只能得出,《王书》认为,以感觉到风是冷的并不能说明人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即使不考虑其中“风是冷的”与“存在的事物存在”之间的关系,充其量也只能得出这里谈到“感觉”与“人是(事物的)尺度”的关系。怎么能够如此轻率地直接得出感觉与存在的关系,并因此强加给《王书》一个“感觉不能说明存在”的看法呢?
与此相关,《朝文》说:“还有两个旁证可以表明柏拉图在这里想用‘风是冷的’这个例子来说明‘人是事物存在的尺度’。就在《泰阿泰德篇》中,柏拉图为普罗泰戈拉设计过一番辩护性的解释:‘我确实像我在著作中写的那样,肯定这是一条真理。我们每个人都是存在与不存在的尺度。但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人与那个人之间全是有区别的,这正是因为存在并对某人呈现的东西,与存在并对另一个人呈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166d)……当然了,按照王路教授的一贯思路,他一定会说这些对话中的‘存在’都应当理解并翻译为‘是’。”(第144页)
删节号中是柏拉图另一部著作中的话,我们可以不用考虑。仅从所引的这段话,似乎看不出与《朝文》所要说明的东西有什么关系。而我想要说的是,柏拉图的这段话是《王书》引用的十段话中第四段中的一部分,而在其余部分,即其上下文中,也有例子,比如食物是酸的(参见《王书》,第8-9页)。同样,《王书》不仅分析了这段译文理解中的问题,包括例子与所要说明的东西不一致,而且也给出了修正的译文:“……我们每个人都是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尺度,但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人与那个人之间全是有区别的,这正是因为某物对此人是这样的并且呈现为这样的,而对彼人是别样的并且呈现为别样的。”(第33页)若是多读上几页,就会直接讨论《王书》对这段话的看法,又何至于推论《王书》会怎么说呢?
类似问题还有一些,兹不一一列举。以上几个问题比较典型,列举它们是想说明,若是认真阅读文本,许多问题本来是不该出现的。
二、关于“人是万物尺度”的理解和翻译
人是万物的尺度乃是一个重要哲学论题。《王书》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指出:中译文把它翻译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而柏拉图讨论它时举的例子是“风是冷的”和“风不是冷的”。由于例子中没有“存在”一词,因此使人不明白,这样的例子如何能够说明人是万物的尺度(参见第2-4页)。如果将以上翻译修正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既是是的事物是的尺度,也是不是的事物不是的尺度”,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例子中的“是”与普罗泰戈拉的命题中的“是”乃是一致的(参见第26-28页)。由于《朝文》没有读这些内容,因而它的一些相关结论我们可以不必当真,但是我认为,《朝文》关于这个论题的翻译本身的一些讨论还是值得认真对待的。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是万物的尺度。
《王书》引了柏拉图十段话,《朝文》的讨论集中在第一段。它认为,对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理解和翻译是我们讨论这节对话的关键”(第141页)。因此它对相关的翻译和理解做了许多讨论。《朝文》指出,西方学者对这句话的“理解从来就不一致”(第141页),并谈到格思里的《希腊哲学史》第三卷和汪子嵩等人的《希腊哲学史》第二卷对这个问题有“详细介绍”和“详尽的分析”(第141页),然后说:
普罗泰戈拉这个命题中出现了希腊文esti。这个词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西方学者一直以来就有两类理解和翻译。第尔斯、弗里曼、柯费尔德、格思里和其他许多学者要么按照exist去理解esti,在翻译时或者译为exist,或者沿用西方现代语言表达“存在”的习惯方式之一,译为to be(英文),Sein(德文),要么突出希腊文eimi的系动词含义,强调应当按照这一核心含义去理解和翻译它。这些西方学者的译文有助于我们理解希腊文的原义,但对中国学者来说,西方学者的前一类译法我们掌握起来比较容易,后一类译法则仍旧存在一个类似我们面对希腊文esti一样的问题,需要我们辨别他们的to be、being或sein到底是什么意思。(第142页)
接下来《朝文》就开始批评《王书》的“一是到底”论,并且陈述自己主张“存在”这种译法的理由。
以上是《朝文》一个完整的自然段。它放在讲述了西方学者的相关理解之后和批评《王书》的观点之前。这就给人一种感觉,它的论述似乎有根有据,毋庸置疑。因此我们要认真讨论这一段论述。
字面上看,《朝文》说明西方学者关于esti有两种理解,一种是exist,一种是系词;而依据exist的理解,又有两种译法,一种是exist,一种是to be。从这段的论述方式来看,似乎exist的理解是主要的,因而exist的翻译也是主要的。或者,至少它没有告诉我们哪一种看法和译法是主要的。我的问题是,《朝文》的说法是不是有道理?由于《朝文》提到了那么多西方著名学者做佐证,却又没有具体地说这些学者是怎么说的,只是此前提供了两个参考文献,我们就不得不看一看,这些西方学者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朝文》提供的第一个参考文献是格思里的哲学史第三卷,说他“在正文分析之后专门加了一个长达四页多的附录详细介绍了各家对原文的不同理解”(第141页)。格思里确实提供了一个附录,讨论对普罗泰戈拉残篇中三个术语(anthropos、hos、chremata)如何翻译和理解。其中与hos相关,讨论的是hos estin,这一讨论有三小段,约一页,前两小段主要围绕hos讨论,第三小段则是关于esti的。下面让我们一起看一看第三小段的论述:
讨论一直集中在这个表达中的hos一词,但是esti这个词同样值得评论。像其他学者一样,我的写作迄今一直基于一种假定:在没有谓项使用时,einai的首要含义(如果不是唯一的含义),乃是“存在”(to exist)。但是卡恩的说法是很有说服力的。他说,它(einai—译者注)的根本价值“不是‘存在’(exist),而是‘是如此的’(to be so),‘是这种情况’(to be the case),或‘是真的’(to be true)”。正像他指出的那样,这适合柏拉图对如下句子的解释:“各事物对我呈现什么样,它对我就是那样”,等等。“如果我们把einai的这种绝对用法理解为……一种对一般事实的肯定,比如‘什么是如此的’或‘什么是这种情况’,那么柏拉图的解释就变得完全自然的和明白可理解的。这样,存在用法,比如一个像‘有原子和虚空’(there are atoms and void)这样的肯定句,就会作为一种特殊情况包含在普罗泰戈拉的陈述hos esti所要达到的这种一般事实断定之中。如果人是万物‘它们是如此或不如此’的尺度,那么,正如人乃是风的是冷的或不是冷的(the being-cold or not-being-cold of the wind)的尺度一样,人也是原子存在或不存在(existence or non-existence)的尺度”。③
这段话显然包含着对esti的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存在”(to exist),一种理解乃是“是”(to be so,to be the case,to be true)。问题是,格思里对这两种理解是如何看的?他是不是就赞同前一种看法了呢?显然不是。他明确地说,存在理解乃是他以前的一个假定。而现在他觉得“是”的理解更另人信服。这无疑表明,他赞同后一种理解。然而,这只是大致的意思。若是仔细分析,还可以看出更多一些东西来。
首先,格思里假定了einai有存在含义,但这是有条件的:“在没有谓项使用时”。这就表明,即便认为einai有“存在”含义,他也没有认为这是这个词的一种绝对含义,因为“没有谓项使用”的情况显然不是einai的全部用法。至于这是不是einai的主要用法,或者什么是einai的主要用法,格思里在这里没有说。在我看来,hos esti字面上不是系词用法,乃是显然的。但是,如果这算是一种用法的话,那么这不是einai的全部用法,也不是它的主要用法,同样是显然的。
其次,后半段是引用卡恩的话。而根据卡恩的论述,应该以“是”来理解einai,并且把它理解为一种对一般事实的肯定。根据这样的理解,hos esti可以理解为“什么是如此的”或“什么是这种情况”。这种解释由“是如此的”、“是这种情况”等等理解演变而来,似乎是自然的。但是它的结果非常重要。因为对einai的一种没有谓项表述的理解演变为一种有谓项表述的理解,即一种系词结构的理解。
再次,有了以上解释,对普罗泰戈拉的命题似乎可以做出更好的理解:既可以理解“是”的含义,也可以理解“存在”的含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解释中,存在用法“会作为一种特殊情况包含在普罗泰戈拉的陈述hos esti所要达到的这种一般事实断定之中”。既然存在用法只是与einai相关的一种特殊情况,由此也就可以看出,它并不是普遍情况和主要情况。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卡恩说的存在用法,在给出的例子中也是there are,而不是exist。这就表明,他把语言层面的there are解释为existence。换言之,字面上是there are,它的含义被解释为existence。
阅读这段引文,直观上还可以问一个问题:既然格思里过去一直认为einai有存在含义,怎么如此容易就赞同了卡恩的观点呢?基于以上分析,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系词含义本来就是einai必要而主要的含义。卡恩的观点不过是更为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且接受卡恩的观点确实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普罗泰戈拉的命题,解决人们过去一直纠结的问题。格思里尽管曾假定存在含义,但是他并没有否认系词含义,因此,他放弃自己的观点,或者至少赞同卡恩的观点,从理解方面说应该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系词的理解至关重要,而且事实如此。④
既然《朝文》提到上述引文作为参考,为什么不据实说呢?“按照exist去理解esti”,这一说法尽管含糊,毕竟与事实出入很大。至少在格思里这里,关于exist的理解显然是有条件的,相反,接受卡恩的看法,因而按照to be去理解,却是明确而主要的。《朝文》读了这些内容了吗?它的说法不会误导读者吗?以这样的说法做前提,能够得出正确结论吗?
《朝文》提供的第二个参考文献是汪子嵩等的《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以下简称《史》,引文只注页码)。《史》也提到格思里“专门加了一个长达四页多(188-192页)的附录,详细介绍了各家对原文的不同理解”(第248页)。下面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史》的相关讨论:
Esti的含义问题。格思里和许多学者一样译为“存在”(to exist)。卡恩(C.H.Kahn)认为,esti或estin的基本意义不是to exist,而是to be so(是如此)或to be the case(是这种情况),to be true(是真的)。柏拉图在解释普罗泰戈拉的命题时说:“每样东西如此显现于我,对我而言它就是如此”(as each thing seems to me,such is it for me)。(《泰阿泰德篇》152A)卡恩认为这种理解是确切的,所以普罗泰戈拉的命题的从句可以译为:“人是某物是如此或不是如此的尺度。”这个命题用中文表达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既是‘是如此’的事物之所以‘是如此’的尺度,也是‘非如此’的事物之所以‘非如此’的尺度。”应该说这才是准确的表述,下面可以看到柏拉图关于两股风的释义就是以这样的公式表述的。但是这种表述法在中文中非常别扭,所以我们在阐明这个命题的含义的前提下仍采用传统的表述。(第250页)
一如《史》所言,它主要是依据格思里的论述说的。非常明显,它在论述中主要是按照格思里的论述介绍了卡恩的观点⑤。对照此前格思里的论述,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差异。格思里并没有把esti翻译为exist,在附录中,他只是假定它在某种情况下有存在含义,而在英译文中,他把它翻译为are。不过,《史》说许多西方学者都这样翻译。因此就需要考虑,其他学者是不是这样翻译的。如果是,那么即使《史》的说法在格思里这里明显有误,也算不了什么。遗憾的是,在《史》后来依次给出的第尔斯-克兰茨、弗里曼、老冈珀茨、柯费尔德等人关于人是万物尺度的四段德英译文中,都没有使用exist,而是用sind(德文)和are(英文),只不过《史》在讨论中把它们都翻译为“存在”了(参见《史》,第251-252页)。这就说明,《史》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不是格思里和许多学者把esti翻译为“存在”(exist),而是《史》这么做。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史》又为什么这么说呢?
可以看到,《史》根据卡恩的观点把普罗泰戈拉的命题翻译为“人是某物是如此或不是如此的尺度”,并且依次进一步解释了它的含义。特别是,《史》认为“这才是准确的表述”,由此还谈到柏拉图关于风的例子。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史》并没有坚持这种认识,而是采用“存在”译法,理由是中译文表达别扭。我一直强调,有关being的问题,并不是翻译的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明明看到了准确的表述而不采用,却从翻译的角度出发采用自己也知道不准确的翻译表述,又怎么能够得出正确的结果呢?⑥由此我猜想,《史》明明看到那些学者没有采用exist来翻译einai,却说他们把它翻译为einai,也许是自己习惯了“存在”的翻译和理解,因而不觉得这样会有什么问题,或者,也许是为自己采用的“存在”译法寻找支持。这种理解是不是正确也许是可以讨论的,但是这种支持毫无疑问是不成立的。
参照格思里的论述和《史》所谈到的众多学者的论述,《朝文》如何能够说他们把einai“译为exist”呢?难道他们不是把它翻译为are吗?除非《朝文》只看到上述引文的第一句,而没有看随后的引文。这样使用参考文献来支持自己的论述,显然是不恰当的。
三、语词与语词所表达的东西
《王书》指出,中译文将普罗泰戈拉的命题翻译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而柏拉图用来说明这个命题的例子是“风是冷的”和“风不是冷的”,这样,由于所要说明的乃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而例子中不含“存在”一词,与存在没有什么关系,因而说明不了所要说明的问题(第4-5页)。但是,这样的问题是中译文造成的,而不是柏拉图本人造成的。若是将中译文修正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既是是的事物是的尺度,也是不是的事物不是的尺度”(第26页),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所使用的例子是“风是冷的”和“风不是冷的”,这是事物对人呈现的情况,也是人感觉到的情况,所以人也会做出相应的判断。因此从提出上述命题到举例说明,直到最终得出结论,“柏拉图的讨论始终围绕着‘是’这个概念在进行。……例子与理论层面的说明乃是一致的,都是围绕着事物是和不是的情况,从而说明人是万物的尺度所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一个人感到风是冷的,这也是风向他呈现的样子,因此他认为风是冷的。以同样的方式,他也可能认为风不是冷的(或风是热的),风是有点冷的,或者风是非常冷的等等。因此,事物对他呈现什么样子,他就会认为事物是什么样子,而不会认为事物不是什么样子。正因为这样,他才会既是是的事物是的尺度,也是不是的事物不是的尺度,因而他才会是一切事物的尺度”。(第28页)
我不知道《朝文》是不是读了这些话,因为他没有对以上论述做任何讨论。它只是围绕《王书》说例子中没有“存在”这个词做文章。一方面,它说柏拉图的所有对话、全部希腊文献“都没有出现‘存在’这个词”(第140页),另一方面又说“如果我们认定eimi是一个多义词,有‘存在’的含义,并且认定eimi在句子中不作系动词‘是’解,而作‘存在’解,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些地方出现了‘存在’一词”(第140页)。正是基于这种论断,《朝文》说:王路教授一方面承认这个词的多义性,“另一方面又反复提出类似的理由来否定对希腊文eimi及其相关变形作‘存在’含义的理解和翻译,造成这种思想上混乱之症结就在于忽略或忘记了希腊语(以及其他西方语言)对‘存在’观念的表达方式”。(第141页)
尽管我不赞同《朝文》的这个结论,但是我还是认为,《朝文》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却是可以讨论的。它的意思可以简单地表达如下:希腊文中没有“存在”一词,但是einai(eimi)是个多义词,有“存在”含义,因此它也可以表达“存在”。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是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
一个问题是,关于“存在”,《朝文》这里有两个表达:一个是“出现了‘存在’一词”,另一个是“对‘存在’观念的表达方式”。我认为,后一个表达可以是清楚的:“存在”是一个观念,这是一回事,对它的表达方式则是另一回事。这也就是我非常重视并强调的要区别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参见《王书》第246-254页)。人们可以认为,希腊人也表达了“存在”的观念,但是人们还要知道,这是如何表达的,即表达它的语言是什么,它以一个什么样的词表达出来。二者无疑是有区别的。《朝文》的表述本身可以显示出这种区别,但是不知道它是不是也认识到这种区别。相比之下,前一个表达则不是那样清楚。“出现了‘存在’一词”是什么意思?我想,《朝文》的意思大概是:出现了einai这个词,它表示的意思是“存在”。因为它明确说过,希腊文中没有出现“存在”这个词。词与词所表达的观念无疑是不同的。
这个区别看似细小,却是至关重要的。联系普罗泰戈拉命题的中译文,比如“(人)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则可以看出,《朝文》的做法是让“存在”这个词“出现”,而不是仅仅让“存在”这个观念“出现”,而在柏拉图的例子中,比如“风是冷的”,它却让“存在”这个词消失了,而让“是”这个词“出现”。至于例子中的“是”这个词表达的是什么,论题中的“存在”这个词表达的是什么,它们之间是不是相关,是不是对应,因而例子中的“是”是不是可以达到说明该论题中的“存在”,如此等等,似乎是不用考虑的。与《朝文》相反,《王书》认为这样做有问题,应该让“是”这个词不仅“出现”在例子中,而且也“出现”在这个论题中,至于它们所表达的东西,包括观念,只能通过“是”这个词来理解,就是说,通过理解含有“是”这个词的句子来理解它所表达的意思。《王书》这种看法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从前面关于众多外国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这正是他们的具体做法。他们在普罗泰戈拉的命题翻译中采用are或sind这个词,这样,无论他们在理解方面有什么区别,至少他们在表述上不会曲解普罗泰戈拉的意思。我强调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之间的区别,意义绝不仅限于此,其实还有更多的意思。比如,普罗泰戈拉在说这个论题时是什么意思?柏拉图在讲述它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或者,字面上看,普罗泰戈拉和柏拉图使用的是einai及其相应的词,那么他们是想让“是”这个词“出现”,还是想让“存在”这个词“出现”?他们是想让einai这个词“出现”还是想让它所表达的观念“出现”?或者,他们是想让“是”这个词所表达的观念“出现”还是想让“存在”这个词所表达的观念“出现”?这就是我所说并总是强调的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朝文》对存在含义的说明。它的确切表述是“认定eimi在句子中不作系动词‘是’解,而作‘存在’解”。这明确告诉我们,einai有多种含义,一个乃是“是”,另一个是“存在”。那么如何“认定”它们呢?也就是说,如何区别这两种不同含义呢?从《朝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是”的认定方式:根据系动词。也就是说,从语法形式上可以看出它。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朝文》赞同将柏拉图的例子中的einai译为“是”,并且赞同《王书》所说的例子中没有出现“存在”一词⑦。但是从《朝文》的论述似乎看不出如何认定“存在”含义,因为它对这一点什么也没有说。如果说《朝文》也给出了认定“存在”含义的方法的话,那么这只能是:“不作系动词‘是’解”。也就是说,识别einai的“存在”含义要依赖于关于einai的系词认识。这相当于告诉我们,系词乃是我们认识einai一词含义的基础。“是”的理解固然依赖于它,“存在”含义也是依赖于它的。具体地说,作系词时,einai的含义乃是“是”,不作系词时,einai的含义乃是“存在”。这里可以联系上述格思里的论述,他的“存在”含义乃是基于一种“没有谓项使用”的假定。所谓没有谓项使用,不过是与有谓项使用(即S是P)相对照的一种说法,而后者则是关于系词表达方式的一种说明。这同样表明,系词用法和含义,乃是einai一词最主要的含义。由此可见,《朝文》的论述与格思里的论述还是有相同之处的。
但是,他们也有非常明显的不同之处。格思里不谈系词含义,这大概是因为,在他看来系词含义乃是必要而显然的,无须多说什么。因此,尽管他从einai的某一种特殊用法出发来理解它的存在含义,然而在看到卡恩的论述之后,他就会赞同后者的看法,这是因为后者的看法更符合einai的系词含义,因而更符合einai的主要含义。而《朝文》虽然谈到einai有系词含义,却没有把它作为einai的一种必要或者最基本的含义,因此他在讨论中没有把系词作为理解的前提,他只是强调存在含义本身。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不具体地讨论和借鉴他言明参照的那些文献。
我强调einai(being)的系词含义是因为,这是它的一种最基本的含义。所谓系词用法,指的是这个词在日常表达中的用法,一如柏拉图的例子所示。哲学家讨论这个词或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与这个词的具体用法分不开,因此必须考虑它的系词含义。《朝文》所说的不作系词的用法,格思里所说的没有谓项的用法,固然是being这个词的一种用法,然而相对它的通常用法即系词用法而言,只是一种特殊用法。在涉及being一词含义的时候,人们既可以说being含有这些句子所表达的意思,也可以认为这些句子所表达的意思是“存在”。问题是,这种“存在”含义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能不能以此就认为being的主要意思是“存在”?⑧
由于《朝文》没有关于系词含义是einai最基本含义的论述,而只强调它是多义的,因此有必要对它说的“不作系动词”做更进一步探讨。如果《朝文》的意思是指God is,There are atoms这样的情况,那么我可以大体上赞同他的说法,只是如上所述,他的说法不是那样明确,容易造成误解。但是,如果他的论述不是指这样的情况,即不是指如同例子所表达那样的语言中的具体情况,而只是与being相关的其他情况,那么我绝不会赞同他的看法。在谈论being的时候,being成为讨论的对象,常常以名词形式出现,因而字面上看不到它的系词特征,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如果《朝文》所说的“不作系动词”指或包括这样的情况,假如这就是前面引文中《朝文》所说中国人仍需辨别西方人说的“to be、being或sein到底是什么意思”的原因,那么我认为它的看法绝对是错误的。我不知道《朝文》以“存在”来翻译普罗泰戈拉的命题是不是因为认为,这里的einai是“不作系动词‘是’解”,而我认为,普罗泰戈拉的命题乃是一种关于普遍性情况的表述,涵盖了einai一词所能够表达的所有情况,因而要以“是”来理解,并把它翻译为“(乃)是是的事物是的尺度和不是的事物不是的尺度”。就是说,虽然字面上不能明确看到系词用法,但是仍然可以看到这是关于以系词用法所表达的情况的看法。
结合这个问题,最后我想说“一是到底”论是别人的说法。我的说法是,西方哲学家关于being的讨论“一脉相承”。我的理解和认识是,应该以“是”来理解和翻译being,并且把这种理解贯彻始终。而且我这种说法和认识一直基于一个基本前提,这就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因此我从来不在乎经常被质疑的一个问题:把每一个being翻译为“是”乃是不可能的,因而坚持“一是到底”论是不可能的。这里可以以举例的方式大致描述一下我的观点。柏拉图讨论普罗泰戈拉的观点:人是万物的尺度,是是的事物是的尺度,也是不是的事物不是的尺度。亚里士多德提出有一门科学,它研究是本身。笛卡尔说,我思故我是。贝克莱说,是乃是被感知。康德说,“是”不是实在的谓词。奎因说,是乃是变元的值。海德格尔的名著是《是与时》。这就是我说的“一脉相承”和“贯穿始终”。如果《朝文》认为这些语境中的being都不是系动词用法,由此而可以确认它们“作‘存在’解”,那么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字面上看,这些论述中的being确实大都是名词或不定式形式,但是字面上它们有没有系词含义?它们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呢?它们表达的东西与以系词表达的东西是相关还是无关?我认为相关。也许《朝文》因为强调“存在”含义而忽略的这一点。“是”与“存在”这两种理解谁对谁错姑且不论。仅从理解西方哲学的角度说,是我提供的翻译好呢,还是像传统那样把其中的being翻译为“存在”好呢?我认为翻译为“是”好,因为它字面上保留了系词含义,因而保留这个词必要而基本的含义,所以保留了正确理解这个词所表达的东西的空间和可能性。而翻译为“存在”则是错误的,因为它字面上消除了系词含义,因而消除了这个词的必要而基本的含义,所以从字面上就消除了理解它的许多相关意义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究竟谁会陷入《朝文》所说的“语言困境”,大概不说也罢。
①除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外,对所引中译文我一般不是给出自己的译文(个别地方除外),而是给出了修正的中译文,即仅对与being及其相关概念的翻译做出修正。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表明我非常尊重中译者及其工作,二是表明我只是在讨论如何理解西方哲学,而不是在讨论翻译的对错。而且,这样的做法我在书中有明确的注释说明。
②参见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5-86页。
③W.K.C.Guthrie:The Sophis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190.格思里在该书序言中说,他的希腊哲学史第三卷分为两部分。该书复制了其第一部分,做了最小限度的必要的修改。我手边没有《朝文》所说的第三卷。所引部分页码与《朝文》给出的大致相符,估计应该是一样的。
④在正文中,格思里将普罗泰戈拉的命题翻译如下: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that are they are,and of the things that are not that they are not。(W.K.C.Guthrie:The Sophists,p.183.)很明显,即使他假定了exist的含义,他在翻译中也没有使用exist一词。
⑤格思里所引用的是卡恩1966年的一篇论文,而后卡恩在1973年出版了专著《古希腊文中“是”这个动词》(C.H Kahn:The Verb "be" in Ancient Greek,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3),全面深入而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在《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一书中用一章专门介绍了卡恩在这部著作中的基本观点。
⑥从中文是不是别扭,是不是通顺的角度来考虑being的翻译问题,不是个别现象。这十分有碍理解西方哲学。对此我做过深入细致的讨论。参见王路:《翻译与理解》,《哲学分析》2011年第5期。
⑦顺便说一下,《朝文》谈到一处“风是冷”这个例子的希腊文中没有系词,直译应该“风冷”。由此说明例子中系词并非一直出现(第140页)。这里我仅想指出,这里需要考虑系词的其他一些特征。比如,为什么不出现系词的情况可以转换为出现系词的情况?甚至行为动词表达也可以转换为系词表达?假如只做字面考虑,我想问,中译文为什么要加系词呢?加系词会影响理解原文吗?中译文为什么不加“存在”一词呢?加“存在”一词又会不会影响理解原文呢?
⑧这是非常重要而有意义的问题。参见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中关于卡恩观点的介绍和关于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与上帝相关的讨论。
标签:柏拉图论文; 普罗泰戈拉论文; 王晓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观点讨论论文; 读书论文; 王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