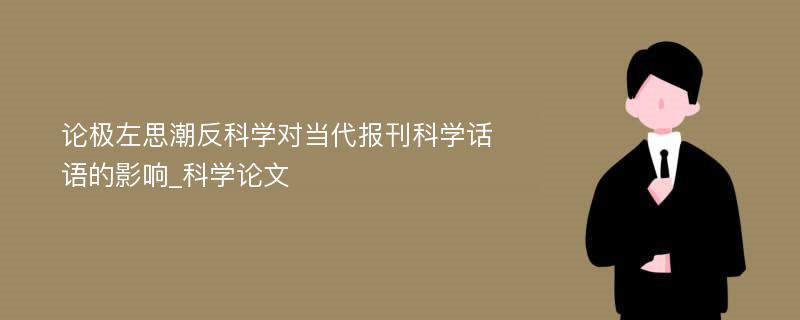
论极左思潮的反科学性对当代报刊科学话语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性论文,思潮论文,报刊论文,话语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传统文化最突出的局限性是科学精神的匮乏,在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中,赛先生(科学)所走的每一步都注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赛先生在中国的对手太多。除了伪科学和封建迷信,赛先生在中国最强大的对手要数极左思潮了。极左思潮从20年代开始就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兴风作浪,它打着最最革命的旗号,以最狂热的面目出现,它给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造成的危害最大。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宁左勿右”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存选择。极左思潮表面看是最革命的,最无私的,但其实它和封建迷信及伪科学都孳生于同样的历史和文化的土壤,有着共同的文化内质。它们都缺乏科学精神,都是愚昧的产物,都虚妄荒诞,都与科学为敌。在1949年以后的现代化建设中,极左思潮的影响或强或弱地一直没有断过,它有着特强的生命力,这恰好证明在中国社会它一直有着孳生的气候和土壤。极左思潮对科学的扼杀表现在许多方面,本文仅从意识形态绝对化、搞假大空、推崇现代迷信及话语风格几个方面予以分析。在当代这个历史时段里,中国报刊最充分地表现了极左思潮与科学较量、厮杀的历史的真相。中国报刊关乎科学的极左话语形成了最完整的谱系,它一直在和科学与真理较劲,它的本质就是反科学、反真理。
一、意识形态绝对化对科学的危害
科学本是没有阶级性的,也不分人种、国别和民族,谁掌握了科学谁就会聪明智慧,谁就会强大。意识形态绝对化,则是把一切人、事都赋予意识形态色彩,这是从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一种怪癖。把新闻、传播、文学、艺术、爱情、婚姻、科学技术、人际关系等等都意识形态化,都赋予阶级的色彩。科学意识形态化后,就有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科学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科学之别。
50年代初中国科学界开展了一场关于生物学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把米丘林说成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生物学家,而把摩尔根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物学家,推崇米丘林的学说、批判摩尔根学说成为报刊言说的一个热点。1950年1月25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科学工作者如何向米丘林学习》的文章,有一段这样的话:“米丘林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辩证唯物主义者。他用自己辛勤的劳作,从无数次失败中找经验;用实际经验,驳斥了唯心的、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是不变的,因而也就没法发展的魏斯曼、莫尔根和孟德尔的反动理论;并用铁的事实把他们打得粉碎。”科学只有百家争鸣才能发展,而这样的言论则极为褊狭,独尊米丘林,称之为“唯一应遵循的道路”,而把魏斯曼、莫尔根和孟德尔的学说称之为“反动理论”,被“打得粉碎”,这样的话语本身就缺乏科学精神,本身就缺乏科学常识,本身就不懂科学发展的规律。1955年11月1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童第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创造性地研究和运用米丘林学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文章,也是这样持论的,文章写道:“在生物学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进行着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斗争。近数十年来在生物科学中形成了这样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唯物主义的米丘林方向,一个是唯心主义的魏斯曼摩尔根方向。”生物学家也持此论,也就偏离了科学家应遵循的求是求真的思想轨道,也就褊狭了视野,暗淡了眼光,阻隔了思路,也就丧失了在世界范畴、在科学王国里去攀登至高峰顶的起码条件。1957年反右斗争中,许多科学家就是因为持有所谓的“唯心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科学观点、被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而被剥夺了科学研究和探索的权力的。1957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迷魂阵里走出来——访生物学家谈家祯先生》的报道,意在提供一个“觉悟”了的科学家的典型,这是极左的报刊话语惯用的伎俩,有意去设置这样的议题,安排这样的反戈一击的典型,来获得更有影响的话语权威。文章有这样的叙述:
在7月18日上海自然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我国有名的摩尔根学派的生物学家谈家祯先生,深有感受地说:“整风初期,我好像进入了迷魂阵似的,自己的某些思想言论不知不觉的和右派分子合了拍子,经过党的启发教育和亲自参与反右派斗争,才觉得已从迷魂阵里走了出来。”
我在政治上虽然对党是完全信任的,但在学术思想上和党有抵触,对党的某些具体政策上,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所以我在鸣放中的有些言论,便和右派分子一拍即合了。右派分子否认党对科学的领导,我对党对科学的领导也有怀疑,我一直很反对在自然科学的头上加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帽子,记得去年在天津讨论教学大纲的会议上,有人硬把摩尔根的学派肯定是唯心的,把米丘林、李森科学派肯定是唯物的,我当时就非常反感,总觉得党在科学的问题上太武断了,(后来在青岛的遗传学会议上纠正了)。因此,我在4月20日市委召开的科学座谈会上,又提出要在学术上展开争鸣,必须摘掉唯心主义的帽子。现在想起来,我讲这话是否认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科学领域中的斗争,实质上也就是否认党对科学的领导。
从这样的报道中,我们可以读到当时科学家境遇的艰难,读到中国科学家的悲哀,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们探讨科学的自由基本上是没有的。他们被权力随意拨弄着,权力大于知识。
批判马寅初等人的人口论也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把马寅初等人作为马尔萨斯人口论在中国的代表进行批判斗争,称之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人口论,给以全盘否定,也是50年代报刊反科学话语的一个典型标本。早在五四时期,《新青年》的先哲们就十分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新青年》第七卷第四期是“人口问题号”。陈独秀、陶孟和、张崧年、顾孟余、马寅初等发表了关于人口问题的论文。马寅初发表的《计算人口的数学》运用“数学的级数”和“几何的级数”去推算北京人口增加的情况,实质上是运用马尔萨斯的计算人口增长的公式作了一个实例的演示。《新青年》先驱们的探讨成为中国这样一个人口问题最突出的国度一种最宝贵的人口理论建树。在50年代中期,以马寅初为代表的学者继承《新青年》先驱的研究思路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又进行了深入研讨。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题为《新人口论》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马寅初以消费和积累的矛盾为中心,论述了新中国的人口问题。他指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太慢,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的比例降低,这样就可以多积累一些资金用于发展重工业和科学研究,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在文章中他指出,新中国的人口在以百分之二的速度增长,他分析了人口的高速增长的原因,并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影响。他认为,我们每年只能在工业中安排100万人就业,其余1200万新增人口只能在农村中找出路,但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且一时无法提高。在文章中,马寅初花了相当的篇幅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论证了他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本质区别。马寅初为代表的包括费孝通、吴景超、陈达等学者、专家关于新中国人口控制的观点不久就受到猛烈的批判。1957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文章,由此揭开对马寅初为代表的学者们关于新中国人口问题意见的批判。文章说:“现在看来很清楚,他们是有意利用人口问题,作为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由头之一,还要进一步把它作为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由头之一。他们不愧是阶级斗争的老手,所以这个问题,提到这样尖锐的阶级斗争高度和政治斗争高度。”文章说,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人和马尔萨斯一样,是一批利用人口问题来麻痹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人。“他们是要利用人口众多这一点来说明:我们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办不到的;好像在沙滩上建设宫殿,白费力气。他们的基本论点是:因为人口多,所以消费很大,所以积累极少,所以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50年代从意识形态角度对马寅初为代表的关于新中国人口控制观点的粗暴批判,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为严重的问题。人口急剧增长,经济发展被拖累,教育跟不上,医疗卫生得不到保障,社会福利系统难以建立,资源消耗大,尤其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未来进程造成沉重的负担。
把科学、教育意识形态化,形成一种治国方略,形成一种全国性的主导的舆论,形成所有报刊传媒的共同话语,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当知识分子全被列入资产阶级范畴而成为“臭老九”的时候,当阶级斗争被认定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甚至唯一动力的时候,当政治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搞科研、学文化、抓业务被认为是“白专道路”而受到干扰批判的时候,当学校和科研机构的领导权都由工人、农民掌握的时候,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之类的话语成为社会的主导话语的时候,把科学、教育意识形态化就走到了极点。对于一个科学、教育十分落后,底子相当薄弱、和先进国家相距甚远的国家来说,这一场折腾无疑是雪上加霜的大灾难。十年“文化大革命”是践踏科学、教育的愚昧的运动,而其基本的表现,其钳制人们思想的权威话语,就是打的“意识形态”的旗号。“口戕口”最致命的最可怕的就是意识形态这张“口”。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每天每日都有这种悲剧发生,报刊话语每天每日就是说的这个理。比如“张铁生事件”,就把张铁生宣传成一个“白卷英雄”,而学习科学知识,进行文化考试都变成了“路线问题”、“修正主义”,这样的导向使全国掀起鄙弃科学知识的高潮,全国所有的报纸都连篇累牍地登载文章,支持张铁生交白卷的行动,都是从阶级、路线的角度立论的。
二、搞假大空对科学的危害
从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假大空的风气在中国就没有完全止息过。在中国的新闻界也没有完全止息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假大空泛滥的极致,它们可以说就是假大空的代名词,象征体,它们是假大空话语营造出来的时代,而这样的时代又时时制造着批发着假大空的话语。“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虽然这股风已不是社会的主流风气,但它的势力和影响依然不可低估。“非典”的报道就是惨痛的教训。陈斌、贾亦凡编写的《2003年十大假新闻》一文对“非典”期间假新闻的报道作了一些归纳综合,特录如下:
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少权威传媒刊出严重失实的报道,如《人民日报》2月15日的报道《广东非典型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大部分病人痊愈出院》。而实际情况却是“2月26日非典型肺炎进入发病高峰,全省发现病例218例,当天增加45例,大大超过此前单日新增病例,2月12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宣布至2003年2月9日,全省报告病例305例,死亡5例;2月28日全省累计发生病例789例……”(《羊城晚报》2003年5月4日)。再如新华社2003年4月4日报道:卫生部部长张文康4月3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局部地区发生的非典型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中国大陆自2003年初发现非典型肺炎以来,截止到3月31日,共报告非典型肺炎1190例,其中北京12例。而事实真相是:截止到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病例1807例,其中,广东1304例,北京339例……这些新闻和事实相差甚远,毫无疑问应列入假新闻范畴,甚至还有望被评为2003年度客里空最假新闻奖。
自上海《新闻记者》举办全国十大假新闻评选活动以来,已历五届,影响越来越大,这个活动本身即是对中国新闻界一个警醒。非典的虚假新闻曾经给我国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损失,即是经济损失就无法估算。假新闻的泛滥归根结底是体制和机制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精神淡薄带来的结果。中国的传媒,尤其是报刊,在某些历史时段已形成了一套非常驾轻就熟的搞假大空的话语体系和运作方式。回过来我们看看“大跃进”时期的报道,仅看新闻标题就足可见这种新闻话语的虚妄空洞荒诞和狂热式的海吹,如:《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福建海星社创花生亩产一万零五百多斤纪录》(《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学理论·用理论·写理论——庄稼汉提笔务虚——新发农业社八十多人写出一百多篇论文》(《人民日报》1958年8月30日);《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争夺战胜利在望——钢产量跳到七百二十多万吨——红十月产钢187万吨以91.7 %的增长速度盖过九月飞速前进》(《人民日报》1958年11月3日); 《承德市区彻底消灭了苍蝇》(《光明日报》1958年8月6日);《地力挖掘不尽,想到就能做到——农业科学家畅谈早稻亩产三万六千多斤的观感》(《光明日报》1958年8月14日);《红专公社一亩晚稻产谷六万六千多斤》(《新湖南报》1958年10月22日),等等。由此一斑可观全豹,那是一个呓语狂言充斥的时代,是一个信口开河的时代,是一个把牛皮吹上天的时代,是一个与科学背道而驰的时代,是一个自毁基业的时代,报刊话语把这个时代的特征充分地展现出来了。我们今天来看这些报刊话语,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们的报刊为什么会荒唐到这步田地呢?从“大跃进”到“非典”,搞假大空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了无以估量的损失,为什么这等风气总是刹不住呢?难道说真话会比说假话造成的损失更大吗?1958年报刊搞假大空新闻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一是费尽心机,特别是重视细节描写和让科学权威现身说法,来证明假新闻中编造的“事实”是确凿无疑的真实存在。这已形成报刊话语的一种套路。下面我们先看《光明日报》(1958年11月19日)的《珞珈山麓成立红孩子科学院》这则新闻:
武汉市珞珈山麓成立了一所“红孩子科学院”,这所科学院是由武大附属共青团中学25个初中一年级的红领巾组成的,设有动物植物两个研究所,在昨天的建院典礼上,他们表示:我们人虽小而志气高,决心在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指导下,大搞学习、生产劳动与科学研究三结合运动,做到人人搞科学,个个放卫星,以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大搞科学研究工作。他们放射出二十斤重的包菜、十斤重的萝卜、一斤半重的冬番茄、十五斤重的白菜等几颗卫星,来迎接1959年元旦,并要在明年五一和国庆,分别放射出两天生三个蛋的母鸡,一胎生十五个兔子的母兔,每蔸2000个直生花生,亩产三万斤小麦,创造耐寒抗旱冬季稻品种,一株结100个棉桃的岱字棉,在芙蓉树上嫁接各种花果等卫星。他们现在正以冲天的干劲,在桃林里,在小麦丰产试验田里,在菜园里进行着深耕密植试验工作。
这是一则“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新闻标本,毫无根据,初中一年级学生能搞出如此堪称人间奇迹的“科研成果”,只要神智清醒的正常人都不会相信的,但记者照说不误。再看《光明日报》的另一则新闻——《昆明除四害成绩很大》(《光明日报》1958年8月6日):
昆明市夏季除四害突击运动,在市委正确领导下,充分发动了群众,获得很大成绩。据7月份初步统计,在半个月时间内,已消灭麻雀五十万六千五百九十三只,老鼠十万八千二百四十九只,蚊蝇三千五百九十一公斤。在郊区并出现了基本四无乡。
为了说明数据的真实性,精确到个位,但蚊蝇以公斤计,却成为令人喷饭的笑话。
“假大空”的传播是中国社会的弊害,是中国人民的公敌,是对科学的亵渎,是对规律的蔑视,建立中国报刊科学、真实的话语言说机制,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最重要的表征之一。
三、现代迷信对科学的危害
现代迷信就是把领袖神化,对领袖的话绝对服从,有如神旨,缺乏任何的独立思考。领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最高指示”。这种现代迷信同样是愚昧的产物,“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两个凡是”还是坚持现代迷信的立场,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才拨乱反正,使党、国家和人民从现代迷信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中国的报刊话语在1957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形成了现代迷信的一套话语体系,特别是形成了一种现代迷信的报刊话语言说机制,极为严密地控制着中国社会的舆论导向,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场。这里我举“消灭麻雀”这样一个小例,就可见出现代迷信对科学的践踏。
1955年冬,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时,听了农民有关麻雀损害庄稼的意见,决定把麻雀同老鼠、苍蝇、蚊子一道作为必须消灭的“四害”,写入纲要中。这样,麻雀成为“法定”的被消灭对象。由于消灭麻雀是领袖和中央的决策,全国兴起灭雀运动,许多科学家明知不妥也缄口沉默,但也有少数科学家出于科学家的良心和责任,挺身而出陈述麻雀不是害鸟、反对消灭麻雀的意见。最典型的是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朱洗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鸟类科学家郑作新。在1956年秋在青岛召开的由中国动物学会召开的麻雀问题讨论会上,朱洗和郑作新都坦陈自己的意见,为麻雀鸣冤。国际舆论和国际友人对我国的灭雀运动也持非议,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她写了长篇报道《麻雀即将灭亡》发往美国的《纽约人》杂志。她描述了她亲眼目睹的北京数百万人民围歼麻雀的全过程,表达了她对北京市锣鼓喧天,鞭炮轰鸣,房上树上真人齐声呐喊、假人随风摇摆、撒开天罗地网围歼麻雀的情景表示极度的厌恶,她说灭雀战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是愚蠢的,这是科学的死亡。但国内科学家和国际的舆论没有能制止这场灾难的发生,“麻雀问题”被赋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所有提出异议的科学家都受到政治迫害。朱洗虽然1962年因癌症去世,但“文化大革命”中被认为胆敢把伟大领袖毛泽东号令灭雀与封建帝王腓特烈大帝号令灭雀相类比,而受到掘坟、砸碑、曝尸骨的惩罚,直到1978年才重新安葬;郑作新的罪名是为麻雀评功摆好,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最高指示”,而挨过无数次批斗,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才平反昭雪。在现代迷信笼罩中国的日子里,为小小的麻雀说话,说点不同的意见,都要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何况别的事情?1958年,全国人民参与的灭雀运动成为大跃进极左运动的一个小小的侧面。报刊话语一边倒,精心构制话语源,构成似乎一律的舆论场。2月13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除四害是前无古人的壮举,要争取在十年内甚至更短的时间内,除尽“四害”,以代表党和人民的声音。周建人在“五四”时期就是在《新青年》撰写科学论文的科学家,1957年1月18 日他在《北京日报》发表《麻雀显然是害鸟》一文,以代表科学家的声音。他说“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他十分尖锐地批评那些反对消灭麻雀的人是“自然界的顺民”与“均衡论”者。他说:“社会已经改变了,但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仍然会残留着。过去时代不少人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顺民,不敢有改造自然的想头,当然也不敢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主人。”科学家也在科学的立场上位移,放弃了百家争鸣的立场,而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给人扣帽子,打棍子。袁水拍在40年代是写政治讽刺诗的著名诗人,《马凡陀的山歌》是其代表作,这时也发表作品,以代表文学家的声音。他在《人民日报》1958年4月20 日发了一首题为《一定要它灭亡!》的诗歌,现录如下:
满城旗帜迎风扬
人民对天辟战场,
家家户户齐出动,
院院房房布哨岗,
敲锣打鼓放火枪,
失魂的麻雀无处藏!
人民齐心除四害,
不许鼠雀抢我粮!
人民齐心除四害,
不许疫病损健康,
管它是人是鬼是虫是鸟,
谋害社会主义的,
一定要它灭亡!
报刊上关于各地灭雀的报道更是数不胜数,形成全民运动、人民战争的舆论态势。《人民日报》1958年4月20 日刊载一篇题为《人民首都不容麻雀生存——三百万人总动员第一天歼灭八万三》的报道,极具典型性,报道写道:
从19日清晨五时开始,首都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全市三百万人民经过整日的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十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八万三千二百四十九只。
19日清晨四时左右,首都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开始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八百三十多个投药区撒上了毒饵。二百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五时正,当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一声令下,全市八千七百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鸣,彩旗摇动,房上、树上、街上、院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睛监视着天空。假人、草人随风摇摆,也来助威。不论白发老人或几岁小孩,不论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全市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麻雀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被轰赶的麻雀在天罗地网中到处乱飞,找不着栖息之所。一些疲于奔命的麻雀被轰入施放毒饵的诱捕区和火枪歼灭区。有的吃了毒米中毒丧命;有的在火枪声里中弹死亡……
这则新闻带着战争年代的报刊话语特色,却是用来描绘灭雀的,难怪韩素音说这是科学的死亡。可怜的麻雀遭到如此残酷无情的剿杀!这是闹剧,是滑稽剧,更是悲剧!是愚昧导致的悲剧,是现代迷信导致的悲剧,是科学不幸的悲剧!再伟大的人也难免犯错误,一旦被神化,他的错误就会演成最可怕的悲剧!
到了“文化大革命”,现代迷信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科学更无从言说。在现代迷信的笼罩下,报刊话语更僵化、苍白和空洞。
四、极左话语风格对科学的危害
所谓话语风格,是指语言由于使用中受不同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而形成的一系列言说特点的综合表现。极左的报刊话语风格即是极左思潮泛滥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报刊话语风格。这种报刊话语成为极左思潮的语码载体,它在语码表层及语码的组合结构、逻辑章法、句式辞式等方面都自成一体,与科学精神、科学风范相悖逆。
首先是假大空的话语风格。“放卫星”成为吹牛皮的同义词,成为一种吹牛撒谎的超级竞赛,这在前面的论述中已可见证。1958年报刊所报道的粮食亩产量和全国钢产量急剧攀升就可见到这种“放卫星”的报刊话语搞假大空竞赛的荒诞情状。1958年8月13 日《人民日报》报道“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仅过一周,到8月22 日就报道安徽省繁昌县东方红三社《一亩中稻四万三千斤——东方红、红遍天》的新闻,而《光明日报》于11月7日则刊登湖北省应城县春光人民公社晚稻“亩产八万三千多斤”的报道。“天下第一田”已是牛皮吹上天,但后面的牛皮越吹越大,“卫星”越放越高,中稻比早稻高,晚稻比中稻高,而且是成番成倍地增长。钢产量的报道也是如此,1958年11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钢产量跳到七百二十多万吨——红十月产钢187万吨以91.7 %的增长速度盖过九月飞速前进》,11月15日报道《全国钢产量突破八百万吨——本月上旬产钢七十八万九千吨,比十月上旬增长151.6%》,12月5日报道《决战意义的一月——十一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钢产量已达969万吨》,12月22日报道《一年之间钢产加番,在世界钢铁史上写下辉煌的一章——1070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千万英雄儿女斗志昂扬奔向明年生产1800万吨钢的新目标》,也是成番成倍地增长。中央报刊如此,地方报刊也不示弱。如《新湖南报》1958年7月28日报道《平江仁胜社传出第一个丰收喜报——两分试验田收干谷640斤》,8月15日报道《醴陵鳌仙社出现早稻王——试验田亩产15665斤》,10月22日报道《红专公社一亩晚稻产谷六万六千多斤》,增长速度更离奇,加番加倍更多更快。在这些报道中,用词尽量渲染狂热,诸如“天下第一田”,“东方红,红遍天”,“跳到”,“盖过”,“飞速”,“早稻王”等等,而自己的报道不几天就把自己所封的那些极致的称誉推翻了。这真像一个感冒高烧的病人畸形病态的热症呓语,展现的是一幅荒唐无比的人间漫画。
其次是霸道尖刻武断。没有讨论的余地,不给人讲道理的权力,戴帽子,打棍子,没有对话,只有斗争,以势压人,气势汹汹,缺乏对人的起码的尊重。随意撷取“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几张《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标题就可见这一特点:1957年8月12日第3版《扫清工程技术界的牛鬼蛇神》、《丘致中甘愿为章罗联盟效劳——森工部职工揭开他的假面具》、《于振武毛遂自荐充当文汇报在新疆的放火人》、《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1957年8月14日第2版《钱孙卿的引魂幡被烧掉了》、《音乐家们投入了反右派斗争——把刘雪庵的阴险面目层层剥开》、《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反对马克思主义——右派分子荣孟源是史学界的骗子》、《到处纵火妄想倒算五反账——郑立斋丑恶面目被揭穿》;1957年8月24日第3版《何迟勾结吕班钟惦 企图独霸曲艺界——天津文艺界粉碎他们的反党阴谋》、《金宝善干些什么勾当?》、《洛滨太不自量——妄想取消马克思主义》、《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的两员干将》;1967年8月28日第3版《大比武是罗瑞卿篡军反党阴谋的大暴露》、《武汉空军某部指战员高举革命批判大旗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火——大树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绝对权威——狠批彭德怀罗瑞卿反党篡军的滔天罪行》;1967年10月15日第3版《打倒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彭真》;等等。在这些文章标题中, 充满漫骂和污辱,看不到任何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思辨,就如随便将人戴高帽子游街示众一样,就像随意将人捆绑批斗殴打往脸上吐唾沫一样,诸如“扫清”、“牛鬼蛇神”、“假面具”、“放火人”、“狐狸尾巴”、“勾结”、“粉碎”、“反党阴谋”、“勾当”、“妄想”、“阴险面目”、“层层剥开”、“骗子”、“到处纵火”、“妄想倒算”、“丑恶面目”、“篡军反党阴谋”、“反党篡军的滔天罪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等等,这都是读解那个时代的“关键词”,是读解那个时代报刊话语的“关键词”。这是一种封建文化的延续,就像封建皇帝要把一个臣民诛九族、凌迟、鞭尸一样,也是用这种类型的语言去宣判他,去漫骂他,以证明对他采用极刑是应当的,是死有余辜的。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上绵延不绝的一种话语,多少忠臣义士站在死囚笼里被万民唾骂当众凌迟悬首示众时的一种情境再现。
再次是故步自封,极端化,表现革命有加,实则愚昧之极。如196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第5版登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世界革命进程中的大跃进》、 《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世界人民是伟大的教导》、《中国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使帝修反发抖》等文章就体现了这种特色,夜郎自大,坐井观天。世界科技在飞速发展,等到中国百般折腾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国家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世界上已经落后得很远很远。一场历史的闹剧只腾起了堆积如山的泡沫,泡沫飞散,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现实。
第四,是这种话语的组合结构、逻辑章法也是僵化死板、千篇一律,没有任何创造的灵性和活力。最显著的一个表现是篇篇文章不能不歌颂领袖和他制定的路线,篇篇文章不能不引用他的语录和指示,篇篇文章不能不由强调领袖指引开篇,不能不强调领袖的伟大结篇,山呼万岁成为最不可缺的报刊话语,篇篇文章、张张报纸都离不开“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样一个话语基调。在这种话语显现其顽强生命力的时候,民族的创造力就会受到严重制约,人民的责任感就受到严重打压。这种封建话语的变体——极左的报刊话语体式,是整个社会的体制和机制所制约所需要的一种语符表达,有如一架什么样的钢琴就会奏出什么样的琴音一样。它归根结底是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当这种话语充塞在每个社会单元的时候,天才也会变成蠢才、庸才,而最聪明的人也许就是最愚昧的人,因此,这种话语是这种社会机体的护身符。它僵化而空荡,易于操作,容易炮制,然而它有如枷锁般沉重,它阉割的是思想的火花,创造的自由。
赛先生在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中虽然步履艰难,布满坎坷,但道路是越走越宽广。没有赛先生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赛先生是在荆棘榛莽中为中华民族开辟一条生存之道、自新之道、发展之道的。我们既要发挥赛先生作为“第一生产力”的角色的作用,又要发挥其作为思想启蒙老师的作用,既要让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成为历史陈迹、也要让与这种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同存的思想文化理念成为历史陈迹。我们只有真正地尊重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才能最和谐地应合历史运行的节奏,把民族前进中的每一步都踏在最合适的地方。
收稿日期:2006—10—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化历史进程与百年中国传播”(03BXW010)。
标签:科学论文; 迷信活动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反社会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科学性论文; 光明日报论文; 新青年论文; 马寅初论文; 人民日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