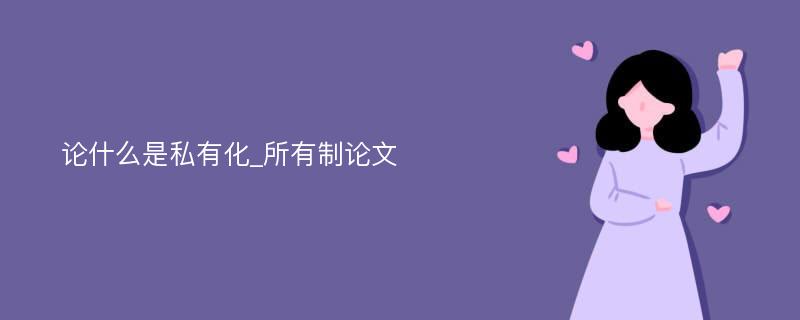
关于什么是私有化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国内理论界对私有化这个概念基本上没有什么专门讨论。经济学家在谈到所有制改革时虽普遍不赞成私有化,但却各有各的理解:有的从公有企业转制的数量上看,认为一部分企业转归私有不是私有化,只有全部公有企业变私有才算私有化;有的从财产所有权的法律名义上看,认为公有企业被私人实际占有不是私有化,只要国家或集体在名义上还是“终极所有者”,企业的公有性质就不会改变;有的从所有权主体的组成上看,认为公有企业转归一个人所有是私有化,转归两个以上个人所有就不是私有化;有的从转归私人所有的方式上看,认为“白给”(公有财产无偿分给个人)是私有化,“拿钱买”(向私人出售公有财产)不是私有化;有的从购买资金的来源上看,认为用剥削收入买公有财产是私有化,劳动者用工资收入买不是私有化;有的从私有者的数量上看,认为少数人成为私有者(公有财产出售给少数人)是私有化,多数人成为私有者(由大众买公有财产)则是财产社会化而不是私有化;有的从财产是否转交给本企业劳动者上看,认为以卖或分的形式转给本企业劳动者不是私有化,转给他人是私有化;有的从国家是否控股(何谓“控股”则又多有说法)上看,认为国家控股不是私有化,反之则是或可能是私有化;有的从企业的组织形式上看,认为公有企业转为个人独资企业是私有化,转为其他如合伙公司、股份公司等则不是私有化;有的从企业的社会功能上看,认为私有企业只要为社会创造产品、扩大就业、提供税收,就“应该算作实际公有制才对”,由此推论,公有企业转为这样的“私有公用”企业也不能算作私有化,等等,等等。罗列起来,国内学者的加上引用外国人的私有化定义,恐怕不下数十种。这样一来,各种各样的私有化定义互相矛盾,以至甲说是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改革主张,在乙看来很有可能属于私有化的内容。
人们对私有化涵义的不同理解和界定,原因可能比较复杂甚至微妙,不少私有化定义往往源于给出者的主观需要,而未能遵循大家比较认同的定义原则。事实上,迄今为止,国内理论界的确尚未形成这样的原则。基于此,本文讨论什么是私有化,并非追求给出一个能让大家接受的私有化定义,而是着重讨论怎样给私有化下定义的方法论原则问题,尤其是怎样联系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殊性质给私有化下定义的方法论原则问题。在笔者看来,西方学者虽然对什么是私有化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但他们讲的主要是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不是社会主义公有企业的私有化,二者在形式上有共同点,性质上却大不相同。因此,西方学者的私有化定义对我们讨论社会主义国家的私有化是不够用的。此外,私有化是一个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理解的概念,很难用一个定义涵盖之。本文的讨论,旨在抛砖引玉,许多问题只是提了出来,即便是多说了几句的一些问题,也还有待深入甚至修正。
二、个别企业私有化与社会经济制度私有化
在讨论什么是私有化时,有必要把个别企业私有化与社会经济制度意义上的私有化区别开来。若不作这样的区分,各自的口径、标准不一样,难免生出多余的争论。例如,在政府将某个国有企业出售或让渡给某个人的场合,要作出是否搞了私有化的判断,恐怕就离不开这里所说的区分:是从个别企业角度讲私有化呢,还是从社会经济制度的角度讲私有化?
私有化现象同“财产”一样古老,现代私有化则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事。(注:虽然我们在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1840年)的中译本中能够找到“私有化”一词(商务印馆,1963年,第127页), 但据西方学者说,“‘私有化’(Privatize)这个词最早是在1983 年才出现于《韦氏新大学辞典》中。”见斯蒂夫·H ·汉克主编:《私有化与发展》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69页。)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在大约十年时间里,不仅波及发展中国家,而且在80年代末终于在前社会主义国家拉开帷幕。不难发现,资本主义国家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私有化,尽管在理论基础、具体做法上有许多共同点,但从私有化的目标、任务和性质上看,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私有化类型:前者的特点是个别企业私有化,后者的特点是社会经济制度私有化。
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化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合乎逻辑的政策,矛头所向是国家垄断,是降低国家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具体国家而言,不论私有化程度有多高,都不会改变社会经济制度。极而言之,假使这个国家的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了,或者原来完全由国有企业组成的某个部门百分之百地私有化了,相对于整个社会经济制度而言,也还是个别企业的私有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制度,国家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形式,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原本就不存在社会经济制度私有化的问题。
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化不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私有化是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取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在个别企业私有化的基础上实现“制度转型”、“制度变迁”,即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这样的私有化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私有化或资本主义化。在这里,个别企业私有化不是作为独立的私有化类型存在的,而是纳入了社会经济制度私有化的总过程并且是后者的基础,或者说,二者之间存在量变与质变的关系。不过,社会经济制度的私有化并不需要全部公有企业私有化。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一定规模的国有经济的存在,是资产阶级国家缓和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占有方式这一基本矛盾的重要手段,是使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得以运转的重要条件,是资本主义私有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把社会经济制度私有化理解为国有(公有)企业百分之百地私有化,既不符合现代私有制的要求,也没有这样的实例。对于前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保留比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稍大比重的国有经济,可能还是这些国家的一个特点。这并不妨碍甚至有利于这些国家转入资本主义轨道,也不妨碍这些未经私有化改造的国有企业成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一种形式。
还需指出,个别企业私有化之量变与社会经济制度私有化之质变并不是完全同一的过程,不是说,个别企业私有化达到一定规模之后,社会经济制度的私有化就完成了。这是因为,社会经济制度的私有化不是个别企业私有化在数量上的简单堆积,它具有更丰富而深刻的社会经济内涵。个别企业的私有化重在财产的分配与再分配,以及由此而来的企业内部管理体制的变化;社会经济制度的私有化则要在此基础上为私有化企业提供一套“活法”,即建立起与资本主义所有制企业运行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体制,使私有产权得以在经济上实现。这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私有化的又一个具体的差别。在资本主义国家,与私有企业相适应的市场体制原已是准备好了的,不需要在个别企业私有化之外再做什么。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原先的经济运行体制是按公有经济的要求设置的(至少主观望是如此),因而仅仅有个别企业私有化,即使数量再多,也还不能做到“事实上的私有化”(注:列宁有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的提法,意指在苏维埃政权下,仅仅有生产资料国有化即形式上的社会化是不够的,还要加强管理,例如普遍的计算和监督等等。见《列宁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495页。)。创造使资本主义所有制能够再生产的一切条件,全面建立与私有化企业运行相适应的市场体制,这是社会经济制度私有化的重要任务。可见,社会经济制度私有化是比个别企业私有化任务更重、时间更长的过程。
西方学者没有社会经济制度私有化的明确概念,他们关于私有化的定义都是从个别企业私有化的角度给出的,因而对于分析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私有化是不够用的。但是,西方学者提供了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应的市场经济理论、经济运行理论,因而有助于人们深化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私有化的认识。例如俄罗斯学者根据本国的私有化实践就明确分析了这个问题。在盖达尔领导的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研究所担任董事的拉狄金区分了私有化的“技术性定义”与“制度性定义”,指出私有化不仅是包括在技术性定义中的向私人(自然人与非国家法人)出售财产等界定财产权利的过程,而且是包括在制度性定义中的建立新的经济机制、法律机制以及体制结构的过程,和国家逐渐自行解除其在市场经济中非固有的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职能的过程。他认为,既然普遍承认所有制是任何经济制度的基础,因而在俄过渡经济中的私有化就具有制度性质;并且,只有在新经济制度所有要素都已成熟的状态下,私有产权才能在经济上充分实现。(注:见A·拉狄金:《过渡经济中的私有化理论》, 《经济问题》(俄)1995年第12期。)应当说,拉狄金从社会经济制度转变、私有产权的全面实现这个高度拓宽对私有化的认识和理解,强调事实上的私有化,这在方法论上是正确的,比起单纯从个别企业角度、财产分配与再分配角度认识私有化前进了一大步。
上述关于个别企业私有化与社会经济制度私有化的区分,显然有助于我们具体把握和正确判断私有化。就以本节伊始的例子言,在社会主义国家,当政府向私人出售国有企业时,无论从西方学者的私有化定义看,还是按照人们对私有化的一般理解,这无疑属于私有化举措。不过,这样的私有化判断只是从个别企业私有化的角度作出的,如果从社会经济制度上看,倒不一定是私有化,至少若干个案不构成社会经济制度私有化。以往由于对私有化不作这样的区分,只是笼统地作出是否私有化的判断,这就难免引起争论。尤其是,若对这种争论不作出正确的理论分析,还会生出许多不良后果来。例如,由于“私有化”一词在社会主义国家确有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涵义,因此,当把出售国有企业的个别举措笼统说成私有化时,就有可能束缚实事求是处理某些国有企业问题的手脚;相反,如果把出售国有企业一概认定不是私有化,又有可能无所顾忌地导致真正的社会经济制度私有化。承认出售国企属于个别企业私有化并与社会经济制度私有化有别,既有利于改革,又不导致理论上的混乱。
由此可见,对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搞私有化的改革也应作出新的解释。我们应当注意和防止的是社会经济制度私有化,对于个别企业私有化,则不应笼统地、绝对地加以反对。个别企业私有化的实例早已存在,在理论上没有必要把实践证明确实需要对个别企业进行的私有化说成不是私有化,如同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没有必要把非公有企业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一样。当然,究竟什么样的“实践”才能证明某个企业确需私有化,是要认真分析论证的,因为不是任何一种实践都是合理的。这是另一个话题,本文存而不论。至于防止社会经济制度私有化,在现阶段,主要体现在正确贯彻“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这个重要原则上面。究竟什么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对此,本文将在第四节有所讨论。
三、从所有权上看的私有化和从所有制上看的私有化
从所有权上看的私有化是从财产的法律关系上考察私有化,从所有制上看的私有化则是从财产运用过程中的经济关系上考察私有化。这一区分对于讨论什么是私有化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在国有企业由个人租赁的场合,要作出企业是否发生私有化变化的判断,就不能不涉及到这里所说的区分:是从企业财产的法律所有权上看呢,还是从企业实际的经济关系性质上看?
所有权与所有制在西文中原本是同一个词。在马克思之前,一般学者只是从法律关系上谈论所有权,指的是财产客体归谁占有、归谁使用、由谁受益、由谁处分等这样的权利关系。由于这样的权利是法律规定和承认的,是由人的意志调节的,因而从法律关系上看,所有权是人的意志关系。马克思的革命在于,他不是一般地从法律关系上谈论所有权,而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着力揭示所有权的经济基础,把对所有权的认识从意志关系领域转移到现实经济关系领域,指出:“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2年版,第142页。)这样,当马克思从现实经济关系上回答什么是财产或什么是所有权时,讲的已经不是法律上的所有权,而是后来人们所说的经济上的所有制。
所有制是所有权的经济基础,所有权则是所有制的法律表现。从这个关系上看,只有把握所有制的性质,才能说清楚所有权的性质。马克思说:“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注:同上书,第1卷,第144页。)资本家的所有权,或者地主的所有权,都是靠特定的生产关系支撑的,资本家和地主都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人格化。因此,离开了对生产关系的考察,单纯从法律关系上谈论所有权,能够说清楚的只是谁为财产的所有权主体,谁掌握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之类,至于这个“谁”到底是资本家还是地主,他的所有权是什么性质的(地主的还是资本家的所有权),就无法说得清楚。换句话说,不考察生产关系,无以区别地主或资本家,不知道哪是地主的所有权,哪是资本家的所有权,只知道张三、李四的所有权。这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分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所有权。
由此可见,要改变所有权的性质,必须改变支撑这种所有权的经济关系,即改变所有制(这里讲的是逻辑关系,并非实际生活中的先后顺序)。但是,由于所有权在法律关系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因而在一些情况下,实际经济关系变了,实际所有权性质变了,而财产的法律所有权名义却有可能不变。例如,在农业资本家租种地主土地的场合,土地是“地主”的,但土地的经营是按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在这样的资本主义农场,生产关系变了,实际确立的是资本家的所有权(资本家实际占有和经营土地的权利,以及对生产过程和雇佣劳动的支配权、对劳动产品和剩余价值的占有权等),但并不排斥或妨碍土地的“地主”所有权,只不过这个“地主”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地主,而是曾经作为地主的张三或李四罢了。
尽管在理论上所有权与所有制存在上述辩证统一关系,但一般来说,从法律上界定所有权仍在于确认财产的所有权主体,“谁”对特定财产行使所有权及其权能,而不是界定所有权性质。确认所有权性质必须联系生产关系,这已不是法律问题,不是法学的任务了。因此,从所有权上看私有化与从所有制上看私有化是有差别的。
从所有权上看的私有化指的是财产所有权主体由国家向私人的转变(为行文方便,这里暂不谈社会主义国家劳动集体所有权的私有化)。西方学者关于私有化的定义主要是从这个角度给出的,(注:本文不拟列举西方学者关于私有化的定义,这里只是指出,西方学者除了从所有权及其权能角度给私有化下定义外,还把国家放松对私有部门的限制、放松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也看作私有化,对于后者,本文不作讨论。)其中包括国家所有权完全私有化,和国家所有权名义不变条件下的私有化。
国家所有权完全私有化的形式在西方国家主要表现为出售国有财产(包括出售股份),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还把无偿分配国有财产作为重要形式。在国外学者看来,出售与“白给”一样,都是国家完全放弃所有权的私有化方式。他们没有这样的说法,例如认为财产所有权分实物形态的所有权和价值形态的所有权,由于国家出售财产(如企业)收回了货币,因而仍然持有价值形态所有权,不是私有化。很明显,这样的说法不过是偷梁换柱的戏法。对货币的所有权不是对企业的所有权。白送也好,出售也罢,国家都失去了对企业的所有权,就像卖女儿送女儿都是失去女儿一样。在这里,稍有意义的只是国家在转让财产所有权时怎样更有利一些,也许出售可以使国家不吃亏或少吃亏,而国家失去企业则是铁的事实。如上所述,所有权意义上的私有化涉及的是所有权主体的转变,与有无等价交换毫无关系。有些人以为,在出售国有企业的场合,一方(国家)得到了企业的价值形态的所有权,另一方(私人)得到了企业的实物形态的所有权,似乎“半斤八两”。这完全是误解。姑且不论所有权的二重化有无道理,即便如此,由于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私人既然得到了企业,也就同时占有企业的价值。私人用货币与国有企业相交换,失去的是货币,得到的是企业,连同它的所谓“实物形态的所有权”和“价值形态的所有权”,而国家则不再拥有企业所有权的任何一个原子。
西方学者把租赁经营等看作是“管理私有化”,(注:埃利奥特·伯格:《出售国有企业资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见前引《私有化与发展》,第26页。)这是国家保留所有权名义下的私有化形式。严格说来,私人租赁经营也是所有权意义上的私有化。这里涉及到对所有权概念的理解问题。完整的、充分的所有权是所有权的各项具体权能的总和。通常把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这四种权利看作是所有权的权能。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和发展,所有权关系也在发展,表现之一就是所有权权能的分解,所以有的西方法学家甚至归纳出十余种权能。(注:参见苏联学者B.A.基科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权学说发展的主要趋势》.载捷克斯洛伐克法学家扬·拉萨尔:《资产阶级法学理论中的所有权》,俄译本,莫斯科法律书籍出版社,1985年,第19页。)所有权的各项权能都是所有权的具体实现形式,所有权的每一项具体权能的转移,都或多或少构成对所有者权利的限制。所有权权能转移得越多,所有者的权利就越少;如果所有权权能全部转移出去了,所有者就只留下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所有权名义了。因此,从所有权角度考察的私有化,不仅指完整的所有权由国家转移到私人手里,也指基本的或大部分所有权权能由国家向私人转移。把财产的使用权、经营权转给私人,如租赁等,在西方学者看来也是私有化,或者说是私有化的一种形式。当然,比起通过出售进行的私有化,二者还是有差别的。
西方学者从所有权角度给出的私有化定义究竟如何评价,这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这里要指出的是,虽然从所有权角度考察私有化是重要的,但是由于西方学者没有所有制概念,西方国家的私有化也不存在生产关系性质上的变化(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都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因而单纯的所有权私有化的观点对于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的私有化是不够用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社会主义国家的私有化,从根本上说,是所有制的私有化,即从经济关系上看的私有化。在顺序上,有的国家可能先有所有权的私有化,随之发生经济关系的私有化(例如像俄罗斯这样的政局急剧变化的国家);有的国家则可能先逐步从经济关系上演变,最后完成所有权的私有化。但在逻辑上,经济关系的私有化是根本,没有经济关系的资本主义化,便没有资本主义所有权的再生产。
究竟什么是从所有制角度看的私有化呢?这里涉及到如何把握所有制的内涵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内涵的问题。
所有制往往被混同于所有权。突出表现是把所有制解释为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归谁使用一类的权利关系。结果是,尽管人们承认所有制不是所有权,但在实际谈论什么是所有制时,又总是把所有权的定义当成了所有制的定义。
所有制不是人们之间关于物的权利关系,而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与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关系。马克思说:“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4页。)马克思的这段话为我们把握所有制的内涵提供了一把钥匙。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差别,在于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即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的特殊性。生产资料的背后是人,即它的所有者。因此,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的特殊性,反映着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的特殊的经济关系。历史上,剥削阶级所有制的共同点在于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分离,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不是劳动者,劳动者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为了使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结合起来,于是有了劳动者直接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财产从而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即奴隶主的所有制;有了通过劳动者对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依附关系而使二者相结合的方式,即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有了使劳动者变成自由劳动者,从而通过劳动力的买和卖(雇佣劳动)使生产的物的要素与人的要素相结合的方式,即资本家的所有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具体体现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诸领域,构成所有制在再生产诸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例如,貌似劳动的价格实为劳动力价格的工资,就是雇佣劳动制度这种使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殊方式即资本主义所有制在分配领域的表现形式之一。由此可见,不论哪种社会经济形态中的所有制,也不论所有制在再生产诸领域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何,我们都可以把所有制高度概括为生产资料所有者与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诚然,分析这种关系不能不涉及到生产资料所有权(完整意义上的所有权),但所有权不是经济意义上的所有制。
抽象地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也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与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与剥削阶级所有制不同的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不再是对立的两极,劳动者同时就是所有者,或者反过来,所有者也是劳动者。劳动者身份与所有者身份合二为一,这是非剥削阶级所有制的共同特点。历史上小生产的所有制就是如此。这是劳动者自己占有生产资料,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因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所有制,是劳动者自主地占有生产过程从而占有自己劳动产品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也是如此,因此,马克思才把消灭资本主义以后建立劳动者的公有制类比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但是, 社会主义制度下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不是小生产那样的“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而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注:同上书,第48卷,第21页。)。劳动者已经联合起来成为集体的所有者和集体的劳动者,生产是使用集体劳动并由集体劳动者自主管理的过程,生产成果是劳动集体的成果并在他们中间按劳动贡献大小分配个人消费品,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关系的基本特点,从而与小生产者的所有制形成差别。
因此,从社会主义公有制角度来看的私有化,是使生产资料所有者与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重新分离的过程,是使劳动者再转化为雇佣劳动者的过程,是劳动与其产品相异化的过程,因而是重新确立资本主义原则即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由社会主义公有制退为小生产是存在的,但总体而言,私有化是资本主义化,小生产则是资本主义体制内的因素。
上述关于所有权私有化与所有制私有化的区分,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显然也是有重要方法论意义的。理论界往往把私有化仅仅归结为所有权的私有化,这样就掩盖了所有权名义不变下发生的所有制在事实上的私有化。租赁经营便是一例。在私人租赁国有企业的情况下,尽管企业财产名义上是国家的,但企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却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由腐败分子把持的国有企业,社会主义公有制名存实亡,这也是连一般老百姓都早已认识到了的。此外,国内理论界更有把所有权私有化进一步庸俗化的流行观点。其理论逻辑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坚持生产资料的公有权,坚持生产资料公有权就是坚持生产资料的价值形态的公有权,坚持生产资料价值形态的公有权就是坚持其等价形态——货币的公有权。这样,当国有企业出售为等价货币以后,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算坚持住了。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国家的口袋里装着的钱上面了。于是,只有“白给”才是私有化。更有甚者,连“白给”也不是私有化,因为只要不是“白给”一个人,而是“白给”好多人,那就已经是“公众所有”了,而“公众所有”据说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形式,是社会所有制形式。于是,私有化也就不存在了。
上述关于私有化的庸俗化观点,理论上的根源在于离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特点来认识公有制,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归结为生产资料共有权。这样一来,生产资料所有者与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就被归结为单纯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于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财产共有关系就被误认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至于劳动者是否也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则从社会主义公有制视野中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论者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类公司都混同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原因。在这类公司中,公司资本是投资者的共有资本,不是劳动者的共有资本。若劳动者也参与投资,理论上也可以成为公司的共有者,但他不是以劳动者的身份成为公司所有者的,而是以投资者的身份成为所有者的,因而与其他投资者无异,但与不投资的其他劳动者有别(这里不谈劳动者投资的数量,因而也不谈劳动者持有的少得可怜的股份是否能使他摆脱雇佣劳动者的地位而上升为公司的实际所有者)。显然,这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劳动者同时就是所有者、以其劳动者身份成为所有者形成根本差别,更不要说公司中每个投资者保留着对其相应投资份额(股份)的私的权利了。
从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关系角度认识私有化还需要进一步具体化,这就不能不涉及到企业生产与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不能不涉及到劳动者在企业中地位的变化,不能不涉及到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劳动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变化,等等。这些问题的讨论已超出本文范围,并且也有待于深入研究。
四、补论“以公有制为主体”
本文第二节最后指出,在中国防止社会经济制度私有化,现阶段主要体现在贯彻“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这个重要原则上面。对于这个原则,有必要进一步深化认识。
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指以公有企业数目为主,这一点人们没有分歧。要不要使公有经济的产出(GDP)在社会总产出中占优势(例如50 %以上)?这一点看来是有分歧的。早几年人们还讲公有经济的产出比重点优势,但近几年不再提这个了,因为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的对比关系已经并且正在发生变化。若干年来,公有经济的产出比重逐渐缩小并有加快之势,在一些地区和部门,非公有经济的产出已大于公有经济的产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意识到公有经济产出的优势恐怕难以坚持得住,于是就把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转移到了资产数量上,即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尽管公有经济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也在下降,但毕竟比产出比重下降要慢得多,并且目前公有资产比非公有资产在数量上大很多,似乎在这一条上足以坚持公有经济的优势地位。仔细想来,不提公有经济产出占优势,只提资产占优势,这里头还有些道理难以说得清楚。第一,产出是反映经济力量的综合指标,倘若公有经济生产的GDP比非公有经济少,一般来说意味着前者的实力比后者弱, 因而,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似不符合。第二,在公有经济资产数量占优势的条件下,若其产出不占优势,即资产优势不能转化为产出优势,这样的资产优势有什么意义呢?除了说明公有经济效率低下还能说明什么呢?若此,公有经济必须在竞争中让位于非公有经济,其资产优势也会变成劣势。第三,所谓公有资产占优势,是经营性资产占优势,还是包括非经营性资产乃至包括诸如土地、森林、矿藏、江河等国有自然资源在内的国有财产占优势?若是后者,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似可“固若金汤”,但这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之特点,至少有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
在笔者看来,讲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不涉及到资产数量、产出数量,但主要不是若干经济指标的数量关系。贯彻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核心在于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方式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统治地位。这一点做到了,资产、产出等指标的数量优势自不在话下,否则,这些指标的优势地位靠“坚持”是坚持不住的。
按照本文第二节提供的方法论原则,确立公有制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实质上就是从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点出发,确立与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相适应的经济机制与体制的统治地位。这也是防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私有化转变的根本。古往今来,没有离开所有制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也没有高居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上,不落实到社会再生产诸领域中的所有制。正所谓公有有公有的“活法”,私有有私有的“活法”。很难想像,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下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下,企业会有一样的“活法”,社会再生产会按照一样的方式运行。所谓“经济机制中性论”,“运行机制中性论”、“经营机制中性论”,都不过是“商品经济中性论”的具体化,而中性的商品经济在现实中是并不存在的,正像不存在中性的生产与分配一样。如果把所有制“高高挂起”,使其“不食人间烟火”,转而按照“中性论”的思维设计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不仅难以保证公有经济在整体上活得好,还会导致丧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二十年来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何以一路下滑,除了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种种原因外,大概与我们为国有企业设置的“活法”并不能使其活好有很大关系。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关键在于保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没有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就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什么要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道理主要不在现实中的国有经济实力强、贡献大上面,而是因为国有经济集中代表着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因而能够通过它的活动在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使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国有经济要起到这样的作用,一要有足够的实力,二要有有利于它起这样作用的经济机制和体制。以个人利已主义为核心的斯密主义,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若经济体制只是一味地刺激每个人、每个企业最大限度地追求个别利益,公有企业就活不好,国有经济实力再强也会失去控制力。
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发展水平不高,而且还与非公有经济处于并存状态。因此,确立与现阶段公有制经济发展相适的经济运行机制、经营管理体制的统治地位,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无视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共同点,闭门造车式地构造经济机制与体制。新的经济体制是以“我”为主,既使公有经济充满活力、又有正确利用非公有经济积极作用(当然包括限制其消极作用),让非公有经济在发展中跟着公有经济走的体制。在这个问题上,同样需要转变思维。
***
关于什么是私有化的理论讨论,还有许多方法论问题值得思考,如所有权的实现形式与所有制的实现形式,现代私有制与法人所有权,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所有制,等等。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能一一论列了。
标签:所有制论文; 社会主义公有制论文; 生产资料所有制论文; 所有权的转移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