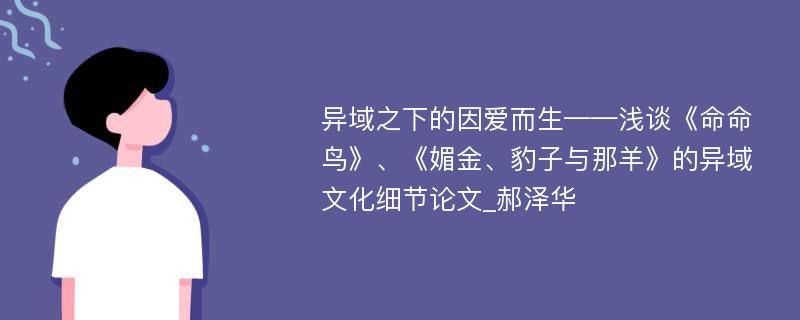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摘要:许地山和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以异域文化为创作素材的作家,对于爱情的诠释中富有异域文化以及异域信仰的色彩,在同样存在“死生契阔”的异域文化主题作品中,从爱情引申出来的事物却是中原文化所少有的。异域对于爱情、对于诺言、对于生存与死亡、对于信仰的独到见解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小说风格的独特性和小说思想的卓越性。本文以许地山《命命鸟》、沈从文《媚金、豹子与那羊》两文为例,从场与域、鸟与羊、喧与静、死与生四个角度探讨异域文化为文学创作带来的独特启发和重要意义。
关键词:异域;异域文化;许地山;沈从文;命命鸟;媚金、豹子与那羊
引言:许地山和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两位文风不同于中国中原风气的两位作家。“生死契阔,与子成说”作为中国古代爱情的一种境界被传颂至今,而不容小看的是,在异域文化的背景之下,同样存在着“生死契阔”般相携赴死的爱情悲壮,但是在异域文化和异域信仰之下,从爱情引申出来的事物却是中原文化所少有的,异域对于爱情、对于诺言、对于生存与死亡、对于信仰的独到见解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小说风格的独特性和小说思想的卓越性。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两位独具风格的异域文学作家,许地山和沈从文堪称两位避开了传统中原风气的叙述手法的文人,在浩荡的文人浪涛之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派清波。本文从许地山作品《命命鸟》和沈从文作品《媚金、豹子与那羊》两文入手,探讨在异域文化之下的作家笔下的因爱而生的种种精神和灵魂层次的追求与信仰。
一、场与域:进步洪流中的淳朴观照
本文探讨的两篇小说,一篇来自以佛为信仰的缅甸,另一篇则发生在与恪守敬天保民理念的中原有着千山万水之隔、信仰傩神和神巫的原始的湘西,两地的共同点之一就是均脱离了汉民族文化或中原文化的桎梏,但又各自有各自独到的信仰和敬畏。
《命命鸟》中时时处处的南国风光无一不透露出异域的风情 ,无论是文中提到的“瑞大光塔”,还是敏明梦中游览的“极乐国土”,都让人有“总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国度的人,学着另外一个国度里的事。”之感,许地山利用异域的独特文化环境与文化氛围,在小说中呈现出了另一个为中国人所不熟知的世界——没有对于死亡的规避与恐惧,亦无“三纲五常”等中国式伦理道德体系对思想的束缚的世界。然而异域使然,爱情却也有无法摆脱的牢笼,时空上的不同,只是在“封建”二字的额间点了一颗伪装的朱砂,依旧伺机等待着释放无尽的洪水猛兽,迷信生肖相克的敏明之父,以及用符咒替他人“制造命运”的蛊师,事实上无异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包办婚姻的父兄之辈。
同样以异域他想为创作主题,许地山的作品中往往更多的流露出平和与从容,其作品中文字的温美以及异域的民俗风情都成为了其创作的表层展现,他善于将景物与其精神体验合二为一,形成一种独特的美学体验,进而为接下来深层次的思想内核进行编织与铺垫。许地山也曾因亲人的相继辞世感受到痛苦,想到过遁世或舍身的念头,但是其人终如其文,有情的世界和众生的悲苦依旧让他有所牵挂而难以彻底地对这人生释怀。对于生活之中的无奈,他选择的是将生之苦难上升为精神层面的思考,赋予文本现实中的观照。
但是,在许地山的作品里,却不乏摧毁“真”、“善”“美”的存在,在《命命鸟》中,许地山选择摘取生活中的痛苦进行创作,在实现自身对于人生哲学的认识的同时,也揭露了生活中的痛苦与险恶,同时暗示了其“生本不乐”的人生观。《命命鸟》中的成年人无一不在举手投足间流露出对于封建思想的流连,彼岸飘落在自称“命命鸟”的男男女女身上几近将其淹没的“情尘”、甚至是最终让两人自沉湖水、投身极乐国土的宗教其本身,实际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封建思想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加陵父亲愿意加陵“跟他当和尚去”、敏明要奉行的独身主义,将青春年华对宗教献祭,诸如此类的事件堪称无时无刻不是在拆散爱情,无时无刻不是在阻挠两个人心灵的契合。
而《媚金、豹子与那羊》则发生在遥远的湘西,一个脱离了传统中国正统思想,有着原始族群的野蛮和血腥的地方,但是那里同时也保留着许多国人沦丧了淳朴与挚诚,例如守信、虔诚、对爱人的珍重和不辜负。沈从文在书写《媚金、豹子与那羊》的时候,一直在以一种淡淡的局外人的口吻进行叙述,并时不时插入自己的一些评论之辞,例如谈及媚金与豹子相约幽会的洞穴的今貌时,他谈到:
不过我说过,地方的好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是下降了,女人也慢慢的像中国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嫌热按时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成为无用东西了,就是有这样好地方供年青人许多方便,恐怕媚金同豹子也见不惯这些家装的热情与虚伪的恋爱,倒不如还是当成圣地,省的来为现代的爱情脏污好!
这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沈从文借小说而兴起的一种对于现代文明的“牢骚”,对于他而言,现实中的湘西或许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但是当沈从文离开湘西以后,他思想之中一直存在的美好的、质朴的、真诚的湘西成为了一种脱离了现代文明和传统礼教自由而独立生长的一朵野花。在这样一片净土上,媚金、豹子以及一只羊的牵绊渐渐展开,变成了一幅立体、真实、有血有泪、有歌有笑的图景。
异域题材的选择实际上是一种独特文化的氛围的选择,作家以此完成真正想要抒写的思想情感,无论是中国封建的另一摹本,还是完全不着封建传统习气的净土,两位作家真正先要表达的,是对于一种生活模式与思维方式的追忆或是向往。两人故事发生的场域虽然天各一方,各具风格,但最终却都走向了死亡,他们想要表达的,是湮灭于社会进步洪流中的某一种美好的精神。
二、鸟与羊:灵魂的慰藉与寄托
“命命鸟”一词出自佛经故事,为佛教传说中的两头一体的共命之鸟,一荣俱荣,一死皆死。许地山巧用此名,赋予了敏明和加陵的异世界的永恒相守。深受缅甸佛教文化思想影响的许地山虽通晓多种宗教,但却并不是宗教的“传教者”,而是将释、耶、儒、道各种思想融合而探索信仰力量的“信教者”,他始终追寻的是一种以精神为力量的名曰“信仰”的宗教,因而他笔下的敏明始终执着于一种信仰的坚守中。
本文注意到,在敏明游幻境看到对岸说笑的男女时的描写:
他们绕了几个弯,当前现出一节小溪把两边的树林隔开……树下有许多男女……都现出很亲密的样子。敏明说:“那边的花瓣落得更妙,人也多一点,我们一同过去逛逛罢。”那人说:“对岸可不能去。那落的叫做情尘,若是望人身上落得多了就不好。”敏明说:“我不怕。你领我过去逛逛罢。”那人见敏明一定要,过去就对她说:“你必要过那边去,我可不能陪你了。你可以自己找一道桥过去。”他说完这话就不见了。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敏明回头瞧见那人不在,自己循着水边,打算找一道桥过去。但找来找去总找不着,只得站在这边瞧过去。
将敏明与对岸的世界相隔绝的“桥”是真爱与虚情之间贯通的媒介,然而身为“命命鸟”的敏明的眼睛是澄澈的,她并没有被情尘玷污而迷失自我,因此她看不到通向虚假的道路,故做不到彼岸的“命命鸟”所言所做的一切。正是因为她的心依旧是洁净而赤诚的,她的面前永远没有导向虚伪的指向标,她的脚下也永远不会存在通往的花言巧语、朝三暮四、反复无常的桥梁。
而《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羊的意义,沈从文进行了详尽的解答:
每一个情人送他情妇的全是一只小小白山羊,而且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与这恋爱的坚固……
湘西的当地人将性爱情感的地位看得十分崇高,而洁白的羊羔则能去除性爱本身存在的某些污浊。本文认为,同《命命鸟》中幻境分隔真假“命命鸟”的河水一样,这只羊同样也充当了“阻隔媒介”的作用。致使媚金豹子最终双双殉情的因素之一正是用来“换取媚金贞女的红血”的小羊。豹子为了找到能匹配媚金的完美小羊,不惜奔波于两座村庄之间。但是也正因对于这种爱情过度的珍视和崇拜,使豹子最终因一只羊失去了心爱的女人。小说结尾的叙述,有一种莫名的平静和安然,而最终的结局是两人死去,而羊得以独存,并成为故事叙说的一条线索。
“命命鸟”和“羊”的相同的作用便是推动故事情节进一步走向恋人的赴死道路,这种推动力是一种类似于冬去春来般的水到渠成。二者均浸润了作者的写作灵魂,并非孤立突兀的存在,它们承担着将作者的所思所将通过自身的独特性而展现出来的义务,是作者长久的感情积淀而物化出来的一种寄托与慰藉。
三、喧与静:无关褒贬的异域美学
喧与静通常是对立的,有时可以转化。在喧与静的问题上,《命命鸟》和《媚金、豹子与那羊》都从各自独特的角度进行了诠释。
许地山的《命命鸟》中,彼岸虚伪的“命命鸟”们聒噪不已,急于表白心意,而此岸真正能够厮守生死的“命命鸟”却是一言不发,木然站在一片盛景之中,与陶潜“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之句有异曲同工之美。安静有的时候是内心安然而超脱尘俗牵绊的表现,敏明虽是少女,却能在一场梦境中参透、真正的“命命鸟”、在一片花草树木各自为乐的环境中,在彼岸虚情假意的“命命鸟”无休止的“海誓山盟”中理解到真正的“极乐”。
而湘西获得思想情感的方式却是要以“对歌”的形式唱出来,《媚金、豹子与那羊》中两人的相识便是对歌的结果,而沈从文的另一篇作品《月下小景》中的对歌甚至占了全文篇幅的大半。湘西人的生活是少不了歌唱的,以对歌而定终身行为,在湘西人的眼中则带有几分率真和质朴的气质。湘西不乏宁静,但是“喧嚣”二字在湘西绝非贬义。对歌是的互问互答,不仅仅是男女互相追求,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更是获取对人生的思考和探讨的重要手段。
在“喧”与“静”孰优孰劣的问题上,本文认为在分析两部作品时,应不在进行判断之前添加个人主观先见。仅仅视其为客观的事物时,“喧”“静”孰是孰非就无可追究了。若是认为《命命鸟》中的“喧”都是负面的代名词,那么又该如何解释敏明歌舞演绎的一首《孔雀孔雀》?若是认为《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喧”是好的,那么又该如何评判最终两个人流淌鲜血的静谧的夜晚、安静的洞穴和不言不语的羊?因此,对于“喧”与“静”的褒贬象征问题,不应过多纠缠,相反,对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时代环境甚至是家庭环境、个人环境,喧静之争是无法辨别出一个客观的高下的,因为实现文字的美学是主观的,喧静之辩,可谓各有千秋。
四、死与生:献祭式超越与涅槃
两个故事,虽然最初都是因爱而起,以死为终,但其死亡的意愿却不仅仅局限于爱情。
《命命鸟》中敏明和加陵的死,更像是一种将肉体对生命和信仰的献祭,这似乎与爱情的关系不大。一些文章认为,《命命鸟》最终的结局是两个人的殉情,但本文并不赞同,在敏明梦中彻悟以后,她对于爱情的见解已经超越了一般程度上的理解范围,最终若不是加陵寻踪追随敏明而去,敏明很有可能孤身走入湖中,实现精神的涅槃与重生。
而《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死亡更像是对于一种古朴的、一诺千金式的浪漫的殉情。沈从文是心软的,他没用让媚金自杀后立刻断气,而是让她挣扎着活到了豹子赴约而来的时候,让她在人生的最后时刻知道心爱的人并没有负她,最终看着豹子把刀子插入胸膛而“含着笑死了”。这种一诺千金,至死不渝的浪漫是很难再汉民族文化的统治领域内得以实现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两个人的死平添了几分悲壮和艳丽的色彩。这个故事似乎在向人们证明着:死亡同样是一条通向真正的爱情的坦途。
如此可以发现,《命命鸟》中两人最终的的死似乎有点先知、圣贤、涅槃的意味,而《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死则是保留着浸润了千年雨雪风霜的古朴,富有一种质朴的决绝。对于死的认识,前者可以称之为灵魂的涅槃,而后者则更可以算作是对诺言的牺牲。不过,虽然两篇小说中主人公们最终赴死的思想认识程度有很大的不同,许地山和沈从文想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却又相交的领域,他们都欲通过这样的文本向读者传递这样的意图:死,并不是一种生命的陨落,因爱而生的死,也并不一定会是一种简单而通俗的殉情。
在汉民族文化统治的地区,这种与爱情有一定关联的死往往只能招致苟且于男女私情而忽视家国之恨的骂声;然而在异域特殊的文化信仰下,两位作家通过两篇小说,都在力图想这个世界证明着:不仅仅是为国捐躯的死亡才称得上悲怆、壮烈或是伟大,小人物的生活,小人物的爱情,小人物的彻悟,小人物的死亡,同样可以造就精神和灵魂上的不朽和绚烂。
结语
因爱而生,但未必因爱而终,这不是一种诅咒或是不详,而是情感和思想认识的升华,是一种真实的人性的歌颂和赞美,沈从文曾提到: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诗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自然、健康而不悖于人性的的人生形式。
或许沈从文和许地山想要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情感:爱只是生命中的一小部分,相遇的缘分或许是因爱而起,但是最终的结局或许有的时候升华于爱情,变成了一种跟同样感天动地,能引起心灵共鸣的人性之美。这种美虽然以异域为媒介表达,但是其实质,却无关异域或是本土。
参考文献:
许地山:《许地山作品新编》方锡德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许地山:《许地山文选》林文光编,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12
沈从文:《神巫之爱》季羡林主编,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12
沈从文:《月下小景》,长沙:岳麓书社,2013.1
沈从文:《月下小景》唐文一编,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3
许地山:《许地山精品文集》膳书堂文化编,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4
艾芜:《南行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7
黄娇娇:《一个”异质“的存文学在——论许地山的创作特色》,北京大学,2012.6
易永谊:《佛教与文学:命命鸟中的对话叙述》,红河学院学报,第五卷第三期,2007.6
论文作者:郝泽华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6年6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10/25
标签:异域论文; 豹子论文; 湘西论文; 爱情论文; 文化论文; 从文论文; 许地山论文; 《文化研究》2016年6月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