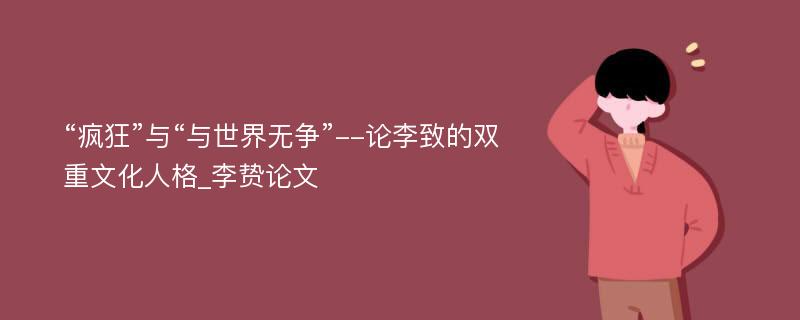
“狂怪”和“与世无争”——论李贽的双重文化人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世无争论文,人格论文,文化论文,李贽论文,狂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谈起李贽其人,学界常常冠之以“狂狷”、“异端”或“狂怪”的字眼,视其为中国此类文人的代表。域外学者如是说(注:沟口雄三以《矢志前行的异端》命名他的著作(《中国的人和思想》10,昭和61年,1986,集英社);荒木见梧在他的《佛教和阳明学》(第三文明社出版)中的第15章,同样将“异端”二字加于“李卓吾”前:《异端的形象——关于李卓吾》。山下龙二在他的《阳明学的寿终正寝》中的第三章《李贽的历史观》这样来评价李贽的历史观:“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极端的、奇异的古今未有的过激思想”,即在他看来,通常人们认为李贽的思想应是“极端的”、“过激”“奇异的”思想。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第7章《李贽——自相矛盾的哲学家》中也有相类的观点。),域内学者也如此说(注:国内的几位研究者也是异口同辞。嵇文甫称:“卓吾思想最狂放,最敢发惊人的议论。”(《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63页)张建业说:“李贽是我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狂狷之士。”《李贽评传前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左东岭说:“他(李贽)唯一所依靠的是其狂怪的个性与激进的思想。”(《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547页)),甚至自万历十四年下半年至二十三年下半年,李贽本人也曾如是说(注:万历十六年,李贽在写给焦竑的信中道:“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李贽《答焦漪园》,《焚书》卷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页。本文所引《焚书》,皆据中华书局1961年版,不再重复,只注页码。因此版取明刊本顾大韶《李温陵集》和以明本为底本的清末本《国粹丛书》本,补缺存长,是目前保存《焚书》原貌较好的本子)李贽还有两篇专论英雄出于“狂狷”的文章。在其他信中,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要做狂狷的话。)。既然李贽自己承认,难道还有什么怀疑?笔者还是怀疑。因为李贽的话是在特定文化情境下的特定心理状态下说的,那特定的情境状态在他七十六岁的生命长河中所占不过一小段,尽管这一小段很重要,但即使在这一小段中依然还存在着与之相对立的另一文化人格,对此,李贽自己也多次提及(注:李贽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本性为“与世无争”一类的话。《与城老》:“平生所贵者无事,而所不避者多事,贵无事,故辞官辞家,避地避世,孤孤独独,穷卧山谷也。不避多事,故宁义而饿,不肯苟饱;宁屈而死,不肯幸生。……唯我随遇而安,无事固其本心,多事亦好度日。”(《李氏续焚书》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352部,第321—3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本文所引《续焚书》文字,皆据《续修四库全书》本,不再注明,只标明页码。因此本为南京图书馆藏明刊本影印本)《寄答留都》:“我但虚己,勿管彼之不虚;我但爱教,勿管彼之好臣所教;我但不敢害人,勿管彼之说我害人。则处己处彼,两得其当,纷纷之言,自然冰释。”(《焚书》增补一,第268页)《复李士龙》说明李贽本心在求道,在超然于名利之外。“既超然于名利之外,不与利名作对者,唯孔夫子、李老子、释伽佛三大圣人尔。……若七十三岁而令人勿好利,与七十六岁而兼欲好名,均为不智,均为心劳日拙也。”(《李氏续焚书》卷一,第318页)《与友人》:“不知天下之事最应当真者,惟有学道作出世之人一事而已,其余皆日用食欲之常,精亦得,粗亦得,饱亦得。不甚饱亦得。不必太认真也。”(《李氏续焚书》卷一,第337页)等等。)。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对立因素的存在,我们所理解的李贽文化人格在结构上便是残缺的,如果我们斩断了李贽生命长河中的绝大部分,只见其一点,那同样不是历史李贽的全人。如果我们论述李贽人格的全结构与历史的全人,那么,愚以为李贽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一种人。
一
本文拈出的“文化人格”一词是指人面对生存环境所表现出的一种自我意识、创造能力和超然自适的精神。这种文化人格既不同于西方将上帝视为至高无上的人格载体的理想人格主义之人格,又不同于中国传统的道德人格。它洋溢着中国晚明时代特有的文化气质。“凡圣如一”的平等思想,尊重自我、肯定人欲的人生观正是这一时代文化精神的核心内涵。受“凡圣如一”思想影响,李贽一方面“舍己”、“从人”,“与人为善”,“与世无争”;另一方面认定人人可成圣、成佛,心中无权威,敢于“非圣无法”。李贽的文化人格正是晚明这一特有文化气质的典型表现。故我舍西方的“个体人格”与东方的“道德人格”词语不用而以“文化人格”一语表述之。
本文所言“狂怪”,指狂狷、怪异。怪异乃与众不同(也指与儒学别样的禅、道),故为众人视为怪。“狂狷”即非孔子口中之“狂狷”,也非孟子笔下之“狂狷”(注:李贽对狂狷的理解既得之于孔子、孟子,又不同于孔、孟。不同处有二:其一,李贽更关注狂狷在胆识上的超人价值。不但狂者见识超人,狷者也同样见识超人。其二,他更强调狂狷与豪杰的关系,正是从这一关系的分析出发,认为豪杰必出于狂狷,而不出于中庸。故将狂狷置于中庸之上,这与孔、孟心目中中庸为上、狂狷次之的观点倒了个儿。),而是指李贽自己所论述的“狂狷”。李贽集中论述“狂狷”的文字有多处,现将其重要论言列之于下:
狂者不蹈故袭,不践往迹,见识高矣。所谓如凤凰翔于千仞之上,谁能当之?而不信凡鸟之平常与己均同于物类……狷者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如夷、齐之伦,其守定矣。所谓虎豹在山,百兽震恐,谁敢犯之?而不信凡走之皆兽。……盖论好人极好相处,则乡愿为第一;论载道而承千圣绝学,则舍狂狷将何之乎?……故学道而非此辈终不可以得道;传道而非此辈终不可以语道。有狂狷而不闻道者有之,未有非狂狷而能闻道者也。(注:李贽《与耿司寇告别》,《焚书》卷一,第27—28页。)
求豪杰必在于狂狷,必在于破绽之夫。若指乡愿之徒遂以为圣人,则圣门之得道者多矣。此等岂复有人气者,而尽指以为圣人,益可悲矣夫!(注:李贽《与焦弱侯太史》,《李氏续焚书》卷一,第320页。)
李生曰:孟子以乐克为善人信人。夫曰善人,则不践迹矣。曰信人,则有入室之望矣,可喜何如也。夫之所以终不成者,谓其效颦学步,徒慕前人之迹为也。不思前人往矣,所过之迹,亦与其人俱往矣,尚如何而践之!……凡人之生,负阴而抱阳,阳轻清而直上,故得之则为狂;阴坚凝而执固,故得之则为狷。虽或多寡不同,参差难一,未能纯乎其纯,然大概如是而已……自今观之,圣人者,中行之狂狷也。君子者,大而未化之圣人也。善人者,狂士之徽称也。有恒者,狷者之别名也。是皆信心人也……是信者,狂狷之所以成始成终者也。……学者不识善人之实,乃以廉洁退让笃行谨默之士当之,是入乡愿之室而冒焉以为登善人之堂也。(注:李贽《德业儒臣·孟轲附乐克论》,《藏书·儒臣传》卷二十四,《续修四库全书》第302部,第222页。本文《藏书》用《续修四库全书本》,因此本为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万历二十七年焦竑刻本。以下注文不重复,只注页码。)
由以上引文可以看出,李贽虽也注意区分“狂”与“狷”,区分“阴”与“阳”、“轻清”与“坚凝”的差异,但更多则是将二者视为“不可以轩轾”的同一概念。这一概念的内涵为:狂狷者“不蹈故袭,不践往迹”,“不肯依人脚迹”,见识高于众人之上;所以高于众人之上是由于狂狷者“皆信心人也”,“信心人”就是相信自己的心胜过相信一切,故而言出于己心,笔出于己心,行出于己心,依心肆行(注:而狂人正是依心肆行者,“陶渊明肆于菊;东方朔肆于朝;阮嗣宗肆于目;刘伯伦、王无功肆于酒,淳于髠以一言定国肆于口,皆狂之上乘者也。”李贽《藏书·儒臣传》卷二十四《德业儒臣·孟轲附乐克论》,第223页。);正因狂狷者信心直行见识超于众人之上,故“求豪杰必在于狂狷”而不在于乡愿(注:李贽将狂狷与乡愿看作性质对立的两种概念:狂狷者为环境不容,目之为怪。而乡愿者为环境所容,“众皆悦之”;狂狷者真心直行,言行一致。乡愿则言行不一,表面装作“忠信”、“廉洁”,内心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狂狷者对于其所处的环境总是处于超逸或背离状态——不与之同流合污。“乡愿”则指对环境采用迁就认同、同流合污的态度。)。总之,狂狷的核心精神就是“信心”直行、超人逆俗意识和反权威精神。也正因超人逆俗、反权威,方被人视为异端、狂怪。
本文所言“与世无争”,是指人面对其所处环境采取超然自适的态度。所谓无争,指对现实层面——名利、是非——的无争。所以“与世无争”,是因为无争者在认识的层面已超越于世俗之上,超越于名利是非之上,步入一个更高的境界,而绝非指“乡愿”。不争名利是因为认识到名利是累、是祸,它带人陷入生死轮回的苦痛之中不能自拔,故而人要免除苦痛就要远离名利,剔除名利之想;不争是非,并非无是非,而是认为人人皆有自己的是非,不必一是非。具体讲就是不与耿定向争高低,争是非。“仆佛学也,岂欲与公争名乎?抑争官乎?皆无之矣。”(注:李贽《答耿司寇》,《焚书》卷一,第29—35页。)你所见是“形骸之内”,我所见为“形骸之外”;你讲“人伦之至”,我讲“未发之中”;你大谈“入世”之学,而我所言则为“出世”之学;你说我剃发为异端,我可蓄发,乃至亲到黄安天窝与你握手言和。所以“与世无争”是“达人宏识”的超逸精神和“与人为善”、“舍己”、“从人”的顺适意识。
超人逆俗反权威的“狂怪”和“舍己”“从人”的“与世无争”的双重人格在李贽身上早就存在着,对此曾做出全面揭示的是李贽最知心的好友焦竑。万历八年,李贽由姚安太守任上致仕,云南御史刘维集官绅所写赠言为一册,题名曰:“高尚册”。李贽将《高尚册》寄于焦竑。焦竑写《宏甫书高尚册后》,其中有云:
宏甫为人,一钱之入不妄而或以千金与人如弃草芥;一饭之恩亦报而或与人千金言谢则耻之;见一切可喜人无有不当其心者而不必合于己;己不能酒而喜酒人;己不能诗而喜诗人;己不能文而喜文人;己不捷捷能言而喜能言之人;己不便鞍马而喜驰骋;己不好弄而喜敌道;己不好斗而喜徘徊古战场;己不好杀而喜商君、吴起、韩非之书;己不爱纷华而喜郭汾阳穷奢极欲,以身系国家之安危;己不欲以谿刻自处而喜于陵仲子辞三公为人灌园;独不喜逊床循墙终日拜伛偻以为恭者,以故常不悦于世俗之人。俗之所爱,因而丑之;俗之所憎,因而求之;俗之所疏,因而亲之;俗之所亲,因而疏之;有时长贫,虽必不得已,已也,故终身不肯假借于人;有时暂富,虽必可已,不已也,故终其身无一钱之积;平生未尝召客,人召之酒则赴;平生不礼贵人,贵人馈之则受。以故虽不悦于人而终不见害于人,以宏甫与世无争故也。(注:焦竑《焦氏笔乘》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129部,第538页。)
这段文字全面介绍了李贽的为人。细加分析,李贽不同于常人的为人行事分为两类,分别显示出李贽自身具有的两类人格因素。一类是性情弘阔、舍己从人的顺适意识。别人不必合于自己的眼光,只要对方有可喜处,即使自己不善长,也无不欢喜。一类是行事与世俗人别样的逆俗意识。世俗人乐于别人说好话,也喜伛偻献媚于他人,他偏不喜此类人,不但不喜欢,且做事常常与他们相反。正是“俗之所爱,因而丑之,俗之所憎,因而求之”的逆俗意识,才使得李贽的顺适无争和“好人极好相处”的“乡愿”得以区分开来。前一类顺适意识源于“与世无争”的人格;后一类逆俗意识则是走向狂怪的内在基因。这相互对立矛盾的因素统一于李贽一身,构成了对立统一的双重文化人格。此双重文化人格在外力作用下此起彼伏的矛盾运动,构成了李贽文化人格演变的历史。不过,就写此段文字时(万历九年)的焦竑看来,后一与世俗别样的逆俗意识依然从属于“与世无争”的文化人格。因为,无论是他处于贫困时“不肯假借于人”,还是骤富“无一钱之积”,皆是其“与世无争”的性情造成的;而且他平时不召客、不礼贵人。客人贵人宴请他、馈赠他,他却都能接受,所以能接受则又无不是“与世无争”性情在起作用的缘故。正因为如此,李贽一生文化人格的底色主调不外“与世无争”。而抗争叛逆式的“狂怪”文化人格则是与世俗别样的逆俗意识处于背逆挑斗环境中的异样发展。对此,李贽自己也有过明确表示。万历二十三年,史旌贤任湖广佥事,扬言对李贽“以法治之”。面对官方的挑衅,李贽明言自己本心贵无事,但也不怕事。“平生所贵者无事,而所不避者多事。贵无事,故辞官辞家,避世避地,孤孤独独,穷卧山谷也。不避多事,故宁义而饿,不肯苟饱,宁屈而死,不肯幸生。……无事固其本心,多事亦好度日。”(注:《李氏续焚书》卷一《与城老》,第322页。)“贵无事”就是“息事宁人”、“与世无争”;“不避多事”就是“宁义而饿,不肯苟饱,宁屈而死,不肯幸生”,就是逆俗超人的“狂怪”。前者“固其本心”,后者是人家来寻事而被逼迫的不得已。两种人格内外分明,主次有序。
正因为李贽一生文化人格的底色主调是“与世无争”,所以“与世无争”的性情在耿、李论战开始阶段仍表现出一定的惯性,延续了一段时间。下面需说明的几个问题是:耿、李论战始于万历十二年年末,为何说狂怪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间是万历十四年?万历十四年(六十岁)之前李贽性情是否为“与世无争”?万历二十四年之后,李贽的狂怪人格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生成两种文化人格的思想基础及其本质是什么?
二
为什么说李贽狂怪的性情在其人格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始于万历十四年下半年,而不是耿、李论战开始的万历十二年?首先,认定李贽的狂怪人格在李贽的性格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标志有两个。一是李贽在其论著(特别是论战的信函)中“与世无争”的思想让位于狂怪思想。二是,李贽自己明确表示要做狂狷,并申明做狂狷的理由。这两个认定的标志集中出现于万历十四年下半年,而在此之前的两年则未出现过。万历十二、十三两年,耿定理去世后,李贽写了约20篇诗文(未写著作)(注:这20篇是万历十二年11篇(首):《答骆副使》(《续焚书》卷一)、《赠何心隐高第弟子》(《焚书》卷六)、《哭耿子庸》四首(《焚书》卷六)、《复耿中丞》(《焚书》增补一)、《又与焦弱侯太史》(《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第十五书(《李氏遗书》卷一)、《答耿中丞》(《焚书》卷一)、《又答耿中丞》(《焚书》卷一)。万历十三年9篇(首):《与焦弱侯太史》(《续焚书》卷一)、《南询录序》(《续焚书》卷二)、《与焦弱侯》(《续焚书》卷一)、《哭承庵》一首(《续焚书》卷五)、《中秋见月感念承庵》一首(《续焚书》卷五)、《大智对雨》一首(《续焚书》卷五)、《答耿中丞论淡》(《焚书》卷一)、《答何克斋尚书》(《焚书》增补一)、《复丘若泰》(《焚书》卷一)。具体考证见拙著《李贽著述编年考》(待出)。),所表达的多是与世无争的思想。这可从他与后来的论敌耿定向以及与好友邓石阳的几封信函中看得很清楚。万历十二年最具代表性的两封信是:《答耿中丞》、《又答耿中丞》(注:《答耿中丞》,《焚书》卷一(第16—18页),《又答耿中丞》,《焚书》卷一(第18—19页),写于万历十二年秋冬间。万历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耿定理卒。见耿定向《观生记·甲申》:“是月二十三日,仲子卒于家。”李贽同年所写《哭耿子庸》:“行年五十一,今朝真死矣。”耿定理生于嘉靖十三年(1534),至万历十二年(1584)恰好为五十一岁。耿定向于这一年八月提升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相当于明初御史台中丞),故称耿中丞。因文中有“则公此行,人人有弹冠之庆矣。”故知写于八月之后李贽得知此消息时。而《又答耿中丞》写于《答耿中丞》之后,可能是耿定向回函后,李贽又写的复信。)。这两封信的中心意思是:你我所学各有不同,“仆自敬公,不必仆之似公”;“邓豁渠之学主乎出世”,“今公之学主乎用世”;“迹相反而意相成,以此厚之不亦可乎?”意思是说,你大度些,大家便相安无事;完全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万历十三年所写《答耿中丞论淡》所论核心乃“达人宏识”,唯有达人才能使心止于空净。非“杂”、非“厌”、非有“纤毫”,能“纯一”则是淡。而所谓“达人”就是“与世无争”,就是“其见大也,见大故心泰,向心泰故无不足。”这显然是自己以“与世无争”的态度劝说耿定向做“心泰”的“达人”,不要强迫别人服从(注:《答耿中丞论淡》,《焚书》卷一(第24页),当写于万历十三年冬间、耿定向《纪梦》之后。《纪梦》:“万历乙酉闰月(九月),既望之夕”,万历乙酉即万历十三年,闰九月实为阴历十月。“中夜梦与荆石王相君曰:“今爱昙阳出世一场,特为相君与凤洲两先生耳。”“惟淡,知乃良”云云(耿定向《纪梦》,《耿天台先生文集》(明版影印)卷十九。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1906页)。次晚,耿定向便向弟子周友山、李士龙诸人说梦,写下《纪梦》一文。此文写于读《纪梦》之后。)。而《复邓石阳》用更大篇幅阐述自己“与世无争”的思想性情:“平生师友散在四方,不下十百,……弟初不敢以彼等为徇人,彼等亦不以我为绝世,各务以自得而已矣。故相期甚远而形迹顿遗。愿作圣者师圣,愿为佛者宗佛。不问在家出家,人知与否,随其资性,一任进道,故得相与共为学耳。”又道:“人各有心,不能皆合,喜者自喜,不喜者自然不喜;欲览者览,欲毁者毁,各不相碍,此学之所以为妙也。”此信写于万历十四年邓石阳子邓应祈为麻城县令之后(注:李贽《复邓石阳》,《焚书》卷一(第10—14页),写于万历十四年。从信中所写的时间来看,应是邓石阳子邓应祈万历十四年任麻城令后。民国《内江县志》卷四《邓应祈传》:邓应祁,字永清,幼以奇童称。举万历壬午第三人,丙戌成进士,授麻城令。万历壬午即万历十三年,丙戌即万历十四年。邓石阳子邓应祁任麻城令为万历十四年,或许邓石阳也随子来麻城小住,遂有与李贽等人一起论学事。第一封信《答邓石阳》中言:“我在此,兄亦在此,合邑上下俱在此。”所谓“合邑上下”显然指麻城全县。《复邓石阳》言:“万里相逢,聚首他县。”所谓“聚首他县”,实指麻城。《又答石阳太守》言:“我二人老矣,彼此同心,务共证盟千万古事业,勿徒为泛泛会聚也!”此“会聚”与上“聚首他县”同。)。可见万历十四年上半年的李贽还是“与世无争”之人。
表明其“狂狷”性情的文章见于万历十四年下半年所写的四封信函之中。一是《答耿司寇》的长文,“与世无争”的性情让位于狂狷(该文并不是没有“与世无争”的思想,只是与狂狷相比少得多了)。其狂狷主要表现为:其一,公开扬言人心本私,无不为己。其二,驳斥对方的虚假,直指其为假道学,伪君子,锋芒毕露,毫不留情。《寄答留都》便直接明言:“我以自私自利之心,为自私自利之学,直取自己快当,不顾他人非刺。”狂狷之态甚明。二是《与耿司寇告别》(注:《与耿司寇告别》一文的写作时间,我以为当在“遗妻归女”之后,而遗妻归女的时间应在周友山上任的万历十三年与邓应祈任麻城令的万历十四年之间,也当在李贽入住麻城维摩庵之前,因考证篇幅过长,故略去。)、《与焦弱侯太史》、《与焦弱侯》三篇文章直言自己是狂狷,并一再阐明“求豪杰必在于狂狷”的道理。“盖论好人极好相处,则乡愿为第一,论载道而承千圣绝学,则舍狂狷将何之乎?”(注:李贽《与耿司寇告别》,《焚书》卷一,第27—29页。)“人犹水也,豪杰犹巨鱼也。欲求巨鱼必须异水,欲求豪杰,必须异人。……今日夜汲汲,欲与天下之豪杰共为圣贤,而索豪杰于乡人,则非但失却豪杰,亦且失却贤圣之路矣。”(注:李贽《与焦弱侯》,《焚书》卷一(第3—4页),写于万历十四年。理由有二:其一,此封谈豪杰的信,是写给落第后焦竑以示安慰的。万历十四年焦竑参加会试再落第。李剑雄《焦竑年谱》万历十四年条:“丙戌,四十七岁。春,在京参加会试,再度落第,归金陵。”(《澹园集》下,附编四,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90—1291页)故此信当写于焦竑落第的当年。其二,耿定向此年三月送妻灵柩回籍,耿定向《观生记》:“万历十四年丙戌,我生六十三岁。正月十四日,彭淑人卒于京邸。三月,以其榇还……其岁,著《译异篇》。”《译异篇》是耿定向为回击李贽本年所写《答耿司寇》的长信,于当年研读佛经后所写。李贽写此信回击耿定向的攻击。《译异篇》写于万历十四年,而回击的这封信也当写于《译异篇》后不久。)他是在直接或间接地指责耿定向找豪杰不从狂狷中找,失去了狂狷,也就失去了豪杰。三封信皆表达“求豪杰必在于狂狷”的同一意思,语气如一,时间为同一年,符合判定李贽性情是否以狂狷为主的两个标准。所以说李贽“与世无争”的性情让位于“狂狷”的时间始于万历十四年。
三
那么,此前六十年,李贽的性格是狂怪还是与世无争?回答既有狂怪的一面,又有与世无争的一面,而主要是与世无争。说明这一观点的证据来自于保存下来的写于万历十四年之前的李贽自己与他人的4 篇文字以及由这些文字所显示的李贽的主要行事大略。依据的4篇文字是:托名孔若谷实则出于李贽自己之手的《卓吾论略》,焦竑的《宏甫书高尚册后》,李元阳《姚安太守卓吾先生善政序》、焦竑《怀五子诗》。
《宏甫书高尚册后》已分析于前,该文虽指出李贽不合时俗的一面,但更强调其为人的根本是“与世无争”。《卓吾论略》真切地叙述了李贽超人逆俗意识和“与世无争”性情发展的历史。李贽超人逆俗意识来自于他幼年、少年形成的“自信”、“自以为是”的性格。文中记述他当时学《论语》的情形:“年十二,试《老农老圃论》,居士(孔若谷对李贽的称呼(注:《卓吾论略》一文是以孔若谷(此人不详)的口气写的,即李贽请孔若谷写的一篇传记,按理应放入孔若谷文集中,却收入《焚书》卷三《杂述》之中,不知是李贽所收,还是他人编《焚书》时收入的。))曰:‘吾时已知樊迟之问,在荷篑丈人间。然而上大人丘乙己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须也。’论成,遂为同学所称。”(注:李贽《卓吾论略》,《焚书》卷三《杂述》,第82—85页。)12岁的李贽就有一种不以孔子的论断为权威,敢以提出与之相反见解的勇气,显示出自立、自信的自我人格与超凡识力。这一人格在其后的生命历程中时有表现,如对朱熹注文的厌恶,背时文戏弄科考,在南京刑部任上后期的“好谈说”和“自以为是”等。不过,在这六十年的生命历程中,李贽更多的是学会了适应环境,更多地表现为以长子应承担的家庭责任为己任。四处谋食,婚嫁弟妹,茔葬父亲、祖父、大母等(四十岁前)。此后便是求道,接受王阳明的心学、苦读佛经、兴注《老子》、《庄子》。由顺敬的孝子、顺势的仕子,到潜心接受心学的学子,再到超然于名利之外“与世无争”的高人,“与世无争”的性格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卓吾论略》一文更可贵处在于揭示了自己“与世无争”性情生成的家族渊源——其父白斋公的人格魅力及其影响。文中道“居士曰:‘吾时虽幼,早已知如此臆说未足为吾大人有子贺,且彼贺意亦太鄙浅不合于理。彼谓吾利口能言,至长大或能作文词,博夺人间富若贵,以救贱贫耳,不知吾大人不为也。吾大人何如人哉?身长七尺,目不苟视,虽至贫,辄时时脱吾董母太宜人簪珥以急朋友之婚,吾董母不禁也。此岂可以世俗胸腹窥测而预贺之哉!’”李贽心中的父亲是位无意富贵的高士,一位不能以世俗胸腹窥测的超凡脱俗的求道君子。这正是李贽不以富贵为意,潜心道妙,不与世人争是非、争富贵的“与世无争”思想产生的家族文化渊源。事实上焦竑所言的长贫而不假借于人,骤富而终无一钱之积的“与世无争”思想,正是与白斋公不以富贵为意却以求道为命的思想人格一脉相承,而且,该文多处写白斋公对他的影响(注:《卓吾论略》或写科考做官是为了赡养父亲,如云:“‘且我父老,弟妹婚嫁各及时。’遂就禄,迎养其父。”或写做官求道,思念父亲,如云:“共城,宋李之才宦游地也,……父子倘亦闻道于此,虽万里可也。”乃至为思念父亲而自改名号:“居士五载春官,潜心道妙,憾不得起白斋公于九原,故其思白斋公也益甚,又自号思斋居士。”),也证明他的“与世无争”思想最早源于他的父亲。
李元阳(张居正的老师)是位善于识人的老者,他眼中的姚安太守李贽既是位有“出俗之韵”、“遗世之风”的人,又是位“以德化民”、“善学孔子”的孔学的当今承继者(注:李元阳《姚安太守卓吾先生善政序》:“先生自幼有出俗之韵,超然不染尘世,每欲遨游五岳,以华其志,然势不得自由者。”乃至说他在理政之暇也如此:“退食自公,载见觞水豆浆之趣,燕寝凝香,而枕石漱流之风。啸咏发于郡斋,图书参于案牍。”云云。又言李贽以德化民:“惟务以德化民,而民随以自化。日集生徒于堂下,授以经义,训以辞章。”其结论乃是:“以愚观之,善学孔子,非先生而谁?”见《李中溪全集》文集,卷六。)。有趣的是,焦竑(李贽的知己畏友)对于李贽的评价竟与李元阳暗合。其写于同时的《怀五子诗》云:“圣人不克见,圣学日荆臻。寥寥千载后,师圣当何因。彼岸久未登,姚安识其津。一振士风变,再振民风醇。”同样说李贽是圣学的承继者,却同样没有一语涉及李贽有狂怪异端的内容,说明姚安致仕前的李贽并未给人狂怪的印象。当万历十四年起李贽演变为异端后,致函焦竑,明言今日李卓吾大不同于此前的李卓吾了:“兄所见者向日之卓吾耳,不知今日之卓吾固天渊之悬也。兄所喜者亦向日之卓吾耳,不知向日之卓吾甚是卑弱,若果以向日之卓吾为可喜,则必以今日之卓吾为可悲矣。”(注:李贽《焚书》卷二《与焦弱侯》,第60页。)李贽的人格正是由此前“与世无争”的“卑弱”变为万历十四年后的“狂诞谬戾”(注:清永瑢、纪昀等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20页(中)。)了。这也反过来说明此前的李贽是位“卑弱”的“与世无争”者。
也许有人会说,李贽说他做官总与上司合不来,总是“触”。与上司“触”,不是狂怪吗?首先须说明,李贽说他为官期间,总与上司“触”的话,见于《感慨平生》。而《感慨平生》为《豫约》中一节,写于万历二十四年,非论战之前,必然带有“不如遂为异端”的色彩,此其一。其二,李贽所谓的“触迕”并非行为上的而更多当是心理上或情感上的内触迕。若果真恣意而行,尽与上司碰撞起来,怎能在官场一帆风顺,只凭一举人身份,便由一县教谕而擢升至一方太守?单以与他触迕最激烈的上司——骆问礼——观之便知其“触”的性质了。在姚安期间,李贽自言他与骆问礼“触”的原因是,一个主张治吏民为宽,一个主张当严。“遂不免成触也。”但李贽对骆问礼的态度依然是:“虽相触,然使余得以荐人,必以骆为荐首也。”(注:李贽《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第189页。)而骆问礼也心敬李贽,当他守制在家闻知李贽欲致仕时,便急致函李贽的上司杨会道:“卓吾兄洁守宏才,正宜晋用……士类中有此,真足为顽儒一表率。”(注:骆问礼《万一楼集》卷二十六《复杨贯斋》。)骆问礼对李贽的印象一直很好,且一生与之保持着亲近联系。相触最烈者尚且如此,与不如此烈的他人相触的情形便可想而知了。所以如此,原因就是焦竑所说的“与世无争故也”。
四
耿、李论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万历十四年至万历二十三年年末),由于假道学视其为狂禅、异端,群起而攻之。逼使李贽不得不“遂为异端”,率意为狂为怪(注:李贽多次向友人表明,人家将其视为异端,他遂不得不为异端;人家要来找他的事端,他只好不怕事端;人家挥拳打他,张口骂他,他不得不还手、还口。一句话,异端是环境逼出来的,不得已。《答焦漪园》:“又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焚书》卷一,第8页)《与曾继泉》:“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焚书》卷二,第50页)《复邓石阳》:“弟异端者流也,本无足道者也,自朱夫子以至今日,以老、佛为异端,相袭而排摈之者,不知其几百年矣,弟非不知,而敢以直犯怒者,不得已也。”(《焚书》卷一,第12页)《与周友山》:“又我本性柔顺,学贵忍辱,故欲杀则就刀,欲打则就拳,欲骂则走而就嘴”(《李氏续焚书》卷一,第319页)。)。这一点,前人论述已多,故不复赘述。现在要说明的是,万历二十四年(注:万历二十三年年终李贽赴黄安与耿定向握手言欢,且在那里过完春节,直到第二年万历二十四年春才回到麻城龙湖(见李贽《焚书》卷四《耿楚倥先生传》及文后所附《周思敬跋》,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43页)。故言其狂怪的九年为万历十四年下半年至万历二十三年下半年,而言其后七年则指万历二十四年春至万历三十年春。)之后,李贽狂怪的文化人格是否有所变化,有怎样的变化?
李贽“狂怪”性情自万历二十四年之后虽时起时伏,但总体呈衰减趋势,“与世无争”的性情则渐呈上扬势头。这一方面与他年老多病的生理与心理有关。自万历二十一年始,李贽几乎年年患病(胃病、痺病、喘病),精神也随身体好坏而沉浮。二十四年后,虽南北奔波,实不过勉强为之(注:如赴刘东星山西沁水之邀、山东济南之邀,是为了还武昌受人家庇护的恩情债;重返龙湖是心中牵挂芝佛院众弟子,为报答众人服侍之情;入河南黄蘖山,北上通州马经纶府,是为了避难等等。)。与生理的衰老相联系,“老年人不如年轻人”的自卑与求安心理甚浓,或表现为人有所求即使过去不愿做的现在也只好将就去做,如代人写“寿序”、祭文;或表现为爱说别人的好话乃至恭维话,颂扬多于批评;如《续藏书》对人物评价好话多,调子趋于温和。对狂狷的认识也发生转变,写于万历二十五年的《与友人书》抑狂狷,赞中行,颂圣人,甚至认为唯圣人可医狂病(注:该文中言:“渠见其狂言之得行也,则益以自幸,而唯恐其言之不狂矣。唯圣人视之若无有也,故彼以其狂言吓人而吾听之若不闻,则其狂将自歇矣。故唯圣人能医狂病。”(李贽《焚书》卷二,第73页))。《明灯道古录》则主张人应处于骄与不骄之间(即倾向于中庸)(注:李贽《道古录》第11章云:“若夫不骄不倍,语默合宜,乃吾人处事常法。此虽不曾道问学,而尊德性者或优为之。”)。一句话,李贽超人逆俗的狂怪人格渐渐让位于舍己从人的“与世无争”的文化人格。今仅举四件事,以见其一斑。一件是与论敌耿定向握手言欢;一件是著文力赞“孝乃百行之先”,令耿定向大为欣喜;一件为著《九正易因》显现出“法孔子”、“法神圣”的思想转变;第四件,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对李贽著作批评的态度由前期的愤慨斥骂变为后期的语调和缓乃至认可。
万历二十三年冬,李贽亲自由麻城龙湖冒寒前往黄安耿定向家,与这位老对手握手言欢,了却多年夙愿(注:周思敬《耿楚倥先生传跋》,《焚书》卷四《耿楚倥先生传·附文》,第144页。)。对这件事李贽颇有点迷途知返猛然醒觉之慨:“使楚倥先生而在,则片语方可以折狱,一言可以回天,又何至苦余十有余年,彼此不化而后乃觉耶?”(注:李贽《耿楚倥先生传》,《焚书》卷四(第141—145页),写于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地点黄安。此文写于到黄安与耿定向和好之后。和解的时间为冬天,文中云:“余是以不避老,不畏寒,直走黄安会天台于山中。……又何至苦余十有余年,彼此不化而后乃觉耶?”周思敬《跋》云:“两先生以论道相左,今十余年矣。”耿定向《观生记》载,万历十二年七月,耿楚倥死。“十有余年”或“十余年”应为万历二十三年。因万历二十二年,不能称“十余年”或“十有余年”。也不可能是万历二十四年冬,因万历二十四年六月,耿定向去世。故知合欢的时间当为万历二十三年。周思敬明言得到《楚倥先生传》的时间为十二月二十九日。“越三日,则为十二月二十九,余初度辰也,得卓吾先生所寄《楚倥先生传》。”可知此文当写于万历十三年十二月间。)且以为两个对手原本“志同道合”,造成长久唇枪舌剑的原因不过是双方的固执己见——两相守而不能两相忘。“天台先生亦终守定‘人伦之至’一语在心,时时恐余有遗弃之病;余亦守定‘来发之中’一言,恐天台或未窥物始,未察伦物之原。故往来论辩,未有休时,遂成轩格,直至今日耳。今幸天诱我衷,使余舍去‘未发之中’,而天台亦顿忘‘人伦之至’。乃知学问之道,两相舍则两相从,两相守则两相病,势固然也。两舍则两忘,两忘则浑然一体,无复事矣。”(注:李贽《耿楚倥先生传》,《焚书》卷四,写于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而且李贽在耿家竟住了一个多月,直到过了春节后才离开(注:据《李氏续焚书》卷一《与城老》(第322页)中有“只有黄安订约日久,不得不往。原约共住至腊尽”语,可能“黄安订约”的时间在前一次李贽去黄安与耿定向讲和时,时间大约为万历二十二年。)。李贽与耿定向的握手言欢这件事本身,李贽是主动者(注:事实上,《焚书》发行,将耿、李的矛盾向社会公开化了。李贽内心便因如此做有些过分而深感内疚。这种内疚心理表现在他几次写信透露与耿定向和好之意。万历十九年有两次。一次在龙湖时,说他一生“专以良友为生,故有之则乐,舍之则忧。”又说:“楚侗回,虽不曾相会,然觉有动移处,所憾不能细细商榷一番。彼此具老矣,……盖今之道学,亦未有胜似楚侗老者。”跃跃欲和之情可见。另一次是本年到武昌后,遭人围攻,写信给周友山,表示要加冠蓄发:“即日加冠蓄发,复完本来面目,二三侍者,人与圆帽一顶,全不见有僧相矣”,又说:“然弟之改过实出本心,……弟当托兄先容,纳拜大宗师门下,从头指示孔门‘亲民’学术。”说的虽是气话,但并非毫无相和之意。不然何必说此软话呢?万历二十一、二十二两年,李贽没有与耿定向论战的信函,气氛较过去平和多了。万历二十二年,他曾去过一次阔别了十年的黄安,与耿定向第一次和解(《与城老》),并写有“一别山房便十年,亲栽竹条已参天”的诗句(《重来山房赠马伯时》,《焚书》卷六,第243页)。)。李贽所以如此做的原因甚多,但有一条是无可置疑的,即“两舍则两忘”的“与世无争”的性情起了主导作用。
另一方面,随着耿、李的和解,李贽与身边思想、政治环境的关系虽时而对抗但总体趋于和缓的态势;同时李贽思想上狂怪的一面在很大程度上被佛经的智慧化释。这方面突出的例子是他写于黄安的《与若无母寄书》。僧人若无的母亲要求儿子守孝,并讲述了一番守孝与成佛互不相碍的道理。李贽读后为之感动,既悔又喜,写下了如下一大篇文字:
恭喜家有圣母,膝下有真佛,夙夜有心师。所矢皆海潮音,所命皆心髓至言,颠扑不可破。回视我辈傍人隔靴搔痒之言,不中理也。又如说食示人,安能饱人?徒令傍人又笑傍人,而自不知耻也。反思向者与公数纸,皆是虚张声势,恐吓愚人,与真情实意何关乎!乞速投之水火,无令圣母看见,说我平生尽是说道理害人去也。又愿若无张挂尔圣母所示一纸,时时令念佛学道人观看,则人人皆晓然去念真佛,不肯念假佛矣。能念真佛既是真弥陀,纵然不念一句‘弥陀佛’,阿弥陀佛亦必接引。何也?念佛者必修行,孝则百行之先。若念佛名而孝行先缺,岂阿弥陀亦少孝行之佛乎?决无是理也。(注:李贽《读若无母寄书》,《焚书》卷四(第140页),写于万历二十四年耿定向未死(六月二十一日)之前。证据有二。其一,李贽对《若无母寄书》赞赏不已。耿定向读后喜甚,并大加发挥,在重病中写了《读李卓吾与王僧若无书》(《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九,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1861—1868页),有两段文字足以证明李贽此文写作的时间。耿定向曰:“又闻李卓吾赏音如是,是以虽在沉疴中,亦大生欢喜不已也。”说明李贽写此信时,耿定向病甚是沉重了。其二,耿定向在此文中还说:“惟卓吾生平割恩爱,弃世纷。今年至七旬矣,乃能反本如是。”此年(万历二十四年)李贽七十岁,而六月,耿定向死。他自言“弥留待尽之日”,也正是此年。)
李贽这段话有两点令耿定向大为高兴。一是说“孝则百行之先”,也是念佛成佛之先。欲成佛者,先行孝方可成佛。二是李贽忏悔自己以前的话多是虚张声势不关真情实意的话。于是耿定向借此文大赞卓吾:“惟卓吾平生割恩爱,弃世纷,今年至七旬矣,乃能反本如是,……闻卓吾赞叹张媪言,亦大欢喜如是也。盖即其欣赏张媪言如是,便知其持学已归宗本心矣。学知求反本心,更何说哉?”(注:耿定向《读李卓吾与王僧若无书》,《耿天台先生文集》(明版影印)卷十九。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1864—1867页。)耿定向说的“求反本心”的“本心”,是指忠孝之心,“人伦之至”之心,虽与李贽所言父子的自然天性有所差异。但李贽毕竟说出“孝则百行之先”一类的话,为孝字大做文章。毕竟耿定向与李贽有了能唱和的共同点,无疑这是李贽一种有意无意向耿定向靠近、和好的表态,是他的狂狷思想略有收敛的表现。
李贽狂狷怪异性情渐趋弱化突出表现于《九正易因》一书。自万历二十六年抵达南京至他去世的万历三十三年的近七年间,李贽主要精力倾注于读《易》解卦(注:李贽《九正易因序》(《续修四库全书》第9部,第611—612页)。本文引《九正易因序》用《续修四库全书》本,因该本《九正易因序》为苏州市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八年陈邦泰刻本的影印本):“《易因》一书,盖予既老,复游白门而作也。……直上济北,而《易因》梓矣,……今马侍御又携予北抵,复读《易》于其所学《易》之精舍。……而定其名曰《九正易因》也。”),故而《九正易因》成为他这一时期思想的主要载体。《九正易因》及其相关史料说明一个重要的事实:李贽狂怪的性情至此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由原来的“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到“法孔子”;由出入三教不固守某家到膺服孔教;待人接物由轻狂薄礼到谦恭如礼。
万历十七年,汪可受在龙湖初见李贽的印象是:“老子秃头带须而出,一举手便就席。”(注:汪可受《卓吾老子墓碑》见《畿辅通志》卷一百六十六“古迹十三”,“陵墓二”。)万历二十九年,于通州再次见到李贽的情形则是:“老子以儒帽裹僧头,迎揖如礼。余惊问曰:‘何恭也?’老子曰:‘吾向读孔子书,实未心降。今观于《易》,而始知不及也。敢不如其礼。’”(注:汪可受《卓吾老子墓碑》见《畿辅通志》卷一百六十六“古迹十三”,“陵墓二”。)李贽所以待人如礼,是由于他心降于孔子而尊依孔教的缘故。汪可受所记载此段文字因与《九正易因序》、《读易要语》暗合,故知其并非虚言。换言之,我们可从出自李贽之手的《九正易因序》、《读易要语》反过来证实汪可受上述言语的可靠性,且进一步表明李贽后期文化人格由狂怪到与世无争的变化。李贽叹服孔子对《易》的妙解。以为“故世之读《易》者,只宜取夫子之《传》详之,必得其《易》象之自然乃已。不然,宁不读《易》。”(注:李贽《九正易因》卷上《读易要语》,《续修四库全书》第9部,第613—614页。)他所叹服孔子是由于孔子能专一发挥神圣心事。“夫子在当时亦已知文王之言至精至约、至约至精,非神圣莫能用矣。是故,于《爻》、《彖传》之外,复为六十四卦《大象》,以教后世之君子。……俾卤莽如余者得而读之,亦可以省愆而寡于怨尤,分明为余中下之人说法。”(注:李贽《九正易因》卷上《读易要语》,《续修四库全书》第9部,第613—614页。)李贽称自己为“卤莽者”,多“怨尤”者,“中下之人”。难以想见这些自谦之词会出于以“圣人”、“豪杰”、“狂狷”自居的李卓吾之口,而这又无疑是李贽的自白,这一自白表明现在李卓吾已不同于十年前的李卓吾了。这种不同更鲜明地体现于《读易要语》的结束语:“余又愿后之君子,要以神圣为法。法神圣者,法孔子者也,法文王者也,则其余亦无足法矣。”《九正易因》所表现的李贽性情、思想,与汪可受所记载的李贽对孔子由“实未心降”到“始知不及也”的思想变化是一致的。
万历二十四年前后,李贽的思想性情由以“狂怪”为主走向以“与世无争”为主,由反叛思维走向顺适思维,还可从《四库全书总目》对李贽著述的评语中得以证实《四库全书总目》对每部书的评语最初虽出于不同编纂者之手,但最终经总编纂官纪昀评定。正因最终经一人评定,所以其尺度手眼相对一致,故而可由其对李贽不同时期著述的评语发现李贽思想性情的起伏变化。《四库全书》收入李贽的书或书目极少,仅有七部,除两部疑非李贽著述外(注:这两部中,一部为《读升庵集》,一部为《三异人集》。《读升庵集》,纪昀从两方面予以否定,其一,未必有编辑动机。“贽为狂纵之禅,慎则博洽之文士,道不相同,亦未必为之编辑。”其二,“序文浅陋,尤不类贽笔。”(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20页中)《三异人集》,纪昀认为“所评乃皆在情理中,与所作他书不类”。并推测作者可能是俞允谐。“卷首题吴山俞允谐汝钦正,或允谐所为,讬之於贽欤。”(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750页上)李贽于来往书函中,并未提及此部《三异人集》。假托李贽之名的可能性较大。),其余五部中写于耿、李论战期(万历十三年至二十三年年底)的有三部,纪昀批语如下:
《初潭集》十二卷,内府藏本。明李贽撰。……大抵主儒释合一之说,狂诞谬戾,虽粗识字义者皆知其妄。而明季乃盛行其书,当时人心风俗之败坏,亦大概可睹矣。(注:清永瑢、纪昀等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20页(中)。)
《李温陵集》二十卷,江苏周厚琑家藏本。明李贽撰……贽非圣无法,敢为异论。虽以妖言逮治,惧而自刭,而焦竑等盛相推重,颇熒众听,遂使乡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故其人可诛,其书可燬。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为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庶无识之士,不至怵于虚名,而受其簧鼓,是亦彰瘅之义也。(注:清永瑢、纪昀等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八,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99页(上)。)
《藏书》六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李贽撰。……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其书可燬,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注:清永瑢、纪昀等纂《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55页(中)。)
纪昀对李贽的“非圣无法”深恶痛绝。从其“狂诞谬戾”、“狂悖乖谬”、“排击孔子”、“颠倒易位”、“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的评语中,可知论战期李贽的思想性情的确是狂狷怪异的。然而对李贽成见颇深的纪昀,在对李贽论战后(万历二十四年及其后)所写的两部书的评价竟变了另一种调子:
《续藏书》二十七卷,浙江总督采进本。明李贽撰。贽所著《藏书》,为小人无忌惮之尤。是编又辑明初以来事业较著者若干人,以续前书之未备。……因自记本朝之事故,议论背诞之处,比《藏书》为略少。(注:清永瑢、纪昀等纂《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55页(下)。)
《九正易因》,无卷数,江苏周厚堉家藏本。明李贽撰。……贽所著述,大抵皆非圣无法,惟此书尚不敢诋訾孔子,较他书为谨守绳墨云。(注:清永瑢、纪昀等纂《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5页(中)。)
同样在纪昀眼中,李贽的议论变得“背诞之处”少,乃至“不敢诋訾孔子”、“谨守绳墨”了。从“排击孔子”到“不敢诋訾孔子”;从“非圣无法”到“谨守绳墨”,不进一步证明李贽的思想性情的确经历了由以狂怪异端为主到以“与世无争”为主的明显的演变吗?只能如此,却难以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
五
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以往研究者多以为李贽是狂怪、异端的典型代表呢? 想必一定有其根据和道理。根据是有的,主要是李贽写于耿、李论战期间的文字(包括《感慨平生》和《自赞》)以及友人袁中道《李温陵传》、焦竑《追荐书》等他人的评介文字。然而,这些文字或写于万历十四年到万历二十三年年底,或写于李贽死后,未有一篇是写于论战期前后的,即写于耿、李论战期的文字必然突现李贽人格狂怪异端的一面。况且在人们普遍看来,李贽死于舌笔,死于《焚书》、《藏书》……,一句话死于异端、狂怪。所以,李贽死后的人也无不将李贽视为异端、狂怪,所写评价语也自然只注目于异端、狂怪一面,于是李贽在后人的印象中仅仅剩下了一个简单而鲜明的符号——“狂怪”、“异端”。
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读。不要说李贽七十六年生命历程中“与世无争”性情占据主导地位,即使在论战期间,李贽的性情也有“与世无争”的一面。且往往与“狂怪”思想搅和于一处。今以耿、李论战期间李贽的代表作——攻击耿定向最猛烈的长文《答耿司寇》——为例略加分析便见其一斑。李贽《答耿司寇》有云:
圣人不责人之必能,是以人人皆可以为圣。故阳明先生曰:“满街皆圣人。”佛氏亦曰:“即心即佛,人人是佛。”夫惟人人之皆圣人,是以圣人无别不容己道理可以示人也。故曰:“予欲无言。”夫惟人人之皆佛也,是以佛未尝度众生也。无众生相,安有人相?无道理相,安有我相?无我相,故能舍己;无人相,故能从人,非强之也。以亲见人人之皆佛而善于人同故也。善既与人同,何独与我而有善乎?人与我既同此善,何有一人之善而不可取乎?故曰:“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诸人者。”后人推而诵之曰:即此取人为善,便自与人为善矣。舜初未尝有欲与人为善之心也,使舜先存与善之心以取人,则其取善也必不成。人心至神,亦遂不之与,舜亦必不能以与之矣。舜惟终身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而已。耕稼陶渔之人既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
“舍己”、“从人”、“与人为善”的“与世无争”思想,源于“圣人不责人之必能”。所以“不责人”,是由于“人人可以为圣”。人人可以为圣,你可以为圣,我可以为圣,又何必以自己的道理去教人、责人不如己?己与人同,故可舍己。人人是佛,你是佛,我是佛,人我成佛相同,故可从人。既然人人皆善,“善与人同”,人人有善可取,那么,为什么不取人之善,与人为善?由此可见,李贽“与世无争”的思想最早源于“人人可以为圣”的“凡圣如一”思想。而“凡圣如一”的思想也可导致反权威的平等思想。既然“人人可为圣”,你可以为圣,我可以为圣,又何必以你的道理去教人?既然“人人是佛”,你是佛,我是佛,你又何必度我,我可自度也。圣人有圣人之是非,百姓有百姓之是非,人人有自己的是非,故不必以他人之是非为是非,不必以某人是非为天下人之公是非,故而也不必以孔子一人之是非为天下之公是非。“善既与人同,何独与我而有善乎?人与我既同此善,何有一人之善而不可取乎?”“又何必专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由此,我们不仅发现,在这封与耿定向论战的长信中依然有着“与人为善”和“与世无争”的思想内涵,而且更重要的是发现了李贽那种“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何必专学孔子而后为正脉”的“非圣无法,敢为异论”的狂怪思想竟也同样源于“凡圣如一”的平等思想。李贽在其他信函中也明言“志大言大”的狂怪人格源于“凡圣如一”的思想:“夫人生天地之间,既与人同生,又安能与人同异?是以往往徒能言之以自快耳,大言之以贡高耳,乱言之以愤世耳!”(注:李贽《焚书》卷二《与友人书》。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3页。)这样一来,李贽超人逆俗的“狂怪”文化人格与其“舍己”“从人”的“与世无争”的文化人格,竟然皆源于“凡圣如一”的平等思想。是“凡圣如一”思想向两面衍生的结果,即“凡圣如一”的思想事实上成为李贽两种对立人格——“狂怪”和“与世无争”——的思想原壤。而这种“凡圣如一”的思想的本质则是在反权威、倡平等中突出自我个性。人人有自己之是非,人人可以为圣,人人可以成佛,正是尊重个性强调自我意识的表现。这种表现同李贽肯定私心人欲的思想相结合,恰恰反映了晚明时代文化思潮的特征,也是李贽文化人格的本质。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到李贽文化人格中“狂怪”的一面,而未看到其“与世无争”的一面,更不知这两种文化人格之渊源及其本质,那么我们对李贽的解读就会仅仅停留于世俗认知标志的一个侧面,那显然不是结构的、历史的、自然鲜活的真李贽。
总之,李贽的文化人格既有“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非圣无法”的狂怪一面,又有“舍己”“从人”、“与人为善”的“与世无争”的一面,就李贽的一生而言,狂怪人格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段仅是万历十四年下半年到万历二十三年下半年的9年(即使在这9年时间里,“与世无争”的人格因素依然有不容忽视的显现),此前的60年主要为“与世无争”,此后的7年,年老力衰,病魔缠身, 狂怪之势大衰,起主导地位的还是“与世无争”。因此对于李贽来说,“狂怪”只是其处于背逆挑斗环境下文化人格的异彩变调,“与世无争”才是其历史文化人格的底色主调。而这两种文化人格同源于“凡圣如一”的平等思想。这种平等思想与李贽肯定私心、情欲主张的和合正是晚明尊重自我、肯定人欲的时代文化思潮的本质,也是李贽文化人格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