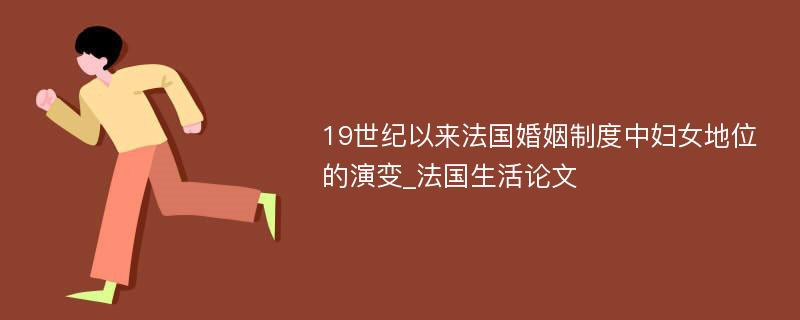
19世纪以来法国婚姻制度中妇女地位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妇女论文,地位论文,婚姻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国当今的家庭模式与19世纪初的相比大相径庭,在近两个世纪中,婚姻制度和妇女在家庭中地位的变化有目共睹。有人认为旧婚姻制度已经灭亡,家庭中的两性平等业已实现,妇女的自主权已受到尊重;有人则持不同看法,在肯定巨大进步的同时,强调旧传统观念的持续性以及在妇女地位改变方面所获成果的脆弱性。事实究竟如何?本文试图通过法国婚姻状况变化的历史轨迹和动因以及夫妇关系现状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
法国大革命的风暴惊天动地,但是对家庭制度却没有多大触动。相反,资产阶级的共和派在歧视妇女和给男人以高一等社会地位这一点上同旧时代的正统派是不谋而合的。在他们看来,合法家庭具有传授家业、传授社会地位的作用,担负着对家庭成员保护、教育等职责,维护作为社会基层细胞、具有等级形式的合法家庭是等级社会稳定的基础,为达此目的,就要树立丈夫的权威,而妻子便充当了牺牲品。在这个问题上的集大成者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拿破仑一世。1804年3月21日诞生的《拿破仑民法》确立了丈夫具有“一家之长”身分的绝对权威。体现“妻子应该服从于他的丈夫”(213条)①这一总原则精神的是无数细致而具体的规定。
首先,妻子在经济上没有自主权,法律严格规定家庭财产由丈夫管理,甚至可自由支配他妻子的工资②。为了维护家庭和家庭财产,继承法规定的继承顺序中,妻子对丈夫的遗产继承名列最后,甚至在私生子之后,实际上被剥夺了对丈夫财产的继承权,连习惯法中的继承特留份都没有。丈夫即使去世了,他还继续在阴间行使其权威;因为在他死前可为寡妇指定一位帮助她对子女进行监护的顾问。如果她怀孕了,他会指定一位遗腹胎儿财产管理人。如果她再嫁,寡妇就要服从家庭监护顾问的决定。③
其次,妻子在生活中不拥有独立的人格。例如,由丈夫确定夫妻的住处,妻子必须相随于他,绝不能住到他处,否则以犯罪论处;丈夫有权检查妻子的信件,并能要求邮政当局把她的信件交给他,甚至可予以毁掉;妻子的一切社会行为都必须得到丈夫的许可,如接受继承、生前赠与、获取财产、让与财产、抵押财产、从事职业、在正式文件上作证、签艺术合同、得到正式证件等。当丈夫因精神错乱、被监禁、被判刑等而无法实行对妻子的监护权时,她并不能摆脱夫权,因为将由法官来代替丈夫行使夫权。④
再次,为了维护合法家庭,立法者始终对离婚抱敌视态度。法国大革命中通过的1792年法令曾规定七种离婚理由,《拿破仑民法》不敢取消这项已成为习俗的法律,但只保留了其中的三条理由:通奸、被判刑、虐待和重大侮辱。离婚条件十分苛刻:严格规定必须双方同意、不得在婚后两年内以及结婚20年后提出、丈夫必须满25岁、父母长辈必须同意、离婚要求在一年中要重复四次;离婚后在三年内不得再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复婚;犯通奸罪的不得与奸夫(妇)结婚……这项法律对妇女的敌视更为明显:如果由母亲监护孩子,到孩子七岁时也必须交给父亲,即使他曾被确认有罪。⑤
最后,在家庭问题上犯法时,夫妻在法律面前不平等。1808年起草的刑法对通奸案和离婚案所作的规定更露骨地反映对两者实行的是不公平的双重道德准则。奸妇可能被判三个月至两年监禁于教养所(298条);而对奸夫只科以100-2000法郎的罚金。妻子只有当丈夫公开把姘妇供养在自己家里时才可能被准予离婚;而丈夫只需对通奸作一简单“揭发”即可获准离婚。⑥法律起草者之一波尔塔利斯道出了这样立法的指导思想:“妻子比丈夫的不忠具有更大的腐蚀性和更加危险的后果。”⑦因为她们首先是传种接代者,她们的行为如偏离道德即可对维护家庭的完整性产生更严重的威胁。
总之,妇女一旦结婚,在公共领域中就失去了自己的身分,她的身分只能通过丈夫来体现,丈夫是她的监护人,她的地位与儿童、精神病患者无异,被确定为终生“未成年者”(1124条)⑧,即“无能力者”。请看当时一位作者在评述《民法》草案时所说的:“妇女、儿童、仆人没有分文财产,因为他们自己是一种财产:妇女属于男人,儿童来源于他们,仆人仅是工具,其时间、劳动、技艺都属于主人。”⑨男子在婚姻行为中是得益者,而女子不仅无益可得,相反是受害者,当时,著名社会学家杜尔凯姆在他1897年出版的著作《自杀》中论述婚姻与自杀行为的关系时是这样说的:“婚姻对自杀行为具有一种固有的预防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只有益于一个性别。”提供的数字表明已婚男子比单身男子自杀的比例小,而妇女在此问题上受婚姻保护的幅度小得可略而不计。他的结论是“夫妻的利益是有差别的,是相对抗的。婚姻是反妇女的”。⑩19世纪上半叶有一位来自于社会底层的著名女社会活动家弗洛拉·特里斯唐为无产者尤其是妇女解放奋斗了一生,她有一句名言十分精辟地概括了法国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受压迫最深的男人可以压迫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妻子。她是无产阶级中的无产者。”(11)法国婚姻制度如此贬低已婚女子地位的做法在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是罕见的,特别不同于英国、美国、德国以及北欧等新教国家,可以说法国妇女的不幸是法国社会的瑕疵。
法国近代工业的发展震憾整个社会,固守旧制度的顽固堡垒──家庭也受到冲击。女权主义者和有志于解放妇女的有识之士进行了近一个半世纪的不懈斗争,为改变妇女在各个领域中的地位,其中包括家庭中的地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婚姻制度没有出现转折性的变化,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只是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有稍许变动,例如:已婚妇女可以不经丈夫同意开银行存折(1881),可以在户籍证明和公证文书中作证(1897),可自由支配自己的工资(1907),可不经丈夫同意加入工会(1920年,但1938年又予以取消),如果父系和母系都没有继承人,可获得丈夫遗产继承权。1938年2月18日法令取消了妇女在民事中的无能力地位,因而已婚妇女除了上述已经争得的微乎其微的几项权利外,又加上从此可在无丈夫允许的情况下报名上大学、参加考试、签署和接受支票、接受赠与、为自己申请做护照、住疗养院而不算犯有抛弃夫妻住处罪。(12)然而上述权利仅说明妇女在人身方面的地位,而妇女在经济上仍处于无权状态,丈夫仍保留了最重要的权利:一是财产管理权,在绝大多数的法国家庭(结婚时未签订婚约的家庭)中,丈夫是夫妻共有财产的管理者,就是说他继续管理着妻子的财产,因为他是一家之长;二是没有丈夫的允许,妻子不可就业。由此可见,到二战前夕,法国已婚妇女尚无经济自主权,在经济上还是“无能力者”。(13)
1945年法国解放,1946年宪法前言确定了“男女在一切领域中的权利平等”原则,(14)尽管如此,婚姻制度在此后的20年中没有多大变动。直到1965年以后,婚姻制度改革才触动了《拿破仑民法》中最不平等的方面。1965年的改革使妻子得到了管理、享用、自由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1428条);(15)可以不经丈夫同意去就业(223条)(16)。1970年和1975年法律建立了家庭中的“双亲权”以取代“父权”,即夫妻在子女面前在精神上和物质上拥有同等权威;妻子可以参与家庭的共同决定,如分期付款购置家庭所用之物等(220条)。(17)
离婚法在一个半世纪中几经周折,它曾于1816年被废除,后来尽管在议会中屡次讨论过离婚法案,但都遭取笑和拒绝。1884年恢复的离婚法条件苛刻而复杂。将近100年后的1975年7月11日法令才进行了重要改革,即有关人身和财产同时分离的改革,此外,婚约的解除变得比较容易,在两种情况下就准予离婚:一是双方同意,二是实际分居至少六年以上,(18)法律不再强调必须犯有罪行或专门的过错才可准予离婚,这无疑是有利于妇女的,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妇女提出离婚。
有关在夫妻关系性领域内妻子自主权的改革是巨大和根本的变化。1967年和1975年通过了两项法令分别对禁止避孕和禁止堕胎的1920-1923年法令予以否定,(19)使妇女从此获得了在控制生育中的自主权,在这个问题上成为自己人身的主人,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不再要屈从于丈夫的意愿。
80年代的法国婚姻制度并非已很完美,仍然残留有不平等因素,最重要的是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还反映出“夫权至上”的痕迹:丈夫是夫妻共同财产的唯一管理者,(20)这里指的是夫妻在婚后生活中共同或分别获得和节余的所有财产(比以往进步的是丈夫不经妻子同意不能转让、出卖、出租属于共同财产的不动产、营业资产等);丈夫是未成年子女财产的唯一管理者;(21)丈夫是姓氏的传授者,妇女婚后要改夫姓,子女也从父姓;(22)在税收法和社会法中保留“丈夫是一家之长”(23)的首要权位,即在纳税和社会保险问题上,已婚妇女在很多情况下没有独立人格,要通过具有一家之长身分的丈夫来面对当局。可见《拿破仑民法》把已婚妇女贬为“未成年者”、“无能力者”的残余尚存。
二
从法律的角度看,法国婚姻制度和已婚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在一百多年中确实经历了深刻变化,纵观这段历程,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一些特点。
法国婚姻制度的变化具有缓慢性和反复性,从而反映了旧婚姻制度的顽固性。已婚妇女从在民事方面的完全无能力状态向具有部分能力状态过度走过了将近两百年,其时间之漫长、速度之缓慢是惊人的。变化的速度前慢后快,前160年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关键性的变化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的短短20年。即使有变化也往往出现反复,例如离婚法从保留到取消,后又恢复;又如妇女加入工会的自主权利曾经得而复失等。变化的迟缓是因为家庭是国家、教会、企业的缩影,在中世纪,丈夫在家庭中的权威象征并确保封建君主在封臣面前的权威;在近代社会,公民服从执政者的权威、工资劳动者服从雇佣者的权威、世俗者服从教士的权威,这样一种秩序是不容随便打破的。封建社会立法者的理论被19世纪资产阶级立法者所借鉴,国家和天主教会毫无保留地支持这样一部建立在丈夫至高权威上的、具有等级观念的家庭法,它们把家庭看作“使人们习惯于命令和服从的最理想场所”,(24)从中看到了自身制度的印证和保障。1804年,波拿巴就曾阻止《民法》的起草者们向自由倾向让步,并强加他自己的观念:独裁专制和执掌管理权的丈夫。(25)甚至到了20世纪中叶还有不少议员在议会中要求给丈夫以更大的权力,他们认为无限缩小一家之长在管理夫妻共有财产中的权力与当时深刻改革政体的设想相违背,因为第五共和国的领导们企图加强执政者的权力以限止议会。(26)掌玺部长阿兰·贝雷费特竟说:“把几百年来的习俗一扫而光使法律发生突变将是危险的。”(27)社会进步使有关婚姻制度的法律不得不改变的情况下,立法者们还是寸土必争,竭力保留哪怕最后一小块阵地,以便卷土重来。最后20年的骤变是由于60年代开始在包括法国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传统权威的文化运动,对社会不同领域中的权威提出挑战,70年代的法国妇女解放运动就是其组成部分之一,矛头直指父权制度,再加上现实生活方式的改变和英、美、德等外国的榜样形成的压力(28)震撼了以往女权运动收效甚微的私人领域。
正因为立法者不甘心彻底变动,故改革后的婚姻制度具有虚伪性和矛盾性。如1907年法律虽给予已婚妇女支配自己工资的权利,但在具体实施中有种种限制,尤其因为她们当时只能在丈夫允许的情况下就业,给予权利的条文在实际生活中就如一纸空文。又如1975年法律规定的“双亲权”是与丈夫仍是未成年子女财产的唯一管理者相矛盾的。在此实施的仍是“父权”,立法者们提出的荒唐理由是第三者(指子女)希望面对他们的只是一个而非两个负责人,那显然是父亲了。他们中的一位毫不掩饰地说:“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在家庭生活中保持丈夫的特权。”(29)再如1965年改革规定妻子对共同财产中不动产和营业资产的处理可表示意见,但实际上这项权利十分有限,因为丈夫掌握着全权,妻子对管理情况的好坏无法知晓;她不掌握了解情况的任何手段。更何况妻子对构成法国家庭主要共同家产的现金和有价证券没有任何控制权。
虚伪性必然导致不合理因素的存在。最大的不合理在于由丈夫管理的家庭共同财产中包括妻子在婚后的个人所获,而她又没有实际的共同管理权,然而如丈夫管理不善而负债,她却要分担一半债务;(30)而且丈夫在管理中的严重错误或舞弊问题只有在共同财产亏空的情况下才能发现,此时妻子也随着一起破产了。又如,在法律中已婚妇女的社会权利要通过丈夫的权利来体现,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是妇女直接与社会保险、家庭补贴、托儿所、学校、医生打交道。一旦丈夫逃避责任或夫妻关系发生危机,妻子就有可能处于绝境。
法国婚姻制度改革的又一个特点表现在法律的滞后性,这是相对于实际生活方式、生活习俗而言的。就是说某些法律的制定是对已经变成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的总结。近代工业社会的形成使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变化,有些旧的法律实际上已名存实亡。立法者之所以改革了婚姻法是因为考虑到“不反映生活习俗的法律将会失去意义而过时”。(31)例如,19世纪以来大批妇女成为职业妇女,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男子上前线,妇女在后方顶替一向为男子垄断的职业岗位,使妇女就职成为不可阻挡之势。可是为了维护合法家庭和丈夫权威,妻子就职要经丈夫同意的条文却迟迟不改,直到1965年才把这早已毫无价值的僵死规定扔进历史垃圾堆。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避孕和堕胎问题。法国鼓励生育的政治家和天主教会在“国家利益”借口下,从人口、宗教、道德、医学等角度提出论据禁止避孕和堕胎。天主教教义认为“婚姻的首要目的……不是完善夫妇双方,而是繁殖和教育新一代”。(32)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法国人口骤降,议会为使出生率增长,竟然于1920年7月13日通过一条极其残忍、极其不公道的刑事法规,这就是刑法317条,要对堕胎和避孕行为加以严惩,哪怕仅仅是意图和宣传。1940-1942年维希政权下,有1.5万宗案子涉及违反刑法317条。1943年一位洗衣女工玛丽─路易丝·吉罗因帮助一些妇女堕胎而被送上断头台。(33)法国解放后,刑法317条并未取消,可无数妇女因不愿生育而到比法国更自由的国家去堕胎或在国内秘密堕胎。由于医疗手段差,往往造成悲剧性的后果,即使如此,妇女们为争取在生育问题上的自主权宁愿冒生命危险。在妇女解放运动期间,包括众多知名人士的343名妇女于1971年4月5日发表“343声明”,声称曾经做过堕胎。(34)1956年自发形成的民间团体“法国家庭计划运动”向前来咨询和求援的妇女提供避孕方法的信息和获取避孕药品的途径,这是冒着被判刑的危险的。上述事实足以说明生活的现实决非法律可阻挡。在各种进步力量的强大压力下,执政者们终于被迫对这个问题公开表态,1965年竞选总统时,密特朗首次宣布赞同取消1920年的“罪恶法律”。(35)法国议会后来分别于1967年和1975年通过不再禁止避孕和允许自愿堕胎的法律,而且又分别于1974年和1982年颁布可予以免费的规定。(36)是不可逆转的生活方式和施以强压的请愿运动迫使立法者去改变法律,以适应社会上业已流行的习惯和行为。
三
六七十年代以后法国婚姻制度的改革似乎确立了夫妻间的平等和不同性别子女间的平等,更有利于个性的自由,对“一家之长”的制度是沉重的打击。改革自然是进步,然而它并没有使现存的生活习惯巩固下来,现实生活又发生了立法者意想不到的变化。所谓平等的婚姻制度并没有像他们想像的那样有一定的吸引力,特别是年轻一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它不屑一顾。80年代出现了以下一些社会现象。
首先,结婚率下降和结婚年龄上升。在200年中法国的结婚率相当稳定,但是自1972年以后有十分明显的下降趋势。1972年结婚的夫妇有41.6万对,到1981年降至31.5万对。单身男子的比例为16%,单身妇女的比例为13%。(37)社会等级越低,单身男子越多;与此相反,单身妇女的人数与社会等级成正比,在高层干部中的妇女有27%为单身。(38)
其次,婚前同居和非婚同居现象增加,在巴黎,不到25岁的无子女的男女同居现象已占有大多数,一般到第一个孩子出生才结婚。此后的发展趋势又进了一步:即使有了孩子但仍然不结婚的比例在上升,如1984年出生的头生孩子有1/4为非婚生子,1/4的非婚同居夫妇有一个或几个孩子,(39)说明非婚生育的新行为模式在发展,传统的合法家庭在减少,在衰落。
最后,甚至已婚夫妇也接受新的观念,从而离婚率从1970年的11.54%上升到1979年的24.2%。单亲家庭越来越普遍,即一个或多个孩子与双亲之一(过去只可能是寡妇或鳏夫,现在有很多是离异的或未婚的)生活在一起的家庭,这样的家庭在1981年有90万个,而其中的80%是母亲在主持。(40)
传统婚姻制度原先具有的合法和标准的价值逐渐在失去,夫妇关系的其他模式已不是罕见现象。他们是年轻人所向往的,更主要是妇女所向往的。妇女是改变婚姻状况的最主要动力。提出离婚的有2/3是妇女,选择同居、非婚生育的,甚至单身生育(无夫妇关系)的也主要是妇女。在婚姻制度变得越来越平等的情况下,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妇女反而拒绝结婚呢?
改革后的婚姻制度仍然没有彻底消除在家庭中男权居上的现象,这是妇女对结婚不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即使在法律上已明文规定给予妇女的权利也未必都能兑现。例如妇女在选择生育自主权上仍然遭到来自社会上保守势力的阻挠。又如“双亲权”在实际生活中得不到保证,在决定子女上什么学校、子女的财产作什么用途等问题上父亲往往不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的责任主要限于家庭内,一旦某项对子女的决定与家庭外的社会发生关系,母亲的权威就几乎没有了。
妇女就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飞速发展,使妇女就业模式发生变化,这是导致她们不愿结婚的另一个原因。1983年就业人数中41.9%是妇女,(41)即使遇到经济危机,妇女失业主要领域在纺织和服装行业。在第三产业和政府部门,妇女就业呈不可逆转之势。1976年第一产业中的妇女约为48万,占就业妇女的5.75%;第二产业中约有200万,占24%;第三产业中约有590万,占70.25%。(42)因此男女角色分工的传统观念,即男子在公共领域、妇女在家庭领域的习俗被妇女所否定,过去的妇女就业以未婚妇女和无子女的妇女或子女已成年的妇女为主,根据统计,以往大部分已婚育龄妇女在25-35岁这一时期中停止工作,这个年龄段的妇女就业呈空缺状态;而在当代,为争取一切领域自主权的现代妇女不甘心被家庭所拖累,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不管是否有子女都继续工作,而且这一年龄段的妇女就业率反而是最高的。如30岁妇女的就业率从1962年的40%上升到1982年的69%。(43)可见妇女就业模式不再像以往那样是选择模式,即要么工作要么结婚和生育孩子,也不是交替模式,即工作─停止工作(生育)─重新工作,而是重叠模式,即既工作同时又组织家庭、生育孩子,从而逐渐接近男子就业模式。有孩子不再是妇女停止工作的理由。重叠模式虽然对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有益,却使妇女疲于奔命,因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男子分担家务劳动在实际生活中十分罕见,双重劳动日使很多妇女对婚姻和生育望而怯步。结婚对男子来说是享受特权,对妇女来说是一种障碍,这障碍体现在由于家庭的牵连使她们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处于不利地位,如在职业范围内的竞争中。妇女就业使婚姻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古老的平衡破坏了,它使妇女经济自主,自然也使她们为争取更广泛的自主权和更强的竞争力而拒绝结婚成为可能。
另一个使妇女有可能拒绝结婚的因素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这个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和发展起来的,目的是保证就业者和他们的家庭在遇到疾病、工伤、失业、年老等自然不幸时有应付的能力。尽管保险制度中存在歧视妇女的方面,但作为就业者或家庭成员的妇女还得到一定保障,例如,就业妇女可享受个人的社会保险,包括医疗保险、产假、老年补助、退休金等;离婚妇女在经过法庭判决后与子女享有生活补助以补贴自己工资的不足;寡妇(即使早已分居)可享受复归的养老金,即若丈夫在退休前死亡,其养老金可转移给寡妇,离婚妇女如果未再结婚也有此权利。(44)旧婚姻制度下的法国妇女没有社会身分,一切就要通过丈夫与社会发生关系,已婚妇女失去丈夫将受到各种自然灾难的威胁,社会保险制度使选择独身、离婚、分居、非婚同居等的妇女都有一定保障,通过结婚建立合法家庭不再成为妇女为得到保护而选择的唯一途径。
教育的普及尤其是有更多妇女接受了高等教育使不少法国妇女有可能摆脱婚姻的束缚。尽管在教育领域中男女的实际平等权仍然存在一定问题,但是自1882年创办第一所女子中学以后,(45)情况在好转。1924年颁布了对男女学生一视同仁的教学大纲,这使男女学生的中学会考及格资格具有同等价值,(46)由于通过中学会考是考入大学的必经之路,这就为女孩子进入高等学校大门开辟了通路。1966年和1970年法国妇女又分别被准许投考技术学校和综合工科大学。(47)根据1982年统计,法国人中取得专业技能合格证书的男子(378.196万)虽比妇女(249.346万)多,但取得业士学位(通过中学会考者)的男女几乎相当,分别是198.48万和195.156万,取得大学毕业证书的妇女(159.018万)与男子(173.392万)相比也少不了多少。(48)虽然到实际生活中在雇用、晋升、待遇等方面仍存在不平等,但妇女的知识水准已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大提高,这增加了她们在与男子竞争中的实力和独立自主的程度。她们不再认为只有结婚才有生活保障,39%不到25岁的女青年认为“如果两个人真正相爱,结婚仅是一种表现的形式”,42%的女大学生持同样的看法。(49)
妇女拒绝结婚是为了反抗婚姻制度中尚存在的父权制残余,她们是否在私人生活中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呢?也许对独身妇女和非婚同居又无子女的妇女来说是如此,否则,只要有了孩子,即使没有结婚,沉重的家务负担仍然落在母亲身上。此外,有可能独身和非婚同居的妇女毕竟不是大多数,如前所说,她们主要是知识层次较高、职业岗位较高的妇女,如教授、高层干部、艺术家、医生、律师等。在已婚妇女中能够做到推迟和控制生育的、能够与丈夫分享“双亲权”以及分担家务和教育子女义务的、能够提出离婚而不至受到生活威胁的也主要是上述阶层的妇女。举例来说,持有大学毕业文凭的妇女平均27岁生第一个孩子,而无此文凭的平均23岁即有头生子。(50)这类妇女基本上在各方面可掌握自己的命运,然而有充分自主权的妇女模式并不是所有法国妇女都能效仿的。由于社会上特别是劳动领域中仍然存在很多性别歧视,同工同酬、公平竞争没有真正实现,妇女社会地位的相对低下必然导致私人领域中地位的低下,无论是作为法律的婚姻制度还是妇女在现实中自己选择的私人生活模式都没有使大多数法国妇女完全、彻底地摆脱家庭中存在的压迫和束缚。法国不平等婚姻制度的地盘已大大缩小,但是离把它彻底埋葬还十分遥远。
注释:
①《民法──根据法理和法学加注》(Code civil,annoté D'après ladoctrine et la jurisprudence),巴黎达洛兹出版社1960年版,第125页。
②马伊特·阿尔比斯图尔和达尼埃尔·阿尔莫加特:《法国女权运动史》,(Maité Albistur,Daniel Armogathe,Histoire de féminisme francais)第2册,巴黎妇女出版社1977年版,第362页。
③阿尔比斯图尔等:《法国女权运动史》,第363页。
④阿尔比斯图尔等:《法国女权运动史》,第361-362页。
⑤阿尔比斯图尔等:《法国女权运动史》,第360-361页;《民法──根据法理和法学加注》,第158-160页。
⑥阿尔比斯图尔等:《法国女权运动史》,第362页;《民法──根据法理和法学加注》第,132,160页。
⑦阿尔比斯图尔等:《法国女权运动史》,第362页。
⑧《民法──根据法理和法学加注》,第465页。
⑨阿尔比斯图尔等:《法国女权运动史》,第363页。
⑩安德烈·米歇尔和热纳维埃伏·泰克西埃:《今日法国妇女地位》(Andrée Michel,Geneviève Taxier,La condition de la Francaised'aujourd'hui)第1册,法国贡梯埃出版社1964年版,第233页。
(11)阿尔比斯图尔等:《法国女权运动史》,第429页。
(12)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妇女问题统计数字》(CNIDF-INSEE,Femmes en chiffres),巴黎1985年版,第10-11页。
(13)《民法──根据法理和法学加注》,第126页。
(14)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妇女问题统计数字》,第11页。
(15)安德烈·勒芒:“有关婚姻制度改革的1965年7月13日法律”(Andrée Lehmann,La loi du 13 juillet 1965 portant laréforme des régimes matrimoniaux),载法国杂志《持有高校文凭的妇女》(Femmes diplomées)第56期,1965年第4季度,第141页。
(16)安德烈·勒芒:“有关婚姻制度改革的1965年7月13日法律”,载法国杂志《持有高校文凭的妇女》第56期,第140页。
(17)安德烈·勒芒:“有关婚姻制度改革的1965年7月13日法律”,载法国杂志《持有高校文凭的妇女》第56期,第140页。
(18)《民法》(Code civil),巴黎1980年版,第51-52页。
(19)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妇女问题统计数字》,第12页。
(20)《民法》,第241-242页。
(21)安德烈·勒芒:“有关婚姻制度改革的1965年7月13日法律”,载法国杂志《持有高校文凭的妇女》第56期,第140页。
(22)1982年法国妇女权利部的调查报告:《生活在不平等社会中的法国妇女》(Les femmes en France dans une société d'inégalité),巴黎法国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95-96页。
(23)安德烈·勒芒:“有关婚姻制度改革的1965年7月13日法律”,载法国杂志《持有高校文凭的妇女》第56期,第140页。
(24)米歇尔和泰克西埃:《今日法国妇女地位》第2册,第235页。
(25)米歇尔和泰克西埃:《今日法国妇女地位》第2册,第236页。
(26)米歇尔和泰克西埃:《今日法国妇女地位》第2册,第235页。
(27)1982年法国妇女权利部的调查报告:《生活在不平等社会中的法国妇女》,第98页。
(28)米歇尔和泰克西埃:《今日法国妇女地位》第2册,第230页。
(29)1982年法国妇女权利部的调查报告:《生活在不平等社会中的法国妇女》,第99页。
(30)《民法》,第249页。
(31)弗朗索瓦兹·皮克:《妇女解放运动及其社会效果》(FrancoisePicq,Le Mouvement de la libération des femmes et ses effetssociaux),巴黎第七大学1987年版,第208页。
(32)西蒙娜·伊夫:“我们的身体属于我们自己”(Simone Iff,Notre corps nous appartient),载论文集《女权运动及其关键问题》(Le fé-minisme et see enjeux),巴黎1988年版,第219页。
(33)西蒙娜·伊夫:“我们的身体属于我们自己”,载论文集《女权运动及其关键问题》,第222页。
(34)弗朗索瓦兹·皮克:《妇女解放运动及其社会效果》,第122页。
(35)西蒙娜·伊夫:“我们的身体属于我们自己”,载论文集《女权运动及其关键问题》,第227页。
(36)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妇女问题统计数字》,第12页。
(37)弗朗索瓦兹·皮克:《妇女解放运动及其社会效果》,第210页。
(38)弗朗索瓦兹·皮克:《妇女解放运动及其社会效果》,第210页。
(39)弗朗索瓦兹·皮克:《妇女解放运动及其社会效果》,第211页。
(40)弗朗索瓦兹·皮克:《妇女解放运动及其社会效果》,第211页。
(41)弗朗索瓦兹·皮克:《妇女解放运动及其社会效果》,第209页。
(42)弗朗索瓦兹·吉罗:《一百项维护妇女的措施》(Francoise Giroud,Cent mesures pour les femmes),法国文献出版社1976年版,第31页。
(43)马尔加莱·马鲁阿尼:“女权运动时代的成果尚存多少?”(Margaret Maruani,Que reste-t-il de nos années de f é minisme),载论文集《女权运动及其关键问题》,第337页。
(44)弗朗索尼兹·吉罗:《一百项维护妇女的措施》,第133-138页。
(45)米歇尔·佩罗:“女权运动的诞生”(Michelle Perrot,Naissance du féminisme),载论文集《女权运动及其关键问题》,第54页。
(46)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妇女问题统计数字》,第11页。
(47)参阅卡罗尔·维特论文:“1960年以来法国妇女地位的变化”(Carole Wright,L'évolution de la condition féminine en Francedepuis 1960),巴黎玛格丽特·杜朗图书馆收藏,1980年。
(48)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妇女问题统计数字》,第67页。
(49)弗朗索瓦兹·皮克:《妇女解放运动及其社会效果》,第112页。
(50)弗朗索瓦兹·皮克:《妇女解放运动及其社会效果》,第15-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