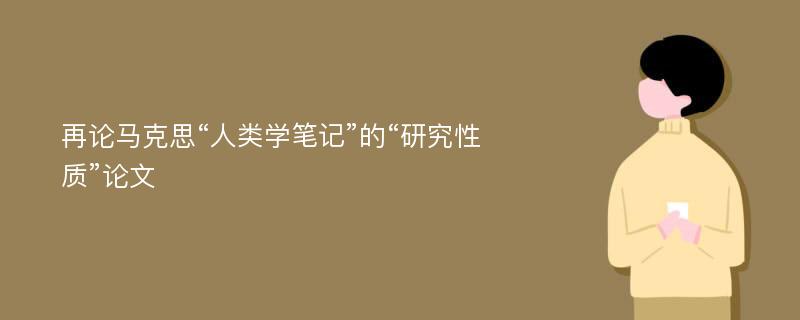
再论马克思 “人类学笔记 ”的 “研究性质 ”*
林 锋
[关键词 ]人类学笔记;研究性质;人类学;唯物史观
[摘 要 ]澄清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与“人类学”的真实关系,正确界定笔记的“研究性质”,对于深刻认识笔记的思想主题及晚年马克思的学术志趣、学术贡献,有着重大的意义。晚年马克思在其“人类学笔记”中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不应定性为实证科学、经验科学性质的“人类学研究”,而应界定为一种唯物史观色彩的“历史哲学研究”。笔记是为了配合晚年马克思一个重要的唯物史观“创新计划”而作的。晚年马克思并不是像摩尔根等人类学家那样去从事什么实证科学色彩的“人类学研究”,而是试图利用当时世界人类学的最新科学成果,创造性地发展唯物史观,系统地探索唯物史观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理论。澄清这一点,有助于还原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真相,深刻理解“人类学笔记”的主题、主旨及晚年马克思学术探索的实质,驳斥西方学界有关“两个马克思”对立的观点。
一、“人类学笔记”的“研究性质”:学界的一种流行见解
晚年马克思曾于1879—1882年对摩尔根、柯瓦列夫斯基、梅恩等人类学家的著作写下五个重要的读书笔记,后人一般称之为“人类学笔记”或“古代社会史笔记”。作为晚年马克思最重要的遗稿之一,笔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笔记于20世纪公开出版后,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和深入探讨,一度成为世界范围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的重点、热点。上世纪后30年(70年代初至90年代末),西方学界、苏联和中国理论界曾先后掀起三次笔记研究的热潮,对笔记进行了力度空前的学术探索,推出了一批具有奠基性、开拓性意义的研究成果。值得一提的是,晚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既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也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早期名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掀起了20世纪世界马克思学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引发了关于“两个马克思”(“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争论的话,那么,20世纪70年代初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全面发表,又掀起了20世纪世界马克思学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引发了新一轮关于“两个马克思”(即所谓“成熟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争论。[注] 林锋:《马克思“人类学笔记”新探》,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7页。 围绕这些笔记,数十年来,国内外理论界作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形成了立场迥异的各种观点及学术范式,其中涉及和包含了关于笔记及晚年马克思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注] 这里借鉴和采用了笔者博士论文《马克思‘人类学笔记’新探”》(第7页)中的相关提法,略有改动。
对厚度为=450 mm锻钢件用2.5探头进行探伤时,用长横孔作起始灵敏度需要在仪器上提高多少dB?在这一灵敏度下发现=320 mm 处有一缺陷波,经衰减8 dB后,该缺陷波为人为标准高度,试求该缺陷相当于多大的长横孔?
在“人类学笔记”研究诸话题中,笔记的“研究性质”[注] 即笔记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的“性质”。 问题占有突出的地位,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特别关注和深入讨论。笔记的许多研究者(包括不少著名学者)都对这一问题予以了关注,表明了学术立场。其中,占学界主导地位、由西方学者首倡的流行见解认为,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从事的是一种实证科学、“经验科学”性质的“人类学研究”;笔记表明了晚年马克思的新动向:修正或超越传统唯物史观立场,放弃《资本论》创作,转向“经验人类学研究”。[注] 在许多国内外学者看来,晚年马克思的“人类学转向”是真实存在、值得关注的,“人类学笔记”从事的是一种实证科学、经验科学色彩的“人类学研究”,马克思与许多早期人类学家一样,都对“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建设做出了贡献。[注] 林锋:《马克思晚年存在一个“人类学转向”吗》,《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这种观点流行甚广,构成学界的主流见解,但并非学界在此问题上的唯一论调。长期以来,学界中一直存有异议。
二、笔记从事的是实证科学性质的“人类学研究”吗?
在系统地质疑学界关于笔记“研究性质”的上述流行论调前,笔者首先作一些“方法论”层面的探讨。人类学原著与“人类学笔记”、人类学家与晚年马克思的“比较研究”,是研究者破解笔记“研究性质”之谜所须从事的一项前提性、基础性工作,甚至是一项“关键性”的工作。这项工作对我们有效澄清和正确判断“人类学笔记”的“研究性质”,消除长期以来学界关于笔记的误解,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上述流行见解在笔记“研究性质”问题上的失误,恰恰是这项“比较研究”工作的缺失所致。通过(作为笔记摘录对象的)五部人类学原著与马克思五个“人类学笔记”之间、摩尔根等人类学家与马克思之间的细致、充分的比较研究,是能够澄清,也足以澄清“人类学笔记”的真实“研究性质”的。
通过原著与笔记的直观比较,我们很容易发现,笔记对相关的人类学原著不过是“摘录”和“注释”的关系,五个笔记均是如此。就基本结构而言,“人类学笔记”主要由马克思对人类学原著带有“选择性”的“摘录”和对人类学原著相关内容所作的“注释”这两部分构成。下面笔者逐一分析笔记与原著这两方面的关系(笔记对原著的“摘录”与“注释”)对判定“人类学笔记”研究性质的学术意义。
通过仔细辨认笔记文本中出现的各处“注释”,可以发现,马克思对人类学原著所作的“注释”,主要是根据其所知的、来自其他学者(比如某些历史学家)的学术知识、学术信息[注] 这些知识或信息通常是某些具体科学研究者“学术研究”的产物。 或(在马克思看来是“可靠的”)学术资料,或者基于他自己的某种观点(其中不少是带有“哲学意味”的理论观点),或他对人类学原著(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中相关资料、相关情况的理解、领会,针对特定的人类学原著中提到的相关事实、相关情况、相关问题甚至相关的词汇,进行具体的阐释、补充、评价、质疑,或以“问句”的形式,提出他感兴趣的问题。需要澄清的是,在作这几类“注释”时,马克思并不是像摩尔根等人类学家那样,基于自己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工作(显然,他没有做过这样的“田野调查”工作)来形成和表达他自己的学术见解。在许多情况下,他依据的不过是来自他人(即其他学者)的“二手资料”(尽管这些“二手资料”在他看来是“可靠的”),而这些“二手资料”也不全是通过所谓的“田野调查”方式获得的。提供这些资料的学者,也往往不是所谓的“人类学家”。即便是在马克思依据自己的某种观点(如上所述,这种观点往往是他带有“唯物史观色彩”的哲学观点)或借助于他自己对人类学原著(比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中相关资料、相关情况的“理解”“领会”,来对人类学原著中的相关资料、相关情况作进一步的解释、阐释或对人类学著作(如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中的说法表示某种“异议”,进行某种“学术评价”时,他也不是基于所谓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来作这种解释、阐释或评价的。可以说,在作上述这些“注释”时,马克思的确是在从事某种“学术研究”(这一点当然是没有“争议”的),但这种“学术研究”却不是以“田野调查”为核心的“人类学式”的学术研究。事实上,在马克思整个的学术生涯中,他从未真正地与“人类学家”的身份“沾边”。不仅在“人类学笔记”中是如此,在之前的学术活动中,亦是如此。笔者注意到,马克思从未自称为“人类学家”,或将他所从事的某项研究宣布为“人类学研究”。“人类学家”的身份其实是后人强加于他的。这种“莫须有”的身份,或许会增添他的“学术荣誉”,提高他的“学术声望”,但终究是不符合事实、站不住脚的。
或许,有读者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如你所说,“摘录”本身并不意味着一种“研究方式”,更不意味着一种“实证科学色彩”的“研究方式”(这一点我们认同),但是,同样如你所说,马克思的笔记除了对原著的“摘录”外,还有不少“注释”和“评论”(尽管其在笔记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后者算不算是一种“实证科学”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呢?对此,笔者的看法是,马克思的笔记对人类学原著的“摘录”当然不意味着一种“人类学研究”(这一点读者容易理解,这里不再赘述),他对原著所作的“注释”及“评论”同样如此。为了确切地说明这一点,笔者需要作一些具体的解释或说明。
研究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可以采用相关分析方法,如果要根据一个或一组变量来估计或预测另一个变量的值,就需要建立变量间的回归方程,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来完成.一般说来,如果用相关分析的方法发现两个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那么可以考虑对其进行回归分析,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两者的依存关系.
首先,马克思各笔记对《古代社会》等人类学原著的“摘录”关系(这是二者最直接、最基本的关系之一[注] 众所周知,对人类学原著的“摘录”占据了五个“人类学笔记”内容篇幅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以致于我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在编译这五个笔记时,均以“┅┅(这里出现的是被摘录的著作的作者的名字——笔者注)《┅┅》(这里出现的则是被摘录的人类学原著的书名——笔者注)一书摘要”的表述方式来称呼这些笔记,比如,在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中,这五个“人类学笔记”的称谓分别是:“‘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1册,1879年莫斯科版)一书摘要’、‘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约翰·菲尔爵士《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1880年版)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75年伦敦版)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年伦敦版)一书摘要’(参见《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一书的 “目录”)”。 )清楚、直观地告诉我们,马克思在各笔记中根本不是像摩尔根等人类学家那样,在从事什么“实证科学”色彩的“人类学研究”。任何熟悉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研究者都知道,在各笔记中,占据了绝大部分内容篇幅的,正是他对人类学原著相关内容的“摘录”。马克思对人类学原著所作的“注释”,在各笔记中只占很小的比重。很明显,“摘录”(说得直白些,就是直接“摘抄”他人的研究成果)本身并不意味着一种“研究方式”,更不意味着一种“实证科学的研究方式”。笔者从未听闻,“人类学研究”(笔者这里说的是一种严肃的、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可以靠“摘录”这种简单的方式来实现,或者说,“摘录了”人类学家某一著作中的相关内容,就是在从事或完成一种“人类学研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任何人都有“资质”从事人类学研究,并自诩为“人类学家”了。情况真的是这样吗?了解“人类学”这门学科的研究者,或许都知道,“人类学”作为一门典型的“实证科学”,有其规范化的、较为严谨的研究范式,它与其他关于“人”的学科(譬如生理学、医学、伦理学、哲学等)的差异,就在于这门学科研究“人”本身的独特视角、独特方法。[注] 参见王东、林锋:《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初答叶志坚先生》(《东南学术》2006年第2期)中的相关说法,有改动。 众所周知,“田野调查”这种实证研究方法,是人类学科学研究的基石。在这门学科的构成要素中,“田野调查”这种研究方法对“人类学”最具“标志性”、“象征性”意义,甚至是人类学成其为“人类学”的基本条件。对此,英国人类学家塞利格曼精确地阐释道,[注] 这里引用的塞利格曼的论断,转引自王东、林锋:《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初答叶志坚先生》,《东南学术》2006年第2期。 “田野调查工作之于人类学就如殉道者的血之于教堂一样。”[注] 哈维兰:《当代人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页。 我国著名人类学家童恩正也指出,[注] 这里引用的童恩正的看法,转引自王东、林锋:《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初答叶志坚先生》,《东南学术》2006年第2期。 当代的文化人类学已经植根于田野调查之中,只有通过田野工作,人类学家才得以获得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验证理论的假设。[注]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9页。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之所以被称作并被公认为“人类学著作”,首要原因便是,这一著作是基于“田野调查”这种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而写成的科学作品。马克思从未做过类似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工作,他的笔记主要是摘录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研究成果。由此看来,称马克思为“人类学家”,将笔记所从事的研究的“性质”定位为“人类学实证科学研究”,是十分不妥的,甚至是过于夸张的。当然,不少研究者自觉地赋予晚年马克思“人类学家”的学术身份,客观上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提高其学术声望是颇有“意义”的。不过,这种宣传也要立足于“实情”,即尊重马克思学术研究的实际情形。否则,人为的“拔高”“美化”,不仅不能产生预期的正面效果,反而导致了某种“消极”的后果。
澄清上述事实,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笔记的理论性质和历史地位,科学评价晚年马克思的理论探索及其贡献,驳斥学界的错误流行见解,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以往在国内外学界(特别是西方学界)中广泛流行的所谓“马克思晚年人类学转向说”“断裂说”等说法,正是建立在对笔记“研究性质”的误读之上的,试想,倘若笔记的“研究性质”并非什么“实证科学性质的人类学研究”,而是“唯物史观性质的历史哲学研究”,那么,所谓“马克思晚年‘放弃了’唯物史观立场和经济学研究,转向了‘实证科学性质’的人类学研究”的流行说法就失去了基本的事实依据和立论基础,而用“哲学—经济学—人类学”来概括马克思毕生理论活动演变轨迹,将“人类学”作为“马克思理论活动最后一站”的说法也同样难以自圆其说了;澄清笔记的这一“研究性质”,有助于我们恰当说明马克思前后期理论探索的连贯性、统一性,驳斥西方学界炮制的“两个马克思”(“晚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或“中年马克思”)对立的神话,恢复笔记本来面目和晚年马克思思想原貌。[注] 林锋:《马克思“人类学笔记”新探》,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17页。
用户负荷具有区域性、时变性、外部气象环境敏感性等特点,配变重过载、低电压等异动状态导致的停运故障时有发生,影响用户用电体验,且由于配网监测终端数据传输的滞后性,故障处理只能采用事后抢修手段,无法消除配网设备异常对客户服务已造成影响事实。
在上文中,笔者依据对“人类学原著”与“人类学笔记”关系的分析,揭示了马克思的学术研究方式与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实证研究方式”的本质区别。在笔者看来,人类学家与马克思,二者的“学术研究方式”是截然不同的。绝不能仅仅因为“晚年马克思摘录了人类学家的著作”,就将二者的研究方式混为一谈,将马克思混同为所谓“人类学家”。如上所述,肯定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重大价值,推崇晚年马克思的学术贡献,不一定要通过将马克思打扮为“人类学家”、将笔记定性为“人类学著作”这种特定的方式来实现。必须澄清的是,摩尔根与马克思在“学术研究”上的关系,不是人类学界“两位同行”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马克思从未认为他与摩尔根一样,也是一位“人类学家”),而是从事“历史哲学研究”的“哲学家身份”的马克思(这里附带说一句,马克思在其学术生涯中,多次对自己的“哲学家”身份加以肯定或推崇)和从事“实证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身份的摩尔根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是“哲学家”身份的马克思借鉴、吸收“人类学家”身份的摩尔根等人的科学研究成果,借以进行相关的历史哲学问题的思考,从而创造性地发展唯物史观,实现唯物史观之“创新”的关系。[注] 参见林锋:《马克思晚年笔记和人类学的关系》,《东南学术》2004年第3期;林锋:《马克思晚年存在一个“人类学转向”吗》,《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王东、林锋:《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初答叶志坚先生》,《东南学术》2006年第2期;王东、林锋:《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与西方学者的学术对话》,《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0期;林锋:《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二答叶志坚先生》,《东岳论丛》2007年第4期;林锋:《马克思“人类学笔记”新探》,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15页。
三、关于笔记与“人类学”、马克思与人类学家的关系:三个重要结论
对于“人类学笔记”与“人类学”、马克思与人类学家的真实关系,应从三个方面来把握。
其一,不能将“人类学笔记”与人类学实证科学著作、马克思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和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实证科学研究”不加区分,混为一谈。“人类学笔记”对“人类学”及其“科学成果”(以摩尔根人类学实证科学著作《古代社会》为代表)的关系,是前者借鉴、吸收后者的实证研究成果,以此作为(哲学研究的)科学基础、学术基础,来进行相关的历史哲学问题的思考,以便创立历史哲学的新理论,实现唯物史观“理论创新”的关系。“人类学笔记”所从事的绝非与人类学著作完全一样的“人类学实证科学研究”,而是与后者有紧密联系但在学科性质上又截然不同的、具有唯物史观色彩的“历史哲学研究”;“人类学笔记”实质上是一种“历史哲学性质”的笔记,是为马克思的“哲学思考”“哲学研究”服务的。[注] 关于这一点,笔者的博士论文(《马克思‘人类学笔记’新探”》)及一些相关论文(比如:林锋:《马克思晚年笔记和人类学的关系》,《东南学术》2004年第3期;林锋:《马克思晚年存在一个‘人类学转向’吗》,《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均有相应的解释或说明。 绝不能不加辨析、不作区分、“不假思索”地将笔记视为“人类学著作”,将马克思描绘成所谓的“人类学家”,并断定马克思晚年存在一个所谓的“人类学转向”。
基础教育课程和教学改革提出了“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的新理念,这就要求教师在使用教材时要具有灵活性和自主性。教材只是为了达到课程目标而使用的数学材料,并不是课程的全部。教材的优点是标准、规范,但这种规范往往会约束教师的创造力,导致教师照本宣科地“教”教材,而不是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来全面实现课程标准所规定的目标,从而影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现代教育理念要求教师要驾驭教材,那么如何驾驭教材呢?
其二,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实证科学研究及其成果是晚年马克思及其“人类学笔记”正确认识原始社会及其发展史的基本依据,此外,它们还是马克思及其笔记进行相关的“历史哲学问题”的思考,实现唯物史观“学术创新”必不可少的科学基础、科学条件。在笔者看来,我们当然不能无视笔记与人类学科学著作的界限、差异,将二者“混为一谈”,但另一方面,我们亦不能否认二者间的“密切联系”,特别是不能否认后者对晚年马克思科学认识原始社会及其进程、从事相关“历史哲学研究”的重大科学意义。读者很容易看出,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是鲜明地将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史研究成果(《古代社会》)作为主要的科学基础和科学依据,来认识“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被马克思高度赞赏和推崇的摩尔根人类学研究成果,还成了他评价其他学者(关于原始社会史的)学术观点的主要依据。[注] 参见林锋:《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二答叶志坚先生》,《东岳论丛》2007年第4期;王东、林锋:《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与西方学者的学术对话》,《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0期;王东、林锋:《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初答叶志坚先生》,《东南学术》2006年第2期。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人类学家摩尔根等人提供的实证科学事实、科学资料,晚年马克思根本不可能进行相关的历史哲学重大问题的思考,更不可能萌生“根据世界人类学最新科学成果来验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并从‘哲学高度’全面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系统创立唯物史观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理论”[注] 林锋:《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地位新界定》,《东岳论丛》2010年第1期;林锋:《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新探》,《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 的宏伟计划、宏伟构想(这一计划或构想被恩格斯在其晚年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部分地实现了[注]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一版序言的开篇之处,开宗明义、直言不讳地谈了该书与晚年马克思及其“人类学笔记”的关系:“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我这本书,只能稍稍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不过,我手中有他写在摩尔根一书的详细摘要中的批语,这些批语我在本书中有关的地方就加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页)。在晚年恩格斯的心目中,《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正是为实现马克思的遗愿(“根据世界人类学最新科学成果来验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并从‘哲学高度’全面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系统创立唯物史观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理论”)而作的。 )。摩尔根的人类学科学研究及其成果,不论是对验证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而言,还是对深化、发展他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而言,都具有特别重大的学术意义。这一点不可否认。
其三,笔记作为一种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思维方式”及晚年马克思对“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深刻见解的“历史哲学笔记”,对现代人类学家从事相关科学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学术意义。对于这一点,我们亦不难理解。笔记关于“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探索这一核心问题,是笔记首要的学术志趣,构成笔记的主题[注] 林锋:《再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主题》,《江汉论坛》2009年第8期。 )的基本思想与治学方法,完全可能对现代人类学、历史学探索相关问题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或具有某种“方法论”上的意义。在笔者看来,虽然笔记与《古代社会》等“人类学著作”不是同一学科层面的著作,但作为“哲学著作”的“人类学笔记”与人类学实证科学著作之间“相辅相成”“相互启发”,完全符合常理。事实上,“哲学”与“具体科学”之间,往往就是这种“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二者之间这种关系的存在,已为我国学界不少著名学者所肯定)。就“人类学笔记”与“人类学著作”最初的关系而言,是前者受到后者的启发,但笔记反过来又给予后来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某种“方法论”层面的指导,笔记所表达的某些基本观点成了现代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继续从事“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可借鉴的“思想资源”。这两个方面既符合事实,亦符合常理,符合人类学术史的一般逻辑,不足为奇。
On the “Nature of Research ”of Marx ’s “Anthropological Notes ”
Lin Feng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Key words ]Anthropological Notes; nature of research; anthropolog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bstract ]Clarifying the tru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s “Anthropological Notes” and “Anthropology” and correctly defining the“nature of research”of those not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Marx’s academic interest and academic contribution in his later years. In his later years, Marx’s academic research in his “Anthropological Notes” should not be characterized as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f empirical science and empirical science, but should be defined as a “historical philosophy stud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Notes were made in line with Marx’s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novation plan” in his later years. In his later years, Marx tried to use the latest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of the world’s anthropology at that time to creatively develop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systematically explore and formulate the theories about the primitive society and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Clarifying this point will help to restore the truth of the history of Marxist thought and refute the views of the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on the“two Marx”opposition.
[作者简介 ] 林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与国际传播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年马克思五个重要笔记新探讨”(项目号:11CZX01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孔 伟 ]
标签:人类学笔记论文; 研究性质论文; 人类学论文; 唯物史观论文;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与国际传播协同创新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