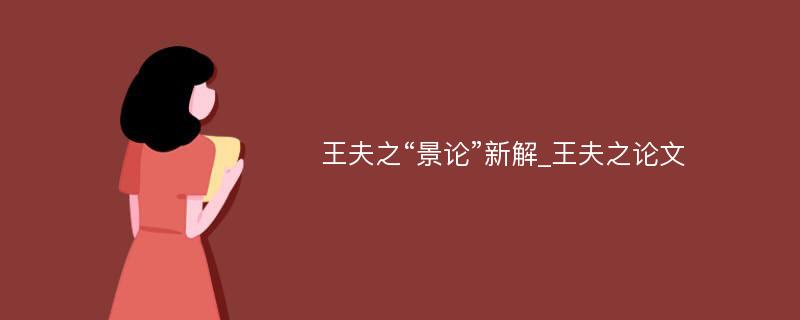
神理凑合,自然恰得——王夫之“情景”论新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景论文,新解论文,自然论文,王夫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0)06-0034-04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湘西石船山下,故又称船山先生,是我国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史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富有独创性的文学理论批评家。王夫之的著述非常丰富。岳麓书社1988年至1996年间陆续编辑出版的《船山全书》收录王夫之的著作67种,共370余卷,涉及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各方面。王夫之的学术思想在其生前就受到一些人的关注,死后对其学术思想进行阐述的更是代不乏人,至今已经形成一门很有影响力的“船山学”。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对王夫之学术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哲学、史学等方面。近20多年来的王夫之诗学研究,不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在研究中,学者们都认识到王夫之的诗学思想丰富、深刻、富于创见,在中国诗学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的甚至认为王夫之诗学是中国古典诗学的总结(如叶朗),有的把他与黑格尔相提并论(如张世英)。
王夫之的诗学思想是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因此要了解其诗学思想,首先必须了解其哲学思想。可以说,王夫之的诗学观是其哲学思想在诗学领域里的延伸。他的诗学思想之所以深刻、富有独创性,也正在于此。王夫之的情景论就体现了这个特点。
中国诗学情景理论始自先秦。在《诗经》中有许多通过自然景物来抒发内在情感的优秀诗篇。这些创作实践是理论上自觉的坚实基础。《礼记·乐记》提出的“物感”说就蕴涵着情景理论的信息:“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初,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音乐由人心而生,人心又由物的触发而动。“物感”说在魏晋时代引起了文学理论家的注意,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陆机《文赋》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钟嵘《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这些论述虽然没有提出“情景”这一对范畴,也没有对情与景的关系作更深入探讨,但是明确揭示了诗歌是主观情感在客观景物的触发下所产生的。唐代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了情、景的观念:“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但最早提出情、景之名作为批评观念的是南宋的黄异。他在《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中说:“史邦卿,名达祖,号梅溪。有词百余首,张功父、姜尧章为序。尧章称其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从宋代到明代,情景理论成为许多批评家关注的中心。但是在论述情与景的关系时,大部分都是从诗歌的外部形式结构方面来谈的,如宋代范晞文《对床夜话》卷二云:“老杜诗:‘天高云去尽,江回月来迟。衰谢多扶病,招邀屡有期。’上联景,下联情。‘身无却少壮,迹有但羁栖。江水流城郭,春风入鼓鼙。’上联情,下联景。”又如明代胡应麟《诗薮》云:“作诗不过情景二端,如五言律,前起后结,中四句二言景二言情,此通例也。”(内篇卷四)从诗歌的外部结构形式来探讨诗歌的创作,应该说对诗歌创作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能方便初学者迅速掌握一些作诗的基本规律。但是这种理论在明代发展到极致,许多人创作不管自己的真情实感,而是从当时编辑的一些“类书”里寻章摘句,拼凑成诗文。对情景理论的探讨就有这种趋向。当然也有理论家能够不同凡俗,提出新的见解。谢榛就是如此。他在《四溟诗话》中对情景的探讨可以说是发前人所未发。他说:“作诗本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浩无涯矣。”“诗乃模写情景之具,情融乎内而深且长,景耀乎外而远且大,当知神龙变化之妙,小则入乎微罅,大则腾乎天宇。”谢榛认为诗歌中的情与景不是一种外在形式的机械拼合,而是如“神龙”一样“元气浑成”的内在有机融合。在形式主义盛行的明代文坛上,谢榛的理论称得上是空谷足音。而王夫之在前人的基础上,完成了对情景理论的全面总结。
针对前人“分疆情景”,把情与景割裂开来,只着眼于语句形式的理论,王夫之批评说:
近体中二联,一情一景,一法也。“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云飞北阙轻阴散,雨歇南山积翠来。御柳已争梅信发,林花不待晓风开。”皆景也,何者为情?若四句俱情而无景语者,尤不可胜数。其得谓之非法乎?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惟意所适。截分两橛,则情不足兴,而景非其景。且如“九月寒砧催木叶”,二句之中,情景作对;“片石孤云窥色相”四句,情景双收:更从何处分析?陋人标陋格,乃谓“吴楚东南坼”四句,上景下情,为律诗宪典,不顾杜陵九原大笑。愚不可瘳,亦孰与疗之?[1](p75-76)
情与景的结合应该是“惟意所适”。如果用“一情一景”、“上景下情”或“先情后景”的“死法”来限定,不顾情与景的内在联系,那是“愚不可瘳”的“陋人陋格”。情与景不可“截分两橛”,二者互涵互摄,“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1](p33)。“珀芥”指琥珀和芥子,能相互吸引。情与景就像珀芥一样,互相作用,不可分离。
王夫之把情景结合的方式分为二种:
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景中情者,如“长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栖忆远之情;“影静千官里”,自然是喜达行在之情。情中景尤难曲写,如“诗成珠玉在挥毫”,写出才人翰墨淋漓、自心欣赏之景。凡此类,知者遇之;非然,亦鹘突看过,作等闲语耳。[1](p72)
一种是“景中情”,在看似冷静客观的景物描写中流露着主观的情意;一种是“情中景”,以写情为主,但能从中体会到鲜明的客观形象。这两种方式只能属于“巧者”。最高境界的是情与景结合“妙合无垠”,达到这种水平才是“神于诗者”。王夫之最为欣赏的是情与景的结合没有规律可寻,心中目中与相融洽、“神采即绝”的作品。他极为称赏谢灵运的诗作,说:
言情则于往来动止、飘渺有无之中,得灵蠁而执之有象;取景则于击目经心、丝分缕合之际,貌固有而言之不欺。而且情不虚景,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神理流于两间,天地供其一目,大无外而细无垠。落笔之先,匠意之始,有不可知者存焉。[2](第十四册,p736)
这段话对于深刻理解王夫之的情景理论十分重要。“言情则于往来动止、飘渺有无之中,得灵蠁而执之有象”,这一层说的是“情”的特点。“蠁”,《说文》解释为“知声虫也”。萧驰认为在这里应该是“通神”的意味。[3](p57-58)萧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扬雄《羽猎赋》云:“昭光振耀,蠁曶如神。”那么“得灵蠁而执之有象”就是用“象”把“神”表现出来。那么“神”是什么呢?它与“情”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涉及王夫之哲学思想中关于“气”的看法。
“气”是王夫之对于宇宙万有的终极说明。他说:“天人之蕴,一气而已。”[2](第六册,p1052)王夫之认为,宇宙间充满了气,宇宙中只有气才是唯一的存在。他说:“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2](第十册,p26)太虚就是茫茫宇宙,茫茫宇宙中看起来什么也没有,但是太虚并不是虚无,其间充满了气,只是人们看不见而已。“人之所见为太虚者,气也,非虚也。虚涵气,气充虚,无有所谓无者。”[2](第十册,p30)“虚空者,气之量;气弥纶无涯而希微不形,则人见虚空而不见气。凡虚空皆气也,聚则显,显则人谓之有;散则隐,隐则人谓之无。”[2](第十二册,p23)能看见的世间万物,我们称之为“显”,而它们只不过是气之“聚”;而我们看不见的太虚之气,只是因为“散”。太虚之气为有,而不是无。王夫之用“诚”来规定气的这种特征:
宇宙者,积而成乎久大者也。二气絪缊而健顺章,诚也;知能不舍而变合禅,诚之者也。谓之空洞而以虚室触物之影为良知,可乎?[2](第十二册,p420)
诚就是实有的意思。王夫之以“实有”来规定气,在中国哲学史上把对“气”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他之前,张载和王廷相都把气作为一种具体的物质。如张载说:气“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易》所谓‘絪缊’,庄生所谓‘生物以息相吹’、‘野马’者与”[4](p8)。张载把气理解为“生物以息相吹”,如“野马”一样奔腾的气体。又如王廷相说:“气虽无形可见,却是实有之物。口可以吸而入,手可以摇而得,非虚寂空冥无所索取者。”(《内台集·答何柏斋造化论》)认为气是“口可以吸而入,手可以摇而得”的一种具体的物质。王夫之认为气是“实有”,而不是某种具体的物质。这是对宇宙本体一种更高的概括。
宇宙元气,无形而实有,具有极“清”的特点。张载说:“凡气清则通,昏则壅,清极则神。”[4](p9)王夫之继承张载的观点,亦称之为“神”:“气之未聚于太虚,希微而不可见,故清;清则有形有象者皆可入于中,而抑可入于形象之中,不行而至神也。”[2](第十册,p31)由于“气”具有这个特点,所以其弥纶万化而不见其迹,化育万物而不见其功。这也就是天“无大不届,无小不入”的特征。太虚之气运动不息,变化无穷,其最终的动力来自于“神”:“变者,化之体;化之体,神也。”[2](第十二册,p84)“天之气伸于人物而行其化者曰神。”[2](第十二册,p79)宇宙间气的运行是由“神”来主宰的。在太和絪缊之中,有气有神,而“神者非他,二气清通之理也”。[2](第十二册,p16)“神”是气所以变化的原因,“化”是气运动的过程。“神者化之理,同归一致之大原;化者神之迹,殊涂百虑之变动也。”[2](第一册,p592)王夫之把气的这种运动变化的规律称之为“神化”:“神化,形而上者也,迹不显。”[2](第十二册,p79)
王夫之认为,他所说的“神”并不是什么让人感觉迷幻虚无的东西:“神,非变幻无恒也,天自不可以情识计度,据之为常,诚而已矣。”[2](第十二册,p68)“神,非变幻不测之谓,实得其鼓励万物之理也。”[2](第十二册,p70)而是“其妙万物而不主故常者,则谓之神”。[2](第一册,p519)宇宙之道(也就是气之道、天之道)并不是遵循着某种固定不变的规律,没有“定理”、“定数”,人们也不能以某种预设的“定理”、“定数”来揣测宇宙的运动变化之道。这就是“神”。王夫之说:
“神”者,道之妙万物者也。易之所可见者象也,可数者数也;而立于吉凶之先,无心于分而为两之际,人谋之所不至,其动静无端,莫之为而为者,神也。使阴阳有一成之则,升降消长,以渐而为序,以均而为适,则人可以私意测之,而无所谓神矣。[2](第一册,p531)
“象”与“数”产生之后都是固定不变的,而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却没有一定之规。这是《易》之道,也是宇宙之道,因为“《易》者,天地固然之撰也”。[2](第一册,p1054)《周易》之道和宇宙精神是相互契合的。天地的变化是“以不齐而妙,亦以不齐而均”。[2](第十二册,p447)“天地非一印板,万化从此刷出。”[2](第十二册,p447)这就是“神无方,易无体”,“神行气而无不可成之化,凡方皆方,无一隅之方。《易》六位错综,因时成象,凡体皆体,无一定之体”。[2](第十二册,p77)王夫之因此批评说:
京房八宫六十四卦,整齐对待,一倍分明。邵子所传《先天方图》,蔡九峰《九九数图》皆然。要之,天地间无有如此整齐者,唯人为所作,则有然耳。圜而可规,方而可矩,皆人为之巧,自然生物,未有如此者也。《易》曰:“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可典可要,则形穷于视,声穷于听,即不能体物而不遗矣。唯圣人而后能穷神以知化。[2](第十二册,p440)
所谓“典”、“要”,就是以一种固定僵死的先验之规律、法则来看待宇宙无穷之变化,用王夫之的话来概括就是“执理以限天”[2](第十二册,p45),“执一以强贯乎万”。[2](第一册,p50)王夫之认为不能用某种静止固定的“理”来理解“神”,“神”是在流变不居的时间中来体现其“妙万物”之功能,只有“与时偕行”才能“神应无方”:
天之神化惟不已,故万变而不易其常。伯夷、伊尹不勉而大,而止于其道,有所止则不能极其变;唯若孔子与时偕行而神应无方,道在则诚,道变则化,化而一合于诚,不能以所止测之。[2](第十二册,p86)
因此,在王夫之的思想里,“神”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作为名词,指至清之宇宙元气;二是作为形容词,指元气化生万物之“不主故常”的特点。
王夫之认为,人和物都禀受(天)气而生,但是人作为“秀而最灵者”[2](第七册,p105),其与物在受命之时和受命之后还是有区别的。气聚而为物,即为形碍,此后就永远不能再与元气相通,所以有形质的物在受命之始即为受命之终,终其一生而不再有什么变化。而人不同,人禀气而生,既有形质,同时又因为人有“心”。心为虚,其能保有太虚至清之气而不使之形碍。这就是人之“神”:“气聚于太虚之中则重而浊,物不能入;不能入物,拘碍于一而不相通,形之凝滞然也。其在于人,太虚者,心涵神也;浊而碍者,耳目口体之各成其形也。”[2](第十二册,p31)“心之神居形之间,惟存养其清通而不为物欲所塞,则物我死生,旷然达一,形不能碍,如风之有牖即入,笙管之音具达矣。”[2](第十二册,p32)
人心之“神”是人区别于物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因为如此,人生之后,其“神气”与太虚氤氲之气就能不断地互动往来。人不断地受天之命,不断地造命,不断地以天之至清之气来变化自己的气质。人死后,其气复归于天虚。人如果努力作为,在其一生中使自己的“气”不变浊,保其清刚之气归于太虚,那么他就是天之克肖子。而动物不同,动物“有天明而无己明”,[2](第六册,p850-851)也就是其受命之后,终其一生不能超出这些天赋的能力。
现在我们再回到前面王夫之关于情景的那段话。王夫之在《诗广传》中有这样一句话:“命以心通,神以心栖,故诗者,象其心而已矣。”[2](第三册,p485)这句话与“得灵蠁而执之有象”说的是一个意思:诗歌就是用“象”把内心之“神”表现出来。因为“神以心栖”,而“心统性情”,所以“情”也如心之“神”一样,缥缈无定。在这段话里,很多人把其中的“神理”看作是一个偏正结构的词组。其实在这里它是由两个名词组成的并列结构的词组:“神”和“理”。我们已经知道“神”的含义,那么“神理”之“理”指的是什么呢?王夫之说:“万物皆有固然之用,万事皆有当然之则,所谓理也。乃此理也,唯人之所可必知,所可必行,非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而别有理也。”[2](第七册,p377)“凡言理者有二,一则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一则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二者皆全乎天之事。”[2](第六册,p716)
理有物之理和(人)性之理的区分。很明显,“神理”的“理”指“物理”,指物体的属性。“取景则于击目经心、丝分缕合之际,貌固有而言之不欺”,说的就是客观事物的“理”。对于客观事物之“理”,应该按着其所“固有”的情况真实反映,“言之不欺”。对于在诗中描绘客观事物如何才是得“物理”,王夫之举了《诗经》中的一些句子来说明。他说:
苏子瞻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体物之工,非“沃若”不足以言桑,非桑不足以当“沃若”,固也。然得物态,未得物理。“桃之夭夭,其叶蓁蓁”,“灼灼其华”,“有蕡其实”,乃穷物理。夭夭者,桃之稚者也。桃至拱把以上,则液流蠹结,花不荣,叶不盛,实不蕃。小树弱枝,婀娜妍茂,为有加耳。[1](p17)
王夫之认为“沃若”只是写出了桑叶的表面状态,还没有深达其内在的“理”,而“夭夭”则不仅得“物态”,还得“物理”。因为“夭夭”写的是小桃树,也只有小桃树才“夭夭”。
“神”和“理”分别与“人”和“物”对应。王夫之说:
天地之生,莫贵于人矣;人之生也,莫贵于神矣。神者何也?天之所致美者也。百物之精,文章之色,休嘉之气,两间之美也。函美以生,天地之美藏焉。天致美于百物而为精,致美于人而为神,一而已矣。[2](第三册,p513)
“精”,《说文》曰:“精,择也。”指优质纯净的米,后来引申为物质的精华。萧萐父、许苏民在其合著的《王夫之评传》中认为,“理”在王夫之的美学思想中相当于“精”。[5](p560)其说甚是。“神”和“理”都是天之所致的结果,其源本一。
所以王夫之的情景理论是以他对“神”“理”的理解为基础的,“落笔之先,匠意之始,有不可知者存焉”。“不可知者”是什么?那就是“神”。情与景的浑然无迹,那就是“神理凑合,自然恰得”:
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青青河畔草”与“绵绵思远道”,何以相因依,相含吐?神理凑合时,自然恰得。[1](p63)
孙筑瑾先生把“神理凑合”解释为“spirit(of feelings)and principles(of objects)united in harmony”,[6](p1149)也就是情与景的融合,而且这种融合是一种动态的融合(dynamic fusion)。[6](p152)这是符合王夫之的原意的。[7]戴鸿森先生说:“‘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二语,可看作船山论诗最重要的美学公式。质实而言,即情、景之间必须有思理、意象上的投合,毫无勉强搬凑的痕迹。”[1](p65)戴先生看到了王夫之的情景理论与“神理”之间的联系,但他对“神理”的理解很显然语焉不详。
[收稿日期]2010-0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