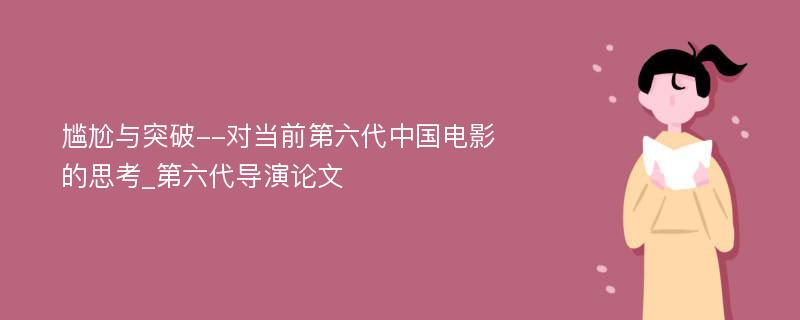
尴尬和突围——省思当下中国第六代电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第六代论文,尴尬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633(2004)03-128-03
本文所谓中国第六代电影,是从文化的角度言,意指一个文化姿态、创作风格相对一致,在20世纪90年代浮出水面并逐渐走上前台,既包括一般认为构成其主体的1985级北京电影学院的一批人,也含与他们同时活跃于当下中国影坛的诸如冯小刚的电影。总的来说,这一群体电影的具体情况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同一个人的作品也有阶段性变化和差异。但作为一个电影现象,他们还是呈现了某些文化特征、美学追求、艺术特征的总体的可把握性,诸如人们常提到的个人化、边缘性、写实性、都市性,对文化转型期中
国青年(尤其是都市青年)的生存状态的捕捉和生命体验,不无夸张的电影语言,与主流
电影美学和电影规范的疏离等等。在这里,笔者也是把他们看作当代中国影坛的一种引
人注目的电影文化现象,进行文化批评。
一、电影危机是精神危机
在一个价值失衡的时代,痞子就会成为英雄。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如此的繁华又如此地贫瘠,如此地喧哗又如此地沉默,如此地高亢又如此地迷茫。也正因如此,才向这个时代的电影艺术家们提出了尖锐的课题:关注人的生存,负起道义的责任,维护起码的人道和正义。
然而,在第六代的中国电影中,我们看到的却是电影人匮乏自己的信仰和价值立场,习惯于依附外在的权威(如“17年”时期的“电影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文革期间更成为帮派政治斗争的工具),而一旦这个权威瓦解了,便普遍陷于精神的迷惘和价值的混乱之中,于是他们便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向外取悦大众,也就是“媚俗”,二是向内自娱自慰,萎靡自己也亵渎着艺术。而这,正是我们从第六代电影中所看到的景象。
先来看“媚俗”,这一方式的典型样板就是冯小刚的电影。冯氏电影的最醒目特性就是“调侃”,即取消生存的严肃性,将沉重的人生化为轻松的一笑,支撑它的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式的“无知者无畏”。它不肯定什么也不否定什么,语言和游戏的快感就是一切,从而也拒绝生命的批判意识,还把承担本身化为笑料加以嘲弄,说到底是趣味的世俗和生命的孱弱。它们迎合的是大众的麻木看客心理,把生活和生命中本该经历和正在经历的苦难化做毫无重量的傻笑,于是,“好好活着”成了必然的结论,大众的宣泄和意识形态的诡计在这里得到奇妙的混合,共同上演着轻浮艺术、伪装生活、背向良知的假面剧,这与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有相同的功效,与当今活跃于电视荧屏的所谓“情景喜剧”走的是一个路子。
而所谓“自娱自慰”,代表就是第六代的某些片子,它们热衷于自我情感的把玩,个体经验的书写,对历史、人类、社会等“宏大叙事”的躲闪和避让,其结果就只能是精神的萎靡和艺术精神的阙如。在第五代导演那里,还是主体性张扬,是影片的内涵层大于叙述层,至少是能指和所指的对称或呼应。而在第六代导演这里,自我意识是个体化的,主体精神是萎缩甚至分裂的,影片的内涵层与叙述层则是基本相当的,甚至可能小于叙述层。常常呈现为一种拼贴式的叙事风格,如片段的或多线索的故事,暖昧的人物关系,摇晃的影像、不规则的构图等等。尤其第六代电影中的主人公大都或者是“活着就好”的琐屑的个人,或者是疏离社会主流的“边缘人”,共同特征是他们游离于社会体制,按自己的无所谓的生活态度生活,以“调侃”来掩饰内心的极度焦虑,也就成为典型的人物形象标识。只是,与第五代导演的群体焦虑、民族焦虑不同,他们的焦虑是个体的、感性的、一己的,如《阳光灿烂的日子》,背景是整个国家民族的伤痛和混乱、迷茫和焦虑,而对于作者和片子中的人物来说,却完全是他自己所记忆和体验到的一段成长经历,是“个人”对历史的感知和书写,而不是社会政治视角观照之下的“伤痕”或“反思”。
无论是“调侃”还是“自娱”乃至自怜,如果追问到极致,就是对“什么是艺术精神”的理解问题,如果我们仍然承认电影是艺术,仍然在艺术的名义下观照电影,那就有一个“在一个缺少诗意的时代,诗人何为”的问题,而恰在这一问题上,第六代电影现象经不起拷问。因为,“调侃”和“自娱”实际上来自于一个共同的生活态度,那就是“游戏”人生,但对什么是“游戏”,我们的导演们没有理解。
在德国古典美学家席勒那里,游戏是弥合人性分裂的途径,是真正人生的体现,涵盖了人生的全部丰富体验,而我们却把它找照中文的字面意义解读成“玩”,并延伸为“逃避”和“解脱”。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是用游戏来解释语言,语言就是对语言的使用,如同按照规则所进行的游戏,在言说之外,并无什么语言的本质,而充分使用语言,就可以充分显示出语言的本质和意义。人生同样如此,人生并不是没有意义,而只是说,人生的意义在于人的生存活动中,人的最高本质即是在自己的生存活动中为自己立法,为自己创造意义。这样的原则用于解释艺术,凸现的恰恰是艺术创造的严肃性和神圣性。而中国的“玩家”们,既不表现出对某种生存方式的解构,更没有对存在的可能性的探索和构造,换句话说,以苍白的内心油滑的生活态度在实在地“玩”,没有了价值的指向和形而上的精神意向性,就只能是“调侃”和“自娱”。
二、文化定位的尴尬
有人喜欢用“后现代”来比附中国电影的当下状况,在我看来这是值得商榷的。的确,第六代电影对个人意识的强调,个体经验性的凸显,从“历史”到“当下”、从“中心”到“边缘”,从戏剧性圆整叙事到写实性的记忆片段,都与转型期文化呈现出的多元文化并存的复杂性,如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混合,价值的混乱和重建、意义的丧失和追求等等相应和,正如电影《顽主》中那个颇具象征意义的镜头: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地主、农民、八路军、蒋匪军、五四青年、红卫兵、模特儿等等,在一个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台”。但是,“后现代”的比附却失之轻率和简化,是一种“误植”和“误用”。
我们知道,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有着特定的含义和社会语境,在文化的意义上,它是指经过一系列建构后的超越性否定,换句话说,它正是探询意义的活动自身,是对现代化的工业理性和商品逻辑的阻击和反抗。
而在我们这里,并没有这样一个过程:既没有现实的社会文化背景也没有主体的探询意义过程,就非常皮相地“嘲弄一切”、“否定一切”、“无价值”、“无深度”、“平面化”、“平板化”等等,滑稽之处就在于: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做?
在一个文化转型、价值转向,旧的理想和信仰遭到置疑而新的价值坐标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嘲弄”和“否定”一切是正常的反映,但它有两种:一种是在否定和怀疑一切之后,重新寻找新的生命坐标,我们否定,是因为我们有新的渴望和不满;另一种否定和怀疑则是否定和怀疑就是一切,它是价值取消主义,只能导向虚无。不幸的是,我们的第六代电影走的是第二条路。
即便是“虚无”,也是被“中国化”的、“第六代化”的。西方文化和哲学中的虚无主义有着独特的意义。它意指近代的理想主义的信仰和价值依据(上帝、科学、理性等),通常是外在于人的生命,而虚无主义所要的“虚”和“无”的,恰恰是这种外在于人的价值依据,而绝不是生活、生命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相反,它是要将生命的价值落实到生命本身。尼采喊出:“上帝死了”,是要提醒人们必须独自面对这个晦暗不明的世界,并在其中找寻出新的生命起点和活下去的勇气。它绝不是《红高梁》中的“李大头死了”,就可以放纵人的粗野,就任原始的本能和本性无羁地狂欢。而是意味着更强的生命力,也意味着人有可能创造出更高的意义。
所以,我们说“后现代的误植”,是说搞错了文化语境。后现代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艺术思潮,它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具体而言,是西方工业文明之后,在商品逻辑充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后,人要寻找新的生存基点和价值平台的冲动和反思。而在目前的中国,还没有经受西方已经经受过的这种洗礼,从历史和传统文化上,我们也缺少科学和理性的滋漫,在这种情况下,大谈“后现代”,岂不是天大的滑稽?
所谓“误用”,是说把西方向前、向上的意义探询活动变成了我们这里的向后的退缩和向下的沉沦。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至少是部分第六代电影所表现出的短视眼光、无支撑点的对主流价值观念的嘲弄、对深度的拒绝等特征。如果说作为他们兄长的第五代们还守着一片赤诚,那么这些“第六代”们则把真诚与伪善混为了一谈。于是,他们嘲弄真诚就像嘲弄伪善一样,油嘴滑舌、痞化、调侃就成了他们最为醒目的形态表征。客观地说,这些影片对于“解构”或“矫枉”中国电影传统中某些违背艺术规律的倾向是有贡献的,它们的出现和确立无疑经过了一个去蔽去伪的过程,它们通过对意识形态化了的陈腐文艺和电影观念的对立和反叛,力争从陈旧观念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中解脱出来,并追求真实的个人化的表达而将自己确立起来。他们复归自我或“小我”,用属于自己的感觉去感知,用自己的性灵去领悟,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个人化的情绪和思考,也使得国产电影开始关注个体性情感的抚慰,在一定意义上满足了我们个人化的精神和心灵需求。
然而,对艺术的真诚不仅是与外部世界相对的,它更要求以虔诚的内心对抗一己的伪善、丑陋和委琐,需要一个绝对的价值尺度作为艺术殿堂的准入证,而这些影人未能进一步超越小我,未能走向神性、永恒和绝对等等超验价值,而是封闭在孤立个体情感之中。因此,他们的影片所包含的内容被抽空和抽象之后,由于既缺乏生存的基点又失去美学支撑而趋于空虚、渺茫和没有深度的调侃。尤其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之下,对中国的文化中恰恰缺乏的神性意识、终极关怀、普遍信仰的摒弃以至嘲讽,不是无知,也至少是选错了射击的靶子或反叛的对象。所以,90年代以来以“躲避崇高”、“消解神圣”相标榜的国产电影,实际上是在上演着堂吉诃德大战风车般的喜剧,这种没有对象的精神反叛为立足点的影片,最终的结果是滑向价值的虚无。在某种意义上,这比“假道德”、“假崇高”更为可怕,因为它抽去了中国电影尚存的一丝对精神家园的留恋、对社会历史责任的承担,从而也把自己推向了被嘲笑和虚无化了的境地。
这也表明,在文化上他们是一群“无所适从”的一代,面对新生代导演这样一个庞杂的群体,用外来的文化批评术语进行简单的贴标签式的批评是无法奏效的。
三、没有立场的价值立场
与第六代电影几乎同时,在中国文坛上兴起了“新写实主义”文学潮流,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主张也成了时髦。
这样一种电影“写作”态度,首先是对第五代的反拨。第六代们初执导筒时,也正是张艺谋、陈凯歌们走向世界之际,第五代如日中天般的辉煌对他们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所反抗的直接对象无疑是第五代的辉煌以及第五代的电影,他们把电影看成是个人的东西,力求不与第五代一样,拍出“自己的电影”;也反对把电影拍成一种寓言或传奇,而是把被第五代忽略的当下现实生活和个体成长作为他们影片重要表现领域。这也就形成了第六代导演们所选择的艺术道路:以写实手法和写实态度更直接地切入现实生活。
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很大一部分影片以一种纪实性的风格呈现出个体生存状态,这种写实风格的更为重要和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影片的主题狭小和边缘凡俗的创作心态。第六代许多影片的题材,已从“摇滚青年”(《北京杂种》)等带自传性的人物身上,扩展到对更边缘和弱势人群。例如,从张元的《东宫西宫》开始,中国银幕第一次直接触及到一个禁忌的话题——同性恋。影片力图探索人性的丰富多样,并表现出对每一种选择的体谅与尊重。贾樟柯的《小武》(1997年)中,表现了一个名叫小武的小偷在剧烈变化的时代生活中,对友情、爱情、亲情美好幻想的丧失。王超的《安阳婴儿》(2001年)中,则表现了妓女、黑道头目和下岗工人三个不同社会底层人物的命运。这都可以看出,他们的影片是纪实风格的虚构性影片,以最为朴素平实的方式,力图唤起人们对乡土、对变动社会中个体生命的关注与悲悯。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白描、写实化的“客观”立场在一个信仰失落、价值观念大转换,良知、正义、公平、美和善等这样一些人生的正面都遭到肢解和嘲弄的时代,是否是作为艺术家应该具有的姿态?作为面向大众的文化产品不表明自己的立场,岂不是精神上的犬儒主义?!换句话说,对过去岁月的苦难不能忘记,失去重量的生命将无力承担历史的拷问。在丢弃枷锁的同时,不能丧失心灵的提纯和天真。对那些权利话语和意识形态化了的伪价值伪道德伪艺术,那些为动乱年代所搞乱了的价值观,那些专事歌功颂德的伪和假的一切,应该批判、反对、舍弃。但问题在于,是否一切称为价值的东西都是伪价值?是否在看透了虚伪和假面之后,坚守一份真诚?是否该为自己的艺术探求重新寻找价值的平台,而不是任浮躁的内心滑过虚无的地表?是否应该区分两种价值和真理,并向着真正的良善、美好、圣洁、爱、信仰和希望敞开生命之怀?
在我看来,“第六代”要解决的核心之处正在于此。他们的电影在自觉不自觉地拒斥着向着真善敞开的精神质素,因而也堵塞了美的道路,至少直至目前,他们仍走在一条简单、片面并最终导致没有深度的路上,它在反价值的同时,将真正的良善、美好的东西一起毫不留情地抛弃和否定了。因为:当反对伪价值的时候而不确定真正的价值,那么,伪价值之伪又如何区分?这反对活动又有什么意义?在真与善两个维度被现代艺术颠覆之后,艺术之美的品性也必然随之倾覆,美的艺术变成了丑的艺术,以丑为美已成为现代艺术的座右铭,而这丧失了真诚之真理和价值的空虚野性的艺术难道是真正的艺术吗?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它根本不是艺术,只是一种自我的宣泄,一种与其他满足各种欲望和享乐的商品别无二致的商品而已。其结果,艺术或赤裸裸地沦落为商品,或仅作为小圈子内自娱自乐的杂耍,这难道不是我们目前国产电影的至少部分事实吗?
新时代已经来临,中国电影站在了新的起点上,在此时,冷静地检视我们当下的电影,寻找新的坐标,该是每一个关心中国电影的人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