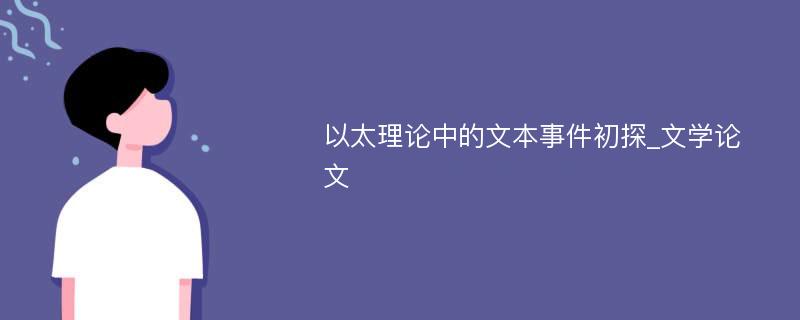
伊瑟尔理论中的文本事件性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本论文,理论论文,事件论文,伊瑟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0)02-018-3
伊瑟尔对文本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20世纪70年代,在现象学视角下从阅读效应透析文本结构,主要作品:《文本的召唤结构》(1970年)、《隐含读者》(1974年)、《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1976年);后期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从文学人类学视角来探寻人需要阅读和创作文学文本的深刻根源。主要作品:《走向文学人类学》(1989年)、《虚构化:文学虚构的人类学维度》(1990年)、《虚构与想像:文学人类学的疆界》(1991年,这本著作是伊瑟尔后期文本理论的系统化成果)。伊瑟尔前期和后期理论对于接受效应问题一直没有忽视,但问题意识有所不同,前期他追问:文本阅读过程怎样发生?后期他承前提问:文本阅读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不可或缺的东西?总的来说,伊瑟尔关注文本的交流沟通功能,侧重于从人本主义理想出发,把文本视为一种事件性的存在,对此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以下,我们就对伊瑟尔理解的文本事件性展开分析。
文本是什么?这是文本理论研究遇到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学者形成两种很有影响的文本观念:摹仿论(再现论)和形式论。摹仿论(再现论)强调文本是对外在现实、神秘力量和客观精神等的摹仿和再现,这些文本外的东西决定了文本客观的意义和本质。比如柏拉图的“理式摹仿论”、亚里斯多德的悲剧“摹仿论”、别林斯基的“文学艺术是现实的创造性再现”等。形式论则转向文本语言形式自身,强调文本是一种指向自身的语言结构。英美新批评和某些结构主义理论是其代表,比如,兰色姆的“构架—肌质”理论、布鲁克斯的诗歌语言“悖论与反讽”论、托多罗夫把叙事作品看作是一个陈述句的扩大。这两种文本观念的共同之处是:在西方强大的理性认识论传统影响下,形成了对文本理解的中心主义或者说本质主义的思维定势。这是一种着意追求的深度模式:文本现象背后一定隐藏着深刻的本质,它构成了文本的中心和内核。根深蒂固的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文本观其实暴露了西方文论中科学主义思维的一大弊端:没有很好的把握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差异性。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没有主体性和能动性,研究者一般不带情感态度,使用实验和求证的方法获得物背后蕴含的认识和真理。人文科学则不一样,它的研究对象是人和人的符号再现,整体的人具有充分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无论是研究者还是阅读者都带着程度不同的情感态度,把对象视为另外一个“你”,和对象产生一种对话关系。对象的主体性使得我们的研究也要采用主体性的态度,研究者重在体验和阐释对象,而不是偏重于求证对象,使用逻辑推演和科学实验的方法获得客观性和本质性的东西。放在整个人类的时空视域看,人文学科中不同的研究主体体验和阐释对象的成果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很难找到唯一客观的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文科学研究对象根本就没有一个客观稳定的本质和中心。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文本观被“理性至上”和“科学万能”的思想迷雾所遮蔽,并没有看清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差异性,把文本也视为没有主体性的物来研究,用科学求证的方法,坚信并探求文本现象背后客观存在的本质和中心。这种南辕北辙的研究思维,使得摹仿论和形式论的众多思想家为“文本是什么?”争吵不休,纠缠不清。
伊瑟尔的可贵之处是坚持人本主义,在“文本是什么?”问题上,一反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思维定势,也反对用科学求证方法剖析文本的客观化中心或者本质。他们主动“走向边缘”,倾向于把文本看作一个事件性的存在,从不断变化的双重意识的边缘线上寻觅文本的真实存在和审美实现。伊瑟尔的文本概念建立在区别文本的客观物质形态和文本的事件性这一基础上。伊瑟尔在前期和后期都明确反对认识论文本观的客观化和中心主义倾向(这种观念把文本视为作者的意图、客观的寓意、审美价值或者真理显现的载体),他关注“边缘”,视文本是多重系统在各自界限边缘的交叉事件。文本的事件性决定了文本是一个不确定的开放结构。他说“不论读者发生了什么状况,都要归因于文学文本具有事件的性质,即发生的事件没有指涉这一事实,因而必须通过文本解读来对其进行处理和反应。[1]”伊瑟尔关于文本的事件性论述有三点值得注意:
(1)伊瑟尔区别“文学文本”(literay text)[2]和“文献”(document)[3]这两个概念,突显文本的交流能力,这种能力构成了文本事件性的前提。他认为,“文学文本”的突出特征就是它的交流能力。它是表达部分和未表达部分相互影响组成的张力结构,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在阅读中它召唤接受者体验不复存在的事物,理解对我们来说完全陌生的事物。它表现为读者不断具体化的动态过程,而不是凝固的物质形态。这就使得读者阅读文学文本不是提炼单一意义或者印证外在现实,而是每读一次就经历一次新的交流事件,发现文本潜在的无穷意义。“文献”(document)则是用文字、图形、影音等符号记录人类知识的一种载体,或理解为固化在一定物质载体上的知识。“文献”只是“文学文本”的外在物质形态,没有“文学文本”的交流能力,两者不能等同。所以伊瑟尔批评具有中心主义倾向的传统阐释规范:“……文学本文(即文学文本,“text”笔者注)就被解释成对时代精神、对社会环境、对其作者的神经病、以及对诸如此类东西的证明;这些本文因此被压缩到文献(document)的水平,这样就被剥夺了那些使它们区别于文献的方面,……它们不能丧失它们的交流能力,这正是文学本文的一个突出特征。……现在,以寻求单一意义为基础的传统解释规范宣布要指令读者;当然,它既易于无视本文作为一个正在发生的事件的特征,也易于忽视由这个正在发生的事件引起的读者的体验。”[4]伊瑟尔敏锐地发现了正是文学文本的交流能力引发了读者把它作为变化的事件而不是固定的文献来体验。
(2)伊瑟尔在前期理论中强调文本作为边缘的交叉事件体现在两个方面:文本和现实之间的交叉;文本和读者之间的交叉。如前所述,文学文本具有交流能力,但是文本无法自我实现,它需要现实和读者两个维度与之展开交叉互动,在边缘汇聚意义,实现文本不确定的内涵。所以伊瑟尔主张用功能主义立场来研究文本的事件性,他说“这种研究必须集中在两个基本的、相互依赖的领域之上:一个是存在于本文和现实之间的交叉点,另一个是存在于本文和读者之间的交叉点;如果人们要把虚构作品的效果作为一种文学交流手段来评价,那么找到某种确定这些交叉点的方法就是不可或缺的。”[5]关于文本和现实的交叉,总的来说,伊瑟尔认为文学文本对现实不是简单模仿,文本和现实之间不是镜子和物象的关系,而是通过“剧目”对现实的重组转化,“剧目”和现实存在边缘交叉关系。剧目是作者参照和选择现实因素引入文本的并且为读者所熟悉的惯例、规范和传统。剧目可以“引用”其他文本,也显现社会规范和历史规范,甚至可以再现整个文化,但是剧目的主要内容是表现为思想体系的社会规范和历史规范。剧目的矛盾性在于,它一方面以流行的社会规范和历史规范为内容,所以读者在文本中总能读到熟悉的现实情境;另一方面,剧目的功能却不是再现现实,而是指向现实的边缘,指向主流社会规范和历史规范所遮蔽的东西。剧目把这些熟悉的东西作为背景,实施各种文本策略来突显被现实排斥的东西并把它推向“前景”的位置。剧目“前景—背景”结构多重转换,使得文本和现实形成交叉的张力关系。文本介入现实,聚焦它的另一面,再现被现实主流意识形态所忽视和排斥的东西,让现实的边缘进入了文本的注意中心(前景),激活现实中僵化的思想体系。同时,现实也介入文本,现实通过文本转化,构造了交流过程的背景,和前景的对照中暴露了现实思想体系的缺陷。文本的虚构世界引导读者聚焦这种缺陷并重新评价现实,现实得到补充和重新塑造。文本和现实互相渗透,那么,文本的事件性就发生在文本和现实交叉的边缘,“在一部文学作品中,存在的活动领域很容易处在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特定思想体系的边缘、或者刚好处在这种边缘之外。”[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瑟尔认为英国18世纪小说和戏剧的中心议题是道德先验基础的可能性,这正是当时洛克经验主义所忽视的边缘问题,文本虚构的东西正好暴露和补充了现实的缺陷。
伊瑟尔把阅读效应看作文本事件的实现,所以文本和现实的交叉关系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文本和读者的互动之中。伊瑟尔在《文本的召唤结构》中区别了一般性文本和文学作品的文本(即文学文本):一般性文本陈述文本之外,不依赖于文本而存在的确定性对象,它使用的是一种“陈述性的语言”;文学作品的文本使用“描写性语言”,它没有确定的对象性,而是从生活世界里取来素材创造自己的对象。所以它不是陈述客观的现实,而是在描写另一种虚构的现实。它展示某种观念和前景,把读者的经验所熟悉的世界转化成另一种面貌。这样,文学作品的文本既不能与“生活世界”的现实对应,也不能与读者的经验完全等同起来,这些差异形成了文学作品文本中多重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构成文本结构,伊瑟尔称之为“召唤结构”。这种结构特征暗示了文本和读者之间根本上的不对称,文本是个迷宫,读者手中没有地图。传达者和接受者没有明确一致的代码来控制文本加工的方式,这样的代码只能在阅读过程中创造。文本的审美实现依赖于读者对“召唤结构”的回应,否则它永远是潜在结构。“召唤结构”召唤读者的想象力来填补文本的不确定性与意义空白,不同读者的意向性投射使文本潜在意义的实现变得丰富多彩,每读一次就是一次生动的事件,读者和文本的交叉构成了事件性,造成读者身临其境的幻象。阅读文学文本对读者的想象力是一种极大的激活和挑战,所以伊瑟尔肯定地说:“由于文学作品文本的现实性不存在于客观事物的世界中,而存在于读者的想象力之中,与那些表达某种含义、陈述某种真理的文本相比,它便具有一种优越性。……文学作品的文本之所以能够摆脱历史的局限性,首先并不是因为它们体现了某种永恒的、超越时代的价值,而是因为,它们的结构允许读者参与到虚构的事件中去。”[7]总之,文学作品文本的特性在于它不是确定对象的复制,而是文本召唤结构和读者想象力之间的不确定性事件,读者的阅读效应对文本的实现起到关键作用。
(3)伊瑟尔在后期理论中把文本(文学文本)视为虚构、想象和现实这“三元”在各自边缘越界交叉的事件。伊瑟尔在后期理论中发展了前期“虚构和现实互补”的思想,并且澄清了我们对“想象和虚构的混淆”,提出文学文本是虚构、想象和现实“三元合一”产物,任何一元都不是唯一的中心或者本质,三元各自超越疆界在边缘交叉形成相互作用的动态事件。按照伊瑟尔的解释,“现实”是对经验世界的参照,对于文学文本来说它是“给定”的各种各样的参照域,比如一个思想体系、一个生活场景、另一个相关的文本等;“想象”是文本中自由的幽灵,难以界定,它自身并没有明确的意向性和稳定的形式,需要借助外在现实力量激活意向。想象往往用伪装和游戏的方式呈现自身,它也以瞬息万变的方式把握对象。伊瑟尔不把想像看做一种人类的思维能力,而是文学文本显现和运作的一种模式,他关注这一模式下想象功能的实现。同样,伊瑟尔悬置虚构是什么的本体论定义,也强调“虚构”功能的实现,关注虚构怎么样。他说“虚构在这里表示一个意向性行为,它包含了关于一个事件的所有性质,……”[8]他把虚构视为越界行为,虚构化行为通过选择、融合和自我揭示的方式跨越现实的疆界,受到作者倾向性意识的引导“侵略”现实世界,越界行为重组现实进入文本,文本中再造的现实撕碎分裂和充实扩展了“被侵略”的现实世界。虚构对现实的越界其实为想象对现实的越界提供了前提。具有意向性和自觉性的虚构在越界中不光激活了现实,而且激活了想象,给瞬息万变的想象一种明晰的形式(完形),这样虚构就在现实和想象之间架起了桥梁。想象以明确的形式对现实越界,以伪装和游戏的方式反映现实,分享现实性。伊瑟尔总结道“现在,我们已经对两个相关过程有了清醒的认识,这两个过程都与虚构化行为有关联。其一是,虚构化行为再造的现实是指向现实却又能超越现实自身的;其二是,无边的想象反倒被诱入某种形式之中。这两种情况都存在着越界现象:现实栅栏被虚构拆毁,而想象的野马被圈入形式的栅栏,结果,文本的真实性中包含着想象的色彩,而想象反过来也包含着真实的成分。”[9]这样,文本就成了虚构、想象和现实“三元”互相渗透、互相越界的交叉事件,文本不是一个稳定的存在,而是“三元”边缘互动的事件。伊瑟尔强调,虚构化行为在“三元”事件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它超越现实(对现实的越界)和把握想象(完形),正是虚构化行为的引导,现实才得以升华为想象,而想象才能走近现实。现实和想象重新组合,带给接受者一个新的世界。可以说,虚构化行为的效果促成了文本事件。
我们发现,关于文本的事件性,伊瑟尔前期理论重点是文本和读者的交叉(文本和现实的交叉实际上还要落实到文本和读者的交叉),读者在文本事件中地位突出,作者因素缺失。后期理论则强调虚构化行为的关键作用,显然虚构的意向性主要来自作者,虚构化行为首先表现为作者创作过程中对现实“疆界”的跨越,然后才能沉淀为文本潜在的虚构性。作者因素在文本理论中得以显现。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在伊瑟尔理论中文本聚合了多重系统,包括读者、现实、虚构和想象,它们形成多层次的交叉互动关系,实际上文本是多重系统在各自界限边缘交叉的事件。伊瑟尔把文学文本视为主要研究对象,他们破除理性认识论对文本深度本质和中心的迷恋,反对文本是客观物的复制,而视文本为一个需要主体介入的动态过程和事件,从“边缘”探析文本的特性,坚决守护文本的人文性。
〔收稿日期〕:2010-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