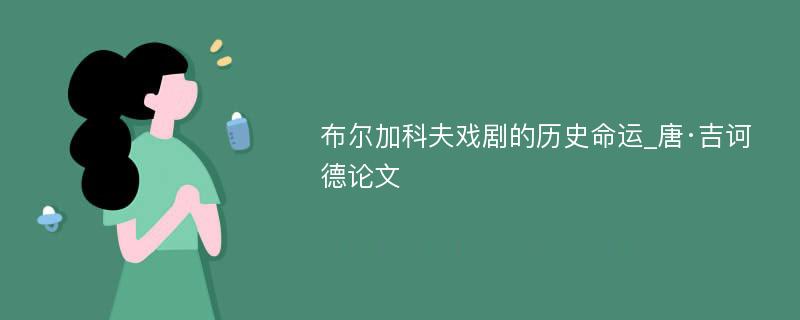
布尔加科夫戏剧的历史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尔论文,科夫论文,戏剧论文,命运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1891—1940)是苏联历史上一个曾经引起很大争议的剧作家和小说家。介入争议的不仅有当时苏联文艺界的领导人,有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这样的大作家、大理论家,而且有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争议的产生和当时苏联文艺界各种思潮流派尖锐激烈的斗争直接相关,因此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这些争议导致了布尔加科夫的剧作屡遭禁演,而且全都未能在他生前出版。50年代中期以来,布尔加科夫的名誉逐渐得到恢复,他的剧作也越来越多地搬上舞台,被结集出版,被作为研究的对象。人们给了他很高的评价。例如苏联学者尼诺夫认为:“继契诃夫和高尔基之后,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历史上没有像布尔加科夫这样天才的、富有独创性的大剧作家。”〔1 〕还有人认为他是20世纪最大的戏剧家之一,说他的戏剧的“回归”是20世纪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观。
在西方,布氏的剧作早就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其中有不少被搬上舞台。例如:美国的布尔加科夫研究者计划出版10卷本的《布尔加科夫文集》,并且已经出了其中的头几卷;美国的剧团还到莫斯科上演根据《大师和玛格丽特》改编的话剧。相比之下,我国的布尔加科夫研究起步甚晚。在《大师和玛格丽特》的中文版出版后,我国读者对布尔加科夫的名字已不感到陌生,但对他的戏剧至今仍然知之甚少,至于研究就更加薄弱了。
然而,即使对俄罗斯学者说来,布尔加科夫剧作研究仍然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课题。这一方面是由于有关布尔加科夫的争议背景十分复杂,另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剧作有多种版本和修改稿,内容复杂多义,有待校勘、订正。这些工作当然只有俄国学者才能胜任。而在这些工作完成之前,匆匆地作出结论显然是不够严肃的。因此,本文不想也不可能对布尔加科夫戏剧作品的具体内容作任何断然的评价,而只是想把这些作品在苏联各个历史时期的遭遇作个简明的介绍,尽可能做到客观公正,但仍可能有不够准确的地方,谨供戏剧界、学术界的朋友们参考。
一、20年代的布尔加科夫戏剧
在20年代,布尔加科夫总共有3部话剧被搬上舞台, 这就是莫斯科艺术剧院于1926年上演的《土尔宾一家的命运》、瓦赫坦戈夫剧院于同年上演的《卓伊卡的住宅》和莫斯科室内剧院于1928年上演的《紫红色的岛屿》。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逃亡》于1926—1928年由莫斯科艺术剧院排练,但最后没有正式上演。这些剧作的命运在俄罗斯甚至世界戏剧史上都是非常独特、罕见和发人深省的。
《土尔宾一家的命运》是布氏根据自己的长篇小说《白卫军》改编而成的。剧中描写了以土尔宾上校为代表的一群“真诚地”信奉自己信念的白卫军军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参加了这出戏的导演工作。瓦赫坦戈夫剧院的《卓伊卡的住宅》首演日期只比《土尔宾一家的命运》迟23天。该剧是一部“悲剧性的闹剧”,对新经济政策时期沉滓泛起的社会丑恶现象作了夸张而入木三分的揭露。在首都两家最著名的剧院同时上演两部剧作,这对于布尔加科夫来说确实是巨大的成功,必然要引起批评界的关注。果然,这两部话剧上演后,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批评“莫艺”走的是一条“保守的”剧目路线,有人指责这两个剧目是“小资产阶级本性的表现”,是“戏剧创作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路标转换派的表现”〔2〕。出乎意料的是,这些指责反而使观众更加踊跃。因此,布尔加科夫的反对者们加紧努力来阻止布氏的另一部剧作——《逃亡》的上演。他们的努力果然奏效。1928年2月, 剧目委员会阻止了这出戏的公演:对《土尔宾一家的命运》的指责同样地用来针对《逃亡》。
高尔基为了保护《逃亡》一剧,特地阅读了全剧。10月9日, “莫艺”举行了剧本朗诵会,由布尔加科夫亲自朗诵。高尔基和许多文艺界负责人都在场,朗诵会获得了成功。两天后,《真理报》发表消息,说《逃亡》在艺术上是合格的,在思想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可以作为上演剧目。剧目委员会也允许莫斯科艺术剧院继续排练这部话剧。高尔基则称赞《逃亡》是一部杰作,并预言它一定能大获成功。〔3 〕国家艺术事业总局的负责人也明确表示支持这个剧本。然而,时间过去不到10天,剧目委员会就再次讨论了《逃亡》。参加者当中没有高尔基,却有“拉普”的领导者们,以及和布尔加科夫对立的人们。结果,两天之后,莫斯科艺术剧院又接到通知,不准在剧院3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上演《逃亡》。原来,反对上演布尔加科夫剧作的有剧目委员会的机关干部,有“拉普”及其刊物《在文学岗位上》的领导人,有受到“左”的文学派别影响的《共青团真理报》文学部和《青年近卫军》杂志的编委们,他们结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和行政力量。
围绕着布尔加科夫的论争从1926到1929年延续了3年之久, 而斯大林给剧作家比利—别洛采尔科夫斯基的一封回信(1929年2月2日)可以看作这场论争的高峰和顶点。它对后来布尔加科夫的命运产生了特殊的影响。事情的原由是:比利—别洛采尔科夫斯基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提醒这位党的总书记要警惕苏联剧坛上来自布尔加科夫一类人的“右的危险”,而这种危险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文艺界领导的放任和姑息行为。然而,斯大林在回信中却指出:在文艺界提出“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这一提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是党内的概念;但是如果在文艺界运用阶级方面的概念甚至“苏维埃的”、“反苏维埃的”、“革命的”、“反革命的”等等概念,那是最正确的。斯大林在信中写道:又如布尔加科夫的《逃亡》,同样不能认为是‘左倾’危险或‘右倾’危险的表现。《逃亡》是企图引起人们对某些反苏维埃流亡者阶层怜悯(甚至同情)的表现,也就是企图为白卫分子的活动做辩护或半辩护的表现。像现在这个样子的《逃亡》是一种反苏维埃的现象。〔4 〕斯大林紧接着说:
但是我决不会反对上演《逃亡》,只要布尔加科夫给自己的8个梦再加上一两个梦,描写出苏联的国内战争的内部社会动力,使观众能够了解,所有这些自称为“诚实的”谢拉菲穆之流和各种各样的编制以外的大学讲师被赶出俄国,并不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任性,而是因为他们曾经骑在人民的脖子上(不管他们如何“诚实”),布尔什维克把这些剥削的“诚实”拥护者赶走是体现了工农的意志,因此是做得完全正确的。〔5〕
对《土尔宾一家的命运》一剧,斯大林的态度比较肯定。他写道:
闹剧本荒的时候,甚至《土尔宾一家的命运》也算好剧本了。……这个剧本本身,它并不那么坏,因为它给我们的益处比害处多。不要忘记,这个剧本留给观众的主要印象是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印象:“如果像土尔宾这样的一家人都承认自己的事业已经彻底失败,不得不放下武器,服从人民的意志,那就是说,布尔什维克是不可战胜的,对他们布尔什维克是毫无办法的。”《土尔宾一家的命运》显示了布尔什维主义无坚不摧的力量。〔6〕这一评价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评价比较接近。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土尔宾一家的命运》是“不少的优点和明显的重大缺点的混合体”〔7〕, 总体上持肯定的态度。
然而,反对布尔加科夫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核心就是“拉普”的一批骨干人物。“拉普”刊物《在文学岗位上》(编委会由阿韦尔巴赫、叶尔米洛夫、基尔尚、李别进斯基和法捷耶夫等人组成)发表了阿韦尔巴赫、基尔尚在剧目委员会1928年10月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导致了《逃亡》一剧的再度禁演。
阿韦尔巴赫发言的意图十分明确:摧毁模范剧院的上演剧目,用“无产阶级剧作家”的作品来取代“可疑的”非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他责问道:无产阶级剧作家的作品不在“莫艺”上演,而“莫艺”上演的偏是布尔加科夫这样的人的作品,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布尔加科夫拿着他的《逃亡》不去找工会委员会,不去找梅耶荷德剧院,不去找革命剧院,而只找“莫艺”,这难道也是偶然的吗?基尔尚在他的发言中则认为,剧目委员会和艺术事业总局准许《逃亡》上演是错误的,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沦为《逃亡》这种劣等剧本的俘虏,也是一个错误。〔8〕
必须指出,“拉普”领导人之所以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布尔加科夫发动围攻,和斯大林对布氏的评价有关。虽然斯大林不赞成在文艺领域运用“左倾”、“右倾”之类的提法,但是他在给比利—别洛采尔科夫的复信中把《逃亡》说成是“反苏维埃的现象”,把《紫红色的岛屿》说成是“低级的作品”,〔9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反对布尔加科夫的运动。结果,到了1929年,就连斯大林认为“给我们的益处比害处多”的《土尔宾一家的命运》在已经上演300场之后也遭到了禁演,被从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上演剧目中剔除了。到1929年中期,布氏的3部已在莫斯科上演的剧作全部遭到了禁演,而即将由莫斯科艺术剧院搬上舞台的《逃亡》则中断了排练。
二、30年代的布尔加科夫:从作家到导演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苏联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清洗。在布尔加科夫的创作生涯中也发生了一次悲剧性的转折,使他一直到去世为止都未能公开发表作品。1929年7月,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 加里宁、斯维杰尔斯基(当时的艺术事业总局局长)和高尔基写了一封信,信中罗列了他的剧作遭到禁演和他本人受到搜查的事件,以及他和他的妻子要求出国而遭到拒绝的情形,并再次请求将他和他妻子“驱逐”出境。〔10〕然而,布尔加科夫没有得到当局的答复。于是,他在1930 年3月28日又写了一封《给苏联政府的信》,以令人惊讶的真诚和勇气表达了自己的创作信念,指出了当局对艺术进行压制的粗暴手段,以及这种手段在过去给苏联文化带来的损害。这封信发出半个多月后,在4月 14日,斯大林给布尔加科夫打电话,和他进行了一次交谈。然而,这次交谈并没有使布尔加科夫变得乐观起来。一年之后,他在致斯大林的另一封信中仍然将自己称为文学界“孤独和唯一的狼”,他说自己曾经试图放弃作家职业,因为“没有一个作家是人们要他沉默的。如果他沉默了,那就意味着他不是真正的作家。”“如果真正的作家沉默了——他就是死了。”“我的疾病的原因——多年受到迫害,后来便是沉默。”〔11〕
然而,布尔加科夫是真正的作家,这一点他的反对者也无法否认——他宁可死去,也不愿强迫自己沉默。
布尔加科夫要从他在信中所描绘的那种悲观绝望的处境中解脱出来,本可以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当局给予他充分的创作自由,让他发表作品,上演他的剧作。然而,在他和斯大林的电话交谈中,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第二种可能是让他出国,这种可能在当时是存在的,然而,布尔加科夫并不是真的愿意脱离祖国的文化,脱离他所熟悉的生活和语言环境。第三种可能,是在根本上改变自己的职业,即不再从事文学创作而调到剧院工作,将毕生精力献给戏剧事业。布尔加科夫选择了后者。他在致苏联政府的信中请求最高当局委派他到剧院去做个职业导演;如果不可能的话,他宁可做一个跑龙套的演员,甚至是舞台工作人员。〔12〕他在4月14日的电话交谈中告诉斯大林, 说他希望去莫斯科艺术剧院工作,结果,斯大林答应了,并使他得到了“莫艺”助理导演的位置。
布尔加科夫以一个新导演的身份在“莫艺”出现后,在和剧院的演员以及艺术领导相处时,难免要发生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只有通过共同的实践活动才可能解决。“莫艺”的创立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作为剧作家的布尔加科夫相识已经有5年的历史, 在“莫艺”排练《土尔宾一家的命运》和《逃亡》时和布氏有过接触。因此,他对这位新导演能否胜任自己的工作并不感到特别的担心。斯坦尼的疑虑在于,助理导演的辅助性工作能在多大程度上使同时是个剧作家的布尔加科夫感到满足,又如何能和他在戏剧界的实际地位相称。斯坦尼由衷地希望布尔加科夫能和谐地把自己对文学的兴趣同他所承担的专业导演的职责结合起来。他还以莫里哀为例,说明一个出色的剧作家完全有可能同时是一个出色的导演和演员,他试图以这种方式欢迎布尔加科夫的到来,同时使他对新的工作充满信心。
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繁忙的导演艺术实践耗费了布尔加科夫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写作,他依然写得很多,经常熬夜,尽管他健康不佳,并且最终垮了下来。
三、“16个剧本全部夭折”
布尔加科夫在他致苏联政府的信中写道:“我的全部作品都是没有希望的。”〔13〕这句话如果用来形容他的剧作的命运,那倒是不过分的。下面是布尔加科夫剧作的一连串经历:
莫斯科艺术剧院在1926—1928年间排练布氏的《逃亡》一剧,但是,如上所述,此剧在作者生前从未正式演过,由瓦赫坦戈夫剧院上演的《卓伊卡的住宅》同样被禁演。
30年代上半期,布氏按照他和几家剧院签定的合同,创作了3 部用怪诞手法来折射现实的幻想剧——《亚当与夏娃》(1931)、《无上幸福》(1934)和《伊凡·瓦西里耶维奇》(1935),然而3 部剧本当时都未能上演。
1930年,布尔加科夫为莫斯科艺术剧院将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改编为剧本,此后,又按照几家剧院的合同改编了托尔斯泰的史诗《战争与和平》(1932)、莫里哀的喜剧《贵人迷》(1932)和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1938)。然而,只有《死魂灵》一剧在作者生前得以上演。
30年代中期,布尔加科夫创作了历史剧《莫里哀》(又名《伪善者们的奴隶》);为了纪念普希金诞生100周年, 还创作了一部在内容上与《莫里哀》相呼应的历史剧——《最后的日子》。不料这两部剧作的命运也很相似:《莫里哀》一剧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7 场之后即被禁演,而《普希金》(即《最后的日子》)则是在布尔加科夫去世3 年后,即1943年,才由莫斯科艺术剧院第一次搬上舞台。
遵照“莫艺”领导的意旨,布尔加科夫在1938年至1939年间完成了一部描写斯大林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传记剧——《巴土姆》。剧院已经着手投入排练,但是斯大林很不喜欢这出戏,结果剧院只好作罢。
在去世前的最后几年,布尔加科夫成了莫斯科大剧院的专业编剧,他写了4个歌剧脚本——《黑海》、《米宁和波萨尔斯基》、 《彼得大帝》和根据莫泊桑小说改编的《拉舍尔》。然而这些剧本一个也没有上演,尽管和他合作的是一些很有名气的大作曲家。
只有《土尔宾一家的命运》,当局在1929年禁演之后,又在1932年特许莫斯科艺术剧院独家上演,此剧后来在“莫艺”继续上演,直到卫国战争爆发为止。难怪有不少人一直到布尔加科夫去世还以为他是“只写过一个剧本的作家”。
1937年10月2日, 布尔加科夫在写给作曲家阿萨费耶夫的信中说:“最近7年我完成了16部各种类型的作品,而它们全都夭亡了。 这种情况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家是一片失望和阴郁情绪……”〔14〕直到完成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大师和玛格丽特》后,布尔加科夫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还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未来”。〔15〕
布尔加科夫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一直到他去世之前,他的全部剧作包括自己创作和改编的剧本、歌剧脚本和电影脚本(《死魂灵》和《钦差大臣》)居然没有一部在他的祖国发表(有几个剧本译成外文后在国外出版)。到他逝世后,“布尔加科夫文学遗产委员会”的作家们才决定向出版部门推荐他的第一个剧作集,其中包括6部话剧, 即《土尔宾一家的命运》、《逃亡》、《莫里哀》、《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最后的日子》和《唐·吉诃德》,然而,这部已经送排的剧作集终究还是未能问世。有人提出疑问:这些剧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曾发表过;因此,它们一旦出版,那么就不仅仅是布尔加科夫戏剧选的问题,而是他的剧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值得发表和引起读者们注意的问题了。这一疑问的提出使布氏戏剧集的出版推迟了15—20年。
四、“解冻”之后:布尔加科夫戏剧的回归和研究者的困惑
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苏联社会处于所谓的“解冻”时期。莫斯科先后在1955年、1962年和1965年出版了3 种布尔加科夫的剧作选集。其中1965年的剧作选收入布氏的《土尔宾一家的命运》、《逃亡》、《莫里哀》、《贵人迷》、《最后的日子》、《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唐·吉诃德》等7部剧作,是当时包容最多的一个选本。 这三种选集的问世对于当代世界剧坛,对于许多国家的读者,都是一次真正的发现。
随之,布尔加科夫很快地成了作品上演最多的剧作家之一。他的话剧和根据他的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改编的剧本,以及其他作品,在世界的许多国家久演不衰。布尔加科夫戏剧的回归成了20世纪后期艺术文化的奇观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是最值得专家们认真分析研究的一个戏剧家。
对布尔加科夫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方面是他的剧作远远没有全部出版,另一方面,已出版的剧本的文本并未经过严格的校勘。例如:仅《土尔宾一家的命运》就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原稿,这就需要进行认真的校订,以产生出一个范本。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布尔加科夫剧作都有这个问题。《逃亡》、《卓伊卡的住宅》、《莫里哀》、《最后的日子》等剧都经过作者多年的反复修改、删节和补充。这些文本的改变往往是被迫的,是根据剧院或剧目委员会的要求,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大部分的修改是作者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更简洁凝练、更富于表现力而进行的。譬如《逃亡》一剧的结尾,布氏为主人公赫卢多夫将军设计了几种不同的命运——从他自国外返回苏维埃俄罗斯到自杀于君士坦丁堡。在1926年到1937年间,这部复调型的、含义相当复杂的剧本,其结局在作者的头脑中变了多次,甚至全然不同。
对布尔加科夫的研究早在60年代中期就已广泛地展开,但是布氏著作的出版计划却迟迟未能制定出来。布氏的某些剧作即使在1965年后依然秘密保存了20年之久,其中包括《卓伊卡的住宅》、《紫红色的岛屿》、《亚当和夏娃》、《巴土姆》,以及《死魂灵》的改编本等。外国的某些版本则是根据从苏联运出去的形形色色的文本排印的,存在各种各样的错误。而布尔加科夫个人档案的全部手稿则在莫斯科的国家图书馆手稿部秘藏着,按照该馆的禁令,这些手稿不可能让专家接触,时间长达5年之久。 这一措施给布尔加科夫著作的研究和出版带来的损失是无庸置疑的。
由于布尔加科夫生前未能出版自己的作品,后来的出版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必须对不同的文本和修改稿进行校勘和订正,以便确定作者对每部剧作的真正意图。结果发现已出版的《土尔宾一家的命运》是经过扭曲的“提台词式”的版本,而不是作者自认为最佳的一稿。《逃亡》的结尾是作者自己拒绝采用的。当今读者和观众看到的《卓伊卡的住宅》和1926年完成并由瓦赫坦戈夫剧院演出的稿本也相去甚远。已发表的《莫里哀》一剧的版本则充满了被迫改写的痕迹。1986年出版的布尔加科夫剧作选所收的《死魂灵》一剧,则是莫斯科艺术剧院改编本的一种拼盘式的变体,而“莫艺”改编本既非该院多年上演的脚本,也不是布尔加科夫本人引为自豪但未曾发表的那份原稿。〔16〕
在布尔加科夫手稿的研究中所遇到的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所造成的障碍,反而使国外那种轻率的商业性的出版,以及苏联国内非专业杂志的各种版本有机可乘。美国有个布尔加科夫的研究者,试图出版一套10卷本的布氏文集。此人已出了一本关于布氏的书。为了造成最大的轰动效应,她在10卷本的第一卷前言中写道:由于不充许接触布尔加科夫档案中最重要的部分,特别是他的手稿,她只能向读者提供目前有可能提供的一切。她不无讽刺意味地说:“我们把文本的校勘工作留给21世纪的苏联文学家。”
五、80年代中期以来布尔加科夫戏剧的出版、演出和研究
在80年代中期的苏联,布尔加科夫戏剧的出版、演出和学术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莫斯科的艺术出版社计划在布氏诞生100 周年时出版由若干卷组成的布尔加科夫《戏剧遗产》,文学艺术出版社也打算出版五卷本的布尔加科夫文集。在1984年、1986年,关于布尔加科夫的学术研讨会接连两次在列宁格勒(即现在的圣彼得堡)举行,并取得不小的收获,与会的专家学者对布尔加科夫研究中若干悬而未决的重大课题非常关注。卢里耶的论文《布尔加科夫对〈土尔宾一家的命运〉文本的加工》将剧本的3种不同稿本加以细致的对照和研究; 古德科娃的论文《剧本〈逃亡〉的命运》则对《逃亡》的几种不同结尾加以比较,都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
布尔加科夫戏剧的上演也达到新的高潮。《逃亡》一剧早在70年代末就由莫斯科的两家剧院分别上演,现代人剧院上演了《莫里哀》和《土尔宾一家的命运》,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小剧场上演了《土尔宾一家的命运》,木偶剧院上演了《贵人迷》。除了布氏自己创作的剧本之外,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话剧也被搬上舞台,例如:莫斯科艺术剧院小剧场上演了《大师和玛格丽特》,莫斯科青少年剧院、列宁格勒苏维埃剧院等上演了根据布氏同名小说改编的《狗心》,环境剧院上演了《戏剧长篇小说》。更引人注目的是,美国的一家剧院也在苏联上演了《大师与玛格丽特》。
与此同时,一批研究布氏戏剧的论文和专著相继问世。其中斯梅良斯基的专著《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在艺术剧院》(艺术出版社,1986)、论文《布尔加科夫·莫艺·〈戏剧长篇小说〉》、《离去》等三项成果都以布氏与“莫艺”的关系为研究题目,是相当引人注目的。原因在于,布尔加科夫1937年发表脱离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声明,说他决不再跨进剧院大门,并在此后的数年中确实恪守了自己的诺言;其态度如此强硬,居然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迫害,这似乎已成了一个难解之谜(研究布尔加科夫达20年之久的丘达科娃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布氏已经把大部分的秘密带进了坟墓,谁也不可能了解这些秘密。这一说法恐怕与此有关)。当然,对布氏戏剧的研究中一个更为重要的课题恐怕还是如何理解和评价他的剧作的问题。在这些方面,也出现了一批成果。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部没有发表的布尔加科夫剧作——《巴土姆》也于1988年在《现代剧作》杂志上发表。编辑部在按语中写道:“……我们请国内主要的布尔加科夫研究者之一丘达科娃谈谈她对这部剧本的出发点和产生过程的假设。编辑部认为,丘达科娃的意见是有趣的,但并非无可争议的。如果读者中有谁持不同看法,我们准备加以研究并继续业已开始的关于布尔加科夫最后一部剧本的讨论。”〔17〕力图采取客观公正的立场。1989年,艺术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出版了《布尔加科夫20年代剧作集》,收集了《白卫军》、《逃亡》、《卓伊卡的住宅》、《紫红色的岛屿》4部剧本和各种不同文本, 包括进行局部修改所得出的剧本片断,从而从根本上打破了将手稿藏于密室的状况,为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该书在正文前头刊登了尼诺夫的论文《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与20年代的戏剧运动》,为研究布氏20年代剧作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资料。
1991年是布尔加科夫诞生100周年,在纪念性的文章中, 有一篇文章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发表在《戏剧》杂志1991年第7 期的尼诺夫的长文《〈巴土姆〉之谜》。作者认为:此剧在布氏的创作遗产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从来没有一部作品使布尔加科夫这样犹豫和痛苦,这样艰难,然而他是志愿地、真诚地完成这部剧作的。尼诺夫的意见当然不是定论。从编者按中可以看出,《巴土姆》这部以年轻的斯大林为主人公的剧本就像是个谜团;这个谜团应如何解开,当时研究者们还在争论之中,难以得出结论。但无论如何,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总比过去那种主观武断的作法要好得多,这是毫无疑义的。
注释:
〔1〕《布尔加科夫20年代的剧作》(艺术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 1989),第14页。
〔2〕参见《布尔加科夫20年代的剧本》,第16页。
〔3 〕参见斯梅良斯基:《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在艺术剧院》(莫斯科,1986),第165页。
〔4〕《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5),第十一卷,第281页。
〔5〕同上。
〔6〕同上,第281—282页。
〔7〕《卢那察尔斯基文集》,俄文版,第3卷,第327页。
〔8〕参见《布尔加科夫20年代的剧本》,第27页。
〔9〕《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5),第十一卷,第282页。
〔10〕参见《布尔加科夫20年代的剧本》,第31页。
〔11〕苏联《十月》杂志,1987年第6期,第181页。
〔12〕参见苏联《十月》杂志,1987年第6期,第180页。
〔13〕同上,第179页。
〔14〕转引自《布尔加科夫戏剧遗产问题》(列宁格勒,1987),第90页。
〔15〕同上,第92页。
〔16〕《布尔加科夫戏剧遗产问题》,第12—13页。
〔17〕参见《现代剧作》1988年第5期,第204页。
标签:唐·吉诃德论文; 布尔加科夫论文; 布尔战争论文; 布尔类型论文; 大师和玛格丽特论文; 死魂灵论文; 莫里哀论文; 剧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