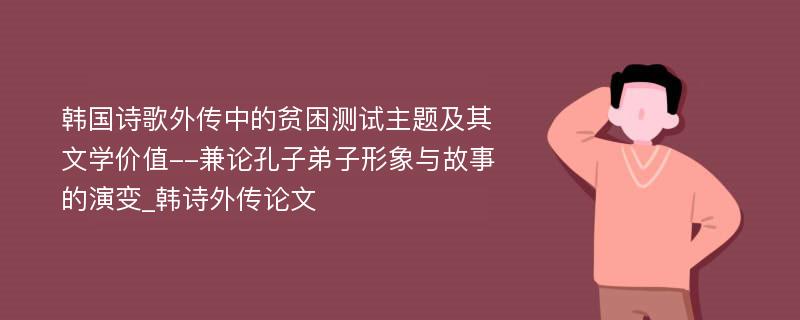
《韩诗外传》的贫困考验主题及其文学价值——兼论孔门弟子的安贫乐道形象和故事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贫乐道论文,弟子论文,外传论文,贫困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492(2006)07-0085-04
现实生活中最基本的衣食住行,有着艰苦与享乐的天壤之别:美酒佳肴、残羹冷炙,锦衣貂裘、衣衫褴褛,车马豪宅、徒步陋室。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况,人们或者沉溺于肉身的安逸,或者以理性超越现实的窘境。儒家给予安贫乐道之士以充分的肯定。《论语》中孔子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 (《雍也》,P59)孔子赞赏颜回甘于贫困的生活,但并不是认为贫困的生活本身有可乐之处,而是强调,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艰难生活条件,并没有改变颜回对于道义的热爱,所谓贫贱不能移是也。颜回之贤,在于能以道义之乐超越现实生活的困窘,不为外物移其心志。
孔子本人对贫寒生活也有亲身体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 (《述而》,P71)在孔子看来,有道君子即使在贫寒的生活中也能够自得其乐,失去了仁义道德,所谓的富贵享乐则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从以上《论语》所记载的孔子言语中可以看到,安贫乐道在儒家学说中,被认为是君子应具备的道德素养。儒家相信道德的力量完全可以克服生活中的种种简陋,消解艰苦的物质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同时还可以乐在其中。能否经受住艰苦生活的考验,甘于贫寒,持守节操,是区分道德境界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韩诗外传》首先是一部儒家经师的《诗》经讲义,以宣扬儒家义理为要旨,汉初儒家经师讲《诗》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目的是:培养具有儒家精神的有道君子,着重于人的道德境界的提升。安贫乐道既然是儒家传统思想中的重要精粹,则习《诗》儒生则必然要受此训导和熏陶。因而在《韩诗外传》中,安贫乐道思想得到了完整的继承。但值得注意的是,《韩诗外传》讲《诗》时采用了以故事说《诗》的方式。这种以古人具体故事作为表达思想、阐释《诗》的方式,在缓和高深的训诂讲解带来的紧张感之余,更有一种切实的亲切感。二者形成一种张力,利于对学习者的引导。孔门弟子作为儒家思想的直接承袭者,他们的言行举止对儒家经义的诠释有着无可比拟的权威性和典范性,是对经义最好的注脚。因此,《韩诗外传》中,有许多孔门弟子安贫乐道的故事出现,形成了贫困考验主题。这些贫困考验故事富有文学色彩,对中国古代早期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
《韩诗外传》第一卷第九章记述了原宪的故事。原宪居住在鲁国,贫困到屋不遮漏、衣不蔽体的地步。肥马轩车、衣着华贵的同门子贡来看望原宪,见他窘迫至此,以“先生何病也”的耻笑相难。原宪毫不退让,严辞反驳:“无财之谓贫,学而不能行之谓病。宪贫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匿,车马之饰,衣裘之丽,宪不忍为之也。”原宪认为自己只是贫困,并不是病,学了道理却不能真正做到的人才叫病。言外之意,真正有病的是子贡,而不是自己;并批判了那些迎合世俗行事,营私交友的人;认为这些人为给别人看而学,为了一己私利而教,追求车马之饰、衣着华丽而损害仁义。子贡听后踌躇不安,“面有惭色,不辞而去。”而原宪则缓步从容,放歌而归。篇末引《诗·邶风·柏舟》中的两句诗作结:“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2] (P35)在这个故事里,原宪是一位安贫乐道的儒家君子,而子贡则以反面陪衬的形象出现。故事所设置的生活场景中,两人贫困与富贵的对比是如此鲜明。但是在两人针锋相对的言辞中,原宪对自己贫困的生活不以为意、怡然适之,对儒家之道则身体力行,自觉恪守。面对车马轻裘的生活享乐,原宪持一种超然的态度,认为以违背儒家的仁义道德来换取华衣骏马的人生享乐,君子不忍为之。原宪在道义上的持守,使他虽处贫寒简陋,却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使以富贵傲人的子贡相形见绌,羞惭而去。原宪故事是对儒家经义的具体阐述,原宪这一形象具体地表现出儒家君子面对贫困考验时所持有的坚定信念。这与结尾处所引之诗在象征意义上相契合。《柏舟》诗原意是作者自述现实境遇虽然艰难,却不能使他移心改志,以石与席的可移可卷来反喻自己意志的坚定,原宪故事着重写原宪不为享乐害义、安贫乐道的品格。在坚守志向,不为外物所移的精神境界上,二者是相通的。但诗的原意及本诗与原宪故事无涉。
《韩诗外传》第二卷第二十九章记载了子夏学道忘食的故事。孔子让子夏谈《诗》。① 子夏在回答中不但谈了诗的妙处,更表明了自己的心志:“虽居蓬户之中,弹琴以先王之风,有人亦乐之,无人亦乐之。亦可发愤忘食矣。”并引诗:“衡门之下,可以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2] (P211)
子夏是孔门弟子中又一位安贫乐道的典范。他不在乎外在生活条件的艰苦,虽身居蓬户,仍能弹琴咏唱,追慕先王的风范,甚至因发愤苦学而忘记了吃饭。这体现了儒家安贫乐道境界的高尚,也突出了儒家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性:在饮食都不满足的情况下,仍可以凭借对道德的向往和趋近来战胜肉体的欲望。子夏所言之心志,恰与所引之诗成为互证。诗见于《诗经·陈风·衡门》,是《诗经》中不多的隐士之诗,说的正是有道君子虽居处贫寒,却可以望泌水、守道义而怡然忘饥。子夏之事与诗在意义上有明显的相合之处,都表现出面对贫寒生活的安乐心态。
《韩诗外传》贫困考验主题故事中儒家君子的故事虽以单章节形式出现,但在同一主题中却形成一个群像式的画卷。另一位在画卷中占重要位置的孔门弟子是曾子。《韩诗外传》第二卷第二十五章中,子路在论述考察士人能否行义的标准时,提到另一位同门曾子。子路认为,士人能否行义,要看他是否能够甘勤苦、轻死亡、恬贫穷。曾子是他例举的能够对贫困恬然适之的代表人物。他连以乱麻作絮的粗布衣裳都没有一件完整的,糙米饭都没有吃饱过,但是如果不合于义,上卿这样的高官厚禄他也会拒绝。并引诗作结:“彼其之子,硕大且笃。”[2] (P200)
曾子在子路的描述中,是一位极度贫困的孔门弟子。故事设置的场景一方面是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能保障的贫寒生活,另一方面是能够带来无尽享乐的高官厚禄。在贫寒与富贵的选择中,曾子能够以义为重,甘于贫困的生活,不改其志,表现出面对贫困考验时儒家君子的高尚节操。章节末尾引诗见于《诗经·唐风·椒聊》。原诗是赞美一位女性体格健硕、生命力旺盛,是原始生殖崇拜的反映,此处却作为对有道之士精神境界的赞美。二者只在象征意义上有相通之处。
原宪、子夏、曾子,这些贫困主题故事中孔门弟子的群体形象传达出如下理念:道义远远重于生活享乐,作为儒家有道君子,应甘于贫困的生活,以高尚的节操面对来自现实生活的种种考验,真正做到贫贱不能移。三人以相同的安贫乐道的儒家君子角色出现在极为相似的贫寒场景中,形象地传达出儒家以义为重,以德为先的精神信念,表现出对于现实生活层面的超越。这不仅是对儒家安贫乐道义理的形象阐发,更为后世儒生面对现实生活贫困考验做出了表率。
安贫乐道在儒家学说中相系于人的道德境界,是儒家君子所必备的美德之一。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安贫乐道?经受贫困考验的艰难过程又是怎样的?《韩诗外传》借孔门弟子克服享乐诱惑的故事,来解说经受贫困考验的曲折、艰难。在《韩诗外传》的贫困考验故事中,以理性的道德精神战胜外在的享乐诱惑,是一个道义与享乐在内心交攻的过程,是在安贫乐道与富贵享乐之间艰难抉择的过程。它不啻是一种精神炼狱,只有经历过焦虑、挣扎、抉择的痛苦,才能完成精神上的蜕变,趋近于道德的圆满境界。
《韩诗外传》第二卷第五章的闵子骞故事形象地展示了经历考验的痛苦过程。闵子骞刚去谒见孔子时,面色苍白、黯淡,过了一段时间后,脸色却变得像吃了肉似的容光焕发。子贡问他是怎么回事,闵子骞答道:“我出身贫贱,来到夫子这里做学生,老师在内心修养方面教我以孝道,在治国方面给我陈述古代帝王的法规,我内心暗自喜欢。但是出门看见王公大人乘车的排场仪仗,心里又喜欢那些东西。二者在心中交攻不已,使我无法承受,因此脸色苍白。现在受老师教诲日深,平时又和同门相互探讨,明白了去就之理,再看见那些华丽的车马仪仗,视若与尘土无异。因而现在容光焕发。”结尾引诗:“如切如瑳,如琢如磨。”[2] (P127)
这一故事着重描述闵子骞经过艰难的内心修炼终于通过贫困考验的过程。故事所设置的闵子骞与子贡的对话场景中,闵子骞详细地讲述了自己面对道义与享乐时内心的矛盾、痛苦,他战胜享乐诱惑的过程,是一个在外力的帮助下通过修炼,提高自我道德境界的实践过程。这不仅是闵子骞面对考验时真实的内心感受,也是对后学有所裨益的经验和修炼心得。一旦战胜享乐诱惑,明白去就之理,道义便如同营养丰富的物质,滋养着人的身心,使人焕发出生命活力。所引之诗见于《诗经·卫风·淇澳》。诗的原义是歌颂一位风度气质美好的君子,像治骨器、玉器那样,不断努力完善自己。这恰与闵子骞故事的内涵在象征意义上相一致,都强调不断修炼、提高自身道德境界的重要性。
安贫乐道意味着对物质匮乏的超越,要求人能够以精神上的追求来战胜肉体欲望。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实在是一种痛苦的历练和难以达到的高尚境界。孔门弟子巫马期以自身事迹为普通人作出了榜样,其事见于《韩诗外传》第二卷第二十六章。子路与巫马期在韫丘山下砍柴,陈国有个姓处师的富人,在韫丘山上举行宴会,周围停着上百辆车。子路问巫马期:“如果让你没忘记你的知识,也不必使劲表现你的才能,就能像处师氏这样富有,一辈子不再见我们的老师,你愿意吗?”巫马期仰天长叹,把镰刀扔到地下说:“我曾经听老师说过:‘为了义,勇士不怕掉脑袋,志士仁人不怕死了被扔在山沟里。’你是不了解我呢,还是在试探我?大概这是你自己的愿望吧?”子路听后羞愧难当,背柴先行返回。孔子问起巫马期,子路就把这件事说给孔子听。孔子听过后,弹着琴说:“你羡慕处师氏的生活,难道是因为我的主张行不通了吗?”结尾引诗:“肅肅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有其所!”[2] (P203)
与闵子骞故事相似,巫马期故事也设置了一个贫寒与享乐对比鲜明的场景。孔门弟子子路与巫马期砍柴劳作于山下,而有钱人处师氏却在山上行宴享乐。面对劳苦与享乐在同一空间中如此强烈的现实对比,子路心摇意动,以富贵享乐试探巫马期。巫马期则是故事中意志坚定的有道君子形象。他的回答表现出自己以道义为重,丝毫不为享乐所动的高尚节操,并严辞质问子路之意。此章所引之诗见于《诗经·唐风·鸨羽》。诗本意古来无大争议,乃征人役夫“不得养其父母,而作是诗也”,[3] (P395)与巫马期故事无关。此处援引,应本于“悠悠苍天,曷有其所”的慨叹,在象征意义上是对子路心无定所之慨叹。二者之间意义上的关联十分微弱,甚至很难寻觅。由此可见《韩诗外传》正是通过字句或象征意义上的联系,用诗对故事的意蕴加以规约,使故事喻义最终归于《诗》学范畴。
如上文所述,在子路的描述中曾子是一位恬于贫困的儒家君子,《韩诗外传》以曾子为主人公的两个章节中,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他难能可贵的安贫乐道品格。
曾子在孔门弟子中以孝闻名于后世。孝在儒家道德伦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君子必备之德。贫困考验主题中,道义与享乐之间的冲突也往往通过孝体现出来。《韩诗外传》第七卷第七章载有曾子的一段自述。他曾经做小官,俸禄很低却很高兴,这是因为可以用它来奉养父母。后来在楚国得封高官,地位尊贵,但却常常北向而泣,是因为不能以此奉养父母。结尾引诗:“有母之尸雍”。[2] (P609)
曾子在此是一位以孝为重、以享乐为轻的君子形象。在自述中,他将孝置于享乐之上,认为孝与享乐之间有着巨大的价值落差。尽孝时虽贫寒却仍欣欣然而喜,富贵享乐时却因无法尽孝而忧伤难过。可见物质生活的匮乏或丰足已经不能影响曾子的心志,只有道义才能带来心灵上的宽慰和喜悦。结尾处引诗见于《诗经·小雅·祈父》,诗的本事是被迫外出之人因不能尽孝于父母而作,感慨自己的母亲年事已高却仍不免于家务操劳。诗的本义与曾子之事并不相类,只是在意蕴上相通,都有不能尽孝的感伤。
《韩诗外传》第九卷第二十五章中对曾子另有记述,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曾子对于享乐的超然态度。曾子请子夏吃饭,子夏怕曾子破费,曾子却说:君子有三种浪费,饮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种快乐,钟磬琴瑟不在其中。三乐三费在曾子看来,都系于道德伦理上的得失对错,而外在的物质享乐不足一提,他对道义的重视远胜过饮食钟鼓的生活享乐。曾子将道义置于人生首要位置,是孔门弟子中以坚定意志超越享乐诱惑的代表人物。
在《韩诗外传》中,闵子骞、子夏、曾子组成了孔门弟子的另一组群像。他们在展示崇高道德境界的同时,也反映出经历贫困考验、战胜享乐诱惑的痛苦与艰难。而一旦通过考验,战胜诱惑,其道德境界便焕发出耀眼的光彩。他们与原宪、巫马期等孔门弟子一道,构成了儒家诗教中安贫乐道的君子图。这种同类角色、同类主题的反复出现,增强了《韩诗外传》传达道义的权威性,对于儒家后学具有很强的引领作用。
《韩诗外传》在讲述孔门弟子的贫困考验故事时,不惜加入想象、虚构成分,将两个人的形象捏合到一个人身上,典型化特征十分明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原宪故事。这一故事在先秦两汉的典籍中还见于《庄子·杂篇·让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新序·节士》。对原宪故事在不同典籍的形态进行比较,可以梳理总结出其叙事手法的发展演变。
《庄子·杂篇》成书时间虽多争议,但作于汉代之前,这是没有疑问的。其中《让王》篇有关原宪的记载,是现存的原宪故事的最早版本,相对来说比较简略,但也已初具规模,是之后其他典籍中原宪故事的蓝本。《庄子·杂篇·让王》之后,最早出现的是《韩诗外传》中的原宪故事,两者在形态和情节上都有较大的不同。
首先,《韩诗外传》中对原宪住所、子贡形象的描写与《庄子·让王》中的原宪故事几乎完全相同,仅有个别字词的差异。但是在对主人公原宪的形象描写上,则有较大出入。《庄子》中,对原宪开门见子贡时的描写只有一句:“华冠縰履,杖藜而应门。”而《韩诗外传》卷一,则在此基础上更加生动形象:“原宪楮冠黎杖而应门,正冠则缨绝,振襟则肘见,纳履则踵决。”
其次,《庄子·让王》中,原宪反驳子贡,分辩自己贫而非病,不以仁义换取生活享乐后,戛然而止,故事到此结束;而《韩诗外传》卷一,则多了一大段对原宪的描写和评论:“徐步曳杖,歌《商颂》而反,声满于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诸侯不得而友也。故养身者忘家,养志者忘身,身且不爱,孰能忝之”。
值得注意的是,《韩诗外传》卷一这些异于《庄子·让王》中原宪故事之处,在《庄子》中也能够看到大致不差的原文,但却是描写孔子的另一高徒曾子的。
《庄子,杂篇·让王》中原宪故事的下一段便是曾子的故事:
曾子居卫,缊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屦而踵决。曳縰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4] (P760)
比较两种文本,《庄子·让王》这段故事除开头两句描写曾子的话外,其他都可以在《韩诗外传》卷一的原宪故事之中找到,只是被移来描写、评论原宪。可以肯定地说,《韩诗外传》卷一中的原宪故事是《庄子·让王》篇原宪故事和曾子故事的杂糅。
《韩诗外传》的作者韩婴作为汉初经学大师,既然采用了《庄子》中原宪故事的素材,必然也熟知曾子的故事。在《庄子·让王》中,曾子是一位与原宪同类的孔门弟子,有着同样高尚的安贫乐道品格。韩婴在处理原宪故事时,作为一位经师,充分考虑到讲经叙事的需要,把《庄子·让王》中曾子的形象和情节移置到原宪身上,塑造出一个更为典型的儒家君子形象。和《庄子·让王》相比较,《韩诗外传》把原宪形象塑造得更为丰满、传神,故事情节更为完整,意蕴也更为丰富,这一故事的艺术性及感染力也大大增强。可以说,这是韩婴对《庄子·让王》中原宪故事和曾子故事的整合与再创造。
韩婴的这一创作手法在今天看来似乎十分平常,类似于鲁迅先生所说的“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亦即现代小说创作中常用的典型化手法。韩婴的典型化手法只是相对简单地将两个安贫乐道之士糅合成一个,但这对中国早期叙事文学的发展却有着重大的意义。韩婴在原宪故事中对于不同历史人物进行的改造、杂糅,可以说,已经带有小说创作的意味,而且是为突出人物形象、增加艺术感染力和生动性而有意为之。
《韩诗外传》中贫困考验故事采用踵事增华的笔法,与韩婴的儒家经师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作者有意为之。
首先,这是孔门弟子在儒家中的地位决定的。曾子、子夏等是孔子的亲传弟子,儒家学说创始阶段的代表人物,儒家道义的直接继承者,后世儒学的传授者,毋庸置疑,他们在诗教中的地位最为重要,他们的言行举止最具有权威性,其表率和示范作用也最大。因而,《韩诗外传》贫困考验故事中,孔门弟子的形象高大丰满,着笔用墨也最为下力。
其次,韩婴作为儒家经师,是儒家学说的持守者和传授者,对儒家教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不可动摇的信仰。因而在讲解孔门先贤时,文笔不但详尽生动,更富有激情,笔下的人物品德高尚、形象完美、栩栩如生。
对于《韩诗外传》的这种叙事手法,后世颇有微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认为《韩诗外传》“其书杂引古事古语”,但“所采多与周秦诸子相出入。”[4] (卷16《经部十六》,P461)这种评价符合客观事实。但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从解经训诂的角度出发,认为这是《韩诗外传》的缺陷,“然韩婴采掇杂说,前后已自相违异,岂可引以诂经?”[4] (卷129《子部三十九》,P3325)清代经学注重考据,且对于经学更是以与史实相符为首要标准。《韩诗外传》与诸子著作中的相异及其故事中自相抵牾之处,必然为清人所诟病,但这却是汉代讲经、诂经的历史事实,也是今文经学为确立儒家权威所做的努力。不拘泥于史实及古书、追求艺术感染力、以生动的描述、典型的人物形象来解说经义,正是韩婴作为经师的匠心所在。从两汉时期的叙事文学来看,这也正是《韩诗外传》宝贵的文学价值。
《韩诗外传》这种文学性很强的叙事笔法,在汉代得到了认可和继承,这从《新序》中的原宪故事可以略见一斑。《韩诗外传》到《新序》中的原宪故事,使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早期叙事文学发展的一条脉络。
刘向所编《新序》中的原宪故事,通篇与《韩诗外传》只有7处差异,即:改“茨以蒿莱”为“茨以生蒿”;改“子贡”为“子髋”;改“槠冠”为“冠桑叶冠”;删“轩车不容巷而往见之”为“轩车不容巷”;简“车马之饰,衣裘之丽”为“舆马之饬”;改“原宪乃徐步曳杖歌商颂而反”为“原宪曳杖拖履,行歌商颂而反”;文章结尾在引诗之后,补“此之谓也”一句。[5] (P235)这7处都是行文中一些字句使用上的细微差异,在意义上无甚区别,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可以说,《新序》中的原宪故事是对《韩诗外传》的完整采用。不止原宪故事,《新序》中更有杂事中的樊姬故事、史鱼故事、周舍故事,节士中的郑相拒收鱼故事、石奢故事,等等不一而足,都与《韩诗外传》中的某些章节极为相似,有的甚至相同。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新序》与《韩诗传》完全相同的共22条,文字出入较大而又缺诗者,共10条,待继续查证的,共14条。[6] (第3卷,P43)可见《新序》一书对于《韩诗外传》全面、大量的吸纳。
《新序》一书的性质及其与早期小说的关系,在学界中早有学人予以关注。他们分别从《新序》的创作手法、形态特征、叙事模式等多方面进行了考察,认为“具有较浓厚的子部小说特征”[7];“类似于小说”[8] (P460);也有学人直接将刘向的著作称为“中国早期小说”[9]。姑且不去追究《新序》是否确属于小说体裁,但它与早期小说的紧密关系则是学界的共识。但是,许多学者在研究古代小说的发展脉络时,从先秦诸子散文直接跨越到刘向的《新序》、《说苑》,似乎从先秦诸子到刘向是一个直接的传承关系。这样的论证忽略了小说发展中很重要的一环,即:今文经学。《新序》中的许多小说叙事因子及材料直接来源于先秦诸子之后的《韩诗外传》。
其实,刘向的《说苑》、《新序》是本经立义,《韩诗外传》则是讲述《诗经》的教材,二者都和经学存在密切的关系。如果在充分揭示《说苑》、《新序》与中国早期小说关联的同时,对于《说苑》、《新序》对《韩诗外传》的继承关系加以梳理,就会从一个侧面把握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双向互动,把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可以说,《韩诗外传》中对于古事古语作有意的生发、敷衍,不拘于先秦典籍的相关记载,这种手法是后世小说创作中想象、虚构与典型化的先声。《韩诗外传》有意为之的典型化手法、加入想象成分的叙事风格,影响了汉代的叙事文学,成为一脉相承的叙事文学传统,即由《韩诗外传》到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再到葛洪的《列仙传》,皇甫谧的《高士传》,叙事的虚构、想象成分逐渐增加,侧重于以故事讲说义理,追求情节的生动曲折和人物形象的丰满传神,虽以史实传说为本但却出入自如。这就形成了与实录型史传体叙事文学相互辉映的另一流脉。《韩诗外传》本身所具有的小说因子和小说形态在中国早期叙事文学研究中应引起更多的重视。
注释:
①他本有作“《书》”。此处从屈守元笺疏。“《周》云:‘孔丛子论书,《诗》,并作《书》。’赵校‘诗’作‘书’,下同。云:‘读《书》’,本皆作‘读《诗》’,案:《尚书大传略说》、《孔从论书篇》皆是‘读《书》’,此以下所论亦是《书》,其作《诗》者,疑后人习读《论语》因妄改此。今据二书,以复其旧。守元案:此作《诗》,亦自可通。古事传闻,每多歧出。赵改此从彼,既无确证,殊不足据。”见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巴蜀书社,1996年3月第1版,P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