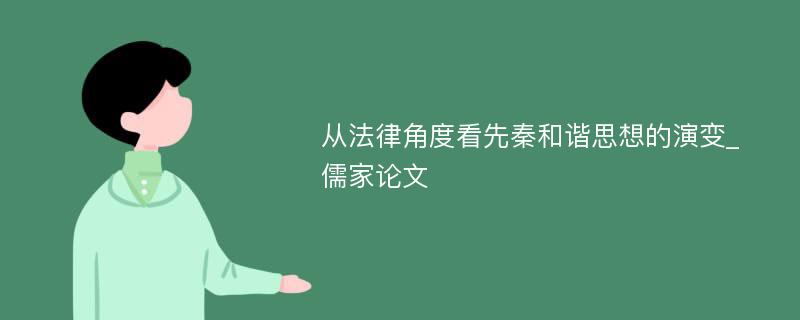
法律视域下先秦和谐思想之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先秦论文,和谐论文,思想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6)05—0071—05
“和谐”一词虽未见于先秦文献,但代表和谐理念的“中”、“和”等语汇则多散见于先秦经史和诸子著述中,并深刻影响着传统文化的走向。虽传统文化几经起落,但直到今天,和谐再次成为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主流话语。从全景扫描看,和谐是一个涵盖比较广的大概念,既有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也有政治和谐、社会和谐、经济和谐、文化和谐等不同界域。法律和谐在先秦时期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往往表现为政治和谐下的德刑并用、礼法兼施,是“人治”与“法治”① 交相互补的混合体。本文主要是从法律的视角,对中华文化源头时期的和谐思想进行研究,以期对厘清先秦和谐理念的原初内涵有所裨益。
一、从“天人合一”到“则天行刑”
正如“和谐”一词非先秦语汇一样,“天人合一”一词的使用也是先秦大统以后的事,但溯其源流,学界普遍认同“天人合一”思想在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中就已经出现。《周易》对天、人关系极为重视,它把世界分为天道、人道、地道“三极”,认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易·说卦传》)强调以天之道证成人之道。通过对天尊地卑的自然现象的体认使阴阳、刚柔的关系神秘化,进而证成“贵贱位矣”的等级秩序乃天经地义、自然天成。《周易·系辞上传》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作为世界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则,认为天道规律是人道的圭臬,“法象莫大乎天地”。人通过观象于天地自然,预见到吉凶悔吝等事态变化,从而察往知来,顺势而为,“明于天之道”的目的就在于“察于民之故”。古人认为天对人类社会是有神喻作用的,所谓“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只有顺应天道规律的“圣人”才能具有交通天人的功能,与天地相交感。
其实,“天人合一”观念的提出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是原始先民在与自然发生依赖和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对自然的认知,逐渐清晰起来的一种自然观,主要讲的是天与人相交感。因此,天人合一的提出不是周代才有的,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已经把天对人世的主宰纳入政治伦理的范畴,认为地上的君王乃是受命于天的,商纣王就自负地认为:“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周人虽不是天人合一思想的肇始者,但周人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发展成熟注入了新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周人提出了天德观,认为天不是无条件地眷顾地上的君王,“天命靡常”(《诗经·文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对天人关系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儒家继承了周初的天德观,将天人合一与仁政、德政联系起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就是用天道秩序来劝谕人世帝王要行德政。而行德政的核心就是中和,是对“天道尚中”规律的奉行。孔子认为自然界中万事万物包括日月运行、四时更迭、百物化生等都是“时中”的,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礼记·中庸》)。有鉴于“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孔子敏锐地提出要把天道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将“天道尚中”作为为社会定典的标准和范式。孔子之所以推崇尧舜为圣人,就在于尧舜能比较成功地将天道应用于人道中,“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达到天人合一。
与儒家不同的道家认为,天地自然的和谐相生是一种至美的境界,天人关系应该是人顺应自然天道,《老子·第二十五章》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天人关系运用到政治上就是无为而治,即“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与道家的无为相比,《墨子·天志》认为“天欲义而恶不义”。而这个义就在于“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是谓天德。”这个天德在人世的表现就是“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义成为善政的标准。并进而认为天有赏罚的功能,“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法家则把天人合一更多地与刑罚联系起来,将天地四时的递嬗与刑杀联系起来。如《管子·禁藏》:“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通过赋予四季以不同的特点,为刑杀以时提供了自然法依据。
天人合一不仅是先秦时代占据主流的政治伦理观念,而且对法律制度的建构也有深刻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则天行刑”等法律理念中。
在古人看来,“刑的本身便是剥夺宇宙间生命的杀戮行为,与四时生杀的自然秩序的关系更为直接,更为密切。”[1](P283) “则天行刑”就是天人合一、生杀以时思想在法制上的体现,其主旨就是因循天道来制定并执行法律,并赋予阴阳四时以赏罚的拟人化特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有言:“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至于为什么春夏有赏、秋冬行刑,《管子·四时》做了较系统的阐释:“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其又曰:“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德刑不失,四时如一。”《礼记·月令》也赋予时令以不同物理,并将之与德刑的施用联系在一起,认为春夏都是生长的季节,因此要施德政,故于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孟夏之月,“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而秋冬则是收藏的季节,则应以刑罚为主,遂有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博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绝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孟冬之月,“行罪无赦”;仲冬之月,对“相侵夺者,罪之不赦”,且“筑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闭藏也”。天人合一观念不仅深刻影响着先秦法制,而且对后世也流弊深远。刑杀以时、秋后问斩等都作为古代法律文化的惯例延续了几千年。
二、从“德刑相参”到“知止不犯”
在三代递嬗中,德与刑的施行却因时代不同、世道不同而各有偏重,体现为德刑相参,宽猛兼为。但总的看,明德慎罚无疑是主流话语,而且经过儒家的发扬光大,逐渐成为先秦时期有为君主和政治家普遍认同的治国原则。
《尚书·康诰》:“唯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把明德慎罚当作先王古制而奉为为政治国的圭臬,要求作君主的要为政以德。在周初政治家看来,德绝非一个简单的字符和口号,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且自成体系。如《周易·系辞传》中把一些卦的义理与德政有机联系在一起,认为“履(也就是礼),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周易》并没有停留在以天道规律来指导人们日常生活上,而是旨在建立一种政治秩序。而这种秩序的基础就是民,为了稳固这个基础,就要为政以德,敬天保民,保合太和。强调为上者要爱惜在下者,“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周易·益·彖》)而反对损下益上,反对对人民的严苛盘剥,警示说“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周易·剥·象》)。体现了敬天保民的民本思想。
在强调德政的同时,先秦政治家、思想家也辩证地认为要重视刑罚的作用,做到礼法兼用、德刑并施。据《尚书·尧典》记载,尧任命皋陶负责司法,“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对于“元恶大憝”和“不孝不友”之徒,则“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周易》)。也强调要“明罚敕法”(《周易·噬嗑·象》),对触犯王法者,根据情节,处以“屦校灭趾”、“愀校灭耳”等轻重不同的刑罚。《周礼·地官司徒》中大司徒的职责主要是:“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早不信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尚书·尧典》中还记述,尧任命契为司徒时,特别指示:“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要求体现宽宥的为政原则。同时指出要充分发挥刑罚本身的教化功能。“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通过刑罚自身的教化功能达到以刑去刑、以杀去杀的目的。《周易》在强调“赦过宥罪”(《周易·解·象》)的同时,也主张对疑难案例要“以议狱缓死”(《周易·中孚·象》),对轻罪要“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周易·旅·象》)。对童蒙之人(指未成年人和智障人)网开一面,使其“用说(脱)桎梏”(《周易·蒙·初六》)。对那些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的顺民则适当宽纵。
在强调明德慎罚,告别是在每每论及刑罚施用时,先秦政治家、思想家都反复强调要慎用刑,要恤民,重要的是要加强教化,使民知止不犯。古代君王治国之术往往与渔猎之人的网捕之道相似,如采取“王用三驱失前禽”① 的“三驱”之法,教民知禁而止,知止不犯,做个良臣顺民,不致触犯法网,破坏纲纪。而昏虐残暴的君主则往往“不教而杀”,意在“罔民”。孔子继承了周初明德慎罚的观念,进而提出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为政观和“宽则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的宽猛相济的中和思想。但孔子始终把教化作为为政的根本,希望通过教化使人们自觉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儒者所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总的说来,“尽管孔子在宏观上强调德政教化,而相对轻视政令刑罚的作用,但这并不等于一般地否定法律刑罚的价值。法律刑罚作为临时的局部的一种手段有其必要性”[2](P49)。
先秦时期的明德慎罚、德刑相参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西汉董仲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德主刑辅、原心定罪,并成为几千年奉行的圭臬。但这也导致一直以来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混淆,现代化法治无从确立的一个重要原因,成为中华法系的一大痼疾。
三、从“刑罚尚中”到“法尚公平”
“中”是和谐的重要表现形式。刑罚尚中则体现了法律中的和谐观。到了周朝,“中”则被当作能够致“和”的刑罚原则而频繁地运用,具有折狱持平、不枉不纵、无所偏颇之意。《尚书·立政》在谈到断狱时,强调:“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这里的“中罚”也即刑罚尚中,实质上就是在运用刑法规制时,要做到“咸庶中正”(《尚书·吕刑》),“不中不井(古刑字)”(见西周《牧簋》铭文)。
作为集中记述周初法律制度的《尚书·吕刑》篇对刑罚尚中原则有比较具体系统的记载。在法理上,强调“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今往何监,非德于民之中,尚明听之哉!哲人惟刑,无缰之辞,属于五极,咸中有庆。受王喜师,监于兹祥刑”。从而把刑罚是否中正和宜作为是否为祥刑的判准。在司法诉讼上,强调“非佞折狱,惟良折狱”,听讼过程中折狱官员要“两造具备,师听上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重申“明清于单辞,民之乱,罔不中听狱之两辞,无或私家于狱之两辞”。从诉讼形式到断案原则都为听讼折狱者设定了兼听两造,不偏听偏信的工作规程,并进而提出了疑罪从无的赦宥原则,即“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集中体现了宽法慎刑、彰明德治的刑罚尚中思想。在定罪量刑上,强调“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量,上服”。提出了“刑罚世轻世重”的刑罚时变观。
除了《尚书》,先秦的计多法律文献也有类似“刑罚尚中”的记述。如《周礼·秋官司寇》的“断庶民狱讼之中”,“求民情,断民中”,“狱讼成,士师受中”;《国语·晋语》的“鬻国之中”;《左传·文公元年》的“举正于中,民则不惑”;《礼记·大传》的“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继承了传统“尚中”观念,生发了“中庸”思想,把“执中”、“用中”视为一种治国之道,讲求适度、适中,反对“过狱不及”,体现在刑罚方面,就是“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随着时代由春秋而战国,刑罚尚中思想逐渐发展为法尚公平。张晋藩先生也认为“中国古代度量衡的发展与应用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联系着的,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因此以度量衡器比喻法律也只有在战国地主经济兴起的时代才是可能的”[3](P55)。这个时期,法字的使用已经由含义比较宽泛的广义“法”逐渐向法律意义的“法”的概念靠拢。“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子·定法》)“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悬命也”(《管子·七法》);“法者,天下之程序也,万事之仪表也”(《管子·明法解》)。尽管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根据法字的三点水而把法解释成“平之如水”已经遭到人们的质疑,但其判定“法,刑也”是持论公允的。而且法的特点就是公平,虽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平之如水”,但在先秦思想家那里,法的特点却与度量衡更为接近,其功能仍主要在于衡平。《管子·七法》曰:“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管子·七臣七主》曰:“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意林》引《慎子》佚文:“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商君书·修权》曰:“法者,国之权衡也”;“先王悬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曰:“椎鍜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矫不直也。圣人之为法也,所以平不夷,矫不直也。”这些都说明在战国时期法家那里,法是用以规范和权衡人们的行为是否合规中矩的度量衡。特别是韩非子继承了商鞅的“刑无等级”的思想,而进一步提出了“法不阿贵”的主张,认为“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从而使法尊崇为“不别亲疏,不辨贵贱,一断于法”的绝对权威,“以法为断”逐渐成为法家眼里“大治”的标准。
从这一嬗变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先秦和谐思想在法律上体现为先是强调“刑罚尚中”,后逐渐为“法尚公平”所取代。但不管是重视德化的刑罚尚中还是侧重法制的法尚公平,其体现的都是一种和谐理念,是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不同解读。
四、从“讼不可长”到“定分止争”
在由野蛮向文明递嬗的上古社会,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争讼也随之出现。在春秋以前,人们对争讼是正视的,认为诉讼是客观存在的,“饮食必有讼”(《周易·序卦传》)。《易经》八八六十四卦中专门有讼卦,而且其内容也是客观记述诉讼的过程和结果,并没有明显的无讼意思表示。无讼思想是《易传》作者对《易经》讼卦的发挥。《易传》根据讼卦初六“不永所事”而提出“讼不可长”,告诫人们不要挑起诉讼;根据九二“不克讼,归而逋”,指出“自下讼上,患至掇也”。认为下告上是招来祸患的根源;根据上九“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而认为“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认为当事人即使在获诉受到赏赐,在人格上也不足以被人尊敬,从社会伦理上对争讼做出了否弃;并根据卦辞中的“终凶”,断言“讼不可成也。”表露出儒家无讼的思想倾向。有学者认为,在讼的问题上,体现为“由讼卦的‘畏讼’、‘轻讼’观念发展出了《易传》的‘贱讼’、‘耻讼’”观念”[4]。杨鸿烈先生也认为这里有一个曲解或误读的问题,他指出,讼卦原意是“官司有时是可以打的,不过打得‘适可而止’罢了,谁料后来竟变为‘讼则终凶’的一个金科玉律。”[5](P26)
息讼、无讼思想实乃儒家之所生发。在孔子看来,争讼是礼崩乐坏的体现,其结果直接危及长幼尊卑、君臣父子的宗法社会秩序。因此,孔子强调克己复礼,反对争讼。对于发生的争讼,孔子也主张要尽量消弭。“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表达的就是孔子对于司法功能的思考。在他看来,司法的终极目的就是要使人们不争讼。历史记载,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司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法官。《荀子·宥坐》中记载了孔子判案的一个小故事。说有父子争讼,孔子把儿子关了起来,三个月不让相见,最后父亲主动请求停止争讼。尽管我们难以断定《荀子》中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这样的叙事应该还是客观反映了孔子强调通过人伦教化来消解争讼的观点。说穿了,儒家的和谐理念在法制上的体现主要就是强调息讼、无讼,并且与儒家一贯宣扬的德主刑辅主张相契合,幻想通过建立一整套尊卑有序的礼乐制度,使人们自觉认同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随,长惠幼顺,从而自觉认同于无讼,实现社会和谐。
但“民生有欲,不能无争,争则必有讼”(丘濬《大学衍义补》)孔子的无讼思想只能是一种理想而已。事实上,正如崔述在《讼论》所说:“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讼也者,事势之所必趋,人情之所断不能免者也。”从西周时期《鬲攸从鼎》、《曶鼎》等青铜器中记载的交易纠纷、盗抢财物等案例,到《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记载的诸如“盗徙封”、“盗采桑叶”、“父告亲子不孝”、“父盗子”、“子盗父”、“子告父母”、“百姓有债擅强质”等犯罪,我们不难看出,争讼不是减少了,而是激增了,无讼只能是儒家的一种理想。要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不能仅仅靠说教来遏止人们的独占欲和争斗心,必须采取新的更有效的手段。为此,战国时期的法家彻底摈弃了孔子以德化来止讼的观点,而强调用法制来定分止争。
《吕氏春秋·慎势》有慎子著名的兔子理论,《商君书》也记载了类似的说法:“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卖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这个故事的道理,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当物权不明确时,按照先占主义原则,谁实际占有该物,就获得了该物的物权。因此,要避免出现众人争夺物权的不稳定状况,首先要做的就是明确物权。这个确定物权的行为就是定名分。
总的说来,在法家看来,光靠人伦教化不能阻止人们之间的争斗,也不可能建立起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只有用法作为手段来明确人们的权利义务,才能真正定分止争,实现社会的秩序化。法家正视人欲,并把人的私欲和所有权不确定看作是引起争端的根本原因。《商君书·开塞》:“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生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有乱。当此之时,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商君书·君臣》:“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商君书·错法》:“人性好爵禄而恶刑罚。”面对这种情况,必须采取法制的强制手段,为人们定分,才能达到止争的目的。《荀子·富国》:“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因此,必须通过法律来定分止争,“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管子·七臣七主》)“分已后,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吕氏春秋·慎势篇》)
历史的发展既没有像儒家所设想的那样,通过教化而息讼,也没有如法家所断言的那样,通过定分而止争。因为,争讼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是私有制社会的赘疣,它必将伴随阶级社会的始终,直到阶级社会的消亡而消亡。尽管儒家的息讼、无讼思想终究是一场梦,但其对后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和为贵,忍为高”,识大体,顾大局,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与世无争,安分守己,成为一个谦谦君子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而敢于维护自己权利,好辩论是非短长的则被冠以好勇斗狠的坏名声,从事法律服务的讼师则被贬抑为讼棍。这些观念长期积淀下来,成为我们民族性中的一个劣根,并严重阻滞着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
收稿日期:2006—01—10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5B0098。
注释:
① 此处的法治与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法治意义迥然不同,这里的法治乃是法家所说的用法来治理,根本上还是人治,法只是治理的手段,而不是治国的目的。
② 此为《周易》比卦卦辞,讲的是田猎习惯和规制。凡狩猎必使虞人将狩猎区域围三面而留一面。围猎时,虞人将猎物赶出来,如果猎物朝着留出的那面逃窜则不能射杀,任其逃逸;而对往里跑的,则逐而猎之。作《易》者以田猎来譬喻管理国家、治理人民。
标签:儒家论文; 易经论文; 国学论文; 天人合一论文; 孔子论文; 法律论文; 古代刑罚论文; 先秦时代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