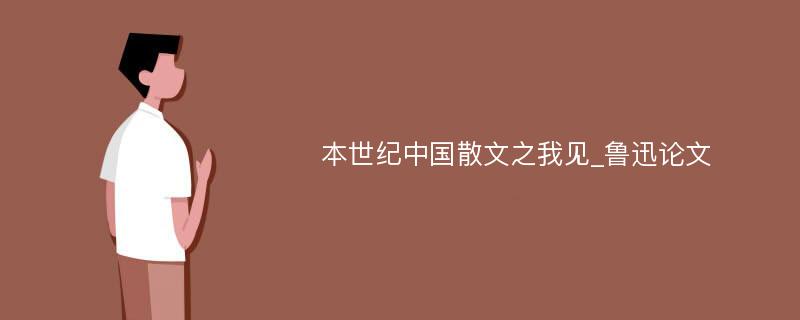
本世纪中国杂文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世纪论文,杂文论文,我见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收到一部新书,名曰《20世纪中国杂文史》。作者不断来信希望我“指谬”,友人来电希望尽快写一书评,且有报刊编辑把版都留好了。我翻了翻书,最后见书的扉页上还印有“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便叹了口气,把书放下了。一部有人出钱的杂文史,还能是杂文史么?唯有杂文这种奇异思维的产物,只能在天高皇帝远的山野之处才可自由自在。尽管作者也算朋友,但是“吾爱吾师,尤爱真理”,对于一本通行套话,滥采伪学的“杂文史”,实在少读为好。一本让人越说越糊涂的书,何必去浪费时间呢?
可是,前两天读梁任公,得到一段话,我马上改变了主意。那段话是这样的:“他(康熙)的怀柔政策,分三着实施。第一着,为康熙十二年之荐举山林隐逸。第二着,为康熙十七年之荐举博学鸿儒。但这两着总算失败了,被收买的都是二、三等人物,稍微好点的也不过新进后辈。那些负重望的大师,一位也网罗不着,倒惹起许多恶感。第三着为康熙十八年之开《明史》馆。这一着却有相当的成功,因为许多学者,对于故国文献,十分爱恋。他们别的事不肯和满洲人合作,这件事到底不是私众之力能办到的,只得勉强将就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P20)
像黄梨洲、顾亭林、万季野、全谢山那样的中国大学人,什么都可以放弃,可以不要,但是历史是不能坐失的。所以即使明知是“非我族类”的怀柔之举,也在所不惜,投入《明史》撰修之中。
和这样的祖宗相比,我算什么呢?为了真正有一本20世纪中国杂文史,为了不让杂文的真相、杂文史的真相被人故为曲笔,掩真出伪,阉割误写,我也当尽一份薄力才是。
于是再细读《20世纪中国杂文史》(下简称《杂文史》),开始尽我的气力,为这本混淆杂文真相,掩盖20世纪中国杂文史真相的书谈一点可能不无意义的意见。
2.
据说中国有几种文艺形式是无法对外翻译的,一个是京剧,一个是相声,还有一个就是杂文。鲁迅先生的杂文那样好,但据说怎么翻译,也不能让老外明白其精妙。
岂但是老外,就是国人自己,好多人也是始终未把杂文弄明白。当然,老外难懂中国杂文,是因为中国杂文中的隐喻、曲笔,非彻底明了中国社会环境、政治生态不可;而一些国人不明了杂文,首先一个难题是,怎么也弄不准杂文的定义与标准。大约从延安时代起,关于杂文的标准就开始争论不休,有说杂文是对敌斗争的武器,只能对敌人,不能对人民内部,所以鲁迅杂文已过时;有说杂文也可以批评的,但矛头不能向上,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怀着善意;有说杂文可大写赞歌,从“缺德派”变为“歌德派”的……五十多年来,争论不休,论战的结果是杂文理论书籍越来越多,够格的杂文作品和杂文家却日见枯萎。
在姚、袁《杂文史》里,作者宣布:“我们认为对杂文的较完整的表述,应该是这样的:杂文是以议论和批评为主的杂体文学散文;杂文以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主要内容,一般以对假恶丑的揭露和批判来肯定和赞美真善美;杂文格式笔法丰富多样,短小灵活,艺术上要求议论和批评的理趣性、抒情性和形象性,有较鲜明的讽刺和幽默的喜剧色彩。”(《杂文史》P5)
也许,在以往的杂文标准阐述中,这一理论貌似比较进步、公正了。可是如果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一百年来,中国现代杂文除了在三十年代以前有辉煌的起步与高峰,随后就每况愈下,在五六十年代全军覆没,直到八十年代才又有一丝悠悠活气,至今未能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为什么?
闭门细想,方才省悟,原来这个标准依然似是而非。照这个标准,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杂文,不会再有鲁迅前期的杂文。试想,这个标准中的“假恶丑”怎么判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心中的“假恶丑”是绝不会一样的,是耶非耶,几十年来从没有争明白过。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历史已一再证明,有时候“无产阶级”认定的“假恶丑”恰恰是真善美。杂文家因此就被迫颠倒黑白,如龚同文之流的“杂文”。
为何李贽、公安三袁、龚自珍、魏源、梁启超、鲁迅等人能写出那样的好杂文呢?就在于他们写杂文时,不是以这样的标准来判定杂文怎么写,他们只是以自由之精神,写独立思考之批判——杂文的本质是我手写我心的独立思想。这种独立思想,既不听命于权贵,也不是事事代表什么反对派在野派的利益,而是一种超越党派、团体的独立意见。它既不是为了推翻当政者,也不是为了建立新王朝,纯粹是一种对人性、对社会的独立思考。而这种独立思想又以短小精悍、文采盎然、生动活泼而区别于学术与文学的其它体裁。
在显学外独立自由地思想、批判(并非一定就是真理),冲破压制、阻碍,勇敢艺术地表达发表,这就是中国现代杂文的本质和标准。
而一切与此相反的杂谈,不论其是“缺德”与“歌德”,都只能是代圣贤立言的“新基调”,是准杂文、伪杂文。这是真假杂文的分水岭,试金石。
以此标准回顾20世纪杂文的兴衰,方可明白一点真相实情。
3.
不懂真正杂文标准,自然不可能看清真正的杂文史。
姚、袁《杂文史》共分五编:一编《从古典向现代嬗变的过渡》(1895-1917),二编《现代杂文的创立和成熟》(1917-1937),三编《现代杂文的全面发展》(1937-1949),四编为《建国后杂文的挣扎和沉寂》(1949-1976),五编《新时期杂文的繁荣和拓展》(1976—至今)。别的不说,仅仅是第三编,不免“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1937-1949年,是中国政治剧变动荡的时期。从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开始,日本人的侵略就把全中国人民都推向了政治生活、战争生活。这种形势对于杂文的影响,便是杂文的极端政治化、党派化。这时候,无论是上海孤岛的“鲁迅风”杂文流派,还是桂林重庆昆明的杂文作家群,都和在延安的杂文家一样,自觉不自觉地听命于党派的政治要求来写杂文。在“抗日”这面所向无敌的旗帜下,杂文家都向政治意识形态缴了械,除了梁实秋、林语堂那么几个边外人例外。自然,这种状态一时是看不出杂文政治化、党派化的弊端的,如果没有延安的杂文悲剧事件。可是偏偏在大敌当前的情形下,延安还是出现了对王实味等人杂文的残酷批判。
王实味、丁玲、萧军、艾青的杂文,无非是说作为革命圣地的延安,也还有不完满的事情,应该用鲁迅式杂文进行批判。他们没有想到,毛泽东虽然极其喜欢鲁迅杂文,声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的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是因为在毛泽东眼里鲁迅杂文是反抗国民党的,是代表共产党意见的,在毛泽东的心中,杂文是对敌斗争的工具。特别是鲁迅杂文,“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杂文是为人民大众的,这当然是毫无疑义,问题是在这里加上了“无产阶级”。如此理论一出,怎么还能再把对敌斗争的杂文用于延安呢?这是丁玲、王实味至死也都没有明白的事。他们料不到,有“鲁迅艺术学院”的延安,已经不准对“内”运用鲁迅杂文了。
一个延安整风,一个杂文家王实味死于非命,已把延安的杂文家们都改变了,而此时国统区的杂文家们,因为主攻任务依然是“反蒋”,当然还感觉不到杂文的标准已经变化,还不明白自己主动进入杂文政治化、党派化的转变,已经给自己今后埋下了苦难的祸根。在国统区的杂文家们可能不知延安发生的事情,也可能知道了也来不及细品细想。等到五十年代后他们才明白,延安杂文家的命运注定要落到自己身上。
可以说,1937-1949时期的杂文家,都陷入了杂文政治化、党派化的雷区,这种陷入,使杂文的独立性、思想性受到致命的伤害。在这样一种杂文灾难的萌芽期沦陷期,怎么能称作是“现代杂文的全面发展”时期呢?
4.
一部新专史,应该有新观念新史料。
作为一部“20世纪中国杂文史”,其对杂文大师鲁迅的评介,是检验其有无新意的关键。
可惜,姚、袁《杂文史》对于鲁迅只有陈词老调——
●他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者,而是急进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也不是一般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传播时代下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至于后期的鲁迅则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多年来,人们从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层次去概括鲁迅杂文丰富、深刻的内涵。瞿秋白从中国近代和现代“思想斗争史上重要地位”评价鲁迅的杂文。郁达夫认为鲁迅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绝不能追随的风格……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之外,别无捷径”。冯雪峰指出,鲁迅在他的小说和杂文中,“以毕生之力作了中国民族的解剖,作奴隶的被逼迫、民族的被征服的史图”,“也作了奴隶——中国大众的血战的鲜明的史图”。徐懋庸在《中国人民的胜利也就是鲁迅精神的胜利》中,指出鲁迅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一致性,看作是中国现代理论思维并峙的两座高峰。(《杂文史》P276)
这些评论当然都是有所依傍的,问题是,鲁迅的后期变化,到底是好事还是憾事?是进步还是后退?鲁迅不是神,不可能完美无缺,他的局限何在呢?
任何伟人都会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格的局限,知识面的局限。
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杂文家鲁迅,当然也难以例外。鲁迅先生的局限主要在什么地方呢?我不赞成一些人现在所考证出的新史料,说鲁迅有些尖刻、多疑,过于防御、好斗……我倒觉得,鲁迅先生之局限,关键在于他当年对于苏俄革命的全盘赞同,奋力歌颂。
时间过去半个世纪,历史的发展证明,鲁迅所想并非全是真理。就是在三十年代,苏联在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专制下,对知识分子对党内、百姓持不同意见者,也以毫不手软的方式进行镇压。这只要想想布哈林及一些苏联科学家、作家的悲惨命运,就会清清楚楚。可惜当年的鲁迅得不到这些消息,或者得到也不相信,他所不疑的,只是几个中国人匆匆采访的表面印象,如《饿乡纪程》之类。
是的,我们可以说,当年鲁迅预见不到斯大林的真相,预见不到苏联的发展和结局,是因为在当时不可能知道全部真情,不可能弄清一切内幕秘闻。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学者、一个杂文家,特别是作为中华民族魂的代表,他是否可以根据中外历史规律而预测苏俄的发展,从而对这新生事物的呐喊有所保留,有所警钟呢?以他的胆识才智,完全应该是可以的。可惜他没有。
一代伟人鲁迅尚且在这一节留下了历史遗憾,我等后生是再也不能重蹈故辙了。近几十年来,许许多多前半生极其优秀的知识分子为何都在后半生的“反右”、“文革”中丧失了人格、丧失了思想?
我们应该明确,人人所赞赏的鲁讯杂文,是不包括其后期有所迷失的文章的。鲁迅精神,主要指青年鲁迅的自由独立批判精神。所谓“鲁迅后期杂文较少片面性”的说法,恰恰是在歌颂“生病的鲁迅”。新中国以后一直以“病中鲁迅”为宣传要点,所以愈宣传鲁迅,愈无鲁迅。鲁迅后期感染的“新基调病态”,带来一场历时半个世纪的杂文的悲哀。
连鲁迅也曾在此处迷失方向,上当受骗,我等凡夫敢不百倍警惕?牢记鲁迅的局限吧,永远当一个真正独立的思想者!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杂文家最重要的教训。
5.
看起来,姚、袁《杂文史》对“新基调杂文”理论持批判态度,但其实,他们并未真明白什么是“新基调”,什么是鲁迅。在《杂文史》中,其实对“新基调”作了抽象的否定,具体的肯定。
说否定,是在书中“杂文理论研究的深化”一节里,对刘甲的“新基调杂文理论”进行了点名批驳。说肯定,则是在具体介绍杂文家时,却把一批没有独立思想、按红头文件作文,代人立言的“新基调杂文”作者排列显要地位,大章大段惠予好评。
众所周知,广东作家吴有恒在八十年代之初写过一篇著名杂文《东方红这支歌》,这篇杂文将《东方红》歌唱救星与《国际歌》里不靠救世主的歌词加以比较,第一次提出了《东方红》这支歌的反马克思主义倾向。这是何等精辟的杂文!这是何等划时代的思想闪光!这样杂文的作者,是何等重要的杂文家!可是姚、袁却在第三十五章“庾信文章更老成”——论述当代老一辈杂文家时,用“忝列末位”这样的方式来排列吴有恒:“第三节 高扬、陶白、吴有恒的杂文。”为何要把高扬排在前面呢?“高扬的杂文始终饱含着一位老共产党员关心国家的民族的命运,关注社会的进步和精神文明的炽热情怀”(《杂文史》P837),这无非是高扬曾为河北省委书记,官比吴有恒大罢了。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作省委书记的高扬怎么能写出超越意识形态、具有独立思想的杂文呢?
排列杂文家的优劣先后,到底以什么为标准?以官职和资历?以是否办过杂文报刊?以发表杂文多少?以思想正统性?不,真正的标准只有一个:谁的杂文思想是真正的深刻批判,前无古人,旁无众随,且文韵悠长,谁就是一流的杂文家;谁的独到而进步的思想贡献最多,且社会实际影响大,谁就是杂文大师与杂文领袖。
显然,《杂文史》并未真正弄懂什么叫“新基调杂文”。虽然刘甲认为“新基调”是“洗尽鲁迅式杂文基调的残痕”,“以国家主人翁的高度责任感,反映国家主人翁的呼声和情绪。”而其实,所谓“主人翁”,不就是要站在正统立场上说话么?由此,实际上,一切不是出于独立自由思想的杂文,皆是“新基调”。
当延安整风整掉了王实味、丁玲、萧军等人的杂文后,当反右、大跃进、文革扫灭了重振杂文的萌芽后,新中国杂文史基本上以“新基调杂文”为主流,所谓马铁丁思想杂谈、龚同文杂文、姚文元杂文、张春桥杂文,都是“新基调”。即便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由于传统的惯性,由于杂文标准的迷失和理论的混乱,至今也是形形色色的“新基调杂文”占据多数版面,真正的自由思想杂文不过是十之二三而已。所谓“新基调杂文,无论是从理论依据还是从创作实践上都是不能成立的”(《杂文史》P772)判断,实在是湖涂至极,睁眼不看事实。最好的事实,莫过于这本《杂文史》,其叙述语言、其杂文标准、其杂文史分期,莫不体现了“新基调杂文理论”的魔力。(连对鲁迅的理解都遵从“新基调”,遑论其它?)
6.
中国20世纪下半叶台湾的杂文,比如柏杨、李敖、龙应台的大无畏杂文有目共睹。关于“丑陋的中国人”、“酱缸文化传统”的批判,超越了政治,深入到了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深层,是和青年鲁迅最接近的当代杂文。可是《杂文史》中对此只寥寥几笔带过,而把当代杂文的高峰定在大陆作家巴金先生。巴金先生纵然有《随想录》,有倡议“建文革博物馆”之远见,但作为杂文而论,无论是质量与影响,恐怕不能不让位于柏杨李敖龙应台。巴金先生是一位一流的小说家,不能强拉他来作当代杂文的主帅。
套用党史、袭用当代文学史的某些说法来做杂文史,虽省力省事,却没有什么真正的学术好处。做杂文史就得扎扎实实研究杂文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治史,一要有新观点,二要有新史料,方可突破。可是考其《杂文史》,满纸尽是已有之文学史、党史、近代史上见过的陈词旧料,真正重新挖掘考证出来的新史料新观点几乎不见。
以建国前的杂文史料而言,近年来已被发现的老宣、李宗吾,都有相当精采的杂文集,在当时的报刊有众人争阅的专文专栏,至少算得鲁迅杂文的背景,具有广泛的影响。可是这些材料,在《杂文史》中一字未提。想来淹没于旧报旧刊书中的珍贵杂文史料还不知有多少。作杂文史者,岂可不去艰苦淘金?
有人曾怀疑,以鲁迅先生对中国历史、中国国民性的深刻研究,他不至于晚年全被瞿秋白、冯雪峰影响所左右,迷失在为党派而呼的杂文之途。他是否会有高尔基那样身后几十年才被披露的清醒之言呢?是否会因为长期以来鲁迅研究、鲁迅的史料、鲁迅解释权被高度垄断而失没其真相呢?
一部杂文史,欲叙述其兴衰真相,要靠其中的代表人物的兴衰真相来辅佐完成。可是姚、袁笔下的杂文家,大抵只有正面材料罗列,看不出早晚青壮的思想变化脉络,看不出时代,对一个杂文家的损伤与局限
7.
姚、袁《杂文史》把现代杂文的源头定在龚自珍、魏源,似乎也大可商榷。姚、袁认为“中国杂文从古典向现代的嬗变”,主要由于鸦片战争的炮火,是外患政治压迫的结果,“历史的辩证法总是这样:压迫总激起反抗,动地哀吟总伴着冲天惊雷,苦难总启发觉醒……”(《杂文史》P1)
其实,中国现代杂文的酿成,既是近代世界性民主、自由思想新潮的催化,亦有中国人国民性、华夏文明传统的力促。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传统,虽然在大一统的王朝建立后遭到压制,但国人以短文策论寓言曲折隐晦表达意见的习性已养成,代代相传,加上封建体制留下的纳谏之风,便给这种传统有可乘之机,于是乎历代皆有看似“体制内”实则“体制外”思维的杂文。到得明代,更有两股潮流,从而演变成类乎现代杂文的杂文。其一是辞官入寺的李卓吾。李贽在云南辞去五品官,入麻城“维摩庵”便大作和王朝正统思想格格不入的《焚书》、《藏书》,抨击传统思想和朝政时弊,其尖锐犀利之叛逆性,其思想精神之高度自由,其博学文采,都堪称是真正的鲁迅杂文之源。而另一派公安三袁,也就是晚明小品的主流,公然一反文以载道大谈性灵,以人生情感抒发的自由,以对生活感悟的独立思考而成为了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小品杂文的源头。
李贽、三袁虽然距现代杂文的产生远去几百年,但梁任公说得好,“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P2)说到底,中国现代杂文既是对宋元明道学的反叛,更是与先秦百家争鸣自由思想传统的接轨,是一种中国文艺复兴的产物。仅仅把其源头局限于魏源、龚自珍,将使现代杂文继续困于狭窄的政治话语圈。
杂文当然要对现行政治予以批判地思考,但杂文决不仅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真正的现代杂文,应该超越政治,站在对人性思考的高度,对人类的各种不公正思想予以争鸣批判。真正的杂文是思想批判、文化批判,而不是政治批判。在此原则下,自然政论杂文是杂文,生活感悟也是杂文,只要有真知灼见,便是好杂文。而以“遵命文学”为旨的“新基调杂文”,就当它是缠绕杂文之树的变态病藤,算是一种过渡景观吧。
一部杂文史,当把这些一一分门别类厘清。不要理论上否定“新基调”,而实际上又把“新基调”杂文者作为鲁迅杂文的主流人物,压在真正的鲁迅杂文家之上,与其遮遮掩掩,不如明马对阵,分而述之,倒不失公正与宽容。算是一种学术精神。
治史者,如果一时功力不够,环境不好,时间匆促,不妨学习前辈学者,先出“长编”、“史稿”(如胡适的《中国思想史长编》,《清史稿》),留有广泛征求意见的充分余地,也不失为一种诚恳的治学态度。可是《杂文史》作者偏偏要毕其功于一役,到底迫于何等功利呢?
8.
玻尔认为:“一些经典概念的任何确切应用,将排除另一些经典概念的同时运用,而这另一些经典概念在另一种条件下却是阐明现象所不可缺乏的。”(《原子论和自然的描述》P9)这一理论来源于一个有趣现象:“当在理论上描述原子现象时,已知使用经典概念是有局限性的,但当解释实验结果时却又必须应用经典理论。”(《智者思路》P141)
姚、袁二人在撰写《20世纪中国杂文史》时,恰恰忘记了这类现代科学新发现,他们在全书中一以贯之地以通行的所谓经典理论和思路进行解释现代杂文史,其叙述话语已到了“新基调杂文”也不屑采用的地步。请看其中一些话语:
“这时的鲁迅已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已是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杂文史》P290)
“在这一历史时期里,中国共产党亲自创办、周恩来直接指导的《新华日报》特别重视杂文,对推进中国现代杂文有过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政论大家无疑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位极富诗人气质的伟大政治家和伟大思想家,他的不少著名政论和演讲,如《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及评《白皮书》的那些著名篇章,都是高屋建瓴、笔挟风雷,观点泼辣、文采斐然的上乘政论文。”(P24)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论家,他的雄文四卷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这个历史功勋是永不磨灭的。”(P572)
“康(有为)文‘指引今古,洒洒万言’,有很大欺骗性和迷惑性。他针对革命派的‘仇满’、‘排满’、‘反满’主张,鼓吹‘满汉平等’,抹煞满汉之间的民族差异……”(P183)
够了,一部在如此官话、套话、假话指导下的杂文史,可以想见它不可逃避的困境与局限了。
杂文本是一种自由思想、自由批评,而撰杂文史更须有高度精神自由才能真正把握其本质。史家的“四长”(史德、史学、史识、史才),作为一个杂文史家更是要时时以勇以胆以德来统帅。一部囿于有人出钱的杂文正史,自然无论它怎么尽力打出“思想解放”,尽力批点“新基调”,实则是如来佛手掌翻筋斗,依然是一部没有杂文精神的杂文史。
“中国的现实在中国,中国的历史在剑桥。”这种史出国外的昔日怪圈何时彻底休止?但愿从恢复杂文史真相开始,我们开始走上一条复兴信史的新路。
标签:鲁迅论文; 杂文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王实味论文; 散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