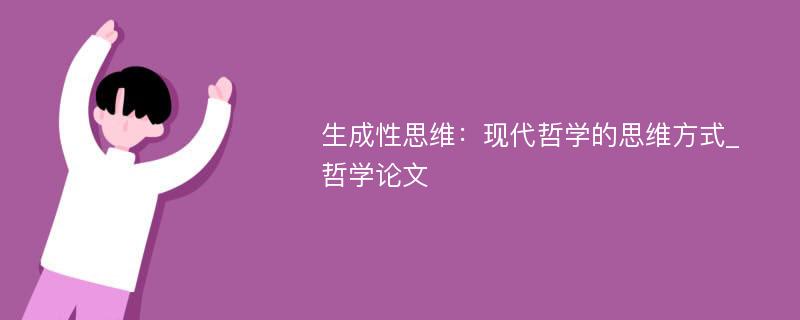
生成性思维: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方式论文,思维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哲学的突出特征是多元化。在现代,哲学的范围愈来愈广,哲学的派别愈来愈多,哲学的分工越来越细,以至于一个哲学家对另一个哲学家所从事的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工作都感到迷惑不解。然而,这不过是现代哲学的表面现象。作为同一时代的产儿,五花八门的现代哲学必然分享共同的时代特征,拥有一致的思维方式。那么,把从马克思开始的现代哲学与近代哲学区别开来的时代特征是什么?现代哲学是怎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呢?透过林立的派别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论题,我们不难发现,从马克思开始,西方哲学便出现了一个转折,即由科学世界观转向生活世界观,由本质主义转向生成性思维。生活世界观或生成性思维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和思维方式。
一、现代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近代哲学的世界观是一种科学主义的世界观。此种世界观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哲学化。它把世界视为某种外于人的、与人无关的、可计算的、本质既定的存在,而人只是这个客观世界的伟大而又渺小的旁观者(人因作为自然的仆役而渺小,又由于有了认识自然的理性能力而伟大)。这样一种世界观所蕴含的是本质主义、客观主义、理性主义、实体主义和进步主义思维,其本质是对生活或现实的人的简化、遗忘和抽象:一旦在生灭变幻的生活世界之外、之上或之后设置一个抽象的科学世界、本质或本原世界,则势必导致还原主义和普遍主义,即对事物的初始条件和状况的探寻,对原初创造者、固定本质和共性的追问,所有这些意味着对人生活于其中的周围世界、对人的当下存在状况和对人的个性的漠不关心。这样一种世界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之个性的增强和进化论的出现而日渐陷入困境。
作为达尔文之“信徒”的现代哲学家们是明确反对近代的世界观及其思维方式的。对于现代哲学家们而言,世界不再是与人无关的自存实体,而是对人有价值和意义的生活世界。虽然不同的现代哲学家对生活世界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如马克思的生活世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现实生活过程,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是前反思的日常生活(注:我们认为,人的生活可分为两类:日常的和非日常的。所谓日常生活是指自在的、自发的生活样式,主要包括日常消费活动(如饮食穿衣等)、日常交往活动(如礼尚往来、闲谈杂聊等)和日常意识活动(如日常对生活的体验、情感活动、做梦、无目的的遐想等);与此相对应,非日常生活则指自为的、自觉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主要包括实践的、理论的、艺术的、宗教的等形式。不过,胡塞尔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与我们所理解的日常生活并不完全相同:他的日常生活更偏重于日常的意识生活。),维特根斯坦的生活世界是指日常的语言交往,但他们在思维方式或对世界的理解上却是一致的,即均持某种生活世界观,均由抽象的科学世界向人的生活世界回归。不仅如此,随着现代哲学的进展,回归的呼声愈益强烈,回归的趋向也愈益明显。这通过对现代哲学的简单梳理便可以看出。
立于现代哲学起始处的马克思坚决拒斥近代的科学世界观。马克思认为,人所居于其中的世界并不是外于人的、预定的存在,他说,那种“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因此,马克思从来不谈论与人无关的自然、世界或存在,而只讲人的现实世界。而人的现实世界无非是人的实际生活过程。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8、131页。)由此,马克思批判以往的哲学是从天上降到地上,即从外在于人的物质世界或绝对理念出发来考察人,而他的哲学则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即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来说明以往哲学中的那个抽象世界的产生。
不仅马克思,其他现代哲学家也都走上了回归生活世界之路。传统上把马克思之外的现代哲学划分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派,现今又有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之分,但不论怎样区分,两派哲学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拒斥传统形而上学。不论是科学主义抑或人本主义,不论其是否重建另一种形而上学,反传统形而上学是现代哲学的一致呼声。这里的传统形而上学是指把世界视为先于人、外于人的科学世界,反形而上学就是指反对抽象地设定这样一个世界的存在,然后再从这一世界出发来考察人和事物,反形而上学的最终目的就是回到生活世界。
在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的同时,人本主义者力图建构另外一种形而上学体系。然而,这却非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追求,人本主义者并不想在摒弃了“死亡世界”(尼采语)和关于存在者的形而上学之后,再建构一个外于人的抽象世界。恰如施太格缪勒所指出的,是“导致产生世界意义和人类存在意义问题”的形而上学欲望在推动着这些形而上学者(注:参见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5页。)。现代形而上学并不是要去刻画什么与人无关的客观世界,而是试图描绘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和人对生活的现实感受。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旨在揭示孤独自我的种种存有状态——恐惧、厌烦、忧郁和绝望;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为的是破除对人的存在的遮蔽,使人的存在敞亮起来;萨特的哲学并非关于“有”或我们“头上星空”的智慧,而是对“无”或“自为存在”的考问,如此等等。
与人本主义相较,科学哲学的回归之路则相对“曲折”。早期的科学哲学(指逻辑实证主义)清除对超验物的探究,回归经验,转向语言和命题意义的分析,这也是向生活世界的某种回归。因为相对于意识和心理,经验和语言更为现实。然而,逻辑实证主义虽不再认为有一个外于人的抽象世界,但其思维却仍沉于本质主义,它对理想语言的追求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只是从后期维特根斯坦开始,科学哲学才逐渐摆脱本质主义,真正转向“现实”或人的生活。此种转向是沿着两条相对独立的道路完成的:在狭义的语言分析领域(指后期维特根斯坦及其弟子),关于语言和意义的适当解释的问题离开了逻辑原子主义的句法—语义学模式而走向彻底语用化的“语言游戏”模式,走向以生活形式为语境的语用学模式;而在狭义的科学分析领域(以库恩、劳丹、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为代表),哲学家的兴趣日益离开了那种发端于数学的辩护主义,而转向关于科学知识与社会环境、科学增长与生活(尤其是科学家的生活)的关系的探讨,转向“后经验主义”、“后实证主义”或“科学解释学”,表现出与哲学解释学趋同的倾向。而一旦把语言的意义归于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将科学与社会环境、科学家的生活联系起来,科学哲学也就由抽象世界回到了生活世界。
科学哲学回归生活的过程,实际上是现代哲学两大思潮日趋合流的过程。目前通行的说法是,合流是20世纪中叶以后才发生的,合流的标志是语言学的转向。此种说法是很成问题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什么是合流?或是什么在合?合向何处?合可以有多种意义,论题的趋同是合,观念的趋同是合,思维方式或哲学基本精神的趋同也是合。只不过前二者是表层之合,后一种才是真正的合流。现代哲学在其初生之际,虽然两大思潮相互攻讦,但当它们共同拒斥形而上学、消解传统思维时,合流便已悄然开始。当维特根斯坦转向日常语言研究,科学分析哲学转向后经验主义时,两大哲学便已合到一处。而20世纪中叶以后所发生的合流其实不过是前一过程的延续、拓展和深化,是从思维的一致到论题的合一。进而言之,20世纪中叶以后所发生的“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现代主义”运动本质上是现代精神的接续,是向生活世界的进一步回归。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后现代主义的各家各派所消解的形形色色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其实都是近代的主客二分式的本质主义的表现。当后现代的思想家批判现代哲学家时,他们所批判的并不是后者的现代性,而是其“近代性”或不彻底性。
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是现代哲学中比较明确提出生活世界理论的哲学家。胡塞尔后期认为,近代科学和哲学所说的科学世界只是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抽象之物,它是以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前科学的、非主题化的、可经验的或可直观的生活世界为基础的。前期追求理想语言的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也认为,世界并不是按照一种特定方式组织起来,然后再用语言把它的结构正确或错误地描述出来。相反,组成世界的可能性首先是通过语言表达才产生的,有多少种描述世界的方法,就有多少种把世界分为个别事态的方式。在这里,不是语言符合事物,而是语言构造事物,不是外部事物赋予语言以意义,而是事物的存在和意义要由语言来认定。既然语言的意义并非源自外物,那么它是如何得来的呢?维氏认为是由创造和使用它的人所决定的。语言的意义即其用法,语言经由语言游戏或日常的语用获得其意义。这样,不同的语境便有不同的意义,语义随生活形式的变迁而改变。海德格尔是明确反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他认为世界是人“在之中”的世界,这样的世界不是数得清或数不清的现成事物的单纯聚集,不是“单子”的总和,而是事物可能存在的条件。海氏强调此种世界与人有独特关联:动物和植物没有世界,一个农妇却有自己的世界,一件艺术品也建立了一个世界。换言之,只有人才有世界,世界就是指人居住于其中、逗留于其中、与之熟悉和交融的生活世界。对于哈贝马斯而言,世界是一个由语言交往所开展出来的、作为交往活动之背景的、前反思的、奠基性的生活世界,它是理解、知识和社会批判理论的意义基础和价值之源。由于上述哲学家分别代表着现代哲学中的现象学、分析哲学、存在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几大运动,而这几大运动几乎是现代哲学的全部内容,所以,它们由科学世界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无疑体现了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
通过上述对现代哲学的简单梳理,我们不难发现,虽然现代哲学不再追问世界的始基是什么,不再探寻认识何以可能等问题,但它并非如施太格缪勒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哲学各派之间的差异愈来愈大的过程,而是一个在思维方式上日趋走向统一的过程。换言之,现代哲学的各家各派,不论它们之间存有多么大的差异,它们均是在生活世界观之下进行思维的,均在由科学世界向生活世界回归。
二、生成:现代哲学的最强音
在一定意义上,哲学是世界观。但是,哲学的本意并不在于提供一幅世界图景,而是经由此种图景向人们展示一种思维方式,一个考察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所谓的世界观其实是“观世界”或如何“观世界”。换言之,任何世界观本质上都是某种思维方式的体现。
如果说近代的科学世界观包藏的是“本质先定、一切既成”的本质主义思维,那么,现代生活世界观所蕴含的则是“一切将成”的生成性思维。马克思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 尼采这样写到:“两种最伟大的哲学观点:生成、发展;生命价值观(但首先必须克服德国悲观的可怜形式)——这两者被我们以决定性的方式揉合在一起。一切都在生成,在永恒地回归。”(注:转引自赵修义、童世骏《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 )柏格森指出:“对有意识的存在者来说,存在就是变易;变易就是成熟;成熟就是无限的自我创造。”(注:柏格森:《创造进化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萨特强调存在先于本质,海德格尔主张此在就是它尚不是的东西。当解释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把解释、科学、语言置于特定历史情境来看待时,它们意欲表达的也是一种生成观念。可以说,现代哲学是生物进化论的产物。在进化论之后,既然哲学家们要求回到经验直观的现实生活世界,那么他们就再也不可能坚持那种本质主义的自然观,而只能充当达尔文的信徒。
近代本质主义思维的总体特征是主客二分,即在人的世界之外又设置了另外一个世界,本质主义者从那个独立自存的实体世界来描绘自己的生存,从那个世界来说明人周围世界的产生,把那个世界作为生活的理想和生命的价值意义之源,用那个世界作为判明真假信念的标准。“这是一种把真实的实在世界同由感觉,或质料,或原罪,或人的理解结构创造的现象世界相对立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异世思维方式”(科学世界即异世)或超世思维方式(神本世界即超世),它反映了人想摆脱时间和历史而进入永恒的企图。罗蒂认为,典型地表现这种异世观的,“就是解构主义者通常宣称为‘传统二元对立’的东西:真的与假的,原始的与派生的,统一的与多样的,客观的与主观的,等等”(注: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98—99页。)。
现代哲学是根本反对二元对立的。现代哲学之所以解构二元对立、主张人与世界的统一,正是为说明在人的现实生活之外并不存在一个独立自存的、作为生活世界之本源、本质和归宿的理念世界或科学世界。而既然只有一个“现世”即人的生活世界,那么认识的标准、人之活动的价值和意义便只能从这个现世即人的生活出发,在现世中或经由现世的历史来说明。从现世即现实的人或现实生活出发是生活世界观的根本旨归。当马克思要求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当胡塞尔把科学世界奠基于生活世界之上时,当维特根斯坦提出想象一种语言即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时,当罗蒂认为“必须以现实境况为起点”时,当德里达解构“在场形而上学”时,他们意欲表达的均是这样的思维,即生成性思维。换言之,生成性思维并不关注人之外的世界,也不为来世烦心。它只关心人在现世的命运,并且它只是立足于现世来谈论人的命运。
与近代本质主义相较,立足于现世的生成性思维有如下特征:1.重过程而非本质。本质主义把事物视为实体,认为在生灭变幻的现象背后存在永恒不变的本质。而在现代哲学面前,一旦回到生活世界,一切对立的东西就消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就溶化了。“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44页。),是一股绵延不绝、奔腾不息的涌流。既然一切都处在产生和灭亡的无限过程中,那么,人的存在便只能是指人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人必是其非是、非是其所是(萨特);语言因而就不存在固定意义,而是依赖于特定语境中的应用(语言哲学);我们才不能想象,“有朝一日,人类可以安顿下来说,‘好,既然我们已最后达到了真理,我们可以休息了’”(注:罗蒂:《后哲学文化》,第84页。),等等。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现代哲学何以要强调时间、重视历史,不难解释“过程哲学”的出现。2.重关系而非实体。所谓实体即是自我封闭、孤立自存的单子,近代的科学世界就是由一个个单子组成的实体世界。而现代哲学则认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卷,第733页。),其中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处于与其他存在物的内在关系中:人是“大写的人”,是“共在”;人与自己的生活世界也是内在统一的,人在世界中,而非世界在人外;人无非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语言也是关系,单个词并不具有孤立意义,语词的意义就是在与其他语词的关系中获得的。“一个句子的意义,同一个信念或一个愿望的意义一样,是其在一个其他句子或信念或愿望网络中的位置。这样说也就是强调符号和思想对上下文的感受性,也就是把语言和思想不是看作事物而是看作一个关系网络中的交点。”(注:罗蒂:《后哲学文化》,第150页。)3.重创造而反预定。 本质主义并非不承认世界的生灭变换,但它却把生灭变换看做假象或现象,认为过程的本质在过程之先、之外便已预成或者命定,如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演化之过程即是如此。既然过程在过程之先便可预知,那么,所谓的过程就只有“流”,而没有“变”,即无发展和创造。这样的“过程”不是生成,而是流程,因为生成的核心是创造。现代哲学家们认为,未来不可能完全预存于现在。未来的不可预知性就意味着过程的创造性。在谈到现代哲学何以反叛近代哲学时,罗蒂指出,“对科学、‘唯科学论’、‘自然主义’、自我客观化、以及对被太多的知识变为物而不再成为人等等的恐惧,就是对一切话语将成为正常话语的恐惧……这种情况令人惊恐,因为它消除了世上还有新事物的可能,消除了诗意的而非仅只是思考人类生活的可能。”(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37页。)4.重个性、差异而反中心、同一。 本质主义并不是设定单个对象的本质,而是设定对象的共同本质,它试图把复杂的对象归结为简单的整齐划一,试图消融差异,在二元或多元对立中确立一个中心。而生成性思维是与此种同一主义、中心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因为,既然过程是创造的,本质是生成的,那么,不同的过程、同一过程在不同的时间便会有不同的本质。这样,差异是实在的,无差别的同一不过是抽象,追求抽象的同一性,抹杀个性和差异,只能导向权威主义和等级秩序,最终消解创造,否定生成。所以,现代哲学家们倾力批判了形形色色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如人类中心主义、客体中心论、语音中心论、男权中心主义、价值一元论、文化一元论、哲学的王者之位、道德理想主义、对本原和终极理想的追求等等,并由此转向了各种各样的非中心论,如后人道主义、后哲学文化、复调文化、价值多元论、道德相对主义等等。利奥塔德大声疾呼:要“向整体性开战,我们要证明不可描述性,我们要激活差异性,我们要拯救差异性,我们要拯救名称的荣誉”(注:转引自张国清《中心与边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阿多尔诺认为,同一性是不真实的,而“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注: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对于后哲学文化, 罗蒂是这样理解的:“实用主义者乐于见到的不是高高的祭坛,而是许多画展、书展、电影、音乐会、人种博物馆、科技博物馆,等等。总之,是许多文化的选择,而不是某个有特权的核心学科或制度。”(注:罗蒂:《后哲学文化》,第153页。 )也正是出于对个性和差异的关注,当代西方才会产生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边缘性话语,许多边缘性学科(指交叉学科)、边缘性问题(性史、监狱、日常生活、常人)的研究才会生发出来。可以说,整个现代文化愈来愈呈现出从一元向多元、从中心向边缘、从绝对向相对的演化趋势。5.重非理性而反工具理性。近代本质主义是与理性主义相联的,本质主义不仅设定了世界和人的理性本质,而且将理性数学化、工具化。现代哲学认为,此种可计算的理性观念不过是权力、永恒、绝对、同一、上帝的代名词,它消融了个性、差异和创造。它在被人变为统治的工具的同时,也成为奴役人的工具。所以,从克尔凯郭尔、尼采到福柯、德里达等现代哲学家都对此种传统理性展开了批判。尼采称理性哲学家为制造木乃伊的人,认为“他们缺乏历史感,他们忌恨生成观念”。利奥塔德提出“理性与权力是一个东西,是同一的”(注:转引自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109页。)。德里达要解构的逻各斯不过是传统理性的另一种说法。在摒弃了“一只眼的理性”之后,现代哲学家们或者转向非理性,或者转向一种“合理的”理性观念,前者如尼采、叔本华(意志)、克尔凯郭尔(体验)和柏格森(直觉),后者如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罗蒂(理性即宽容态度)等。但是,上述区分是相对的,“两类”哲学家事实上均否定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均认识到传统理性的片面性,均不同程度地把理性与非理性统一起来。如罗蒂所言,在把理性解释为“清醒的”、“合情理的”之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区别与艺术同科学之间的差别就没有什么特别关系了”(注:罗蒂:《后哲学文化》,第78页。)。尤为重要的是,上述思想家不论是强调非理性还是推崇新理性,均是为了保证个性、差异和创造的存在,因为非理性是个体的、偶然的,而谈话中的宽容则意味着允许他人自我的存在和“反常话语”的出现。6.重具体而反抽象主义。本质主义即是抽象主义,即对事物、世界本质的抽象设定和对抽象本质、抽象思维的尊崇。既然现代哲学否定了本质物的存在,那么它便理所当然转向对生活世界一个个不能相互归属的具体物的研究。走向具体性是现代哲学的一般趋势,这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哲学主要关心的是具体的东西,或与人的现实生活相关的东西,如语言、科学发展、日常生活、人的现实存在状况等等。这在一些哲学家那里甚至表现为对所有整体的东西、宏观的东西的拒斥,表现为对琐碎、微型、个体性东西的无休止关注。其二,不再用一种抽象的眼光来看待事物,而是就具体物本身来研究具体物,把具体物放置到具体的、历史的现实情境中来看待。马克思要求从现实出发,现象学要求回到“事情本身”,罗蒂主张以“现实境况”为起点等等,说的均是一个意思。现代哲学之所以关注历史性,其意义也在于此。实用主义就认为:“为了说明‘真理’、‘知识’、‘道德’和‘德性’,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回顾这些术语在其中产生和发展的文化的详情细节”(注:罗蒂:《后哲学文化》,第260页。)。
并不是现代的每一位哲学家都清楚明白地表达出上述思维,生成性思维本身也有一个生成过程。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生成性思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60年代之前,现代哲学与近代哲学之间主要表现为“论题”的转换,如胡塞尔所指出的,近代哲学视世界为科学世界时,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物所附有的文化特性(注:参见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60年代前的哲学家正是要试图把失落了的主体、精神和文化寻找回来,重新融入世界。换言之,60年代前的现代哲学家更多地是从论题追溯到思维方式,从人学出发追问到近代人学导向人的失落的原因。所以从一开始,此一时期的哲学家便是“建设性的”,即他们否定近代哲学的目的是为建构另外一种人学。此种建设性目的使得其中的一些哲学保留了某种形而上学的形式,并与近代哲学之间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或相似。60年代后,随着解构主义的兴起和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完成,哲学问题的语境完全改观了,哲学不再从论题入手,而是从思维出发,哲学的直接目的就是要解构传统思维方式,所谓“人的终结”只是“反……”、“非……”、“否……”的副产品。即是说,此时的哲学家是“反动性的”,只是要摧毁,而在摧毁的同时却又避免有一个自己的观点(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第322—323页。)。所以,他们不仅批判近代哲学,而且也指责他们之前的现代哲学,并把后者归于近代哲学(统称为“现代”,而称自己为后现代)。60年代后的现代哲学尤其是以解构主义为主流的后现代主义,的确是在一种更为彻底的意义上解构传统哲学的。萨特提出人的本质在于没有本质,而罗蒂则认为没有本质也不是人的本质,我们根本就不能说人存在本质。看来,后现代主义不过是一种非常极端意义上的生成性思维。后面将会看到,正是此种极端性或彻底性使其陷入困境。
三、两种生成观: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
虽然同为生活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但对于生活和生成,不同的现代哲学家却有不同的理解。大致而言,现代哲学对生活和生成的理解可分为两种:马克思哲学的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这两种生成观,将有助于把握哲学的未来走向。
对现代西方哲学家而言,生活主要是指日常生活,如日常消费活动(衣食住行等)、日常交往活动(礼尚往来等)和日常意识活动(情感活动、胡思乱想等);生活世界主要是指前科学的、非反思的、非主题化的日常生活世界,即自在的、自发的、私人化的活动领域。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是一个前科学的、非主题化的世界,在提到生活世界时,他多次用“前科学的”加以限定。这里的“前科学的”是指:生活世界是一个经验的、可直观的实在世界,即一个“直接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在流动中表现自己的一个整体”(注: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第37页),是一个日常的、伸手可及的、可感的现实世界;所谓的“非主题化”则意味着:生活世界的存在是不言自明、毋庸置疑的,人们并不对这个世界的存在发生怀疑、提出问题,并不把它当做一个课题来研究,因为它是一个始终对人都有效的世界,是一个人们在其中生活但并不对之关注的世界。虽然人活着就要关注着某物,但是,要使人们对某物发生持久的兴趣,则需要另外的动机,而沉迷于日常生活中的人却缺乏这种动机。胡塞尔这样写道:“这是一个在经验中,并通过经验对我们来说才有意义和才存有的世界;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永久有效的,具有无疑的确定性的,简单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世界;这个世界具有这样那样的在特殊的实在对象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只是有时在个别的细节方面被提出疑问,或被认为是无效的假象。”(注: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第90页)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源于外物,它是在“语言游戏”中生成的,而“‘语言游戏’一词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即讲语言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9页。),所以,“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5页。)。在这里,所谓的“语言游戏”并不是规范的、科学的语言交往,而是日常的语言交往;所谓的生活形式当然也不是非日常的或自觉的、自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而是日常语言交往镶嵌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他说:“我们所做的是把字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带回到日常用法。”(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7页。)海德格尔把“在世中”看做此在存在的基本情态,或者说,视为此在存在的最基本的生活样式。“在世中”既不是现成的人存在于现成的物中,也不是主客二分的状态,而是此在在世界中的历史性的生存,是人“融身”于世界中、“依寓”于世界中、繁忙于世界中、与世界不分彼此的状态,是理论与实践混沌未分的日常生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把社会解放与个人解放联结起来,而联结的桥梁就是日常生活批判,所以,不仅卢卡奇、赖希、葛兰西、马尔库塞等研究日常生活问题,而且还形成了以列斐伏尔、科西克和赫勒为代表的日常生活学派。哈贝马斯正是在这样一个传统中生长起来的,与胡塞尔所要回归的生活世界相似,哈贝马斯所理解的、作为知识和社会批判理论的意义基础和价值之源的生活世界,也是一个可直观的、完全适于经验分析的、具有可信性的世界,“生活世界构成直观现实的,因此是可信的,透明的,同时又是不容忽视的,预先论断的网”(注: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页。)。这是一张犬牙交错、混沌未分、界限模糊的网,是一个非主题化的视野:“生活世界用我们从经验中获得的保证构筑起一堵墙,用它来抵挡那些仍然是产生于经验中的惊奇”(注:转引自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53页。)。持续的惊奇是一种主题, 而生活世界却不属于可以主题化的领域,它始终作为主题的背景。后经验主义者试图把科学发展与科学家的生活联系起来,而他们所说的生活也主要是指科学家的情感、欲望、追求、日常消费等日常活动。也就是说,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家来说,生活主要是指日常生活,生活世界主要是指日常生活世界,那种自觉的、自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主要指科学)基本上未进入他们的视野。
在现代西方哲学家的视野中,一个纯自在的、随意的世界虽然能说明人的自由、个性和生成性,但却“很难”找到共性、普遍性、规律性和确定性,而在一个没有确定性的世界,生成虽消除了限制,但也没有了历史、保证和方向。这样的生成虽然是一条永不止息的河流,但却是人无法把握的“克拉底鲁之河”。此种生成观除了陷入相对主义之外,并无它途。如伯恩斯坦所言:“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看来是他们从事的这种探索路线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注: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8页。)。
与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不同,马克思是从人的对象性来看待人的生活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人是对象性存在物,这一方面是指,虽然人有意识,但人首先是一个感性的、肉体的存在物,而人之感性说明人并非自我完满的存在,而是一个需要或依赖感性对象的存在物,人必然受对象制约——既受他物和他人制约,其精神也为感性所制约。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感性存在物,人是在感性活动中能动地表现自己的存在物,即对象化存在物。人虽受对象制约,但人不是像动物那样被动地受对象制约,而是主动去接受制约即只是由于对象被人纳入人的活动系统中,对象才制约人;只是在人创造对象的过程中,对象才限制人。马克思认为,恰恰是这种自觉的、有意识的对象化活动即劳动才把人从动物界提升出来,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劳动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是人“复现”、生成自我的过程:人不仅在劳动中创造自己的他在,而且在劳动中改变、完善着自身。如马克思所言:“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 )正是基于对劳动或对象化活动的此种理解,马克思才把生产称为生活,才用了“类生活”、“生产生活”、“生活生产”、“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商业生活”、“政治生活”、“作为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等用语。
自觉的对象化活动即劳动有多种形式,在马克思那里,他大致把劳动分为两类:物质的和精神的。前者即实践或物质生产,后者指理论的、艺术的等精神生产活动。这两类活动中,针对他生活的那一时期唯心主义盛行的现实,马克思特别强调实践的基础性地位,认为它不仅是迄今为止人类生成自我的主要方式,是人的生活的主要内容,而且制约着人的其他活动,是人的其他一切生成活动发展的基础。所以,马克思才说出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等话语。
当然,把实践置于社会生活的基础性地位并不说明马克思轻视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更不意味着他把它们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一方面,劳动本身就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马克思强调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只是为指出一种现实,即精神生产不能脱离物质生产而独自发展,但他并不认为精神生产可以归于物质生产,也不认为精神生产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相反,在他对需要的异化的揭示中,在他对自由王国的憧憬里,我们甚至可以读出他更为推崇、欣赏人的精神生活。他说:“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当然即使在这里,马克思也并未忘掉现实,所以他接着指出:“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这就是马克思,他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另一方面,虽然马克思没有使用过“日常生活”一词(当然也没有使用“非日常生活”),也并未专门论述日常生活的地位和作用,但他不仅没有遗忘日常生活,而且是从日常生活出发“推出”物质生产的基础性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9页。)同时, 他还谈到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家庭生活,认为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的产生、人口的繁殖并不是社会活动的三个阶段,而是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或“三个因素”,他进而把生育和劳动“统称”为“生命的生产”,指出它们本身都是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79—81页。)。仅从上述论述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并未刻意区分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他是把社会生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待的,在他那里,日常的、非日常的、物质的、精神的等等所有生活形式均是现实生活之内容,缺少了任何一种形式,人的生活便不再现实。也就是说,与现代西方哲学家所理解的生活世界不同,马克思所说的生活世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
生活世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统一,人的生成既非本质既定的、无创造的“流”,也不是虚无主义的、无任何确定性的、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变”;既不是随机的、偶然的生命体验,也不是从能指到能指的语言之链的任意滑动,而是继承与创造、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或流与变的统一:人之受动性和实践的实在性昭示着生成的连续性、确定性,而人之能动性和实践的创造性则意味着生成的间断性、非确定性。立足于这样一种思维,才不至于退回到本质主义,也才能避免相对主义。
标签:哲学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西方哲学家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科学世界论文; 胡塞尔论文; 哲学史论文; 科学论文; 现世论文; 世界观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