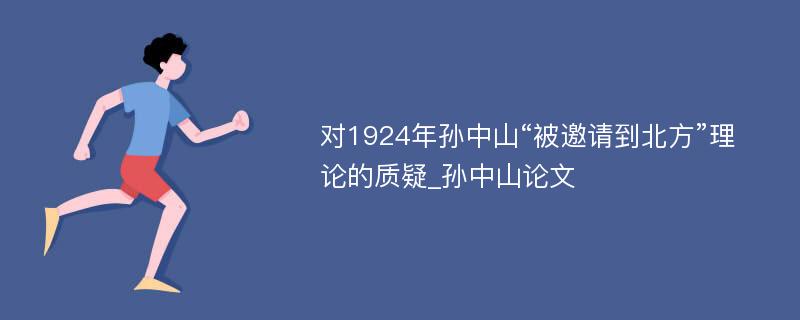
质疑孙中山1924年“应邀北上”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4799(2007)03-0052-04
“孙中山北上”指的是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11月13日离粤北上,途经上海、日本、天津到北京,直到1925年3月12日病逝这100多天的活动。它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专用名词,是中国现代史上令人瞩目的事件。长期以来,史学界盛传“孙中山应冯玉祥、段祺瑞的邀请而北上之说”,然而其依据值得商榷。如1980年出版的《孙中山年谱》(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主编,中华书局)称:“1925年10月25日冯玉祥在北京政变成功后举行政治军事会议,决定电请孙中山北上。”年谱注释说明:此说源于冯玉祥的《我的生活》。
请看《我的生活》原文:“多年以来,不断地和国民党朋友往还,中山先生把他手写的建国大纲命孔庸之先生送给我,使我看了,对革命建国的憧憬,益加具体化,而信心益加坚强,其间徐季龙先生奉中山先生之命,常常住在我们军中,教育总长黄膺白先生及其它国民党友人亦过从甚密,他们都多次和我商洽反直大计。这时眼看着第二次的直奉战争的爆发一天天接近了,我一面由于内发要求的驱使,一面为了各位朋友的有形与无形的鼓励,誓必相机推倒曹、吴,缩短这一祸国殃民的战争。”[1] 2
很显然,由这段引文只能看出冯玉祥在发动北京政变前受到孙中山的影响和与孙的来往,却与邀请孙中山北上没有直接的关系。
又如茅家琦先生担纲的《孙中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十五章第一节的第二个小节的标题就是“应邀北上”。其依据是孙中山1924年10月27日给冯玉祥、段祺瑞的“感”电,现特恭录“感”电全文:
北京冯焕章、王孝伯、胡笠僧、孙禹行诺先生均鉴: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孙文叩。[2] 252
天津段芝泉先生大鉴:大憝既去,国民障碍从此扫除,建设诸端亦当从此开始。公老成襄国,定有远谟。文拟即日北上晤商一切,藉慰渴慕并承明教。先此奉达,诸惟鉴照是荷。孙文。[2] 251
很显然,以上两封电文只能看出是孙中山告诉冯玉祥、段祺瑞自己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国是”,而看不出是孙对他们邀请电的复电。既然不是复电,当然就不存在孙“允北上商量国是”的事情。
冯玉祥等接到孙中山“感”电后,于11月1日复电,表示:“先生国家元勋,爱国情切,宏谟硕画,佩仰夙深。万乞发抒谠论,俾国内人士知所遵从。并盼早日莅都,指示一切,共策进行,无任叩祷之至。肃电奉佈,伫盼教言。”[3] 这份电文欢迎孙中山北上的意图倒是跃然纸上,但复电不是主动邀请,则是十分清楚的。
台湾方面的学者对此也没有提供第一手原始资料。李守孔先生的《国民革命史》(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岁诞辰筹备委员会编,1965年版)对此写道:“先是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回师北京之初,曾联电国父北上主持大计,并派马伯援为代表,赍函南下欢迎。”“段祺瑞、张作霖等亦先后电请国父莅临北京共商国是”。《国民革命史》的注释说明它没有对此作专门的研究,只是借用了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国民军史稿》和《国父年谱初稿》。从行文来看,这样的表述给人的印象是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立即与他人联电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并且派马伯援南下迎接。这与文献记载不符。经查,《晨报》(北京)、《申报》(上海)、上海《民国日报》等报纸在1925年10月23日至10月27日孙中山的“感”电前,没有发现冯玉祥向孙中山发出邀请北上主持大计的电文。《晨报》于1924年10月24日第二版,以《冯玉祥等主张和平之通电》为标题,刊登了冯玉祥等发动政变将领联名于23日发出致包括孙中山在内的24位社会贤达和各省督军、督理、督办、省长、护军使等各地实权派暨全国父老昆弟的“梗”电,电文全文如下:
国家建军,原为御侮,自相残杀,中外同羞。不幸吾国自民九以还,无名之师屡起,抗争愈烈,元气愈伤。执政者苟稍有天良,宜如何促进和平,为民休息。廼者东南火起,延及东北,动全国之兵,枯万民之骨,究之因何而战,为谁而战,主其事者恐亦无法作答。本年水旱各灾,饥荒遍地,正救死之不暇,竟耀武于域中,吾民何辜,罹此茶毒,天灾人祸,并作一时。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无泪,受良心之驱使,为弭战之主张,爰于十月十三(日)决意回兵,并联合所属各军,另组中华民国国民军,誓将为民致用。如有弄兵好战,殃民而祸吾国者,本军为缩短战期起见,亦不恤执戈以相周旋。现在全军已悉数抵京,首都之区,各友邦使节所在,地方秩序,最关重要,自当负责维持。至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会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所谓多难兴邦,或即在是,临电翘企,伫候教言。
很显然,这个通电是冯玉祥等表明发动北京政变的动因,提出与社会各界会商政治善后问题的倡议,不是专给孙中山的电文,更没有单独邀请孙中山上北京的意思。虽然电文中有邀请社会贤达“会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等句,但属于一般表态性质,既无会商的具体的内容,也无会商的时间和地点。再说冯玉祥发“梗”电时,北方时局扑朔迷离。时冯只有一个师的兵力,加上孙岳和胡景翼的部队,共二师一混成旅,数万人。他虽然成功地回师北京,囚禁了曹锟,并与张作霖有默契,但吴佩孚的十多万主力尚在。吴闻讯后立即联络长江流域苏、淅、鄂、皖、赣、及豫、闽等7省直系欲讨伐冯玉祥等部,时战争胜负很不明朗。所以冯玉祥此时也不具备邀请社会各方举行商讨国事会议的条件,只是一个政治表态。
至于冯玉祥派马伯援持函南下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更与孙中山北上没有关系。因为据记载,冯玉祥是11月1日复孙中山的“感”电后,才派马伯援南下。11月17日马在上海拜见孙中山。
至于段祺瑞,他虽然在事件前后与孙中山有联系,但“野居五年”[4],无公开邀请孙中山北上的名义和资格。事实上他于11月3日才对孙中山“感”电表示欢迎:“公元功照耀,政想宏深,命驾北来,登高发响,此天下之所想望,尤南北合力统一之先声。祺瑞野处有年,见闻鄙陋,愿乘安教,伫近行旌。”[5] 有鉴于此,孙中山北上与段祺瑞无关。
笔者认为孙中山先生1924年11月是主动北上,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第一,直接的目的是冯玉祥等发动的北京政变。北京政变使中国整个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将向何处去?这是每一个政治家都必须加以考虑的,并要迅速做出反映,孙中山更不例外。自从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孙中山认为中国的乱源在曹、吴,因此他就将直系作为最主要的敌人,为此联合奉系、皖系,形成了反直“三角同盟”。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此时是推翻直系统治的大好时机,遂于9月10日举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定举行北伐。9月13日,孙中山将大本营移韶关,挥戈北进。18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同日,孙中山以国民党的名义发表《北伐宣言》,指明这次北伐的目的“不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以持续反对革命之恶势;换言之,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也。”[2] 76
由于直系将领冯玉祥一直受到直系主流集团的排挤,加上他长期以来倾向革命,所以孙中山与他保持联系。1923年孙中山就派国民党人士刘守中、丁惟汾、王法勤等到北方,与冯玉祥等联络,策动“首都革命”。1924年初,北方同志曾多次致函孙中山,称他们不久便可发动“中央革命”,催孙北上天津等候。尤其江浙战争爆发,他们又催促孙中山,说“首都革命”很有把握,发动的日期,就在日前,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万不可失。孙中山答应只要北京发生事变,便马上北上。所以北京政变后,孙中山“为践成约起见”,毅然决定北上,虽然他并不认为北京政变就是“中央革命”,但政变无疑是一个进步,“可以望造成一个大规模的中央革命”。政变虽然不是完全的革命举动,但可以推测,彻底的革命一定可以在北京发生,于是他“为了答北方同志的欢迎起见,决定去北京”[2] 265~266。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可以说孙中山是“践”北方同志之“约”而北上的。
第二,北上是孙中山为振兴中华,和平统一中国所作的最后努力。孙中山处在国势日衰、江河日下的危难时代,铸造了他强烈的爱国情怀,因此一登上历史舞台,就立志要改变中国被列强凌辱的状况,使祖国赶上世界前进的步伐,成为一个独立、繁荣、富强的现代化中国。他以“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将改造国家为己任,不惜采取一切可行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他成立兴中会时,就已认清了中国的国情,主张采取武装斗争作为主要的斗争手段,最终结束了封建帝制,创立中华民国。
为了使国家迅速结束内战,恢复元气,成为强国屹立于世界,孙中山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和平统一。他历来“主张和平统一”[2] 331。民国元年,他为了停止南北战争,不计较个人的名位,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后来当他发现自己的选择是错误时,就再次举起武装斗争的大旗,为民主共和继续奋斗。
北京政变后,孙中山虽然清楚这并不是一场真正革命,但它却给革命开创了新局面,为政治解决中国内乱,结束军阀混战,实现和平统一和建设提供了一次良机。为此,他毅然停止了北伐,寻求和平方式以救国。他冒险“单骑到北京,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6] 65。鉴于国内各派势力不统一,他北上为“调合各方,使国家得和平统一以慰国民之望”。[7] 12月31日,他抵达北京后,发表了《入京宣言》,诚恳地表示:“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为特来与诸君救国的。”[2] 532在生命即将结束时,他呼出的口号仍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第三,北上主要是要宣传三民主义,使打倒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更加深入人心。孙中山将北上纳入其实现国民革命目的之轨道。他的革命目的就是在中国实现其三民主义。应该特别指出,三民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的。陈炯明事件后,他“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加新创”[8] 882,开始系统的阐述三民主义,他是“兼收众长,益加新创”的,使三民主义有了新时代的内容。这在孙中山的《北上宣言》中得到进一步的阐述。他说:“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其内容为何,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已详述之。盖以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为基本。”[2] 295“语其大要,对外政策:一方在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及特权;一方在变更外债之性质,使列强不能利用此种外债,以致中国坐困于次殖民地之地位。对内政策:在划定中央与省之权限,使国家统一与省自治,各遂其发达而不相妨碍;同时确定县为自治单位,以深植民权之基础;且当以全力保障人民之自由,辅助农工商实业团体之发达,谋经济、教育状况之改善。盖对外之政策果得实现,则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归于消灭,国家之独立自由可保:对内政策果得实现,则军阀不致死灰复燃,民治之基础莫能摇动。此敢信于中国之现状,实为对症之良药也。”[2] 29511月12日在广州各界欢送会上,他对此作了明确的说明,这次北上,不是去掌握政权,而是进行革命主义的宣传,到北京“去宣传主义,组织团体,扩充党务,我想极快只要半年便可以达到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主张,极慢也不过是要两年的工夫便可以成功。”[2] 308在途中,他继续修订三民主义的讲稿,计划到北京将民生主义讲完。
第四,北上是为了召开国民会议,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和民主。孙中山北上有两大要务,一是国家的统一,一是国家的建设。所谓建设不仅是经济建设,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的建设。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封建专政体制,作为对这个体制的否定,孙中山提出了民主共和。但民国创立以来,清王朝的专制体制却被军阀专制所代替,十三年来民国徒有虚名,毫无民国之实,实是一个假民国。北京政变后,他觉得“大憝既去,国民障碍从此扫除”,给国家实行民主共和提供了新的契机,也给人民实行民主和讲话提供了的极好机会,为此他欢欣鼓舞,提出国家和平统一,消除国内祸端的唯一办法就是召开国民会议,“中国前途的一线生机,就在此一举。如果这个会议能够开得成……中国便可以造成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造成了这种国家,就是全国人民子子孙孙万世的幸福。”[2] 341其具体主张是:在国民会议召集之前,可先召集一个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宜。预备会议由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反对直系的地方实力派、各政党的代表参加,再由以上团体成员直接选举产生国民会议代表。
孙中山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一开始就遭到段、张北方军阀的阻扰和反对。对此,孙中山是清楚的,所以沿途他反复宣传国民会议的主张,并计划派于方舟等一批宣传委员,分赴北方13个省区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必要与意义。
第五,北上也是发展党务的大好时机。革命要获得成功,必须有现代意义的政党领导。这是孙中山创立中国同盟会、改组国民党的根本目的。长期以来,革命的势力基本上在南方,北方力量十分薄弱。北京政变表明革命势力已经越过了黄河,发展到了北京。如果能够以北京作为革命的基地,革命将会获得彻底的成功。所以孙中山北上,以联络北方各省的同志,成立一个国民党党部,使之成立革命基地,实现“中央革命”,以改变中国命运。
由于北京政变主角冯玉祥等的实力与思想基础,无法将孙中山的“中央革命”变成现实,相反与张作霖等作妥协,造成了北京政权被奉系和段祺瑞所控制,使孙中山北上的近期目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愿望付之东流,但孙中山的长远目的——鼓动民众、宣传主义,却产生了深远效果,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号,通过孙中山的北上,愈加深入人心,为一年后的北伐战争作了一次广泛的政治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