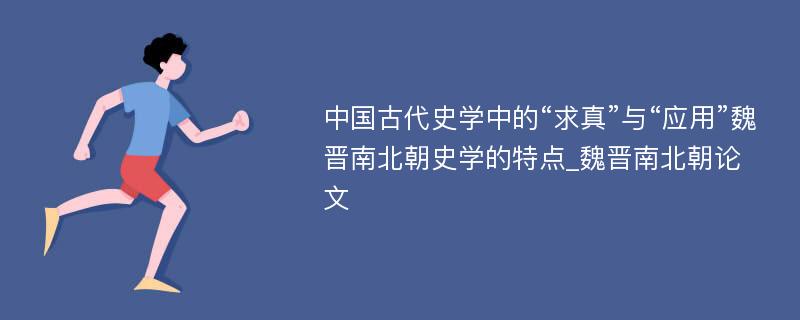
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3.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经世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时期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致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政治、直书与曲笔、求真与致用、文辞与内容等各种矛盾关系,相比较其他时代显得更加突出。在继承先秦两汉史学经世观念和经世传统的基础上,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经世取向表现得更为强烈,史学经世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历史撰述体例的创新成为史家以史经世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与此同时,强烈的经世取向和特殊的政治及社会环境,在史学领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曲笔现象,激发了人们对直书实录的再思考。
一、史学经世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先秦时期,以《尚书》为代表的“殷鉴”观和孔子积极倡导以史入世,从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把史学与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赋予史家明确的角色意识和责任意识,将中国史学引上了经世之路。秦亡汉兴,在汉初大规模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司马迁、班固、荀悦等人对史学社会作用的认识得到深化,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史学经世思想。具体地说,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沟通过去、现实和未来的有机联系,认识到历史盛衰变化规律及其动因。故此,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是基于古与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对于史学社会作用的精辟见解。班固撰写《汉书》宣扬“汉绍尧运”,突出汉的历史地位,表彰汉的功业,神化汉的统治,直接把历史撰述作为一种手段和方法运用于满足现实政治的需要。班固又通过总结西汉一朝的历史经验,“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序》),“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戒焉”(《汉书》卷14,《诸侯王表序》),把史学经世思想推向深入。荀悦撰《汉纪》以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把史学经世的途径由资治鉴戒延展到明道、教化、记功、考得失和立典制等多个方面,进一步拓宽了史学经世的思想内涵和认识视野。
魏晋南北朝是个变动的时代,皇朝迭兴骤亡,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激烈,政治斗争风云变幻,使这一时期史家对史学经世问题有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从不同方面深化史学经世的思想内涵,提升人们对史学经世问题的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经世思想的发展固然可以从不同方面揭示,但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
其一,积极倡导入世的人生价值取向。魏晋南北朝时期复杂多变的政治局面和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使许多士人走上了一条消极的避世之路,清谈玄理,放荡形骸。与这种避世的社会风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期的史学家没有回避各种社会问题和人生困境而消极避世,而是以一种鲜明的角色意识,倡导积极入世的人生价值取向,承担起经国济世的社会责任,将史学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说“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明确地把历史和现实通过史籍联系起来,要求人们通过史籍这个中介去认识过去,审视现实,思考未来,形成总揽全局的历史器识和察古观今的历史意识。在积极入世的人生价值取向影响下,史家们学史、撰史、研史,从不同方面推进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多途发展。他们撰述前朝史或当代史,辨论兴亡,探求治道,把史学作为说明和解释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手段。《陈书》本传说何之元自梁入陈,屏绝人事,锐意著述,修撰《梁典》以考兴亡之运,盛衰之迹。《魏书》本传则说崔鸿撰作《十六国春秋》,揭示十六国“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乖会之势”,以垂之将来,昭明后世。范晔撰《后汉书》,明确标立其总结东汉一代盛衰兴亡的历史经验是为了“正一代得失”。沈约在《自序》中也把“式规万叶,作鉴于后”作为撰写《宋书》的重要旨趣,如此等等,都充分体现了魏晋南北朝史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和经国济世的史家情怀。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逯耀东先生感慨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动乱的时代,由于知识分子为了寻求自我的存在,他们特有的时代感情,势必激起他们对历史的探索。中国的史学黄金时代在魏晋与两宋,明末真正的史学家,却隐于危亡之际泣血著述。所以世变方殷之日,正是史学创作之时。”(逯耀东:《魏晋史学及其他》,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3页)
其二,将以史为鉴提升为以史为政治和制度的模范典式。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反复强调资治鉴戒,但这不是先秦秦汉以来“殷鉴”观的简单复述,而是根据时代要求赋予了新的内涵。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根据时代需要力求从总结历史经验入手,从以史鉴戒扩展到以史勾画理想、稳定的社会发展图式。刘勰认为“原夫载籍之作,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徵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文心雕龙·史传》)显然,刘勰认识到史学不仅能够资治鉴戒,还能为国家提供长久的典范模式。杜预认为《春秋》“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春秋经传集解·序》)。常璩则说“夫人为国史,作为圣则”,“天人之际,存亡之术,可以为永鉴矣”(《华阳国志·序志》)。北魏李彪更认为史学的建立“此乃人间之绳式也”(《魏书》卷62,《李彪传》)。这些不同的说法,把前代的殷鉴观、史鉴观提升为史为国家典式这样一个新的高度,其实这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史学资治提出的更高要求。
其三,将史学惩劝从政治意义延展为社会意义。史学可以惩恶劝善,这是先秦以来已有的基本观念。但自先秦两汉以来,人们把史学的惩劝作用更多局限在政治方面,即通过史学惩恶劝善,以达王道,尊王权。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也在反复强调惩恶劝善,其中既有对前代思想的继承,也有受时代激发所作的新的阐释和发挥。陈寿的《三国志》被人们视为“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东晋袁宏更是把史学惩恶劝善的教世作用概括为“笃名教”,《后汉纪·序》说:“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宏敷王道。”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则认为史传具有“彰善瘅恶,树之风声”的作用。这些观点和认识显然把以史惩恶劝善的对象从少数乱臣贼子扩大到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把以史教化的目的从达王道、尊王权、垂鉴戒延展到有益风化,即树立和引导社会风气;把史学见盛观衰以佐治道的政治功用引入道德领域,通过以史笃扬名教,维护以纲常名教为最高原则的社会秩序。史学的社会作用范围拓宽了,史学经世的途径更广了,史学的社会责任也更重了。
二、以史经世与历史撰述体例的创新
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与统一、皇朝更迭与兴亡,民族冲突与融合,正统与非正统,门阀制度及其存在成为魏晋南北朝最突出的时代问题。面对这些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家以不同形式,从不同角度反映这个时代,解释社会的变化,探求历史盛衰之迹。在继承前代以史经世各种方法和路径的同时,此期史家不断创新历史撰述体例①,以反映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为皇朝的兴衰变化提供历史论证,为民族融合和国家的统一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
如何撰写政治分裂局面下的皇朝史?如何用纪传体形式揭示魏蜀吴三个并存政权的历史?如何用史学的形式表明中华民族由统一到分裂,再由分裂到统一复杂的历史过程,这是陈寿面临的新问题。《三国志》创立了分中有合,合中有分而终归于合的历史撰述体例,以记述从三国鼎立到三家归晋的历史发展。陈寿一方面将魏、蜀、吴三国都当作彼此独立、互不统属的三个平等个体对待,不仅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分别反映三国的历史,而且其反映历史的篇幅、卷数与实际情况相符合,也大体均匀合理,此为合中有分。另一方面又在“分”的格局下,根据三国各自力量的大小,地位的轻重,区别对待。尽管形式上为魏、蜀、吴各立一书,但在书法上“纪”曹魏而“传”吴、蜀。为魏主立纪,以曹魏纪年作为全书之纲,旨在为鼎立的三国勾勒出一条中国统一的历史走向,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三国分立的界限,突出了由分裂归于统一的历史发展主线。这样的布局和安排,固然是作者对历史的尊重,却也表现出陈寿总揽全局于胸中的历史意识,此为分中有合。白寿彝先生指出,在历史事件的记述、在人物传记的设立和安排上,“《三国志》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15页)
朝代兴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关注的焦点。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这种历时性的总结,虽然可以勾勒出历史盛衰大势,但难于对某个皇朝盛衰变化进行微观探究,而从共时性上对皇朝盛衰之变作具体的显微分析,却是魏晋南北朝政治所迫切需要的。干宝创立《总论》这一新的历史撰述体例,便是对西晋兴亡所作的一种微观剖析。《总论》不拘泥于一人一事的历史认识,而是站在历史高度,纵论一朝一代兴亡盛衰变化的历史总结。从现存文献看,晋代以前尚无《总论》这种史论形式。干宝将史论以《总论》的形式置于书末,形式类文,内容是史,立足于现实问题,总结和评论全书所记述的历史事实,着眼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相对于那些寓于史书之中的史论,《总论》更有利于史家摆脱过往史论就事论事的局限,便于集中发表对历史的看法,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下提出自己的历史观点,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理想,并对《晋纪》全书起到了理论总结和历史总结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南朝和北朝的统治者“莫不自命正朔”,互指对方为僭伪。从史学面临的新任务看,南北朝时期历史撰述都试图确立本朝的正统地位,排黜对方。《宋书》创设《索虏传》,以记北魏兴衰及南北战争、通好、和议、互市的史事;《南齐书》设《魏虏传》,记述北魏历史发展,视宋、齐为正,以北魏为伪;而魏收的《魏书》创设“岛夷”列传,以“岛夷刘裕”、“岛夷萧道成”、“岛夷萧衍”分别记述宋、齐、梁三个皇朝的历史。“索虏”、“岛夷”传的设立,既是国家分裂局面在史学上的反映,也是史家以史学为工具替本朝争正统,并进行历史合法性论证的手段和方法,适应了从史学角度为各自政权争正统的需要。
然而民族融合和国家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史学也需要为这一历史趋势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魏收撰写《魏书》,创设了《序纪》这一新的历史撰述体例。《序纪》既是《魏书》12篇帝纪的引言,也是全书的总纲和义例所在。《序纪》虽然是叙述道武帝追尊的28代君长的世系和事迹,但作者的匠心和微旨贯彻其间。《序纪》在《魏书》列为“帝纪第一”,《太祖道武帝纪》列为“帝纪第二”,显然《序纪》是自有系统的独立存在的一纪,不是帝纪的附属。《魏书》为何要在12帝纪之前设立《序纪》,魏收没有明确解释。从历史编撰的角度来看,最主要的意义应该在于通过一篇《序纪》叙述鲜卑族拓跋氏的族属源流,从血统上把鲜卑族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从文化上认祖归宗,论证北魏政权在中国历史发展序列中的正统地位和合法性。此外,李大师不满于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分裂而导致南北各朝历史撰述中的互相谩骂和曲笔倾向,立志编年以备南北。李延寿子承父志,抄录连缀旧史,编次列传,共为部帙,成《南史》和《北史》,实现了李大师编年以备南北的愿望。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地主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在史学领域里,历史撰述反映门阀地主的要求和趣味就颇为显著。一是门阀政治对这个时期史学有着特殊的时代要求,二是这个时期史学成为门阀地主获得或维护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工具。附传本来是一种以类相从的历史撰述方法。为了节省笔墨和篇幅,对同类人物,有时并不需要一一作传,而可采用为主要人物立传,然后将其余相关人物的事迹附载其后的方式。但魏晋南北朝时期附传已发展为一种家族传,其性质与《史记》、《汉书》中的附传有明显不同。这种附传,或子孙附于父祖,或父祖附诸子孙,如《史通·编次》所言:“每一姓有传,多附出余亲。”《魏书》为高门大族立传,对他们的世系、姻亲详加胪列,不仅记传主的家世子孙,而且叙及后代子孙,甚至旁及疏枝远族,一人之下附记十余人乃至数十人。如陇西李宝,传中附列50人;赵郡李顺,传中列举59人;《穆崇传》附记穆姓鲜卑贵族66人。这些人有的仅附列官爵而毫无事迹,有的连官爵都没有,仅列其名号。一篇人物列传,实际上就是一部简明家族发展史,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十“南北史子孙附传之例”条中批评说这是在“代人作家谱。”
三、余论
魏晋南北朝史学领域里直书与曲笔的矛盾和斗争尤其突出。既有韦昭、孙盛、高允等秉笔直书的史家,也有刘知幾《史通·曲笔》篇所列举的种种曲笔撰史行为。不能否认,魏晋南北朝时期曲笔现象表现得相当严重,与这个时期政治对史学的过分要求和史学一味迎合政治和现实的需要也有一定的关系。
以史经世,发挥了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曲笔泛滥,损害了史学直书实录的传统,反过来又制约了史学经世的效果。这个矛盾已经引起了魏晋南北朝史家的高度关注,他们一方面大声疾呼撰作信史,务从实录,对班固“遗亲攘美”、“徵贿鬻笔”,薛莹、谢承“疏谬少信”的虚妄态度提出批评;对司马迁实录无隐,司马彪著史之“详尽”表示赞扬。另一方面提出史学经世致用要以求真为前提,认为史著责任重大,“乃弥纶一代”,要让历史能起到垂训作用就必须诚信,诚而可信,真而服人。(《文心雕龙·史传》)北周史官柳虬说:“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鉴)诫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故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周书》卷38,《柳虬传》)这是从信史原则发展到对史官直笔的理论说明,即一是“记事”保存信史,二是“监诫”以彰善瘅恶,以树风声。这本是史学的目的,但史学如果没有秉笔直书作为前提,这两个目标都不能达到。
注释:
①史书体例不仅仅是史书的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表述形式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定的撰写体例,表达作者一定的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正如刘知幾在《史通·序例》篇中所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
标签:魏晋南北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南北朝论文; 汉朝论文; 宋朝论文; 三国志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魏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