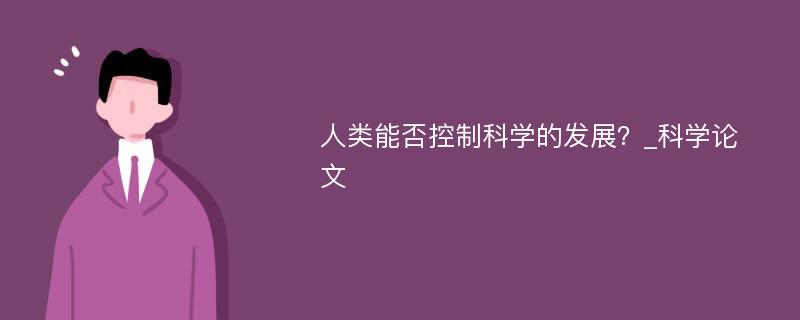
人类能够驾驭科学的发展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技术如何影响日常生活?关于这个问题,“绿色和平”与英国的《新科学家》杂志向来是唱对台戏。然而在另一个重要问题上,他们却表现默契,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公众积极参与有关科学话题的讨论、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以及对于科技决策的影响力是制约未来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绿色和平”和《新科学家》不久前联合组织了四场主题辩论,从深层次上探讨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未来生活和思维方式可能产生的影响。
5月28日举行的第四场辩论的主题是《人类能够驾驭科学的发展吗?》。这场辩论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当科学的发展主要来自“华尔街”的授意时,将会产生怎样的危害?一些国家在转基因食品的研究上投资数亿,相形之下,对于生态研究的投入却是九牛一毛,这种资金分配合理吗?如果科学技术仅仅造福于有钱人而将穷人置于被遗忘的角落,这会引发新的矛盾吗?是否应该赋予社会普通成员参与关于科学问题决策的实质性权利?如果允许他们参与,又将从何做起?以下为现场辩论实录。
主要辩论人简介
马丁·里斯(Martin Rees):英国皇家天文学家,著有《我们的宇宙栖息地》
史蒂夫·福勒(Seve Fuler):英国沃里克大学社会学教授,著有《对科学的管理》
威廉·施图尔特(William Stewart):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主席,英国首相前科技顾问,英国政府前首席科学家
范丹纳·席瓦(Vandana Shiva):英国牛津大学物理学家,著名环境活动家,著有《生物海盗:对自然和知识的掠夺》
马丁·里斯:如果哪个做父母的不关心自己孩子的未来,我们会很难理解。同样的道理,就连最纯粹的科学研究者也应该去充分考虑自己的科研工作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科学家应该去热情接纳对自己研究成果的有益应用,同时也有责任警告和坚决抵制那些危险的副产品。
经济和政治是影响科学成就造福于人类的最主要障碍。在我们这个极端不平等的世界里,向富人提供奢侈品,远比为穷人提供必需品要有利可图。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科学,而是大范围的重新分配、有力的政府津贴,或者是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的创新。
一些人赞成控制和引导科学的应用,但同时又宣称:“纯粹的科学研究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这种想法过于简单,它们两者之间实际上没有明显的划分。正是技术与社会这两个模具铸造了科学。
公众是否应该去制止某些学术领域的科学研究呢?比如某些正在大学实验室里进行的研究?如果这种研究实验存在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是,当这个科学实验看起来无懈可击,而它的成果却有可能会被错误地利用,产生危险的影响的时候,你又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认为答案同样应该是肯定的。科学领域内的投资,应避开那些看似不错但却容易引起应用问题的科研项目。
最后,我想悲观地结束我的谈话。设想一下,当成千上万甚至数以百万计的人掌握了生物技术,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产生呢?到那时,某一个人的疯狂想法就可能导致灭顶之灾。除非我们可以消除激起怨恨的根源——社会的不平等。大家应该明确:全球化不能只给富国带来福音。
史蒂夫·福勒:在18世纪的英国,作为启蒙运动的推动力,科学深深地植入了人们的生活。不论你是否在做科研,你都应该懂得科学,而且能谈得头头是道,甚至应该参与科学研究的决策过程。这些日子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作为一名致力于科学民主化的社会工作者,我满腔热情地想要唤醒这种启蒙运动时期的科学观念。这种观念淡薄泯灭的原因之一是科学民主化进程的滞后,原因之二是人们总是认为科学与公众格格不入。并不是公众讨厌科学,科普书籍从没有卖得像现在这么火。正是科学取代宗教,创造了新的大众精神信仰。
人们为什么会感到失望呢?因为他们不明白科学与政治、工业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更重要的是,没有给普遍人提供可以对科学发表意见的讲坛。如果要谈及科学和社会的民主化,就应该从建立能够让大众参与讨论的机构开始。
我有一个建议。我们需要召开民意大会。这和公民陪审团的基本模式相仿,普通大众担当“陪审员”,“专家证人”则来自科学机构和特殊利益团体。“陪审员”的首要任务就是草拟出政策的指导方针,为立法者制定政策指定大方向。
你会发现在民意大会中,人们能够跳出个人或家庭利益去思考问题,制定出合理的方针。我自己不需要进行基因治疗,但如果别人需要,我也不会反对,因为事实证明基因治疗有好的效果,而且我并不认为它有多可怕。
人们可能会喜欢民意大会这种形式,原因之一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受到了重视。科学界总认为什么问题都出在公众的无知和对科学的畏惧心理,其实,这仅仅是一个参与问题。有了民意大会的帮助,慢慢地你会发现,公众参与将激发出更广泛的融合和更多的坦诚,你会发现公众将更加信任科学家,科学家也更加信任公众。
威廉·施图尔特:我把20世纪70年代看作英国科学研究的黑暗时期,那时,只有个别科研项目能得到两三年的资金支持,而通常需要半年的时间来申请汇报,并且绝大多数学术委员会被那些无所事事的科学家所把持,他们没有课题可做,转而当起了行政官员,他们只会让科学界万马齐喑。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重要问题就日显突出:环境问题、农业问题、经济问题、健康问题、生活质量问题。主要的解决方法就是靠科学和技术。众所周知,英国当时做着全世界5%的科学研究,同时世界各地还有很多的实验室在进行重复研究。
因此,必须利用科学在某些重要领域创造竞争优势,这也是实行“科技前瞻计划”(Technology Foresight Programme)的出发点(编者按:该计划由英国科技厅(OST)制定,1993年正式颁布,提出了英国未来十年所要发展的前瞻技术,计划提出之后即成为英国政府资助国内科研活动的指导原则)。这个计划的意义不在于指导英国从事某个具体项目研究,例如:培育绿色植物,在三五年之内帮助固氮等问题,其真正意义在于它把英国的科学引向至关重要的领域。
这使我完全相信,科学技术可以给我们很多东西,这种回馈不需要等100年,而是短短的10年。我想,纳税人不应该花钱支持每个人都去拿一个博士学位,而不去考虑这个博士学位的质量如何。对诺贝尔奖我也有些个人看法,我们推崇诺贝尔奖,但是每一个奖项都会花费纳税人两千万英镑,这也算合理利用资源吗?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应给最好的科学家一定的空间,让他们自由地从事研究工作;如果他们的研究工作能够在私人资助充裕的大学进行,那就再好不过了。
然而,对于多数人,应该引导他们为国家多做一些实事,比如:创办新公司、改善生态环境、改良农作物等。如果做不到这些,我想以后纳税人在资助科学研究时会变得谨慎起来。
范丹纳·席瓦:科研经费是引导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办法,经费决定了科研的目的、科研的方向以及科研的产出。
在一些重要的研究机构中,科学研究不断发展,关于“科学”一词的概念也随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也许现在的某个研究领域在古代文化中根本就不属于科学范畴,例如:200年前,西方没有人愿意资助印度药草学的研究,可现在这个领域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最近,托尼·布莱尔首相发表演说,就科学的引导与控制问题发表了看法。布莱尔表示,他的演讲是受我们印度的启发。他说,在印度的班加罗尔他会见了一些学者,这些学者告诉他:“在促进科学研究方面,欧洲总是前怕狼后怕虎,而我们印度却在大步流星地追赶,你们将会坐失良机。”这些印度学者认为英国充斥着太多抗议和反对的声音,而反对者们习惯于用情感代替理智。
坦率地讲,印度人可不会这么保守,即便是对于生物技术这种争议纷纭的产业。科学商业化对斑加罗尔的研究机构影响深刻。印度科学研究所最出色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都被孟山都公司攫取了。其实,并不只是英国人喜欢抗议,不负责任地运用生物技术在哪儿都会招来不绝于耳的反对声。
科学被商业化这个“幕后角色”操纵着。有意思的是居然连布莱尔在他的演说中都不只一次地提到,自己是“幕后角色”的代言人。科学的民主化本来就非常脆弱了,而这种“科学私有化”进程则更会将它推向绝境。
《新科学家》杂志的阿玛蒂尔·森(Amartya Sen)曾经说:科学将会重塑经济模式,市场的供求关系也会左右科学的发展。但问题是缺乏知识共享,科学发展将无从谈起,现在出现一个很不好的苗头,就是大家很少思考这种市场供求关系是怎样影响科学发展的,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再不就此开展讨论,科学将无路可走。
杰里米·韦伯(Jeremy Webb)(《新科学家》编辑):如今“独立科学家”已经成了“珍稀动物”。科学院、政府、产业界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样会不会使公众对科学界丧失信任,而我们是不是应该阻止产业界挖走我们最好的人才?
范丹纳·席瓦:科学与商业的合作加剧了研究成果被掠夺的程度,然而这种新的合作关系却没有能孕育出新的知识。科学是公众的事业,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也许“华尔街”在每个季度都能从科学发展中赚取高额利润,但是“华尔街”却是科学糟糕的指挥者。
史蒂夫·福勒:某些科学家在对各种公共事务发表看法的时候头头是道,但是如果科学记者们能够去挖掘出这些谈话背后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并将之作为新闻的例行内容来报道,那将会是一件大好事。一旦科学家们了解到媒体曝光的威力,他们就能够学会三思而后行。
听众提问:既要促进科学发展,又要避免负面影响,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马丁·里斯:我们都面临着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形:想要获取利益,就得承担风险。费曼·戴森(Freeman Dyson,杰出的物理学家兼作家)写过一篇文章《说“不”背后的代价》,文章提醒我们,如果过分谨慎,就会丧失潜在的利益,例如:花费过长的时间、过高的投入去研制开发某一种药物。这原本就是一种有得有失的交易,然而这种风险与利益的交易是否值得,科学家应该听取别人的意见。
史蒂夫·福勒:某项研究一旦被批准,我们就应该具备控制和监督其进程的能力。人们通常容易走极端:要么听之任之,要么完全禁止。我们需要用制度为健康的科研保驾护航,只要出现问题,我们就亮起红灯。
听众提问:如果今天听完这场辩论以后,“商业化”给我们留下的是欺骗和可耻的印象,我想我真的会觉得非常失望。
范丹纳·席瓦:从本质上说,问题并不是出在商业化,我们正在进行的科研商业化进程也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商业化的程度。5家大公司控制着英国的农业生物技术。这就是我所说的“华尔街科学”。由华尔街来授意科学该做什么,这将腐蚀科学事业的基础。
史蒂夫·福勒:如果我们让科学成果的商业价值更公开、更透明,那么企业界就不仅限于开采大学的科研成果,还会更加公开地去投资其他科研项目。希望企业变得更诚实,减少暗箱操作。
迈克儿·勒·帕热(Michael Le Page,来自《新科学家》):我们在宇宙空间站上花费了100亿美元,而对艾滋病和疟疾的研究投入却微乎其微,这些疾病正在吞噬千百万生命,很显然,巨额的投入误导了科研。我想请问,这合理吗?如果不合理,我们又该做点什么呢?
范丹纳·席瓦:当然不合理。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全新的挑战——新的科技成果与其产权归属如何有机的结合。如果处理不好,人们享有医疗、水、食品的权利就会受到威胁。任何社会中,我们都应该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来决定科技的未来。
史蒂夫·福勒:科研投入的决策过程应该更透明,它不仅仅是一个项目与另一个项目相比孰优孰劣的简单问题。
马丁·里斯:全球一体化不应只让发达国家获利,热带疾病的研究无人问津,发展中国家药品匮乏等等问题,都是世界不平等的症状所在,这种不平等不仅影响科学,同时也影响着世界发展的方方面面。
(万扬 杨柳青 译自新科学家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