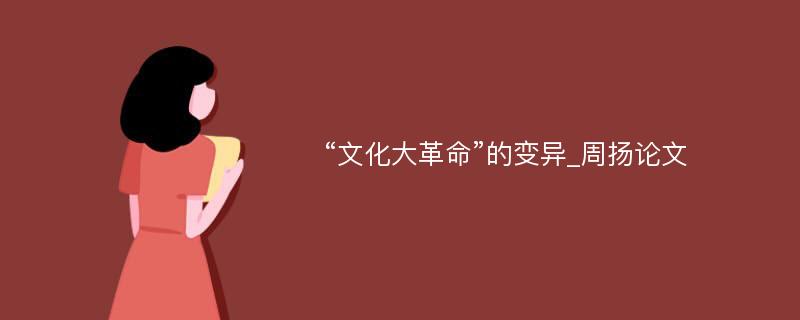
“文化革命”变异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后,为统一领导全国文艺界的整风,他提议成立了一个中央五人小组。那时,这类没有级别,也不设专职人员的非常设机构很多,都是为领导和配合某个运动或某项中心工作的。虽说是“小组”,参加者的级别都很高,权限也非同一般。
这次成立的五人小组,按常理应由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负责。但两个“批示”对文艺界的否定,显然也表明建国后代表中央一直管文化意识形态工作的陆定一难辞其咎,事实上毛泽东也当面批评他“见事迟”。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表示自己不适合当五人小组的组长。陆定一是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一道去毛泽东那里谈论此事的,并当面提出由彭真负责小组工作。彭的地位当时仅次于总书记邓小平,毛泽东当然同意。这样,五人小组的组长便是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后来正式定名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到1966年撤销,存在了一年多时间。
“文化革命”是建国后在毛泽东的言论和中央文件里频繁出现的词汇。最初的意思,无疑是立足于创造和建设。毛泽东在1956年1月知识分子会议上说得很明确:我们现在要搞科学,搞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革技术的命,革文化的命。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力提倡文化革命时,味道已有所变化,重点在针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要“拔白旗”,强调“又红又专”和群众性的文化创造活动。两个“批示”出来后说的文化革命,重点又转向了破除旧的文化思想(包括建国后的文化现象),营造出整顿和批判文坛的气氛,并且越来越染上了阶级斗争的色彩。“不破不立”、“大破大立”是当时文化革命的重要口号。到1966年春天,所谓文化革命,事实上已经是指全社会、各领域的一场政治运动了。其标志,就是这年4月间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新组“中央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稍后的“中央文革”的雏形),还在“文化”和“革命”之间加了一个“大”字,与这之前的文化革命全然不是一回事情。
“文化革命”的含义不断演变,并且在用语上竟然和那场导致全民族十年浩劫的政治运动有着如此联系,实在是一个让人感慨、令人深思的历史话题,总让人觉得当代文化轨迹似乎蕴藏着某种“劫数”。
且说从1964年7月开始,文化革命在文艺界的体现,已经不只是针对某些抽象的思想理论观点了,也不再是对事不对人了。有关方面对文艺界的负责人开始了排队清查,试图以事实说明文艺界不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
当时,公安部长谢富治搞了一份“文艺界一些领导人的情况”的材料,由江青转送给了毛泽东一份。里面说,阳翰笙(中国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党组书记、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田汉(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阿英(中国文联副秘书长)有历史问题。还说中国剧协研究室8个干部4个有问题;文化部艺术局3个局长两个有问题。
还有人告诉毛泽东,在文化部领导班子里,部长茅盾写的三部曲,实际上是自首书;副部长齐燕铭搞封建主义;副部长夏衍是30年代电影的祖师爷,右派;副部长徐平羽出身于高邮的一个大家族,他的目标是修家谱。还说整个文化部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联合专政。60多个事业单位,很多也烂掉了。文化名流中,有一些是国民党右派文人;有一批30年代文人,是名义党员。
这年8月,江青又把一份《党的监察工作情况反映》送给毛泽东,上面载有一篇《文化部一些领导干部的冷和热》,说文化部“对旧东西感兴趣,对新东西不热心”,“对工农群众手冷心也冷,对小资产阶级手热心也热”。所列事实有:话剧界的1962年话剧工作会议为“大洋古”开门,不支持提倡革命现代戏;戏曲界大演鬼戏,鬼进了文化部的大门,京剧会演中的好戏,都是1958年搞的;音乐界建国以来一直有一股风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这个领域的人的思想中,世界观的“政权”在资产阶级手里。电影界则吹嘘30年代的东西,不抓工农兵的题材。
看来,火力渐渐对准了作为政府机关的文化部。所谓文艺界,主要集中在两大坨,一是文联、作协,一是文化部所属单位,工作上都归中宣部领导。前者性质上属群众团体,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便针对他们。后者是政府部门,是掌握实权的,在回答究竟谁占领着文化阵地这个问题上,似乎更有象征意义。第二个“批示”后重点解决文化部的问题,也事属必然。
有关部门给毛泽东的各种吹风材料,显然加强了本来处于惊弓之鸟境地的文化部党组领导的危机感,急忙检查自己的工作,还专门编了一个内部的《检查工作简报》,刊登一些揭发出来的“坏人坏事”。一位中央领导在文化部党组1964年8月15日的一份《简报》上批示说,文化部及其直属单位的领导机构的改组和加强,必须依靠从党和军队中选拔新生战斗力量,绝不能再从原有的上层文化人中找替代,否则,在文化部门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难以建立起来的。这份简报和批示,经新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阅后,转送给了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
接着,毛泽东在11月底进一步作出判断:整个文化系统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的手里,整个文化部都垮了。在部长、副部长里面,有没有一个人站得住?现在看,都垮了。还说,文化部长为什么不能撤掉?
果然,1965年的元旦刚过,当了15年文化部长的茅盾被免去职务,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茅盾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在建国后文坛的领导人中,说起来他和毛泽东相识最早,渊源最深。大革命时期他是毛泽东最为欣赏的党内“著作家”,还专门调他到自己主持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秘书之职。1940年到延安时,毛泽东又让他到“鲁艺”讲课,作一面文化旗帜。由于大革命失败后一度离开党的组织,茅盾在建国后是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任文化部长的,实际工作由兼任副部长的党组书记主持。他一向处世稳重,小说创作也以理性见长,建国后同毛泽东的交往似乎并不密切。开国时,他本想专心写作几部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是毛泽东亲自出面找他谈话,说文化部长这把交椅是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想请你出来。茅盾问:“为何不请郭老担任?”毛泽东回答:他已经担任了两个职务,一个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一个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再让他兼文化部长,别人就更有意见了。为说服“不愿做官”的茅盾,毛泽东还表示:“你可以挂个名,我们给你配一个得力助手,实际工作由他去做。”这样,在文化部主持实际工作的,先是周扬,接着是钱俊瑞,以后又换了齐燕铭,中间虽偶有微澜,中央都没有动茅盾的意思。例如,1957年5月初整风时,他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一个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作了《我的看法》的发言,主要是分析中共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来源。别人的发言都登了报,他的发言却不见登出来。正在疑惑的时候,有关方面向他暗示:你那个发言有错误,不公开发表是对你的爱护,你要汲取教训。在继起的反右派运动中,身为文化部长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他必须表态,于是,不得不写了几篇文章驳斥在“双百方针”、写真实、公式化和概念化等问题上的所谓右派言论。[①]
1964年底,中央动议换文化部长的时候,周恩来曾找茅盾解释说:“文化部的工作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搞好,这责任不在你,在我们给你配的助手没有选好,一个热衷于封建主义,一个又推崇资本主义文化”,“现在打算满足你的要求,让你卸下这副担子,轻松轻松”。茅盾提出把连任十几年的中国作协主席也一并辞去。周恩来拒绝了,回答说:“你不当作协主席,还有谁能当呢?”
茅盾辞去文化部长一周后,周扬登门长谈了一次,主要是向他介绍文艺界学习和贯彻毛主席两个“批示”的情形,也谈了夏衍、田汉、阳翰笙所犯的错误。还说:“主席对文化部和各协会的批评,主要责任在党员领导干部,是他们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犯了错误。”
其实,周扬这个时候也自身难保了。
如果把建国后文坛做一梳理的话,我们大致可捋出这样一条线索:建国前夕的第一次文代会,被称为解放区(包括解放军)和国统区两支文化大军的会师。为此中央特别提出的口号是团结和融合。但不能回避的是,从大方向来说,经受过延安整风洗礼的文化人,无疑是更符合毛泽东文化建设思路的基本力量,从而具有更多的心理优势。随后出现的文化战线的“三大战役”(有人说是三大“公案”),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及冯雪峰、批胡风的结果,说明了这一点。到1957年反右以后,执掌文坛的就基本上是来自解放区的文化人和在国统区文化界工作的党员文化负责人了。
就创作队伍来说,17年文坛仍然有几代文化人。其中经历“五四”的郭沫若、茅盾、叶圣陶、郑振铎等,除了在文联或作协挂名外,也在政府部门担任了实际职务(尽管性质也多是挂名)。由于他们近乎新文化运动“元老”的特殊身份,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对他们都保持了相当的尊重,再加上他们说话也还谨慎,历次运动中多是有惊无险,没有受到冲击。与他们的境遇相似,但没有在政府部门任职的有齐白石、徐悲鸿等绘画大师和梅兰芳、程砚秋等戏曲大师,搞文学的则有巴金、老舍、曹禺、冰心等。一些人的创作高峰期,尽管在50年代事实上已经过去了,但一直在“文革”前,他们的存在和地位,都是文坛结构完整性的不可或缺的象征。再就是30年代成名的一大批文艺家。他们在建国后多多少少负点责任,创作成就也各有不同,在历次运动中或全身而退,或进取有为,或受到冲击,总的来说是17年文艺的中坚力量,因而常常处于“运动前线”。还有一类文艺家,即40年代或50年代登上文坛的人,他们在建国后写出自己的代表作(如梁斌、杨沫、柳青、赵树理、杜鹏程等等),或写出一些引起争论的作品(如萧也牧、路翎、王蒙、刘宾雁、流沙河等等),可以说,讲17年的文艺成就要说他们,17年文艺方面的讨论,也常常由他们的作品引发出来的。他们带着新鲜生活感受和旺盛的创作心态,有意识地做些艺术探索。于是,年轻气盛而又选择敏感题材者遭受挫折,生活阅历深厚而主要又是写革命历史题材者尚能无恙过关。但到60年代以后,艺术探索的空间总趋势是越来越狭小了。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就明确说《达吉和她的父亲》怕被说成有人性论倾向,而在影片中没有让父女相认时流下眼泪,不合常理,还说他的校友曹禺建国后的创作锐气不足,受束缚而胆小,举的例子就是其60年代初写的《胆剑篇》。
两个“批示”以后,具有个性的创作追求基本上就停止了。一方面文坛建设的重点已转向了江青插手的“京剧革命”,文坛批判的重点也开始转向“30年代文艺传统”,而30年代的文坛人物多是建国后涌现的创作生力军的“师辈”。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甚至老师的老师,这时候都产生了一种即将被时代抛弃在一旁的预感。1966年4月14日,时年74岁的五四先驱、文坛泰斗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竟也作了这样一番言过其实的自我解剖:“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来,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4月28日,经他同意,《光明日报》公开了这段在预感中半是真诚半是表态的讲话。
“文革”前夕,首当其冲受到批判的夏衍、田汉、阳翰笙和阿英,都是30年代左翼文坛的活跃人物,前三位同周扬的关系非同一般,在左联内部的争论中曾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阿英又名钱杏村,是太阳社的主要成员,20年代末同鲁迅的争论中和周扬等人的观点相近。他们事实上在建国后都被称为“周扬的人”,每人都主持着文坛的一方土地。剪除“羽翼”,把根子挖到周扬那里,也就指日可待了。说来也是文坛的悲哀,30年代左翼文坛骨干中与周扬有些旧隙,建国后很可能成为文坛领导人物的冯雪峰、胡风、丁玲,在50年代的运动中就已一个个沉降下去了。
在60年代中期的批判文化艺术界的思路里,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现象,即辉煌的“30年代文艺”,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也就是说,否定和批判建国后的文艺工作,总要从30年代说起,好像如今的“错误”,早就有根源似的。其实,根本原因,无非两点:一是用60年代中期的观点,来衡量30年代进步和革命的文艺思潮及其作品,自然是太容易发现毛病了。一是当时文艺界的负责人和名流,多是30年代登上文坛或叱咤文坛的。要批倒他们,当然要否定他们过去的功绩,否定他们过去的作品,要说明他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民主革命时期,并为害于今天的“文化革命”,就必然要否定30年代的进步文艺运动。
否定30年代文艺的一些人当中,最积极的,似乎最有发言资格的,自然要数当时名噪一时的演员蓝苹、如今的江青了。1964年7月间,文化部、文联和各协会在整风中编印的《检查工作简报》上面,陆续登了一些诸如“关于大肆宣传30年代的电影的情况和问题”;“阳翰笙宣扬30年代的戏剧电影的情况”;“文联一部分负责干部吹捧阳翰笙及相互吹捧的情况”等等。江青生怕毛泽东不清楚对30年代文艺的批判也是“文化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凡是检查30年代文艺的材料,她都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也都批示:“已阅,退江青。”
在1964年12月一次讨论把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改拍成电影的会议上,江青一上来就大讲30年代文艺的错误,周恩来顶了几句,说:我们不搞小圈圈和宗派主义,至于30年代,也有好的,在座的就有周扬同志、江青同志你们这些人嘛。
老谋深算者,更别有新招,即往路线斗争上扯,从党史上找依据,哪怕是莫名其妙的依据也要找一找的。比如,1966年3月在杭州的时候,康生告诉毛泽东:“鲁迅反对国防文学,鲁迅的大众文学与党的国防文学是两条路线。”而当时领导“国防文学”那条线的“党”,是谁的“党”呢?康生言下之意,当然不是正在长征中的党,而是王明路线的那个“党”。这样,同中央失去联系在上海主持文化艺术工作的周扬等代表人物便属于王明线上的人了。而毛泽东当时最敏感的恰恰是“路线斗争”,康生此招,可谓击中要害。这个问题虽然早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就当面同周扬谈开了、解决了,但时事变迁,毛泽东在这时也认为,国防文学是民族浪潮淹没了阶级性,还说起鲁迅对夏衍的《赛金花》的批评。
写到这里,有必要说说周扬了。
1930年从日本回来在上海投身左翼文艺运动的时候,他才22岁。26岁左右,又当上了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左联党团书记,在同中共中央隔绝消息的情况下主持上海的革命文化运动。1937年到延安后开始和毛泽东来往,即受重用。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文协”主任、“鲁艺”院长、延安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长等职。建国后17年间,一直以中宣部副部长之职负责全国的文艺工作,在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都挂了副主席之职。他的角色不光是文艺活动家,还是文学翻译家,其代表性的译著即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他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有人说可能对毛泽东的文艺观点颇有影响。他最主要的角色,当然还是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从30年代到60年代前期,他写的大量文艺理论和评论文章,可以说是中共领导的波澜壮阔的文艺运动的一个缩影。特别是到延安以后,他的重要文章发表前或发表后,毛泽东都特别注意。建国后有关文艺工作的报告,事先他都主动送请毛泽东审改。显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周扬不是个普通的文艺家,而是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一线主持人,比较欣赏他的办事能力、政治家的魄力见识(丁玲、冯雪峰、胡风等人无疑缺少这方面的素质),因而为文坛公事同周扬交往最多。于是,在一般文艺家的眼里,在建国后17年的文艺运动史上,周扬甚至有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政策的代言人之称。对他和毛泽东的这种关系,周扬自己也说过:“主席对我的确关系很深,确实对我很热情、爱护、培养。整风(指1942年——引者)以后我写的文章,很多都是主席看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指‘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引者)批判我的时候,引我的文章并不多,都是引我的讲话。”[②]
如果从一个文艺家的角度来看,周扬给人的感觉是“完全政治化了,总的来说他是很真诚的”,“多次赞叹说:‘毛主席确实是一个非常特出的人物,非常特出’”[③]。于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尽管他都能够全身而退,但其性格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要在文坛这麻烦敏感的地带领导政治运动,自斗斗人,又能在自危中自保自励,那心境决不亚于在凌空的钢丝上如履薄冰地行走,需要很大的自持力,这是一般文化人难以做到的。除了全心全意地工作,据说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兴趣,表面上谈笑风生,内心却孤独郁闷,以致有人说他太缺少友情。周扬曾多次对人说他早年如何如何地崇拜反传统、尚强权的尼采哲学,这对理解他的行事作风或许不是闲笔。“对上面的东西,无论对的错的,太忠实了,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且雷厉风行地执行。别人要是有点情绪,他就发火。没有多少友谊,缺乏同志式的温暖。在运动中他也想保护一些人,不想扩大化,但如果上面有指示,尽管想不通他也执行”[④]。
最让人感慨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兼具文艺家和政治家双重胸怀的人,在1965年以后也陷入了困境。最直观的解释是,两个“批示”以后,文艺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当然要反映到人事关系上来。以江青为代表的一股力量开始左右文坛走向。而毛泽东的思路也明显发生了变化。以他一向引掖后进人才的性格,对30年代的人长期主持文坛一事(别人告诉他这是‘霸占’文坛),肯定是不会感兴趣的。据当时的《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回忆:“1965年,毛主席把周扬找去,表面上态度和缓,实际上厉害。他就相信康生、江青的材料,认为‘四条汉子’专横地把持文艺界,要公开批判其中的另外三位:夏衍、田汉、阳翰笙。毛对他说:‘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后来,根本不相信周扬,就假手林彪、康生、江青的部队文艺座谈会。”[⑤]
以毛泽东在周扬心目中的地位,他完全体会得到毛泽东当时这几句话的份量。他自然不太想得通,但想不通又不能不想。这时候,文艺界正在深入地整风。本来,文联、作协系统1964年6月导致第二个“批示”的报告草稿,就以为整风整得差不多了,问题也检查出来了。但毛泽东的批示表明,上面似乎觉得还整得不够彻底,自然还要进一步来整。接下来的整风矛头,显然也把周扬包括进去了。而周扬此时在文艺界事实上也已无所作为了。
张光年还回忆:“宣布文艺界整风这件事我当时在场。那是第二次全国戏曲汇演闭幕式,我在主席台上,和阳翰笙坐在一起,还有周扬、田汉等,我们邀请康生来。他谈得很激动,说外地文艺界的人到北京来,不是来找党的,而是来找祖师爷。实际上就是批评周扬等‘四条汉子’。他一边讲,一边激动地把外衣剥下来,指手划脚。他带着批田汉、阳翰笙的文章,批判《北国江南》、《不夜城》等。”[⑥]
张光年说的这个“第二次全国戏曲汇演闭幕式”,很可能就是1964年7月间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总结会。康生在会上点名批判的影片作品,除《北国江南》和《不夜城》外,还有《早春二月》、《舞台姐妹》、《逆风千里》、京剧《谢瑶环》等,说它们是“毒草”。值得一说的是,这当中,《谢瑶环》的剧作者是田汉,《北国江南》的编剧是阳翰笙,稍后批判的《林家铺子》的原作者是茅盾,改编者是夏衍,《早春二月》的剧本也是经夏衍修改过的。也真是凑在一块儿了,都是30年代进步文艺运动的领导人和骨干。
最先受到公开批判的是《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1964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还加了一个编者按,说去年刚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北国江南》“在怎样反映时代精神,怎样正确反映阶级斗争,怎样塑造正面人物,怎样对待中间人物等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都存在着严重的错误”。9月15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加编者按发表署名文章批判《早春二月》,分别说这部作品“关系到作家、艺术家的世界观和立场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到“如何对待20年代、30年代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想”这个“具有原则性的重要问题”。
事情既已做起来,就不能不紧紧跟上。中宣部于8月间曾给毛泽东、彭真、康生、邓小平送上《关于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里面说:这是两部思想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影片。共同特点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和温情主义,抹杀和歪曲阶级斗争,着重表现中间状态的人物并以这种人物作为时代的英雄。从这两部影片,可以看出某些人竭力提倡和鼓吹的所谓“30年代的传统”的一个标本。因此,公开放映和批判这两部电影,对于清除电影界、文艺界的错误观点……都是有好处的。
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康生,自然有在这个报告上表态的权力,而且目光从30年代收回来,投向现实政治中最敏感和最迫切的话题。他在上面批注说:“《北国江南》不仅是所谓‘30年代的传统’问题,而是更严重的是有现代修正主义思想。现在的种种坏电影,用‘30年代传统’还概括不了,某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确是‘今不如昔’。”这种说法无疑会引起毛泽东的兴趣。他在上面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该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陆定一在毛泽东批示后,让周扬和林默涵(中宣部副部长)照毛泽东的批语,布置放映,还有一些坏片子,也挑出来,分期分批地放映,同时组织批判文章。
对这样的做法,中央一些领导人也不是没有看法的。比如,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1965年3月2日主持书记处会议时,就谈到1964年以来的文化界的现状。他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⑦]就像周恩来当着江青的面说30年代文艺也有好的一样,这种健康的声音,是很微弱的,不可避免地被大批判的浪潮吞没。
批判照样发展,且来势更猛。江青一伙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就在1964年12月那次讨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改拍成电影的会上,江青一口气点了许多50年代至60年代的影片,她说看了《球迷》觉得“呕心得要吐”,严寄洲导演的《哥俩好》里的“那些兵活像疯子”,王苹拍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丑化了人民解放军,把反帝的内容抽掉了,这是夏衍、陈荒煤他们搞掉的”,又说水华导演的《红岩》“没有生活,没有时代特点”。总之,她提出要把这些作品“拿出来见见太阳”,进行批判。
我们当然不能小看这类文艺批判对人们文艺欣赏和接受兴趣的影响。事实上,那个时代许多读者观众,在这样的氛围中,也就自觉地养成了搞大批判的人所灌输给他们的思维定势和挑剔眼光。而这正是批判者们所希望的,他们本来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运动群众”,来搞“群众运动”。这样一来,像根据长篇小说《红岩》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这样完全是歌颂革命气节、宣传共产主义理想的作品,竟也有不少观众挑出了它的错误。江青如获至宝,在1965年7月间送给毛泽东一份题为《北京三九三○部队部分官兵对电影〈烈火中永生〉的反映》的材料。
这个材料说:江姐、许云峰的形象不够光辉伟大;反面人物形象不够阴险狡猾。“有同志说,影片中的江姐和许云峰虽然有着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但缺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气慨。在与徐鹏飞的斗争中,徐大肆宣扬没落腐朽的反动哲学,软硬兼施,而许云峰不是充分地揭露,有力地打击敌人,不是大力宣扬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以一种磅礴的革命气慨压倒对方。但对敌人的方法多半是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态度,仿佛像位清高的旧式文人。”“徐鹏飞逼江姐说出党组织的名单来,她只是说:‘上级的名单知道,下级的名单也知道。’这种回答,十分无力,好像只是党的组织性的约束,才不得不这样做,没有突出一个英雄人物的高度的革命自觉性,没有变被告席为审判席,利用敌人的法庭做宣传。”“江姐在丈夫牺牲后回华莹山,理当让她为党多做些事,可电影匆匆就写她被捕,似乎革命者只是遭受挫折,而无作为似的。”“于蓝扮演江姐不大合适,她既无江姐的气质,也没有真正理解这个人物,演得比较弱,同样,赵丹演许云峰也演得像一个清高的文人。”
这当然已不是在谈论文艺作品了,而是离开作品来说抽象的大道理,脱离生活实际要求高大完美的人物形象。由此可见,“文革”中的“三突出”、“高大全”模式早有文化心理背景。毛泽东阅读时,还是在上面几段话中的许多句子下面都画了着重线,看来还是比较注意和认同这些说法。
对文艺作品的过火批判,是“文化革命”变奏中的强音,也可以视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序曲。
注释:
①韦韬、陈小曼:《茅盾的晚年(三)》,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期。
②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③④⑤⑥《谈周扬——张光年、李辉对话录》,载《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2期。
⑦引自《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1期第38页。
标签:周扬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央文革小组论文; 历史论文; 新文学史料论文; 毛泽东论文; 茅盾论文; 文艺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