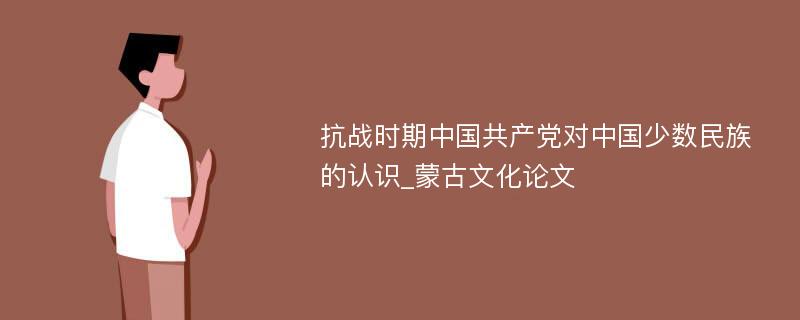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少数民族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中国共产党论文,少数民族论文,时期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3)03-0001-009
对国内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认识,既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组成部分,又是这一民族理论的基础构成。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内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认识方面,中国共产党取得显著的成就,其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广度。因此开展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内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认识问题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深入研究抗战阶段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取向、党的新民主主义民族平等团结理论提供新颖生动的视角,因而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
一
客观存在,是指在意识之外,不依赖主观意识而存在的事物。由于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游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因此,“民族是客观存在的实体”(注:金炳镐、青觉:《论民族关系理论体系》,《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第29页。)。从时空上看,一定的人们共同体之间是有差异的。当这些人们共同体的存在及其差异为意识所反映时,人们就可以把某一国家内人口居于少数的人们共同体称为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各民族之间逐渐形成人数居多的汉族和人口较少的其他民族的区别。这种民族人口上的区别成为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被称为少数民族的基本原因。然而少数民族的客观存在是一回事,国家和社会对它的承认是另一回事。尽管中国少数民族是作为民族实体而存在的,但是国家和社会的承认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对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确认既取决于人们的立场态度和思想认识,更取决于国家的肯定。国家和社会对少数民族存在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从本质上讲反映了不同阶级的民族观。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即肩负起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党在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中,逐渐加深了对国内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认识。北伐战争时期,冯玉祥在五原誓师以后,中共中央曾给在其部队工作的共产党人发去指示,指出:“冯军在甘肃,对回民须有适当的政策,不损害这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注:《中共中央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以下引文,简称《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页。)。据考证,从此,“少数民族”一词日益成为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话语体系中使用频率很高的重要词汇。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内少数民族的态度是:“为了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了民族解放,更应清楚的了解这些少数民族的存在,和如何使他们参加抗战,增强抗战力量,巩固团结,争取胜利。”(注:汉夫:《抗战时期的国内少数民族问题》,《群众》2卷12期,1938年12月25日版,第597页。)为了使抗日战争真正成为全面的全民族战争,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内少数民族存在的认识呈现出比较过去更全面、更深入、更具体的特点。论述这一问题,首先不能不援引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关于“中华民族”的论述。毛泽东指出: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土地之上。
……
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十分之九为汉人。此外,还有回人、蒙人、藏人、满人、苗人、夷人、黎人等等许多少数民族,虽开化的程度不同,但他们都有了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
中华民族不但是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对于外来民族的压迫都是不愿意的,都是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的。……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注:《毛泽东选集》卷1,晋察冀日报社1944年编印,第61-63页。)
毛泽东的这段论述既从生产、生活、政治等方面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内在联系和整体性,又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民族称谓、民族种类、民族人口、民族历史的总体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内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权威性表述。
其次,我们在党的历史文献中还看到其他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国内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具体阐述。这些阐述主要有:
1.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的种类繁多,人口不少,其分布地区十分广袤
1939年,八路军政治部在编写的《抗日战士课本》一书中写道:“中国是一个最古老的国家,有五千余年的历史。”“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是世界上最勤苦耐劳,最爱和平的民族。”(注:《汇编》第807页。)这段话中已经包含着一定的民族统计成分。
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少数民族称谓和种类的认识并不止于此。据笔者统计,1937-1945年党的文件、报刊文章和领导人的著作、演讲中使用过的少数民族称谓就很多,现将这些具体的称谓列举如下:
蒙古、回回、藏、满、苗、瑶、番、黎、维吾尔(畏吾尔、缠回)、哈萨克、柯尔克思、锡泊、索伦、塔塔尔、乌兹别克、塔兰其、塔吉克、归化、番回、东乡回、萨拉、朝鲜(韩)、安南、僮(壮)、仲家、夷(彝)、摆夷、水田夷、山头夷、阿昌夷、磨些、僰、罗罗、朴曼、栗粟、卡瓦、卡拉、民家、普拉、乌尼、崩龙、马喇、怒、求、茶山、曼尼、撒海、古宗、黧黑、缅人、野人、散民、阿你、土佬、力些、浪速、台湾同胞(注:分别参见《抗战时期的国内少数民族问题》;民族问题研究会编:《回回民族问题》,《汇编》第869页;罗迈:《回回问题研究》,《汇编》第847页;《中共中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批示》,《汇编》第551页;《边区参议会应有的任务》,《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内部发行,第651页;刘健:《云南少数民族问题》,《群众》7卷7期,1942年4月15日版,第157页;李子坚述:《云南问题》,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委民族工作部、省民委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工作》,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渥丹:《民族问题和民族语言文化》,《群众》6卷1-2期,1941年3月18日版,第28页,等等。)等。
抗日期间,共产党人进一步了解了一些少数民族的人口和分布情况。兹择其概要:蒙古族:其生活在外蒙古、内蒙古、宁夏蒙古、青海蒙古、新疆蒙古等地区,“全部人口约一百七八十万人”。(注:《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汇编》第657页。)回族:“具有约四百万人口”,“他们散居全国各省。其中西北最多,约二、三百万。次多为云南、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江苏诸省。”(注:《回回问题研究》,《汇编》第841页。)藏族:“分布得很广,除了西藏全部,还有西康全部,青海大部,四川北部,甘肃西部和云南北部。总计起来,他们居住的地区,要占全国面积的六分之一。”“全部藏族大概有三百五十万到五百万人的样子。”(注:韩晋:《藏族和西藏》,《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8日第3版。)苗族:“住在贵州、云南、广西、湖南和四川边境的深山里”,“我国苗民当在三百四十万以上了。”(注:石国保:《简谈中国苗族》,《解放日报》1941年9月26日第3版。)夷族:其“内部极为复杂,……人数近千万左右,散居在云南,广西,四川,西康,贵州诸省的边界。”夷族中最大者为摆夷、倮倮,其中摆夷“散布在上列各省,人数约数百万,其主要部分则居住在云南国道和澜沧江下流”;倮倮“散布在川,康,滇,黔的边界上,人数约二百余万,其主要部分——一百万以上——则居住在西康宁属。”(注:朱青:《西康宁属的夷族》,《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日第2版。)黎族:其所在地是“五指山脉一带山地”。在海南岛三百三十万人口中,“黎族人口约五十余万”。(注:《中共中央对琼崖工作的指示》,《汇编》第671页;《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延安新华书店1944年版,人民出版社1953年重印,第128页。)撒拉族:“共只三万多人”,“居循化”,(注:《回回民族问题》,《汇编》第875页。)等。此外,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新疆有“十四个民族四百万民众”;(注:《中共中央电贺新疆反帝军、反帝会成立七周年纪念》,《汇编》第685页。)西康宁属“海拔二千公尺的丰富高原,几千年来是夷民生息之所,全境夷民约百余万,居住全境四分之三的土地”。(注:《西康宁属的夷族》。)青海:“人口有谓六百万,当然不确。一般人说仅仅只有二百万,但久居青海的回人说才不过只有百数万,回人十之四,汉民番民十之六。”宁夏:“人口原有八十万,……现在只剩下不上五十万了;内回民十之四”。甘肃:“据官方统计:有六百二十九万余人,回民约二百万,但实际数目仍属可疑。”(注:云衢:《甘肃近况》,《晋察冀日报》1941年4月18日第2版。)云南“少数民族人民逾九百万人。而全滇人口总数不过一千三百万左右。”这些少数民族,“其种类是异常复杂的。……仅滇省政治力量所能完全达到的九十六个县内,即有一百二十四种之多。”(注:《云南少数民族问题》,《群众》7卷7期第157页。)
2.少数民族自古生活在中国土地上,其历史源远流长
中国共产党人在讨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是在中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发芽滋长起来的问题时,曾根据考古学、古人类学的材料以及中国古典文献的传说来探求中国远古的文化系列。他们指出:“中国社会不是孤立的东西,在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受到外来民族的影响,民族的混合,以及民族文化的交流都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基本上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来源有其独立和有别的特点”。(注:尹达:《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中国文化》1卷5期,1940年7月25日版,第22页。)与此同时,在国内少数民族的族源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历史记载,或辅之以考古资料,程度不同地探求了满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摆夷等少数民族的由来。他们分别指出:
满族,“古称东胡族”。(注:杨松:《论民族》,《汇编》第767页。)
藏族,“在秦汉时称为羌族,到唐宋时称吐蕃。”(注:韩晋:《藏族和西藏》(续),《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9日第3版。)
维吾尔,其前身是唐朝的回纥及唐末、五代和宋朝的回鹘,元朝的畏吾儿或畏兀儿,清朝的缠回。“历史上回纥、回鹘、畏武儿的活动区域,最初是在外蒙、内蒙古与贺兰山一带,后来逐渐转移至新疆与甘肃西部……形成维吾尔民族。”(注:《回回民族问题》,《汇编》第867-869页。)
蒙古族,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在河套地区发现原始人的头骨化石是和蒙古人的头骨类似的,由此可以推论散布长城以北至西伯利亚的种族“或是蒙古民族的祖先”。其民族来源有四种一时难以断定的说法:室韦契丹种;突厥种;突厥种与东胡种的混合种;鞑靼种。蒙古这一名称,远在唐、宋、五代时就见于中国史书,历来的汉文记述中的译写有“蒙兀”、“蒙瓦”、“盟古”、“盲骨子”、“蒙古”、“忙豁仑”、“鞑靼”等名称。明代以后,汉文书都写作蒙古。(注:分别参见《蒙古民族问题》,《刘春民族问题文集》(续集),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128页;《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汇编》第657页。)
回族,其主要来源“是元朝进入中国的回回氏”,回回氏及其后裔构成“中国回回的主要组成部分”。唐朝之后进入中国并且留居下来的“波斯大食人”,自然地加入到回回中去。因为回汉杂处,有些汉人自愿的或被迫的“从了回教”;因为回人可以娶汉女为妻,“汉人在回回民族的构成中,是—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此外,唐宋诸朝时期,留居甘、宁、青等地的回鹘,“因为与回回杂居,可能同化于回回。”(注:《回回问题研究》,《汇编》第842页。)
摆夷,是云南少数民族中的主要民族。摆夷在中国古书内早有记载,曰“僰”、“伯夷”、“伯”、“摆”、“歹”、“泰”、“闪”等。“这许许多多不同的名称,或同子音,或同母音,要为一音之转,故‘皆今之摆夷族’。实为居住云南历史最优久的民族之一。当孔明南征时代,他们就已是古滇的先进民族”。其他分布于云南的少数民族,“如朴曼、栗粟、卡瓦等,或多系汉朝以后始入居云南。”(注:《云南少数民族问题》,《群众》7卷7期第157-158页。)
3.少数民族基本上处于前资本主义的诸种社会形态,但也有其经济、政治上变异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认识国内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致力于民族问题研究的杨松于1938年在《论民族》一文中指出:少数民族“除外蒙外,大都还停滞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阶段。在政治上还完全是封建制度统治着,有的还过着封建社会以前的原始部落、奴隶社会的生活。”(注:《汇编》第767页。)
共产党人在概括当时国内少数民族的诸种经济形态的同时,还对若干少数民族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等基本状况和显著特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一是其基本状况。社会经济上,当时有人看到,西南一些少数民族仍然保持着原始经济形态和奴隶制经济形态。他们曾经写道:云南许多少数民族,“他们的经济是落后的,有的还是奴隶制度的社会和原始的农村公社”。(注:《云南问题》。)在西康宁属的夷族社会中,奴隶已成为奴隶主贵族主要的“生产工具”,作为贵族的“黑夷”,一人“拥有数十至数千的奴隶”,而“娃子即是替黑夷服役的奴隶。”(注:《西康宁属的夷族》。)有人对与汉族经济发展相接近的少数民族的封建经济形态作了较多的介绍。譬如,“比较汉族社会经济来,回族社会经济的封建性更为浓厚,尤其是回回更多聚居的甘、宁、青。”“由于封建势力厉行劳役、征发、强捐、勒派等非经济的残酷剥削,致使农村经济激烈的破产,农民生活激剧地恶化,人口大批死亡与逐年激减,农村中的阶级对立日益尖锐,主要是农民与封建剥削阶级的对立。”(注:分别见《回回问题研究》和《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汇编》第842、648、649页。)又如,蒙古“还保持着封建畜牧经济的地区:王公贵族仍然保持着家长式的统治,宗教的压迫和剥削仍严重,牧人仍过着农奴式的生活”。(注:《蒙古民族问题》,《刘春民族问题文集》(续集)第139页。)再如,在青藏地理条件较好的地区“已经是农业为主了。在这些地区,土地名义上是国有的,但是已经分配给寺院租贵族了,农民需要向地主贵族和寺院租地来耕种,缴纳一定的租税。”在阶级关系上,“藏族现在有贵族(地主)喇嘛和农民,牧人两个阶级。”(注:《藏族和西藏》。)此外,“摆夷民族在经济发展上,大体是与汉族相差不远的,主要生产方式为农业的;并且似已达到和汉人一样的农业技术水平。”清末以来,摆夷中普遍实施“以榨取方式的的农奴生产”。(注:《云南少数民族问题》,《群众》7卷7期第158页。)
政治上,不少人从体制的角度分别揭示了某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原始社会后期的政治体制、奴隶制下的政治体制、封建制下的政治体制。概括起来说,在青藏高原从事游牧经济的某些藏族地方有部落制;在西康宁属夷族地区、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有土司制;在内蒙古等地有盟旗制。至于西藏地方,“还保持着‘图伯特王国’的称号”,藏族社会内部“等级的划分却非常复杂而严格”。(注:《藏族和西藏》。)
二是其变异性。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条件下,一些地方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发生的变异,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视。他们指出,在奴隶生产或农奴生产方式下面的摆夷人民,都一样要受宣慰司的封建统治、汉人的高利贷剥削、帝国主义的商业经济榨取,以及外来官吏的压迫等。摆夷之外的其他云南少数民族除一部份已“汉化”者外,“其社会生活的特点,在其所具有的原始社会与商业和政治社会组织接触后杂乱而混合发展的形态。”(注:《云南少数民族问题》,《群众》7卷7期第159页。)又指出,“回族内部开始生长着民族资本主义的成分。已有公路交通、制革、制烟、制肥皂等工业。”但“回族中很少产业工人,更少工商资本家’;“回族大商业中没有纯粹经营商业的商业资本,绝对多数是和地主、军政当权者以至教权者相结合而成的封建垄断性的商业资本”;“回族中某些商业资产阶级同日寇有密切的联系”;“回族主要的居住区,回族社会,就是—个落后的半封建社会”;“回族的上层统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上层建筑”——西北回族军人政权的统治。(注:分别参见《回回问题研究》和《回回民族问题》,《汇编》第843、899、901、849、898页。)还指出,蒙古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极端复杂与不平衡,“在外蒙古是革命已经胜利的地方,初期封建经济与帝国主义剥削已被完全推翻,并且正在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以便进一步向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日寇统治下的内蒙古东三盟已经是殖民地的经济,而察绥蒙古的经济也开始了殖民地化的过程。在未沦陷的蒙古地方,……一般的它还保存着原来的初期封建经济性质。”这种情况反映到政治上,就是内蒙古等地既有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傀儡政权,又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盟旗制度。“内蒙古及西北各盟旗,非但未能脱离帝国主义侵略与异民族压迫的境地,而且由于日寇对中国不断的侵略与进攻,更加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注:关烽:《蒙古民族与抗日战争》,《解放》100期,1940年2月29日版第22、21页。)“蒙古民族在政治上的此种附属性与其经济上的落后性是密切联系着的。”(注:《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汇编》第659页。)
4.少数民族有些已部分融合于汉族,但仍保持着本民族的文化特征
杨松等中国共产党人还从比较少数民族“汉化”情况的不同来认识少数民族客观存在问题。一方面,他们认为国内存在某些“已同化了的”少数民族。他们说:这些“已同化了的满人、回人、番人、苗人、蒙古人、黎人等等在经济生活、语言、风俗、习惯等等方面已与汉人同化,并且已与汉人杂居,因而失去构成民族的特征,但是在风俗、习惯上仍与汉人有些区别,他们既非原来的种族,也非汉人,而是一个新形成的近代民族——中华民族。”(注:《论民族》,《汇编》第766-767页。)这里对“中华民族”概念的使用虽存在着问题,表述也不尽精当,但在强调这些“已同化了的”少数民族的有别于汉族的“风俗”、“习惯”却显得意味深远。从这一论述中已可以窥见共产党人确认中国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意向。
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国还有更多的少数民族其文化特征十分显著。他们指出:“在中国境内还存在着少数民族,……这些民族,除满人大部份已与汉人同化外,其他各少数民族仍然保持着自己底民族区域、民族语言、民族风俗、习惯,……这些蒙古人、西藏人、回人等等,就民族来说,是各个不同的民族”。(注:《论民族》,《汇编》第767页。)尽管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党还不可能进行以后意义上的“民族识别”,但共产党人仍程度不同地论述了蒙、回、藏、夷、苗、摆夷等民族的文化、心理状况。诸如以下的话语在有关的论述中就颇有典型意义和代表性:“历史指明,回回有坚强的民族意识”;“回教和回族的发展密切不可分离,回教不但是穆斯林的‘绳索’,而且是回族七百年来团结奋斗的一个旗帜。”“回族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汉化’,但仍然保持了自己民族的许多特征。”(注:《回回问题研究》,《汇编》第848页。)“夷民身体高大结实,食荞麦粑,饮冷水,处高山,居矮小板屋。不洗换,无桌凳寝具,终年赤足披毡,主要的从事农业生产,迷信,开矿,洗脸,认为皆会影响收成,酷爱酒,重义气”;“夷民信仰的是佛教,但无庙宇及繁复的宗教仪式,每年在秋收后九月的初一,十五,三十,在纸上写上祖先的名字,做几样菜供奉一下,从九月至十二月有些家庭请夷民和尚念三天夷文佛经,叫做‘做拜’,亲朋邻居,都来参加,那夜男女杂睡,是夷族中唯一可‘恋爱’的时候。”(注:《西康宁属的夷族》。)“从语言文化上说,摆夷是有自己的语言及文字的。据永昌府志中载:‘摆夷字,大约习爨字而为之。汉时有纳垢酋之后名阿呵者,为马龙州人,弃职隐居山谷,撰字字如蝌蚪,二年始成;字母十(?)千八百有奇,夷人号为书祖。’……由这点可以知道:被一般人蔑视为‘南蛮’的民族,实则是有其良好的文化的”。(注:《云南少数民族问题》,《群众》7卷7期第158页。)
5.少数民族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其反侵略的民族意识在抗战时期空前高涨
在探讨历史上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传统问题时,回族人民前仆后继反对封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英勇斗争尤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注意。他们断然反对回族是所谓“反叛”民族的错误论调,而提出:“历史指明,回回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民族。回回受过长期的压迫,经过长期的斗争。长期的民族压迫阻碍了回族的发展,因为他的长期斗争,未曾能够使他脱离被压迫民族的境地。但长期斗争锻炼了回族,把它锻炼成为一个英勇的有丰富革命传统的民族。回族曾经继承了并且发扬了穆罕默德的奋斗精神。”(注:《回回问题研究》,《汇编》第848页。)对于苗族人民的革命传统精神,有人在党的报刊上撰文指出:“我们可以这样说:历代苗民的历史,是一部残酷的向内外(主要是向外)统治者反抗和战争的历史,对外抵抗侵略是苗族之所以能够延绵其民族生命的原因”。(注:《简谈中国苗族》。)
中国共产党人从民族革命斗争传统的探讨而进入抗日战争历史条件下民族意识的研究,认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民族意识在少数民族中空前高涨。有论者根据全民族抗战兴起后西北各省回族人民抗日斗争浪潮发展的新情况,指出:“回族同胞之奋起,证明他们是富有‘回教徒决不与日本人妥协’的精神,是在发扬摩罕默德的英雄传统的。这一举动,是国内其他小民族的模范,……同时,它向全世界证明回族是中华民族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注:许涤新:《加紧回汉团结抗战到底》,《群众》1卷13期,1938年3月12日版,第233页。)有报刊发表评论:“今日报载松潘三峨落西番部队,为川境夷人最大支族,近鉴于日寇侵凌,为表示同仇敌忾,特推举代表赴省请缨杀敌,……这表示民族觉醒已逐渐深入到国内各少数民族中去,使日寇煽动分裂我民族团结的阴谋,日益失败。这种民族团结同仇敌忾的精神和实践,自然大有助于抗战事业”。(注:《短评:川境夷族请缨杀敌》,《新华日报》1939年3月4日第3版。)又有文章指出:“‘九一八’后,日寇侵华益急,中国国民之一部份的苗民,也就更迫切地要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全国同胞共求解放了。”“芦沟桥事变后,……作为中华民族之一支力量的苗族,不特对抗战和统一战线是始终热烈的拥护,而且确确实实的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注:《简谈中国苗族》。)类似的认识,也同样出现在党的报刊关于蒙古族、藏族、新疆和云南等地若干少数民族投身疆场、支援抗战的报道、述评之中。
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认识,无论是其认识的目的和意义——把握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动员各少数民族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以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民族问题的妥善解决,还是其认识的内容——少数民族的民族称谓、种类、人口、分布、族源、经济、政治、文化等,总的来说,都是以抗战以前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的有关民族情况的认识为前提的,都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民族平等,一贯承认中国境内生产、生活着诸多少数民族的思想的继承。作为共产党人的一种思想,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之一。但是,八年抗战期间党关于国内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认识,由于全民族抗战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以及全党更加注重中国的国情认识、更加致力于民族调查研究与处理民族问题,因此,这一认识本身就被赋予鲜明的特点,因而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首先,抗日时期党对国内少数民族客观存在问题的认识,更具有全党性的规模。
作为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重要认识成果,其言论不仅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若干重要文件中,如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回回民族和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参议会的某些文件等,而且见诸于中共中央和一些地方党组织及部门主办的报刊,如《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抗敌报》、《晋察冀日报》、《群众》、《解放》等所发表的部分社论和文章。党和解放区的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李维汉、贾拓夫、林伯渠、聂荣臻等;党的一些理论宣传工作者如杨松、章汉夫、刘春、牙含章、关锋、许涤新、潘梓年等;边疆民族地区的一些普通共产党人如杨湛英、江枕石、李晓村、张光年(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工作》,第12、243页。按:文中所提到的杨湛英,白族人,云南迪庆第一个中共党员。1942年至1943年秋他两次深入滇西北边远地区,行程五千里,费时一年余,对滇西北地区8种少数民族的源流、分布、语文、宗教、习俗、生活、家族、社会特性,以及政治经济教育等情况作了全面的调查研究,写成长达15万字的《云南滇西北边区调查记》。)等,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吕振羽(注:分别参考荣天琳:《论抗战时期翦伯赞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北京大学历史系《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110页;吴泽、朱政惠:《吕振羽史学研究》,《历史教学问题》1987年第1期,第5页。)等,都在中国少数民族的客观存在的认识与研究领域作出自己的贡献。那时候,在延安成立的民族问题研究会对回、蒙等民族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延安回民救国协会有的回民干部也在党的报刊上撰文,介绍一些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注:如延安回民救国会的理事金浪白,于1941年10月25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题为《回族概述》文章。)延安民族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摇篮和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主要场所,学院对那里的各族青年学员进行包括党的民族政策和蒙、回等族历史在内的思想文化教育。据李维汉回忆: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成立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虽然“我们党从事少数民族工作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但是,以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为武器,系统地研究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并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则是从西工委开始的。”(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57页。)由于抗战阶段共产党已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因此其国内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认识、研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之大,非党的早期所能比拟。
其次,抗日时期党对国内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认识,重点突出、涉及面广,更具体更明确,并且显示出强烈的针对性和鲜明的论战性,成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认识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里所说的“重点突出”“涉及面广”“具体明确”,其突出表现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中把对蒙古族、回族的认识作为研究的重点,专门著述《蒙古民族与抗日战争》(1940.2)、《回回问题研究》(1940.6)、《回回民族问题》(1941.4.)、《蒙古民族问题》(1944年底)等。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学说为指导,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具体调查,详实地探讨了回、蒙这两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显示出相当的研究力度。对于《回回民族问题》,著名学者白寿彝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书对于回回民族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不少的新的正确的看法。书中有些材料和解释,尚有待商酌,但这并不损害它为一本优秀的著作。”(注:白寿彝:《回回民族的新生》,东方书社1951年版,第115-116页。)着重研究蒙、回民族是适应积极动员地处抗日前线的蒙、回广大人民投入抗战、争取民族解放的迫切需要的。但是,党对少数民族的认识并不限于一两个民族。如已在本文中所述,就我们所接触的材料来者,中国共产党人承认那些人口很少、社会发展还很落后的人们共同体为民族,他们直接提及的民族称谓已经超过60多种,而抗战以前党的文献中有记载的少数民族他称和自称只有20余种(注:据目前看到的史料,抗战以前党的文献中提过满、蒙、回、藏、苗、瑶、僮、夷(彝)、仲蒙、黎、番、朝鲜(高丽、韩)、台湾、安南、越人、依人、摆夷、土佬、沙人、普拉、立梭等民族成份。)。两相比较,许多从前共产党人闻所未闻的少数民族在抗战中首次被提到。尽管那些民族称谓中或许是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称谓代表同—个少数民族,或者是一个称谓指向若干少数民族;也尽管这些称谓与今天所确认的民族名称有较大的出入,其解答难免还有疏漏或有问题。但如果从民族称谓量化增加值和当时的语境来看,抗日时期党对于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认识的确更加具体明确了。可以说,其视野之开拓,认识面之广泛,实属空前。已有论者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列数的国内少数民族作了统计,其统计结果为十几个(注:张有隽、徐杰舜主编:《中国民族政策通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页。)。其实,这一结果与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党对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实际认识是存在着较大的距离的。抗战时期共产党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国情认识大大深化了。这里所说的“针对性”,主要是指抗战期间党在强调少数民族的客观存在时,很注意结合民族革命战争的实际,进一步阐发蒙、回等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对于抗日战争不容忽视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如在回回民族的认识问题上,党的主要领导人张闻天曾从回族的历史发展肯定了回民是—个民族,并指出回族在抗日战线中和西北的重要作用(注:张青叶:《张闻天与民族工作》,张培森主编《张闻天研究文集》第3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52页。)。这就将对少数民族的客观存在的认识同对少数民族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的论证联系起来。这里所说的“论战性”则主要是指,对抗日中阴霾不散的不承认国内少数民族存在的错误思想,共产党人义正词严地进行了驳斥。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对“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抨击,以及民族问题研究会对日本帝国主义所谓“回教民族”谬论的批判,极大地加强了党对国内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理论认识的战斗性。
再次,抗日时期党对国内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认识,进一步推动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进程,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所进行的民族识别的先声。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要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就必须认识、处理国内民族问题。其认识、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指导就是马列主义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再加上共产党人对中国多民族存在的实际经验感受与思想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党在早期并未拘泥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而是承认国内汉族和少数民族(又称弱小民族)的存在,并在此认识基础上制定党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而努力。(注:举例来说,1926年1月瞿秋白在上海大学编著《现代民族问题讲案》。《讲案》对“民族”作了阐释:“民族者乃因资本主义之发生而形成之一种人类的结合,有内部的经济关系,即共同之地域以及共同之语言文字等者也。”这里的阐释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已接受了斯大林对民族定义的概括。但作为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在革命斗争中并未否认中国少数民族的存在,且主持制定过党的民族纲领、民族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大量地翻译出版,斯大林民族定义在解放区得到广泛宣传和介绍。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广泛传播并为中国共产党人普遍接受,一方面为他们深入考察中国各民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一个突出的理论问题和重大的现实问题,即根据民族四个特征是一个完整的定义,这四个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并且这一定义指的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民族,那么,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中华各民族究竟属不属于民族?特别是当时有人拿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来测量回回,发现回回没有完全具备斯大林定义所指出的四个特征,因而认为回回不能算作一个民族。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介绍、肯定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同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这一定义:(1)“斯大林所下的民族定义,并不是木制的箱子,要我们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讨论任何一民族问题时,都把这木箱子拿去,试装一下,放得下去的才算,才成为一个民族;不是这样,相反的,马列主义所要求我们的,是对—个原则具体的活的应用。那么,讨论中华民族问题时,就应根据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的地位来考察中华民族!”(注:编者:《关于“中华民族”问题》,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晋察冀中央局主办《抗敌报》,1940年5月30日第2版。)这段洋溢着思想解放的言辞,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看来仍然发人深省、熠熠生辉。(2)借助斯大林有关欧洲历史上存在过两类民族和两种民族国家,即一类是上升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现代的民族”和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现代的民族国家”,另一类是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多民族国家”及其国内所包含的“还来不及在经济上而结合为一个完整的民族”的思想,指出:“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作为统治民族的汉族,正处在进化为近代民族的过程中,……至于被排挤在后面的诸民族如回回、蒙古等,更没有来得及在经济上结合而成为一个现代民族。但他们仍然都是民族,不过还不是完全的现代民族。”关于回族,“的确,依斯大林定义中的四个特征,回回在今天还不是一个完整的民族。可是,斯大林在下定义时,他所指的是现代的民族。”(注:《回回问题研究》,《汇编》第851、850页。)这实际上是将民族概念宽泛化,对其四个要素“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论断突破的初步尝试,因而在民族识别问题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由此,中国共严党人论证了回回等少数民族的确是“民族”的思想。(3)有的共产党人在考察、研究他们所在区域的回族状况时,对上述思想作了如是发挥:“在这些少数民族中,回民是民族特征非常明显的民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其民族的宗教与宗教礼节和生活习惯,有其独特的经济生活——大部分经营小商业,售卖牛羊肉,务农者很少”。(注:《社论: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少数民族问题》,《晋察冀日报》1941年8月5日第1版。)以上事例说明,建国后民族识别中不是教条而是灵活地运用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思想倾向和识别原则,早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认识中已开始萌生,其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思想取向和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至此,“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注:布赫、赛福鼎·艾则孜等在《毛泽东解决民族问题的伟大贡献》(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探讨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贡献,提出毛泽东所使用的“中华民族”词语,是不同于斯大林对于西欧资产阶级民族形成概念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该书第7页)这一论述对于深入理解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内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认识有其启发意义。)已初步形成。
最后,抗日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认识,是无产阶级民族平等的一个重要体现,这种认识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民族工作中的落实,使少数民族人民感受到民族平等与自由,扬眉吐气作了主人。
本来,在全民族抗战的年代,少数民族的客观存在更应当得到国内的承认。但在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统治下,情况却并不是这样。以回族为例来看,大汉族主义者极力宣布回族不是一个民族,回回问题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宗教问题。抗战后,刊物中如《时代精神》、《新政治》,报纸中如陕、甘等地某几种报纸等,都充斥着这种言论。回族中虽然曾发出不少抗议的呼声,回民的刊物虽曾登载不少批驳的文章,但在大汉族主义的高压下,也只好“忍气吞声”,渐渐敢怒而不敢言了。(注:参考《回回民族问题》,《汇编》第902-903页。)然而,解放区的情形与此迥异。陕甘宁边区的回民曾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无不感动地说:在边区,“俺们才翻了身。‘回子’,‘贼回回’变成回民,回族,回胞了。”(注:边江:《回民的抗议》,《解放日报》1943年8月29日第4版。)中国共产党承认国内少数民族的客观存在,以兄弟般的友爱诚恳地对待和努力帮助少数民族,使少数民族深深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他们的“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帮助者和领导者”,解放区是他们“自由生活、自由发展的家乡”,是“民族解放的灯塔”,(注:参见1940年陕甘宁边区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总报告,《汇编》第927、930页。)从而促使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投身到神圣的抗日战争中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平等、自由、解放而奋斗。因此,仅从这个意义上就可以说,抗日战争时期党关于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认识,就为中国共产党强调全民族共同抗战,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成功铺就新民主主义民族平等团结之路打下了基础,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标签:蒙古文化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回族论文; 汉族人口论文; 解放日报论文; 民族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