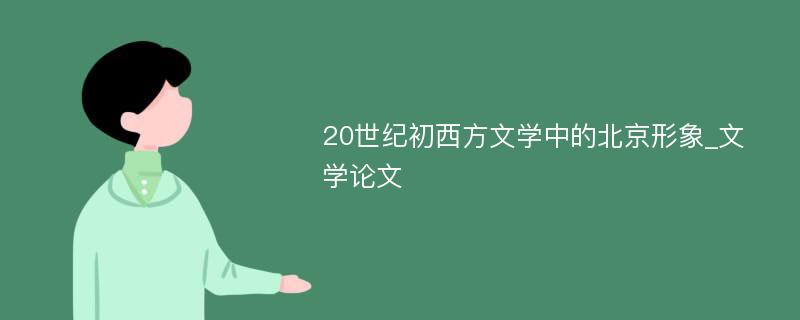
20世纪初期西方文学中的北京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初期论文,形象论文,世纪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03-0111-04
国内学界对中国文学中的北京形象研究现已取得相当可观的成果,蔚为壮观的“北京学”已初现端倪[1]。然而,关于西方文学中的北京形象研究却乏善可陈。其实,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是西方作家笔下出现频率最高的中国城市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人眼中的异域中国形象。笔者以为,西方文学(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中的北京形象是一笔可观的文学财富,有待比较文学学者和城市文化研究者去整理、发掘,只是和国内文学作品相比,语码和解读的方式不同罢了。作为异托邦的东方帝都,古城北京有着独具特色的建筑文化,是一个借以生发幻想和表达欲望的中国城市。此外,一些西方作家还努力透过北京封闭而自成体系的城市空间,透视封建帝国时期无处不在的跨文化管制力量。
一
翻阅历史文献,我们会发现,北京作为中国的首善之都,频频出现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帝都北京作为中国传统城市的代表,对西方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诚如身处异邦的林语堂所言:“不问是中国人,日本人,或是欧洲人,——只要他在北平住上一年以后,便不愿再到别的中国城市去住了。因为北平真可以说是世界上宝石城之一。除了巴黎和(传说)维也纳,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像北平一样的近于思想,注意自然,文化,娇媚,和生活的方法。”[2](P508) 20世纪前期的一些西方作家异常留恋古城北京。中国作家萧乾曾谈到一位英国作家哈罗德·阿克顿时说:“1940年他在伦敦告诉我,离开北京后,他一直在交着北京寓所的房租。他不死心呀,总巴望着有回去的一天。其实,这位现在已过八旬的作家,在北京只住了短短几年,可是在他那部自传《一个审美者的回忆录》中,北京却占了很大一部分篇幅,而且是全书写得最动感情的部分。”[3](P44) 萧乾认为,这位20世纪30年代曾在北京大学教过书的作家,他所迷恋的,“不是某地某景,而是这座古城的整个气氛”[3](P44)。
关于迷恋北京的西方人,中西文学作品中都有相关记述。中国文学方面以老舍《四世同堂》中的英国人富善为例,他是一个极度痴迷老北京的“东方主义者”。富善在北京生活三十余年,对北京的酷爱,甚至让他“眼睛变成中国人的,而且是一个遗民的”[4](P58)。他熟谙北京的风土人情,流连于古玩市场,刻意收藏京畿旧物,如绣花鞋、鸦片枪、顶戴花翎等等。日久积多,他在北京的租房逐渐成了“小琉璃厂”。面对那些到北京旅行却又浅薄傲慢的外国人,他常常会讥讽道:“一星期的工夫,想看懂了北平?别白花了钱而且污辱了北平吧!”[4](P57) 他的平生夙愿是撰写一部题名为《北平》的著作,但却始终不知如何下笔,直到临死时依然念念不忘。在西方文学方面,除下文将要重点分析的谢阁兰及其作品《勒内·莱斯》外,可举法国作家皮埃尔—让·雷米的《火烧圆明园》为例,主人公之一汉斯从法国抵达北京后,不仅要看宫殿、寺庙,更渴望“呼吸那纯净的气息”,“倾听那屋檐上的风铃声”,“那些卖花人、卖菜人的叫卖声”,还要感受“蔚蓝天空下的宁静”,闻“老胡同的味道”,亲自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穿行,去发掘“从永恒的蓝天与灰墙中溢出的一种生命潜力”[5](P183)。
不难推想,有如此众多迷恋北京的西方人,必然应该有描写这座城市的文学作品。国内学者赵园曾指出:“尚未闻有一本题作‘北京’的长篇小说出诸欧美作家之手。即使如克利斯多福·纽居沪那样有居京数十年的阅历,也未必敢自信能读解得了北京的吧。”[6](P204) 诚然,北京并没有和克利斯多福·纽《上海》相对应的长篇小说,但以北京为故事背景的欧美长篇作品并非阙如。此处仅举其要,如英国作家毛姆的戏剧《苏伊士之东》安·布里奇的小说《北京郊游》,哈罗德·阿克顿的小说《牡丹与马驹》;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的游记《北京末日》;维克多·谢阁兰的小说《勒内·莱斯》,等等。可见,20世纪初的北京依然古韵犹存,吸引着一大批西方作家带着怀旧和猎奇心态对其大写特写。笔者以为,写北京并不一定必须对该城市有着透彻的了解,西方文学中的北京形象正因为文化“误读”而精彩,我们所关注的是他者“建构”怎样的东方帝都形象,以寄托其想象的异托邦。
二
关于北京的城市环境,两位著名英国作家有着亲身体验。英国作家迪金森曾于1913年来访北京。6月8日,留居北京的迪金森给E.M.福斯特写信说:北京虽然比较脏,“到处是泥塘水泊,即使乘人力车也是不可能的”,但“北京的房屋精致得无以形容”,“环游北京,真仿佛置身于意大利一般”[7](P300)。1919年,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游历了四个月,途经北京等地,陆续发表一系列涉及中国的作品,如戏剧《苏伊士之东》、散文集《在中国屏风上》等。据资料记载,以北京为背景的《苏伊士之东》1922年在伦敦王家剧院上演时,其场面之宏大,令观众惊叹。该剧第一场布景就是北京皇城附近的一条热闹大街。剧团从伦敦唐人街雇四十多个华人做临时演员。毛姆来中国最想寻觅的是帝都昔日的荣光,而全然不顾当时中国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现实。他笔下的北京是神秘的地方,百姓优雅,风度翩翩,一条商店鳞次栉比的狭窄街道:“许多木雕铺面都有它们精美的格状结构,金碧辉煌。那些精刻细镂的雕花,呈现出一种特有的衰落的豪华。”在这条神秘莫测的街道上,就连驶过的马车都“满载着东方的神奇与奥秘”[8](P3)。在当时满目疮痍的中国土地上,毛姆感兴趣的莫过于在暮色里消逝的东方神奇,也正是那种衰落的豪华寄予着他的怀古幽思。
最能体现西方人对北京建筑文化迷恋的著作当属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该书是海外汉学家描写北京的第一本著作,它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作为历史文本来解读,极力去诠释那些灌注在砖石中的中国文化思想。这些外观分外古朴和绵延不绝的城墙,在作者笔下凝结着浓重的文化气息。在清晨的城墙上俯瞰时,连绵的屋宇被想象为波浪:“当晨雾笼罩着全市,全城就像一片寒冬季节的灰蒙大海洋;那波涛起伏的节奏依然可辨,然而运动已经止息——大海中了魔法。莫非这海也被那窒息中国古代文明生命力的寒魔所震慑?这大海能否在古树吐绿绽艳的新的春天里再次融化?生命还会不会带着它的美和欢乐苏醒过来?我们还能不能看到人类新生力量的波涛冲破那古老中国的残败城墙?”[9](P11-12) 从这饱含感情色彩的描述中,我们不难体会作者对北京城及其文化内蕴的深刻理解和新颖阐释,以及期待帝都重现昔日光彩的热切希望。
古城北京对西方作家的感召力甚至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4年,瑞士德语作家弗里施发表小说《彬或北京之旅》,表现了希望来北京生活的主题,其中“抽象的我留在了欧洲,具体的我则到了北京”。北京在小说中是一个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的美丽意象。作家是这样描摹北京城的:“那闪光的塔楼、屋顶、桥梁和水波荡漾的海湾、风帆,在空中盘旋的蓝鸟。”[10](P45) 考虑到心生向往之情的是一个参战的士兵,并且该小说写成之际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最为惨烈的时期,所以,北京在此处“成了战时人们向往和平安宁的象征”[11](P154)。作品中对蓝色的渲染,如“蓝色的幸福”、“蓝色的水手”、“浅蓝色的清凉”等,更增加了北京浪漫而又略带忧伤的神秘色彩。这种神秘早在20世纪初西方作家对帝都的描摹中便已开始出现,半个世纪后,“北京”仍然是欧洲人心中那个美好神秘、未被西方文明侵蚀过的原始天堂,在那里,可以找回纯洁和谐的自我。而这也正是作家让“彬”——那个“具体之我”到北京旅行的真正动机。
三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更有一些西方作家不仅迷恋北京独具特色的建筑文化,还努力透过北京封闭而自成体系的城市空间,透视封建帝国时期无处不在的跨文化管制力量,这里主要以法国作家谢阁兰的长篇小说《勒内·莱斯》为例。
谢阁兰的声名虽然在中国并不显赫,但却在世界文坛中享有崇高声誉,这可以从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盛赞中看出:“难道你们法国人不知道,唯有谢阁兰方可入选我们时代最睿智的作家行列,而且也许是唯一曾对东西方美学、哲学做出创新综合的作家?……你们可以用不到一个月就把其作品读完,但却要用一生的时间去理解他。”[12](Pvii) 从1909年到1917年,谢阁兰先后寓居北京等地达七年之久。《勒内·莱斯》中主人公有两位:叙述者“谢阁兰”及其汉语教师勒内·莱斯(杂货店老板的儿子,贵胄学堂的老师,父亲是比利时人,母亲是法国人)。现实中的谢阁兰,确曾跟随法国使团进入紫禁城拜见年幼的皇帝溥仪;而莱斯也有其人物原型,即作者1910年在北京结识的法国青年莫里斯·鲁瓦,鲁瓦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并颇为熟悉首善之都的风土人情和官场内幕。因此,我们可以说《勒内·莱斯》是一部“建立在与现实紧密相连关系上的小说”[13](P101)。叙述者“谢阁兰”向往紫禁城“四堵墙垣之内的魔力”,但却始终没有机会深入这个“神秘御苑”(作者最初拟定的小说题目),而17岁的年轻人莱斯不但可以自由出入紫禁城,还是光绪皇帝的朋友,隆裕太后的情人,秘密警察的头目,多次参与宫廷的政治阴谋。在梦幻离奇的叙述中,作者向我们叙述了一个融真实和想象为一体的异托邦[14](P239),是一个自我借以生发幻想和表达欲望的他者城市。
西方文学中的北京被认为“是一个被城墙、围墙、城门僵硬界定的城市”,并且“圈圈相套”[15](P1)。作为空间封闭的城市象征,其意象最多的当属“门”和“墙”,小说《勒内·莱斯》当然也不例外。在京的欧洲人虽然享有身份特权,但许多区域仍是难以接近的。叙述者“我”渴望进入禁城,窥探帝国核心的奥秘,但谜底却“被重重围墙包裹着”,“门并不向我打开”[16](P28-29)。此外,“我”为了保护莱斯,头一次闯入那些平日难以接近的胡同,还必须假装醉酒骑马为掩护[16](P198)。考察西方文化传统中墙和门,它们都有着深邃的含义:“墙在传统意义上是围住一个空间以保障其免受不祥外力的侵扰。它一方面有限定其圈中领域的不便,另一方面,也有保障其防范的裨益”[17](P653);“门是两种状态,两个世界,已知与未知之间的通道。它一方面禁止不纯的邪力进入,同时也是保障有权通行者进出的通道”[17](P779)。从这一层面审视谢阁兰笔下的北京城墙与宫门,它们都成了“禁止”、“封闭”的象征,很少有“通行”、“开放”之意,整个城市空间犹如莲花般层层延展的迷宫。
在小说中,“谢阁兰”宁愿住在外国军队保护区的外面,以表明他的跨文化交往欲望。他以“我的城”命名北京,以“我的宫殿”命名租住的四合院,以“我的瓷器室”(一语双关,又译“我的中国”)命名书房兼文物收藏室。他觉得四合院住起来“舒适又方便”,北京城则是“梦寐以求最理想的居家之地”。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他真正要面对的北京是一个“非常知道怎样将游人嵌入时间和空间中的城市”[18](P100),它由网格式的四合院和错综复杂的胡同组成,通过院墙、阁楼、沟渠等多种手段隔离并监控在京的外国人,把他者禁锢在各文化圈中,防止文化杂糅和交流,并对逾越行为加以惩罚,以保持帝国曾经存在的权力秩序。诚如莱斯对“谢阁兰”的多次告诫:“在中国,绝不要忘记你是欧洲人。”“谢阁兰”刚开始还以为这是种族特权,后来才发觉这是阻碍文化沟通的身份障碍。譬如,“谢阁兰”为了探听紫禁城内部的秘密,几乎穷尽所有的办法:先后尝试从太监、欧洲医生、中国医生等处获取蛛丝马迹,但结果都是白费心机。最后他终于有幸随法国公使团入宫觐见摄政王,却什么秘密也没发现,甚至回家之后,即便对照从欧洲高价购来的北京地图也无法回忆起觐见的路线。在无数次文化交往的努力失败之后,“谢阁兰”终于发现:北京营造了一个环境,在这里,“了解北京风貌和中国文化”一方面被许诺是可以尝试的,但另一方面却始终实现不了。北京对擅自跨越文化疆界的最严厉惩罚便是莱斯的离奇死亡:莱斯固守着文化混血儿的身份,试图在两个文化之间来回穿梭,在探秘的历程中虽有短暂成功,但由于他的行为“展示了神圣的秩序和神话内部的令人忧虑的分裂”,“暴露了‘家族秘密’”[19](P130),最终只能以失败落幕。
总之,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在西方文化中一直是东方异域情调的代表城市之一,对西方作家而言有着神秘的诱惑力,是西方文学作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中国城市。作为异托邦的东方帝都,古城北京有着独具特色的建筑文化,是西方作家借以生发幻想和表达欲望的地方。北京城的空间分布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差异,刺激着许多西方作家试图透过北京封闭而自成体系的城市空间,透视封建帝国时期无处不在的跨文化管制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