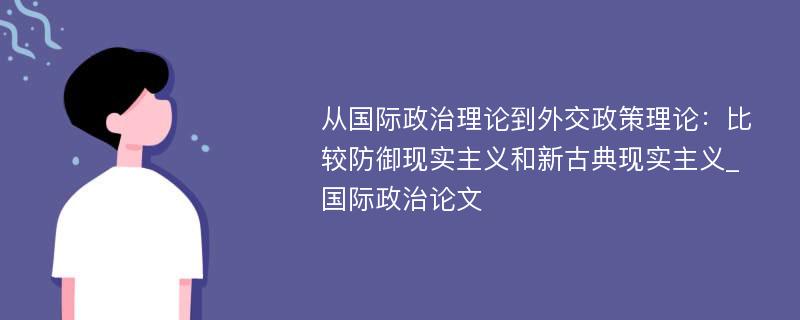
从国际政治理论到外交政策理论——比较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防御性论文,外交政策论文,政治理论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认为,现实主义是一种包含了某些思想硬核的理论范式。对于这些硬核是什么,大多数学者往往将其理解为一套基本假定。正如斯蒂芬·沃尔特曾经指出,“事实上,现实主义是包含了许多相互竞争理论的广泛研究工程。现实主义者承认一些一般性的假设,例如,国家是关键的行为体,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实力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中心地位。”① 他的这些论述与罗伯特·基欧汉等学者的总结是基本一致的。② 但是,在涉及具体的外交政策行为时,例如,针对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符合国际体系要求的理性政策,如何处理实力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等问题,现实主义之间都存在着广泛的争议,由此,也发展出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等诸多不同的外交政策理论。
一、缘起:现实主义如何解释外交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所探讨的问题十分丰富。这些问题既包括体系层面的问题,诸如单极结构的稳定性,也着眼于大国的对外战略,诸如联盟行为的起源。在这些热烈的讨论中,霸权国和帝国的外交政策一度占据了中心位置。常见的一种观点是,以肯尼思·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不能充分、有效地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事实上,沃尔兹严格区分了国际政治与外交政策,并且对构建一种具有全面解释力的理论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国际政治理论解释的是国际关系领域内反复出现的少数重大事件,例如战争的不断发生。③ 换言之,国际结果是一回事,而外交政策又是另外一回事。对其他许多现实主义者来说,他们感兴趣的是解释外交政策,而这种兴趣又和二战后制衡行为的特殊性、冷战后制衡行为的缺失等具体问题密切相连:为什么二流大国和最强大的美国结盟来对抗实力与霸权国相差甚远的苏联呢?虽然可能存在隐性的软制衡,为什么没有出现针对美国霸权的明显制衡呢?
为了解释大国外交政策中偏离体系要求的现象,许多重要的现实主义者不得不引入更多的国内政治、文化观念、地理位置等新变量。他们的努力导致了现实主义内部的分化,也有学者称之为“分析层次的回落”,④ 言下之意是,这些学者开始把目光从体系层次转向国内层次。在新出现的现实主义理论流派中,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两支。一方面,由于它们在很多方面存在共同点,都试图解释丰富多彩的国家对外行为,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学者自身立场的模糊,即使在美国学术界,对二者也存在相当混淆的看法。⑤ 而几乎同时出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试图以一种相对纯粹的国际结构理论来解释大国对外扩张、获取安全目标的行为,因理论逻辑过于简单、脆弱,已经遭到了许多批判。因此,本文的主要目标是,试图比较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评价它们在创造一种外交政策理论方面的努力。
在具体展开论述之前,围绕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在此先分析一下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的关系,以方便后面几节的探讨。一方面,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出现,的确都着眼于解释结构现实主义面临的难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理论仅仅针对外交政策。也就是说,它们的确可以称为外交政策的理论,但这些理论是建立在国际政治的一般性理论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如果缺乏有关国际政治本质、结构的一些前提,就不可能建立相关的外交政策理论,只有类似于官僚政治模式或者组织过程模式等具有普遍性、技术性的模式,可以勉强算是外交政策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共同具有的一大优点,就在于它们都基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信念。这两种理论虽然都力图解释霸权国和大国的外交政策,与所谓的大战略研究紧密相连,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恰恰是国际体系的结构使然。正是在单极结构之下,霸权国和二流大国都有了比两极结构之下多得多的活动空间,也才使得霸权国自身的观念和内部政治变得如此重要。因此,不能因为现实主义理论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新发展,而贬低国际体系理论的重要性,突出比较政治学的重要性,虽然后者也很重要。
另一方面,我们说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进一步发展了外交政策的理论,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不能提出自己的外交政策理论。⑥ 只能说,由于传统现实主义和结构性现实主义是普遍性的国际政治思想和理论,从它们发展而来的外交政策学说也相对粗糙,得不出特别具体的国家行为假设。例如,在传统现实主义中,我们知道国家利益是物质利益,而不是维护普遍正义这样的道德利益,也知道追求国家利益取决于自己的实力,但却难以深入理解大国的制衡、旁观、结盟等政策。⑦ 再如,在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我们可以预期,大国之间彼此会互相学习,这最终导致系统的势力均衡。⑧ 但是,小国会不会如此积极地学习,参与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经济秩序,则不确定。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许多落后国家仍然没有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来。⑨ 同样,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我们也推导不出有关制衡行为优先、防御性政策符合理性的假设。在不同的结构下,国家的行为可能是制衡,也可能是追随。例如,在两极结构下,两极之间互相制衡,但其他国家可能趁机扩张,以色列就发动或参与了多次中东战争。国际结构提供了国家行为的基本前提,但对于国家行为来说,往往并不是“只有一个出口”。正如肯尼思·沃尔兹所言,结构现实主义本身既不是进攻性的,也不是防御性的。⑩
对于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来说,最棘手的问题莫过于如何合理地把国际结构之外的其他因素整合进来。从体系理论的角度来说,国际结构的定义是相当严谨、完美的,不可能再塞进任何其他的东西。但是,从外交政策理论的角度来说,国际结构的因素还可能需要其他变量的辅助,甚至还需要与之结合。如果这样做,会不会像一些学者所说的,损害现实主义范式的纯洁性?在解释国家对外行为领域,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都做出了许多精彩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防御性现实主义方面,公认的代表性学者包括斯蒂芬·范·埃弗拉、斯蒂芬·沃尔特、杰克·斯奈德和查尔斯·格拉泽等;在新古典现实主义方面,公认的代表性学者有兰德尔·施韦勒、法利德·扎卡利亚、柯庆生和威廉·沃尔福思等。(11) 接下来,本文将比较和说明这两种理论有关国际政治、外交政策的观点,以及创造理论的途径。而本文的重点是第三个方面,也就是比较这两种理论如何处理与外部变量的关系。本文的结论是,在创造一种外交政策理论方面,新古典现实主义更为成功,建立了以现实主义核心变量为主体的外交政策研究新议程。
二、国际政治观点: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
前面我们谈到现实主义者都持有一些核心的信念或者说假定。稍微展开来说,现实主义的思想内核包括它在国际政治和外交上的一些基本假设。在国家层面上,总结一下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的看法,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者持有以下核心信念:(1)国家利益是物质性的而不是观念或者意识形态的;(2)相对实力决定了国家利益的范围;(3)国家的对外政策必须符合现实状况并且要小心谨慎。(12) 在国际层面上,总结新现实主义者的论述,现实主义者持有以下核心信念:(1)物质性因素,特别是实力自身具有意义,不一定要通过观念才能起作用;(2)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依赖于当时的国际结构;(3)如果国家的行为过度偏离国际结构的选择,迟早会受到惩罚。(13) 在有关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性质和国家主体地位这些基本信念的基础上,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里面既有基本的相同点,也存在重要的差异。
1.对国际政治体系的看法
在如何认识国际政治体系的问题上,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者都认同肯尼思·沃尔兹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们都承认,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不存在一个中央权力机构来实施法律、维护秩序的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最终只能通过自助(包括从内部强大自我和从外部争取盟友)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而各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则构成了决定国际政治结果的一个关键因素。不过,对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实力结构所导致的国际体系的性质,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进行了非常不同的推理,而且两者都认为自己是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合理延伸。(14)
防御性现实主义澄清了国际关系学界对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些片面印象。首先,它指出在无政府状态之下,国际体系的逻辑不一定是竞争性的。简单地说,虽然合作是有风险的,但竞争中的失败也会损害国家安全;其次,国际体系的紧张程度可以由攻守平衡的变化而改变。罗伯特·杰维斯指出,当可以区分防御性武器和进攻性武器时,在使它自己变得更加安全的同时,国家有可能不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当防御对于进攻有明显的优势时,一国安全水平的大幅度上升只会轻微伤害其他国家的安全。维持现状国家可以享受高水平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摆脱自然状态;(15) 再次,结构现实主义用最坏打算的方式来假设对方意图,这是偏颇、弄巧成拙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如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烈斯基也谈到了国际体系可能的紧张状态。他认为,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情况下,当进攻比防御更有优势时,这就会导致特定区域内独立政府数目减少,他们控制领土的范围则扩大,他们也更容易强化对已统治地区的控制。而在防御占优势时,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16)
在防御性现实主义者看来,从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出发,得不出国际体系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看法。相反,通过考察历史和现实,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安全往往并不稀缺,国家不一定要通过扩军备战、对外扩张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而且,财富来源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降低了土地资源的价值。(17) 民族主义情绪的勃兴、防御性武器有效性和可支配性的增加,都使侵略者攻占土地、征服民众和获取收益越来越困难。(18) 在注意到这些长期趋势未能阻止一战和二战之后,斯蒂芬·范·埃弗拉更具体地指出,“在1945年之后,发达工业国家生产方式朝着知识经济的转变,降低了征服者抽取资源的能力”,从而使得“征服欧洲的战争变得更困难和更不划算了”。(19) 因此,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是乐观的现实主义者,而这种乐观既来自于对结构现实主义与国家行为之间逻辑关系的思考,也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把握。无政府状态虽然会使战争、冲突不能完全避免,但在其他因素的干扰下,其紧张程度是可以缓解的。我们可以看出,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和温特建构主义表现出重要的共同点:一方面,它们都认为无政府结构下存在着竞争与合作的多种逻辑;另一方面,它们都认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不断进步的。
新古典现实主义则认为,领导人同时受到国际和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无政府状态既不是霍布斯状态的,也不是良性的,而是模糊不清、难以解读的。国家难以辨认安全是充裕的还是稀缺的,不得不在微光中摸索前行,依据经验法则来理解不全面的、问题百出的事实。一般而言,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秉承了肯尼思·沃尔兹对国际结构稳定性的看法,认为在多极结构下和实力对比出现明显变革的过渡期,发生大国扩张和体系冲突的可能性要大一些。(20) 在他们看来,国际结构始终是最重要的、第一位的因素,无政府状态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难以因为其他因素而得到彻底的缓解。所以,不能因为时代发生了某些变化,我们就把“修正主义国家”排斥在正常国家之外。兰德尔·施韦勒指出,虽然国际关系学者的传统观点是,国家将会制衡那些带来威胁的实力增长,但矛盾之处在于,历代以来的实践者们所抱持的国际政治形象却是见风使舵。他借用杰克·斯奈德的话来反击防御性现实主义,“大多数为广泛承诺做辩护的帝国战略家们害怕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大多数正在崛起的挑战者预期到见风使舵的效应。”(21) 施韦勒总结说:“修正主义国家更青睐它们所垂涎而不是已经拥有的,从非安全目标的扩张中所得到的收益要超过战争的代价。为了建立对维持现状国家的压倒性优势,心存不满的国家联合起来,特别是在只有这样做才能比守旧一方更强的时候。”“一般来说,修正主义国家是联盟行为的最初行动者,而维持现状国家则是‘反应者’。在缺乏一个合理的外部威胁的情况下,国家不需要、一般也不会参与制衡。”(22)
在有关美国早期外交政策的研究中,扎卡利亚所得出的中心结论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虽然国力已经强大,却没有扩张,这不是因为美国没有海外野心,而是因为政府本身过于虚弱。(23) 因此,实力对比的变化迟早也会带来国际体系的变革、大国的对外扩张和国际冲突的发生。虽然现存的一些因素可以缓解或者阻碍国际结构的影响,但是还远未达到自由主义者或者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所设想的程度。艾伦·弗里德伯格曾经指出,“新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多极体系可能是内在不稳定的。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什么因素是同等的,非结构因素可能加重或减轻体系结构导致的趋势。”(24) 如曾有研究表明,至少在20世纪的前半期,在一些特定条件下,征服者事实上可以从战败的工业社会抽取重要的净收益。控制领土包括稀缺的自然资源(例如石油)的收益,仍然是很可观的。(25)
因此,在有关国际体系紧张程度的问题上,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与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分道扬镳了。不过,必须重申的是,虽然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强调扩张的可能性和收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认定体系永远充满紧张安全问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即使是强调不断增强自身实力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也不会主张盲目扩张。(26)
2.对国家主体地位的看法
不论是防御性现实主义还是新古典现实主义,在坚持国家是国际行为主体这一基本的国际政治观点上,立场都是非常坚定的。在这两个理论流派看来,由于自身拥有主权而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国家是国际社会中最主要的行为体,而政府则代表国家行使对外职能。虽然国家内部的政府结构不同,导致某些社会因素能够影响国家的理性和对外决策,但是,代表统一国家的政府,尤其是行政部门最终制定、执行这些决策。(27) 而且,一旦做出决策甚至使之成为法律,社会中的各个团体、政党都必须遵循。因此在这方面,它们和自由主义有着重大差异:国家并不是一个四分五裂、水平运作的利益集团,主权的存在,保障了国家本质上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结构。它们的共同点还在于,都在一定程度上拒绝了原子式国家的基本假设,以及进行“黑箱”处理的纯体系研究方法。也就是说,这两种理论并不假设国家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以及国家永远都具有有限理性。(28) 在现实中,国家不可能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它必然由地理、人口、社会组织和政府等要素构成。而且,国家也不可能一直保持有限理性。也就是说,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国家领导人头脑发晕,甚至本身就是疯子和精神病,导致他们做出的决策不一定顾及国家安全和其他重大利益。在这两种理论流派看来,既然我们要发展外交政策理论以解释现实,那么就不能把国家当作是原子式的、永远具有基本理性的行为体。
吉迪恩·罗斯指出,在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里,外交政策活动是理性国家正确回应那些明确的体系诱因的过程,只在安全困境高度强化的情况下,冲突才会发生。不过,这一节奏常常被流氓国家反复打断,后者常常误读或者忽视外部环境所提供的真正影响安全的诱因。(29) 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把国际体系看做是那些“自然”行为的动因,他们认为,在军事技术或者某种其他因素提供了进攻占据优势的明确诱因之后,国家的进攻性行动才会发生。他们把进攻性行为归结为“非自然的”,利用添加国内变量的辅助性假设来加以说明。(30) 国家的内部观念和政府结构会有力地影响国家领导人的决策,导致其在某些情况下偏离体系要求的轨道。
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也承认这一点。他们把内部观念和政治结构的种种变量,视为体系力量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干扰变量或者说棱镜。吉迪恩·罗斯清楚地总结了这一点:“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外交政策选择是由实际的领导人和精英做出的,因此,起作用的是这些人对于相对实力的认识,而不只是对现有物质资源或者武力的数量比较。这意味着,在中短期里,各国的外交政策不一定会密切、持续地吻合实力发展的趋势。而且,这些领导人和精英不一定能从社会中抽取到他们所想要的所有资源。因此,实力分析还必须考察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和力量对比。”(31) 具体来说,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扎卡利亚曾经写道:“美国历届总统和他们的国务卿们一再试图将国家的上升力量转化为海外影响,但他们管理着一个联邦形式的政府结构和弱小的官僚体系,无法自由地从州政府和社会获得人力和财力。”(32) 柯庆生引入了“国家政治权力”的概念,其含义是“国家领导人为实现安全政策动议,动员国内人力物力的能力”。这是国家面临的国际挑战和国家所采取的应对战略之间的关键连接变量。(33) 对此,防御性现实主义也会表示一定程度的赞同,即国家实力不是简单的总体实力,可能受到地理、技术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查尔斯·格拉泽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两个实力相等的国家可能对于抵御对方都有着很乐观的预期,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这种预期却很低。”(34)
反过来,国际体系的要求也会导致国内政治结构的变化。从这方面来说,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表现出相当的共同性。例如,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杰克·斯奈德曾经从这个角度,解释了在世界一些地区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军事竞争和经济变革不但为民族主义政治行为提供了理性动机,而且还增加了精英分子创造民族主义神话的动机。军事和经济压力增加了对国家的要求,使得统治更加困难。弱国、处于困境中的国家或新出现的国家会试图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增强自己应付这些挑战的能力。”(35) 不过在这里,斯奈德似乎抛弃了国际体系主要带来理性诱因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基本论点。在讨论冷战时的中美关系时,柯庆生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认为,虽然中美两国领导人从心底里并不把彼此视为威胁,但为了增强国内的凝聚力和动员能力,却进行了大量彼此敌对的宣传,以对付来自苏联的真正的威胁。(36)
三、外交政策观点: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
从对国际体系性质的不同认识出发,在解释国家利益、行为模式和非理性行为等外交政策方面,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存在许多重要的差异。总的来说,防御性现实主义主张国家可以通过防御性的政策来获得安全,而新古典现实主义则强调,国家应该抓住体系中的结构条件,扩大自己的实力和影响,或是及时采取制衡行动。
1.对国家利益的看法
在外交决策领域,防御性现实主义者特别关注国家安全问题,并且认为这是决定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利益。根据这种理论对国际体系的认识,“安全是充裕的”,侵略会被迅速反制,技术和地理形势通常有利于防御者。(37) 既然国际体系提供了良好的安全条件,那么维护国家安全的有效办法是谋求有限的外部利益,建立小规模的军队和执行谨慎克制的外交政策。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再次乐观地指出,近代的历史事实告诉各个国家,采取大规模侵略行动或以正当的理由发起先发制人军事行动的国家是少数。除非出现五种情况(当然不仅仅是这五种),不具有领土野心的国家才会采取行动,这就是:危险迫在眉睫;生存严重依赖于敌对国家及其周边外部环境的改变,且这种前景变得不确定;对手具有压倒性的力量;对于一个正在准备侵略的国家,外交或集体制约行动已不再奏效;改变现状具有极大的诱惑。(38) 事实上,在怀疑和担心现实威胁及如何反应之间,还有较大的活动空间。(39)
因此,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不太关注相对收益和实力最大化,而着眼于避免相对损失(保持它们在实力排序中的位置)以及最大化它们的安全,也就是说,国家是寻求保持现存势力均衡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者”。(40) 当然,在实践中,国家常常会超出自身客观的安全需求进行扩张,但是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拒绝把这些扩张行为的动因归结为国际体系。相反,他们认为,体系中的其他因素导致了国家的错误判断和不安全感的上升。例如,当进攻具有优势(技术上或地理上)的时候,国家将会感到威胁,并且变得具有进攻性,因此,扩张来自于不安全感。(41)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真实的不安全状况并不多,大多数时候,不安全都是虚假的信念。例如,斯蒂芬·范·埃弗拉就认为,“从中世纪以来,欧洲的不安全感首要来自于安全稀缺的错误信念。”他宣称,总体而言,“国家并不像它们自己所想的那么不安全……夸大不安全的感觉,以及由其强化的有害行为,是国家不安全感和战争的首要原因。”(42) 在《战争的原因》一书中,他雄辩地指出,“现代强国的低死亡率可以表明真实的不安全是罕见的。”“通过事后的认识能够发现,如果德国行为规矩些,它的安全是可以确保的。威廉德国是在欧洲占有优势的国家,拥有欧洲最强大和增长最迅速的经济。它的主权并未面临着任何似乎可能的威胁,除了它通过它自己的敌意所创造出来的威胁以外。”(43) 乔治·奎斯特进而写道,“今天‘对战争的恐惧’怎么会比1938年更少呢?今天这种恐惧的确更少一些,某些种类的战争威胁的确更加‘可信’,因为大部分的‘战争恐怖’都与核战争威胁相联系,并且看起来也被核战争威胁所慑止。”(44) 因此,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既把国家利益界定为安全利益,又认为安全目标不难达到,只要国内不出现虚假的不安全感。
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可能会对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乐观主义感到迷惑,因为在历史上,威胁没有得到及时制止,大国扩张的行为比比皆是。虽然一些扩张行为,引发过如保罗·肯尼迪和罗伯特·吉尔平所说的过度扩张问题,但没有人会否认,扩张势力范围和影响力是一种强有力的诱惑。另外,一个让人感到迷惑的地方在于,既然国家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那么,为什么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很少提及海外经济利益、主导国际秩序这样的国家利益的重要性。(45) 因此,与汉斯·摩根索和肯尼思·沃尔兹的看法相同,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并不把国家利益限定于“安全”这样一个最低限度的目标。这些学者假设,国家寻求控制或者塑造它们的外部环境,以应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不确定性。国家所追求的利益涵盖了从维护生存到统治世界等各个层面。不管国家界定它们利益的方式如何复杂多样,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声称,国家可能追求的不只是减少外部的影响,还可能反过来谋求力所能及的外部影响力。(46) 当然,国家能追求多大范围内的利益,这最终取决于其相对实力的大小。扩张意图可能首要的来自于一国的国内政治,但是这一政策能否成功肯定与国际环境相关。(47) 他们中的另两位代表人物威廉·沃尔福思和斯蒂芬·布鲁克斯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由于冷战后美国所具有的单极地位,虽然有时候其他一些国家会采取制约美国的行动,或者发表一些制衡的言辞,但实际上,我们很少能找到经验证据来支持所谓“软制衡”的问题。(48) 在他们刚刚出版的《失衡的世界》一书中,中心的论点就是,在当前实力如此集中于一国的情况下,没什么能制约美国的安全政策。(49)
2.对行为模式的看法
既然国际体系环境是良性的,国家对外扩张的行为无利可图,并且常常遭到失败,那么对于自身的安全状态,大多数国家可以抱一种较为放松的态度,只需要集中精力来应付很少的外部威胁。基于以上判断,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除非安全处于紧急状态,否则国家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整军备战和对外扩张。一般而言,适度的制衡就足够了。防御性现实主义建议,国家应采取适度的战略,而这是维护安全的最好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际体系的强国应当实施表明节制的军事、外交和对外经济政策。(50) 不仅如此,国家还可以进行合作,不用太担心被欺骗之后的严重后果。对此,自由主义者肯定会表示强烈的赞同。例如,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和阿瑟·斯坦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处于一般境况下的各个国家其行为举止比结构现实主义所描述的那样要更具合作性,大部分情况下的结果也是没有遭受痛苦。”(51)
在有关国家行为模式的研究中,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主要关注制衡行为。例如,马修·伦德尔运用该理论分析了拿破仑战争之后制衡行为的延续,“在1815年后,势力均衡依然发挥了主要作用。最重要的是,它限制了唯一心怀不满的国家法国。沙皇俄国的官员也小心地避免形成一个反俄联盟,因为它需要盟友,尤其是英国,以防止在和法国摊牌时,俄国孤立无援。反过来,柏林也不愿意承受法国的打击。英国和俄国可能联合行动来达成它们的欲望,但彼得堡知道,这种进攻可能会导致伦敦制衡它。”(52) 以斯蒂芬·沃尔特为代表,他们修正了势力均衡理论,发展出“威胁均势”的理论。势力均衡理论预言,国家会联合起来对抗体系中的最强者,而“威胁均势”理论则预言,国家会联合起来对抗最具威胁性的国家。因此,后者不仅能解释国家为什么联合起来对抗最强者(如果它的实力使它看起来最危险的话),也能解释为什么国家会选择制衡某个并不是最强者的国家,其中原因可能在于地理的邻近、进攻性意图或者拥有特别强大的征服手段。(53) 也有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不反对有限的机会主义扩张,尤其是在那些处于权力真空的地区。马修·伦德尔仅仅把防御性现实主义限定在如下范围:一般来说,国家会制衡那些潜在的霸权,试图统治一个大国体系是不切实际的。(54) 但这样一种论述冲淡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防御色彩”,也仅仅针对大国行为体。此外,其他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能否认同他的观点,也不得而知。
新古典现实主义者既然不把国家利益仅仅限定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制衡行为的意义、有效性等诸多方面就必然成为他们质疑的目标。在这方面,扎卡利亚和施韦勒都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批驳,他们都认为,国家寻求扩大自己的影响是一种常态,而不是异常。因此,新古典现实主义者最重要的经验预测就是,长期来看,国家占有的相对物质实力资源会塑造其外交政策的目标和范围:随着实力的增长,国家会寻求更大的海外影响力。一旦实力下降,它们的行动和野心又会随之收缩。(55) 因此,国家行为是制衡、搭便车还是袖手旁观,这取决于实力对比等诸多因素,国家应该伺机而动。扎卡利亚指出,“防御性现实主义混淆了体系对国家的影响。他们相信国家应该从体系的运作中学习。一方面,每个国家学到的教训都不可能同其他国家完全一样;另一方面,如果国家学到的都是制衡将会出现的同样教训,那么就会出现大量的集体行动问题,因为所有国家都会面临巨大的免费搭车的问题。因此,防御性现实主义有关体系诱因将会导致制衡行为的理解,不会像它自己宣称的那么普遍。”(56)
施韦勒则进一步分析了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对于“见风使舵”或者说“搭便车”这一行为的误解。他准确地指出,在防御性现实主义那里,对“见风使舵”概念的定义过于狭窄,也就是向威胁屈服,这仅仅与制衡威胁相对应。实际上,国家选择“见风使舵”还是制衡,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制衡的目标是保障自我生存和已经拥有的价值,而“见风使舵”的目标常常是扩展自我利益,获得那些垂涎已久的价值。简单地说,制衡源于避免损失的渴望,“见风使舵”则源于可能获益的驱动。(57) 他举例说,1940年当意大利向法国宣战、日本决定同轴心国结盟的时候,德国的安全都不会是首要的动机。与之类似,斯大林在1945年热衷于同日本作战,更多的是看中了不劳而获的战利品,而不是从美日那里获得更好的安全保障。(58) 他的结论是,制衡为什么比“见风使舵”更普遍是一个误导性的问题。在实践中,即使是大国也常常选择做旁观者,以避免积极制衡那些强有力的掠夺性国家所带来的高昂代价。(59)
也有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如杰弗里·托利弗则认为,领导者担心和厌恶国家损失相对实力与威望,这促使他们在边缘地区进行扩张,采取冒险的外交和军事干涉战略。(60) 在前面,我们提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也认为极端的安全考虑会带来扩张。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第一个不同是,新古典现实主义所界定的利益不仅仅是国家安全,源于实力与威望的考虑也会促使国家采取干涉主义行动。第二个不同在于,新古典现实主义并不把这类扩张视为非理性行为。托利弗认为,与扩大它们的优势相比,大国对于保存它们现有的相对实力和声望更感兴趣。从这种理论出发,可以推出三个命题:首先,当看到相对实力或威望可能受损时,高级官员更可能在边缘地带采取外交和军事战略;其次,当国家的相对实力或威望面临损失时,这些官员可能倾向于采取更具有风险性的(risk-acceptant)行动;最后,官员们可能会坚持甚至扩大他们在边缘地带的冒险干涉战略,尽管这些战略正陷入失败的困境。因此,他们不太可能重估、收缩或者中止正在施行的战略。(61)
3.对非理性行为的看法
根据前面对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介绍,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知道,它所指的非理性行为主要是指那些不经常出现的、基于虚假不安全感的扩张行为。如果国家为了真实的不安全而扩张、制衡,或者在体系中攻守平衡倾向进攻一方时冲突增多,这些都是防御性现实主义自己的逻辑所在。但既然国际体系是良性的,威胁是相对明确的,国家为何又会有许多虚假的不安全感呢?在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和许多其他现实主义者看来,历史上大量的扩张行为根本不是寻求安全的目标,也不是国内社会有什么虚假的不安全感,而是纯粹的延伸自己利益和影响的行为。防御性现实主义求助于国内政治变量,来解释该理论中国家的非理性行为。斯蒂芬·范·埃弗拉在《战争的原因》一书中,首先论证了战争行为的非理性,然后指出,“权力结构本身是良性的,而且基本上并不引起战争,但被人们所认知的权力结构经常是恶性的,而且可以解释大量的战争。”“实际上,这种错误的认知是普遍的:国家经常夸大抢先行动所能带来的利益范围,机会和脆弱性窗口的大小,资源的累积性程度以及征服的轻松程度。于是它们就能依据这些幻觉采取引发战争的政策。”(62)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错误的认知或者说“帝国的迷思”呢?斯蒂芬·范·埃弗拉对此提出了四种解释。第一种认为,当职业军人对国家施加决定性影响时,导致战争的国家观念会普遍出现;第二种认为,国家往往自我灌输自命不凡的、自我粉饰的以及中伤别国的沙文主义神话,说服民众为公共利益牺牲,并为领导者获取公众支持;第三种认为,官僚机构不称职,向当权者说实话很少得到回报;第四种解释认为,国家往往使它们的国家战略保持不确定的状态。(63) 对这个问题,杰克·斯奈德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指出,部门利益集团,诸如军队、外交官和大商人,其本身不一定想要帝国主义,但是他们能从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政策中获益。这些集团绑架了政府机构以实现自己自私的目标。相反,纳税人却没有为自己的利益成功游说的组织能力和接触途径。为了获得支持,扩张论者欺骗公众、制造帝国的迷思,这包括征服带来财富、进攻性战略占据优势、威胁具有效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精英也开始相信自己制造的这些神话,使得收缩不太可能。(64) 斯奈德承认独裁者难以预测,他们可能是十足的扩张主义者,因为国内制度不可能制约他们。他们也有能力压过那些帝国主义的卡特尔组织,从而表现出明智的行为。民主国家只能是中度的扩张者,因为纳税人拥有权力,可以通过选举和责任制来制衡那些利益集团。(65) 因此,在防御性现实主义看来,某些时候国家表现出不符合体系要求的进攻性行为,是某些国内既得利益集团操纵的结果。这些利益集团挟持了政府和社会,灌输了种种错误观念,导致过度扩张行为。
对于新古典现实主义来说,国家的非理性行为比较难以判定。柯庆生写道,“考虑到沃尔兹的理论在分析外交政策方面的不足,如果我们想要从国际能力分配过渡到特定国家的安全战略时,我们就需要有关行为体如何回应国际体系的理性假设。”(66)“如果领导者误解了能力的分配,他们可能在冲突的关键时刻袖手旁观,对不重要的威胁过度反应,甚至在战争中站错队。如果领导者误把强国当成了弱国,那么它们甚至可能会站在强者一方,使它们的行为看起来更像是见风使舵而不是制衡。”(67) 从前面介绍的基本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如果在有机可乘的时候没有扩张,或者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盲目扩张,或者该制衡威胁的时候没有加以制衡,这些都算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界定的非理性行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种和第三种。扎卡利亚的《从财富到权力》一书,主要探讨美国在崛起为大国后,缺乏明显扩张行为的原因;施韦勒的《未回应的威胁》关注的是,为什么受到明显威胁的国家不能做出有力的制衡回应,例如在美国内战和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英国对美国南方和普鲁士都没有采取积极遏制的措施。在该书中,施韦勒说他提出了“关于错误的理论”,并把这些偏离归因于有关国防政策的国内政治干扰。他指出,国家精英们对环境变化和战略调整的认识状态、精英的凝聚力、社会凝聚力和政府的脆弱程度,这四个变量结合起来影响着国家能否做出合理的制衡反应。(68) 与施韦勒和扎卡利亚一样,大多数新古典现实主义都从“国家—社会”的关系角度,来进一步考察相对实力经过政府结构过滤之后的影响。托利弗总结说,只有经过动员的实力才能被使用。两个因素对此特别重要:国家抽取资源的能力以及(通过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鼓舞动员的能力。(69) 因此,总的来说,对国家非理性行为的解释,新古典现实主义也是求助于国内政治因素,认为后者使国家不能准确地把握体系的要求。
那么,同样是引入国内政治变量来解释非理性行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在下面一节中,将更清楚、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但在这里,至少可以指出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对非理性行为的解释,抛开了体系因素后单独完成。换句话说,要么就是符合体系要求的理性行为,要么就是与体系要求背道而驰的非理性行为。因此,体系因素并不总是主导性的。而新古典现实主义则不同,它解释的非理性行为更多的是偏差(deviation),换句话说,就是合理应对的策略为什么推迟出现,或者甚至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一定会遭到国际体系“结构选择”下的惩罚)。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即使在非理性的行为中,国家仍会试图理性地回应那些行为,但由于国内政治的干扰,而没有办法做到。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注意到前面提到的、双方对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持有的不同观点,我们就会发现,防御性现实主义在引入国内政治变量时,强调的是这些变量单独起作用,例如利益集团追求自己的私利、制造种种“迷思”,最终操纵了国家决策。而新古典现实主义则重点考察这些变量对无政府状态下实力结构的修正作用,也就是说,把它们精确到政府(认识到自己)所能掌控的相对实力这样一个概念。既然政府的认识可能有偏差,或者政府结构使得国家总体实力发挥不出来,那么,也就能很好理解国家的理性回应为何不能及时出现。因此,我们可以说,防御性现实主义是平行引入了国内政治变量,来解释与体系要求背道而驰的行为,而新古典现实主义则附着引入了国内政治变量,以解释与体系要求出现广泛偏差的行为。当然,如前所述,对于什么是国际体系的理性行为要求、什么是非理性行为,双方也有着重大认识差异。
四、理论创造途径: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
我们可以看到,总的来说,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共同点都是力图把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发展为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又都引入了大量的国内政治变量。除了在国际体系、国家利益和国家行为等方面看法不同以外,它们最重要的差异在于解释的逻辑不同。防御性现实主义是用体系结构变量和非结构变量来分别解释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而新古典现实主义是在体系结构变量解释力不足的基础上,附加国内政治变量来解释某些非理性行为。另外,防御性现实主义涉及的非结构变量要多于新古典现实主义,如军事技术和地理形势。如果要理解它们解释逻辑出现重大差异的原因,必须追溯它们在理论创造途径方面的重大差异。简单来说,防御性现实主义是把体系变量和几个其他重大变量并列放在一起,扩大了核心概念的数目。而新古典现实主义则是继续以国际结构变量为核心,使之和国内政治变量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新的核心概念。
1.为什么没有纯粹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
为什么这两种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都不得不引入大量的国内政治变量呢?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在宏观的国际体系层面,如果要建构一种解释国际结构与国际结果之间关系的因果理论,那么,我们可以保持现实主义的绝对纯洁性,仅仅以国际结构作为核心变量。但是,一旦涉及解释国家行为的问题,那么就必然会面对大量的国内政治变量。与国际结果相比,外交政策和国家行为的确会在更多情况下受到非结构变量的影响,并且在外交政策领域,这些非结构变量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其在国际体系领域的影响。在这里,以结构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为例。作为解释体系稳定性的结构理论,结构现实主义是一种相当纯粹的理论。正如沃尔兹自己所说的,“如果有人认为某个因素被不恰当地省略掉了,必须被加进来,那么就必须证明它能够在一个连贯一致并且有效的理论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70) 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现实主义是真正的“最大现实主义”。建立在结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进攻性现实主义试图发展出一种解释大国外交政策的简约结构理论。但是,我们看到,即使米尔斯海默从结构理论中得出国家为了安全会不断扩张的结论,他对具体大国行为的研究,仍相当多地涉及地理环境的变量,甚至还包括核武器这样的技术变量。例如,他认为海洋的存在使得大国不可能获取全球霸权。(71) 这样看来,米尔斯海默关于大国行为的理论也并不是真正的“最大现实主义”。
事实上,对于任何一种体系理论来说,一旦它要较为精确地解释外交政策问题,它就必然面临如何处理该理论的核心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关系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在把一种国际政治理论转变为外交政策理论的过程中,如何引入外部变量。外部变量的引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并没有哪个变量只能是某种范式的理论专有。正如布赖恩·拉思本指出,建构主义从文化、认同等角度来使用观念变量,而理性主义从信息的角度来使用观念变量。他说,“所有的国际关系范式都可以使用国内政治和观念变量。后者并不只属于某一种特定的范式。每一种范式都必须用服务于和表现出它自己逻辑的方式来使用这些因素。关键的区别在于范式是‘怎么样的’,而不是范式的‘涵盖内容’。”(72) 换句话说,某种理论范式总是包含着一定的核心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核心概念就是理论只能包含的唯一变量。没有一种变量能解释所有的事情,也没有一种变量是完全独立起作用而不受其他变量的干扰的。
我们还可以从罗伯特·吉尔平对现实主义国际制度理论的发展中得到启发。国际制度相对于国际结构来说,它是一个外部变量。但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又难以回避国际制度。于是,罗伯特·吉尔平在霸权结构兴衰的基础上,完美地纳入了国际制度的变量。在他的理论中,国际制度既是维护霸权利益的工具,又是霸权兴衰中的斗争目标。因此,新现实主义者完全可以在不否认国际制度变量重要性的条件下,使其为我所用。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相比,吉尔平的国际制度理论仍然是以国际结构为核心变量,而国际制度只是一个辅助变量。但是,没有人会否认吉尔平的理论是一种新现实主义理论。(73)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即使在相当宏观的体系解释层面,结构变量也不是唯一的变量。因此,外部变量的引入并不一定意味着“范式的退化”,或者丧失现实主义内部的一致性和独特性。(74) 关键在于,国际政治的体系理论如何引入外部变量,来创造新的外交政策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代表着两种外交政策创造的理论途径。这两个流派的学者均具有相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意识,力图发现最重要的变量,都具有相当的简约性。在这方面,它们发展出了相当有价值的“威胁均势”和“攻守平衡”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者所做的工作更为精致,其中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扎卡利亚的“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和沃尔福思的“相对实力观念”理论。
2.平行引入的泛化发展:防御性现实主义
在引入外部变量的时候,防御性现实主义基本上遵循了现实主义的三大原则:实力结构本身有意义;其他因素的作用大多数时候取决于结构背景或者与实力结构有关;背道而驰的非理性行为会受到惩罚。例如,我们在斯蒂芬·沃尔特的“威胁均势”理论中可以看到,总体实力就起到了独立的作用。沃尔特指出,“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一国的全部资源越多,它对别国的潜在威胁也就越大。”(75) 由于实力的投射需要地理的距离,所以地理邻近性也很重要。但全部实力只是背景,能直接攻击的是进攻性能力,所以第三个变量也出现了。不过第四个变量,进攻性意图则是相对独立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把那些盲目扩张的观念称为“迷思”,并指出它们常常带来巨大的损失。然而,总的来说,在第二条原则方面,防御性现实主义有点举棋不定,并没有特别强调国际结构的主导作用,而是强调其他因素,诸如意图在很多时候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总的来讲,它是一种平行引入的思路,把实力结构和其他因素并列起来。相应的,在解释国家行为的时候,体系因素主导了对理性行为的解释,其他因素则主导了对非理性行为的解释。
防御性现实主义并不认为这种泛化发展的做法是错误的。自然,他们也不同意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对理论“硬核”的坚持。斯蒂芬·沃尔特曾经指出,“对特设性调整(ad hoc adjustment)的抵制和实际的科学实践也是不一致的。特设性的调整如果能解决某个反常现象,同时不导致新的事实,这仍然是理解上的进步。毕竟,它回答了一个难题。如果这一调整导致了其他的概念或者经验困难的时候,这一调整才是有问题的。”(76) 马修·伦德尔就认为,防御性现实主义更好地说明了欧洲协调,因为它结合了结构现实主义和有关国家偏好的非现实主义理论。(77) 他指出,正如布拉尼斯拉夫·斯兰切夫所观察的,“对于每一块潜在有争议的土地,那些致力于阻止不必要改变的国家都结成了某种联盟。”国家可以得出结论说,扩张会使它们的边界难以防守。如果事实如此,那么理性的安全追求者就会支持保持现状或者收缩。但是,大国的节制也有单元层次的因素。(78) 作为一位相当激进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伦德尔甚至不赞同把“防御性现实主义”称作是“现实主义”。他宣称,“防御性现实主义者的错误不在于结合了结构层面和单元层面的理论,而在于坚持把这个混合总体称为‘现实主义’。例如,斯奈德的过度扩张理论,用现实主义来确定国家应当如何行动,然后用国内政治理论来解释它们为什么不这样做。现实主义理论应当确定国家面临的外部制约和诱因,而不是垄断有关国际政治的解释。”(79) 从某种意义上说,伦德尔看到了防御性现实主义平行引入外部变量后对现实主义理论范式的冲击。
既然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不考虑外部变量与原有现实主义核心变量的密切结合问题,在引入新的变量方面,他们就比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要大胆得多。“攻守平衡”的理论应该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发展。“攻守平衡”依赖于大量的单元层次因素。简单来说,“攻守平衡”主要取决于两个变量:(1)军事技术;(2)地理状况。如果更详细地来看,“攻守平衡”的研究包含了下列因素:技术、地理、实力规模、民族主义以及资源的累积性(从被占领土上抽取资源的能力)。(80) 在防御性现实主义看来,“攻守平衡”的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国际体系紧张程度的变化、国家的外交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攻守平衡”理论抛弃了防御性现实主义对国际体系性质的定性,这一点和新古典现实主义是一致的。这种理论既可以解释冲突,也可以解释合作。不过,“攻守平衡”理论家一般认为,随着核武器的出现,防御一方已经明显具有优势,因此他们的理论为防御性现实主义提供了支持。“攻守平衡”理论同样是平行引入了这些单元层次的变量,理论家们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分辨不同因素作用的大小,从而得出不同的攻守平衡结论。但是,这种分辨、计算和总结即使是可行的,也是相当复杂和困难的。实力对比因素仅仅成为其中的一个变量。在布赖恩·拉思本这样的理论家看来,它的确也算不上是一个现实主义理论了,而是一个综合了各种理论因素、用来分析攻守平衡问题的分析模式。
简单地总结一下,在发展一种外交政策理论时,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不恰当地使用了“分析折衷主义”的做法,也就是平行运用几个理论的要素来解决问题,虽然在不同条件下各个要素的作用有大有小。(81) 这使得他们提出的“攻守平衡”理论或者“威胁均势”理论,强烈地泛化了现实主义色彩,变成了某种分析模式。尤其是“威胁均势”理论,已经成为社会建构主义抨击现实主义的突破口。(82) 从某种意义上说,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路径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理论创造,本文更愿意称之为“理论折衷主义”。
3.附着纳入的主体坚持:新古典现实主义
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也引入国内政治和观念变量,来解释偏离体系要求的非理性行为,但是他们强烈坚持国际结构这一新现实主义核心变量的主体地位,并试图将其与外部变量巧妙地结合起来。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看来,防御性现实主义的错误在于,它强调国家对威胁采取回应,却忽视了这种威胁的观念可能部分地受到相对实力分配的影响。这种理论的错误还在于,纯粹的体系假设说明不了许多实际行为,因此迫使其支持者们把解释性工作,转给了带有特设性质的国内层次变量。(83) 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强调体系因素始终是非常重要的背景,是分析外交政策时第一位的因素,因为从长期来看,一国的外交政策不能超越国际环境所赋予的限制和机会,即使在短期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内政治变量的重要性也取决于结构所给予的国家行为的自由度。这与肯尼思·沃尔兹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后者曾指出,现实主义者并不否认国内政治影响外交政策,但是他们主张,“国际竞争的压力要重于意识形态偏好或者国内政治的压力。”(84) 而且,由于相对实力这样的结构性因素,其影响对于政治行为体自身来说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者提醒说,分析家如果不从一开始就仔细考察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就可能会错误地归因于那些虽然可见、但只具有附属意义的因素。(85)
在法利德·扎卡利亚看来,斯奈德的名作《帝国的迷思》最大的错误在于它对体系动因的轻视。(86) 扎卡利亚雄辩地指出,在分析英国和日本的扩张行为时,斯奈德舍弃体系因素所做的解释费力不讨好。斯奈德认为,英国作为民主国家是中度的过度扩张者,而日本由于国内的军国主义是极端的扩张者。但是,1914年英国统治的帝国疆域是顶峰时期的罗马帝国的两倍。而日本则相反,仅仅在世界的边缘地区谋求地区优势。扎卡利亚指出,英国的政策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英国不那么卡特尔化,而是因为它更强大。如果英国占世界和欧洲GNP的份额,使得一个针对它的“压倒性”联盟事实上不可能出现的话,对于美国而言,则更不可能。(87) 他指出,斯奈德虽然想要结合国内和国际层次分析,但是他错误地最小化国际体系对国家行为的强大影响。“结果,我们没有获得有关体系和国内决定性因素的新结合,而只是对传统的国内政治案例进行重述。”(88) 而正确的做法是,“一个好的外交政策理论,首先应该询问国际体系的因素如何影响国家行为,因为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最有力的、可归纳的特征,就是它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位置。”(89)
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坚持以国际结构作为基础主变量的做法,使得它在引入新的变量方面相对谨慎,并且煞费苦心。如何能使新的变量和国际结构变量很好地结合起来呢?这是摆在现实主义理论家面前的难题。到目前为止,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关注的,主要是国内政治结构和领导者对于相对实力的观念这两个方面。但在形成新的核心变量方面,他们还不够成熟、明确。由于地理变量较难与国际结构变量结合起来,因此,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做的比较少。(90) 但他们的基本点是相同的:以国际结构变量为主,再结合其他变量。这就使得他们与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区分开来。不管国际结构的主变量是与其他变量结合,形成新的核心变量,还是仅仅把其他变量当作中介变量来处理,这种理论创造的途径都具有两个优点:其一,现实主义范式保持了它的相对纯粹性;其二,较好地厘清了主变量和其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是把它们简单糅合在一起。
在这里,只以扎卡利亚和沃尔福思的研究作为例子。法利德·扎卡利亚的“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可以作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一个很好的代表。在这个理论中,扎卡利亚试图修正结构现实主义的实力结构概念。在他看来,国家总体实力的变化未必会带来外交政策的变化,因为对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的国家领导人来说,他们感觉到的是政府所掌握的力量。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承认政治家面对的不仅仅是国际体系的压力,还要面对政府结构的结果,主要是国家力量转化为政府力量的程度”。(91) 扎卡利亚认为,政府结构的四个要素可以影响到国家实力向政府能力的转化,包括政府的职能范围、是否自治、财政能力和集权程度。(92) 通过把国家的总体实力转变成政府掌控的相对于他国的实力,扎卡利亚很好地解释了美国在1865—1889年间的不扩张现象。不过,需要注意扎卡利亚研究里面的一个细节,那就是,对于一国政府来说,它在比较自己与他国的实力之时,可以较好地掌握本国的政府力量(如财政状况、集权程度),但并不能一定很好掌握他国的政府力量。因此,还是会出现误判的可能性。不管怎么样,依据政府能力分布来界定的国际结构,是一个坚持了现实主义主变量的新核心变量,可以更好地解释许多大国在体系中总体实力地位一致时行为并不一致的状况。
威廉·沃尔福思是另一位重要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他把观念变量和国际结构相结合来解释冷战结束的做法,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沃尔福思坚持认为,戈尔巴乔夫终结冷战的做法与苏联的物质利益是基本一致的。换句话说,苏联的政策观念与国际结构所大体确定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因而,这个例子看不出观念的独立作用有多少。(93) 在《实力、全球化和冷战的结束》一文中,沃尔福思和威廉·布鲁克斯则指出,实力结构的变化和精英们观念的变化不可能是即时发生的,两者之间总有一个间隙,因为领导者们获得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也很难克服路径依赖效应,实施激进的政策转换。当精英们在意识到实力结构发生变化之后,政策的变革就会迟早出现。(94) 在苏联的这个案例中,有关苏联衰落的观念的确落后于现实物质变革的状况,但这个间隙并不是特别的大。(95) 不过,如果回溯他在1993年出版的著作《难以把握的均势》,则更有可能提出一个结合了观念变量的新核心概念——被感知到的相对实力。该书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前提:既然实力影响着国际政治的进程,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它是通过影响那些代表国家做出决策的人们的观念来实现的。一些领导者高估他们的实力,另外一些则低估其实力,还有一些人错误理解了相关的趋势,偏见和误解总会出现。(96) 他认为,“在我们建立因果关系时,需要牢记的关键之处包括:实力总是相对的,观念和期望把实力与政策联系起来。当新的证据出现,理性评估可能迅速发生变化。”(97) 力量观念的转变甚至可能和实际的物质能力分配相距甚远。沃尔弗斯断言,“实力观念比物质关系更具有动态性。国家行为的剧烈变动,可能来源于其观念中的实力分配的变动。用典型的能力测量分析是不能得到理解的。”(98)
通过探讨上面两个典型,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结合了包括政府结构在内的政府能力分配,还是结合了观念变量的认知实力分配,都是以现实主义国际结构概念为主体建构出来的新概念,拥有作为外交政策理论核心概念的潜力。扎卡利亚和沃尔福思的研究涉及国内层面的核心变量,但又不仅仅把它们作为中介变量,而是巧妙地将其与国际结构结合起来,从而可以更精确地解释具体的国家行为。虽然引入了新的变量,但是他们的研究并未损害现实主义理论范式的基本原则与纯洁性,也没有给理论的简约性造成太大的麻烦。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新变量的加入可能使得他们的理论不如结构现实主义那么简洁,例如政府结构的界定和观念的认定,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但这些社会建构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样需要面对,给它们带来的麻烦更大。而且,在有些时候(特别是通过解密的外交文件),考察相对实力观念或者说观念中的实力结构,比起考察现实中真正的实力结构还要容易和准确。因此,本文以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已经(有意或无意地)提出了外交政策理论的新核心概念,是一种坚持现实主义基本传统的理论创造。
五、总结与评价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现实主义迎来了持续、迅猛的发展,出现了大量杰出的理论和实证文献,比较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但是,在最后,论文还是打算对这两种理论做一些简单的总结和补充评价。总的来看,到目前为止,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基本上都保持了现实主义范式的基本传统,但在理论观点和理论创造方面,两者都出现了重大的差异。
防御性现实主义一个让人迷惑的地方在于,它在界定国际体系性质的时候,不是完全从理论逻辑出发,而是包含了对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复杂考察,从而得出了国际体系是温和的这样一个观念。问题在于,即使可以证明国际体系的总体性质(或者如基欧汉所说的“世界政治的性质”)在发生转变,不同国家所面临的外部威胁和机遇总是千差万别。因此,也就不能说,国际体系总体是安全的,那么国家行为模式就应该是有节制的、制衡主导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提出的许多外交政策主张(例如有节制的军事和经济政策)看起来更多的是规范性的主张,是从历史和现实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其实,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攻守平衡”理论,在不排除国际体系存在紧张状态时,可以很好地解释很多历史和现实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攻守平衡”理论是防御性现实主义中较有希望的一支。
不过,即使是“攻守平衡”理论,它也面临着引入变量过多、变量如何衡量以及如何处理国际结构变量和外部变量关系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太多的理论化的系统探讨,主要停留在一些技术主导的论断上,例如核武器的出现决定性地使防御具有优势。但是,如何认识恐怖主义和不对称战争呢?如何解释那些不存在核武器的地区的攻守平衡呢?斯蒂芬·沃尔特的“威胁均势”理论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探讨,其确实扩大了势力均衡理论的解释范围,但是这样做在带来好处的同时,却造成了同样多的麻烦,也就是如何评估进攻性意图这样的观念变量的独立性和重要性。杰克·斯奈德引入了大量的国内政治变量来解释非理性行为,很多时候则忽视了体系因素潜在的、但非常重要的影响。从理论的简约性要求来看,这样一种“理论折衷主义”的确会带来现实主义范式的退化。
关键的问题不是应不应该引入其他外部变量,而是如何引入其他外部变量。一些学者谈到“分析层次的回落”,其实这仅仅是针对防御性现实主义,而不是使结构现实主义核心概念更加精致化的新古典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不同,新古典现实主义并不给国际体系做一个紧张还是松弛的定性,再依据这个定性来发展外交政策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虽然意识到了把现实主义等同于竞争性逻辑的不妥,但它自己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防御性逻辑。新古典现实主义坚持,国际体系是国家所面对的环境,不同国家由于自身情况的不同,面临问题的不同,必然执行不同的外交政策。因此,在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上,新古典现实主义都没有明确的价值偏向,这也使得它所能解释的范围更为广泛。从理论的创造途径来说,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放弃国际结构优先的论断,并努力把结构主变量和其他附着纳入的外部变量,巧妙结合起来,初步创造了新的核心概念,从而可以更好地解释大部分外交政策现实。这是一种真正的理论创造,也是现实主义理论家展现他们思维之美的闪光。
注释:
① Stephen M.Walt,“The Progressive Power of Realism”,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1,No.4,December 1997,p.932.
② Robert Keohane,“Realism,Neorealism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in Robert 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7-16.
③ [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④ 有关体系层次分析的局限以及所谓的“分析层次的回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在2008年第7期的“学术争鸣”专栏里,刊登了陈小鼎《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上升与回落》、李巍《层次回落与比较政治学的回归》、刘丰《结构分析的范围与限度》以及左希迎《层次分析的反思与研究领域的拓展》四篇论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一读。在本文最后,笔者将会提到自己的看法。
⑤ 如杰弗里·托利弗(Jeffery W.Taliaferro)把防御性现实主义归为研究外交政策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一支。他首先区分了关于国际政治的理论(新现实主义)和关于外交政策的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两者都有进攻性或者防御性的变体。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变体,不管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古典现实主义,都挑战了安全困境一定会产生紧张冲突的观念。它们都指出,虽然合作是有风险的,但竞争也如此。国家不能预先肯定军备竞赛或者战争的结局,而竞争中的失败会危及国家的安全。参见Jeffery W.Taliaferro,“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3,Winter 2000/2001,pp.131-132,134.因为扎卡利亚坚持认为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必伴有势力扩张的倾向,还有学者将其归入进攻性现实主义,参见Sean M.Lynn-Jones,“Realism and America's Rise:A Review Essa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2,Autumn 1998,pp.157-182。
⑥ Colin Elman,“Horses For Courses: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Vol.6,No.1,Autumn 1996,pp.7-53.
⑦ 例如,许多中国学者把势力均衡理论作为传统现实主义的核心,但摩根索承认,势力均衡理论是不确定的、不真实的以及不充分的,既不是一种好的解释理论,也不是一种好的政策选择。[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60—283页。
⑧ [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55页。
⑨ 宋伟:《全球化的趋势:一种现实主义的再思考》,《国际观察》,2003年第3期。
⑩ Kenneth Waltz,“Neorealism:Confusions and Criticisms”,Journal of Politics and Society,Vol.XV,2004,http.//www.columbia.edu/cu/helvidius/archives/2004_waltz.pdf.
(11) 笔者在《外交评论》2007年第1期的《国际结构与国家行为:内斗的现实主义》一文中,错把兰德尔·施韦勒划入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范畴。
(12)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第4—21页。
(13) 参见[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14) Charles L.Glaser,“The Necessary and Natural Evolution of Structural Realism”,in John A.Vaquez and Colin Elman,eds.,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A New Debate,New Jersey:Pearson Education,Inc.,2003,pp.268-269.
(15) 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No.2,1978,p.187.
(16) Stanislav Andreski,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p.75-76.
(17) Carl Kaysen,“Is War Obsole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4,No.4,Spring 1990,pp.42-64.
(18) Klaus Knorr,The Power of Nation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Basic Books,1975,pp.124-125.
(19) Stephen Van Evera,“Primed for Peace: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5,No.3,Winter 1990/1991,pp.14-15.
(20) Randall L.Schweller,“Tripolarit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7,No.1,March 1993,pp.73-103.
(21) Jack Snyder,“Introduction”,in Robert Jervis and Jack Snyder,eds.,Dominoes and Bandwagons:Strategic Belief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Eurasian Rimlan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3.
(22) Randall L.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1,Summer 1994,pp.105-106.
(23) [美]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门洪华、孙英春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
(24) Aaron L.Friedberg,“Ripe for Rivalry: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1.18,No.3,Winter 1993/1994,p.11.
(25) Peter J.Liberman,“The Spoils of Conques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2,Fall 1993,pp.125-153.
(26) 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Norton & Company,2001.pp.147-152.
(27) 扎卡利亚在讨论美国政府早期对外政策时,谈到了当时国会盲目反对行政机关,以及在很多事情上添乱,这导致了政府力量的虚弱。这种解释似乎符合现实主义者的一贯倾向:强调外交政策领域的理性和统一,贬低自由主义在操作层面的效率低下和混乱倾向。参见[美]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第131—135页。
(28) Bryan D.Jones,“Bounded Rationality”,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1999,pp.297-321.
(29) 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World Politics,Vol.51,No.1,October 1998,pp.149-150.
(30) Ibid.,p.150.
(31) Ibid.,p.147.
(32) [美]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第12页。
(33) Thomas J.Christensen,Useful Adversaries:Grand Strategy,Domestic Mobilization,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1947-1958,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26.
(34) Charles L.Glaser,“Realists as Optimists:Cooperation as Self-Help”,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1994,p.61.
(35) [美]杰克·斯奈德:《新的民族主义:现实主义的阐释及其超越》,载[美]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和阿瑟·斯坦主编:《大战略的国内基础》,刘东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3页。
(36) Thomas J.Christensen,Useful Adversaries:Grand Strategy,Domestic Mobilization,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1947-1958,pp.242-262.
(37) 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49.
(38) 刘鸣:《国际体系:历史演进与理论的解读》,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221页。
(39) 同上书,第222页。
(40) Randall Schweller,“The Progressivenes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in Colin El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eds.,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ppraising the Field,Cambridge:MIT Press,2003,p.328.
(41) Fareed Zakaria,“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A Review Essa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1,Summer 1992,pp.191-192.
(42) Stephen Van Evera,“Offense,Defense,and the Cause of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4,Spring 1998,pp.42-43.
(43)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何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4页。
(44) [美]乔治·奎斯特:《国际体系中的进攻与防御》,孙建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3页。
(45) 即使是查尔斯·格拉泽,他在《作为乐观主义者的现实主义者》一文中,也止步于国家考虑安全利益并不妨碍合作这一阶段。扎卡利亚敏锐地指出,防御性现实主义存在一些现实主义传统上讽刺的理想主义假设,诸如“国家容易满足”(《从财富到权力》,第44页。)在笔者看来,防御性现实主义可能认为大国海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上升反而会遭到制衡,因此避而不谈。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似乎国家参与国际体系就没什么大的利益了。不过,这可能是笔者或者扎卡利亚阅读有限的缘故,而非防御性现实主义自身的问题。
(46) 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p.152.
(47) Fareed Zakaria,“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A Review Essay”,p.185.
(48) 有关“软制衡”的问题,2005年第1期的《国际安全》杂志专门做了一个“制衡行为”的专栏,里面收录了沃尔福思的论文。参见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0,No.1,Summer 2005。
(49) 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World Out of Bala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p.1-21.
(50) Jeffery W.Taliaferro,“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p.129.
(51) [美]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阿瑟·斯坦:《超越现实主义:大战略研究》,载[美]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和阿瑟·斯坦主编:《大战略的国内基础》,第12页。
(52) Matthew Rendall,“Defensive Realism and the Concert of Europ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2,2006,p.538.
(53) Stephen M.Walt,“The Progressive Power of Realism”,p.933.
(54) Matthew Rendall,“Defensive Realism and the Concert of Europe”,p.525.
(55) 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p.152.
(56) Fareed Zakaria,“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A Review Essay”,p.195.
(57) Randall L.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p.74.
(58) Ibid.,pp.82-83.
(59) Ibid.,p.106.
(60) Jeffery W.Taliaferro,“Neoclassical Realism:The Psychology of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in Jennifer Sterling-Folker,ed.,Making Sens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Colo.: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2006,p.38.
(61) Ibid.,p.42.
(62)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第6页。
(63) 同上书,第307—309页。
(64) Fareed Zakaria,“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A Review Essay”,p.182.
(65) Ibid.
(66) Thomas Christensen,Useful Adversaries:Useful Adversaries:Grand Strategy,Domestic Mobilization,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1947-1958,p.12.
(67) Thomas Christensen,“Perceptions and Alliances in Europe,1865-1940”,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1,No.1,Winter 1997,p.68.
(68) Randall L.Schweller,Unanswered Threats: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Introduction”.
(69) Jeffrey Taliaferro,“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Extractive State”,Security Studies,Vol.15,No.3,2006,pp.464-495.
(70) See Kenneth N.Waltz,“Neorealism:Confusions and Criticisms”.
(71) 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现在看来,笔者在《外交评论》2007年第1期《国际结构与国家行为》一文中把进攻性现实主义认定为“最大现实主义”的说法值得商榷。
(72) Brian Rathbun,“A Rose by Any Other Name:Neoclassical Realism as the Logical and Necessary Extension of Structural Realism”,Security Studies,Vol.17,No.2,2008,p.300.
(73) 参见[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74) Jeffrey W.Legro and Andrew Moravcisk,“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2,Fall 1999,pp.6-8.
(75) 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p.22.
(76) Stephen M.Walt,“The Progressive Power of Realism”,p.932.
(77) Matthew Rendall,“Defensive Realism and the Concert of Europe”,p.523.
(78) Ibid.,p.539.
(79) Ibid.,p.540.
(80) 详细的讨论参见:Charles L.Glaser and Chaim Kaufmann,“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4,Spring 1998,pp.44-82。
(81) 关于“分析折衷主义”,详细介绍参见:Rudra Sil and Peter J.Katzenstein,“What Is Analytic Eclecticism and Why Do We Need It:A Pragmatist Perspective on Problems and Mechanisms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http://www.asu.edu/clas/polisci/cqrm/APSA2005/Sil_Katzenstein_Eclecticism.pdf。
(82) Alexander Wendt,“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Summer 1995,pp.78-79; Jeffrey W.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pp.37-38.
(83) 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p.151.
(84) Kenneth Waltz,“A Response to My Critics”,in Robert O.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p.329.
(85) 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p.151.
(86) Fareed Zakaria,“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A Review Essay”,p.185.
(87) Ibid.,pp.186-187.
(88) Ibid.,p.178.
(89) Ibid.,p.197.
(90) 现在看来,笔者在2002年第2期《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上发表的《关于地缘政治结构的理论:批判与建设》一文,尝试的正是以国际结构为主体、结合地理邻近性变量所作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换个角度来说,米尔斯海默的研究方法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也有相同之处,试图把体系因素与地理因素结合起来,但一般来说,后两者都不会赞同他的国际体系永远充满了紧张冲突的观点。
(91) [美]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第54页。
(92) 同上书,第55—57页。
(93) William C.Wohlforth,“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s a Hard Case for Ideas”,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7,No.2,Spring 2005,pp.165-173.
(94) 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Power,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Reevaluating a Landmark Case for Idea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3,Winter 2000/2001,pp.27-29.
(95) Ibid.,p.33.
(96) William C.Wohlforth,The Elusive Balance: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p.2,6.
(97) William C.Wohlforth,“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Winter 1994/1995,p.109.
(98) William C.Wohlforth,The Elusive Balance: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p.294.
标签:国际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