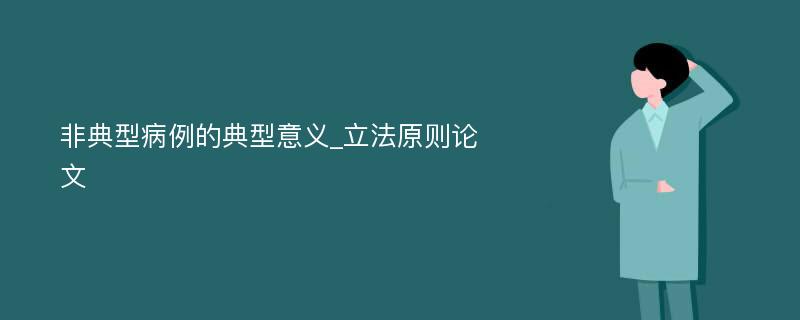
非典型案例的典型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典型论文,典型论文,意义论文,案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0)06-0129-08
一、“非典型案例”的概念:从“疑难案件”谈起
德沃金(R.Dworking)在构建他的“作为整体的法律”理论时曾提出“疑难案件”(hard case)这一概念,他认为,所谓疑难案件即“在法律规范体系中,没有清晰的法规可以明确规范到的案子”。[1]当然,有必要予以明确的是,在德沃金那儿,所谓没有明确规则(norm)可循的案子并非没有法律(law)可循的案件,因为在他看来,除了显在的规则以外,法律还由潜在的原则(principle)以及政策(policy)构成。德沃金并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恰恰是原则和政策、或者说单单原则使得所有的法律构成因素可能组成一个前后连贯的整体。因此,即便出现了没有明确规范可循的案子,也决不意味着法律本身的一个漏洞被发觉,毋宁说,它更多地意味着的是法官的无能:一个称职的法官一定可以在规则之外找到某些既存原则来裁判疑难案件。①
在某种意义上讲,本文所谓“非典型案例”其实也就是德沃金所谓之“疑难案件”,因为非典型案例最典型(或者说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现存法律规范体系中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以用来作为裁判依据。那么,本文为何不径自使用“疑难案件”而要新预设一个“非典型案例”之术语?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德沃金的“疑难案件”有其特定的理论语境,即“作为整体的法律”;第二,两者确实存在某些不同。前文对“非典型案例”的界定表明,非典型案例强调的是没有明确的法条可以遵循,而法条既可能被用来设定规则,也可能被用来设定原则。相对而言,德沃金似乎在界定“原则”时没有很清楚地界分在法律条文中予以明确的原则和没有在法律条文中予以明确的原则;由于德沃金非常强调隐藏在规范背后的原则,并且他自己也明确承认,“我们不能设计出一个公式,用来检验如果使一条原则成为法律原则需要多少制度上的支持,需要哪一种制度上的支持,也不能用来确定它的量度和尺度”,因而“原则是有争议的,原则是有重要分量(差)的,原则是数不清的,并且,它们的转移和变化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当我们还没列举到一半,这一清单的开关就已经过时了”。[2]这至少意味着,德沃金所谓的原则本身很可能成为一个争点,而本文的“法条”则可以实证,因而也不易引起争论;再考虑到有时人们本就很难区分法律条文中的原则与规则,因为二者区别本就不那么清楚——事实上,很多人在区分原则和规则时往往用的也是前者比后者的“抽象性更强”等诸如此类的程度性说法。因此,将“法条”而非“规则”、“原则”作为非典型案例的界定关键词至少从清晰程度上似乎更加可取。第三,“非典型案例”与“典型意义”可以形成一种文体上的对偶关系,也更利于凸显本文的主题。
当前,人们在讨论非典型案例时,似乎更多地是以一种“对策法学”的立场去关注案例本身,这是一种典型地关注非典型案例之非典型意义的研究;或者以一种消费主义的态度拿一个非典型案例来“验证”或“印证”某种理论、观点。这看似与前者不同,然而实际上它却可能具有更大的问题,因为一则此种研究往往是论者先有了某个认识或观点进而“找到”该案例,而非真的从该案例出发进而推衍出某种理论或观点。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此种研究以“实证”之名行反实证之实,因而很可能是一种不诚实的研究;二则此种研究从根本上与前者是一致的,因为它们研究的都不过是非典型案例所具有的非典型意义。② 申言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当前讨论非典型案例的理论文章,更多地关注的恰恰是它的偶然的、非典型的方面,却忽视了它更必然的也即典型的方面。考虑到理论以抽象性、概括性、理想类型性为其本性,因而真正的关于非典型案例的理论研究恰恰不应是此种非典型性或偶然性研究,而应当就非典型案的解决提出一种理论化的模式,以揭示、解释它对于认知法律、探析法律理论所具有的典型意义。
二、非典型案例对于法制实践的典型意义
对于那些笃信三权分立、笃信“严格依法办案”、笃信司法官“在任何案件中都不应有自己的意志”③ 的人来讲,所谓法律的意义也许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因为法律(即通过立法机关制定实在法,以下有时径称“立法之法”)白纸黑字地写在那儿,它的意义当然也就是清晰、显然而确定的;即便有时候面对非典型案例时法律的意义会显得模糊,那也仅仅是因为立法技术尚未完善或立法者疏忽所致,而非立法之法所本应有的面貌。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具有政治正确性但却未必可取的观点。说它政治正确,是因为它符合当前人们对司法权运作的一种道德期待,也符合人民主权以及议会主权至上的政治理想;说它未必可取,则因为它仅仅考虑了司法实践的“应然”层面,而没有从技术上去考虑它在实践操作中是否“可能”。
那么,所谓“法律的意义是清晰、确定和明确的”是否可能?又在哪个程度上可能?我们不妨借用一对语言学中的范畴,即语法语句和语用语句,来回答此类问题。所谓语法语句,是指那种无论从它的构造上还是对其意义的解读上都是按照并且只需按照语法规则就可以进行的语句,在语言实践中,最典型的语法语句应当是语文教程中的例句,此种语句可以大体对译为英文“Sentence”;而所谓语用语句,则指的是存在于具体语境中并且因而也只能结合该具体语境才能被准确理解的语句,相对应地,这种语句则相当于英文中的“utterance”。[3]考虑到人与人的交往其实总是语境化的(也许语言教学除外),因此可以认为任何一个交际语句之意义都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被准确把握,也即其意义必定只能显现于一定的语境之中。进而言之,再考虑到“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是人类公共交往的守则”、“立法规范的意义只有在面对具体案件时才能显现出来”等诸如此类的关于法律之共识,则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用以表述法律的语句只可能是一种语用语句,而非单纯的语法语句,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立法语句都必定也应当是一种交际语句。也就是说,承载着立法意图的立法语言之语义只有在具体的语境(面对具体案件)中才能显现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大体可以称“立法语言是一种语用性语言”。[4]
“立法语言是一种语用性语言”这一论断表明,所谓立法之法的意义“明晰、确定而准确”如果可能的话,也注定只能是语法层面的;④ 从法律实施角度讲,也即在法官眼里它永远也不可能像理想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明晰、确定而准确”,因为当它面对具体语境(也即具体案件)时必得像理解其他语用语句一样需要借助各种语境性因素才能使其意义明晰化。举例来说,我国《刑法》关于盗窃罪的规定从语法角度讲不可谓不清楚,然而当我们用它来打量一具体行为、活动时,却会发现必须结合一系列语境性因素方有可能将该行为或活动认定为“盗窃”,而该行为或活动一旦真的被认定为盗窃,其实也就等于释放了“盗窃”以及相关规定在类似此种语境中的意义。
此种情形不仅发生在典型案例中,而且也发生在非典型案例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6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从语法角度讲,这一规定不可谓不准确、肯定、清晰而具体,然而,这种准确、肯定、清晰、具体其实并不具有多大意义,因为这仅仅是一种纸面上的或“死的”准确、肯定、清晰、具体。当它在落实也即成为“活的”或生活中的规定时,尤其是当它面对诸如这样的案件(语境)时,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它也是不清楚的。譬如,一对分别为21周岁和23周岁的天阉去登记结婚,是否符合该规定?又譬如,一对分别为21周岁和23周岁的同性恋去登记结婚(我国目前并无明文禁止同性婚姻因而这种婚姻从法理上讲应当是合法的),是否符合该规定?甚至于一20周岁的变性男子跟他23周岁的变性未婚妻意欲登记结婚,又是否符合该规定?此时,无论法官最终作出了怎样的理解和判决,都等于实际上赋予也即创设了《婚姻法》该条文一种典型意义以外的意义。更重要的也许是,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一旦一个非典型案例最终被宣判,也即一旦某些法律在该具体案件中的规范意义被认定,它也往往会成为(或至少规范)此后相当一部分地区在面对类似案件时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该法律条文的理解。这也就是说,每一个非典型案例实际上在法律的典型意义以外创设了一种新的规范意义;换言之,一个非典型案例往往也就意味着法律的一种新规范意义被发现,而这即非典型案例对于法律实践所具有的典型意义。
有必要予以指出的是,就当下中国的法制实践来看,由于大部分一审法官在面对非典型案例时往往倾向于选择请示上级人民法院的批复意见,因此,非典型案件的判决往往“贯彻”的是高级人民法院甚至最高人民法院的意志。不难想见,在这种情况下非典型案例的如上典型意义可能会体现得更加明显而典型。以前些年轰动一时的“许霆案”来看,它实际上就赋予了我国《刑法》关于“盗窃金融机构罪”之条文以一种典型但全新的意义:所谓盗窃金融机构,即利用取款机之弊端反复套取金融机构现金的行为,哪怕这种套取在光天化日之下并严格按照银行规定的操作程序进行。笔者相信,由于该案依据的恰恰是上级人民法院的批复,并且又经过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因而它实际上为“盗窃(金融机构)”这一立法术语创设了一种新的规范意义。⑤
还应指出的是,考虑到社会生活的不断流变性,因此,在有些时候还往往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针对一个法律条文起初的典型意义是非典型案例的案子,由于社会情势的变迁而导致类似案件大量、反复地出现,渐渐地它们所赋予该法律条文的非典型意义开始变得与原先的典型意义形成一种分庭抗礼的格局,从而成为该法律条文的典型意义;久而久之,它甚至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而成为该法律条文的唯一典型意义。有关这种案例,最典型的也许是美国宪政史上的“违宪审查”制度的创建:在1804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宣判之前,尽管有少许州法院在实践中从美国《联邦宪法》的有关条文中解读出法院具有违宪审查权之意义,但应该说此种解读不过是一种典型的非典型解读,也就是说,相关宪法条文的典型意义中并不存在此种意义。但随着“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宣判,当然也伴随着其他一些社会情势的变更,法院根据宪法具有违宪审查权似乎反倒成了相关宪法条文的典型意义。[5]指出这一点,是为了明确本文所谓的“一种意义”并不仅仅可能是非典型意义,当放在一个历史长镜头前面时它也可能是典型意义甚至唯一的典型意义之肇始。
再一点需要明确的是,非典型案例对于法制实践的典型意义可能还包括其他方面,或者说可以换从其他角度进行描说。譬如说,我们可以认为非典型案例为立法者完善立法提供了一种启示;我们也可以说,非典型案例为法官判案提供了一种示范意义;我们还可以说,非典型案例为守法者提供了一种理解立法之法的活生生的榜样;等等。但我相信,其中最核心、最具原生意义的必定仍然是为法律创生新的规范意义这一条。
总之,“具体的判决事务在法律问题上并不是理论的陈述,而是‘用词做事’,这是很明显的。正确解释法律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其运用为前提。我们甚至可以说,法律的每一次应用绝不仅限于对其法律意义的理解,而是在于创造一种新的现实。这就像那种再现的艺术一样,在那里对于现存的作品,不管它是乐谱还是戏剧文本,都可以超越,因为每一次演出都创造了和确立了新的现实。”[6]事实上,也只有明确并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即便是认为实证规范可以成为一张“无缝之网”的规范实证主义者凯尔森(Hans Kelsen),也强调“不论一般规范打算如何具体,但司法判决所创造的个别规范始终将加上某些新的东西”。[7]
三、非典型案例对于法学研究的典型意义
在任何一种理论或学术体系中,都存在着大量的公理性或公设性命题、观点,这些命题或观点往往被冠以“权威”、“通说”等名号。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一种理论欲转化为“通说”,则要么是它得到了更上一级权威或通说的支撑,要么就是它在理论界被反复研究、证立,要么则因它为实践所反复应验。考虑到更上一级权威本身也是一种通说性、权威性理论,再考虑到至少在法学这一典型的实践理性之学领域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⑥ 基本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大体可以说:法学研究中的通说以及所有有说服力的观点都应建立在具体法制实践的反复应验基础上。将此论断具体到本文理路中则为:典型案例对法学研究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它可用来作为证立经典理论、通说观点的实践材料;相对应地,非典型案例对法学研究的典型意义则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重思(开放出一个问题的新层次或新面向)、反思乃至否思法学经典命题、理论的契机。
首先,一个或几个非典型案例的出现可能导致我们将长期被遮蔽于经典命题中的问题“问题化”,进而开启对该经典命题重思、反思之进程。所谓“问题化”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借用海德格尔(M.Heidegger)的一段话来予以说明,“所谓遇上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意味着这问题作为问句被说出来让人听见和读到,而且是说,对此问题提问,亦即:使问题得以成立,使问题得以提出,迫使自己进入这一发问状态中。”[8]也就是说,“问题化”一个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口头上说出或笔上写出这个问题,而是释放出该问题之所以是问题以及为何应当关注该问题等“背后”的东西,从而使提问者以及被提问者进入到一种“思”的状态中。譬如说当年的所谓“足坛第一黑哨案”(龚建平案)就给学界问题化了一些曾被遮蔽的刑法学理论问题:首先,该案当然是非典型案例,因为我国《刑法》仅仅规定了商业贿赂和一般贿赂,故而像中国足协这样一个半民间、半官方但显然不是商业组织的机构授权的裁判收受足球俱乐部贿赂的行为,显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以规范,但却又似乎符合犯罪的实质要件“社会危害巨大”;其次,该案的出现使得学界将重新思考贿赂罪的构成体系当中是否应当在商业贿赂、一般贿赂之外设置竞赛贿赂?如果设置,其合理性和可行性在哪儿?进而言之,所谓罪刑法定原则仍然是启蒙或理性主义意义上的而非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吗?⑦ 可以说,没有相关非典型案例的出现,没有不断变动的生活的逼问,而仅凭学者们的凭空冥想或灰色理论的逻辑推衍,那么,也许这些问题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遮蔽下去,甚至永远不被发现。
论及此处,我们不妨重新回到德沃金的“作为整体的法律”观。假如没有“埃尔墨案”、“河鲈科淡水小鱼案”、“麦克洛克林案”等非典型案例的出现并进而“命令”(command)理论界回应这样一些问题,可能根本就不会有德沃金的“作为整体的法律观”这一精辟理论的出现:首先,既然这些非典型案例无法可循,那么,法官应当如何作为?他显然不应该以无法可循为由驳回起诉,那么,他是否应该造法裁判?如果他造法,那么,这意味着法官实际上是用案件发生之后的法来追溯地适用到一个案件中,这是否也就意味着对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违背?甚至,如果他造法,是否又意味着法官对立法权的侵蚀,进而违背了三权分立这一基本宪政架构或原则?如果他既不以无法可循驳回起诉,又不造法裁判,他又应当如何做?可以说,正是对如上这些因非典型案例所带来的问题的思考、回应,才使德沃金构建出他的著名的“作为整体的法律”观。[9]
其次,非典型案例可能为一些理论命题或理论难点提供一种新的或别样的论证思路、角度。正如前文曾提及的,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已经惯于接受诸如“严格依法办案”等政治正确的口号;把相应观念往前推一点则可以说,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立法语言应当“清晰、准确、肯定”或“具体、明确”,以至于法官只需要扮演“法律的自动售货机”之角色即可,与此同时还长期不愿承认立法之法从根本上讲永远也不可能“完善”这一首要事实。一般而言,人们在证立或证否如上相互对立的命题时,往往走的是权力是否应当分立、司法是否应当克制、人类理性是否万能等路数,因此,也往往会倾向于选择接受前者而否弃后者;然而,如果人们正视非典型案例出现时所带来的立法、司法困境,那么,至少在非典型案例前面,所谓“法官说什么,法律就变成了什么”、所谓立法之法的不完善等虽不具足够道德吸引力或政治正确性的说法,可能才恰恰道出了事实的某些层面。申言之,非典型案例的出现为相应理论命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论证角度、思路。
有关这一点,我们还可以“法律规范的一般性”命题的分析、证立来作为典型例证进行说明。按照国内的通说,所谓“规范的一般性指对于和可能处于其效力范围内的主体有同等的国家要求的必须遵守性。换句话说,规范的一般性指对同一范围内的一切人,适用同一的尺度”。[10]根据此种认识,可以认为一般性是一种可以并仅仅通过立法者的眼睛就能观察到并确定下来的法律属性。因而可以进一步推论,法的实施过程对于立法之法的一般性具有的不过是“印证”或“宣示”功能。应当说,如果这个世界只有典型案例,那么,如上认识似乎也足敷用,因为每一个典型案例所“做”的似乎确实不过是印证、宣示法律所具有的一般性属性而已。然而,一俟我们面对非典型案例所带来的挑战——它看上去似乎并不具备与典型案例的同一性因而似乎也不宜适用该相关规范——则必将产生这样的疑虑:难道非典型案例属于立法之法一般性的“例外”?或者说,非典型案例溢出了立法之法的一般性?答案显然应当是否定的,因为如果一个法律规范的一般性真的在立法者那里就可以得到明晰、确定而非典型案例又真的溢出了该一般性,那么,更严谨的做法就应当是排斥该规范的适用而非“拉郎配”式地强将该规范与该案件结合并进而得出判决结论。那么,是否非典型案例就真的无法得到合法性(legality,而非legitimacy)地解决?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因为几乎所有的非典型案例至少在一个高明的法官那儿几乎总是可以得到妥当的解决。这后一事实非常清楚地表明,法律的一般性并没有在非典型案例面前消逝或隐退,而这很可能意味着我们此前对法律的一般性之认识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根据非典型案例所带来的这点启示,我们不妨换个角度看待法律的一般性:即法律的一般性无法通过立法者的眼睛看到,反而是通过用法者的法律适用才能得到规定。我们当然不好说这种认识一定比当下的通说更为合理,但至少它似乎更加符合法制运转的基本情况。因为正是一个个鲜活案例对立法之法的填充(并且正如前述还是创造性的填充),使得立法之法的意义得以明确,同样地我们也可以说,正是法律适用赋予了立法之法以一般性;而且,它更加符合辩证逻辑:马克思主义者反复强调,世间其实根本就无所谓先在、抽象的一般性,有的都一定只是通过具体得到规定的一般性;而辩证逻辑主义者黑格尔(F.Hegel)更是明确指出,“我们把个别归置于其中的一般正是通过这种归置而对自身进行着规定。因此,一条法律的法学意义是通过案例才得到规定,而规范的普遍性从根本上说也是通过具体的事例才得到规定。”[11]可以说,若没有非典型案例带来的此种困惑,我们可能就不会对如上关于法律一般性的认识产生疑问;或即便我们通过他途产生了疑问,也可能找不到合适的方式、角度重思如上命题或理论。
最后,非典型案例有时候还可以为解决某些理论难题提供现成(或几乎现成)的答案。大体上可以说,理论与实践的一大区别就在于理论更加讲求概念的准确以及逻辑的圆满,而实践则更多地是一种全面、妥协的智慧。从这个角度讲,理论家们追求概念的准确、逻辑的圆洽当然无可厚非,但有些时候却也确实会因为这种追求而导致结论的难产。举例而言,“宪政如何可能”就曾经是一个长期困扰理论界的难题。从逻辑上讲,宪政意味着“(良善)宪法至上”,然而却导致如下问题:第一,这似乎与人民主权、议会主权观念相悖;第二,宪法依据什么得以至上?第三,又由谁来看守她的至上性而同时该主体的设置不至于更大程度上冲击人民主权观念、权力分立原则?事实上,这些问题也正一次次地困扰着当年美国这一宪政母国的宪政发展历程。[12]如果仅从逻辑出发,似乎如上逻辑悖谬永远无解。然而,实际中的一系列非典型案例,如1780年新泽西州的霍姆斯诉沃尔顿案、1782年弗吉尼亚州上诉法院判决的共和国诉卡顿案、1784年纽约拉特格斯诉沃丁顿案(汉密尔顿辩护律师)、1786年罗德岛州特雷卫特诉威登案以及联邦最高法院1804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等,使得人们通过对它们的解决,找到了虽不完全符合逻辑但却足以应对如上困境的违宪审查机制:宪法至上源自某种超越法,而法院通过违宪审查权的行使看守宪法的权威,但大法官们需要得到行政首脑的提名和议会的通过。如果考虑到法学是一种典型的实践理性之学,这也就是说法学本就需要更多的经验而非单纯的逻辑,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非典型案例的出现和解决对法学研究有着并且将来一直会有巨大的贡献。事实上,在法律科学的发源地古罗马那里,法学本就直接源自案例尤其是非典型案例的解决。在古罗马世界中,“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乃是同一的。他们的理论是构建来即刻加以适用的,而他们的实践则因为秉受科学的洗礼而全然升华”。[13]
总之,非典型案例对于法学研究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它可以问题化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而问题化的过程往往也意味着一种思考问题的新角度、新进路的出现。正如加达默尔所言,提问本身就已经“包含了由问题视域所划定的某种界限。没有这种界限的问题乃是空的问题”。[14]当然,通过非典型案例的解决,有时候还可以直接为某些理论难题提供答案——考虑到法学乃实践理性之学,故完全可以预计这并非什么罕见的情形。
四、结语:镜与像的比喻
镜子是我们日常生活用品的一种。它的有趣之处在于,一方面,镜中像虽存于镜子中,然而这些镜像却并非镜子本身的,而是镜子所印射之物件的镜像。尽管如此,镜子的价值却恰恰体现在当它被使用也即当它印射出某些物件的镜像之时;另一方面,在镜子中你看到的虽然注定只是幻象而不是“物自体”自身,但这些幻象毕竟能够反映物自体的某些方面。如果不通过镜子形成的幻象,人们甚至无法看到所意欲观察的对象(如微生物)。至少可以说,镜子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别样的、不通过镜子就无法提供的观察对象的途径(如没有镜子你也可以看到你的新衣服,但镜子却显然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观看方式)。申言之,通过镜像,尽管镜子本身并非“看到”的重点,但却实现了它的价值,而物件也得到了显现或不同的显现。
在某种程度上,非典型案例相对于立法之法而言就是一面非典型镜子,如果没有这面镜子,立法之法的某些规范意义可能也存在,但却无法为人们所“看到”——而非典型案例的出现则为把握立法之法的某些规范意义提供了可能:通过非典型案例的映射,立法之法“成像”了,尽管这种像不是立法之法本身,但却清楚地提示出了立法之法的某些层面。可以说,非典型案例也正是通过提供这种“非典型”镜像的可能,从而实现了自己在立法之法前面、进而言之在整个法制实践中的价值,就正如镜子通过提供一种不通过镜子就无法提供的“像”之途经实现自己的价值一样。同样的,非典型案例对于法学理论中的某些命题而言也是一面非典型镜子,通过这个不一般(相对于典型案例而言)镜子的映射,人们可以发现某些可能长期被遮蔽的问题,可以探寻某些新的解决问题的途径,甚至也可以直接提供一种不同的结果。考虑到不断变动的生活提供非典型案例的无限可能,非典型案例完全可以映射出一种理论或一个命题的无限面向,从而为重思该理论或命题提供足够的契机。
在探讨非典型案例的典型意义时将它比作镜子的另一贴切之处在于,无论是通过非典型案例映射出的立法之法的不一般规范意义,还是某个理论、命题的不一般层面,都不是非典型案例本身所具有的,这就正如镜像不是镜子本身所有的一样。因此,非典型案例的典型意义虽然出自非典型案例但却并不属于非典型案例,而属于立法之法或法学命题本身,因为当这些意义通过非典型案例显现并被“看到”之时起,非典型案例就已然退位了。换言之,通过非典型案例发现的典型意义是一种典型的通过非典型案例但又超越后者的典型意义。而这,恰恰也凸显出本文不同于那些就事论事型或消费主义式非典型案例研究的地方。
收稿日期:2010-08-30
注释:
① 关于德沃金的“作为整体的法律”观,是其《法律帝国》一书的主旨,有兴趣者可阅读此书,尤其是该书第六章、第七章。参见R.Dworking,Law's Empire,Massachuset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② 以曾经轰动一时的佘祥林案为例,按照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佘祥林”为“主题”进行检索、阅读的结果(全部文献共有225篇,笔者仅仅阅读了除硕博士论文以外的期刊论文)来看,关于非典型案例之研究的典型作品样式就是这两种,而没有或几乎没有本文立场式的研究。其中,关于非典型案例的“对策法学”研究的典型作品有:陈峰:《佘祥林案的另一种思考》,《人民检察》2005年第7期;张文静:《拷问佘祥林一案诉讼程序上的瑕疵——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和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德恒论坛第三讲》,《中国司法》2005年第7期;陈卫东:《“佘祥林案”的程序法分析》,《中外法学》2005年第5期,等等(其中,发表在报纸上的相关作品几乎全部是此种研究)。关于非典型案例的消费主义式研究的典型作品有:周叶中等:《法律理性中的司法和法官主导下的法治——佘祥林案的检讨与启示》,《法学》2005年第8期;陈兴良:《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考察:以刘涌案和佘祥林案为标本》,《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冀祥德:《民愤的正读——杜培武、佘祥林等错案的司法性反思》,《现代法学》2006年第1期;吴丹红:《角色、情境与社会容忍法社会学视野中的刑讯逼供》,《中外法学》2006年第5期。当然,还有些文章则可能兼具这两个特点,典型者如陈实:《佘祥林案件的思考与启示》,《理论界》2005年6期。
③ 马歇尔(John Marshall)语,转引自B.Cardozo,The Nature of the Judicial Proces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21,P.169.当然,必须明确的是,这并不仅仅是马歇尔,而是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人的观念。
④ 当然,按照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的语言游戏理论来看,则“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维特根斯坦著:《哲学研究》,汤潮,范光棣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31页),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抽象、先在的语法规则可以规定或确定一个词的所有语义。因此,从根本上讲,其实即便从所谓语法角度讲也无法准确、肯定、清晰、具体地拓清一个词的词意。事实上,人们之所以可能误认为这立法之法的语法语义是清晰具体的,很可能是因为他忽略了这种清晰具体其实不过是下语境式的,对于将来的一个法律适用者(或一个单纯的法律文本读者)而言,很可能由于其语法本身以及所处大背景的变更而使得这些立法术语变得模糊、抽象。
⑤ 这里也许有必要简略探讨一下在判例法系国家非典型案例对于法制实践的意义。从表面上看,由于判例法系国家不像大陆法系那样依据法典来裁判案件,而主要用先例作为判案依据,因此,本文关于非典型案例可以“探知法律的一种意义”之结论可能未必适用于判例法系。实际上若我们深入分析二者就会发现它们并无根本的不同:在法典法系国家,非典型案例探知的是立法规范的一种新意义;相对应地,在判例法系国家,非典型案例探知的是某个先例所具有的一种新意义。申言之,它们的核心都在于可以探知作为其判案依据之大前提的一种新意义。
⑥ 虽然这话的直接来源是一篇政论性文章因而可能仅仅具有较重的意识形态味而未必具有理论说服力,但实际上它恰恰建立在周密的理论分析、论证基础上。详可分别参见《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毛泽东:《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马克思:《冠以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
⑦ 笔者曾专门撰文讨论这个问题,详可参见周赟:《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辩证法》,载《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