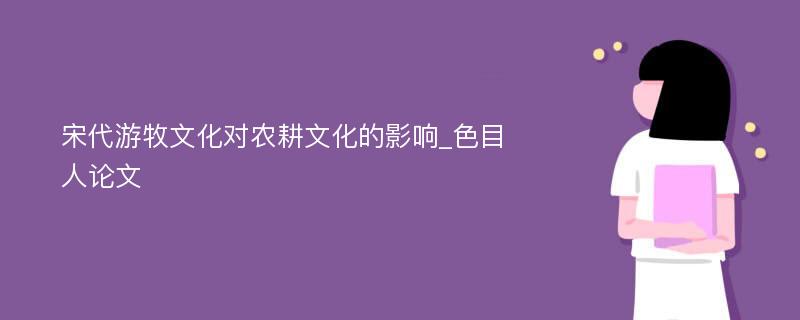
宋元时期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冲击毁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宋元论文,农耕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经济的倒退
自北宋建国之日起,北方游牧民族一直对中原农耕民族构成巨大的武力威胁,其总的趋势,是游牧民族在军事上呈进攻态势且步步南逼,到元帝国建立最终达到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全面统治。
从更长的时间段及更广阔的空间中来看,游牧与农耕的对垒乃亚欧大陆数千年未易之基本格局。“整个亚欧大陆古来即存在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特征迥异的经济类型,由此导致了生活在亚欧大陆核心部位的游牧人与生活在亚欧大陆东、南、西三方濒海边缘地带的游耕人之间长达数千年的冲突、互补和交融。”①只不过在中国,这种冲突、互补及交融在宋元数百年间表现得尤为突出罢了。
游牧与农耕是依据各自生态环境所发展出的不同经济类型,从人对自然的适应而论,并无先进落后之别。但不同的经济类型,会制约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人类学家研究发现,游牧人的社会文化组织虽可能比初级农业生产者复杂,却一般较集约农业生产者简单。例如,游牧人与集约农业生产者相比,在人口密度上是后者较高,在社区规模上是后者较大,专职手工业者及专职政治官员也是后者较多②。具体到中华大地上,中原地区的农业早已发展到一个极为成熟的水平,农耕人较之游牧人长期保持着一种经济文化上的优势。
中原农耕人的这种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在北方游牧人军事上的优势面前被粉碎了。因此,无论女真人还是蒙古人,当他们踏入中原农耕区之后,依然循其旧有的生活习惯行事时,就造成了广大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上的停滞或倒退。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③
例如,金人实行奴隶制,他们侵占北方后,对掳掠的汉人一律变为奴隶,据南宋洪迈《容斋三笔》卷三《北狄俘虏之苦》载:
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问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而金人囿于其生活旧习,轻视农耕,大量圈占民田,改建为牧场或猎场,致使大面积良田荒废。失去土地的农民,沦入离乡背井,身无所寄的悲惨境地。“汉族人民和他们的土地被金统治者强占之后,人民不是被转变为他们的奴隶或‘驱口’(近似奴隶的农奴),就是被远徙到‘阴山之恶地’,而无以自存。”④农人的失业及田地的他用,必然严重破坏北方的农业生产,使生产力骤然降低。
人祸还会招致天灾。金人的游牧所需的是无尽荒野而非纵横阡陌,故他们对农田水利全不在意,日积月累,河道淤塞,泛滥成灾。同时,大量树木被砍伐,自然生态受到破坏。这些都使天灾频降,使人员伤亡。在号称人口最盛的金章宗时,连同塞外移来的金人在内,北方总人口不过4千余万,而北宋神宗时同一地区的人口已有5千余万。人口减少造成劳动力不足,实耕田地也大量减少,如金宣宗时,河南军民田总数为197万顷,实耕仅96万顷,南京路旧垦田约40万顷,金时只有约10万顷。⑤
经济的倒退在元朝表现得更为突出。蒙古人以前所未有的宏大气魄,建立了一个“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⑥的大帝国,大江南北尽为其所有,游牧民族深入农耕民族的腹地,二者的矛盾冲突必然深刻地显现出来。“蒙古兴起后连年发动战争。所过之处,人民遭屠戮,农田受破坏,工匠被驱役,财物被掠夺。蒙古统治者用统治草原畜牧经济的方式来管理中原高度发展的封建农业经济,使中原地区社会经济逆转。”⑦
改农为牧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还在元太宗窝阔台征服金朝北部之初,就有蒙古大臣上书曰:“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⑧虽然其后悉空汉人以为牧地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但局部地改农为牧的事件却频频发生。据杨志玖先生总结,改农为牧可分三种情形⑨。一是在京师和大城市周围开辟牧场,如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七月,“谕河南管军官于近城地量存牧场,余听民耕”⑩。至元十年(1273年)十一月“大司农司言:中书移文,以畿内秋禾始收,请禁农民复耕,恐妨刍牧”(11)。二是在蒙古军驻地周围也多占民田为牧地。《元史·姜彧传》曰:“行营军士多占民田为牧地。”《元史·奥敦世英附侄希恺传》亦曰:“蒙古军取民田牧,久不归。”三是蒙古贵族强占民田。据《续文献通考》卷1《田赋》引赵天麟《太平金镜策》曰:“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甚至有的贵族圈占农田为牧场,面积之大,达十余万顷。如山东沿海登、莱一带,都成了“广袤千里”的牧场(12)。由此数项,即可见元时农业受害之严重。
与金人相同,蒙古人也实行奴隶制,故其在占领中原的过程中,所俘获者多被降为奴隶。清人赵翼即指出:
元初起兵朔漠,专以畜牧为业,故诸将多掠人为奴,课以游牧之事,其本俗然也。及取中原,亦以掠人为事,并有欲空中原之地以为牧场者。耶律楚材当国时,将相大臣有所驱获,往往寄留诸郡。(13)
例如,《元史·张雄飞传》载:“阿尔哈雅行省荆湖,以降民三千八百户
没入为家奴,自置吏治之。岁收其租赋,有司莫敢问。”
蒙古入主中原之初,还实行了许多妨碍农业生产的虐政。例如“括马”,又称“刷马”,即强行无代价的从民间搜刮马匹。蒙古人是马上民族,他们特别注意马政。对他们来说,马是重要的财产,又是不可或缺的作战工具,一方面自己需要,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汉人利用马匹反抗。有元一代,通过“括马”从民间搜刮去的马匹总数已难以一一计数,据估计,在元朝统治的百余年中,中原汉人地区被括马匹应在百万匹以上(14)。此外,还以微薄代价从民间强买了大批的马和牛。须知在尚无机械动力的时代,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畜力的使用,民间大批的牛马被元朝统治者搜刮而去,对当时农业生产的消极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经济的倒退是有阶段性的,主要表现在游牧民族进入农耕地区的初期。在不同文化发生接触时,必然经历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15)的过程,经济文化上占优势地位的民族会对相对处于劣势的民族产生较大的影响。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过:“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16)中华大地上的游牧民族在征服文化较先进的农耕民族过程中也逃脱不了这条规律。游牧民族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明智之士在与农耕民族的接触中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接见南宋降臣高达时即曰:“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虽得其地而无民,其谁与居?今欲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17)这样的认识,终于导致忽必烈全面改革旧俗,推行“汉法”。
“农耕与游牧作为东亚大陆两种基本的经济类型,是中华文化的两个彼此不断交流的源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文化是农耕人与游牧人的共同创造,中华文化是农耕人与游牧人在长期既相冲突又相融汇的过程中整合而成的。”(18)因此,宋元数百年间游牧与农耕的碰撞、北国与南疆的交流未尝不是中华文化弃旧图新、广纳博采的一个有益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的某些时期,不同文化与民族间的相互隔膜、抵触、敌视,却也使中华文化的发展陷入停滞乃至倒退的歧途。蒙古人与农耕民族在文化上的格格不入(如蒙古人热衷向西方游牧地区扩张而对南方农耕地区兴趣不浓、占领农耕区后改农为牧以及多数蒙古族官吏不喜学习汉语等),即妨碍了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间的有机整合,亦未尝不是导致大元帝国在中原统治不过百年的重要因素。
二 东亚的“种姓制”
中国历史上诸民族的活动范围,多在今中国之内,与宋对峙的辽、西夏、金亦是如此。但成吉思汗所统率的蒙古人则不然,蒙古人崛起大漠后,先用兵于西北,至太宗、宪宗之世,蒙古人之疆域除中国之西北部外,还据有今之内外蒙古、天山南北路、阿富汗、波斯之北部、俄罗斯之南部等处。在蒙古西征胜利之际,成吉思汗划分了四子的封地,此即四大汗国。长子术赤封地为钦察汗国,国势最盛时东到额尔齐斯河、西至多瑙河下游、南至高加索、北达今俄罗斯保加尔地区。次子察合台封地称察合台汗国,为西辽故土。三子窝阔台封地为窝阔台汗国,领有今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方。四子拖雷之子旭烈兀封地为伊儿汗国,领有今高加索山和里海以南地方。蒙古人横跨欧亚的军事占领,使得大蒙古国中包含了众多的种族和民族成分。
忽必烈于1271年建立的大元同样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混居的大帝国。面对人口远远超过蒙古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元统治者采取了民族分化的政策。其实,早在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中,任用掌管兵权、钱谷的官吏,即按民族规定了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的四等级顺序。元统治者则根据民族和被征服的先后分人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在用人行政、法律地位及其他权利、义务各方面都有种种不平等规定。
在四等人中,蒙古人为元朝的“国族”,元统治者称之为“自家骨肉”。蒙古人有多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即载有蒙古氏族七十二种。第二等色目人,是元朝统治者对除蒙古以外的西北各族、西域以至欧洲各族人的概称,据陶宗仪称有钦察、唐兀、阿速、康里、畏吾儿、回回、乃蛮等三十一种。但“色目”原意即为“各色名目”,其种类繁多,加之译名不一,故很难统计出元代色目人的具体种数。第三等汉人,又等汉儿、乞塔,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直、高丽诸族以及较早为蒙古征服的川、滇二省中人。据陶宗仪称,汉人有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赤歹、渤海八种。第四等南人,又称蛮子、囊加歹、新附人,指最后为蒙古征服的原南宋境内各族。四等人中,第三等的汉人和第四等的南人绝大部分都是汉族。
元朝的四等人制度,不免令人联想到印度的种姓制度。在印度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就出现了种族奴隶制,此制与婆罗门教的教义相结合,将世人分为四大种姓。一为婆罗门,即僧侣贵族,他们掌握神权,主持祭祀,是人民精神生活的统治者。二为刹帝利,即武士贵族,他们掌握政治和军事实权,是古印度国家的世俗统治者。三为吠舍,即农牧民和工商业者,是被剥削的小生产者。四为首陀罗,是奴隶、杂工和仆役,首陀罗来自被征服的达罗毗荼人和地位下降的吠舍。在印度社会中,不同种姓之间不能通婚、不能交往,甚至不能同坐同餐。印度的种姓制是独特的,但是,“就种姓体系而言,印度与其他一些也拥有封闭性阶级和众多少数民族的国家,从根本上说是相似的”(19)。元朝的四等人制便与种姓制在基本特性上相似。
元朝的四等人制与印度的种姓制都是一种社会分层或曰社会阶层化(socialstratification)。“无论任何东西在其安排上,若是分为高低不同的各种等级,都可称为阶层化。其中每一等级都是一个阶层(stratum)。应用于社会方面,它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人,按照某一个或几个标准,如财富、权力、职业、或声望之类,被区分为各种不同等级的安排方法或状态,其中每一等级的人都是一个社会阶层。”(20)自原始社会解体后,除极少数采集狩猎民外,大多数社会都存在社会分层现象。分层的情形又可分为两种类型,即开放阶级制(阶级界限不严格,各阶层间人员可自由流动)和封闭阶级制(阶级界限严格,各阶层间人员不能自由流动)(21)。极端类型的实例较少,大多数社会的分层情形是介于开放与封闭之间。
用开放与封闭的标准来衡量元朝的四等人制度,可以看出此制是偏于封闭一端的。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这四个阶层,大略是以种族或民族划分的,其间有血缘、地域或文化上的差别,本就难以逾越,更何况元朝统治者还有种种细密的规定,用以防止四种人在身份地位上的混淆。如《元史·世祖纪》曰:“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八月,定拟军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儿等依各官品充万户府达鲁花赤,同蒙古人。女直、契丹同汉人。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由此可见诸等人间界限之分明。
各阶层成员在地位和待遇上的不平等从许多方面表现出来。首先,在官吏任用上有别。“官有常职,位有长员,其长皆以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故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22)中央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的丞相,通常“必用蒙古勋臣”,连色目人都极少得任此职。对军机重务,元朝统治者更是严防汉人涉足,故掌兵权之枢密院长官终元一代除少数色目人外皆为蒙古大臣,无一汉人,“以兵籍系军机重务,汉人不阅其数”(23)。元代有荫叙制度,即官吏的子孙可自然得到一定官职,也对蒙古人和色目人优惠。如《元史·成宗纪》曰:“大德四年(1300年)八月癸卯朔,更定荫叙格:正一品子为正五,从五品子为从九,中间正从以是为差。蒙古、色目人特优一级。”
其次,各阶层人在法律地位上不平等。“犯罪者处罚时,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各别。以前者宽后者严为原则。”(24)例如,据《元史·刑法志》所说,“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欧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其后又改为“蒙古、色目欧汉人、南人者不得复”,于是前者得以援例肆意欺压后者。而各阶层人犯同样罪,在量刑上也有不同,如同是犯偷窃罪,汉人、南人断刺字,而“蒙古人有犯及妇人犯者,不在刺字之例”。
蒙古统治者还对汉人、南人进行严密的军事防范。如禁止民间收藏兵器,对汉人、南人极严,于蒙古人、色目人却并不禁止;又如括马,亦是汉人多征,色目人少征,于蒙古人则不征。据顾炎武《日知录》卷12《禁兵器》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汉民持铁尺手挝及杖之有刃者悉输于官。六月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入官。……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四月癸酉,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入官。”对兵器的收藏也有不平等规定,如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分汉地及江南所拘弓箭兵器为三等。下等毁之,中等赐近居蒙古人,上等贮于库。有行省、行院、行台者掌之。无省、院、台者,达鲁花赤、畏兀、回回居职者掌之。汉人、新附人虽居职,无有所预”(25)。元朝政府甚至禁止汉人、南人畜鹰、犬为猎,违者没入家资。丞相伯颜当国时,为防止南人造反,还曾禁江南农家用铁禾叉。
以上种种,均使得四等人之间畛域分明,成员彼此流动甚难,四等人制真正称得上是“东亚的种姓制”。但元朝的四等人制尚不是极端的封闭制,且不说第三等人汉人与第四等人南人间本就无法割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后两等人与蒙古人、色目人之间,也未必总是判若泾渭。如有的学者便曾举例说明元代色目人中的回回与汉人通婚之事并不少见,由此而促使回回华化(26)。而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又“互相仿效,更易名姓,氏族淆惑,乃不可辨”(27)。可见元代的四等人在某些层面上还是可以沟通的。
除民族与种族的等级界限外,元朝统治者还将社会上的职业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28)。文人儒士竟屈居“老九”,位于娼妓之后,仅先于乞丐一步,真个是斯文扫地。另一方面,元朝很少举行科举,虽汉官屡次请求开科取士,却总被拒绝,直到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政府才恢复科举(29)。但即使恢复科举,亦有种种不平等的规定:在考试科目上,蒙古人、色目人仅考二场,汉人、南人则需考三场,且考试内容前者易后者难;如“蒙古、色目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30);发榜则蒙古人、色目人为“右榜”(蒙古以右为上),汉人、南人另立一榜为“左榜”;录取名额虽汉人、南人应试人数多于蒙古人、色目人,但四种人录取名额却一样,且派起官来,蒙古进士比色目人高一等,色目人又比汉人、南人高一等。其实,蒙古人、色目人要做官自有其路径,没必要参加科举,他们可在一定年龄后充当皇帝侍从,然后继承父兄职位或提拔担任其他职务。
职业的分级及科举的罕有,使元代文人基本上处于贬之唯恐不低、进取却是万难的困厄境遇之中。于是乎,文人学子或隐居著述、优游林泉,或晦迹技艺、以自存活。这种局面造成的后果之一,便是元曲之勃兴。“王国维曾说,元初不举行考试,反倒是杂剧勃兴的原因。盖自唐宋以来,读书的人们,一向都是以科举为目标,来努力用功的;一旦那作为学问的目的的科举废止了,不消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条件。把出世的道路断绝,效果消失,并且特意修得的学力,也无所发挥;因此便形成转向当时新流行的杂剧,挥洒其才笔的情形了”(31)。
元曲是辉煌的,它是我国古典文学自唐诗、宋词后的又一高峰。从这个角度上看,文化的福与祸确实是相倚并存的。但元曲的成就并不能掩盖元代统治者对文化及文化人进行摧残的劣迹,因为后者是有意实施的文教政策,而元曲只是“无心插柳”的意外收获。其实,在元曲中就饱含了对当时社会上民族压迫文化潦倒的控诉。有学者指出,元曲在精神上有两大主调,一是倾吐整体性的郁闷和愤怒,二是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32)这两大主调,正是元代文人学子失意心态的反投。
当今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者,比上个世纪末的古典进化论者谨慎得多,他们不愿贸然判定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优劣正误,而宁愿坚持文化相对性(cult-ural relativity)的立场。但是,元代禁止社会阶层间流动的四等人制以及蔑视轻视文化人的种种做法,造成了社会阶层间的不平等,妨害了多数人的身心自由,践踏了文化的尊严,从中实难寻出有利中华文化健康发展的因子。将这段时期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去观照,不能不说对民族、职业分等的做法是一种社会倒退、是蒙昧压倒了文明。
注释:
①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109页。
②〔美〕恩伯夫妇:《文化的变异》(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2页。
④尚钺:《尚氏中国古代通史》下卷,第199页。
⑤尚钺:《尚氏中国古代通史》下卷,第201页。
⑥《元史·地理志》。
⑦韩儒林主编:《元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
⑧《元史·耶律楚材传》。
⑨杨志玖:《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136页。
⑩(11)《元史·世祖纪》。
(12)《中国史稿》第5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页。
(13)赵翼:《廿二史札记·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
(14)杨志玖:《元史三论》第140页。
(15)文化涵化指的是不同文化的群体在持续的直接接触中所发生的文化传播过程,其中某一群体通常有较为发达的文明。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页。
(17)《元史·世祖纪》。
(18)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第125页。
(19)〔美〕马文·哈里斯:《文化人类学》(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297页。
(20)(21)龙冠海:《社会学》,(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300、303页。
(22)赵翼:《廿二史札记·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之长》。
(23)《元史·兵志》。
(24)〔日〕箭内亘著,陈捷、陈清泉译:《元代蒙汉色目待遇考》,转引自周谷城:《中国通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6页。
(25)《元史·世祖纪》。
(26)杨志玖:《元史三论》,第156-162页。
(27)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7页。
(28)谢枋得:《叠山集》,转引自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第737页。
(29)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9页。
(30)《元史·选举志》。
(31)〔日〕盐谷温:《元曲概说》(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23页。
(32)余秋雨:《中国戏剧文化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
标签:色目人论文; 蒙古文化论文; 农耕文化论文; 元朝历史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农耕文明论文; 中华文化史论文; 元朝论文; 元史论文; 游牧民族论文; 汉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