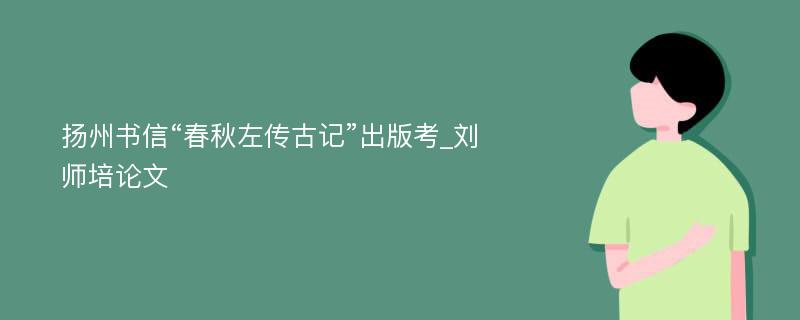
“扬州书信”所见《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出版考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注疏论文,扬州论文,书信论文,所见论文,春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6;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0)04-0115-08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是近代经学大师、扬州“青溪旧屋”刘文淇祖孙三代相传补续而成的一部书稿,在《左传》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34-1938年,南桂馨、钱玄同、郑裕孚等在为刘家第四代学人刘师培(1884-1919)编纂《刘申叔先生遗书》过程中,也启动了刊印这部凝聚着祖孙三代毕生心血的刘氏“镇家之宝”的工作。后因种种原因,不但刊印工作没有成功,而且其事也成为鲜为人知的学术文化出版秘密。近日,笔者在梳理刘师培曾孙女婿、扬州收藏家巫庆先生保存下来的数十封20世纪30年代的书信时,有幸觅得其珍贵印迹,同时也留下了一些有待破解之谜。
一 刘氏三代传一经
建造于清中期的扬州“青溪旧屋”,系清代嘉庆、道光、咸丰年间著名经学家刘文淇故居,也是其曾孙、中国近代国学大师刘师培故居。在中国学术史上,“青溪旧屋”刘氏以祖孙“三世一经”而闻名于世。所谓“三世一经”,特指从刘文淇开始,到儿子刘毓松、孙子刘寿曾,祖孙三代对《左传》旧有注释所做的疏证工作,其所成稿即《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刘文淇(1789-1854),字孟瞻,江苏仪征人,出生于中医家庭。其父刘锡瑜悬壶乡里,治病救人,但家境并不富裕,刘文淇从18岁起便颠沛流离,为养家糊口,做过塾师、编辑、幕僚等。不过,刘文淇真正给自己的人生定位还是学者,并为此做出了种种艰辛努力,最终获得了“扬州纯儒”的赞誉。他一生著作等身,传世有《楚汉诸侯疆域志》3卷、《扬州水道记》4卷、《读书随笔》20卷、《青溪旧屋集》12卷和《重修仪征县志》等多种,甚至还写有关于种植与收藏兰花方法论的《艺兰记》问世。其中最高的一座丰碑,自然是由他肇始的“三代传一经”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他之所以撰著此书,缘起于清代经学家对旧有《十三经注疏》,尤其是对唐宋旧疏多有不满意之处,于是他和几位同道在道光八年(1828年)商定另作新疏,并由他负责《左传》;但仅完成《春秋左氏传旧疏考证》8卷,草创《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资料长编几十篇,未及写定,便于咸丰四年(1854年)遽尔遗世。
刘文淇有子毓崧(1818-1867),字伯山,一字松崖。道光二十年(1840年)得优贡生,因为人质直,先后十赴乡试,均未中举,主要以教书为业,曾办金陵书局。刘毓崧幼承家学,尽读父书,淹通经史,旁通诸子百家,岿然为江淮大师。他除继续进行《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外,还著有《通义堂文集》、《通义堂诗集》、《通义堂笔记》、《周易旧疏考证》、《尚书旧疏考证》、《王船山先生年谱》等。
刘寿曾(1838-1882),字恭甫,一字芝云,刘毓崧子。同治三年(1864年)、光绪二年(1876年)两中副榜,入金陵书局校定群籍。著有《传雅堂集》、《芝云杂记》、《春秋五十凡例表》、《读左札记》等。他真正矢志以殁的大著,则是继志先祖事业,严立课程,发奋补纂和手录祖父刘文淇创始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可惜因积劳成疾,竟以45岁英年去世,使刘氏三代《疏证》的历史时针,不得不定格在“鲁襄公五年”。
《春秋》一书原系春秋时期鲁国的官修编年史,后经孔子修订,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242年历史。《左传》依《春秋》而作,全称为《春秋左氏传》,起于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比《春秋》稍长。从鲁隐公元年到鲁襄公五年是154年,占全书的百分之六十。刘氏《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先列《左传》原文,将旧注列于相关文句之下,然后加以疏证。取材广博,资料丰富,可谓集《左传》研究之大成。
对于这部家藏之稿,刘寿曾长孙刘葆儒在生前曾留下详细说明,现今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刘葆儒侄孙女婿、扬州收藏家巫庆先生家中。其文共分五段,主旨也各自有别:
《左传旧注疏证》之著,始于先高祖孟瞻公,至先曾祖伯山公,未果卒业,先祖恭甫公继之,至襄公五年传“不可谓忠乎”句成绝笔(《清国史·儒林传》称至襄公四年,与存稿实状不符)。
原稿多为恭甫公手录。
稿本中,隐、桓二公有墨迹稿,有誊清稿;庄、闵二公仅有誊清稿;僖公元年至廿二年有墨迹稿,其誊清稿则大半出自先三叔祖谦甫公(即刘寿曾之弟刘富曾——笔者)手(誊清稿元年至十六年,经为全文,自十六年传,至廿二年,仅见引证书名);文、宣、成、襄四公有墨迹稿,文、宣二公一部分由先三叔祖手抄,成、襄二公稿由葆儒手抄,原稿墨迹有不易辨识者则阙疑。
原稿共分装七本,誊清稿分装十一本。
稿上附笺为当时著者征得各家意见,惟出诸何人,多不可考,书头批注亦然。其在本文添注字句,显出先三叔申叔公(即刘师培——笔者)。书中夹有纸条,乃葆儒纪录,有襄公以后各年文字,而引文散见于襄公前各年本文者。
笔者曾在巫庆先生家中看到他保存的两卷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疏考证》手稿。纸张用的是当时著名纸店“青藜阁”所售之纸,上面盖有“孟瞻审定”字样的刘文淇私章,每页9行,用工整小楷写成,字迹清秀,一丝不苟,几乎看不到涂改的痕迹。由此可以推断,这是刘文淇手稿的誊清写定本。
在两卷手稿上面,还留有当时著名经学家刘宝楠、包慎言等人的遗墨。如第222页原文:“杜注:雎水……有妖神,东夷皆社祀之,盖杀而用祭。”刘宝楠用一张纸条夹注标明:“杜佑言‘社祀之’,依《释文正义》,‘祀’当作‘祠’。”两卷手稿上,这些大大小小的纸条有十多处。这表明,刘文淇当年将书稿誊清写定后,曾请与他交谊较深的刘宝楠、包慎言等学者审阅,刘、包等人就边看边夹注自己意见,以示不同见解,也就是上文刘葆儒所说的“稿上附笺为当时著者征得各家意见”者。可见,这份残缺不全的手稿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还传达给我们重要的学术信息,既表现了刘文淇虚怀若谷的治学精神,也表现了刘宝楠、包慎言等人互相探讨商榷的学术合作精神。
二 南桂馨与刘家商议如何刊行《左疏》
虽然刘家《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只是一部未完成的书稿,但它凝聚了祖孙三代经学大师的毕生心血,因而不仅成为“青溪旧屋”刘氏的“镇家之宝”,也成为当时学界文人心羡瞩目的对象。出于对刘氏源远流长家学的敬重,南桂馨、郑裕孚等人在为亡友、刘家第四代学人刘师培编辑出版《刘申叔先生遗书》的同时,决定另外出资,刊行这部众所仰望的刘氏“镇家之宝”。但是,迄今为止,学界对此事皆语焉不详。近日,在巫庆先生家中发现了五十多封民国时期信函①,其中有十余封是围绕《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出版计划的有关信函(以下简称“扬州书信”),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前所未见的原始资料。
在这十余封通信中,主要涉及南桂馨、郑裕孚、刘师颖和刘葆儒四人。南桂馨(1884-1968),字佩兰,山西宁武人,中国同盟会会员。他一生从政二十余年,是晋北有名富户,为人果敢,机敏善变,著有《山西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捐资出版刘师培《遗书》。郑裕孚(1882-?),字有愚、友渔,号淡志室主人,广西临桂人。南桂馨刊印刘师培《遗书》时,聘他作校对。刘师颖(1896-1944),字容季,刘师培堂弟,时任天津市中国银行襄理。他读书敏异,擅长诗古文词,精通楷法,也是一位功底深厚的学者。刘葆儒(1899-1952),字次羽,刘师颖堂兄刘师苍之子,当时在上海谋职。著有《广告学》一书,是中国广告学创始人之一。刘葆儒在上述四人中年龄最小、辈份最低,但他既是刘寿曾长孙,而且刘寿曾与祖、父三代所传之《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稿及整个刘氏家族的大量论著稿也都保存在他的上海家中,因此他是关涉整个刘氏家藏稿的核心人物。
作为编纂刘师培《遗书》的主创者,南桂馨在一封答复刘师颖的书信中,在告知《遗书》编纂事宜时,顺便了解《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的总体情况:“容季仁兄雅鉴:大札诵悉。令先兄遗书,前已托钱君疑古整理核定。《攘书》一种用否付印,俟与钱君商之。《左传疏》稿凡若干册,约有若干万言,须有一番统计,再定铅印刻版之计画(划)。再,襄公后不书,申叔先生已否一律补?抑或仅有长编?□仅有长编,鄙意可由当代经学家代为添补,庶成完璧。请致函令侄时一详询之。”②“令侄”即刘葆儒。从此信内容和语气分析,应该是刘家先提出《左疏》之事,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也只是顺便简单地询问是否可以将《左疏》印行,因此南桂馨的回答首先也是简略言之:该书篇幅如何,“须有一番统计”,然后再定。但是,他紧跟着特别询问,《左疏》在鲁襄公五年戛然而止,刘师培是否为它补续完成③,如没有完成,他认为可以请当代经学家代为添补,以成完璧。是则,南桂馨不仅是在了解该书的基本情况,而且已经在为出版该书开始策划了。这使我们不能不推他为出版《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的最早总策划人。
不过,南桂馨此信的写作时间,只署有“十四”这个具体日期,年月均不详。南桂馨为编纂刘师培《遗书》,邀请钱玄同作编辑、郑裕孚作校对。为此,钱玄同曾69次致信郑裕孚,其中第4信、第28信都曾谈到对《攘书》可否印行的争议问题。第4信作于1934年4月18日,也就是刘师培《遗书》刚刚启动不久,因此不会这么快就谈及《左疏》出版之事。但是,到1935年岁末时,“既得之稿已印成十之六七”④。钱玄同第28信即作于1935年9月10日,谈论《攘书》可否印行事也比第4信深入具体、鲜明有力,而从次年2月16日的第32信,即开始了对《攘书》的校勘付印工作。⑤因此,笔者认为,上述南桂馨致刘师颖信,应该写于1935年秋冬之际。也就说,从这一时间开始,南桂馨启动了对《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的出版规划工作。
刘师颖接南桂馨来信后,将其意转至刘葆儒,叔侄间开始为出版《左疏》一事通信,但目前尚未发现这两封最早的通信。1935年农历“除夕”,亦即1936年1月23日⑥,刘师颖致信刘葆儒:“次羽吾侄如晤:一月廿三日来信收悉,关于刊行《左疏》稿事,侄所拟办法甚是。惟叔尚略有意见如下:一、书版刊就印出,由叔经售,随时抽还南氏刻资,还清后即将版权收回,自属稳妥。惟此项书籍如欲大宗销行,尚须从事宣传。关于批发代售等事,手续亦甚繁重。叔事务趋忙,实难兼顾。今南氏既代刻书,如于刻就之后,将书版及印成之书并由出家收回,不再令其过问,似不甚好。叔意宜与南氏洽商,该书刻成后,由南氏自行酌印若干部,由其自售,该价作为归还南氏刻资。候此批书印就,而将书版交还吾家。其售书各事,由其自办。二、原稿存津,由南氏派人来津抄校,又恐南氏不肯照办,而此事在彼既属一番热心,似不宜令其感觉不便。叔意请南到津后,拟仍照三叔刻稿办法,送平交重威兄存入东交民巷中南银行库中,由南氏陆续看抄,俟前卷还来,再接次卷,似不至有意外危险。三、《左疏》稿拟俟见稿刻齐,再行办理,稿件可稍缓带来。以上各节,侄意如何?希见复。”
在这封信里,刘师颖结合刘葆儒的意见,就《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出版问题谈了三点看法。第一,版权问题。南桂馨出资刊书,同时享有一定的版权。刘师颖主张该书刻成后由南氏自行酌印若干部,由其自售,售价即作为刻资归还南氏,待还清后将版权完全收回刘家。第二,书稿交接问题。刘师颖意见是,仿照编纂刘师培《遗书》的办法,将书稿交给刘师培弟子、北平中南银行经理张重威保管,由南桂馨派人“抄一还一”,以免发生书稿丢失或损坏等意外事件。第三,目前还不能急于出版《左疏》稿,须等刘师培《遗书》(即信中所言“见稿”)刊行后,再来运作。显然,在前揭南桂馨来信基础上,刘家已经与以南桂馨为代表的出版方开始具体商讨“镇家之宝”的出版事宜了。
2月中旬,作为出版当事人之一的郑裕孚来到上海,并先后两次与刘葆儒联系。第一次在15日,因刘葆儒不在家,未能晤面,遂留下便信:“次羽仁兄如晤:走谒未晤,因接洽谈印书事,必须一见。请台驾于明晚八时后,在府稍候,弟当再来也。《左传》如在手边,检出明晚阅谈更好。”郑裕孚与刘葆儒16日谈话的具体细节,因资料缺乏,尚不明晰。笔者在“扬州书信”中发现夹有一张A4纸大小的便笺,上面写有几行钢笔字:“一,印书 部数多少不拘;二,影印铅印均可;三,铅印时墨迹稿须抄过,不能污损;四,墨迹稿及抄稿均须有人负责保存,印后归还,不得遗失;五,在京、平、沪印均可;六,印成后赠书□部;七,稿件由南先生付印或由他人刊印均可。”由下文所引刘葆儒去世前对此事的总结可知,这张便笺是刘葆儒事先写在纸上,用来与郑裕孚谈话的纲要,属于双方对各种事项的约定。从其所涵盖的各个方面看,双方存在着诸多有待协商解决的问题,例如是影印还是铅印,印书地点选在哪里,印书部数多少等等。从措辞看,刘葆儒显然是在迁就出版方的各种意见,并期望通过这次会谈能够达成一锤定音的最终结果。因此,双方在刘家已经让步的前提下,能否谈成出版事宜,只有看出版方的态度了。
2月17日,也就是刘、郑晤谈的第二天,刘葆儒即写信给刘师颖,告知其有关情况,可惜此信目前也尚未发现。刘师颖接信后,于20日发出复信:“《左疏》印行事,叔意最好用影印办法办理。但万一前途必欲排印,为早日流传计,将原稿带平排印,亦可照办(取借等手续,请在沪办妥)即希与郑君洽定。至版权一节,如对方完全系为流传学术而非图利,即照《左庵集》办法,以若干部由吾家赠送亲友可也。郑君此次南行,尚有若干日达躭阁(耽搁),此事能乘其在南方,得与之洽定否?并希见告。”在此信中,刘师颖根据事态的进展,提出了几点新的想法:一是《左疏》稿的印行,最好用影印的方法办理。二是如果南桂馨等出版方坚持用“铅印刻版”的排印方法,为了这部“镇家之宝”早日问世流传,也可以将书稿带到北平排印,但取借等手续必须在上海刘葆儒家里事先办好。这比上述“抄一还一”的做法当然简洁了许多。三是版权事情可以商量,如完全是为传播学术而非图利,即应按照出版方刊行刘师培《左庵集》的做法,在《左疏》稿正式出版后赠送刘家若干部,由他们转赠亲友。由于郑裕孚正在上海,因此刘师颖就请刘葆儒与郑裕孚当面商讨这些事情。
然而,就在刘师颖复信之前,郑裕孚已经离开上海到了南京,并在20日致信刘葆儒,对其接待表示感谢,然后话锋一转:“《左传注疏》手稿,鄙意可先由鸿宝斋印出一张(二开本),惠赐三五份,以便分送南公诸人商量一切,想尊意当以为然也。”信后还特意注明了他在南京的通讯地址。由此看来,郑裕孚在刘葆儒家里见到了他想“检出阅谈”的《左疏》手稿,但他只是南桂馨聘请来协助做事的,并不能做任何决定,于是他提出由刘家在上海鸿宝斋先行印出手稿中的一张,分送南桂馨等人审阅,然后再讨论出版事宜。这反映出,郑裕孚与刘葆儒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结果。
对于刘师颖2月20日来信,刘葆儒未及时回复,于是刘师颖又于当月28日再次致信刘葆儒,询问他对自己建议的态度:“关于南公拟刊行《左疏》稿一事,叔前函所述各节,未知侄意如何望便中见告。”可惜刘葆儒是否回信,意见如何尚未找到材料。
不久,刘师颖遇到一个新的情况,遂于3月12日致信刘葆儒:“日前在此晤见东方文化会桥川子雍先生,即数年前访问吾家之学者。谈及《左疏》稿印行问题,渠主张由文化机关影印若干部,以一大部分由承印机关经售,收回成本,一小部分作为刘氏家版,如印五百部,可以一百部为刘氏家版。据云,该会印行傅沅叔先生之《藏园丛书》,即系如此办理。谆劝吾家早日著(着)手并询:(一)原稿本有无孟瞻、伯山两公(即刘文淇、刘毓松父子——笔者)亲笔,抑系恭甫公(即刘寿曾——笔者)手录?(二)是否至襄公四年为止?(三)共有若干本若干页?用特函达,即希函复,以便转告。再,此稿并无副本,将来如在华北影印,原稿运送颇系问题。此层亦曾谈及,桥川之意,该稿本可由大使馆邮袋运送,并加保险,可免疏虞。此层当须加以考虑耳。”
桥川时雄(1894-1982),字子雍,号醉轩,日本福井人,汉学家。1918年来华,任《顺天时报》记者,1927年创办并主编《文学同盟》杂志。1928年起,任东方文化教育事业委员会委员及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总务委员署理等职。1946年回日本。信中所谈的“傅沅叔”,即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1872-1950),著有《藏园群书题记》、《藏园群书经眼录》、《双鉴楼善本书目》等著作多种。此信表明,日本学者早已注意到刘家这部三代所传的“镇家之宝”,因此在谈到书稿出版之事时,不但主动提出由他们影印发行,而且还特别强调了保证书稿绝对安全的措施,敦促刘家早做决定,交由他们办理。影印是刘师颖坚持采用的办法,而且他从此事一开始启动就极为重视书稿的安全问题,因此日本学者在这两个问题上都与他意见一致,无非是想先打消他的后顾之忧,以便诱使刘家尽快交出书稿,把出版权拿到手里。
对于刘师颖此信,刘葆儒在当月27日回信表示:“查《左疏》原稿悉为恭甫公手录,嗣有一部分为侄就原稿所誊。查隐、桓有墨迹稿、有誊清稿(不知何人手);庄、闵有誊清稿,无墨迹稿;僖有元年至廿二年墨迹稿,其誊清稿出三叔祖手,考大半(自元年至十六年,经为誊清全文,自十六年传,至廿二年,仅抄出引证书名)计自元年至卅三年,其中有自十六年传至廿二年一部分未抄全稿,不知何故;文、宣、成、襄皆有墨迹稿、有抄稿,文、宣中一小部分为三叔祖手抄,成、襄抄稿为侄手抄。稿本至襄五年‘可不谓忠乎’止。惟原稿墨迹颇有不易辨识处,誊抄者只有阙疑,且僖公中小处均有待整理。原稿共七本,誊清稿共十一本,页数则视本数之厚薄而异。前此,郑友渔君排印计划为就墨迹影印,一以免舛错,二以省校对之不便。但在华北影印原稿似太不便,且原稿亦待整理,可否婉商桥川先生暂从缓议。将来或于整理后,仍由吾家名义印行。不知长者意见如何。”此信大旨有四:一是答复桥川时雄询问的几个问题,并婉言拒绝了由日本方面影印出版《左疏》的计划。二是认为影印地点选在华北地区不妥。三是与刘师颖商量,是否将《左疏》整理后由其家自行印行。四是告知刘师颖,郑裕孚想就刘氏家藏《左疏》墨迹稿影印出版。这应该是郑裕孚与刘葆儒当面晤谈时表示的意见之一。
刘师颖接信后,于4月5日复信刘葆儒:“《左疏》稿以原稿照相石印,费用既省且免错字,自以改用影印为宜。此事承南公热心,允为财力及人力之帮助。现在如改为在沪影印,则仅须南公确认财力,办理自无甚困难。惟所虑者,南公不克见原稿,无从著(着)手做序跋耳。下星期此间放春假数日,叔拟赴平一行,与南、郑诸公面议此事,如南公同意在沪影印,将来拟由南公派代表赴沪,迳与书店订立影印合同,第一批新书由南公销售,收回成本,以后版权仍归吾家,不知侄章以为如何?”此信表明:一,刘葆儒与出版方的商讨工作已经更加深入,达成了“以原稿照相石印”的影印出版方式。刘师颖自然没有意见,因而他在表示同意的同时,顺便解释和强调了影印的两大好处,即节省成本和避免手民之误。但是,正如上文所示,刘葆儒在3月27日致刘师颖信中并没有谈及这些事情,因此这只能是刘葆儒在3月13日致刘师颖的信中提到的,可惜目前尚未见到该信,内中详情,特别是由谁提出了“以原稿照相石印”的办法等问题,只能付之待考。二,刘师颖提出,如果影印地点改在上海,则只需南桂馨提供财力支助即可,不必再由他提供人力帮助,由此可免去一层关系,待第一批书出版后由南桂馨销售,收回其成本,此后版权收归刘家。三,在上海影印也带来一个问题,即身处北平的南桂馨就不会看到《左疏》原稿,由此他也就不能为之写作序跋了。因此,刘师颖准备利用假期;亲赴北平,与南桂馨商讨这些事情。
4月14日,刘师颖从北平回来后,致信刘葆儒;告诉他此行的结果:“南、钱、郑诸公,此次在平,均经晤见……《左疏》稿事,南公说,前函所云‘长编’系因《书目答问补正》内有‘长编已具’一语⑦,并非欲请当世经学家代为足成;此稿现既无长编,渠对影印办法亦甚赞同,随后当再接洽办理等语。叔意拟俟三叔《遗书》刊行后,即与南公接洽进行,将来或由南派代表赴沪,迳与影印书店订立合同。至版权一层,上次谈时,南公并元要求版权之意,故此次亦未提及,将来嘱办时拟仍照上次所谈办法,在第一批书价内归还南公成本,版权仍属吾家。又,该稿如照影印办法,未知需时若干可以竣事,郑君托为打听,并祈探询见复为盼。”此信中,刘师颖除介绍晤谈中所了解到的刘师培《遗书》出版情况外,主要还是谈《左疏》印行事宜,其大旨有三:一是南桂馨更正了以前来信中的说法,表示《左疏》既然连长编都不具备,也就无意请当代经学家代为补成全书,直接将手稿影印即可,但眼下并不急于去做。至于何时再谈,南桂馨并未说明,刘师颖认为,可以等刘师培《遗书》刊行后再具体接洽此事。二是版权问题,因南桂馨此前并无要求版权之意,所以这次面谈根本没提此事,可能会按4月5日信中所说的办理。三是刘师颖在北平晤谈期间,郑裕孚向他了解影印书稿需要多少时间,于是刘师颖请刘葆儒去书店了解此事。这表明,出版方已有意将影印地点选在上海。
上述刘师颖4月5日、14日两信只标注有具体日期,年代不详,但在钱玄同与郑裕孚的通信中,第41信作于1936年4月17日,连同此前各信,并无谈及《左疏》之事;第42信写于4月30日,内中有答复郑裕孚问五条,其第2条云:“彼所云《左疏》拟用徐积余先生之主张,用原稿照相石印,此法最佳:易于成书,一也;用款经济,二也;无须校对,三也;不会错误,四也。鄙意可即用此办法,请以此意转陈佩兰先生为荷。”⑧通观刘、钱这四封信件可知:第一,刘师颖这两封信及此前各信写于1936年无疑。第二,其间大致情形可以推知如下:自郑裕孚、刘师颖在2月提出影印办法后,刘葆儒又在3月采纳了著名学者、藏书家徐乃昌(1862-1936,字积余)的建议,“用原稿照相石印”,随后在当月13日致信刘师颖。刘师颖在4月5日的回信中表示赞同,并在10日至13日到北平,与南桂馨、钱玄同、郑裕孚等晤谈《左疏》及刘师培《遗书》事。这期间,刘师颖曾为《左疏》事致信郑裕孚。4天后即17日郑裕孚连续向钱玄同发信三封,询问有关刘师培《遗书》的问题,顺便将刘师颖三信一并附寄,征求钱玄同对影印《左疏》的看法,于是就有了上述钱玄同的答复。显然,钱玄同是明确表示了自己的赞同态度,并列举了四条理由,请郑裕孚转达给南桂馨。由此可以推知,南桂馨等人虽早就口头答应采用影印办法,但内心还是犹豫不决,甚至不排除持有反对意见,所以才会在与刘师颖晤谈后,还要致信钱玄同,探寻和征求他的意见。南桂馨等人为什么会有如此矛盾的举动?是为学术计,还是其中有商业玄机?不得而知,但钱玄同既已明确极力赞同,向他征询意见的南桂馨等人又将如何呢?
关于影印出版的方法,与刘家有世交的国学大师柳诒徵亦持赞同态度。他在1936年9月8日答复刘葆儒来信时,顺便建议:“尊府所存《左传疏》,似亦无须另写清稿,最好以原本影印。经师手泽,三世清芬,使阅者如亲炙,似胜于雕版或排印也。”显然,这是柳诒徵得知《左疏》出版一事正在筹划后所提出的一己之见,其信尾落款为“廿五年九月八日”,从而再次证明,上述刘师颖各信全都写于1936年。与刘师颖、郑裕孚、钱玄同相比,柳诒徵特别强调,原本影印可以使读者亲眼看到三代经师手泽,“使阅者如亲炙”,从而在感性上激起人们对学术的崇敬与热爱之情。
1937年2月28日,郑裕孚在南京致信钱玄同,其中附有当月18日刘葆儒致郑裕孚信。钱玄同4月2日复信称:“似乎《左疏》之影印,大有开工之希望,想南公当亦欣然首肯也。” ⑨这说明,半年多来,双方仍在继续接洽出版《左疏》一事,并有了较大进展,南桂馨也已经同意了影印的办法。但是,其间是如何发展的,因资料匮乏,详细情形还不是很清楚,好在刘葆儒本人在去世前曾对此进行过总结回顾,使我们稍知其大概:
前此,宁武南佩兰桂馨先生以与先三叔有雅,故于刊印《左庵丛书》后,为先四叔容季公言,拟请当代经师补注,俾《左疏》可成完璧,至已成部分,或排印,或木刻,或石印,以广流传。后托郑友渔裕孚先生经纪其事。郑先生旋与葆儒数度商洽,为免舛错及省校对手续计,主张影印墨迹稿,不全部分则配以手抄稿。故除向百宋铸字印刷局(该局曾受葆儒之托,排印先祖《传雅堂集》)取得排印估价外,再度向鸿宝斋书局取得影印估价单及样张数份。当时,葆儒与郑先生约,影印部数不拘多少,墨迹稿须保持整洁。后经张重威先生与南先生接洽,允为刊行,板权仍属刘姓。当时南先生意至厚,且有钱、黎、郑诸先生相助为理,惜计划未及实现。⑩
首先说,南桂馨拟定出版《左疏》,是在编纂刘师培《遗书》过程中,并非是在其刊印之后,而且南桂馨了解《左疏》稿本情况后,很快放弃了起初“拟请当代经师补注,俾《左疏》可成完璧”的想法,此皆刘葆儒晚年之误忆。除此两点外,其所述内容不仅与上文相符,而且提供了新的信息,即刘葆儒在接到前述刘师颖4月14日信后,得知郑裕孚向他了解影印之事,于是不但向百宋铸字印刷局取得排印估价外,还向鸿宝斋书局取得了影印估价单及样张数份,随后寄给刘师颖,由刘师颖转寄给北京的张重威;经过张与南桂馨联系接洽,南桂馨同意刊行,并答应板权仍属刘家。(11)至此,出版方与刘家之间为出版《左疏》一事的往来商议阶段基本结束。钱玄同所说,“看此情形,似乎《左疏》之影印,大有开工之希望”,当即指这种情况。时在1937年2~3月。
可惜的是,尽管南桂馨与刘家进行了精心筹划,尽管有钱玄同、黎锦熙、郑裕孚等人相为助理,但这部凝聚了刘氏祖孙三代经学家心血结晶的大著,并没有像紧接其后的刘家第四代学人刘师培的《刘申叔先生遗书》那样顺利出版,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遗憾。对此,刘葆儒在上述总结回顾后更是极为痛心地写道:
私意《左疏》稿性属文物,总期其能流布,俾治斯学者大多数人可收参考之益。由当代经师续成未竟之业,自属上策,而原《疏》欲期其不致澌灭,影印不失为一办法。南氏计划如能实现于今日,则感且不朽者,当不限刘氏子孙也!(12)
显然,刘葆儒晚年对《左疏》未能顺利出版是再三致意的,其字里行间,对南桂馨充满感激之情,而其内心痛苦也溢于言表。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大有开工之希望”的事情最终化为泡影?难道真的是要等到已近尾声的刘师培《遗书》彻底编纂完成后再来着手此事,还是有别的原因起到了牵制作用?对此,刘葆儒没有透露任何只言片语,以致迄今还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只能期待于日后能有新资料的发现。不过,日本帝国主义在钱玄同欣喜“大有开工之希望”的三个月后,即发动了欲图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使国内文化出版事业倍受摧残,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13)
三 百年巨著终面世
历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艰难岁月,虽然祖孙三代心血凝聚而成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没有刊行,但书稿也没有散失,仍被刘葆儒精心保存在上海家中。刘葆儒还在工作之余,补抄了部分稿件,准备日后送到图书馆收藏,不料竟于1952年秋遇车祸去世,此事遂被耽搁。两年后,刘葆儒之子、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刘经传被选送到苏联莫斯科大学深造,欲将其母接到北京居住。这使刘师培的外甥梅鹤孙(14)深为《左疏》稿本担忧,特地赶到刘家,建议刘母将其送交上海市文献图书馆保存,以防散佚。刘母深明大义,极为赞同。于是梅鹤孙与徐森玉、尹炎武联系,又与馆长顾廷龙约定好日期。献书当天,刘葆儒胞弟刘崇儒在梅鹤孙、徐森玉和尹炎武陪同下,捐献《左疏》原稿7册、清稿7册,顾廷龙馆长亲自接收,并出具了收据。这便是刘家第一次向政府献书(15),这部家传巨著终于得到了安全之所。
不久,中国科学院得悉此事,将书稿借调到北京。科学院领导认为这部书稿虽未最终完成,但价值很高,有必要整理印行,遂将书稿交与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资料室,组织人员,经过两三年整理,于1959年5月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从清道光八年刘文淇与友人约定承担《左传旧注疏证》时起,到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一百多年间,正是外族入侵、战争频仍、灾害不断的动荡时期,这部书稿能够保存下来,刘家几代人付出了极大心血,而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即由政府组织人力,将它正式出版,这既是对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极大尊重和热爱,是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一件盛事。
46年后,《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又迎来了另一件可喜可庆之事:2005年5月,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氏乡后学吴静安所著《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一书,完成了刘氏三代百年未竟的事业。吴静安1915年生于江苏仪征,其伯父吴遐白、父亲吴粹一都曾受学于刘氏门下,并亲承刘师苍和刘师培兄弟之教。吴静安承袭了他们的衣钵,幼年即随伯父吴遐白攻读《左传》。自1936年以来,他先后完成《广春秋世族谱》、《春秋地名今释》、《三传徵礼》、《春秋地名解诂补》、《世本集解》、《纪年集解》等著作,为《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的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几十年间,吴静安潜心研习《左传》,遍访各种版本,广泛阅览经史百家之书,辑佚清以前诸家旧注50余家,疏证80余家,并随时加以个人研究心得。其书起于鲁襄公六年,结束于《左传》截止的鲁哀公二十七年,将刘氏开始的疏证工作补续完整。至此,吴氏《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与刘氏《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连为一体,刘葆儒、南桂馨等人在几十年前既已慨叹为未竟事业的“左氏学”,终于得成完璧!
注释:
①这些信函全是刘氏族人与外界的往来通信,但远非当时所有往来信件的全部。内容除围绕《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者外,还有围绕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和其他整个刘氏家族论著的。
②本文所引书信,皆系扬州收藏家巫庆先生所藏“扬州书信”,见《史学月刊》2010年第4期所载《新见民国时期扬州“青溪旧屋”刘氏往来书信》。
③刘师培确实已经开始了补续家传《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的工作,但远未完成,其所成稿即收录在《刘申叔先生遗书》中的三页《春秋古经旧注疏证零稿》。
④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总目说明》,《刘申叔先生遗书》卷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另见《钱玄同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⑤钱玄同与郑裕孚通信,全部收在《钱玄同文集》第6卷。
⑥“扬州书信”大多没有署明写信的具体年代,此处“1936年”是笔者据钱玄同信推导出来的,详见下文。
⑦原信“一语”下有刘师颖自注:“系根据《儒林传》稿,故以相询。”意即南桂馨说他此前信中所言“长编”事乃是据《清史稿·儒林传》所记,但不知其记载是否属实,因此向刘家询问。另外,在“《书目答问补正》”下也有刘师颖自注:“柳诒徵撰。”但不知此注是刘师颖转述南桂馨之意,还是他自己所加,不过,《书目答问补正》乃是范希曾所著,柳诒徵只是在范死后为其出资刊印并作序而已,并非该书作者。
⑧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55页。这69封信中,整理者很少使用书名号,文中《左疏》之书名号为笔者自加。
⑨此为钱玄同致郑裕孚第63信,见《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91页。
⑩(12)刘葆儒关于《左疏》出版一事的这份总结,原件系用铅笔在宣纸上写成,至今仍保存在扬州收藏家巫庆先生家中。可惜其相关内容虽完整无缺,但前后都没有对这件材料的任何说明,也没有写作时间。其中谈到日本人桥川时雄欲影印《左疏》之事,基本与前文吻合,但时间误忆为“抗战中”,其实此事发生于1936年3月。不过这个误忆却告诉我们,刘葆儒这份总结是写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故而内中称卒于1944年的刘师颖为“先四叔”,而刘葆儒本人卒于1952年秋,因此这份总结是写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至1952年秋之间。
(11)“扬州书信”中保存有一封刘师颖给刘葆儒的来信,可与此互相佐证,但只有第1页,内容如下:“前日接张重威兄来函,谓已带平之三叔遗稿,南氏已刊成十分之八,家中之《左疏》稿并由重威与南公洽商,允为出资刊行,版权仍归刘氏等语。兹将重威原函附希阅终。叔意南氏之意甚厚,且有钱、黎、郑诸氏帮忙,机会殊不可失。现在所应考虑者,即为抄录副本问题。如照重威与南氏所商办法,即将原稿带平,由南氏托人抄校,自属最(下缺)。”由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总目说明》及此信中刘师培遗稿“已刊成十分之八”一句可知,此信写于1937年5月前。但是,刘师颖却说,张重威与南桂馨所商办法并非是就刘家所藏原稿影印,而是找人抄校刊行。此信是当事人述当时事,且有张重威原函作证,内容之真实性自属无疑,但此信后半部分尚未找到,不知下面是否还有其他转折之语,故仅列此备考,而未在正文中予以考察。
(13)南桂馨在1962年说:“日伪统治时,(刘师颖)在津曾与余约,于光复后,将其家三世所撰《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原稿影印行世。其密赴重庆时,临行叮嘱再三,不幸道出西安,遽然作古。余亦病发,未能如愿。”这是目前所见有关《左疏》未能刊行之原因的唯一说明材料,但也只是78岁老人的晚年回忆,6年后南即去世。如果此说属实,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就是《左疏》未能刊行的最直接的首要原因。南语见梅鹤孙著《青溪旧屋仪征刘氏五世小记》之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4)梅鹤孙(1894-1964)母亲刘师铄是刘师培胞姐。梅鹤孙从1958年动笔,至1962年,历时5载,撰成《青溪旧屋仪征刘氏五世小记》,真实记述了刘氏五代即刘锡瑜、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至刘师培的鲜为人知的史料,其中对刘师培记述尤为详尽。梅鹤孙去世后,其子梅英超对该书进行校勘整理,并增加刘师培集外遗文,于2004年7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5)1982年,刘家第二次向政府献书,由刘葆儒之子刘经传与堂兄刘模女婿巫庆等人经手。刘模系刘葆儒胞弟刘崇儒之子。据巫庆先生所藏政府出具的献书证明,这次捐献,计有图书43种、尺牍35册、字画87种、拓片57种,另有尺牍手稿56种。其中包括刘文淇稿本《春秋左氏传旧疏考证》及其《青溪旧屋尺牍》(计2409页)、刘毓崧《通义堂尺牍》(计2153页)、宋刊本《省元林公集资治通鉴详节》,以及清嘉庆、道光年间著名学者丁晏、魏源等手迹,皆有极高的史料及文物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