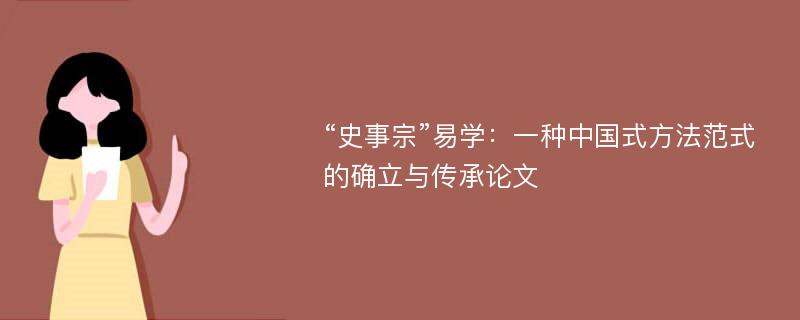
“史事宗”易学:一种中国式方法范式的确立与传承
曾华东 杨效雷
顾炎武《日知录》勾勒了《易》学发展简史,不但泛滥易学的“玄”“理”二家,还清楚看到了“史事宗”这家存在的可能性,并深度揭示了史事“参证”方法在杨万里等《易传》中得到确立,认为“史事宗”《易》学以用《易》为学术趣旨,是方法论与目的论的高度统一。顾炎武作为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不但以史证《易》,还由此在其《音论》等著作中推出“广证”“博证”之法,终至形成乾嘉学派赖以存在的“疏”“证”相结合的范式。乾嘉学派虽以“复古”“回到汉学”为旗帜,但纯粹“注疏”的方法范式毕竟已成过时的笺注学。后继的乾嘉学者们分别以吴派、皖派大成之作《周易述》《孟子字义疏证》等为代表,蔚成了以考据、考证为特征的乾嘉学派,标示了中国哲学方法范式薪火相传的学术气派。
[关键词] 顾炎武;史事宗;乾嘉学派
两宋时期,政治上先后经历了“庆历新政”和“安石变法”,科技上“四大发明”有“三大发明”发生在宋代。思想、学术上理学昌明,新学、程朱理学、陆学蔚为主流。南宋中兴,首先是文化中兴,大理学家辈出:朱熹、胡宏、杨万里、陆九渊、杨简、叶适、陈傅良等,并产生了易学义理派的第三个学派——由李光、杨万里创立的“史事宗”学派。这个易学义理派的形成,标示了一种中国式“参证”方法范式的最终确立。这位传薪播火者,就是乾嘉学派的领袖人物顾炎武。
研究顾炎武易学早有其人,都为炎武易学做出了有益的学术阐发。本文认为,仍有必要探讨两个问题:第一,顾炎武虽没有自己的易学专著,但他的《日知录》卷一系统阐述了其易学观点,给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易》学发展的简史;第二,顾炎武较早看出《易》学分宗分派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甚至为“史事宗”易学这种证、阐与用《易》相结合的范式提出了理论根据。
一、炎武易学与诚斋《易》
《日知录》卷一写了一部易学发展的简史。在这部“易学发展简史”的最后,炎武希冀告诉人们,《易》的源头和归宿均在用《易》或《易》用,当然不是占卜之用,而是教化、人伦之用:“《易》以前民用也,非以为人前知也。求前知,非圣人之道也。是以《少仪》之训曰:‘毋测未至’。”[1](P56)
顺着《日知录》卷一的大致目次可以看到,炎武首先关注朱子的《周易本义》,其次关注程子易学和王弼易学,但更看重诚斋易学。顾炎武在《日知录·朱子周易本义》中云:
自汉以来,为费直、郑玄、王弼所乱,取孔子之言逐条附于卦爻之下。程正叔《传》因之。及朱元晦《本义》,始依古文。……其“彖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无,复依程《传》添入。后来士子厌程《传》之多,弃去不读,专用《本义》。[1](P4)
在“秦以焚书而《五经》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经》亡”[1](P9)的讨论中,当谈到“《易》《春秋》尤为缪戾”[1](P9)时,顾炎武归结到“复程、朱之书以存《易》,备《三传》、啖、赵诸家之说以存《春秋》,必有待于后之兴文教者”[1](P9)。炎武虽未明确说谁是“后之兴文教者”,但宋代杨万里曾云:
《易》者,箫何之律令,《春秋》者,汉武之决事也。《易》戒其所当然,《春秋》断其所以然。圣人之戒不可违,圣人之断不可犯,故六经唯《易》与《春秋》相表里。[2](第一一六一册,P214)
大学生在返乡就业创业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很多,除其自身就业创业能力不足外,更主要的是社会对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的支持力度不够,特别是在政策、资金、教育等方面的支持还存在很多不足。
顾炎武虽言“复程、朱之书以存《易》”,但随后的“备《三传》、啖、赵诸家之说以存《春秋》”,说明他肯定“参证史事”者既在做“存《春秋》”的工作,又在做存《周易》的工作。
水浸提液是板栗花综合利用的主要中间产品,饮料和酒是大众化的消费品,应当持续开展板栗花饮料和板栗花酒的开发研究,针对不同的消费人群(如青年人、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开发不同的配方产品。还可以将板栗花直接预处理、烘制等,或将板栗花定量加入到茶叶中,开发出多样性的板栗花茶等。
顾炎武等乾嘉学派都是排斥图书学的。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一《易,逆数也》题下说道:
若如邵子之说,则是羲、文之《易》已判而为二,而又以《震》《离》《兑》《乾》为数已生之卦,《巽》《坎》《艮》《坤》为推未生之卦。殆不免强孔子之书以就己之说矣。[1](P46)
朱熹是推本图书学的,据顾炎武以上所论,在某些场合顾炎武是疏离朱子的,但对诚斋学的疏离几无。清代全祖望(1705—1755)似遥相呼应,有如下千年一叹:
易至南宋,康节之学盛行,鲜有不眩惑其说。其卓然不惑者,则诚斋之《易传》乎!其于图书九、十之妄,方位南、北之讹,未尝有一语及者。……中以史事证经学,尤为洞邃。[3](卷四十四,P1433)
顾炎武在其《卦爻外无别象》的讨论中,小结如下:
王弼之注虽涉于玄虚,然已一扫《易》学之榛芜,而开之大路矣。不有程子,大义何由而明乎?[1](P10)
顾炎武看到了玄、理二家的区别,更看到了诚斋易学的魅力和殊胜之处。诚斋易学的魅力和殊胜之处,说到底,就是基于大量史事“参证”而确立了该方法论范式(显别于其他各家各色参证),并由此建立起了它的易学新形态和新宗派——“史事宗”易学。顾炎武把这种在南宋,甚至在元代都看来很“新奇”①,但也遭到某些人诟议的阐《易》之法,运用到自己对《周易》义理的理解和阐发当中。接下来,《日知录》连续对《周易》的《师出以律》《既雨既处》《自邑告命》三个议题,均“以史证经”。在《师出以律》条下,炎武以“战长勺以诈而败齐,泓以不禽二毛而败于楚”阐发其“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才是“师出以律”的正判。[1](P15)在《既雨既处》条下,用了隋文帝与独孤后、高宗与武后的故事,来说明“妇制夫,其畜而不和,犹可言也。三之反目……既和而惟其所为,不可言也”[1](P16)的经义。在《自邑告命》条下,用了周桓王中祝聃之矢,唐昭宗用师而犯歧之兵的故事“以史证经”,来说明“保泰者,须豫为之计”[1](P17)。
顾炎武在不到1.5万字篇幅的《日知录》卷一中,直接援引《诚斋易传》的至少有以下几处:
杨氏(万里)曰:“初九动之始,六二动之继,是故初耕之,二获之,初谶之,二畲之。”[1](P21)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安定胡氏改“陆”为“逵”,朱子从之,谓合韵,非也。《诗》“仪”字凡十见,皆音牛何反,不得与“逵”为叶,而云路亦非可翔之地,仍当作“陆”为是。渐至于陵而止矣,不可以更进,故反而之陆。……此所以居九五之上,而与九三同为陆象也。朱子发曰:“上所往进也,所反亦进也。渐至九五极矣,是以上反而之三。”杨廷秀曰:“九三,下卦之极;上九,上卦之极,故皆曰陆。自木自陵,而复至于陆,以退为进也。巽为进退,其说并得之。”[1](P33)
在《周易·损上九》的解读中,顾炎武更是明确了他的《易》学“厚民”“正民”之旨:
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岂必自损以益人哉。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所谓弗损益之者也。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诗》曰:奏格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铁钺,所谓弗损益之者也。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其道在是矣。[1](P24-25)
古初以迄于今,万事之变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乱。圣人有忧焉,于是幽观其通,而逆绸其图。[4](P1)
此圣人赞上九不损之损之盛徳也。上九居损之终,位艮之极。居损之终,则必变之以不损。位艮之极,则必止之以不损。当节损之世,下皆损己以益其上,上又能不损其下以益其下。宜其无咎,宜其正吉,宜其利有攸往,宜其得臣无家,无往而不得志也,故曰大得志也。大禹菲食,而天下无饥民。文王卑服,而天下无冻老。汉文集书囊、罢露台,而天下有烟火万里之富實。皆损之上九也。得臣,谓得天下臣民之心。无家,谓无自私其家之益。[4](P239)
4.合适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的每日平均需要量为150g/d,提供的能量应占总能量的55%~65%,同时应避免摄入过多的精制糖,并且要注意粗细搭配。
大庆炼化公司明确地提出了“四责”管理理念,创新了企业的管理方式,促进了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推动了企业更高、更快的发展。
下面,我们再看看诚斋易学观与炎武易学观的联系。诚斋说:
顾炎武在谈到“厚民之生,正民之德”时,典型地发挥了《诚斋易传·损上九》中的“大禹菲食,而天下无饥民。文王卑服,而天下无冻老。汉文集书囊、罢露台,而天下有烟火万里之富实。皆损之上九也”[4](P239)的史事“参证”。与“天下无饥民……天下无冻老……天下有烟火万里之富实”相对应的,是顾炎武的“谷不可胜食也……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不可胜用也”,进而得出“厚民之生,正民之德”等《易》学观点。而《周易本义》《周易注疏》《周易程氏传》对此几无涉及。《诚斋易传·损上九》曰:
炎武说: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之乱。盛治之极,而乱萌焉,此一阴遇五阳之卦也。孔子之门四科十哲,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于是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盛矣,则《老》《庄》之书即出于其时。[1](P26)
此条,炎武与万里的阐《易》几乎亦步亦趋。在《日知录·包无鱼》条下,炎武说:
国犹水也,民犹鱼也。幽王之诗曰:“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秦始皇八年,河鱼大上。《五行志》以为鱼阴类,民之象也;逆流而上,言民不从君为逆行也。自人君有求,多于物之心,于是鱼乱于下,鸟乱于上,而人情之所向必有起而收之者矣。[1](P27)
万里说:“九二,君民之相遇,得其时义者也。……初六阴而在下,民之象也。鱼亦阴类,古者以鱼比民。”[4](P256-257)
显见炎武在《日知录·包无鱼》条下的“鱼阴类,民之象”。鱼为民之说来自万里《诚斋易传》,而《周易本义·姤九二》《周易程氏传·姤九二》《周易注疏·姤九二》均未见此说,只有孔疏《周易注疏·姤九四》有“《象》曰远民者,阴为阳之民,为二所据,故曰远民也”[5](P246),《周易程氏传·姤九四》有“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6](P254),但二家均未涉及“鱼”为“民”之说。
无独有偶,“史事宗”另一家——李光在其《读易详说·姤九二》中亦训“鱼”为“民”:“二远君而近民,五阳在上,一阴在下,故初有民之象。”[2](第十册,P391)由此不难窥见,“史事宗”二家有共同的学术趣旨。
顾炎武借说《易》之机,责难晚明心学之流弊,他认为士大夫“存心”,当存于“当用之地”,所以说:
心有所主,非虚空以治之也。至于斋心服形之老、庄,一变而为坐脱立忘之禅学,乃始瞑目静坐,日夜仇视其心而禁治之……夫心之说有二,古人之所谓存心者,存此心于当用之地也;后世之所谓存心者,摄此心于空寂之境也……而士大夫溺于其言,亦将遗落世事,以独求其所谓心……得乎?此皆足以发明“厉,熏心”之义,乃周公已先系之于《易》矣。[1](P31-32)
在《日知录》卷一的最后,顾炎武请出孔圣。在“孔子论《易》”条下,炎武归本周孔,认为孔子论《易》不但在于用《易》,还在于其用《易》之道有二:一,“庸言、庸行之间”“出入以度”“寡过反身”;二,“体之于身、施之于政”“与民同患”。总之就是人伦日用,用《易》在民,而不是修道、练身,存己为本。[1](P50-51)
杨万里通过他的《诚斋易传》,终于把“以史证经”的参证方法确立下来,其用《易》主旨及其价值和方法论范式也终于引起儒林的重视并得到传承。清人乾嘉学派大家钱大昕在其《跋诚斋先生易传》时谈到:“其说长于以史证经,谈古今治乱安危、贤奸消长之故,反复寓意,有概乎言之。”[7](卷二十七,P434-435)
二、参证与疏证
“史事宗”以其史事“参证”或曰以史证《易》方法见著,并因此而在《易》学领域分宗立派。早有学者称:儒理宗受玄学宗影响,“史事宗”受儒理宗影响,所以这“影响”并不影响其分派立宗。而且,由今看来,“史事宗”遗至清代的影响应该不限于乾嘉学派。我们只要考察从“参证”到“疏证”的形成路径便可知晓。
史事参证这一方法在《易》学方面延伸到清代,甚至近代和民国。黄忠天写于1995年的博士论文《宋代史事易学研究》,详尽地揭示了民国各家从“古史辨”派顾颉刚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到闻一多的《周易义证类纂》直至胡朴安的《周易古史观》等,及至李镜池《周易探源》、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均受“史事宗”易学波及。吕绍刚导读胡朴安的《周易古史观》时说过两段话:
古代有以史证经者,如宋人杨万里的《诚斋易传》,李光的《读易详说》。近世以史证经者亦不乏人。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学者顾颉刚等人从史料考辨的立场着力研究《易》中之史,多少有些进展。至1941年,闻一多在昆明从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周易》,不主象数、不涉义理,计可补苴旧注者百数十事。[8](导读P1-2)
又说:
乍一听“头脑”的名称,我还以为是用“筋头巴脑”为主要食材做的炖菜,结果亲口品尝时才发现,“头脑”是一道没有半点筋头巴脑的滋补汤!——我犯了典型的“顾名思义”错误!太原古城拥有灿烂的饮食文化,而“头脑”便是古城久负盛名的一道独特美食。
撰写《周易义证类纂》,闻书钩稽九十条史料,分为经济、社会、心理三类详加辨析,纠正和补充旧注若干,于易学研究实有贡献,但仍是做零碎的史料工作,不以《周易》为史书……到1942年,胡朴安撰成并自行印制200本的《周易古史观》,才全面地,“无一字不解,无一句不说”地解读六十四卦,形成《周易》古史系统。从此,在《周易》卜筮说、《周易》哲理说之外,正式出现了《周易》古史说。[8](P2)
这里已明确告诉我们:把《周易》当历史的那些人,实际上是受到杨万里等人“史事宗”易学的启发。胡朴安在自序中同样谈道:
古来以史证《易》者,以朴安所知,除杨诚斋外,如清章世臣之《周易人事疏证》、查彬之《湘芗漫录》、易顺豫之《易释》,然皆不以《易》之本身即史也。[8](P9)
这也告诉我们,胡朴安是受了杨诚斋的影响,只是他感觉杨氏做得还不够,他要直接化易为史、认易为史。当然,胡朴安的《周易古史观》这部书做到了。
“史事宗”易学以“参证”方法而赖以存在,乾嘉学派则以“考据、考证”方法而赖以存在。前者对后者有无实质的影响?其实,前面花大篇幅讨论顾炎武的以史证《易》就是要说明这一点。顾炎武不仅在《易》学领域,还率先在其《音论》和其他著作中实践这套方法。延至乾嘉学派其他人物,如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惠栋的《周易述》,实际上都是在做“疏证”的考订工作。由此,我们窥见了一条由“史事宗”的“参证”到顾炎武的“旁证、博证”以及稍后的阎若璩等人的“疏证”,再后的惠栋、戴震的学术发展线索。
论到“疏”“证”结合,二者应该是先分后合的。然后,才是它们如何走到一起的。“疏”——条疏、疏通,汉代早已有之,并且早已定型,可视为常法。“证”法在汉代甚至更早亦早已有之,但并未定型,可视为非常法。如东晋干宝,甚至更早的缪和。廖名春在《帛书〈谬和〉译文》中指出:《谬和》以此法治《易》,开了以史证《易》先河。[12](P228)关于“疏”“证”,戴震也是先分开说的,所谓“复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更有趣的是,顾炎武门人潘耒亦将之分开来说:
《日知录》为(炎武)生平精力所集注,则又笔记备忘之类耳。……然则炎武,所以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者,何在?则在其能建设研究之方法而已。……一曰贵创,二曰博证,三曰致用。[9](P11-12)
其实,顾炎武作为乾嘉学派的领袖人物,“其能建设研究之方法”一说,可视为我们论题所议及的“一种中国式方法范式”的由来和出处。但其中的“博证”之法首先绝非来自所谓开“以史证经”先河的干宝、缪和之流,至少在顾炎武的论集中未见提及。与之可圈可点的,倒是其在自己的集子中大力提倡杨万里证经之法和《易》用之道,如前所述。
潘耒在《初刻日知录序》中,也是把“疏”“证”先分开来说,所谓“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这里,实际还有一层意思,梁启超说炎武所谓“旁证”“博证”,其实就是“疏证”之法耳。
2010~2015年山东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量不断增加,增长率为8.26%,其中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增幅分别为 7.95%和78.77%。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病床使用率均维持在50%上下,其中乡镇卫生院的使用率均高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但乡镇卫生院的最高使用率在56.92%,社区最高为50.54%。截止2015年底,共有116199张床位,从经济类型来看,床位主要集中在公立医院,公立医院床位占比为96.94%,非公立医院占比为3.06%;从主办单位来看,政府办医院占比为92.18%,社会办医院占比为5.56%,个人办医院占比为2.26%。(见表5)
(炎武)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其自述治音韵之学也,曰:“……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自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音论》)此所用者,皆接近世科学的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在当时则固炎武所自创也。[9](P12)
同样,在这段话中,梁启超说的“固炎武所自创”的“本证、旁证”之法,后来衍成乾嘉学派的主要之法、基本之法,故梁公有“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的话,但梁任公这“皆接近世科学的研究法”却是虚室生白。并且,光一个“固炎武所自创”是说不过去的。杨万里等的“以史证经”说是来自干宝、缪和之辈,炎武所“创”亦必有所出。炎武的“本证、旁证”之法,梁启超说是“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自他书也”。这里,实际上说的是“以经证经”,《日知录》已有端倪,而由“以史证《易》”衍生出来的“以经证经”及其证法、证用之道,梁任公自然是没有看到,也就无法分说了。
对乾嘉学派的成因,名家、大家扎堆其中,成绩斐然又众说纷纭。敖光旭认为,“堆马铃薯式”的归纳讨论是有问题的,而“夷夏鼎革”则是乾嘉学的重要成因,恰恰“史事宗”易学的证用、证道、证法之影响再次被全然排除在外。黄克武将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分为六类:(1)考证学源于明末前后七子的复古以及杨慎、陈第、方以智等个人的经历与博学的雅好;(2)考证学受到耶稣会士所传西学的影响;(3)由于清廷的高压统治;(4)考证学与社会经济变化有关;(5)考证学源于思想性的因素或儒学内部的发展,例如认为考证的兴起涉及于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之反动;(6)认为考证学的出现是由于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交互影响,并强调上述第四项社会经济变化的重要性。[10]
综上所述,有几个问题有讨论的必要。第一,黄克武全没有提到乾嘉学派领袖顾炎武、阎若璩等,可谓至失。恰恰明末前后七子除王廷相是哲学家外,其他都属于文学流派,但王廷相除“气一元论”之外,方法论上实无所创。第二,政治上的“文字狱高压说”颇为盛行,但“文字狱”并没有发生在顾炎武时代,而且该学派门类虽林林总总,但它们共同的赖以存在的方法论范式却鲜见提及。第三,经济上的原因即使靠谱,也是要找到方法论范式,学派方可流行。所谓“学派方可流行”,是指大家遵循一定的范式,因而才有大致相同的学术趣旨。何况,乾嘉学派赖以存在的方法论范式就是“疏证”等。第四,“疏证”之法来自哪里?“史事宗”易学虽然研究者也众多,但实际上处于被边缘化状态。不是顾炎武倡之,谁能想到二家的学术关联?②
《周易本义·损上九》《周易注疏·损上九》《周易程氏传·损上九》均无相关内容,即除诚斋外,各家均没涉及“厚民之生,正民之德”的话题。炎武看到了参证方法在诚斋易学中得到确立,并且,此种易学范式已成为治《易》常态。他认为:治《易》以用《易》为旨,而不是“玄”“无”如王弼学,“天理论”如程子《易》。诚斋治《易》与用《易》的结合,正是炎武信奉的易学趣旨。
其实,上述六个原因,梁启超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著中亦大致谈到,尤其第五所说“考证学源于思想性的因素或儒学内部的发展”是较为靠谱的说法,但他也没涉及乾嘉学派赖以存在的方法论范式——“疏证”,而且,所谓“考证的兴起涉及于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之反动”,有人说这是在强调二者的疏离,甚至断裂,与梁启超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的“清学的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9](P7)相同。弄清乾嘉学派赖以存在的方法论范式出自哪里,应是重中之重。
再看看稍后的乾嘉学另一开山的学术表现。阎若璩(1638—1704)干脆把自己的著作叫《尚书古文疏证》,甚至后来乾嘉学的集大成者戴震(1724—1777)著述《孟子字义疏证》,都绝非偶然。戴震对“疏证”还进一步解释说:
温简也很久没有见过夏小春了,她想她和顾青应该已经顺风顺水地在一起了吧,她是那个能让顾青不辛苦的人,而她舍不得让顾青辛苦所以才让他走。这应该是真的爱情吧,所以她才会如此地疼痛,如此地不舍。
所谓“疏证”,戴震说是“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还要“比类合义,灿然端委毕着……经之大训萃焉”[11](P61)。这实际是把乾嘉之法,兜底归纳展示给我们了。所谓“兜底归纳展示”,是说戴震关于“疏证”的这段说明,实际上也讲清了“旁证”“博证”之法及其功用。戴震作为四库馆臣之一,曾受器重而追随纪晓岚左右。四库馆臣关于《易》学“二派六宗”的“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的话,戴震应该是直接在场、耳有所闻的。何况戴震的直接老师江永(1681—1762)曾受业顾炎武,因此,可以说戴震关于“疏证”的那些解释,正好是顾炎武的“旁证”“博证”的另一种说法,或延展的说法而已。
至于什么是“旁证、博证”,二家学术如何发生联系,请看梁任公是怎么说的:
此《日知录》则其稽古有得,随手札记,久而类成此书者。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1](P2)
梁启超在谈到炎武“博证”之法时,还专门说道:
目的蛋白Flagellin-3M2e理论相对分子质量大小为67 000。如图2所示,与未诱导菌体相比,在相对分子质量为70 000处诱导菌体都出现了浓厚的条带,与预测相符,初步表明诱导菌体表达了融合蛋白,而且随着诱导时间的增加,目的蛋白量也随之增加,但诱导6 h后蛋白量无明显改变,因此以诱导6 h作为最佳诱导时间。取诱导后菌体超声破碎离心,并取上清过镍柱纯化,浓缩后测得目的蛋白浓度为1.13 mg/mL。Western印迹法鉴定,在相对分子质量为70 000处出现了单一的特异性条带,因此纯化的蛋白即为设计的融合蛋白(Flagellin-3M2e)。
尤其顾炎武本人,亦是将“疏”“证”先分开来看的。首先,顾炎武有诗《述古》云:“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赅通,百家亦兼取。”[13](卷四,P384)这诗分明在赞赏汉代经学大成者郑玄及其注疏之法了。但是,炎武对郑玄的态度及其作法又是矛盾的,比如,他在自己的《日知录》卷一中又说道:(《周易》)“自汉以来,为费直、郑玄、王弼所乱,取孔子之言逐条附于卦爻之下。”[1](P4)这就不难看出,炎武等复古就绝非去完全重走古文经学的老路,而是坚定了炎武及乾嘉学要兼取“证”阐和“疏”通的学术新路。尤其“博证”等,难怪梁启超要说炎武所“自创”证法了。但就“证”法而言,除了前述的在《日知录》卷一中顾炎武赞赏杨万里以史证易,并多处援引杨氏的证案、证法之外,在对《日知录》的提要中,四库馆臣还说道:
⑥杜安世《卜算子》(深院花铺地):双调46字,上阕4句23字3仄韵,下阕4句23字3仄韵。句式:55733。55733。
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策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杨慎、焦豌诸人偶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2](卷一百十九,P222)
这里,“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与《四库总目》经部易类小序中“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的说法何其相似。“参以证佐”与“参证史事”何其相类。《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一文中谈到,顾炎武的考据方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点:一,考辨文字音韵以通经学;二,归纳大量例证;三,验诸实证。[14]这里,“考辨……以通”可理解为“考辨……以疏通”。“验诸实证”表述为“验诸参证”似更恰当。顾炎武开创的乾嘉考据方法,归纳起来还是他的门人潘耒在《初刻日知录序》中说的“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得之。
三、程颐与杨万里的史证
顾炎武是说过“昔日说《易》者,无虑数千百家……然未见有过于《程传》者”[13](卷三,P384),但不能仅凭这一句话,我们就认定他只认《程传》这一家的阐《易》之法。
程颐阐《易》始以儒理,终以儒理,亦有史证之法,但我们是否可以说,既然顾炎武如此推崇程子《易》,顾炎武“博证”之法就是取自程子证《易》之法呢?显然不能,至少这方面不见顾炎武提及。而且,我们只要看看程、杨二家证法、证道的分殊便知。另,程子说《易》之关注点不在“以史证经”,更未想将此法确立、沉淀而彰显之。前虽有所述,不妨再拿出几条来分析:
高血压自我管理小组的建立和发展,作为提高群众保健意识及全民身体素质的一项治本工程,已列入政府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随着其内涵和内容的不断延伸,如何建立健全“医患合作、患者自助、自我管理”群防群控慢性病的社区居民健康自我管理模式已成关注重点。由于自我管理小组投入小、效果突出,因此,随着自我管理队伍的逐步扩大及覆盖面的不断延伸,将使包括高血压在内的所有慢性病防控工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落地,对辖区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姤·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程颐释曰:
进度管理在项目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进度优化是进度控制的关键。BIM技术可实现进度计划与工程模型的动态绑定,最终可通过横道图、网络图及三维动画等多种形式直观表达进度计划和施工过程,为工程项目的施工方、监理方与业主等不同参与方直观了解工程项目建设进度情况提供便捷的媒介,实现信息模型和实际工作的“数字孪生”。
自古人君至诚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贤,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于梦寐,文王遇于渔钓,皆由是道也。[6](P255)
这里,程颐只用了史证来说明君求贤的道理,而万里史证却更深入了一层。万里释曰:
此九五、九二之君臣刚遇,中正之盛也。九五以刚明之德,乃含其耀而不矜,以下逮九二中正之臣,如杞叶之髙而俯包瓜实之美。九二以刚正之德,亦奉君命而不舍,以上承九五中正之君,如命从天降,而决起盍归之志。君臣相遇之盛如此,一小人虽壮,何足虑也?尧下逮舜之侧微,以杞包瓜之象。舜遇尧为天人之合,有陨自天之象。何忧欢兜?何畏孔壬?固其理也。[4](P258-259)万里史证不但说了“君臣相遇”,还指出了“君臣相遇之盛”有去小人之威势。程子证《易》,言尧、舜处甚多,此处却未逮。
《乾·文言》:“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隠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万里证阐曰:
此一章亦再释爻辞。蹨于身为德,形于事为行。龙德,圣人之事,非贤人事也。初九虽潜,而龙德具矣。潜者,位而已,所性不存焉者也,而横渠张子以颜子行而未成当此一爻,恐颜子不敢当也。程子谓未成者,未着也。以舜之侧微当之,得之矣。[4](P21)
此处,万里直言横渠、程子证《易》之失,一言“颜子行而未成”,一言颜子“未成者”,皆是“颜子不敢当也”,颜子“未着也”,并提出自己的证道“舜之侧微当之,得之矣”。
在《乾·文言》“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徳也”条下,程颐进行了折冲和转圜,故有:
从式(8)中可以看出,幅度计算无需用到除法YN/XN的结果,但一阶多项式的系数krai与krbi的取值与值YN/XN的区间有关,将xm近似处理后,YN/XN取值区间的判断通过移位和比较运算即可完成,有利于FPGA实现.
圣人在下,虽已显而未得位,则进德修业而已。学、聚、问、辨,进德也。宽居、仁行,修业也。君德已著,利见大人,而进以行之耳。进居其位者,舜、禹也。进行其道者,伊、傅也。[6](P11)
余始为《原善》之书三章,惧学者蔽以异趣也,复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而以三章者分为建首,次成上中下卷。比类合义,灿然端委毕着矣,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11](P61)
推进阳光体育是中小学体育改革的重要内容,“达标争优,增强体魄”是阳光体育的运动口号,为此,体育老师要紧跟体育改革的步伐,为学生设计出科学合理的运动负荷,既要保证学生体育训练的强度和密度,又要关注学生身体和心理的承受限度,运动负荷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在具体的体育教学中,老师要认真研究体育新课标的要求,结合不同年级学生的心理特点,制定相应的运动方案;并且要跟进学生的训练情况,切忌纸上谈兵,对学生的运动负荷要作详细的记录,发现不合理的地方及时修改完善,从中摸索和把握好不同年级男女学生的运动负荷规律。体育教学坚持运动负荷适中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再追求教学内容的多样化。
这里,“君德”可以是“进居其位”的舜、禹,也可以是“进行其道”的伊、傅。此处,将二个证道折中处理得好。
对程、杨二家,潘雨廷在《读易提要》中说得精辟:
夫杨氏精于史,此书之特点即每以史事证经。……观文王系辞而及高宗、箕子,孔子系辞而及汤、武,非明证乎?焦赣以刘邦、项羽当《随》之得失,郑玄以尧末年当《乾》上,可见汉时本有用此法解经者。晋干宝承用之,惜纯以周室事当之,反觉隘矣。《程传》《汉上易传》《读易详说》等用史事之处,亦屡见不鲜,然皆未若此书(《诚斋易传》)之以史事为主也。且此书取材精细,配合恰当,反复引证,曲然有致。[15](P213)
在谈到每自诩“以史证经”的李杞时,潘雨廷也对杨、李二家治《易》进行了比较分殊,他指出:
夫此书(李祀的《周易详解》)与《诚斋易传》同时同类,然内容殊不同。杨氏于《易》义全从《程传》,乃一心致力于史事之配合,故所取之史实极精细,而李氏于《易》义有所自见,其于史事得其概要而己。[15](P209)
杨万里代表“史事宗”易学以史证《易》,没有第二,只有第一。乾嘉学派的领袖人物顾炎武及其后继者,推崇杨万里及其证法、证道,正是要彰显和传承其道、其法。
四、结 语
值得说明的是,乾嘉学虽以“复古”为旗号,但却不是简单地回归“以严格笺注为形式”,以“明经学、表节操”为目的的汉学。这里,再回顾一下林忠军的一段话比较有益:
注不破传,疏不破注的局限,显得苍白无力。……这意味着以严格笺注为形式、以追求经文“本义”为目的的经学已没落,“史事宗”以史证的方式完成了义理之学理论体系的建构。[16](P262)
从汉学的疏不破注,到清乾嘉的疏以证之,不但发扬“史事宗”的以史证《易》,还以史证经,以经证经。中国自古就有疑经变古的传统,是“史事宗”易学的证《易》阐经在清学中得到弘扬,才使清代众家在“疏破注”“考证经”方面有了可循的章法,直到形成自己的朴学。“史事宗”使“参证史事”方法得到确立、沉淀而彰显,引起乾嘉学派的领袖人物顾炎武等高度重视,并被援引并揭示。经后继者的转圜、实践,四库馆臣的总结、推介,疏证方法在经学中得到普遍应用。乾嘉学术脱离宋明学问的空疏,还以明清尤其清代实学致用的便捷。“史事宗”以“参证”方法影响了乾嘉学派,乾嘉学派的朴学又影响了后面的胡朴安的《周易》古史派,《周易》古史派又影响了后来的古史辨派。薪火相传,蔚为大观。这恐怕就是中国范式、中国哲学的学术气派。
注释:
①说它“新奇”,并不是指它首发“以史证经”,而是说杨万里以醇儒的方式,作了大量的“以史证经”,并将这种方法固定、确立下来。全祖望说诚斋“中以史事证经学,尤为洞邃”,有类此说。
②亦有人认为,考证学当起于宋代,包括朱子,而恰恰是朱熹否认自己的考证、考据一事(见朱熹:《答孙季和》)。说宋代史证者家遍地都是,大史家亦不在少数,如司马光、欧阳修等,这恰恰忘了两点:史家是史家,不是史证家;所有史证者都没有像“史事宗”那样将“参证”一法确立下来,以致有四库馆臣在各家《四库提要》中的不断数落,自是不待赘言,“史事宗”之“参证”一法幸得顾炎武等应用、倡导,也自是不待赘言。中国学术忽视方法范式,与轻视逻辑的习惯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明)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清)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清)纪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
[3](清)黄宗羲.宋元学案[M].(清)全祖望,补修.北京:中华书局,1986.
[4](宋)杨万里.诚斋易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魏)王弼,(晋)韩康伯,(唐)孔颖达.周易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6.
[6](宋)程颐.周易程氏传[M].王孝渔,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
[7](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8]胡朴安.周易古史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0]黄克武.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J].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91,(11).
[11](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张涛.周易文化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3](明)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王俊义.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J].贵州社会科学,1997,(2).
[15]潘雨廷.读易提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6]林忠军.易学源流与现代阐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中图分类号] B2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19)03-0015-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史事宗’易学研究”(14BZX050)
曾华东,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南昌大学江西省大学生思想政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江西南昌 330029)
杨效雷,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87)
【责任编辑: 赵 伟】
标签:顾炎武论文; 史事宗论文; 乾嘉学派论文; 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