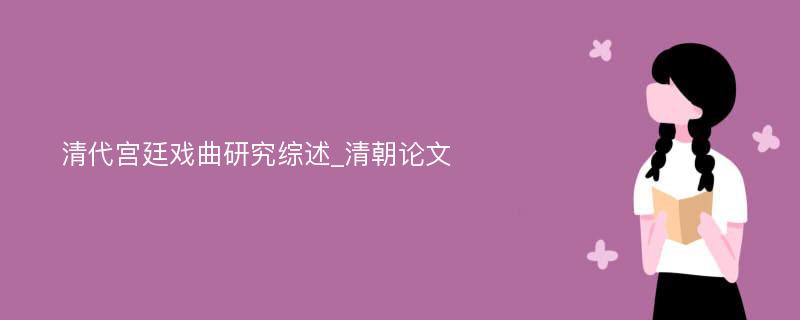
清代宫廷戏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清代论文,宫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开启中国古代戏曲研究之路以来,学界对宋元明戏曲的研究一直处在蓬勃发展的阶段。到了20世纪初,随着清代戏曲文献的不断发掘,清代戏曲渐受学者关注,目前有关资料已远远超过前代,对于清代一些曲家,如南洪北孔的研究和价值认可,丝毫不逊色于前代大家,而对清代其他作家和作品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但是与民间戏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相比,对清代宫廷戏曲的考察和研究则要落后很多。本文试图对清代宫廷戏曲的研究历史进行梳理,以期对今后的清宫演剧研究起到借鉴和帮助的作用。
清代宫廷演戏是历代宫廷演戏的高潮,清代历代皇帝,大都嗜好戏曲,尤以乾隆和光绪为最盛。虽然清宫演戏频繁,但是直到清廷覆灭,大批内廷档案文献流出宫外,清代的内廷演戏情况才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20世纪上半叶以来,对清代宫廷戏曲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 20世纪30年代
1911年清朝宣统帝被迫退位,封建王朝走向了彻底的结束。随着清廷的覆灭,大量内廷戏曲档案文献流入民间,最先接触到此类文献的是朱希祖,他在叙述此过程时曾说:“民国十三年十二月十日,余在北京宣武门外大街汇记书局,购得《昇平署档案》及钞本《戏曲》,共一千数百册。时清废帝初退出宫,一切宫殿即附属衙署,均收归民国政府,委员管理。各宫殿衙署太监,皆纷纷散去,出宫城者,搜检极严,故未有失物;惟昇平署在宫城外,故其太监得私以档案及戏曲稿件,售于小书铺。”①从此开始,清代宫廷戏曲开始进入戏曲史研究的视野,并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清宫演剧研究的第一个高峰。
这一时期,清宫戏曲的研究文章主要见诸当时的报纸杂志,涉及清宫演剧的各个方面。大致为:1.介绍清宫演戏情况。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是1923年署名“铁鹮客”的《清宫传戏始末记》②,记述了清逊帝大婚,内廷仍按旧例传内廷供奉入宫承值的情形;还有《前清内廷演戏回忆录》③,根据曾任内廷供奉的曹心泉口述,详细描述了慈禧太后当政时期清宫传戏的规制、开团场戏目、外学承值人员以及为太后表演时的一些具体情形,是难得的由亲历者讲述的第一手资料。傅惜华在《南府轶闻》④中对昇平署内外学演出承应戏时的规制流程介绍颇为详细,如为帝后表演前的“报请”到帝后出观时的“迎请”再到演毕时的“送驾”以及正式演出前舞台上的“跳灵官”,还有帝后对内外学太监和伶人们的奖惩等,为我们揭开了内廷演出的神秘面纱。岫云在《昇平署之闻见》⑤系列文章中,通过自己的收藏以及对已故内廷承值人员、笛手方星樵的访问,介绍了内廷自乾隆至光绪以来的演剧情况。2.介绍清宫戏台。戏台是演戏留下的物质遗产,对于研究演戏意义重大。这一时期对清宫戏台的介绍不少,如齐如山《风雅存小戏台志》⑥、《南府戏台志》⑦,还有傅惜华的《清宫内廷戏台考略》⑧等,分别介绍了内廷的普通戏台,如颐和园里的听鹂馆戏台、南海中央的纯一斋戏台等;规模宏大、体现皇家气派的三层大戏台,如宁寿宫畅音阁大戏台、颐和园内德和园大戏台等;还有一些可随传随演的小戏台,如重华宫漱芳斋室内小戏台、宁寿宫倦勤斋室内小戏台等。3.介绍清宫演剧的具体戏目。这其中既包括对连台大戏的介绍,如《升平宝筏——清代伟大之神话剧》⑨、《记〈封神天榜〉——清廷承应传奇之一种》⑩、《昭代箫韶之三种脚本》(11)、《〈混元盒〉剧本嬗变考》(12)等,也包括对各种宫廷承应小戏的说明,如《内廷普通之承应开场剧》(13)、《内廷承应传奇之开场》(14)、《内廷除夕之承应戏——如愿迎新》(15)、《〈鱼篮记〉与〈戏鱼篮〉——中元节之应节戏》(16)、《迓福迎祥》(17)、《清宫承应与梨园所演之——〈天香庆节〉》(18)、《清廷之月令承应戏》(19)。4.介绍清宫演剧管理机构。如《南府之沿革》(20),作者清逸居士作为曾任管理内务府大臣的庄恪亲王的后代,认为南府改为昇平署是乾隆年间事,而据周明泰《清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21),改称昇平署为道光七年,一般后世沿用了周明泰的说法。5.介绍承值内廷的外班梨园。这其中包括《谈昇平署外学角色》(22)、《清末内廷梨园供奉表》(23)、《清末戏班承值内廷史料之一斑》(24)以及《清末戏班承值内廷之小统计》(25)。这些文章让我们看到了清代后期内廷与民间的演剧交流情况,也为我们考察京剧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大量的参考。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介绍清宫演剧的专著,除了上面提到的《清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外,还有1931年朱希祖的《整理昇平署档案记》、1934年王芷章的《昇平署志略》(26)和四卷本的《清代伶官传》(27),几部著作将清宫演剧的管理机构——昇平署的沿革、制度、档案、运作机制等详细做了介绍,还记载了当时宫中的各种演剧活动及署中伶人的起居、职责,并收录供演剧目、戏单及剧本等,从而全面地反映了清代宫廷演剧的情况。
综上,这一时期因为距离研究对象的时间很近,还有机会访问到当事人,虽然相关资料档案等还在不断挖掘过程中,但是毕竟还是保留在研究者手中,其存在有共享性,因此30年代的清宫戏曲研究呈现出自身的特征,大体如下:
(一)涉及面广,资料性强,为今后的清宫戏曲研究打下了基础。直到现在,这些文章专著依旧是我们研究清代宫廷戏曲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特别是在很多资料已经收归博物院、档案馆保存,外界已极为稀见的情况下。
(二)很多信息的披露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线索,因此愈显珍贵。如在《内廷普通之承应开场剧》中,傅惜华指出,内廷搬演的承应开场剧“其性质类皆为歌功颂德之作。体制则为南北曲,由一折以至四折不等,或搬昆曲,或演弋腔,惟尚未见有皮黄承应开场剧之编制也”。这一论述解决了承应开场剧的声腔问题,也为民间与宫廷的昆弋到皮黄的过渡与发展的比较提供了参考。再如,在《昇平署之闻见》中,通过对老伶人的访问,详细介绍了三层大戏台的机关使用方法,这是后来的研究者在物质遗产不能再现使用的情况下得到的最可靠的资料,该文还指出由底到上三层戏台的名字原本是“福寿禄”,是慈禧太后将其改为寿字当先,这对研究宫廷戏曲的受众心理也是珍贵的材料。
(三)侧重于清宫演剧情况的介绍,而非学术性的研究。这一时期因为是清廷覆灭不久,对清宫演剧的认识还处在初始阶段,出现的文章也以介绍基本情况、理清基本脉络为主,很多资料和档案还没有被发现,因此研究性、学术性的文章专著还不多见,这也为今后的清宫演剧研究留下了空间。
二 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
这一时期由于战乱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对戏剧的讨论侧重在话剧方面,以便更好地发挥其鼓舞、宣传和战斗作用,而对待宫廷戏曲,则认为其是封建糟粕,大多对其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实际上这一苗头在30年代就出现过,郑振铎在《清代宫廷戏的发展情形怎样?》(28)一文中曾就宫廷大戏说过:“在戏曲史上看来,这一批空前的宏伟的剧本是没有多大重要的价值的。戏文的发展走上了这样的一个路途,便更是自绝与民众,而不能不同时走上了灭亡之路了。”
因此,由于意识形态的局限,对清宫演剧的介绍和研究在这一时期陷入了停滞状态,但对戏曲史的描述却没有忘记清宫戏曲。周贻白先生30年代着手写作,于50年代出版了《中国戏剧史》(29),在“皮黄剧”一章下介绍了昇平署与内廷演剧,不仅肯定了宫廷戏曲作为戏曲史的重要一环,而且结合前一时期相关文章,详细介绍了清朝内廷演出的机构、档案、戏台、各种承应大小戏等,为宫廷戏曲在戏曲史上争得了一席之地,也为后世的戏曲史和清代宫廷戏曲研究奠定了学术史的基础。后来,这部著作于1957年秋修订,改名《中国戏剧史长编》,相较前者,明确提出了清宫戏曲对“皮黄”的影响:“今日的‘皮黄剧’能具有一种高度发展,关于清代内廷演剧的这一番经过,我们是不应当忽视的。”(30)
在1962年,蒋星煜先生发表《清代中叶上海著名连台本戏剧作家张照》(31)一文,不仅关注了宫廷戏曲作家,还考察了张照编写的两部作品——《劝善金科》和《升平宝筏》的版本与流传问题,文章最后依然延续了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路线,指出:“张照的《劝善金科》、《升平宝筏》和其他戏曲作品,都是秉承封建统治阶级意旨直接为宫廷演出而写作的。因此思想内容有很多糟粕”,但是同时也认为“张照也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对遗产肯虚心学习,擅长结构布局,对唱词的写作很严格认真,而这些都是今天的连台本戏作者所容易忽略的。所以对张照的全部作品进行研究和批判地学习,对提高连台本戏的写作水平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蒋星煜的这一看法也是对这一时期连台本戏大讨论的参与,但是从宫廷戏曲角度入手,还是具有一定学术独立性的。
“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进入了起步阶段,学术性的研究迎来了春天。1979年,清宫演剧研究的大家朱家溍先生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上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分别是《清代内廷演戏情况杂谈》(32)和《清代的戏曲服饰史料》(33),前者全面介绍了清代宫廷戏曲演出的机构、规制、编演、剧本、戏台等情况,后者则是他在接触到了第一手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穿戴提纲》和《戏曲人物画》后,从服饰方面对清宫演剧进行了考察,角度新颖,对材料的分析翔实,将清代宫廷戏曲研究重新拉回人们的视线,并开启了下一个阶段研究的先声。
三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解放,学术环境相比以前得到了极大改善和提高,随着材料的不断挖掘和研究角度的不断拓宽,这一时期的清宫演剧研究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宫廷戏曲正式进入戏曲史研究视野。如果说以前的戏曲史著作也曾注意过清代宫廷戏曲,那也只是部分作品的罗列和介绍,如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中提到了清人传奇《劝善金科》、《升平宝筏》、《鼎峙春秋》和《忠义璇图》等。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关于昆曲余势时代之戏曲的乾隆期诸家时,提到内廷七种:《月令承应》、《法宫雅奏》、《九九大庆》、《劝善金科》、《升平宝筏》、《鼎峙春秋》和《忠义璇图》。
进入到80年代,学者们不仅意识到清代宫廷戏曲是清代戏曲史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并且它的意义和作用更应该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周妙中《清代戏曲史》在介绍乾隆年间戏曲和咸同时期花部的兴盛时都将宫廷戏曲单独开列,展开论述,更将宫廷戏曲的研究意义归纳为:“宫廷戏曲和民间戏曲的相互影响,在演出方面,无论剧情、场面、腔调、行头、脸谱、道具、做工等等都有很大程度的改进,并影响到全国各个地方剧种。”(34)“在艺术性方面,清代宫廷大戏对后世的京剧、地方戏的影响很深很广,无论剧目、曲牌、服装、脸谱、道具、演技、唱腔、音乐等等,都较以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也推动了后世戏曲的演进,这种影响也是戏剧研究工作者所不应忽视的。”(35)
(二)对清宫演剧的介绍在前一时期中断后又重回研究者的视野,着重介绍了宫廷戏曲的演出、管理机构和规制。戴云的《简论张照与〈劝善金科〉》(36)、丁汝芹的《清内廷经常上演的剧目》(37)把着眼点放在演出剧目上,分别介绍了内廷经常上演的折子戏和宫廷大戏。杨常德的《清宫演剧制度的变革及其意义》(38)、郎秀华的《清代昇平署沿革》(39)和《清代宫廷戏曲浅谈》(40)、朱家溍的《南府时代的戏曲承应》(41)、丘慧莹的《关于〈昇平署志略〉论及“南府”、“景山”的几个问题》(42)介绍了南府、景山和昇平署等宫廷戏曲演出管理机构的情况,与30年代的相关文章相比,介绍更为系统、详细,便于学者们进一步考察。
(三)沿着前面取得的成果以及大量资料的发现,对清宫演剧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分类考察。龚和德的《清代宫廷戏曲的舞台美术》(43)从现代戏剧表演的角度论述了清宫演戏的舞台设备、灯彩切末和服装化妆,廖奔的《清宫剧场考》(44)则从历时的角度考察了历代宫廷演出的场所以及清代宫廷戏台的种类和使用情况等。《清代避暑山庄演戏琐谈》(45)一文则展示了除紫禁城之外的宫廷演出情况。朱家溍在《昇平署时代“昆腔”“弋腔”与“乱弹”的盛衰考》(46)一文考察了昇平署时代昆腔、弋腔与乱弹消长的真实情况,并得出结论:一直到光绪末年昆腔才在北京让位给乱弹剧种,同时指出,“中国戏曲史应据此改写这一章节”。
丁汝芹在这一时期发表了系列文章论述清廷演戏的情况,其中《清仁宗与戏曲》(47)、《嘉庆年间清廷戏曲活动与乱弹禁令》(48)、《清前期的宫廷演戏》(49)与下一个时期的《同治年间清宫演剧》(50)、《康熙帝与戏曲》(51)等一起,构筑了以朝代为界的清宫演剧图谱,细化了清代宫廷戏曲的分期,描述了不同历史时期宫廷演剧的特点。《南府、昇平署里的太监们》(52)和《清宫演戏的伶人们》(53)则从演员身份角度分析了内廷演戏情况,后者在结尾处指出那些进宫承应的民间戏班的名角们“客观上将京剧整体表演推向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
李玫的《清代宫廷大戏三题》(54)从欣赏者角度探讨宫廷戏曲,指出清代宫廷大戏“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戏曲如何调动接受者欣赏热情的机制”。而赵山林先生更是在《中国戏曲观众学》(55)中专门论述了宫廷戏曲演出的观众接受问题,总结出宫廷戏曲演出的功利性和极严的等级性,并认为与普通戏曲演出相比,内廷的演出在演员与观众的互动性方面是最不理想的。
四 21世纪以来
这一时期虽然距离清宫演剧的时代已经越来越远,但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有充分的时间结集文献资料,深入到曲本和演出的内部,挖掘内廷演剧的意义和价值,也由此形成了继20世纪30年代后的又一个清宫演剧研究的高峰。
(一)大批清宫演剧文献得以整理、出版。《古本戏曲丛刊九集》(56)收录了《劝善金科》等10部清宫连台大戏,已于1964年出版。而《故宫珍本丛刊》(57)涉及南府、昇平署的档案曲本等共计59册,由故宫博物院编辑,于21世纪之初出版。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58),共108册,这些已经成为文物的资料得以结集出版,的确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二)出现了系统研究清宫戏曲的专著。清宫演剧专家丁汝芹在1999年出版了《清代内廷演戏史话》(59),作者查阅了很多前辈学者如朱希祖、王芷章等未能看到的史料,首次将清宫戏剧史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是第一部研究清宫演剧的专著。此后,朱家溍与丁汝芹合著的《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60),正如其《综述》所言:“本书主要汇集了现存有价值的清代内廷关于演剧事宜的档案,以及清人笔记中关于宫中演剧活动的记载。”“我们从各个年代演出的戏单、前后不同的剧目中可以看到清代戏曲发展的轨迹,演出曲种的嬗变以及表演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研究民间戏曲发展史料的不足。”
(三)深入到宫廷戏曲演出内部的专题性研究越来越多。范丽敏的《清代北京戏曲演出研究》(61)一书从声腔流变的角度考察了内廷戏曲的演出情况,材料丰富、全面。幺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62)在谈到清宫戏曲的价值和意义时称:“宫廷戏曲对整个清代戏曲的兴衰变易,无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其中,帝王的意志、喜好与戏曲本身的艺术规律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问题。”另外,丁汝芹《关于道光朝改南府为昇平署》(63)一文对清廷突然改变演剧定制没有遵循普遍看法,而是通过大量史料档案,认为乃道光朝的时局使然。宋俊华《〈穿戴提纲〉与清代宫廷演剧》(64)分析了《穿戴题纲》对我们了解清宫的演剧历史、演剧服饰、演剧习俗以及研究宫廷演剧对民间演剧乃至整个中国戏剧发展史都有着重大影响。曾凡安《礼乐文化与晚晴宫廷演剧的变革》(65)与罗燕《试析清宫承应戏中的仪式性特点》(66)二文则从文化的角度解析了清宫演剧特点。
(四)对宫廷大戏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清宫戏曲研究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在管理机构、演出情况、内外人员和舞台设备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积累,但是对剧本的专门探讨还是在最近几年,特别是对清宫连台本大戏的研究。胡淳艳《清宫“西游戏”的改编与演出——以〈升平宝筏〉为核心》(67)是对《升平宝筏》的研究,而李小红《〈鼎峙春秋〉研究综述》(68)和《〈鼎峙春秋〉演出研究》(69)两篇则专门探讨三国大戏《鼎峙春秋》,这也是她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王春晓《清宫大戏〈忠义璇图〉创编时间考述》(70)和康小芬《清宫“水浒戏”的传播——以〈忠义璇图〉为核心》(71)都是对《忠义璇图》的考察。戴云的《劝善金科研究》(72)则对《劝善金科》及其改编者张照进行全面研究。其他宫廷大戏的研究则未见有,可见,有关清宫连台本大戏尚待开掘的潜在研究领域还是非常广阔的。
综上所述,从清王朝覆灭到现在,对清代宫廷戏曲的研究一直在延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与元杂剧和明清传奇研究相比,宫廷戏曲的研究还相对薄弱。由于文献的缺失和阅读渠道的困难,再加上长时间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宫廷戏曲一度成为戏曲史研究的薄弱环节,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宫廷戏曲自身的学术史建设基本处在停滞阶段,因此,对清宫演剧研究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对以下问题的厘清。
(一)有助于我们完善清代戏曲史
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们普遍在描写戏曲史的时候将目光着眼于民间的作家作品,对宫廷戏曲是基本排斥的。但是作为清代戏曲演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宫廷演剧的缺失不能不说是清代戏曲史描述的一大遗憾,正如《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的《综述》所言:“戏曲艺术(包括剧本文学、表演、演唱、音乐乃至舞台美术)在清代得以高速发展,与统治者的倡导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在新的时期,我们应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对清宫戏曲做出客观、正确的评价,积极将其纳入清代戏曲史的范畴,使之成为戏曲研究不可缺少的一环。
(二)对清宫承应小戏的研究还很薄弱
承应戏作为宫廷演剧的特殊形式,在清宫演剧的早期研究中还有所涉及,但是随着文献的增加和研究思路的拓宽,对承应戏的探索反而越来越少。对连台本的承应大戏还在版本、来源、传播、改编等方面给予关注,而对诸如月令承应、九九大庆、法宫雅奏等承应小戏,则因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研究方面还很薄弱。实际上,自道光以来的内廷档案中涉及承应小戏的内容相当多,其他如《清代杂剧全目》(73)等也相对完整地罗列了各种承应场合与剧目,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结合剧本材料,对承应小戏的声腔、文化美学意义、所反映的民俗民情内涵、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宫廷礼乐制度的变化等方面继续深入挖掘。
(三)对清代宫廷戏曲在戏曲学术史上的作用还没有引起重视
通过以上的分析论述,我们发现对清廷演戏的研究大多还是集中在演戏机构的设置上,对剧本编撰研究,宫廷与民间演出的相互影响,内廷演戏对京剧的产生、繁荣和发展的影响,宫廷演戏的文化、美学意义以及作为受众的帝后们的审美要求对宫廷演剧的影响等都涉及不多或者不够深入;从横向的角度看,历朝历代都有宫廷演出,那么清朝宫廷演出与前代的比较、清代宫廷演出在宫廷演出史上的地位等更是鲜有提及。搞清楚这些问题,才能更全面地界定清宫演剧的形态和本质,也才能更好地健全戏曲学术史。
①朱希祖《整理昇平署档案记》,《燕京学报》第十期单行本,北平燕京大学1931年版。
②铁鹮客《清宫传戏始末记》,《戏杂志》第六期,1923年1月。
③曹心泉口述,邵茗生笔记《前清内廷演戏回忆录》,《剧学月刊》第二卷第五期,1933年5月。
④傅惜华《南府轶闻》(一-三),《国剧画报》第一卷第八期、第九期、第十期,1932年3月11日、18日、25日。
⑤岫云《昇平署之闻见》(上、下、三-九),《国剧画报》第一卷第十四期,1932年4月22日;第十五期,1932年4月29日;第二十期,1932年6月3日;第二十二期,1932年6月17日;第二十五期,1932年7月8日;第二十六期,1932年7月15日;第二十八期和第三十期,1932年7月29日和1932年8月12日;第三十三期,1932年9月2日;第三十九期,1932年10月14日。
⑥齐如山《风雅存小戏台志》,《国剧画报》第一卷第六期,1932年2月26日。
⑦齐如山《南府戏台志》(上、下),《国剧画报》第一卷第三十九、四十期,1932年10月14日、21日。
⑧傅惜华《清宫内廷戏台考略》(一-四),《北平晨报·国剧周刊》,1936年7月30日、8月6日、8月20日、9月17日。
⑨傅惜华《升平宝筏——清代伟大之神话剧(一-六)》,《北平晨报·艺圃》,1930年12月16日、17日、18日、19日、20日、21日。
⑩傅惜华《记〈封神天榜〉——清廷承应传奇之一种》,《北京画报》第一百八十一期,1931年5月27日。
(11)周志辅《昭代箫韶之三种脚本(正、续)》,《剧学月刊》第三卷第一、二期,1934年1月、2月。
(12)傅惜华《〈混元盒〉剧本嬗变考》,《北平晨报·国剧周刊》1936年6月25日。
(13)傅惜华《内廷普通之承应开场剧》,《北京画报》第一百七十八期,1931年5月18日。
(14)傅惜华《内廷承应传奇之开场》,《半月戏剧》第一卷第四期,1938年2月25日。
(15)傅惜华《内廷除夕之承应戏——〈如愿迎新〉》,《国剧画报》第一卷第四期,1932年2月5日。
(16)傅惜华《〈鱼篮记〉与〈戏鱼篮〉——中元节之应节戏》,《北平晨报·国剧周刊》1936年8月27日。
(17)曲葊《迓福迎祥》,《北平晨报·国剧周刊》1936年8月27日。
(18)仲涵《清宫承应与梨园所演之——〈天香庆节〉》,《北平晨报·国剧周刊》1936年10月1日。
(19)傅惜华《清廷之月令承应戏》(上、下),《北平晨报·国剧周刊》1936年11月26日、12月3日。
(20)清逸《南府之沿革》,载《戏剧丛刊》,天津古籍书店1993年影印版。
(21)周明泰《清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几礼居丛书》第四种,又名《掌故骈臻》,1933年初版。
(22)齐如山《谈昇平署外学角色》,载《戏剧丛刊》,天津古籍书店1993年影印版。
(23)松凫《清末内廷梨园供奉表》,《剧学月刊》第三卷第十一期,1934年11月。
(24)寰如《清末戏班承值内廷史料之一斑》(一-六),《北平晨报·国剧周刊》1936年8月6日、13日、20日、27日,9月3日、10日。
(25)寰如《清末戏班承值内廷之小统计》(上、中、续、续、续),《北平晨报·国剧周刊》1936年9月24日,10月8日、15日,11月5日、12日。
(26)王芷章《昇平署志略》,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27)王芷章《清代伶官传》,中华书局1936年版。
(28)郑振铎《清代宫廷戏的发展情形怎样?》,载《文学百题》,生活书店1935年版。
(29)周贻白《中国戏剧史》,中华书局1953年版。
(30)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第5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31)蒋星煜《清代中叶上海著名连台本戏剧作家张照》,《上海戏剧》1962年第9期。
(32)朱家溍《清代内廷演戏情况杂谈》,《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
(33)朱家溍《清代的戏曲服饰史料》,《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4期。
(34)(35)周妙中《清代戏曲史》,第184页、第19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6)戴云《简论张照与〈劝善金科〉(上、下)》,《戏曲艺术》1995年第3、4期。
(37)丁汝芹《清内廷经常上演的剧目》,《文史知识》1999年第8期。
(38)杨常德《清宫演剧制度的变革及其意义(上、下)》,《戏曲艺术》1985年第2、3期。
(39)郎秀华《清代昇平署沿革》,《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1期。
(40)郎秀华《清代宫廷戏曲浅谈》,《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2期。
(41)朱家溍《南府时代的戏曲承应》,《紫禁城》1998年第3期。
(42)丘慧莹《关于〈昇平署志略〉论及“南府”、“景山”的几个问题》,《南京师大学报》1998年第2期。
(43)龚和德《清代宫廷戏曲的舞台美术》,《戏剧艺术》1981年第2、3期。
(44)廖奔《清宫剧场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4期。
(45)李国梁《清代避暑山庄演戏琐谈》,《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2期。
(46)朱家溍《昇平署时代“昆腔”“弋腔”与“乱弹”的盛衰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S1期。
(47)丁汝芹《清仁宗与戏曲》,《紫禁城》1993年第2期。
(48)丁汝芹《嘉庆年间清廷戏曲活动与乱弹禁令》,《文艺研究》1993年第6期。
(49)丁汝芹《清前期的宫廷演戏》,《文史知识》1998年第10期。
(50)丁汝芹《同治年间清宫演剧》,《中华戏曲》2004年第1期。
(51)丁汝芹《康熙帝与戏曲》,《紫禁城》2008年第6期。
(52)丁汝芹《南府、昇平署里的太监们》,《紫禁城》1996年第1期。
(53)丁汝芹《清宫演戏的伶人们》,《文史知识》1998年第12期。
(54)李玫《清代宫廷大戏三题》,《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1期。
(55)赵山林《中国戏曲观众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56)《古本戏曲丛刊九集》,中华书局1964年版。
(57)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
(58)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中华书局2011年版。
(59)丁汝芹《清代内廷演戏史话》,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版。
(60)朱家溍、丁汝芹《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61)范丽敏《清代北京戏曲演出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62)幺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63)丁汝芹《关于道光朝改南府为昇平署》,《戏曲研究》第56辑。
(64)宋俊华《〈穿戴提纲〉与清代宫廷演剧》,《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65)曾凡安《礼乐文化与晚晴宫廷演剧的变革》,《文学遗产》2009年第3期。
(66)罗燕《试析清宫承应戏中的仪式性特点》,《文化遗产》2010年第4期。
(67)胡淳艳《清宫“西游戏”的改编与演出——以〈升平宝筏〉为核心》,《戏曲艺术》2006年第4期。
(68)李小红《〈鼎峙春秋〉研究综述》,《兰州学刊》2008年第2期。
(69)李小红《〈鼎峙春秋〉演出研究》,《戏曲研究》第76辑。
(70)王春晓《清宫大戏〈忠义璇图〉创编时间考述》,《四川戏剧》2011年第1期。
(71)康小芬《清宫“水浒戏”的传播——以〈忠义璇图〉为核心》,《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1期。
(72)戴云《劝善金科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3)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