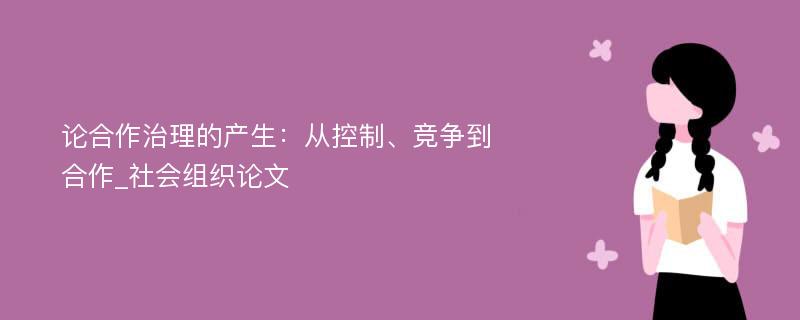
论合作治理的生成:从控制、竞争到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竞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各种复杂且相互缠绕的问题纷至沓来,强调管控的传统治理模式在应对这些问题时往往纰漏百出,表现出政府习惯性迟滞、经济间歇性失控和社会危机频发①等治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改变现行的治理模式和治理逻辑,在探索多元治理主体如何实现合作的维度上思考治理范式的转变,才能有所突破。 (一)控制导向的社会治理 在人类社会的演化发展中,社会治理模式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前工业社会的统治型治理、工业社会的管控型治理以及后工业社会的参与型治理。在前工业社会的统治型治理模式中,政府始终是在控制追求的逻辑下开展治理活动的。在大多数时候,君主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社会治理权力,并借由“君权神授”来自证其身份权威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这种国家与社会高度受控于一人的统治型治理在农业社会尚足以应对低度复杂的公共问题,但是当人类社会开启工业化进程之后,刻板滞后的统治就远远无法有效应对现实问题了。随着启蒙运动的勃兴,在“祛魅”后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原子化的个体被赋予不同的角色,随即融入各种各样的组织之中。社会治理系统借助“社会契约”抽离了个人的政治权利,从而实现对组织和社会的高效管控,使“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对立成为了社会治理关系的基本内容”②,此时“社会从属于国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命令与服从的单向权力关系,国家和政府公共权力将私人权利的空间压缩到最低限度”③。然而政府对高效管控的狂热追求最终招致了社会运行的整体性“失控”,各种治理困境接踵而至,“大萧条”和“滞涨”的爆发彻底宣告了管控型治理的失败。此时,尽管行政学界已经认识到在社会治理中一味强化管控的弊端,但控制追求已然为治理画地为牢,政府无法摆脱“放权”与“集权”的二元思维桎梏。更多的时候,治理系统的变革只是在如何防止政府成为治理寡头这一问题上踟蹰,公共部门的改革也主要聚焦于经济职能领域,为迎合市场形势而渐进地、被动滞后地进行着治理方式的微调。 将人类社会的治理历史描绘成一部控制追求的演化史毫不为过。人类在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中渐渐误读和夸大了其对外在环境甚至内在思维的控制能力,对自然和自身的双重僭慢(hubris)从工业革命之后逐渐发展到顶峰,人们相信通过精确严密的制度设计可以控制一切,妄图消灭所有潜在和显在的不确定性,这无疑是控制追求和技术理性思维发展到极致后产生的错觉。后工业社会的复杂性、不确定性都是工业社会所无法比拟的,出现于后工业社会的参与型治理虽然将“社会”作为新的主体纳入治理体系之中,但仅仅是在更大程度上让社会力量参与政策制定,并没有赋予社会组织平等的治权,也没有改变在社会治理上的控制追求。“在实践中,参与治理往往使政府在多种相互冲突的意见中面临选择困难……参与治理也许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缓和了政府的控制导向,使政府表现出一种对社会的温和控制,它所实现的只是量的意义上的改变,并没有促使这种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④。所以说,尽管统治、管控和参与这三种社会治理的运行逻辑、集权程度、组织模式、治理方式截然不同,但事实上都是在控制追求的指引下形成的不同治理形态。随着社会复杂性、不确定性的增加,“中心—边缘”结构下的网络中心所能够提供的治理,无论是在数量的充足性还是手段的多样性上均已无法满足现实社会的诉求。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一个中央政府,不管它如何精明强干,也不能明察秋毫,不能依靠自己去了解一个大国生活的一切细节。它办不到这一点,因为这样的工作超过了人力之所及。当它要独力创造那么多发条并使它们发动的时候,其结果不是很不完美,就是徒劳无益地消耗自己的精力”⑤。在控制追求逻辑下的“中心—边缘”治理网络终会走向治理垄断和集权,造成市民社会的衰落,遭遇治理失灵。 “综观整个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这个社会自身就处在一种逻辑悖论之中,关于这个社会的所有建构方案都在其主题阐释的过程中走向自反的结局”⑥。形成于工业社会的那种强调控制的社会治理同样存在着无法克服的二律背反。依照其逻辑建构出的社会治理系统频繁地与后工业社会的现实发生摩擦,表现为各种治理的紧张和失灵。控制追求是为了有效减少社会的不确定性,然而这种方式在后工业社会无法奏效,人们又无法摆脱对其的依赖,面对复杂多变的公共问题,政府部门总是条件反射地强化管控社会的力度,试图将大量涌现的公共问题按压下去。但是,治理的长期动态性妥适需要建构在及时、准确、完整的信息获取的基础之上,现实中治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信息难以如此对称,政府也无法长期地前瞻未来。于是,为了维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政府只能不断强化自身“操控社会”的能力,而被强力控制所扼住的却是社会的活力而非社会冲突,最终表现为:政府本是为了减少不确定性而加强控制,反而堵塞了社会矛盾的释放路径,导致社会运行变得更加不确定;社会运行风险性的上升反过来又刺激政府进一步强化管控力度,形成恶性循环。以强调控制追求的现代科层制为例,科层制通过一系列缜密的制度设计和森严的层级管控,使得实际操纵社会治理系统运行的是制度本身而非具体的某个人,管理者只是制度的“维护者”。科层制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维持组织秩序、抑制背离组织目标的活动,更多的情况下,公共部门会受到外界环境的高复杂性和高风险性逼迫而在组织内外采取强制式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会赋予去人性化的控制追求以一种虚幻的正当性,让人们认为唯有完全听命于政府才能化解危机,而不去反思是否还有别的可能,或者这种制度是否过于严苛、过于“非人格化”⑦。一旦制度能够将组织中的人牢牢控制,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组织内部的不确定性。但是,政府在后工业社会所要面临的真正挑战来自于外部环境而非内部,为了有效应对外部不断涌现的公共问题,政府只能被动地不断增设新的治理部门、扩容组织规模,导致政府组织臃肿和治理裂化。同时,崇尚专业分工的科层组织解构了个人责任,要求部门化地实现角色目标以便完成每天的工作任务⑧,这种分工—协作强调的是“我在性”,让组织中的人更关注自身能够从协作系统中获得什么,而非组织能获得什么,更不会对组织之外的利益纠葛详加考量,这种看似趋利避害实则唯利是图的逻辑极易滋生行政傲慢和贪污腐败。我们并不否认政府部门的控制追求确实是在力图实现公共善(public good)⑨,但在实际运行中却衍生了行政之恶(administrative evil)⑩,其本源正是控制追求所形塑的技术理性文化。可以说,在后工业社会中,控制追求是一剂会导致治理系统去功能化的“毒药”。 (二)社会治理中竞争逻辑的自我否定 自由竞争是市场的运行逻辑,随着全球经济市场化和一体化的发展,市场逐渐获得了社会治理的主体地位,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将竞争逻辑带入到治理之中,产生了诸如强调企业家精神和为顾客服务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思潮。然而竞争逻辑在社会治理中却表现出一种自我否定:人们希望通过在公共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来提高治理绩效、摆脱权力衍生的行政之恶,但竞争逻辑的高扬却使行政和治理走向了自反的结局。由自由竞争、价格机制、效率崇拜组成的市场逻辑对社会资源的分配机制投射了一套财富霸权主义,这不但会使“拜金主义”扭曲大众文化,更使公共权力出现异化,转变成为资本服务和维护资本家利益的工具。 在社会治理中,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的。既然治理主体不再唯一,那么必然涉及主体之间如何互动,或者说合作路径如何建构的问题。在竞争逻辑大行其道的环境中,多元主体的合作路径构建被异化为一种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过程,治理主体更关注的是能够在合作中获得多少“利益”而非这种合作能否实现“正义”。“市场把它的手向非经济生活领域伸的越深,市场与道德问题就纠缠得越紧”(11),也就与正义问题产生了割裂不开的联系。市场根据价格体系调节资源的配给,而价格体系的作用机理是按照人们的偏好来分配物品,并不追问这些偏好本身是否正义、是否道德。而且,市场逻辑在当今市场经济遍布全球的大环境下具有非常强大的侵蚀力,一旦其介入非经济生活领域,就能够迅速将该领域原有的配给伦理排挤出去,最终使得一切事物(包括人)都被打上标签待价而沽,货币交易成为唯一的配给方式。也许,市场逻辑如此具有吸引力的本质正是它并不对其所满足的偏好进行道德上的审视和判断,但长期任由市场逻辑占据非私人领域话语权未必会使社会交往更有效率,却一定会贬损公共话语的道德含义,抽空公民社会的力量源泉。而且,若将公共服务视为一种可售商品,即便再高效也是对治理正义本身价值的贬损。 政府将市场的自由竞争逻辑引入社会治理领域,试图通过多元主体的治理竞争增进治理效率、改善公共福利、缓和矛盾和对抗。但是,自由竞争的前提是地位平等,而在合作逻辑尚未形成之前,政府相较于其他治理主体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在工业社会中,“一方面,出于竞争的需要,必须壮大自己的力量,必须通过与他人的合作而去获得优势;另一方面,竞争必然会破坏合作,会根据自己的利益要求及其实现状况而去决定对合作的态度,会经常性地出现背叛合作的行为”(12)。在公共问题的复杂性、随机性不断上升的后工业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挑战是空前的,治理的合理性甚至合法性都受到质疑。环境倒逼着政府本能地收紧治理权力,集中力量去解决不断涌现的治理失灵问题,从而再次重蹈追求控制的覆辙。所以,在主体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下,多元治理主体的竞争格局只是镜花水月。在公共行政中出现的所谓“市场化取向”丝毫没有撼动政府在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即便是通过立法强行赋予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同等的治理权力,在控制导向的治理逻辑下,多元竞争的格局也是不稳定且交易费用畸高的。因为,竞争就会牵涉到利益分配,同等治理权力意味着收益丰厚的领域会出现大量重复建设。竞争会使大量的人力物力被消耗在各主体间多次不完全信息的博弈之中,但无论市场和社会组织如何努力,也不可能与拥有公共权力的政府抗衡。 (三)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合作治理的形成 一个成熟健康的治理系统,需要大量社会自治组织的参与。虽然社会组织在工业社会中就已大量存在,但大多是以非营利组织的形象出现,主要在社会服务及市场经济领域发挥作用。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为了纠正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社会成为政府及市场之外的另一治理主体,社会组织也因其能够将原子化的个人整合为目标统一的行动体而具有了公共性和政治性,公民社会理论更为社会组织在治理中发挥政治功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操作空间。社会组织在治理中的作用不再仅仅是公共服务的供给者,或是政府和市场的监督者,而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社会自治的发言人,社会组织是行动者们“互助行动的结构化,是稳定的合作形式”(13),也是现代民主体系的重要内容,它奠定了基层民主特别是社会自治的组织基础(14)。 然而在管控型社会治理中,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很难得到真正的发展,其形成、注册、筹资和评估会受到来自政府和市场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钳制。在政府眼中,社会组织是一个具有潜在对抗性和躁动性的团体,如果引导得当则能够形成多元主体的合作,处理不当则很有可能引发冲突。企业也不会视社会组织为值得信赖的伙伴,而是将它们看作竞争者和博弈对手。所以,在控制追求和竞争逻辑的桎梏中社会组织很难获得成长的空间,更无法以平等主体的身份进入社会治理体系,在后工业社会,要真正发挥社会的力量,必须构建新的治理框架,赋予社会组织平等的主体地位。 这种新的治理框架就是追求合作的治理模式,然而合作治理的生成又离不开社会组织的成长,这要求政府和市场必须充分信任社会组织在治理中的作用,帮助并引导社会组织快速成长为成熟的社会自治力量。在工业社会中,政府与社会存在三种关系:政府放权,向社会组织转移某些职能;政府与社会组织协作实现共同治理;政府培育社会组织发展(15)。这三种模式都是“分工—协作”思维逻辑下的主体间互动,这种相互补拙的伙伴关系只体现了合作治理的一部分内涵。在追求合作的治理环境中,社会组织作为平等的治理主体,其使命在于重塑治理网络结构,使其从蛛网状(单中心化)向蜂巢状(去中心化)转变——这也就意味着长期占据社会建构话语权的“中心—边缘”结构即将成为历史,政府对社会资源的虹吸效应(16)也将随之消退。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组织是使治理变革转向合作维度的催化剂,是一种整合社会网络中大量行动者的组织载体。社会组织的治权并不是任何人授予或行动者们让渡的集合,而是在治理行动中获得的。 治理主体多元化、社会的崛起和行动者的归来是相伴而生的。在传统治理中,寻找到各主体的权力清单是治理开展的前提,人类社会习以为常的分工逻辑要求先厘清权责界限,为各个主体所负责的治理领域立好界碑,然后分别由不同主体供给服务,最后再将这些不同类型的服务拼装组合起来供给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复杂现状颠覆了这种工业化印记明显的流水线或供给模式,要求人们不再着力去探寻更细致的分工机制,转而在多元合作的维度上创造进步的空间。与工业社会原子化个体在治理洪流中的无助感不同,后工业社会中任何一个人都能对公共生活产生影响,任何一个社会组织都可以为争取自己群体的利益而清晰发声。合作治理的生成预示着治理范式的转变,将会打破长期固化的“分工—协作”逻辑和“中心—边缘”结构,由此形成相互信任、资源共享、平等协商的合作治理行动者系统。 ①Y.Papadopoulos,"Cooperative Forms of Governance:Problems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in Complex Environments",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2003(4). ②张康之、张乾友:《民主的没落与公共性的扩散——走向合作治理的社会治理变革逻辑》,《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2期。 ③施雪华:《论传统与现代治理体系及其结构转型》,《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期。 ④张康之:《论主体多元化条件下的社会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⑤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00~101页。 ⑥张康之:《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页。 ⑦全钟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孙柏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⑧E.Staub,The Roots of Evil:The Origins of Genocide and Other Group Violenc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⑨迈克尔·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邓正来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⑩艾赅博、百里枫:《揭开行政之恶》,白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11)迈克尔·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第90页。 (12)张康之:《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第77页。 (13)张康之:《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第79页。 (14)若弘:《中国NGO——非政府组织在中国》,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页。 (15)郁建兴、徐越倩:《服务型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页。 (16)柳亦博:《政府引导视阈下的社会冲突治理:一个基于冲突治理结构的解释框架》,《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