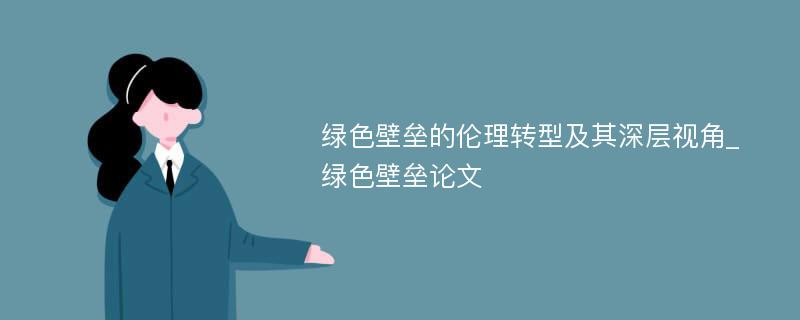
绿色壁垒的伦理蜕变及深层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壁垒论文,伦理论文,透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完美的理论总是无法掩盖丑陋的现实,善良的愿望总是无法抵挡强权的意志。国际贸易中引进适当的环境保护政策从理论上说可能达致了伦理地通往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和尊重地球的美好境界,但在现实中却往往被居心险恶者歪曲了,蜕化为非伦理和反伦理的藉口。要言之,从运用绿色壁垒的动机看,绿色壁垒具有正当性和不正当性之分。正当性的绿色壁垒是出于切实保护环境的目的,并且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是公正的;不正当性的绿色壁垒是以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其被抬高的本国环保标准其实是为了阻挡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而构筑的屏障。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中,这样的“不正当性”正在冲淡国际贸易的环境政策,使绿色壁垒成为反伦理的代名词。其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一)对各国采取所谓“统一”的环保标准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巨大差异,在科学技术、经济实力、立法要求、环境标准都处于制高点的发达国家,在贸易谈判时总是企图以国际标准甚至高于国际标准的要求来统一为环保产品划定达标线。一些贸易协定也从中推波助澜。如TBT规定,如果国际标准不是一国想达到的国内环保水平,缔约国可以实施特殊的国内强制措施,但必须强化透明度和通知原则。发展中国家显然不同意这种无视“南北差异”的“一刀切”的提议。因为“统一”的环境标准貌似公正,实则损害的恰恰是公正。公正的环境责任,不是平均分摊,也不是统一要求,而是在衡量历史差异、现实状况和未来影响等诸多层面后的通盘考虑。保护环境的确是全球的责任,但由于各国在技术、立法、价值、收入、污染控制、措施费用以及自然条件方面的差异,环境保护的要求程度也是因国而异的。必须首先承认“异”是客观存在而且是解决问题的前提,然后再掂量,这里的“异”究竟“异”到什么限度才是合理的、公正的、可行的?过高的标准有损公正性,过低的标准又不能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有些学者认为,统一全球环境要求不是个好办法,是无效的,而标准过于局部化则有可能导致其有效性的降低和被滥用的可能。他们建议:为了减少出现严重的、无法挽回的环境损害的风险性,协调出最低的要求可能是合理的。同时,他们提醒,这种最低要求也只能适用于少数的情况,因为在每个方面都提出各国协调一致的环境要求必然招致反对,是不可能的,必须另谋他途。(注:参见(瑞典)Thomas Andersson等著《环境与贸易——生态、经济、体制和政策》,黄晶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9-61。)也许探求一种既有利于环境保护又有利于贸易发展,既合乎环境伦理准则又合乎市场追求规律的道路是遥远的,但指导这条道路走向的原则无疑是建立在正义基础之上的原则。
(二)对特定国家的相同产品给予歧视性待遇
最惠国待遇既是维护自由贸易正常进行的原则,又是表征交易者道德水平的伦理性规范。不遵守这一原则就会妨碍贸易自由,也是对道德准则的侵犯,构成歧视性。绿色壁垒常常可能被人利用,借环保之名,行歧视之实。如1996年美国与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的“海虾/海龟案”。美国以该四国捕海虾未使用TED(turle-excluder-device:一种防止误捕珍稀海龟的装置),违反美国国内法(609条款)为由禁止从这些国家进口海虾。印度等国认为,不能仅因为生产或加工方法的不同就对来源于不同成员方的但实质相同或类似的进口产品实行有差别的待遇,TED的使用与否并不影响海虾的实质物理构成,美国权凭捕捞方式的不同就确定对未使用TED的出口国实施禁止进口措施,显然违背了WTO的最惠国待遇。由此可见,进口国以保护环境为理由实施绿色壁垒时,如果不遵守相应的贸易原则和贸易道德规范,绿色壁垒便很有可能蜕化为不正当性的绿色壁垒,不但有违绿色壁垒的初衷,反而成为保护主义的保护伞。
(三)对国内产品与国外同类产品实行双重标准
为达到既保护环境又获取商业利益的双重目的,应当采取怎样的环境标准确实颇费思量。如果降低本国的环保标准,宽让他人的较低标准,那么虽然短期利益上可能会有损失,但对出口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一种扶持,长远地看,不但能赢得道义的声誉而且也有助于环境的改善。但是,一些在这方面有能力、有作为的发达国家的做法恰恰相反,他们对本国的产品采取宽裕的尺度而对出口国的产品却一味“严厉”要求。如美国委内瑞拉汽油案。这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受理的第一起贸易纠纷。美国环保署于1994年为在美国九大城市出售的汽油制定了新的环保标准,规定汽油中的硫、苯等有害物质的含量必须低于一定的水平;美国国内生产的汽油可以逐步达到有关标准,而进口汽油必须在1995年1月1日该规定生效时立即达标,否则禁止进口。委内瑞拉作为向美国出口汽油最多的国家,是这一规定的最大受害国,因而上诉世贸组织。世贸组织本案专家组认为,尽管各国在制定贸易法规时有权根据本国的情况制定相应的环保标准和措施,但对进口商品的有关待遇不得低于本国相同或相似的商品;而美国对进口汽油环境标准的要求超过本国汽油,限制了外国汽油的进口,违反了WTO的国民待遇原则。WTO支持委内瑞拉及其他石油国的立场。上诉机构在受理本案中似乎倾向于这样一个原则:环保例外措施必须在不造成不公平和随意的歧视、不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前提下才可应用。这个原则是符合伦理精神的,它表达了正义的基本价值诉求。本案的圆满解决揭示了环境保护和贸易发展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也说明绿色壁垒的启用并不是任意的,它要求动机的伦理性和道德准则的参与。同时,还说明,环境伦理的基本理念能够与经济发展相融合并为它提供有益的现实指导和发展思路。
(四)对他国的内政进行干涉
根据国际法,每个政府在其领土内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当然包括对本国资源的处置权和生产方式使用权。但是,有些国家居然认为,在国际贸易中,进口国可以要求出口国的产品按照本国国内法生产,也可以要求产品不符合进口国法律要求的出口国,改变相关政策。显然,这种要求超越了国际法,是有意要干涉他国内政。如美国与墨西哥等国的“金枪鱼—海豚”案。在太平洋的东部赤道地带,金枪鱼一般与海豚混游在一起,用围网捕捞金枪鱼时时常造成海豚的意外伤亡。美国国内法《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规定,如果某个向美国出口金枪鱼的国家不能向美国权威机构证明其符合该法规所制定的标准,则美国政府必须停止所有来自该国的鱼类进口。墨西哥等国是所涉出口国,受到美国法院诉讼。此案之所以涉嫌干涉他国内政,根本之处在于,美国借机要迫使墨西哥等国改变捕捞金枪鱼的生产方式并拿出“一项调整海洋哺乳动物捕获的、可与美国相比拟的规划”,即改变鱼类政策。该案专家组认为:美国不能仅仅因为墨西哥关于金枪鱼生产方法的规范不符合美国的法规就停止从墨西哥进口金枪鱼;GATT的规则不允许一个国家为试图在另一个国家执行其国内法的目的而采取贸易行动——即使是为了保护动物健康或可耗竭的自然资源。我们可以合理推论,如果美国的提请获得通过,那么那些强势国家在今后都有可能假借他国的环境政策与本国不相应(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环境政策差异的存在是客观事实)的理由,强行把自己的法律运用于域外,迫使弱小国家修改相关政策——这除了是干涉他国内政,焉有他哉?!
(五)对发展中国家的压榨和盘剥
绿色壁垒对于处于优势的发达国家有利,而对于处于贫困、人口困境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更多的被动和压力。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还要承受不正当性绿色壁垒的盘剥和压榨。欧盟环保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早在1996年,欧盟国家禁止进口的“非绿色产品”价值达200亿美元,其中90%的产品来自发展中国家。我国每年约有7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因绿色壁垒受阻。(注:魏龙、徐茜:《环保时代的国际贸易前景与策略》,《武汉工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究其原因,除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薄弱和技术劣势外,还与发达国家利用不正当性绿色壁垒对发展中国家极尽压榨之能事脱不了干系:低价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又用高价制成品攫取利润,但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损失和资源以外的价值均由发展中国家承担,并且还要承受发达国家“破坏全球环境”的指责;把污染企业和废弃物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环境法规不健全和环境标准宽松的特点,将国内的“夕阳产业”、工业和生活废物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不仅从中谋取大量经济利益,还严重破坏当地环境;利用各种形式的绿色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用技术、资金等优势抢占世界绿色市场,维护其贸易霸主地位;把接受其环境理念和环境要求作为优惠贷款、国际投资、无偿援助等方面的先决条件。日本环境社会学创始人饭道伸子针对国际环境问题的不平等现象指出:“今天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大规模开发和工业建设的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居民的生活和健康受到损害,土著民族的原有生活方式遭受彻底破坏的过程。”(注:(日)饭道伸子著《环境社会学》,包智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32页。)实际上,这种破坏还应包括国际贸易中的不正当性绿色壁垒。
二
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政策所体现的种种美好规划本应迈向伦理之境,它之所以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伦理的不伦理性”、“道德的不道德性”的困境,有着复杂的原因。
(一)西方发达国家惯有的霸主心态使绿色壁垒不可避免地被反伦理利用
由于发达国家在技术、资金、环保、消费需求等等方面的既有条件都比发展中国家占有优势,比较成本较之劳动力低廉、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偏高,而支持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是成本比较优势,因此发达国家面对这种局势历来心态很矛盾: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始终落后的话,就难以作为成熟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从中牟利;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发展较快的话,又构成竞争威胁。如何既不使发展中国家壮大为贸易对手,又不至于把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憋死,是发达国家始终绞尽脑汁要对付的问题。
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副教授托马斯(Thomas Andersson),瑞典皇家科学院贝耶国际生态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卡尔(Carl Folke),OECD经济与环境政策一体化小组副组长史蒂芬(Stefan Nystrom)在他们的合著中分析到,国际贸易格局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变化,东亚国家如中国和越南、拉丁美洲以及南非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大大增强了工业竞争力,传统的经济强国(北美和西欧)已失去了在扩大的世界贸易中的统治地位,“对此,他们正在寻找相应办法”。(注:参见(瑞典)Thomas Andersson等著《环境与贸易——生态、经济、体制和政策》,黄晶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3页。)他们没有指出“办法”的内容是什么,但明眼人一望即知,其中必然包括遏制他人自己渔利的绿色壁垒。1996年,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美国外交与21世纪全球环境挑战》一文中比较明确地回答了“办法”的内容:环境问题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贸易政策。这应合了世界银行经济政策和预测局局长尤里·达度什的话:“世界上许多最贫困的国家未能从全球经济日益开放中受益,一个原因是它们政策机构的问题;但是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工业国对它们的产品所设的保护主义壁垒所产生的影响。”(注:转引自黄卫平、程大为:《发达国家贸易壁垒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研究》,2001年第3期。)为了维护国际贸易中的霸主地位,发达国家决不会放弃任何有助于增强这种地位的机会,在赤裸裸的强权声名狼藉、失去道义和效应后,名义合理、形式合法、内容广泛、手段隐蔽的绿色壁垒是最合发达国家口味和最能满足其心态需要的一道“良药”了。
(二)构筑绿色壁垒的国际公约、条规本身的陋缺为这种不正当性的产生留下了空间
环保浪潮对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产生了一定影响,在WTO的有关文件(主要是《GATT1994》、TBT、SPS三个文件)中均涉及环境问题。但是,WTO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不明朗,条文不具体。一方面,WTO原则上承认各个成员为了保护各自的公共秩序和防止环境污染,有权制定本国的环保政策并组织实施,另一方面则要求这些政策和措施不能妨碍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的正常运行、使环保措施成为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然而,它没有为此做出更多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和说明,这不仅不能达到绿色国际贸易的要求,预防贸易保护主义的变相滥用,反而为其变相滥用提供了堂而皇之的理由。
具体地说,WTO的环境贸易规则在以下三点上为不正当性绿色壁垒开了“绿灯”(注:参见那力、何志鹏编著《WTO与环境保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1-102页;赵春明主编《非关税壁垒的应对及运用——“入世”后中国企业的策略选择》,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4-216页。):
1.“环保例外权”的内容不明确。WTO对各成员如何行使此权力缺乏有效的、明确的约束性规范。这容易被贸易保护主义者盗用和滥用,诱发为不正当性绿色壁垒,从而对全球贸易自由化,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构成新的威胁。
2.“环保例外权”的限制条件不具体。WTO对行使这项权力虽然作出了限制,但缺乏严谨规定,含混其辞。如“不对情况相同的成员方造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歧视”或“不对国际贸易构成隐蔽的限制”等。这些表达均模棱两可,什么是“情况相同”?什么是“武断的”、“不合理的”、“隐蔽的”?均无衡量标准。这便给了贸易保护主义者以可乘之机,为不正当性的绿色壁垒披上合法外衣,而使受害者和仲裁机构鞭长莫及。
3.对发展中国家缺乏差别性待遇。这种无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标准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差异,“一视同仁”的做法,显然有意偏袒、照顾优势的发达国家,而对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不利。这不仅加剧了南北矛盾,而且为不正当性壁垒大开了方便之门。
(三)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所具有的普适性虚妄、话语霸权倾向为绿色壁垒的堕落提供了理论支持
西方生态伦理为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伦理准则找到了理论根基。但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协调原则、处置方式、理想预期等各有其特殊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更是悬殊。发达国家在短短数百年间,以机器化大生产从“征服自然”和以掠夺行为、不公平贸易等方式从欠发达国家那里所获得的利益中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建立了繁华的工业文明,也大大改善了自己的环境状况。如今几无“发展”后顾之忧的发达国家,企图维护的是既有利益和既有利益的延续性,因而追求的是“清洁生产”、“绿色消费”、“绿色工业”……,而仍为贫困、生计担忧的发展中国家关心的是当前发展和当前发展的超越性,它们虽然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但仍无可奈何地置之于“发展”之后。遗憾的是,衣食无忧者竟然毫无羞涩地要与食不果腹者同等地为世界环境危机分忧解愁!西方生态伦理同样忽视或漠视甚或无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把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幻化为普遍的、与发达国家相同的样式,在某种程度上是肯定和欣赏这种责任均摊的虚假公平的。因而,人们不能不责问:如果西方环境伦理学只津津乐道于人对大自然的义务,却闭口不谈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义务,不愿意降低发达国家对资源的人均消费水平,那么,我们有理由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现实性和可行性表示怀疑。
环境伦理的这种普适性虚妄和话语垄断作为一种理论取向已经反映在绿色壁垒的不正当性上。因此,国际贸易社会在以全球环保为旗帜,号召人类共同行动时,理当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的特殊性,理当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既解决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环境保护的问题,又能缓和并克服全球性环境危机。否则,环保的旗帜就会成为强权者挥舞着的屠刀。这样不仅会伤害广大弱势国家对环保的钟情,对生态伦理的追求,更会加剧世界的不平等和全球环境的恶化。这是地球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