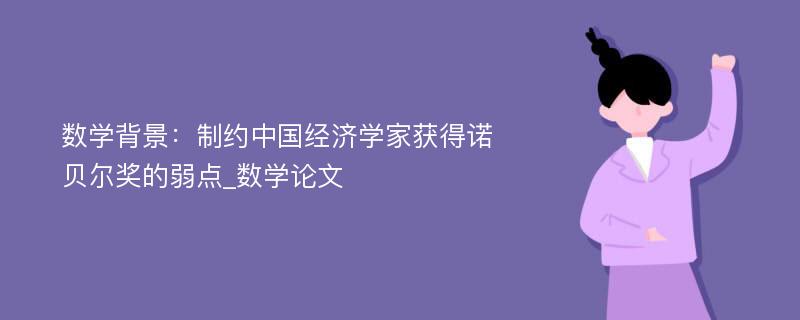
数学功底:制约中国经济学家摘取诺贝尔奖的软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软肋论文,诺贝尔奖论文,经济学家论文,功底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一直被国人引为骄傲,也令世人所瞩目。然而,中国为何不能产生牛顿、爱因斯坦?中国本土学者何时才能摘取诺贝尔奖桂冠?究竟是谁扼杀了我们的科学创造力?这些问题颇值得我们深刻地反思。在中国的经济学界,由于一种“诺贝尔奖情结”与“诺贝尔奖情绪”的长期并存、磨合及博弈,不仅折射出中国本土学者学术素养、学术风格、学术习惯以及思维模式、治学方法的某些局限或缺陷,而且也形成了一个“经济学悖论”。其具体表现形式是:一方面声称要鼓励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方面又对市场化、民营化、“经济人”假设、数学模型、数理统计等现代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学术范式和分析工具加以排斥,而统计经验告诉我们,后者恰恰正是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因素。它所凸现的是某些“理论的尴尬”。不管人们承认与否,中国经济学界客观存在的以环绕“诺贝尔奖情结”与“诺贝尔奖情绪”之惑为表象的悖论,几乎每时每刻都会令人尴尬与困扰;正是因为如此,才令人深思,令人不得不去深入探究。而对于这一“经济学悖论”的分析,无论对于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还是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摘取诺贝尔奖桂冠,无疑将是大有裨益的。
一、一些学者对经济学“数学化”的非议
在中国的经济学界,“诺贝尔奖情结”与“诺贝尔奖情绪”几乎同时存在。因而,出现以下悖论:一方面渴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获得诺贝尔奖;另一方面研究成果似乎又与获取诺贝尔奖的一些基本标准或要求相背离。比如,市场化、民营化、“经济人”假设、数学模型、数理统计等,乃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ABC,也是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但遗憾的是,我们的许多经济学家、理论权威,在改革开放实践冲破旧的理论禁区近三十年的今天,却仍然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或不屑一顾,甚至“坚决反对”。然而,同样遗憾的是,诺贝尔奖委员会对此却似乎不感兴趣。
中国本土学者中并存的这种“诺贝尔奖情结”与“诺贝尔奖情绪”及其悖论,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悖论(或二律背反),但它却是一个与学术问题紧密相关的悖论,我们姑且称之谓“准学术悖论”。这种看似“非学术的”悖论,却十分令人困扰。剖析这一悖论,从表象来看,它似乎只是涉及到学者们的学术兴趣以及对获取诺贝尔奖的兴趣高低或有否牢骚甚至浮躁情绪等;对于有志于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又对现代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不感兴趣甚至“坚决反对”者,它似乎有点类似叶公好龙或自相矛盾的典故。而顺藤摸瓜,进一步分析其深层的根源,恐怕与学者长期形成的某种思维定势有关。在经济学领域,人们对西方经济学的学术范式及“数学化”的方法,往往嗤之以鼻,或谈虎色变,甚至杯弓蛇影,总是习惯于将一些普世性的科学理论和分析工具妖魔化。似乎那些东西就是万恶之源,就是洪水猛兽。这些情绪化、非理性、欠科学的东西,且不说对获取诺贝尔奖会有负面影响,它对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也几乎是有害无益的。
上述由“诺贝尔奖情结”与“诺贝尔奖情绪”引出的悖论,犹如一个人对同一问题,一会儿举起右手说“坚决支持”,一会儿举起左手说“坚决反对”。当然,他并不是直接反对获取诺贝尔奖,就经济学而言,他反对的只是西方经济学的学术范式及“数学化”的方法(如市场化、民营化、“经济人”假设、数学模型、数理统计等),而从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作品统计分析结果看,这些学术范式和分析工具恰恰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的重要因素。这种“经济学悖论”,它所凭借的理论,看起来似乎无懈可击,天衣无缝,然而,将它置于“科学无国界”、“学术无禁区”、“全球化”的背景来科学理性地审视,其局限性或矛盾甚至荒谬之处则是不言而喻的。当人们蓦然回首,当虔诚而善良的人们一旦顿悟,也许会发出这样一种疑问:“我们的某些理论到底怎么啦”?!
当今世界,面临“全球化”浪潮,科学知识“数学化”的波涛不断地拍击着古老中国的学术海岸。但时至今日,在一些地方,反对经济学“数学化”的声音似乎司空见惯。在学术领域,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发展。然而,问题是,面对一些学者对经济学“数学化”的非议和批判,使本应宽松和谐的学术氛围似乎变得有点尴尬,令人费解。下面,请看几位学者“反对经济学‘数学化’”的有关论述:例如,尹世杰先生近期发表的文章题目就是《经济学应该“数学化”吗》。该文指出,“经济学决不能‘数学化’”,“反对‘数学化’的偏向”。文中甚至借用另一位学者的语言,称“一些人鼓吹经济学的‘数学化’”,“是伪学问”,“属伪学者”。[2]而何炼成先生则撰文认为,“数学分析和模型的构建太多”,是“数学教条主义”,“洋八股”。甚至对使用“产权”、“寻租”、“后工业化”等名词概念都不赞成。[3]
还有一位名叫余斌的学者,最近大胆地提出:“我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之所以称之大胆,倒不是说西方经济学不能否定,只是因为他用了“全盘”两个字。目前,从上到下都是讲的要“批判地借鉴”,而这位学者却要“全盘否定”。他还解释道:“以前的全盘否定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我的不是,我是基于学术逻辑来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的。我是学数学出身的,西方经济学大量使用数学模型,这些数学模型都是有问题的,西方经济学不是在运用数学,而是在糟蹋数学,西方经济学在学术逻辑上站不住脚”。他还指出:“西方经济学不可能成为指导中国人民取得更好境界的理论。我甚至嘲笑它说,它甚至连指导资本家发财都不合适。西方经济学家不是一个合适的会计,他们连资本家有哪些资产,应该怎样运作都不知道”。[4]
这位学者观点的偏激、武断甚至逻辑上的错误,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大家知道,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计量经济学中,几乎全是“大量使用数学模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成果,也几乎全是“大量使用数学模型”。但如果按照余斌先生的判断,“这些数学模型都是有问题的”,那么,其逻辑结论似乎必然是:计量经济学“站不住脚”,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成果“站不住脚”,所以,进而余斌先生向世人宣告:“我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
人们不禁要问:难道经济学“数学化”就那么可恶吗?据说,余斌先生等人号称“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不知他们是否知道,老祖宗马克思说过的那一句名言:“一种科学只有在能运用数学的形式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5]而从《资本论》中运用大量的(有的章节甚至满纸都是)统计资料、数学公式、表格、数据、符号,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学“数学化”的研究方法和表现形式,并不反对,甚至可以说颇为赞赏,而且应用自如。
在马克思时代,计量经济学尚未诞生,他所用的数学模型、公式、图表、符号等,远不如今天这样广泛、多样和深奥。尽管如此,它也足够令那些自命为“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反对经济学“数学化”的人汗颜。须知:“拍脑袋讲话”、“闭着眼睛讲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非理性、非科学的做法,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显然,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光靠“拍脑袋”、“耍嘴皮”是不行的。其实,对于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而言,虽然数学模型、数理统计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数学模型、数理统计却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可以说,推进经济学“数学化”的步伐,乃是经济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更应是如此。
二、“数学化”是一种科学精神和学术传统
不言而喻,经济学“数学化”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创新、完善的过程。它也是一种传统,一种理性思维、严谨求证的科学精神和学术传统。在西方,在科学界,在经济学界,理性思辨、数学思维、实验方法等科学精神,乃是渊远流长的。且不用追溯到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更不用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暨古希腊时代,仅就笛卡尔传统和培根传统而言,业已是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的;至于牛顿、莱布尼茨这两位科学巨人同时又是微积分发明人的治学精神及其理论和方法,乃至爱因斯坦精致的相对论以及原子结构理论,则更是影响深远。
被誉为“近代自然科学之父”的伽利略曾说:“数学是上帝用来书写宇宙的文字”。[6]有“数学王子”美誉的德国大数学家高斯则称:“数学是科学之王”。[7]而牛顿相信上帝根据数学原理设计了世界。莱布尼茨也认为世界是像上帝所计算的那样创造的。爱因斯坦则说:“迄今为止我们的经验使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大自然是可构想出来的最简单的数学概念的实现”。[8]在人类科学史上,正是数学把亚里士多德、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培根、康德、牛顿、莱布尼茨、爱因斯坦、史蒂芬·霍金(当代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宇宙学家)、贝塔朗菲(系统论创始人)、申农(信息论创始人)、维纳(控制论创始人)等闪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美国当代杰出的数学教育家、数学史学家、数学哲学家、应用物理学家M·克莱因指出:“具有奇妙的适用性的欧氏几何学,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超常准确的日心说理论的模式,伽利略、牛顿、拉格朗日和拉普拉斯辉煌、包罗万象的力学,在物理上不可解释但具有广泛的应用性的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爱因斯坦精致的相对论以及原子结构理论。所有这些高度成功的发展都依赖于数学概念和数学推理”。[8]不难发现,尤其在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两位科学巨人身上,深深烙印并折射出了数学的光芒。而这种数学与科学的相辅相存、相映生辉,可依稀追溯到古希腊文明。
这些公式被誉为“神仙写出的公式”。爱因斯坦甚至说:“任何充分理解这个理论的人,都无法逃避它的魔力”。[9]同自然科学领域一样,作为重要的分析研究工具,数学暨“数学化”如今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架构的方法论支点。在经济学领域,数学和统计学从来就是其基础的基础。而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理论的数学、科学支点,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笛卡尔、尤其是牛顿、莱布尼茨等大师。几乎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研究成果,除了建立新的数学模型,对经验统计数据进行科学的描述,其基本理论框架,似乎大多来自《国富论》这一市场经济理论宝库。的确,斯密所构筑的理论体系,乃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而从另一方面又看出:当代经济学研究“数学化”的创新,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我们知道,诺贝尔奖设立之初(1901年),只有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与和平5个奖项,直到1969年,才设立经济学奖。这一年,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朗纳·弗里希和荷兰经济学院教授扬·丁伯根,因为“使经济学有了数学的准确性,并给了它一定结构,从而使定量分析和对各种假设的数学证明成了可能”,[10]从而分享了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继而第二年(1970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则颁发给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获奖领域是“局部与一般均衡理论”,获奖成就是“运用科学研究方式发展了静态与动态经济理论,并提高了经济科学的分析水平”。[11]萨缪尔森是作为当代对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最有贡献的经济学家而获奖的。而他半个世纪之前撰写的巨著《经济学》,集当代经济学之大成,至今仍然风靡全球。他一直坚持认为,数学对于理解整个经济学起着最本质的作用。
自从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数学化、公理化的色彩更加浓厚了。数学模型、数理统计、公式、图表、符号等数学语言,在经济学中真正找到了用武之地。或许,正是因为现代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强的“数学化”,以至于给许多人的印象是:诺贝尔经济学奖是颁发给经济学界中的数学家的。而2002年,“一部根据荣获199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数学家John Nash(约翰·纳什)的传记拍摄的电影《美丽心灵》,获得了对公众影响更大的奥斯卡奖,更使人以为,原来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奖给数学家的”。[11]2005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则是奖给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罗伯特·奥曼教授及美国的托马斯·谢林教授,以表彰他们在博弈论领域做出的贡献。这是继199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的约翰·纳什教授、约翰·豪尔绍尼教授和德国的莱因哈德·泽尔腾教授之后,经济学家再次因博弈论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2]再看2006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亦由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摘取,他的贡献是“加深了人们对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费尔普斯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是一位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其数学功底深厚。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他与弗里德曼分别对当时盛行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统计学教授菲利普斯提出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提出了挑战,并提出了“费尔普斯曲线”。[13]而2007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由三位美国人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获得,以表彰他们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所作的贡献。“机制设计理论”也可以看作是博弈论和社会选择理论的综合运用。
据统计,从1969至2008年,在60多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他们几乎既是经济学家,同时又是统计学家或数学家。而其中有39位美国人获奖,占了将近2/3。这些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大多是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他们的获奖成果中,几乎都运用了大量的计量经济学模型。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我们的经济学、统计学及其定量分析,甚至还要越来越依靠计算机这个神奇的“电脑”去运算,令人们在“数学化”的基础上又加上“电脑化”。荣获197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如此赞叹:“45年前一名熟练操作员用台式计算器需3个月,用当时最先进的大规模计算机需40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一项多重回归分析,现在用电脑不到30秒钟即可完成了”。[14]不难发现,当今世界,经济学理论研究已日趋精密化、数学化、公理化、模型化。也就是说,对经济学家而言,提升经济学研究“数学化”的强度,与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并行不悖的。
三、中国经济学界的前沿正悄然与国际接轨
客观地讲,过去,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因不太懂数学,而拒绝数学模型、“数学化”,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国外一位统计学家直言:“不能计算的人才不愿计算”。然而,我们的一些学者,倘若自己“不能计算”,或“不愿计算”,却又反对别人“计算”,提出“反对经济学‘数学化’”,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有关诺贝尔经济学奖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先生讲过这样的一段话:“对于诺贝尔奖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我们要肯定它的意义。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在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方法或者技术层面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但是,诺贝尔奖从来不奖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诺贝尔和平奖只考虑奖给中国不同政见者。因为社会科学有意识形态性,评奖者有政治上的偏见,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因此诺贝尔奖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当然,如果我们有些学者的经济研究和理论,在不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这也不是坏事,但是我们不必追捧这个奖,更不能把它作为我们经济学教育的奋斗目标。因为对于中国经济学理论真正作出马克思主义贡献的人,一定是得不到诺奖的。”而关于经济学的“数学化”问题,刘国光先生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但并未提出对充分运用数学的非议。他指出:“数学在经济学当中只是一个辅助工具”。[15]显然,这些问题的确颇值得我们更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和深刻反思。
令人欣慰的是,如今,中国经济学界在经济学“数学化”方面,业已初见端倪。请看中国的几份权威性经济学期刊,近20年来,数理经济、计量经济、定量分析的论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现已蔚为大观。举最为权威的《经济研究》杂志来讲,过去几乎全是定性分析,全是文字性(或被称为“文学性”)描述的文章。而现在,则几乎85%以上的文章是定量分析。[16]如今,每当人们翻阅《经济研究》、《管理世界》、《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统计研究》、《统计与决策》、《预测》等杂志,几乎满纸统计数据、数学模型、公式、图表、符号。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先生在纪念《经济研究》创刊50周年笔谈中讲到:“今天的《经济研究》已越来越像一本真正的学术期刊了,……20年前,《经济研究》上很少看到数学公式,而今天的情况是很少看不到数学公式。……这正是中国经济学越来越成熟的标志”。[17]这里,给人们的信号或许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前沿,已正在悄然与国际接轨。较之于文字性(或“文学性”)描述,数学语言、公理化的表述,显然才更易于与国际学术界对话。而中国经济家的诺贝尔奖之梦,或许有望在这种科学理性的耕耘创新之中实现。
当然,再好的数学模型、再精确的数理统计也不可能是万能的,有时甚至难免出现误差,但它总比“拍脑袋讲话”、“闭着眼睛讲话”强一百倍!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东西羁绊着我们科学奋飞的翅膀?众所周知,自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开设伊始,“数学化”便是其评奖的硬条件、硬尺度、显规则。而必须正视,数学功底不深,“数学化”的强度不够或缺陷,乃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软肋。人们对市场化、民营化、“经济人”假设、数学模型、数理统计等西方经济学的学术范式和分析工具,似乎仍然心有余悸,相关分析研究往往着力不够,这些恐怕是构成中国经济学家难获诺贝尔奖的重要因素。如果我们纵有一些满腔的“诺贝尔奖情结”,却又有一些始终挥之不去的“诺贝尔奖情绪”:既不愿与国际主流经济学家交流、对话;也不愿接受国际主流经济学家通用的学术范式和分析工具;甘愿关在自家埋头苦干,自说白话,孤芳自赏,甚至于还批判人家的东西;或渲染存在文化差异、语言障碍以及所谓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而影响评奖的客观性、公正性,甚至强调那句“北欧的某些诺奖评委别有用心”。这样,“天上会掉下馅饼”吗?诺贝尔经济学奖恐怕不会“花落咱家”,相反,我们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距离甚至会愈来愈远。
四、结语
这里,有一点必须指出:中国人的智商之高,是举世公认的。也就是说,中国科学家、学者的个人禀赋并不逊色,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李远哲、崔琦、钱永健先生及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先生获取诺贝尔奖便是例证。中国中学生每年在国际数理化奥林匹克赛中频频夺冠,更令世人瞩目。而勿庸讳言,个人智商以外的种种因素的差距(包括某些“情绪化”的东西),恐怕仍是影响中国本土学者摘取诺贝尔奖桂冠的无形障碍。当然,全球学术界的“马太效应”亦是难免的客观存在,但它也并不能成为影响或窒息我们创造性思维的一种托词。从技术层面讲,要获取诺贝尔奖,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及医学这些“硬科学”,较之于经济学、文学,难度要高得多。但从美籍华人学者的获奖来看,凭中国人的智商,是不怕“硬科学”之难的。相对而言,经济学以及文学,本应更有可能去问鼎诺贝尔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和作家较之于科学家,却似乎离诺贝尔奖还相当遥远。
总之,在学术界,发现悖论,分析和研究悖论,有助于促进学术的繁荣和科学的发展。许多貌似科学的理论(实属悖论),在未被发现和指出其弊端之前,曾盛行一时,但后来终究被人们所“识其真面目”。本文所指的因“诺贝尔奖情结”与“诺贝尔奖情绪”形成的“经济学悖论”,本身所承载或依托的理论背景,似乎难以经受严格的逻辑推导。当然,若要识其“庐山真面目”,还需要人们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和探寻,并需要借以唤起人们蕴藏着的科学理性精神的进一步觉醒。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恐怕还在于:作为经济学家,必须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者风范,同时,也要挥手告别那些浮躁的、非理性的“诺贝尔奖情绪”。并且,套用一种时髦的表述,就是要“将数学模型进行到底”,“将‘数学化’进行到底”。否则,中国的经济学家或许将永远与诺贝尔奖无缘。请想一想,当今世界,有哪位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不精通数学、不精通统计学?又有谁见过没有数学模型的经济学成果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呢?目前,尚须进一步营造能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茁壮成长的更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和土壤。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当今中国是一片经济热土,它亦呼唤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诞生。
标签:数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诺贝尔论文; 数学模型论文; 诺贝尔经济学奖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数学中国论文; 经济论文; 西方经济学论文; 数学素养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科学论文; 诺贝尔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