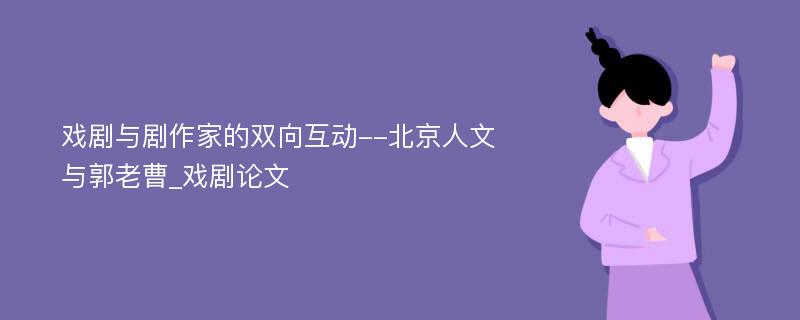
剧院与剧作家的双向互促——北京人艺与“郭、老、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作家论文,剧院论文,北京论文,双向论文,人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剧院为出戏出人,到处寻觅好剧本,但是好剧本实在难求,话剧尤甚。戏剧主管部门以及话剧院、团为了争取水准较高的剧本,不借在全国“高价悬赏”。以前总觉得剧本稿费太低,演出酬金菲薄,因而作家对写戏的热情日益降温。现在祭起“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个屡试不爽的老法宝,有的地方、有的剧院一旦采用剧本,就付上万、几万元稿费,上演之后,还可提成,如果一台戏能演出几十、上百场,而且上座不错,作者可得到几万、十几万元。这价码与一次卖断的畅销书以及动辄几十集的电视剧的稿酬还没有多少可比性,但在戏剧圈来说,已经是破天荒的了。以我愚见,写一出戏若能收取几万、十几万的回报,从以诚实的劳动收取合理的报酬来说,这已经是很可以的了。但是即便有这样的“重赏”,好剧本依然比晨星还要少。从各征集点的情况看,应征的剧本数量为数不少,但主要是二、三流剧本在“流传”,上品位的好作品极少极少。这是为什么?窃以为要从编剧队伍萎缩、人才流失、技能退化上去找原因。如今的戏剧创作队伍,老一辈因亡故、病痛,基本上连硕果仅存都难说了;中年编剧队伍中,确有一些精英高手,有的在为戏剧苦苦耕耘,也有相当一些为“挡不住的诱惑”所苦,他们的电脑贮存库里,诸如电视连续剧等“当令紧俏”之作,已把戏剧作品挤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这也无可厚非,“写什么和怎么写是作者的权力”,我只是为戏剧叫苦罢了)。即使出了几个好戏,也是僧多粥少,供不应求。编剧队伍中更多的是热情有余而经验或素养尚未老到丰盈的新手,可是戏剧恰恰是所有文学样式中最困难的样式。如此,好剧本难出、难觅,当是意料中的事情。从戏剧的历史轨迹来看,由于创作与演出处于互依互存的关系之中,剧作家哺育了剧院,剧院反过来又培植了剧作家,所以历来许多戏剧大家,许多经典剧作,都是在剧院团的培育、扶持、帮助下受到激励而产生的。没有莫斯科艺术剧院就没有戏剧家契诃夫;没有法兰西喜剧院,莫里哀可能就无从谈起;莎士比亚也是为他的剧院写戏而成为莎士比亚的。所以谈大剧作家的出现和戏剧佳作的产生,要从两方面看,一是从创作队伍看,同时也要从剧院、团这方面看。本文不想冲着戏剧创作队伍发议论、发感慨,而是想从伸手索取剧本的剧院、团这一方探个究竟。因为工作关系,最近常翻检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材料,重温这个当年被称为“郭(沫若)、老(舍)、曹(禺)剧院”的艺术殿堂是如何得益于这些戏剧大师,同时他们又是如何以自已的高超艺术眼光和精* 的演出,促发、催生和帮助这些大师写出一部部不朽名作的历程,这对剧院团如何抓创作,如何催生佳构力作大有参考价值。空说道理不如摆事实,所以本文采取史料钩沉的写法,提供大家了解当代话剧史上这一段已经过去了的辉煌,以达温故而知新的目的。
人们过去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郭(沫若)、老(舍)、曹(禺)剧院”,这是一种十分简约、高度概括的说法,这种说法反映了这几位戏剧大师与北京人艺之间非同寻常的紧密的关系。这是一种双向互动、互相促进,甚至可以说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在北京人艺头十年的演出剧目中,郭、老、曹的戏共有16个,从数量来说,约占演出剧目总数的20%。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更重要的是这些剧目大多数成了人艺的看家戏,每年反复上演,久演不衰。正是这些大师的力作哺育了北京人艺,北京人艺通过演出他们的作品形成了剧院的风貌,而这些大师的剧作也正是由于北京人艺精心的舞台创造而发出夺目的光辉,他们本人因此受到激励而迸发出新的创作活力。北京人艺和这些大师在创作上的双向互促,形成了我国话剧演出史上最辉煌的景观。老戏剧家刘厚生先生曾这样说:“由于他们都是建国前久已成名的剧作家,我们当然应该说,是他们的作品哺育了北京人艺,形成了北京人艺的面貌,没有他们就没有北京人艺;但是,我们也有理由说,正是因为有了北京人艺这个剧院,这个长期合作的集体,才‘挤’出了老舍的《茶馆》、《女店员》,曹禺的《胆剑篇》(还有后来的《王昭君》),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田汉的《关汉卿》这样的大作……我们可以大胆地说,除了别的客观和主观条件之外,是北京人艺的演出实践推动、促进了几位老剧作家登上了一个新台阶,甚至是自己创作的高峰。”他的说法非常明快而确切地表述了北京人艺与这些大师为代表的作家群的关系,这已经成为流传久远的佳话,而且为剧团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郭沫若是我国著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历史学家、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又是以其历史学家和豪放诗人相兼而独步于剧坛的历史剧作家。他的历史剧解放前曾广为演出,产生过强大的战斗作用。解放后,郭沫若是我国科学文化的重要领导人,忙于政治、外交和社会活动,无暇顾及历史剧创作。1956年4月,北京人艺决定排演郭沫若抗战时期所写历史剧《虎符》。这年春季,周恩来总理在观看昆剧《十五贯》以后,曾在文化部和中国剧协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指出:《十五贯》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值得话剧界学习。他说:“我们的话剧,总不如民族戏曲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中国话剧还没有吸取民族戏曲的特点。”显然,周总理的见解引发了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特别是总导演焦菊隐的共鸣。焦菊隐亲自执导《虎符》,他在这个戏的排演中,进行了话剧体现民族风格,向戏曲艺术传统学习的实验。次年1月31日,《虎符》演出,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戏剧界一致肯定《虎符》所作的尝试,虽然还不尽善尽美,但是它为中国话剧的民族化走出了一条新路子。郭沫若几次观看《虎符》的连排和公演。郭沫若高兴地说:“整个地说,作为作者,我感到光荣!焦先生改得好,夷门桥一场有南画风味,处理得好。省略与增加都是恰到好处。”郭沫若还夸赞这个戏“演得好,处理得好,布景、灯光、效果都好,剧本改得好,导演的手法点石成金”。显然北京人艺领导和艺术家们的胆识、艺术功力和创作作风,激发了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热情。在观看《虎符》连排之后的第二天,即1956年10月13日,郭沫若邀请《虎符》剧组游颐和园,在长廓漫步时,北京人艺的同志请郭沫若给剧院写一个新戏。郭沫若虽然当时没有许下保证,但是到1959年初,他仅用7天时间,写了五幕历史剧《蔡文姬》,他主动提出此剧供北京人艺排演,并要求由焦菊隐执导。为此剧的排练做准备工作期间,郭沫若亲临剧院介绍时代背景和创作意图,他还亲自到剧院朗读剧本。他由衷地说:“感谢大家,曹禺同志和剧院的同志给了我不少鼓励,要我写这个戏,现在剧本出来了,成不成还不敢说。”这部新作具有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独特个性与风格,他毫不隐晦地宣告:“蔡文姬就是我……其中有不少我的感情的东西”,“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郭沫若在多次观看排练时,一再表示:“写这个戏时,我是动了感情,流了不少泪的,但是,这个戏行不行,还得请大家多提意见。”这不仅仅是郭沫若的谦逊,也反映了他对北京人艺的信赖。事实上,《蔡文姬》边排边修改到最后完稿,北京人艺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
郭沫若的《蔡文姬》剧本出来后,有关文化领导部门及戏剧界的几位著名人士在总体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意见。这些意见可归纳为以下三点:①对曹操的歌颂有些过分;②台词中现代语汇太多;③涉及民族关系的问题应再慎重考虑。意见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指示“戏要演出,但要改一改”。由于郭沫若要出国访问,总理指定先由北京人艺提出修改方案。人艺提出修改稿后,送田汉、阳韩笙审阅加工,待郭老回国后由周扬征得他的同意后定稿。
焦菊隐和《蔡文姬》剧组负责人及主要演员参考各方面意见,对《蔡》剧作了修改。
郭沫若回国后,对《蔡》剧改稿仔细斟酌了几遍,认为“改得很好”。他在感谢信中肯定了几处他认为改得好的地方,有两处他认为增加得不够妥当,维持了原稿中所写的。
北京人艺不仅在《蔡文姬》剧本修改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以焦菊隐为首的艺术家们,对排演《蔡》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提出要使这个戏“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达到深刻完美的境地”。该剧经过精心排练,公演后引起很大的反响,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文化艺术界负责人及戏剧界的专家名流,都热烈赞扬此剧,认为演出传达了郭沫若作为诗人剧作家的浓烈情感;导演在话剧民族化上做了进一步开创性的工作,学习民族戏曲传统比《虎符》更纯熟、更深化、更和谐了;演出气魄很大,富有诗情画意,气象瑰丽,舞美有独到特点,演出精湛。此剧当年演出达120场,并成为北京人艺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郭沫若对《蔡文姬》的演出十分满意,他曾对焦菊隐的导演处理作了高度的赞美,曾对他说:“你在我这些盖茅草房的材料基础上,盖起了一座艺术殿堂。”
1959年11月5日,曹禹、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给郭沫若写信,祝贺《蔡文姬》演出100场,信中谈到《蔡文姬》上演以来,以其磅礴的诗情风靡了首都观众,100场演出的上座率一直保持在107%以上的空前记录,这是剧院的盛事,也是首都剧坛的盛事。信中希望郭老再写新戏。郭沫若写了热情详溢的复信。由于受到《蔡文姬》成功的激励,郭沫若很快又写了一部历史剧《武则天》,郭沫若通过武则天打击裴炎阴谋篡位的事件,为历史人物武则天翻了案,并且对从隋朝到初唐几百年里屡屡发生不顾百姓死活的大臣篡位的历史现象作了批判。北京人艺1960年2月就接到《武则天》这个本子,6月开排,由于种种非艺术因素的影响,此剧改改排排,停了又排,排了又停,直到1962年6月29日才得以公演,表现了北京人艺对一个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锲而不舍的坚毅精神,特别是以焦菊隐为首的艺术家,通过博大精深的研究,分析了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总体风格,以及《武则天》这个戏独具的特色,使郭沫若这出戏再次成为辉煌的舞台杰作。
郭沫若是我国创作最早、影响最大的历史剧作家,但是其创作高峰恰恰是《蔡文姬》、《武则天》这两部戏。而这两部戏的诞生与北京人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北京人艺与老舍之间所建立的则是另一种更为亲密、更为新颖的关系,用老舍的儿子、中国当代文学馆副馆长舒乙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互相尊重、互相信赖、互相学习、互相支持的关系,这里凝聚着友情、崇敬、体贴、关切,对创新的追求,对新高度的渴望和艰苦的探索与实践”。
老舍是我国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和曲艺作家。解放初他的力作《龙须沟》由于北京人艺的上演而珠联壁合,名噪一时,而后北京人艺又上演了老舍为他们所写的《青年突击队》、《春华秋实》、《红大院》、《女店员》和《茶馆》。老舍熟悉北京市井生活,他的富有北京文化特色、浓郁京都生活气息和民族传统特色的戏剧作品,对造成北京人艺擅长演“京味话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龙须沟》的成功,老舍获北京市颁发的“人民艺术家”称号。《茶馆》的演出则把中国话剧推向高峰,并且使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向世界,载誉全球。在催生这些名作的诞生以及创造中国话剧演出史上的辉煌业绩方面,北京人艺功不可没。老舍与北京人艺的关系诚可谓相得益彰。
老舍先生1948年赴美讲学,1951年回国不久,即应北京人艺之邀,写了话剧《龙须沟》。当时还是“老人艺”时期,院长由当时任北京市文委书记的李伯钊兼任。李伯钊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主张剧院要“五湖四海,团结作家;古今中外,兼收并蓄”。时值建国不久,全国人民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经济恢复运动,当时北京市市长彭真提出写一出反映城市建设面向基层市民的戏。他把这个建议作为重要提案在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提出,形成决议后,委托李伯钊 贯彻实施。李伯钊很有魄力地决定请刚从美国回来的老舍当此重任。老舍先生熟悉旧北京市民的生活,但对解放后的变化还不了解,李伯钊 亲自将治理龙须沟的施政计划交给老舍先生。老舍先生有感于人民政府关心人民疾苦,新旧社会两重天,激发了创作热情。但是他有腿疾,不能过多地亲自到龙须沟去考察和采访,于是北京人艺动员演员深入生活,这一方面是为演戏做准备,同时也是为了替老舍收集、提供大量生活素材。老舍曾以感激之情表扬演员,说“演员们体验生活深入细致且形象,把我的一双脚变了几十双脚”。
为了保证使演出具有高水平,李伯钊请当时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西文系任系主任的著名戏剧家、翻译家焦菊隐担任《龙须沟》的导演。焦菊隐在这出戏中实现了他的现实主义戏剧的理想,并且表现了丰富的导演经验。著名表演艺术家、原北京人艺副院长于是之认为是“《龙须沟》奠定了北京人艺的现实主义基础”。
老舍在《龙须沟》中用的是“一片生活”的写法,这种结构文学性很强,推向舞台,有时会觉得“散”而难以“出戏”。北京人艺很尊重老舍,老舍也很尊重、信赖北京人艺以焦菊隐为首的艺术家们。他曾对焦菊隐说:“是杀是砍,全交给您了,台上怎么合适就怎么弄吧!”焦菊隐执导《龙须沟》时,保留了剧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及大部分台词。但在结构上做了大调整,有的地方删一点或加进一些对话或穿插。《龙须沟》演出获得巨大的成功。为了尊重北京人艺艺术家们的创造性艺术劳动,老舍提议《龙须沟》出版两种版本,一是作者原著《龙须沟》的文学剧本,再是北京人艺的演出本。后来果然这样做了。而今人们可以从这两个版本里看到老舍剧本文学创作的独特魅力,也可以从另一版本中领略北京人艺艺术家们的智慧,特别是焦菊隐的、老舍赞为“化石成金”的导演手法。
《龙须沟》的成功奠定了北京人艺与老舍的互相信赖和亲密合作关系,此后不是北京人艺向老舍出题“定货”,便是老舍有了新作主动供给剧院。碰到要写现实生活题材的戏,北京人艺总是大力帮助老舍收集素材,寻找采访对象,找到“典型”之后,剧院的人便陪同去访问、参观或开座谈会。进入写作阶段后,老舍每写出一幕,便找北京人艺的人去听他朗诵,然后听由大家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老舍则从其善者而修改或润色之。老舍称这种创作方式为“民主剧本”。他说,这是他“久以追求的写作方式,解放前,靠写文养家,生活清苦,不能这么办;现在,终于得以实现,欢欣之至”。老舍以后给北京人艺的几部戏,都是以这种“民主剧本”方式创作而成的。
老舍不仅以《龙须沟》奠定了北京人艺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而且以其另一部不朽名著《茶馆》把北京人艺推向演剧的高峰,谱就中国解放以来演剧史上的光辉篇章。早在演《龙须沟》的时候,其中一个场面是龙须沟在暴雨来临季节,臭水泛滥,居民搬到位于高处的一家茶馆躲避。在焦菊隐的导演处理下,这一场面排得非常热闹好看。老舍就中看到了北京人艺导、表演的“能耐”,想日后专门给他们写一出在茶馆里演的戏。不想此念却成了后来不朽名著《茶馆》的创作动因之一。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老舍也很激动,想写一个话剧来歌颂宪法所制定的合法公民的普遍选举权(简称“普选”)使中国人民真正能当家作主,行使民主的权力。1956年8月,他果真写出了这个剧本,还没来得及起剧名,就拿着初稿,来到北京人艺,读给曹禺、欧阳山尊、赵起扬、刁光覃、夏淳等人听。这个剧本从戊戌变法写起,一直写到解放后剧中的主线是主张实业救国的秦仲义一家,其中第一幕就发生在清朝末年北京的一家茶馆里。曹禺等人听了剧本后,一致认为第一幕茶馆里的戏写得生动精彩,后几幕戏写得不理想。他们研究后认为可以把第一幕作为基础,发展成一个戏,因为通过茶馆这样一个四方杂聚之地,是能够反映社会的历史变迁的。曹禺、焦菊隐、赵起扬带着这个想法,来到老舍家里。老舍听后立刻表态说:“好!这个意见好!我3个月后给你们交剧本!”
果然在3个月之后,这个名之为《茶馆》的剧本有了着落。北京人艺领导和艺术委员会在首都剧场前厅二楼聆听老舍亲自朗读《茶馆》。读完第一幕曹禺就预言式地赞叹:“这能出一部警世之作”,“够古典水平”。事后,北京人艺艺委会专门开会研究,一致认为第一幕很精彩,后两幕尚需进一步加工修改。会后,由副院长欧阳山尊到老舍家中,谈了人艺艺委会对剧本的意见,建议对第二、三幕再作加工。老舍欣然接受意见。由于第三幕是写解放前夕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时的情景,当时老舍远在美国,对国内情况不熟悉,老舍希望对这一幕大家帮助出主意。此后历经不断修改、不断听取意见的过程,时至1957年年底,新改本三幕话剧《茶馆》终于完稿。这年12月2日,老舍再次踏上首都剧场前厅二楼,向人艺全体演员朗读剧本。读完剧本,《茶馆》导演之一夏淳宣布演员开始申请角色。经过角色认定,剧组立即开始体验生活和准备排练工作。与此同时,《茶馆》剧本在《人民文学》发表,立即引起巨大社会反响。12月19日,《文艺报》为《茶馆》召开座谈会。会上,焦菊隐介绍了《茶馆》创作历程及初步导演构思。出席会议的林默涵、赵少侯、陈白尘、王瑶、张恨水、李健吾等文艺名家都给《茶馆》以高度评价。当时中国作协领导人之一、著名戏剧家陈白尘认为此剧“是老舍同志在写作上的重大收获,才三万字,就写了50年70多个人物,精炼程度真是惊人!”林默涵认为:“现在很需要这样的剧本。老舍同志是通过对旧社会的批判,表现了他热爱新社会,才对于旧社会有更深刻的憎恨。观众,特别是年轻的观众看了这出戏,会更加爱护今天的新社会。”
虽然大家对《茶馆》给予很高评价,但是,经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接着“大跃进”的鼓声开始响起,政治上的“左”必然导致文艺思潮上的“左”,此时此际把《茶馆》推向舞台,已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还是投排了《茶馆》。此剧于1958年5月首演,连演49场,反响热烈。到7月10日,当时文化主管部门某负责人严厉批评了北京人艺的剧目路线,特别点名批了《茶馆》。就在他讲话的当晚,老舍和梅兰芳陪同苏联专家彼德罗夫看完《茶馆》的演出后,《茶馆》的第一轮演出就此偃旗息鼓。
《茶馆》的演出一搁就是4年,到1963年,文艺出现宽松气氛。北京人艺没有忘记这出戏,这年1月5日,决定重新整理、复排《茶馆》。由于当时匆忙停演,连排演的资料和场记都没有。北京人艺决定成立一个整理小组,凭大家的记亿拉出当年演出的大样,然后再请焦菊隐细排。4月7日,《茶馆》再度出演。但此时大演现代戏之风随着反右倾运动的加温而日益强劲,北京人艺已经接到要用90%力量抓现代戏的指令。所以《茶馆》再度公演不久,有的好心人为北京人艺捏一把汗。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军旅演员蓝马私下里告诫北京人艺:“现在是什么时候啦,你们还敢演这样的戏?!”北京人艺依然“顶风”演出《茶馆》,但心总像是“悬”着似的。直到这年7月7日,周恩来总理特意来看《茶馆》的演出,对这出戏在政治上、思想上、艺术上给以明确肯定之后,北京人艺的上上下下才算松了一口气。这一年《茶馆》共演出53场。
时至1964年,迫于形势,北京人艺当年演出剧目单上,全都是现代戏了,《茶馆》就此无疾而“终”。直至“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北京人艺抹去岁月的尘封,在老舍诞辰80周年之际,于这年3月中旬,恢复上演《茶馆》。这次演出阵容如旧,但老舍先生和导演焦菊隐先生却已蒙冤作古。3月19日,新华社作为我国重大文化现象,对外播发了《茶馆》重新上演的消息。直到此时,中国才真正认识《茶馆》的价值,国际文化界也才注目这颗夺目的东方戏剧名著。中国话剧由《茶馆》而登上国际舞台,戴誉三大洲。北京人艺终于以自己伟大的艺术贡献,告慰了老舍先生及焦菊隐先生在天之灵。
北京人艺的院长一直是戏剧大师曹禺,北京人艺建立之后,所演的第一出“五四”以来优秀剧目就是曹禺的《雷雨》,这在当时是敢为天下先的创举。此后接连演了曹禺7部戏,除了个别剧目以外,都是精美的演出。曹禺的戏培养了北京人艺几代导演和演员。在人艺排曹禺的戏最多的是著名导演夏淳,他曾说:“曹禺大师的剧作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培育演员的沃土,是使演员成长的温床”,“我们剧院建院以来前后演过曹禺同志7个剧本,他的剧本不仅培养出了众多的演员,更重要的是奠定了剧院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剧院的美学追求。”北京人艺的确是曹禺剧作的最大受惠者,但是我要说北京人艺也最热爱、最理解他们的老院长曹禺和他的作品,并且也是他的剧作的最有力的支持者。
解放初期,由于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也可以说是迫于无形的压力,曹禺曾修改并出版了贯穿阶级斗争学说的《雷雨》新改本。1953年北京人艺决定上演《雷雨》时,经过郑重研究和讨论,决定按照原版本上演《雷雨》。这是何等有胆有识之举。他们没有发表宣言,说明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但是他们的行动说明他们对艺术的忠诚和对自己老院长艺术珍品的竭诚保护之心。曹禺先生接受他们的选择,他没有说什么,我想他心里是感激和欣慰的。请记住,当时是1953年。以后,人艺又排了《北京人》、《日出》等曹禺剧作,当时看这些戏的演出,是要隔夜站队才能买到票的。在排这些戏的时候,剧院内外,都有一些“左”的非议,人艺的领导核心和艺术骨干,都顶住压力,保护了曹禺原作的艺术完整性。在排《蜕变》时,由于剧中主要人物以抗战时期政府官员中爱国人士身份出现,因而引起当时有左倾幼稚病的一些人士的大哗,认为必须进行大改才能演出。北京人艺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顶住压力,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忠实于原著,精心排演了此剧。曹禺解放后所作的话剧有三部:《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这些新作悉由人艺演出。人艺对这些新作的诞生都是出过大力的。《胆剑篇》是曹禺与于是之、刁光覃合作而成,《王昭君》是曹禺应周恩来总理之请而写,“文革”前只完成了第一幕,“文革”之中曹禺身心备受伤害,但他谨守承诺,矢志完成此作。但是如果没有北京人艺的一片赤诚的艺术家的协力帮助,曹禺未必能如愿以偿。曹禺先生多次在文章和言谈中,流露出对北京人艺的同事们的深厚感情,他与人艺的毕生合作,恐怕是他一生事业中最欣慰的纪念。
对以上中国演剧史熠熠生光的一隅的回顾,是想说明剧作家(即使是大师级的作家)和高素养的剧团之间的双向互促。这种互促互惠,正是产生大剧作家和高水平演出、培养大艺术家的温床。而今物是人非,剧作家和戏剧团体的人文际遇、生存环境、价值观念,已与昔日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任何时候,真正的不朽的精神产品、艺术杰作,只能在一片赤子之心,一腔至诚之情,一股高山仰止的艺术企求,一种宁静致远的氛围,一种无私虔诚的精神驱动中才能产生。以上追述,不仅让我们看到剧院与剧作家的精诚合作,而且看到融贯其中的艺术家的可贵的心地、精神和情怀。
标签:戏剧论文; 话剧论文; 焦菊隐论文; 曹禺论文; 龙须沟论文; 茶馆论文; 曹禺现象论文; 北京演出论文; 艺术论文; 剧院论文; 武则天论文; 老舍论文; 雷雨论文; 蔡文姬论文; 历史剧论文; 曹先生论文; 中国电视剧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智利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