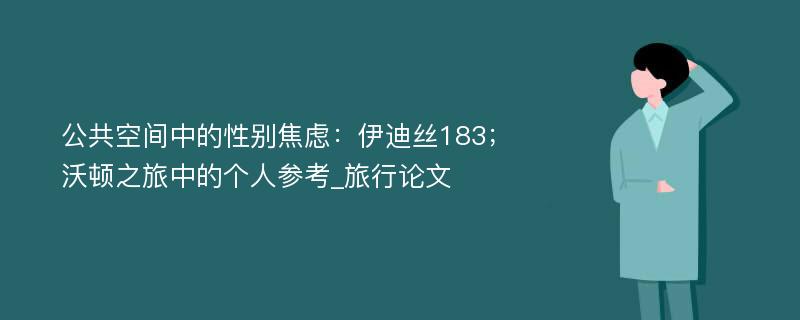
公共空间中的性别焦虑——伊迪斯#183;华顿游记中的人称指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称论文,焦虑论文,迪斯论文,游记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三四十年以来,游记作品研究吸引了西方学术界众多学者的目光。在2002年出版的《游记作品剑桥文学指南》“前言”部分,主编彼得·休姆和蒂姆·杨斯写道:“游记已在近年来崭露头角,成为人文社科领域的关键词,相关的游记研究数量之多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文学、历史、地理和人类学等学科均克服了先前那种轻视游记的心态,开始大量推出跨学科研究成果,使得这一文类的历史复杂性得到了充分展现。”①游记作品研究常常和文化、历史、地理、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以学科交叉的优势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内容。
随着后现代思潮在各个学术领域的不断渗透,人们对于游记的认识和研究逐渐丰富起来。游记不再只被看成一种实用性游览手册,更是一种文化文本,处处显露出作者对世界的观察和阐释。在游记“客观”描述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作者对自身、对他人、对各种文化现象的思考和探讨。同时,在对异域他乡的描述中,不同性别的游记作者把不同的社会要求和性别意识投射在各自的文本之中,在丰富游记写作的同时也使游记作品变成了一扇扇丰富多彩的文化窗口,生动形象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性别关系。
一、旅行与性别
从字面看,“旅行”指的是从一地到另一地,从一个熟悉的环境变换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它不仅隐含了“自由走动性”(mobility)和冒险性,而且常常和“闲暇”、“异国情调”等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这种无羁无绊的自由走动似乎是男性的特权。例如,兴起于1660年左右的英国贵族子弟“欧陆游学”(Grand Tour)就主要是“为了让男人受教育”②,让他们能够“浸润在欧洲大陆宝贵的艺术品和使人变得高贵的社会之中”③。女性则一般被排除在这种奢华教育的范围之外。外出旅行、寻求冒险、增加阅历、丰富知识似乎成了西方男性的特权;而家的概念却总是和女性连在一起。正如罗兰·巴特所言,“纵观历史,女性是缺席话语的承载者:女人静坐家中,男人狩猎远征;女人忠心耿耿(在守候),男人变幻无常(远航而去,漂洋过海)”④。
尽管旅行的概念在传统意义上浸透着男性中心主义的意味,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女性旅游者的足迹也同样踏遍了世界各地。不论是作为勇于冒险的探索者,或者是跟随家人远涉海外的“偶然旅行者”⑤,还是殖民时期被派送到殖民地为白人男性服务的中下层西方女性,外出游历对于女性来说意义重大。对于那些被长期羁绊于家庭的女性而言,她们的视野和认识范围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局限,因而,“社会对于性别、种族、阶层的一些观点和看法要不就是被遮住了,要不就是她们视而不见”⑥。外出旅行,尤其是出国旅行能够使女性走出视线受限的私人空间,进入通常由男性主导的公共空间,而这种空间的转化使她们能够看清社会加上女性身上的种种限制,从而能够在比较之中更加清晰地认识自身和世界。
美国人外出游历的时尚始于十九世纪前半期。由于其特定的历史渊源,当时的美国人一般把远行目的地定在欧洲大陆。如果说早期的美国游客仅限于少数上层人士的话,航海技术的提高使得赴欧人数逐年增加。据记载,“十九世纪中期,横跨大西洋的游客已从一年五千人增加到两万五千至三万人左右”⑦。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成熟的航海技术、简便舒适的设施以及更低的旅行费用使得相当一部分美国人能够走出国门,到欧洲大陆观光旅游。在这大潮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新型女性旅行者。她们“有独立的生活来源,独立的思维,像同时代的某些男性一样渴望通过旅行拓宽知识面和自主活动范围”⑧。对于这些具有独立精神的女性而言,旅行不仅仅标志着远离家庭的束缚和限制,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感受异地的文化和自然氛围。更主要的是,在跨越地理边界的同时,她们挑战了社会对女性设置的种种性属边界,在新的环境中积极行使自主权和自决权,充分锻炼自己独立观察和思考的能力,建构自己的种族与性别身份,并以批判的目光对故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
国外旅行拓展了女性的视域,给女性带来了新的思维模式,也带来了女性游记作品数目的增加。据统计,“从1830年到二十世纪初,美国作家出版了1765本关于国外的游记。在这些出版物之中,女性作者达195人,其中只有27本是内战前出版的”⑨。不过,在通过游记书写自我的过程中,很多美国女性在文本中显示出一种微妙而尴尬的处境。一方面,她们渴求新的生活方式,希望能够摆脱社会强加在她们身上的性别羁绊,另一方面,多年来内化于心灵深处的性别意识又让她们身不由己地遵守社会规则,在抗争和妥协中获得一种奇怪的平衡。伊迪斯·华顿(1862-1937)是一位独立批判意识很强的女作家,但是性别因素在她的游记中依然有着很明显的影响作用。
二、消隐的女作家身份
华顿与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是同时代人。他们有着相似的社会、文化和家庭背景,过从甚密。两人都出生于美国中上层社会,幼年时跟随父母往返大西洋两岸,接受欧洲文化与艺术的熏陶。成年之后,他们又都选择在欧洲居住,并在感受欧洲文化的同时,把各自的印象和看法付诸笔端,为后人留下了风格鲜明的游记作品。詹姆斯1907年最后一次游历法国就是由华顿夫妇陪同的。他们一起参观了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故居,一起“探访了房子的一层,观看了乔治·桑著名的木偶戏,然后在花园里漫步”⑩。华顿和詹姆斯都著有关于法国的游记作品(11),去过一些同样的地方,在一些事情上持相同的观点,但两人在游记文本的叙述策略和人称指代上却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翻开华顿1908年的游记《穿越法国》(A Motor-Flight Through France),我们会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书中很少见到第一人称代词“我”(I)。这似乎有点奇怪。按照常理,游记记载的是作者在各地旅游的经历,它是作者面向大众的最直白的表露。读者在这样的作品中应该很容易觅到作者的踪迹。然而,在华顿的游记中,我们却基本感觉不到“我”的存在。在她的游记文本中,主体“我”(I)和其视觉媒介(eye)之间有一种断裂,横亘在二者之间的是一些让作者个体形象变得模糊的人称指代和委婉的措词。
“汽车带回了旅行的浪漫”——华顿的《穿越法国》这样开头。接下来的第二句话是,“它使我们免除了火车的限制,不用和火车打交道,不必恪守固定时间固定线路,不需穿越火车沿途的丑陋荒凉地带就能前往每一个小镇,它带回了曾让我们的祖父母旅行之路熠熠生辉的奇迹、冒险和新奇”(12)。在这句话中,华顿用“我们”这一集体称谓面对读者。她以“我们”的口气说话,提到的是“我们的祖父母”,这里面没有突出她本人作为名作家的骄傲与自豪。相对于华顿当时的名声和影响而言,这似乎有些太过谦逊。事实上,华顿在出版《穿越法国》之前已在当时的欧美文坛有了相当的名气。她1905年出版的小说《欢乐之家》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成功”(13)。1905年10月14的第一版卖了4万册;10月30日又加印2万册,十一月再次加印2万册;及至当年年底时已达14万册(14)。如果用今天的商业术语来形容的话,华顿是当时无人不晓的畅销作家。对于这样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女作家,她应该大大方方地直面读者,让读者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
细读全书,我们会发现,华顿一直尽力隐去作者“我”,将自己淹没在众人的影像之中,用众人的投影遮盖自己的身形。途经法国的卢瓦尔河(Loire)时,华顿不是突出自我感受,将自己眼中的河道美景再现于读者面前,而是把自己藏在复数的人称代词“我们”(We)的后面谦逊陈辞:“那一天当我们沿着卢瓦尔河弯曲的河道前行时,我们当然收获了很多:宽阔稳重的水流让人感受至深,两岸景色宜人,繁茂的花园和葡萄园构成道道风景,给人以甜美的平整感,呈现出精心耕作但又稍显平淡的社会……”(15)类似的叙述方式书中随处可见。事实上,华顿不仅在描述法国美景时将自己隐于“我们”的影子之中,在发表自己看法时也尽力不露痕迹。在游记的第三章,当华顿一行人在塞纳河沿岸驱车前行时,路上经过的一个古迹让她感慨颇深:“啊——可怜的破残的飘摇于风中的古迹,如此单薄,如此的岁月印痕,如此多的风暴和地表侵蚀留下的谜团,立在岩石之上垂首的它好像是一面破败的旗帜,皱褶之中写满了被人遗忘的胜利!比起那些漂亮整齐的风雨不蚀的城堡——皮耶枫(Pierrefonds),郎热(Langeais)等等——,这些摇摇欲坠的石头多么有力地诉说他们的故事,多么深远地将我们带回到过去之中——可城堡修复人员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这些古迹缩减成博物馆陈列厅的展品、考古学的玩具,它们身上所有的岁月留痕都被无情地剥蚀一空。”(16)显然,华顿对古迹修复持否定态度。但她在文中不是以权威的口吻直抒胸臆,而是把重点放在古迹上面,以古迹为叙述中心,从而避免了与读者的正面接触。
除了“我们”这一复数人称代词之外,华顿在行文中有时还用“某人/一个人”(one)来表述观点。有感于法国亚眠(Amiens)的教堂,华顿写道:“不过,如果把这种渊源关系搁置一边暂且不提,如果一个人不加挑剔地全身心浸润在业已产生的总体印象之中,如果一个人认可时间和气候这些意外因素在总体印象中占据的全部价值——亚眠还算幸运,没有刮擦的痕迹,上面刻的很多圣贤形象都披上了北部岩石才会有的最丰富的铜绿色——简言之,如果一个人把一件物品既看成一种象征,又看作‘天然之作’,(所有古代建筑在时间之手的作用下都变成了天然之作),那么,亚眠的前门肯定是哥特艺术所能表现出的最耀眼的一个景观。”(17)这里的“一个人”是一个泛指的人称代词,似乎既指代身历其境的旅游者,又指代阅读作品的读者,但同时又不具体指向任何一方。它不像第一人称代词“我”那样直接把作者推到前台,对着读者坦诚述说,而是产生一种漂游不定的感觉,遮掩了作者的真面目。
在《穿越法国》这部游记中,复数人称代词“我们”和泛指代词“某人/一个人”基本占据了叙述的中心位置。事实上,整本书一直到第三章才出现了作者的踪迹。有感于法国人淡定而愉快的生活方式,华顿觉得,眼中的法国人,不管是运河上的船夫,面包房的伙计,还是在街头叫卖的女贩,都体现了一种法国式的“生活智慧”,甚至于蜷伏在女贩大车下的白狗也不例外。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华顿写道:“所有这些人(在这一名称之下,我特意把狗纳入其中)都很淡定从容,或者以一种开朗的心态经营各自的生意,而这些均来自他们对现有状态的明智接受。”(18)从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把“我”置于括号之中,让人感觉这只是对前文的补充说明,给人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书中另外一处“我”出现在倒数第二章,“里昂,我相信,是法国名城中最平淡无奇的一个”(19),而这一处的“我”也是一带而过,因为下文立刻换成了“我们”和“某人/一个人”的口气。这样的一闪而过,这种匆匆的变换“看起来有点像编辑的一时疏忽”(20)。
当华顿在游记中小心翼翼地遮盖自己的作者踪迹时,詹姆斯却是自自然然地以作者“我”的身份对读者侃侃而谈,而且显得娴熟自然,没有任何顾忌。《法国掠影》(1884年)一开篇,詹姆斯就亮相出场,“我们这些感觉很好的美国人——我不是随口说的——特别容易把法国想成巴黎,就好像我们常被指责的那样,特容易把巴黎想成一座天上城市”(21)。在这里,詹姆斯直截了当地面向读者,而且还特意强调自己言之有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詹姆斯的书中,从头到尾,基本上都是作者“我”在指指点点,激扬文字,向读者传递信息。在这样的叙述模式中,作者“我”时时处在叙述的中心,和读者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这种展现自我的表述方式突出了“我”的在场,“我”的可信度,“我”的威望。
和华顿一样,詹姆斯也游览了法国的卢瓦尔河,但他的叙述和前者截然不同,“不过,我写的是我上一次见到的情形:河床满灌,水流宁静而有力,在大而缓的河湾处拐弯,映回半边天光。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你从昂布瓦斯(Amboise)的城墙和露台上看到的河道好景。某一个明媚的星期天早晨,当我从高处往下看时,透过秋日阳光的柔柔闪烁,它看起来就好像是慷慨仁慈之河的楷模”(22)。在这段文字中,作者身居高处、俯视大河的情景跃然于读者眼前。作者“我”那颇具权威的口气使得不在场的读者“你”在不知不觉之间接受了他的叙述,把他描绘的图景印在脑海里。
作为一名游历法国的美国男性,詹姆斯在当时的社会享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他可以在白天独自一人四处游览,也可以在星光之下单身外出,这种作法不仅得到社会的承认,而且常被视为英雄气概的体现。在游记中,这常表现为作者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叙述自己的探险经历。比如,当詹姆斯到达舍韦尼城堡(Cheverny)时,天色已晚,过了参观时间。可对于暗夜下的阴森古堡,他不仅不介意,而且觉得是一种享受,“这是我最喜欢的参观时间,看什么都行。我的车夫在一面围有高墙的大门前停下,下车后我沿着大门里一段不长的路步行;那些地方的车夫,要命得很,特别不愿把车赶到房子前面,这其中的原因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了。门房是个女子,干净小巧,正坐在自己的小屋前欣赏夜色,旁边还有一两个小孩陪着。她投以质疑的目光,可我接受了挑战。她告诉我再往前走点,然后往右拐。我按她说的那样一字不差地照办,拐个弯后,一座魅力十足的房子出现在我眼前,像童话故事里的古老庄园一样。”(23)在这段描述中,一个勇于冒险,敢于探索他人不愿涉足之地的旅行者形象清楚地出现在读者面前。
这样一种直白式叙述,这样一种孤身暗夜入古堡式的故事在华顿的游记中基本上是找不到的。对于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白人女性而言,社会对于女性的活动空间和范围有着很多的限定。长久以来形成的社会偏见束缚了女性的自由,“单身旅行的女人一是易受伤害,二是显得不守规矩,道德上很可能有问题”(24)。对于那些一贯被视为“天生既脆弱又虚弱”(25)的中上层白人女性而言,单身外出不仅可能危及人身安全和贞操,还要蒙受社会舆论压力,稍不留意就身败名裂,众叛亲离。在社会对性别的不同要求和规定中,詹姆斯星夜独自游玩古堡会被视为有胆识的不凡之举,而华顿如果这么做的话,则很可能遭到鄙夷或者谴责。
詹姆斯对古代遗迹的重修也不赞成。不过,他不像华顿那样委婉陈辞,把叙述中心放在古迹之上。在游记中,他完全以作者“我”的观察和感受作为叙述的中心,把“我”的所思所想直截了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于我自己而言,我是一点都不会犹豫。在任何情况下,我喜欢损毁的原迹都要胜过重修后的形象,不管前者损坏得多么严重,后者修复得多么堂皇。原先剩下的要比后加上去的珍贵:一个是历史,另一个是虚构;两者之间我更喜欢前者——因为它更加浪漫。”(26)毋庸置疑,詹姆斯是以作者“我”为出发点,这里的观察主体“我”是一切观点的发散之源,是文本的统领者。读这样的文字,读者很容易感受到作者的权威性存在,作者对叙述整体的控制。
詹姆斯之所以能够以“我”的口气畅快无阻地评点一切,这固然和他在文学界的名声有关(1879年出版的《黛西·米勒》和1881年出版的《一位年轻女士的画像》已经确定了他的权威地位),更重要的是,他在当时社会享有男性作家的性别特权。如前所述,华顿在出版游记之时,同样闻名于世,但作为女性作家的她却要处处隐匿起“我”的踪迹,只以一种画外音式的存在对文本进行遥控。
三、性别焦虑的影响
华顿在游记中很少把控制文本的作者“我”暴露在读者面前,这种把叙述主体从中心位置移开的做法在她同时代的女性作家游记作品中比较普遍。为了符合社会规范,为了“避免游记文本叙述中常见的自我中心和自我拔高这些不当之举,女性常常让作为叙述者的‘我’失音,以遮盖起她们的好奇心和自主性”(27)。对于这种“失音”,这种“字句间的缺憾”(Infection in the Sentence),我们可以借用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解释来分析: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迪金森、勃朗特、罗塞蒂这样的女性都被囚禁在家中,囚禁在各自父亲的屋子里。事实上,几乎所有十九世纪的女性都在某种意义上被囚禁在男性的屋子里。换一种形象的说法,这些女性被禁锢在男性文本之中,要想从这样的文本中逃脱,只有通过精心设计和迂回绕道才行,这一点我们已经见到了。(28)
华顿出生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美国上层社会,从小接受了严格的淑女教育,很了解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一个有宜人性格的女性必须容貌精美,礼节周到,性情高雅,言语温柔,在表露感情和行为举止方面恰到好处,尽力远离绯闻和公众的视线,喜欢倚人肩背受人呵护”(29)。应该说,早年的生活背景和诸多社会规范对她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尽管在写《穿越法国》之时,华顿已经是一位有思想、有个性、独立自主的成名作家,但她在书中依然行文于“男性文本”的禁囿之中,小心谨慎地遵守着某些潜移默化的规则,尽力将自己的身形隐匿起来。她了解男权社会的行为准则,知道社会不希望看到女性抛头露面,不希望她们“展示自立的一面,分享那些自由走动、强壮有力、无拘无束的白人男性才有的权力和特权”(30)。
作为一名职业作家,华顿有自己独立的版税收入,她的名字也常常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之中。她的名作家身份事实上已经背离和挑战了社会加在女性身上的性别准则。不过,出书成名虽给她带来了成就感和满足感,但也导致了她与旧圈子的疏离,给她带来了愧疚感。她为自己的女性作家身份感到焦虑和不安。在自传中她这样写道:“我在文学上的成功与其说让老朋友们印象深刻,不如说让他们困惑尴尬。在我自己家里,我的成功造成了与年俱增的家庭关系的紧张。没有一个亲戚跟我谈我出的书,没有赞美,没有指责——他们压根提也不提。在我们家庞大的纽约表亲圈里(其中包括很多跟我关系相当亲近的表亲),这个话题是免谈的,好像这是让家人丢脸的事情。即使能被原谅,也会让人耿耿于怀,心里不舒服。”(31)在华顿家族的社交圈里,做一名作家已是不雅之事,做一名女作家更是令人难以接受。有时候,华顿的“职业作家身份让她有种性别的无归依感”(32)。无疑,充满偏见的社会规范导致了明显的性别焦虑,并以种种方式反映在她的文本建构策略中。
另外,从职业经营的角度来看,华顿本人也倾向于在游记文本中“失音”。写作是华顿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但她不是为自娱自乐而写作,所以不会在写完之后把稿件束之高阁。要出书,就得遵守文学市场运作中的潜规则,就必须考虑出版界的要求,考虑来自编辑、文学评论家及公众的反应,而在这些领域起控制作用的又常常是男性。对于这一点,与华顿同时代的女作家夏洛特·珀金思·吉尔曼深有感触:“有些人是以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身份写作,他们就很难顾及编辑的要求。有些人是为了谋生而写作。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就必须取悦编辑。而编辑呢,要想挣钱谋生,就必须讨好购买者,讨好公众,这么一来,我们就有了媚俗文学这个了不起的行当。”(33)华顿是个精明的作者,她对图书的销路和版税非常关注。她常常“指挥她的出版商,告诉他们如何接近文学市场,以便让她的作品成为有价值的商品”(34)。她知道,在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女作家要想获得读者的认同,就“不可以像十九世纪的男性一样随心所欲地表露自我意识,把自己展现为叙述的中心人物”(35)。为了得到出版界的支持,为了能把自己的作品推介给读者,她需要把叙述者变成无声之我,把自己藏于阴影之中。但同时,她也知道,要想吸引读者,自己的作品就必须有新意,有独特之处,有一定的权威性。这就使得她不得不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在女性规范内挣扎,却又不能打破这一规范”(36)。
作为一名白人女性作家,华顿的游记显示出很多性别焦虑的痕迹。社会对女性作家的规范限定了她的表述方式和叙述策略。在分析性别与文本建构之间的关系时,萨拉·米尔斯指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女性话语为中产阶层的女性设定了各种角色,其中绝大部分被限定在私人空间之中。“女人味”的女人料理家事,搞好关系,还得关注家族的精神和道德健康。这些话语对女性的游记文本建构方式有着明显的影响[……]女性在不断的强化之中进入了描述个人事务的私人空间,虽然说她们写游记这一行为本身已经探入了公共空间。(37)
这一现象确实值得深思。对于华顿这样的女性游记作家而言,她们在推出游记之前必定已经抛头露面,四处游览,走出了闺阁式的私人空间,进入了开放的公共空间。在游记创作中,她们介绍自己的行程,发表自己的看法,将自己的经历公布于众多读者面前,让读者了解自己,认识自己,这更是一种步入公共空间的做法。然而,即使身处公众的目光之下,她们依然试图保持自己的“女人味”,保持自己的中上层淑女形象,把自己限定在某种女性角色之内。这种矛盾状况清楚地说明了西方女性游记作家当时的尴尬境地。
注释:
①Peter Hulme & Tim Youngs,"Introduction" in Peter Hulme and Tim Youngs,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ravel Writ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1.
②Kristi Siegel,"Women's Travel and the Rhetoric of Peril:It is Suicide to be Abroad" in Kristi Siegel,ed.,Gender,Genre and Identity in Women's Travel Writing(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2004)58.
③James Buzard,"The Grand Tour and after(1660-1840)" in Peter Hulme and Tim Youngs,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ravel Writ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38.
④转引自Karen R.Lawrence,Penelope Voyages:Women and Travel in the British Literary Tradition(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viii。
⑤Mary Suzanne Schriber,Writing Home:American Women Abroad,1830-1920(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97)107.
⑥Jennifer Bernhardt Steadman,Traveling Economies:American Women's Travel Writing(Columbus: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7)4.
⑦Foster Rhea Dulles,Americans Abroad:Two Centuries of European Travel(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4)44.
⑧Sidonie Smith,Moving Lives:Twentieth-Century Women's Travel Writing(Minneapolis &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1)16.
⑨Jennifer Bernhardt Steadman,Traveling Economies:American Women's Travel Writing(Columbus: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7)69.
⑩Peter Brooks,Henry James Goes to Paris(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209。
(11)华顿著有五本关于欧洲大陆的游记,《意大利别墅与花园》(Italian Villas and Their Gardens,1904),《意大利背景》(Italian Backgrounds,1905),《穿越法国》(A Motor-Flight Through France,1908),《战争中的法国:从敦克尔克到贝尔福》(Fighting France,from Dunkerque to Belfort,1915)及《法国方式及其意义》(French Ways and Their Meaning,1919)。詹姆斯著有三本关于欧洲大陆的游记,《法国掠影》(A Little Tour in France,1884),《英国风情》(English Hours,1905)和《意大利风情》(Italian Hours,1909)。本文重点分析华顿的游记《穿越法国》,并与詹姆斯的《法国掠影》进行比较。
(12)Edith Wharton,A Motor-Flight Through France(London:Macmillan&Co,1908)1.这里的黑体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后面所有引文中的相关人称代词都以黑体着重号标识出来,以便更清楚地显示原文中的人称代词使用情况。
(13)Richard Warrington Baldwin Lewis,Edith Wharton:A Biography(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Inc.,1975)154.
(14)Richard Warrington Baldwin Lewis,Edith Wharton:A Biography,151-154.
(15)Edith Wharton,A Motor-Flight Through France,36.
(16)Edith Wharton,A Motor-Flight Through France,26.
(17)Edith Wharton,A Motor-Flight Through France,9.
(18)Edith Wharton,A Motor-Flight Through France,28.
(19)Edith Wharton,A Motor-Flight Through France,147.
(20)Valerie Morrison Smith."Crossroads:Cultural Autobiography and Imperial Discourse."(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2001)80.
(21)Henry James,A Little Tour in France(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Company,1950)1.
(22)Henry James,A Little Tour in France,4.
(23)Henry James,A Little Tour in France,40.
(24)Kristi Siegel,"Women's Travel and the Rhetoric of Peril:It is Suicide to be Abroad" in Kristi Siegel,ed.,Gender,Genre and Identity in Women's Travel Writing(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2004)57.
(25)Kristi Siegel,"Women's Travel and the Rhetoric of Peril:It is Suicide to be Abroad",61.
(26)Henry James,A Little Tour in France,144.
(27)Sidonie Smith,Moving Lives:Twentieth-Century Women's Travel Writing(Minneapolis &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o Press,2001)18.
(28)Sandra M.Gilbert and Susan Gubar,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83.
(29)转引自Jennifer Bernhardt Steadman,Traveling Economies:American Women's Travel Writing(Columbus: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7)112.
(30)Jennifer Bernhardt Steadman,Traveling Economies:American Women's Travel Writing,9.
(31)Edith Wharton,"A Backward Glance" in Cynthia Griffin Wolff,ed.,Edith Wharton:Novellas and Other Writings(New York:Library of America,1990)891.
(32)Jennifer Haytock,Edith Wharton and the Conversations of Literary Modernis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2.
(33)转引自Janet Beer,Kate Chopin,Edith Wharton and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Studies in Short Ficti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7)3-4。
(34)Sharon L.Dean,Constance Fenimore Woolson and Edith Wharton:Perspectives on Landscape and Art(Knoxville: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2002)210.
(35)Sidonie Smith,Moving Lives:Twentieth-Century Women's Travel Writing,18.
(36)Kristi Siegel,"Women's Travel and the Rhetoric of Peril:It is Suicide to be Abroad",3.
(37)Sara Mills,Discourses of Difference:An Analysis of Women's Travel Writing and Coloniali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94-95.
标签:旅行论文; 法国作家论文; 法国旅行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游记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