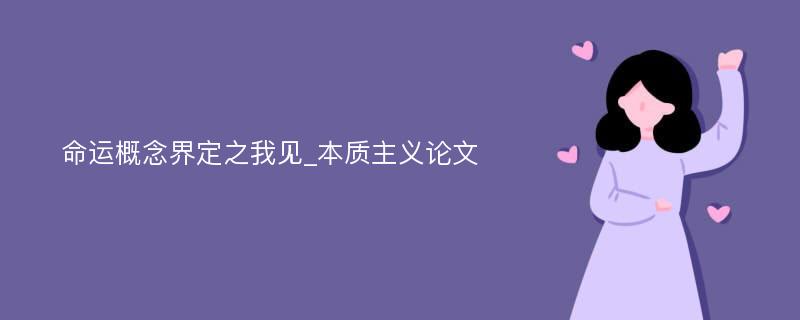
命运概念界定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见论文,命运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448(2000)02-0014-06
马克思主义是否有自己的命运观
命运,这是一个人们都十分关心而又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什么是命运?翻阅哲学思想史,你会发现,不同的思想家有着不同的思考和解释。
那么,马克思主义关于命运概念是怎样界定的呢?在具有权威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中没有关于命运一词的解释。至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得到理论界普遍认可的关于命运概念的哲学界定。因此,这里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结合科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的思想资料,概括和超越以往各种不同的关于命运的思想,作一个较为合理的界定。
对命运概念的合理界定首先需要厘清两个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讲不讲命运;第二,对命运的概念能不能有一个界定。
先说第一个问题。由于命运这个概念曾经是包含着神秘性,是与神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人们在理论上是不敢讲命运的,似乎讲命运就和天命论、宿命论划不清界限,就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说:“马克思主义者是不相信‘命运’的。命运这个概念,即‘希克查尔’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偏见,就是胡说,就是古希腊人的神话这一类东西的残余,古希腊人认为命运之神支配着人们的命运。”“‘命运’是一种不合乎规律的东西,是一种神秘的东西。”[1]这是一种“左”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者不相信有非人的或超人的命运之神,反对对命运作神秘主义的理解。但是,不能因为否定命运问题上的偏见、胡说、神秘性,就连命运的概念也加以否定。命运问题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命运概念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概括表达。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忽视命运的问题,不能回避命运的概念。即使斯大林本人,也免不了要用命运一词来概括表达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他在《悼列宁》中曾经大声疾呼:“工人阶级的命运痛苦不堪。”
前苏联学者伊·谢·科恩说:“命运这个概念就形而上学的意义而言,是表示人生非理性的、不可捉摸的定数。但命运也往往被理解为由人赋予方向和意义的个体生命存在的内在规定性。前者强调由外因决定的不自由,后者强调个人选择的终极性、不可逆转性。”[2]这就是说,他也认为,对于命运的概念,在不同的人那里是会有不同的理解,可以作唯心主义的解释,也可以作唯物主义的解释。
1843年5月,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一封信中写到:最先朝气蓬勃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但愿我们的命运也同样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各个人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条件是早已确定的:阶级决定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决定他们的个人命运,使他们受它支配。”[3]
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曾说:“自从命运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见面之后,这两位朋友的毕生工作,就成了他们两人共同的事业。”[4]在谈到《国际歌》时,列宁说:“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5]
江泽民也说:“年轻同志必须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觉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6]
所以,问题不在于否定命运之概念,而在于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其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从而使人们摒弃神化和神秘性的理解。
再说第二个问题,即能不能对命运概念有一个界定。
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命运被前人从多种角度、不同意义上引申使用”,“根本不可能用一个单一概念加以定义,只能把它视为对人生状态的描述。”[7]按照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对命运的概念不可能有一个界定。
的确,我们在文章中可以看到,命运一词被人们从多种角度、不同意义上引申使用。但这并不是对命运的概念不可能有一个界定的理由。“从多种角度、不同意义上引申使用”本身就说明命运一词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含义,不然,怎么能说是“引申使用”?“只能把它视为对人生状态的描述”,既然如此,就说明人生状态是命运概念应该具有的基本含义。
实际上,“命运”一词和“自由”一词在这一点上有类似之处,就是都有日常使用和哲学概念的区别。日常使用的自由一词与哲学上的自由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我们不能因为有了前者,就不去对哲学上的自由概念进行界定。同样,日常使用的命运一词与哲学上的命运概念也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我们也不能因为有了前者,就不去对哲学上的命运概念进行界定。总之,这并不影响我们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什么是命运的概念界定。
命运表现为生存状态及生命历程
那么,应该如何界定命运的概念呢?我们认为,命运是指人的生命主体与其赖以存在的环境在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生存状态及生命历程。
对于命运一词,我们不同意“根本不可能用一个单一概念加以定义”的观点,但的确存在着人们“从多种角度、不同意义上引申使用”的情况。我们认为,命运的本义应是指向人的生命主体,包括个体、群体和人类;至于说一种理论的命运、一项事业的命运、一类动物的命运,显然都是从引申的意义上使用的。我们这里主要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谈人生的命运。
问题的困难不在于这样来界定,而在于如何论证这样界定的合理性。下面我们就作些解释与论证。
在对命运概念的定义中有一种“遭遇论”:
《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命运的词条写道:“①指生死、贫富和一切遭遇(迷信者认为是生来注定的)。②比喻发展变化的趋向。”
《人生哲学》一书的作者在谈到命运时认为:“人生哲学中所讨论的命运,主要是指个人的命运,是个人人生旅途中实际存在的种种遭遇和境地。所谓境遇,就是人们面对的并生活其中的现实。”[8]
《人生学论纲》中说:“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命运’,无非是人生的一定遭遇,即人生所处的自然、社会客观环境和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主观努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结合而产生的结果。”[9]
后两种定义虽然是在前一种定义的基础上有所发挥,但本质上还是一种“遭遇论”。这样定义命运当然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但存在的缺陷是,遭遇的概念讲的是遇到的事情,是从外在的角度表达客体或环境对主体的关系,不是从主体的角度表达人自身的生存状态。生存状态离不开遇到的事情,包含了遇到的事情,但又不仅仅是遇到的事情,它强调的是生命主体的自身状态。生存状态的内容包括生死康病、富贵贫贱、吉凶祸福、成败得失、悲欢苦乐等等,这些绝不仅仅是遇到的事情之问题,所以,也绝不是遭遇所能概括了的。
生死康病是讲人的生理状态;富贵贫贱是讲人的经济状态和政治状态;吉凶祸福是讲主体在某种意外情况下受到外界客体的肯定状态或否定状态;成败得失是讲人生事业的情况和状态;悲欢苦乐是讲人的心理状态。这些都是生命主体生存状态的重要内容。现实生活中人们谈论命运,往往就是在涉及这些内容的时候。南北朝时代的学者刘峻在《辩命论》中写道:“所谓命者,死生焉,贵贱焉,贫富焉,治乱焉,祸福焉。”刘峻讲的虽有不足,但意思和我们这里说的命运概念大致相同。
生存状态的生死康病、富贵贫贱、吉凶祸福、成败得失、悲欢苦乐等几个方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形成了人生命运的总体内容。生当然是基础,只有生,才能谈得上其他几个方面,否则一切都谈不上。但在生的基础上,其他几个方面可以是面面俱好,也可以是面面俱差,还可以是好中有差或差中有好,由此可以分为四种结构模式。人们在评说命运的好和差,虽然可以是针对生存状态的总体内容,但往往是指某个或某些方面,因为人们总是在具体情境下进行评说的。在这几个方面中,除了生死康病,在一般情况下,其余几个方面可以说都与成败得失相关,所以,人们对命运的关注主要是对事业的成败得失的关注。评说命运的好或差,有其客观的现实,也有主观的观点。观点的不同,对同样的现实会有不同的评价。
仅用生存状态还不足以概括人生命运的全部内容,还应加上生命历程。生存状态是从存在的角度对人生的命运作横向观察,是人生命运的横坐标。生命历程是从发展的角度对人生的命运作纵向观察,是人生命运的纵坐标。生命历程是生存状态的变化和延续。刘峻在《辩命论》中也谈到生命历程的方面,他说:“命体周流,变化非一,或先号后笑,或始吉终凶。”他把人的命运分为两种发展类型:先差后好,“先号后笑”;先好后差,“始吉终凶”。明代的文人李翔在《戒庵老人漫笔》中讲得更具体:“人之生也,多少壮富贵盈满,至老不能享其终;少壮艰苦酸辛,至老获享丰厚,安逸其闲。值数之奇,亦有终身不遇者;值数之偶,亦有终身获享全福者。”在这里,李翔把人的命运分为了四种发展类型:先好后差,“少壮富贵盈满,至老不能享其终”;先差后好,“少壮艰苦酸辛,至老获享丰厚,安逸其闲”;始终皆差,“终身不遇”;一生都好,“终身获享全福”。
生存状态和生命历程是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概括人生命运的具体内容,这样概括比用遭遇来概括更为确切和全面,但这还只是停留在结果和现象的层面,还没有深入到原因的探究和本质的揭示层面。
命运的本质是主体的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对命运概念的合理界定,不仅仅是要确切而全面地概括人生命运应该包含的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要深入到原因的探究和本质的揭示。那么,如何认识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历程种种结果的原因和本质呢?
恩格斯说:“相互作用是我们从现代自然科学的观点考察整个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东西。……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追溯到比对这个相互作用的认识更远的地方,因为正是在它背后没有什么要认识了。……只有从这个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了解现实的因果关系。”[10]上述恩格斯提出的关于相互作用的观点,为我们指明了认识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历程种种结果之原因和本质的方向。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历程的种种结果,正是作为生命主体的人与其赖以存在的环境在相互作用中形成的。我们应该也只能从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来理解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历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名论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1](43页)的命题,认为,历史不外乎是各个世代的依次更替,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遭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这些因素、关系便构成了特定的环境。一方面,这种特定的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本质。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二者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过程,这种相互作用被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1](17页)所以,马克思主义又认为,实践是人的本质,人是实践的产物。讲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历程是人与其赖以存在的环境在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与讲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实践是人的本质,人是实践产物,都是相互一致的。
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一方面,由于生存空间的不完全一样,社会关系的不完全一样,所以每个人的所处环境是不完全一样的;另一方面,每个人的主体自身条件也是各有特点,不完全一样,因而,形成了人与人之间命运的差别或不可能完全相同。
马克思主义从实践的角度即从人与环境的双向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待人的命运,一方面,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性和自主性的,是有意志自由的,承认人的主体能动性,同时又认为这是有一定限度的;另一方面,认为实践活动的环境是既定的,是主体实践活动所依赖的条件,对于主体的实践活动具有制约作用,它既具有能为主体实践所改变的一面,又具有不为主体实践所改变的一面。所谓“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的条件就是能为主体实践所改变的一面;所谓“创造条件也要有条件”的条件就是不为主体实践所改变的一面。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命运是主体自主性与环境制约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在认为人的命运是主体自主性与环境制约性的统一的基础上,更注重主体能动性的发挥。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天才,但认为人的先天素质是不一样的,由于先天素质的不一样,再加上后天家庭和社会的环境影响不一样,因此人的主体能动性及其发挥是不一样的。由于人的主体能动性及其发挥的不一样,在对个人命运的把握方面也就不一样。在从事同样的实践活动中,有的人能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有的人不能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人生命运。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决定论认为,在事物的变化发展过程中,既有必然性的一方面,又有偶然性的一方面,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相互统一。根据这种观点,从实践的角度即从人与环境的双向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待人的命运,既要看到其中的确定性因素,又要看到其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一个人是否出生在一个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都十分优越的家庭环境,本人又是否具有较好的天赋条件,都是一个人今后一生命运的确定性因素,基本奠定了这个人今后一生命运的基础。但是,一个人一生的命运,除了与他本人的天赋条件、家庭环境这些相对确定性因素有关之外,还与很多不确定性因素有关。这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为人们提供的是可能性空间,是何种程度的可能性。从前瞻的角度看人的未来发展,来谈命运,是对尚未现实化的人的生命历程可能性的把握。
在对待人生命运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观是既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又反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宿命论。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认为人的意志是绝对自由的,夸大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用以指导实践必然导致实践中的碰壁。客观唯心主义的宿命论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但本质上是认为有一种神秘的未知力量决定人的命运,使人放弃发挥主体能动性,其结果只能是害人误国,对国家和人民都不利。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有一只“无形的手”即价值规律起着支配作用,使人们面临种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感到无能为力,这种认为有一种神秘的未知力量决定人的命运的客观唯心主义宿命论尤其有市场,因而危害性也最大。
在现实生活中,有人说命运是自己不能自主的;有的说命运是自己能够主宰的。这两种说法,明显地是各自陷入了一种极端,都是片面的。究其原因是没有认识到人的命运是人与其环境在相互作用中形成和决定的。在相互作用中,人作为主体有其主体性、自主性、能动性的一方面,同时人对于环境又有其派生性、依赖性、受动性的另一方面,是这两方面的统一。因此说,个人对于自己的命运既有能够把握的一面,也有不能把握的一面。无视了前一方面,就陷入了前一种极端,和客观唯心主义的宿命论是相通的;忽视了后一面,就陷入了后一种极端,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是相通的。对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这两方面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人对于命运的思考,当在背逆和失败的情况下,容易导致走向前一种极端;当在顺利和成功的情况下,容易导致走向后一种极端。
应该看到,我们现实的社会环境还存在着种种不公平和不平等,这样的社会环境使得人们在把握自己的命运时也遇到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不能完全靠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性来把握自己的命运,个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马克思所说的“偶然的人”,即个人的命运受偶然因素影响很大。只有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有个性的人”才能最终代替“偶然的人”[3](79页),个人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
我国现代著名学者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写道:“命乃指人力所无可奈何者。我们作一件事,这件事情成功与失败,即此事的最后结果如何,并非作此事之个人之力量所能决定,但也不是以外任何个人或任何一件其他事情所能决定,而乃是环境一切因素之积聚的总和力量所使然。如成,既非完全由于我一个人的力量:如败,亦非我用力不到;只是我一个因素,不足以抗广远的众多因素之总力而已。作事者是个人,最后决定者却并非任何个人。这是一件事实。儒家所谓命,可以说即由此种事实导出的。这个最后的决定者,无以名之,名之曰命。”[12]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命运的解释虽然没有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但实际上意思也是一致的:“是环境一切因素之积聚的总和力量所使然”。不过这样一种思想认识,在儒家那里尚未达到。
宋锦添认为:“命运是一个反映人生中重大价值状态的修饰性语言,是指人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客体对人的肯定或否定的价值关系。”[13]这个定义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用主客体相互作用来揭示命运的本质,为马克思主义命运观的理论探讨作出了贡献,不足之处是有些过于繁琐和不易懂,此外还失之于是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而不是从主体的角度来界定。
刘忠礼等在《人生观和价值观新论》中认为:“命运是指在人生道路上主客体相互作用中客体对人的肯定或者否定的价值关系,是指与人生中重大价值有关的那类遭遇。”[14]这个定义也用相互作用的观点来说明命运概念,是值得肯定的,但仍然没有避免从主客体关系角度来界定的缺陷。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可以把命运界定为是指人的生命主体与其赖以存在的环境在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生存状态及生命历程,这也就是说,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历程是作为生命主体的人与其赖以存在的环境在相互作用中形成的。
收稿日期:1999-1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