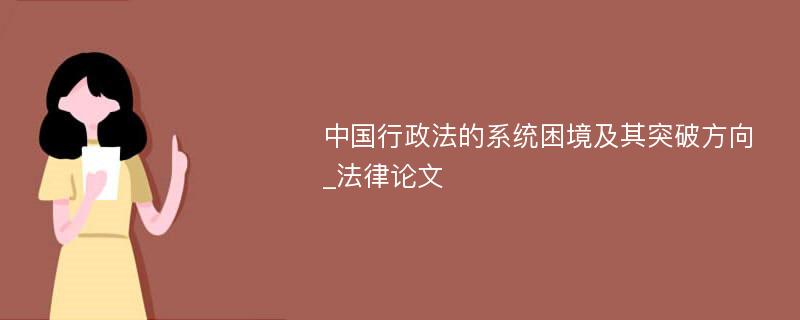
中国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困境及其突破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法学论文,困境论文,方向论文,行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行政法学面临着多重的学术任务,一方面其尚未完成自身的理论体系建构,即理论内容本身尚未达将行政法提升到价值统一性和逻辑一致性的层面。①另一方面又必须针对现实生活中不断复杂化的问题,直接进入各个具体的行政领域进行理论归纳尝试。②或许在是否已经完成理论体系建构方面,学界会有争议,但无论如何,既有的理论中存在着诸多如本文下面内容所指出的那些困境,因而需要找到突破点,寻求走向未来发展方向,这应该是学界的共识。而问题解决的前提,无疑需要找到当前理论体系建构困境发生的关键之处,以及其发生的机理,只有这样才能进而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可思考的走向。 本文就是针对上述事项所做的一点尝试。由于所涉论题极其庞大,一篇短文决然无法覆盖全局,因此,本文只是针对相关思路做些初步的整理和提出问题而已。本文的研究对象只限于构建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方法,基本不触及行政法学与相应国家社会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尽管后者是一个更为有价值的分析方向,且在发展中国行政法学方面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主题,但在现阶段只能暂时将其另文讨论。 一、困境一:缺乏统领性的抽象概念 (一)体系形成的出发点:抽象的“行政行为” 中国行政法学发展至今,外形和渊源上都与德国行政法学相关。③回溯行政法学的发展史可以看到,行政法学的形成,其实是以其理论体系成立为标志。1895年,德国法学家奥托·迈耶出版《德国行政法》一书④,建立了学理意义上的行政法学体系,由此他被誉为“现代行政法方法真正的开山鼻祖和经典人物”。⑤ 在《德国行政法》一书出版之前,德国并非没有行政法的教科书或者著作,但迈耶与之前的行政法学家们不同的是,他采用法学的方法建构起了行政法教义学,刻画出一个高于实定法的抽象层面,在此层面运用关键性概念统合行政法学整体,使其内在内容逻辑一贯。其中,在该书的“总论”部分,奥拓·迈耶没有描写如税法、公路法等个别的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法律规定,而是从繁杂的凭经验(尤其是法院和其他机关的判例和实践)而总结出来的现象中分析法的一般范畴。⑥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他以法院的司法裁判为模本,创立Verwalrungsakt这一被中译为“行政行为”的德国行政法学上的核心概念⑦,并以此概念作为核心建构了总论体系。 在这个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中,这一高度抽象化的“(德国法学上的)行政行为”概念,统合了行政法所共通的原理而舍弃各种具体的行政权力现象,⑧使行政法获得了形式化抽象,表现为可以被外在判断的法律形式要件,以此实现宪政的法治国家目的。同时,法治国家在进行主权干预时要受一般法律的约束,并且在法律应用的具体情况下接受独立法官的审查。⑨因此,司法可以依靠清晰的概念和体系,将行政活动在形式上予以规范。“法治国意味着行政司法化。”⑩ 我国的行政法学理论形成方面,也深受上述法学方法的影响,因为迈耶建立行政法学的方法及其成果,其作用不仅仅限于德国自身,还深深地影响了大陆法系与德国相关一系的各个国家。回溯历史可以看到,如日本和20世纪初期的我国便深受影响。例如,即使在现今的日本行政法学总论中,各个教科书中典型的体现概念还是“行政行为”(或与此具有相同功能的学术概念,如“行政处分”等(11))。该概念本身如同德国行政法学理论那样,“主要是作为学理上的概念发育而成,而并非为实定法上的概念”,(12)法学界围绕着“行政行为”概念构筑起了作为学术产物的行政行为理论。(13)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法学也同样受此影响,早年自日本承继德国行政法的台湾行政法学界,由50年代初期的林纪东教授的行政法教科书至目前,也大体上维持奥托·麦耶所确定了的架构。(14)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台湾的行政法学体系也一定程度地影响着中国大陆法学重建过程。如今我国的行政法学体系本身及其建构方式都能显现上述影响的痕迹。 (二)我国行政法学的核心:半抽象的“具体行政行为” 在我国当代的法学建设中,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的行政法学学科体系建设,是否也受到迈耶体系的影响当然尚需详考。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在《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处于学术探索阶段的教科书在尝试创设核心概念的过程中,尽管所用名词表述不同,但也会设置类似于“(德国法学上的)行政行为”这样的高度抽象的学术概念,凭此统合行政活动整体特征及其相关的内在逻辑的学术思路已经显现。例如早期王珉灿主编的《行政法概要》就设有“行政行为”专章,指出“行政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活动的总称,它是国际公认的研究行政法学的专用名词,实际上是行政管理活动的代称”。(15)由于当时《行政诉讼法》远未颁布,从这种表述方式可见作者们将“行政行为”概念作为行政法学体系中理所当然的核心概念。而自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后,在相关的行政法学者的教科书等研究作品中,清晰地可以看到,学者们构建的行政法学总论体系尽管在具体的构成部分方面各展千秋,但在整体结构上与迈耶的法学方法处理结果有着类似性,都会存在一个或多个彼此关联的核心概念贯穿整个学理体系,其中“具体行政行为”(或者类似的概念)这个核心概念来承担着类似于“德国法学上的行政行为”概念的作用,并且教科书的这个体系仍然维持至今。(16) 从整体的形式而言,由于有了“具体行政行为”这一核心概念对整个体系的学理统领,至少在外形上而言,我国当前的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在总论层面上已经相应成立。但是,就抽象于实定法的法学方法而言,不得不说,我国“具体行政行为”概念还属于一种半抽象的法学概念。其理由如下。 首先,“具体行政行为”直接作为法学概念使用,是在《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后。该法第二条直接创设了“具体行政行为”这一法律概念,构筑了该法在体系和运用方面的核心概念。该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且该法第五条将该“具体行政行为”设置为司法审查的对象。由此,这里的“具体行政行为”首先成为一个被解释的对象概念,是一个被规定在《行政诉讼法》具体条款中的具体的实定法律概念。(17)正因为如此,在与《行政诉讼法》相关的法学理论框架中,“具体行政行为”并非是一个抽象的法学概念,而是被法学解释和研究的具体的法律概念。 然而,在随后的中国行政法学发展过程中,“具体行政行为”并没有完全停留在具体的实定法律概念的层面上。众所周知,中国行政法学和行政法体系的发展成型,正是以《行政诉讼法》为起点发展而至。围绕着司法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标准,在随后的行政法制建设时期建立起了诸如《行政许可法》等等一系列行政法律规范。如今,这些实定法规范在法律的层面上已经构建起了规范行政活动最为基本的法律规范制度。如《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中有关的实体规范部分、《立法法》中的行政立法规范部分、《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所建立的相应规范和《国家赔偿法》中行政赔偿规范部分等等单行的法律规范。由于这些单行的法律规范都以调整我国行政活动最为基本层面的问题为对象,因此可以说,无论就其形式还是就其功能而言,这些单行的法律规范构成了在理论上可以称之为行政基本法中的相关部分。 由于这些单行的行政法律规范各自使用的概念不同,例如《行政许可法》中的“行政许可”概念、《行政强制法》中的“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这样,在合法性标准与司法审查的关系方面,需要研讨这些具体的法律概念是否被《行政诉讼法》中的“具体行政行为”所包含。不仅如此,如上所述,由于《行政许可法》或《行政强制法》属于行政基本法规范,因此,在判断其各自包含的下位法或者特殊法中的概念时,也同样要判断这些法中的特定概念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设定了机动车驾驶证制度,在行政诉讼时,司法审查判断该法律法第19条第二款规定的“发给机动车驾驶证”行为是否合法时,不仅要判断该法定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许可法》中规定的“行政许可”行为,还必须同时断定其是否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这种判断概念与概念之间是否存在包含关系的过程中,“具体行政行为”成为架构在诸如“行政许可”或“发给机动车驾驶证”等等这些具体法律之上的概念,在一定的法律适用范围之内,其地位上升为在法学意义上具有统括相应法律概念基本特征的概念,由此,在这个领域之中,“具体行政行为”概念具有了一定的抽象性,成为法学概念。 由此可见,正是在上述的前提之下,中国行政法学中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一方面是一个具体的被解释的统括性的实定法律概念,另一方面又属于具有一定抽象性的法学概念。换而言之,“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这种双重属性导致中国行政法学目前的并没有完成自身的理论体系化。 与此相关,在确定“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学中的位置时,行政法学教科书时常会设置一个该概念的上位概念“行政行为”。这里暂且不论这样将“具体行政行为”理解为偏正结构的词汇,因而基于修辞性质的设词方式是否能够当然地支撑起法学逻辑体系,就目前而言,该“行政行为”概念与“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一样,无疑无法承担与“(德国法学上的)行政行为”同样的功能。(18) 当然,在“具体行政行为”的发展过程中,并非不能观察到一些将此概念进一步抽象,或者寻找更为一般意义上的概念的尝试,例如近年来行政法教科书中出现的“行政决定”或“行政处理”等概念,至少在形式上脱离了“具体行政行为”外形。(19)但是,从源头上而言,这些学术作业都是在遇到实定法概念“具体行政行为”与需要进行学理抽象统和作用的法学概念“具体行政行为”之间的无法调和的矛盾之后,所寻找的替代方案,而非学术上抽象概括作业的结果。例如,使用“行政处理”概念的学者指出,“行政处理”概念“实质上是狭义行政行为的代名词,更确切地说,也会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具体行政行为’”。(20)再如,在“行政决定”概念使用方面,从时间上看,学界中“行政决定”概念的出现,是在国务院2004年3月22日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之后,该文件使用了“行政决定”概念。由于在使用“行政决定”概念的教科书中作者并没有对该概念与“具体行政行为”在内容方面作出学理性区分,因此至少在目前阶段两者只是形式的不同而已。但是,尽管如此,学者在教科书中使用“行政决定”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学界或多或少意识到了作为实定法律概念的“具体行政行为”难以承担法学概念应有的抽象功能。因此,虽然“行政决定”或“行政处理”等概念替代了“具体行政行为”的表述,但是,很难判断这些新概念在功能上与“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有何不同。 二、困境二:既有概念无法统合新的问题 如上所述,“具体行政行为”概念并没有完成将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化的任务。但是,尽管如此,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并不意味着只要在学术上坚持采用上述迈耶法学方法,就能最终把此概念抽象至与“(德国法学上的)行政行为”具有同样统合程度的核心概念。这是因为现今中国行政法学与其他国家的行政法学一样,因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近年来,以行政行为为核心概念的行政法总论体系也不断受到各方面的挑战。概括而言,当今在构筑行政法理论体系时,下述两方面的变化,已经成为必须考虑的内容。 (一)原来法学方法延长线上的发展变化 如果将上述以迈耶的法学方法为源头的行政法理论体系称之为传统体系的话,那么必须注意的是,该体系的初始基础是建立在19世纪德国立宪主义基础之上,体现了自由主义性质的法治国家理念,关注的是公法上实现国家任务的高权性的行为形式,如警察处分、课税处分等行为等行政活动的行为形式。严格而言,这个时期的行政法学刚现雏形,尚处摇篮期内,因此,即使在当时已经在制度中存在了的,旨在启蒙专制国家中促进臣民幸福为目的的福利性行政措施也被舍弃在体系之外。(21)在此之后,此一脉的行政法学在“德国法学上的行政行为”基础上,统合同类方式的行政活动,形成了行政的行为形式理论。如今,从已经形成的结果来看,在以“权力·非权力”为纵轴与以“法律行为·非法律行为”为横轴形成的框架中,“德国法学上的行政行为”发生的前后延伸出行政立法、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契约等等行为形式,无论在行政法学中还是在实定法上都获得了定型和定位。而这样的概念及其体系所表现出的特征,一是舍弃行政活动的目的而依据其对外效果进行分类,二是行政活动被分解为行政过程中的最小单位,以此适用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22)这里可以看到,中国行政法学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同样具有该“德国法学上的行政行为”的形式化和对应司法作用这两项特征。 但是,具有这样特征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已经无法包容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现今的需求。这表现为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其一,新制度对应的新概念。近来行政法学中,因立法的发展所产生了一系列与实定法紧密相关的一些概念,如行政程序、行政调查、行政指导、政府信息公开、公私合作、民营化、私人行政等概念。这些概念并非完全来自事后司法审查的需要而设,有的甚至无法直接归入“具体行政行为”的框架之内。例如行政程序概念,当其在《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框架内讨论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时,即司法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时,此处的行政程序构成了具体行政行为的一个合法性要件。但另一方面,当关注的是行政活动的过程时,体现行政活动过程合法性要求的行政程序本身并不构成“具体行政行为”,尤其在现代行政活动的复杂性和连续性要求下,行政程序所对应的是同一政策目的之下的整个行政活动过程,因而无法将其截成断片以嵌入单个具体行政行为的要件要求框架之内。同样,行政指导、公私合作等本身体现为行政活动的一种类型,其本身并不当然发生法律效果,因而也无法纳入“具体行政行为”的框架之中去考察。因此,这里暂且不论这些概念本身是否强调行为形式,其在行政活动中对行为形式的要求,甚至难以纳入上述“权力·非权力”与“法律行为·非法律行为”构筑的框架。 其二,新形态对应的新作用。就行政与其对应的国家作用而言,欧美国家存在着由秩序行政阶段而进入福利行政阶段的历史发展进程,而且在福利行政之后,而今又有被定义为“保障行政”或“担保行政”的发展阶段。(23)如前所述,“行政行为”概念产生于19世纪德国的自由法治主义时代,体现了该理念之中的法治国家理念,直接关注的是警察行政等秩序行政,对应的是自由等消极权利。同时其开始时就排除了福利行政的目的。因此,该概念所具有的形式化和对应司法作用的属性也在一开始就与此历史属性紧密相关。这里撇开该“行政行为”概念在德国百年历史中的发展变化,以及发展至今日的实际状态,由于中国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也具有这两项属性,因此在现今的制度运行中,无法区分在各个行政形态中,其构成方面是否应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司法审查阶段,仅仅从法定的形式要件的角度,显然无法在理论层面上区分征税行为与发放福利待遇行为的差异。更为复杂的是,在欧美国家作为历史进程三个阶段的秩序行政、福利行政和保障行政,在当今的中国,由于全国社会发展的不均衡,这三种形态却是同生共存于同一时间空间。这样的法制现状中,“具体行政行为”所应担负的功能必然会较之欧美国家的要更为繁多和更为复杂,而这些已经脱离了“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现有属性所能承担的范围。 (二)来自研究方法及视角的变化 另一个新的变化来自于对司法审查有限性与中国立法体系化不足或立法密度不足认识,从而脱离属于内部视角属性的法学方法而使用社会科学方法对行政法学的审视。(24)如上所述,以“具体行政行为”构建的中国行政法学体系,其侧重点在于通过司法审查的作用来保障其合法性,以此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这一点与迈耶的体系具有同构性。但是,相对于这种“面向司法的行政法学”而言,近年来出现了“面向行政的行政法”或“规制行政法学”的学术走向,其研究的关键点不在与“具体行政行为”相关联的司法审查标准之处,而是更注重行政本身的过程及其法律对此的规制方式和实效。(25)这类的研究,一方面改变了原本行政法研究注重法律形式要件的方法,转而侧重行政活动的目的,由此使法学方法中原本至关重要的形式性和对应司法的两个属性受到了质疑;另一方面,由于行政过程因行政领域的复杂分割,而导致这方面的行政法学研究在一开始就必须进入到了具体而细致的特定行政领域,而不是抽象的理论论述层面,换而言之,这类研究自始就没有在法学方法体系的框架之内展开,而是生长于与理论体系化的行政法总论相对的各个具体行政领域范围之内。正是这样不同发展的学术路径,导致了当今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化建构的新困难。 三、困境三:形式框架难以容纳政策目的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提到,法学方法论中的行政法学体系属于学术性质的抽象理论建构,因此,学术体系是与各个具体的行政领域中的法制度相分离才获得存在的价值。也正因为如此,一旦学术分析进入到具体行政领域的法制度之中时,从体系的角度往往会将体系的理论作为大前提去涵摄具体行政法制度中的相关事项。但是,这种具体行政领域中的制度发展则对应的是现实行政活动的需要,而不是理所当然地必须适应抽象的理论框架。因此,抽象的行政法学体系究竟应该如何对应具体行政领域中的法制度,也必然影响着行政法学的体系建构。 (一)体系中政策目的的定位困境 其实就一般意义而言,行政法学的体系化一直以来也就是行政法学总论的体系建构。奥托·迈耶的行政法学自开始就有着轻视乃至无视行政法各论的宿命性倾向。(26)因此,依照构建总论的法学方法,在同一方法之下难以形成法学意义上独立的行政法学各论,各个行政领域中的法制度只是适用总论设置的抽象解释规则的对象。 但是,行政法学无论如何体系化,都必须回答发生在各个具体行政领域中出现的法律问题,因此,由各个具体行政领域中的法制度构成的行政法各论(或称“分论”)与抽象体系化的总论之间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也是讨论中国行政法学如何体系化时无法回避的事项。 从过去存在的行政法学各论的情况看,其构成方法有别于总论所采用的行政的行为形式,各论的基础是行政目的。参考对我国有影响的日本行政法学体系的形成史可以看到,早期的行政法学各论是在行政形式理论与单行法之间的层面上,将完成了一定程度抽象的行政目的与实现此目的的法技术这两个视角进行组合,形成了警察法、公用企业法、公用负担法、财政法等类型。(27)但是,在现代行政活动中,早期这种先验的目的与实现方法的当然一致性被否定之后,现代行政法学究竟该如何构建各论呈现了多样的走向。其中无论各自的逻辑体系如何布置,行政目的是其中核心的考虑要素。例如,在相关学术走向中,有的日本学者在建构各论及其体系时,是按照现代国家中社会管理功能的制度化要求,从组织法(承担者的组织化)、生活行政法(含传统意义上的警察法、公用企业法、经济行政法和社会保障法)、生活环境行政法(含公共设施法、城市规划法、开发行政法和环境保护法)等方面铺设逻辑框架。(28)再如,德国传统的行政法学分为警察法、地方自治法、建筑法和公务员法四个“相关领域”(29),德国行政法的总论正是从这四个相关领域抽象而成,其构成可以适用于这些领域的共同学术原理。但是,从当代行政所承担的行政任务而言,仅限于这四个相关领域已经不能面对行政在对经济、自然生存基础的维护、社会安全以及学术等领域应承担的行政任务,因此,在当代,环境行政法、社会行政法、学术行政法和经济行政法也成为行政法学的各论。(30) (二)我国的现况 这些各论建构方法总的取向都侧重于政策目的。但是,包括我国在内,相关学术动向中,政策目的究竟应该如何具体化和类型化,相关的基准则尚欠清晰性。在这方面,可以借助日本战后相关的学术动态作为参考点进行观察。日本战后在这方面可以看到其中的两个相关学术走向,(31)其一,行政法总论的基础是依据宪法上的法治国家原理与权力分立原理,那么,行政法学各论应该将各个单个的宪法权利予以体系化;(32)其二,由于单行的行政法律是以相关的行政组织为前提制定的,其具有将行政组织法所设定的任务和事项具体化的职责,因此,行政法学的各论可以根据行政组织的结构进行编制。这项学术归纳,也同样为观察我国行政法学中各论的建构方法提供了一个视角。 从我国当前的学术成果来看,行政法学中直接以行政法学各论为标题的教科书或学术体系著作并不多见。(33)早期的行政法教科书所展示的学术体系中,其内容有涉及各论的部分,如王珉灿主编的《行政法概论》。该书按照我国行政机关实际实施行政管理时的大体分类,设置了七个各论部分,即人事行政管理、外事行政管理、民政行政管理、公安行政管理、司法行政管理、国民经济行政管管理、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的行政管理。(34)而该类各论的建构原理旨在基本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至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行政活动。(35)而这里的这些分类,如对照我国《宪法》第89条的规定内容,可以发现,其内容基本与该条规定的内容,尤其是第六至十项的规定内容相一致。由于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即确定在总体的国家机构可行使的职权范围中设定给最高行政机关的具体职权,属于组织规范的属性,因此,该书这样的各论分类方法,可以将其归入上述的第二个种类之中。自此开始,在组织规范的层面进行分类的学术尝试一直在持续发展之中。我国在构建行政法学各论的尝试中,在对应总论的关系中,如“部门行政法”等的分类一直是被时常使用的概念。尽管“部门行政法”这项概念的定义并不确定,但其中之一的定义方法就是紧密与行政组织的职权结构相一致。(36)这类方法或许可以称之为行政机关“职权对应型”的各论建构方法,其通过总论形成的框架为基础,将与相关行政机关职权紧密相连的法律规范进行体系化整理。在方法一致的基础上,这些各论中的行政法建构,理论体系本身适用着总体的体系,只不过在名称上冠上该领域的名称,如“公安”具体行政行为等。因此,就各论中体系本身并不存在特定的意义,但是,各论之所以为各论,其本身强调着的,恰恰是其目的性,即在相关实定法的规范约束中如何保障和实现相关行政职权的合法性目的。 这样的各论建构方法以及形成的行政法学知识体系,最初步的作用可以使行政实务工作可以直接获得法学层面上的归纳和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使法律法学化,其具有直观的指导意义。但另一方面,就法学意义本身而言,如何对相应的实定法上的行政机关职权进行抽象归类,尤其是按照怎样的标准进行抽象归类,这决定着各论构建的结果走向。 如果仅仅按照现实的具体行政机关职权相关的实定法进行各论建构工作,如针对现行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职权方面的法律规范整理工商行政法,其本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适用行政法总论的要求,但是,仅仅如此显然不具有多少学术属性。这是因为,如工商行政管理行政机关职权中的发放工商执照,与公安(警察)行政机关职权中的发放机动车驾驶证,在法理层面完全属于同一类型而并无工商行政管理行政与公安行政之间的差别。 在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同样是在“职权对应型”的框架之中进行的各论建构尝试,但与上述仅仅整理实定法中的职权规范不同,这种行政法学各论建构的探讨进入了对特定行政领域中的行政活动如何进行特征概括的学理探究,同时其又关注行政法学总论理论与该领域中的特定行政活动直接的关联性。例如,近年来在警察法、药品法等方面的研究中,无疑可以看到结合中国法律制度的学术努力。(37) 在上述所有的各论建构的学术活动中,还有一点在方法论方面需要关注的是,如果依然采用“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的抽象方法去统合某个特定领域的行政活动的话,那么,其结果无疑还是设立适用于该领域的行政法学总论,或者说是行政法学总论适用于该领域的方法,其作用对相关行政活动仍然是将此整合到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的外延中而已,其依然是行政的行为形式问题。当然,由于这个整合过程也是依照既定的“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标准对行政活动的验证过程,因此,其也同时存在着反向作用。当过滤出了实定法中与既定标准不同行为形式的行政活动,便会形成特殊法的事项。在这样的前提之下,针对特定行政领域所需处理的,是属于无法由行政法学总论概括的特殊法问题。行政法学各论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性,原因之一就是对应这方面的特殊法问题。这样就会形成另一种各论,即作为与总论不同的,作为特殊法的行政法学各论。在各论层面上所需进行的学术抽象作业,肯定应该包含将这两者的整合,而建构中国行政法学体系之时,这两者理应被统合其中。 四、新体系建构的基础摸索 从上述的学术状况可见,中国的行政法学体系无疑尚未成型,且在思考如何构建行政法学体系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局面,较之可参考的法学发达国家更为复杂。概括而言,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建构所在的困境是,一方面已经无法在传统的法学方法层面上继续推进原有的思路,因为“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或具有同样功能的概念已经不能完全承担体系统合的作用,无法将日益丰富的行政法现象纳入其中。在这样的前提下,在学理层面上就必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该设置什么样的新的核心概念或者概念群,以此能够起到统合中国整个行政法体系作用。另一方面,与行政法学体系不同的另一面,现实的具体行政领域之中的法律制度及其运行方式,究竟能够在多大范围内能够被纳入学术体系,成为可以涵摄的对象范围。同时,具体行政领域中的法律问题,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行政法学体系的建构提供素材。这些问题在思考中国行政法学体系建构时是必须要考虑的基本事项。总之,中国行政法学的体系已经不可能全然按照既有的法学方法进行抽象建构了。 如何面向未来建构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这是中国行政法学者的共同任务,其最终的成型,尚需假以时日,通过学者各自的尝试和探索,在相互之间充分争论的基础上才能探究出中国自身特性的理论体系,而现今肯定最重要的是寻找出发点。 (一)新体系建构的出发点:关联领域及交互影响关系 在寻找新的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方面,我们不能全然不顾对中国已有影响的法学思考方法。如前所述,迈耶理论本身固然在今日中国作用有限,但其法学方法发展至今的成果,同样有助于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建构。因此,一方面应该关注的是中国行政法学能否形成如德国行政法那样“不受实定法秩序影响,并获得普遍承认与遵守的,包含法概念、制度、基本原则的整体教义”,(38)另一方面,这项工作还不可回避地需要纳入对于政策目的的讨论。概而言之,未来无论从何种角度建构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都应该兼容法解释功能与承担政策目的的制度设计功能。(39)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借助德国阿斯曼教授的理论,尝试着为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寻找一点当今或许可行的基础。 阿斯曼在讨论现代行政法学体系建构时,将行政法学基本理论一总论与各个具体行政领域中的法制度(各论)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交互影响关系,各论因此与既往的定位不同,形成行政的关联领域。(40)未来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应该形成于这种动态的交互影响关系之中。 这一点非常值得中国行政法学的关注,这种交互影响关系或许也不失为探求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建构的现今出发点。这里,不仅与既往的学说一样,各论——即各个具体行政领域中的法制度(包括其中的判例)属于构成总论一般性学说的素材——成为建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基石,但更关键的是,在交互影响关系的框架中,各论不仅仅停留在素材的范围之内,或者是作为单向的被法解释的对象,而是积极发挥作用,促使行政法总论理论结构适应相应的变革;反之,行政法总论也提示关联领域的制度改革,从而构成各论理论的准则。(41)通过这种交互影响关系,总论能够避免称为缺乏实定法支撑的空洞理论,从而通过建立能够应对和检讨实定法中新生问题的理论框架,完善自身建设。反之,关联领域也因此避免自身的理论是被封闭在自己独有的法解释或者法政策的范围之内的困局。 (二)当前中国可选的核心概念及其关联领域 理论体系的建构工作,首先需确定什么行政领域作为关联领域进行分析,同时,又需要决定应该选择什么概念作为基本概念,以此作为探究之出发点。 对于德国行政法中一直存在着的警察法、地方自治法、建筑法和公务员法的领域,阿斯曼首先肯定这些目前仍然是重要的关联领域,此外,根据当前重要的行政任务,他认为基于当前国家对于经济、对于自然生存基础的维系、对于社会安全以及对于学术等领域的责任,应确定环境法、社会行政法、学术法、经济行政法这几个领域为关联领域。(42) 由于相关领域中法的发展无法用行政法总论的一般论证来说明,“因为行政法学的体系与概念并不只是将行政实务予以抽象化而已,而是需要一个切入观点来选取或规范事实,这样才能发展成为学理而不只是实际行动的完成而已,而且意味行政法的体系是从国家的上位概念导出,所以国家任务的转变也会导致行政法学方法论的转变”(43)。由此,阿斯曼选择了其认为与宪法规范及规制方面的讨论具有相关性,同时也是行政法学知识起始点的几个概念作为体系建构的基本概念,即利益、行政任务、行政类型和责任作为基本概念。(44) 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摸索,同样可以自这些基本概念出发,同样可以设定同类的关联领域,并期待通过考察相互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来逐步向前推进。这是因为阿斯曼的如此设计所面对的社会和行政制度问题,中国也同样存在。但是,由于发生机制不同,如前所述,德国等欧陆国家行政介入社会的方式由秩序行政而福利行政,继而进入当前的保障行政阶段,此刻作为秩序行政功能核心的警察行政,业已发展成熟完备甚至成为法律控制密度作为严格的领域;但在中国,法治国家建设才刚刚起步,尽管如此,此时社会保障行政与生存权的关系、公共服务民营化之后相应领域政府与企业的责任分配规则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也都是行政法学必须面对的。这样,德国等欧陆法治发达国家在历史经过中经历的几个时间阶段中发生的问题,在中国成为同生共存的空间中存在的问题。警察法如此,中央与地方关系如何法律制度化如此,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之中城市规划法建筑法如此,行政组织对构成员自我管理的公务员法也是如此。因此,在中国构建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之时,警察法、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城市规划与建筑法、公务员法与环境法、社会行政法、学术法和经济行政法具有同样重要的位阶,具有同等重要的研究和发展必要性,彼此之间不应存在传统既有的或者是现今新兴的关联领域之区分。 当这些关联领域成为中国行政法理论建构的基础之时,同样基于上述与法治发达国家在历史进程维度上存在的差别,中国行政法学不能仅仅对关联领域中的法规范及其运行方式进行纯粹学术技术性的整理,而是必须考虑到中国现阶段法治国家建设尚处起步阶段的现实,因此,还必须从更高的立场,即宪法在基本权利体系方面的要求出发,对其在解释论和立法政策论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45) 在基本概念的选择方面,中国行政法学所处已远非迈耶的行政法学起步时代,已经处在无法预设一个唯一核心概念(如同奥拓·迈耶的“行政行为”概念)作为最高位阶的概念,以此统领所有其他基本概念并支撑起整个学术理论体系,而且现实的学术发展中也已经出现位阶不同的各种概念。因此,如何在纷杂的多元概念之间建立具有逻辑一致价值一贯的核心学术框架,并通过选择或设置一组基本概念来支撑起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已经成为我国行政法学可以尝试的一种方向。在此前提之下,与上述关联领域的功能同样,阿斯曼提出的利益、行政任务、行政类型和责任结构同样可以建构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基石。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上述基本概念中,“行政任务”一词所承载的学术使命在中国尤其重要和沉重。如前所述,由于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偏重与司法对应的概念,在内容上过多地反映了行政诉讼法的需求,而导致自身缺乏实体性的法理内容。(46)中国行政法学由于存在着同样的结构性问题,近年来国内出现的,在本文第二部分中第2部分内容以及第三部分中触及的“面向行政的行政法”或“规制行政法学”,其提倡者所做的学术努力也正是针对同样的问题在寻找解决方案。行政任务概念的导入,就其积极意义而言,在关联领域中讨论具体的行政任务并由此抽象出可以构建理论体系的基础,以此可以为公共政策目的进入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制造一个入口,从而将行政规制等内容整合入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本身之中。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整合作业还必须注意的是,在法治国家建设起步阶段的中国,在确定行政任务概念的定位时,与法治发达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并不相同,并没有出现适用法治主义时形式要件要求走向僵硬的局面。因此,当讨论“面向行政的行政法”等命题之时,如何避免行政(规制)法制建设脱离法治国家基本目的的走向,是中国行政法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五、结语:现在只是开始 本文归纳了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建构所面临的困境,并借助阿斯曼理论为突破该困境设置了可以尝试的方向。这里尚需指出的是,中国行政法学发展至今只有短短的二十多年,就理论体系建构而言,可以说整体上还停留在探索的开始阶段,远非欧陆法治发达国家那样持有逻辑缜密、学理充实的学术体系,更谈不上因这类学术体系发展至僵硬化而须凭借法学的外部知识进行突破。在这样的阶段,进行理论体系建构是既无传统可依凭,也无桎梏受羁绊,可以有相当大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借助现代学术业已成熟的主张和框架作为起点,无疑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本文借助阿斯曼的理论框架,只是尝试为建构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奠定第一步的基础。随着今后的学术研究进展,其结果是否定还是肯定乃至发展此理论框架,皆在可能之中。即使始终坚持使用同样的关联领域和同样的基本概念,最终此理论框架未被修改,但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的探讨和建构作业,因其内容终须紧扣中国法律制度历史的积淀和当前的问题,所以最终的结果,在内容上肯定会脱离开始时暂借的思考框架而显现出自身的特色。 注释: ①就最近的文献而言,参见赵宏:“基本原则、抽象概念与法释义学——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体系化均衡”,《交大法学》2014年第1期,第128页。赵宏认为:“我国行政法虽然在短短几十年内发展迅速,却自始缺乏系统思考和体系建构,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中国行政法学的整体和均衡迈进。”有关法学或行政法学体系化特征方面的文献,最近的成果参见赵宏:“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均衡”,《法学家》2013年第5期,第34~54页。 ②有关这方面的最近文献可见《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的“专题讨论”栏目“面向具体领域的行政法”,刊登有金自宁:“风险行政法的前提问题”、骆梅英:“论公用事业基本服务权”、宋华琳:“国务院在行政规制中的作用——以药品安全领域为例”和高秦伟:“论行政法上的第三方义务”。 ③赵宏指出:“现在的中国行政法,在整体架构上近于德日,在具体制度中又兼收英美,为提升实践操作的可能,又吸收了中国传统的行政模式和理念”。前注①,赵宏文;第127页。 ④中文版参见[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⑤[德]米歇尔·施托莱斯:《德国公法史(1800-1914)国家法学说和行政学》,雷勇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42页。 ⑥参见何意志:“德国现代行政法学的奠基人奥拓迈耶与行政法学的发展”,载前注④,[德]奥托·迈耶书,(代中文版序)第2页。 ⑦由于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中学者也时常使用“行政行为”一词,为了与迈耶所创用语概念的区别,在下文部分如表述迈耶德国行政法学中的行政行为概念时,将此表述为“(德国法学上的)行政行为”。前注④,(德]奥托·迈耶书,第98页;前注⑤,[德]米歇尔·施托莱斯书,第545~546页。 ⑧参见陈新民:“德国行政法学的先驱者”,《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38页。 ⑨参见前注⑤,[德]米歇尔·施托莱斯书,第545页。 ⑩前注④,[德]奥托·迈耶书,第64页。 (11)参见[日]人見剛:“行政処分の意義と分類”,载[日]芝池義一·小早川光郎·宇賀克也編:《行政法の争点》(第3版),有斐閣2004年版,第28~31页。 (12)[日]田中二郎:《新版行政法·上卷》(全订第2版),弘文堂1974年版,第103页。 (13)参见[日]芝池義一:《行政法総論講義》(第4版),有斐閣2001年版,第17、122页以下。 (14)参见前注⑧,陈新民文,第39页。 (15)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97页。 (16)例如,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除了复议诉讼事后行政争讼程序之外,最主要的就是第三编“行政行为”,其中最为具体展开的部分为与司法审查直接关联应对的“具体行政行为”。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360页。 (17)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将该法相关条款中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修改为“行政行为”。从修改后的该法律整体来看,新旧两个概念属性相同,其具体内涵尚待今后的判例和相应的研究成果。 (18)对于此类“行政行为”概念,赵宏指出,“尽管我国几乎任何一本行政法学教科书都不曾放弃对‘行政行为’概念的确定努力,但这一概念却至今轮廓不明,界限不清;其作为学科基石的原因从未被彻底说明,与之相关联的学理建构也显著地缺乏有机整体的容惯性。”参见前注①,赵宏文,第127页。 (19)例如,姜明安主编教科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十四、十五章(杨建顺撰写),参见前注(16),姜明安主编书,第220~307页;叶必丰教科书曾将行政决定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别称使用,表述方法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决定),但之后又恢复直接使用具体行政行为概念。参见叶必丰:《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所载图9-1,与叶必丰:《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页所载图8-1之间的差别。 (20)前注(16),姜明安主编书,第220页(杨建顺撰写)。 (21)有关此内容,参见[日]板垣勝彦:《保障行政の法理論》,弘文堂2013年版,第23~24页中引述的Schulze-Fielitz,a.a.O.,Rn.14。 (22)这里借用了日本大阪大学野吕充教授的结论。因中国行政法学与迈耶行政法学总论体系具有相当程度的同构性,再加上与德日法学之间存在着的继受关系,所以,这方面的分析应该具有很高的启示。参见[日]野呂充:“行政法の規範体系”,载[日]磯部力·小早川光光郎·芝池義一编:《行政法の新構想Ⅰ·行政法の基礎理論》,有斐閣2011年版,第53~54页。 (23)参见前注(21),[日]板垣勝彦书,第42页。 (24)有关这方面发展动向的最新综述文献有:本刊编辑部:“中国行政法学发展评价(2010-2011)”,《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第681~683页;李洪雷:“中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趋势——兼评‘新行政法’的兴起”,《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112~126页,尤其是第116页以下。 (25)同上,本刊编辑部文,第683页。与“面向司法的行政法学”相对应的“面向行政的行政法学”的命题,目前尚无直接的论证文献,但笔者记忆中,这是沈岿教授与毕洪海博士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的一次沙龙上讨论时归纳出的命题。有关此命题的综述还见于于立深:“中国行政法学30年的理论发展”,《当代法学》2009年第1期,第4页。 (26)参见[日]遠藤博也:《行政法Ⅱ(各揄)》,青林書院1977年版,第1页。 (27)例如,[日]田中二郎:《新版行政法·下卷》(全订第2版),弘文堂1983年版中的“行政作用”部分的分类。 (28)参见前注[26],[日]遠藤博也书,第18~22页。这里所提到的一些法,有的因其与总论不一致的特殊性而形成了独立的部门法,如经济法等。作者在这里的分类中只是涉及相关的社会管理内容。 (29)[德]施密特·阿斯曼:《行政法总论作为秩序理念——行政法体系建构的基础与任务》,林明锵等译,元照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1页。 (30)同上,第124~161页。可以理解的是,在当代环境行政法等关联领域首先的意义在于作为行政法学总论的基础,其次才因此而在总论的作用下同时又具有了各论的地位。 (31)有关这方面的综述文献可见前注(22),[日]野呂充文,第61~62页。 (32)这方面的成果如[日]室井力編:《現代行政法入門(2)(第4版一行政組織·主要な行政領域一)》,法律文化社1995年版。该书第86页在说明设置“主要行政领域”一编时指出:“现代行政活动非常广泛且相互深度交错,已经难以用几个类型将其全面囊括,但尽管如此,难以否定的是,现代行政法学的中心课题之一,就是在客观认识现代国家中行政作用·功能的基础上,基于宪法价值基准,明确与行政所特有的法中的原理和原则,同时通过解释论或立法政策论将其具体实现。为此,需要具体分析怎样的权利利益,通过怎样的承担方式获得保障,其与扩张中的行政权之间是否存在紧张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之中,斟酌与行政紧密相关的法的一般性特质和各种行政领域中具体的特质,并用法学方法将此描绘出来。”该书选取的主要行政领域有警察行政与防卫行政、医事卫生行政、公共设施与生活环境建设、教育行政、社会保障与劳动保护行政、经济行政、财政。 (33)这里不包括某一行政职能部门的实务法律指导书和某一行政领域的专题研究学术著作。 (34)参见前注(15),王珉灿主编书,第41页以及第三编的内容。 (35)同上,第42页。 (36)如早期司法部教材编辑部曾审定了一个名称为“中国部门行政法系列教材”系列教材,由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了《工商行政法》、《土地行政法》、《民政行政法》、《环境行政法》、《海关行政法》、《审计行政法》、《公安行政法》、《税务行政法》、《交通行政法》等多种教材。有关此事项参见孟鸿志:“论部门行政法的规范和调整对象”,《中国法学》2001年第5期,第55页。 (37)有关警察法方面的研究见余凌云:“部门行政法的发展与建构——以警察(行政)法学为个案的分析”,《法学家》2006年第5期,第138~145页。有关药品法方面的研究见宋华琳:“部门行政法与行政法总论的改革——以药品行政领域为例证”,《当代法学》2010年第2期,第55~63页。 (38)前注①,赵宏文,第126页。 (39)阿斯曼教授指出:“行政法学之方法论必须同时兼具‘适用(法令)导向的解释’及‘制定法令导向的决定’之学术”。参见前注(29),[德]施密特·阿斯曼书,第33页。 (40)同上,第11、123~124页。 (41)同上,第123页。另日本学者原田大树教授的近作也为理解“关联领域”概念提供了很多帮助,参见[日]原田大樹:“行政法総論と参照領域理論”,《法学論叢》[第174卷(2014年)第1号],第1~20页。 (42)参见前注(29),[德]施密特·阿斯曼书,第124~161页。 (43)同上,第161页注145所引Badura,Verwaltungsrecht im liberalen und sozialen Rechtsstaat,S.5。 (44)同上,第161~195页。 (45)这样的学术作业应该能够从本文第三部分中第2部分提到的日本室井力教授的思想中获得启发。 (46)参见前注(22),[日]野呂充文,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