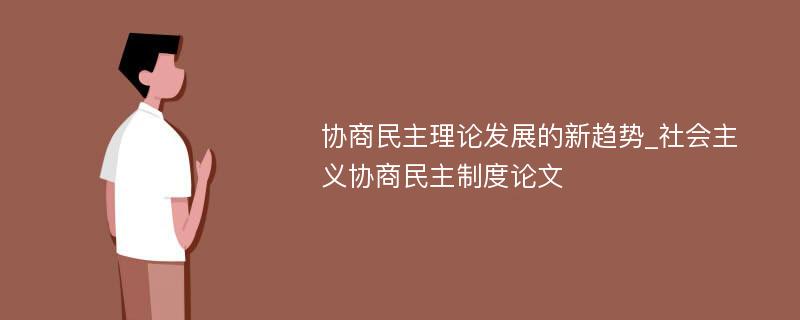
协商民主理论发展的新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趋势论文,民主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德雷泽克在《协商民主及其超越》一书中,开篇即指出,民主理论自1990年代以来出现了“协商转向”①。10年后,他在新著《协商治理的基础与前沿》一书中,再次使用“转向”一词,认为新世纪以来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发生了四个方面的转向:制度转向、系统转向、实践转向和经验转向②。其实,早在1998年,当博曼称“一个协商民主的时代来临”时他就已经注意到,协商民主的实践可行性问题可能是协商民主理论研究下一个阶段的重要议程“最佳的、也是最具可行性的协商民主方案必须接受经验社会科学的检验③”。事实也确实如其所料,自2000年以来,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越来越集中在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问题上,越来越注重对现实世界实际发生的协商活动进行经验研究。 本文将借助前贤的观察,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述协商民主理论发展的一些新趋势:从规范研究到经验研究、从理想设计到制度构建、从协商转向到民主转向。 一、从规范研究到经验研究 众所周知,协商民主理论首先是作为一种政治合法性的理想被提出来的。作为一种理想,它主要是规范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因此,在协商民主理论产生的早期,其目标是探讨政治应该如何运作,而不是描述政治实际是如何运作的。作为一种理想,协商程序应该是一个自由而理性的意志形成过程,它要求所有受政策影响的人都应该有机会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其参与的方式不是投票,而是讨论,通过公开、理性的讨论,参与者检视相关证据,反思偏好,形成共识,使更佳的论证成为决策的基础。但是,很多学者认为,建立在哈贝马斯式话语伦理基础上的这种协商民主理想是一种纯粹哲学式的协商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反事实的构想,缺乏经验基础。有人甚至认为协商民主是一个乌托邦,它不仅不可能实现,甚至在实践中是有害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波斯纳,他认为公众是糊涂无知而自相矛盾的,任何试图将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④。 面对来自实证研究领域的批评,协商民主理论的倡导者们认为,应该直面问题,做扎实的经验研究。这一经验转向的目的是为了检验其规范性诉求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协商民主理论应该去追问:现实世界中到底有多少协商?哪些因素有助于协商的有效进行?人们真的有协商的能力吗?协商到底是会产生出像协商民主理论所主张的更好的决策,还是会产生出其批评者所说的糟糕的决策?在方法论上,应如何把握复杂的协商现象? 2005年《政治学学报》杂志连续出了两期专刊,讨论的主题就是“协商政治的经验取向”,该领域的很多大牌学者均为其撰文,哈贝马斯还专门做了一个评论。专刊的导论认为,纯粹从哲学层面来讨论协商民主模式的局面已经发生了改变,大量的经验研究已经开展,通过经验研究,一方面可以检验协商民主的规范性理想是否具有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检验人们对协商民主的批评是否合理。其中,特别需要加以检验的理论预设和研究假设包括:公民能力、协商对话的质量、协商对集体和个体所产生的影响⑤。既有的研究表明,对协商民主的一些批评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协商的作用有限,但是,它确实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如此。 事实上,通过经验研究来检验协商民主规范性理想的脚步一刻未停,而且步子迈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快,很多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尤其是政治科学和政治心理学的方法,被借鉴过来用以检验协商民主的规范性理想。与此同时,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协商民主实验也为经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从1990年代初开始,菲什金就倡导协商式民意调查方法,这既是一种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也是一种经验研究方法,它就被用来检验协商民主的一个规范性命题:协商可以促使参与者对偏好进行反思,进而改变参与者的偏好⑥。2011年出版的《当人民决定》一书则致力于检验协商民主理论的另外一个基础性假设:人民是否有能力做出明智的政治决策⑦。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协商民主在很多时候不一定产生出理论家们所期待的积极结果。例如,有学者对美国新泽西州举办的5次关于种族问题的市镇会议进行考察,发现协商并没有减轻冲突,也没有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宽容⑧。 有学者提出,在未来,协商民主的经验研究至少应该在如下四个方面进一步推进:1、协商的真诚性及其证据,以区分协商性行为和策略性行为;2、多层次分析,以探究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行为者和各种中间变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3、对公民社会领域的协商和正式政治制度中的协商的质量进行比较研究;4、协商可能产生的未预期的后果和不当的后果。 当然,协商民主理论的有些主张不是经验性的,例如,经过协商程序所产生的决策合法性更高,因为协商程序尊重参与者的道德意志。协商民主的这个好处是内在于协商程序本身的,它不是协商程序所产生的结果。因此,这个主张就不适合于用经验研究的方法来加以检验⑨。 二、从理想设计到制度构建 从协商民主理论产生之初,就不断地有人质疑其现实可行性,认为协商民主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构想,很难在操作层面上予以落实。因此,很早开始,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就将制度化问题作为其重要议程之一。大体而言,关于协商民主制度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以下三个方面: 1、对协商民主的各种实践形态的发掘。这方面的努力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个方向是发掘体制内的协商资源,一个方向是探索公共领域的协商民主实践。 就前者而言,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无疑是约瑟夫·毕塞特,在其1980年发表的《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他就探讨了如何让国会恢复其协商性质。1994年,毕塞特出版《理性的温和声音:协商民主与美国政府》,对国会、总统、公共舆论在政策协商中的作用进行了系统梳理。2014年,他撰写的教科书《美国政府与政治》更认为协商民主贯穿于美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立法、行政、司法制度,还是政党、利益集团、选举,他都从协商民主的视角来加以阐释。很多学者都沿着毕塞特开辟的这一方向对不同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制度中的协商实践进行考察,产生了大量的成果。例如,鲁米斯研究了美国参议院的协商;斯坦纳等人对议会的协商实践进行了跨国比较;祖恩则探讨了协商民主和司法审查制度之间的关系;杜利斯以美国为例探讨了宪政制度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商机制。针对行政机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协商所进行的个案研究更是数不胜数。 就后者而言,可以说是近年来协商民主理论着力最多的领域,按照斯蒂芬·艾斯特的归纳,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已进入第三代,第三代协商民主主要关注的就是协商的制度化问题,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瓦尔特·巴伯、罗伯特·巴特莱特、艾温·欧弗林、约翰·帕金森和史蒂芬·埃斯特伯等。瓦尔特·巴伯和罗伯特·巴特莱特以环境政策为例,倡导建立有效的跨国协商机制;艾温·欧弗林则关注在存在严重分歧(如种族冲突、宗教冲突)的社会中协商民主如何有效运作。布鲁斯·阿克曼和詹姆斯·菲什金提出了“协商日”的构想。伊森·里布甚至提出一个更为大胆的建议,通过随机挑选的公民陪审团组建政府的第四部门——公众部门来制定法律,他还花了大量篇幅探讨如何将公众部门嵌入既有的三权分立的体制之中。约翰·盖斯提尔和彼得·列文主编的《审议民主指南》一书系统梳理了公民共识会议、公民陪审团、协商式民意调查、国家议题论坛、二十一世纪城镇会议、学习圈、民主学习中心、网络协商等实践形态,并对协商民主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马克·沃伦则通过加拿大关于选举制度改革协商的案例,展示了各种协商机制的组合运用。何包钢和陈朋对中国本土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进行了深度解析,从中提出了很多具有理论意义的洞见。 2、不同的协商领域之间如何相互衔接。协商民主理论家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关注的是不同协商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要解决的是体制内的协商资源和公共领域的协商制度创新之间的衔接问题。德雷泽克将其称之为“系统转向”,但笔者认为系统转向其实是制度转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早在1999年,曼斯布里奇就提出了协商系统的概念,后来,帕金森对之进行了发展。帕金森认为,在协商式的决策过程中,社会运动、专家论证、行政部门开展的咨询、公共听证会、公民论坛、媒体、立法机构、请愿活动等等,都可以在其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不同的沟通方式对协商具有特定的功能,例如,修辞就在协商的议程设置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⑩。 2012年,他们二人合作主编的《协商系统》一书出版,该书可以说集结了协商民主研究领域的顶级学者,致力于探讨协商民主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大规模的协商如何可能?该书提出了协商民主的系统性路径,认为协商系统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既包括村庄、城镇、学校或医院,也包括国家的立法机构,既可能是地方协商网络,也可能是跨国、乃至全球的协商网络,它们之间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每个部分都具有独特的功能,通过劳动分工,联接成为一个复杂的整体,共同以对话的方式应对政治冲突、解决现实问题。该书还探讨了协商系统运作中需要解决的一些核心问题。在作者看来,协商体系建设面临五大病理问题:一是连接过紧问题。如果协商体系中的各个部分之间结合得过于紧密,会使体系丧失自我纠正的能力;二是脱节问题,体系中的某个部分所提出的有说服力的理由无法对其他部分产生影响;三是制度性支配问题,体系中的某一个或几个部分拥有过度的权力或特权;四是社会性支配问题,特定的社会利益群体和阶级控制了协商体系中的其他群体,或对其施加不当的影响;五是顽固的派性偏见问题,公民、议员和行政官员可能由于意识形态、种族、宗教或其他的社会分歧,不愿意自己的偏好受到质疑,更不愿意听取协商所产生的意见建议。 3、协商制度创新如何与既有的制度安排进行对接?这是协商民主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其核心问题是:协商如何实现与决策的对接? 协商与决策之间的断裂一直困扰着协商民主理论。尽管在实践中确实有一些协商实践对决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是,大量的案例则是协商对决策几乎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更不用说将协商整合到决策体系之中了。德雷泽克以差不多同时在丹麦、法国和美国举行的关于同一议题的协商实践为例,说明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中协商对决策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丹麦具有悠久的参与传统,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公众,对于公民共识会议都高度认同,因此,共识会议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建议被直接交到议会相关的委员会,并对决策产生影响。与之相反,法国的议会就认为共识会议不具有合法性,甚至将其视为对自身权威的挑战。1998年法国举办的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共识会议对相关政策基本没有什么影响,相反,它是被政府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希望共识会议能提供赞成转基因技术的意见,以平衡民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怀疑。美国联邦政府从来就对组织普通公民的论坛没有兴趣,所以,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共识会议是由大学里的研究者组织的,尽管其协商结果可以对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作为多元主义模式中相互竞争的众多主张中的一种主张发挥作用的,而且是很微弱的一种声音。我们可以发现,在丹麦,共识会议与决策过程是一体的;在法国,共识会议处于被政府管理的地位;在美国,共识会议则是作为倡导者发挥作用(11)。 那么,协商可以通过哪些机制来影响决策呢?第一种方式,由协商者直接做出决策。有人认为,协商民主的逻辑应该是,协商不仅应该提供建议,而且应该有权制定权威性的法律或政策(12)。但是,这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在现实中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第二种方式,由协商者将协商结果递交给相关的决策部门(立法机构或政府部门),并对决策过程产生影响。丹麦科技委员会组织的共识会议是这种方式的代表;浙江温岭的公共预算协商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影响党委和政府的决策;德国的规划小组一开始就和政府签订响应契约,这个契约规定,政府必须考虑并正式响应规划小组的提议,即便是负面的响应,也必须说明理由。因此,规划小组本身就是政府决策过程的一个环节,这就确保了它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13)。 第三种方式,协商民主与公民投票制度的结合。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举办的关于选举制度改革的公民会议有一个创新之举:将民主协商的结果交给公民投票来决定。尽管最后因2.3%的得票之差没有通过,但它确实开辟了一个新途径,使协商与决策过程衔接起来(14)。这种方式后来也为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所采用。 第四种方式,通过影响公共舆论,间接地对决策部门施加压力,从而影响决策过程。例如,澳大利亚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共识会议就影响民众关于这一议题的认知,并促使相关政府部门认识到,不能仅仅向公众推销转基因技术的好处,应该采取更加平衡的立场。 三、从协商转向到民主转向 如果说协商转向是20世纪民主理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话,那么,民主转向则是协商民主理论发展的一个新动向。这个新动向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协商主体的民主化、协商方式的民主化和协商传统的民主化。 1、从精英协商到大众协商:协商主体的民主化。可以说,协商转向的同时也是民主转向的过程,因为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其实是将以往局限于精英的协商拓展到普通民众。自古希腊以降的协商,一直是精英的专利,协商从来都不是民主的。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协商民主其实是将协商“民主化”了,它使得协商不再局限于代表们,而是扩展到普通公民;不再局限于正式的政治机构,而是扩展到公共领域。 2、从理性到修辞、从理解到权力:协商方式的民主化。理性论证的要求是协商民主理论的核心(15)。桑德斯和艾利斯·杨都对哈贝马斯版本的公共理性概念提出批评,认为它隐含着文化偏见,会形成一种隐性的排斥机制,将很多边缘群体排斥在外,例如女性,她们很多人不具备协商所要求的理性论证的能力,她们在协商过程中更多的是提供信息、提问,而不是陈述自己的观点或参与论战。桑德斯和杨都强调各种替代性沟通形式的重要性,如礼节、修辞、讲故事乃至抗议等沟通形式,以弥补单纯诉诸理性的不足。通过这些方式,那些弱势群体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诉求(16)。 她们的观点后来得到很多人的响应和进一步深化。例如,伊安·夏皮罗就认为,协商民主理论忽视了现实政治的逻辑是利益和权力,而不是理解和更佳的论证(17)。10年后,夏皮罗的这一观点以更加鲜明的方式得以呈现:《论自利和权力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这篇由曼斯布里奇起草并由多位名家联名发表的文章认为,只要对自利进行适当的约束,它应该成为协商的一部分,而不是像经典的协商民主版本那样认为协商只能考虑公共利益,并将自利排除在协商之外。将自利纳入协商过程之中,可以让群体在思考公共利益之时更好地将每个人的特殊利益与之结合起来;同时,协商机制与非协商的民主机制之间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这意味着协商不排斥谈判和讨价还价等机制。当然,这种协商式的谈判必须是非强制性的,不能使用威胁等手段。尽管它本身不是协商行为,但是,当它被置于协商程序之中并受到程序的约束时,它可以成为协商的有益补充(18)。 3、从西方中心到超越西方:协商传统的民主化。尽管在非西方世界存在大量的协商活动,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研究者都相信,在西方世界之外协商很难有效运作。例如,迪戈·甘贝塔就认为,协商是盎格鲁-萨克斯文化的产物,这种文化建立在分析性知识的基础之上,它重视正确的推理、经验的验证;相反,有些文化则建立在导向性知识的基础之上,重视赢得争论而不是聆听和学习。就此而言,非西方文化基本上倾向于权威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19)。但是,这种情况在最近十多年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西方中心论的民主观是有问题的。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非西方背景的学者的努力功不可没。 2003年,印度裔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指出,协商是一种普遍现象,协商民主在全球各地都有其自身的根基。在他看来,协商能力、与人合作的能力、进行公开讨论的能力是人性的一部分。他还以佛教的早期发展为例,说明通过公共讨论以解决争议的实践广泛存在于印度和东南亚地区(20)。华裔学者何包钢等人则通过对中国本土协商实践和协商传统的发掘,指出中国有着丰富的协商传统,在古代中国,士大夫在朝堂之上会就公共政策开展讨论;在现代中国,还建立了专门的协商机构——人民政协。这些努力逐渐改变了很多西方学者的观念,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2014年,政治学领域的权威杂志《政治理论》出了一期专刊,主题就是“超越西方协商民主”。放在若干年前,这样的标题可能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超越西方协商民主”这期专刊中,萨斯和德雷泽克明确提出政治协商的普遍性问题。他们指出,学界对中国、巴西、印度等非西方语境下的协商理论和实践越来越感兴趣,因此,有必要追问政治协商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普遍性的实践?我们不能将西方的协商实践作为衡量的标准,要通过对不同语境下的政治协商进行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以确定协商实践可以采取何种形式,在何种条件下方可发展。他们以埃及为例,考察了伴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而出现的协商文化。专刊中有两篇文章则是以中国为例,研究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协商政治。 对非西方世界协商实践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破除西方中心的魔咒,走出协商文化特殊论的困境,而且,非西方的协商实践可以为协商民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思想资源。近期,何包钢通过对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的解析,回应了西方学界关于代表制问题的相关争论,指出中国的实践将菲什金的统计意义上代表改造成为政治代表,提高了其政治合法性,并成功地将其整合到决策过程之中。在中国,抽样代表和选举产生的代表有机结合,形成了混合式的代表制度,中国的协商民主不是削弱选举民主或代议制民主的政治逻辑,而是强化了这一政治逻辑。可以说,中国基层的政治实践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21)。 在其他地方,笔者曾呼吁,在十八大之后,尤其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出台后,协商民主研究应该将研究重心从规范性研究转向经验研究,关注协商民主的规范性理想如何才能落实到实践之中?如何才能制度化?用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话来说,就是“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既是我国协商民主实践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国际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给我们的启示。 协商民主理论在最近十多年的经验转向、制度转向和民主转向告诉我们,只有保持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在进行理论建构时对实践经验保持高度的敏感,理论的创新才有源头活水,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体系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理论自信才能水到渠成;与此同时,在关注经验事实时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才能用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实践不断向前发展。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对本土的协商民主实践进行提炼总结,对传统的协商资源进行发掘;一方面也要求我们积极借鉴域外经验,包括印度、拉美、阿拉伯世界的协商民主经验,并借助社会科学方法开展协商民主实验,不断深化对协商民主的认识,为协商民主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我国协商民主实践的发展,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共同推动协商民主理论的创新。 ①John S.Dryzek,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Beyo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 ②John S.Dryzek,Foundations and frontiers of deliberative govern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6-8. ③James Bohman(1998).‘The Coming of Age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6:400-425,here 400. ④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实用主义与民主》,凌斌、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 ⑤Shawn Rosenberg,The Empirical Study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Setting a Research Agenda,Acta Politica,2005,40,pp.212-224. ⑥James Fishkin.When the People Speak.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Public Consult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⑦Patrick Fournier,Henk van der Kolk,R.Kenneth Carty,André Blais,and Jonathan Rose,When Citizens Decide:Lessons from Citizen Assemblies on Electoral Refor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⑧Tali Mendelberg and John Oleske,Race and public deliberation,Political Communication,17.2(Apr-Jun 2000),pp.169-191. ⑨Dennis F.Thompson,Deliberative Democratic Theory and Empirical Political Science,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08,11:497-520. ⑩Jane Mansbridge,Everyday talk in the deliberative system.In Deliberative Politics:Essays on ‘Democracy and Disagreement',edited by S.Macedo.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211-239.; John Parkinson,Deliberating in the Real World:Problems of Legitimacy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166-173. (11)John S.Dryzek,Foundations and frontiers of deliberative govern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170-174. (12)Russell Muirhead(2010)Ca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Be Partisan?,Critical Review:A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Society,22:2-3,pp.129-157. (13)Claus Offe,Crisis and Innovation of Liberal Democracy:Can Deliberation Be Institutionalised? Czech Sociological Review,2011,Vol.47,No.3,pp.447-472. (14)Warren Mark E.,and Hilary Pearse,Design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The British Columbia Citizens' Assembl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7. (15)Dennis F.Thompson,Deliberative Democratic Theory and Empirical Political Science,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08.11:497-520. (16)谈火生主编:《审议民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123、323-354页。 (17)Ian Shapiro ‘Enough of Deliberation:Politics is About Interests and Power',in S.Macedo(ed.),Deliberative 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28-38. (18)Mansbridge,Jane,James Bohman,Simone Chambers,David Estlund,Andreas Follesdal,Archon Fung,Cristina Lafont,Bernard Manin,and José Luis Martí.The place of self-interest and power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Volume 18,Number 1,2010,pp.64-100. (19)约·埃尔斯特主编:《协商民主:挑战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4页。 (20)Sen,A.Democracy and its global roots.The New Republic,October 2003,pp.28-35. (21)Baogang He,Reconciling Deliberation and Representation:Chinese Challenges to Deliberative Democracy,Representation(forthcoming).标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论文; 协商民主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决策能力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