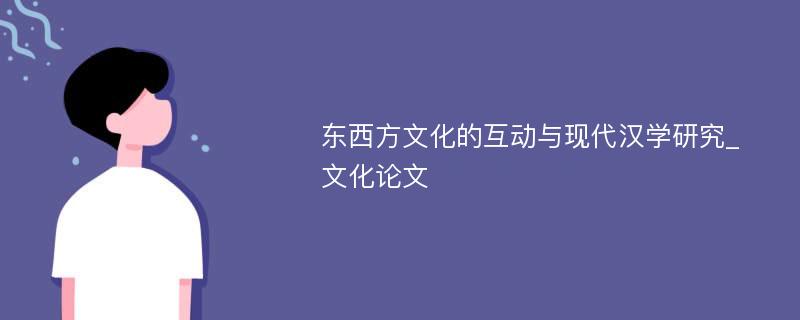
东西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学研究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互动论文,近代论文,东西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4-0013-06
西方人对中华文化的介绍与研究,如果以代表人物为标志,可以划分为马可波罗时代(14~15世纪)、利玛窦时代(16世纪~19世纪中叶)与伯希和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中叶)。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关注,是从商旅、行者的游记开始,中经传教士筚路蓝缕,逐步发展为近代以来对中华语言、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艺术、民俗等全方位的研究,最后在19世纪更加专门化而走入欧洲大学的讲堂,习惯上称之为“汉学”(Sinology)。②
在这一过程中,从“利玛窦时代”开始,东西方文化明显地出现互动,正如佛家的“灯镜”之喻,当两张镜子面对面观照中间的一个对象(灯)时,就会出现“灯镜交光,重重无尽”的现象,形成“互融互摄”的结果。近代以降,中国学者对“汉学”经历了从关注、介绍到研究的过程。
中国近代国学与汉学的互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为了“国学”的发展而关注“汉学”——主要表现为包括“整理国故”在内的“新思潮运动”中对西学方法的关注,这是中国人对汉学进行研究的早期阶段;第二,利用西方“汉学”开拓的新领域和新方法来进一步发展和深入国学研究——主要表现为通过中西交通史的研究而利用汉学成果和进一步了解汉学;第三,随着以西方人为主的域外学者对中国西部的探险考察及敦煌、考古等一系列重大发现,中国学者通过参与研究、双方合作等方式介入,使“汉学”的方法为我所用,促进了中国学术在近代的发展,从而对汉学也有所推动。
1919年底,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把“整理国故”纳入“新思潮”运动,同时,胡适还在《北京大学月刊》连载了一篇长文《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在这篇文章里,他称清代的音韵学为“有系统有价值的科学”。③在胡适这些文章的影响下,“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成为当时流行的口号和思潮。当时,另一位提倡这种精神的大学者、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在1922年指出:“西洋发明的科学,固然用西洋方法来试验,中国的材料——就是中国固有的学问,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他。”④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蔡元培两位大师,并不是简单地提倡“整理国故”、回到乾嘉时代,而是强调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这里有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背景。
就国内而言,清朝道、咸以来,“求新”之风由少数人的呼吁逐步成为学人的共识,恰如王国维所说:“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⑤道咸以降,求新的代表人物是龚自珍、魏源等人,他们从富国图强的立场出发,呼吁国人要睁眼看世界,这对学术界也产生同样重要的影响。
从国际方面看,欧美19世纪末期以来,是欧洲“东方学”兴盛的时期,汉学家人才辈出。法国学者考狄(一译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编辑出版了《西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1878~1924)及补编,创办了著名汉学杂志《通报》(T'ung Pao),以这两项成果而成为这一时段早期最著名人物。考狄之后,考狄的学生法国的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德国的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等,都是名噪一时的汉学家。福兰阁以《中华大帝国史》著称。沙畹于1889至1893年和1907年两度来中国,部分翻译了《史记》。他的三位学生: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马伯乐(Henri Maspéro,1883~1945)、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都是20世纪初欧洲汉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也为当时的中国人所关注。
早在1914年,蔡元培在法国留学时,就看到欧洲人在汉学方面的成就,因而在《学风》“发刊词”中发出感叹:“中国之地质,吾人未之绘测也,而德人李希和为之;中国之宗教,吾人未之博考也,而荷兰人格罗为之;中国之古物,吾人未能有系统之研究也,而法人沙望、英人劳斐为之;中国之美术史,吾人未之试为也,而英人布绥尔、爱铿、法人白罗克、德人孟德堡为之;中国古代之饰文,吾人未之疏正也,而德人贺斯曼及瑞士人谟脱为之;中国之地理,吾人未能准科学之律贯以记录之也,而法人若可侣为之;西藏之地理风俗及古物,吾人未之详考也,而瑞典人海丁竭二十余年之力考察而记录之;……庖人不治庖,尸祝越俎而代之,使吾人而自命为世界之分子者,宁得不自愧乎?”
这里提到的人物中,已知的有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和——今译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荷兰汉学家格罗——今译高延(J.J.Maria de Groot,1854~1921),法国汉学家沙望——今译沙畹(见前),美籍德裔汉学家劳斐——今译劳费尔(Berthold Laufer 1874~1934),瑞典汉学家和探险家海丁——今译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1865~1952),英国学者布绥尔——今译布舍尔(Stephen W.Bushell,1844~1908)。其中也有笔者尚不能确切指出姓名的学者。他们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和实地考察的成果,至今仍值得重视。而在当时,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在某些方面走在中国学者前列,对中国学者有一种刺激的作用。
事实上,在20世纪初期,许多留学欧美的中国学者都感觉到欧美东方学对中华本土学术研究的冲击。其中既有像蔡元培这样的知名学者,也有不大为人所知的学者。例如音乐研究者王光祈(1892~1936),就是20世纪20年代较早介绍德国汉学的中国学者。他与德国著名汉学家福兰阁、尉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都有交往,并翻译了他们的汉学著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西交通史研究在20世纪初发达起来。⑥中国早期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学者,都是对西方“汉学”特别关注的人。正如当时人朱希祖所说,中西交通史的主要意旨,是“撢中欧之文化,明相互之灌注。”⑦这方面研究的开创者是清末民初的学者沈曾植(1850~1922)⑧,其后,以张星烺(1888~1951)、冯承钧(1887~1946)、向达(1900~1966)、方豪(1910~1980)、张维华(1902~1987)、阎宗临(1904~1978)等人为主要代表。
张星烺先生是我国早期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学者,也是“五四”以来最早批评国人对西学“重理轻文”的人。他说:“新时代既启,留学国外者,何啻数万人。欧美之拜金主义,机械生活,随回国留学生而输入华夏。至如文学、史学、地学、史地学,以及高尚之道德、宏毅之精神,则输入者远不如机械学之多。岂中国固有之物,已足以抵制舶来品欤?抑外国所产者,实不足学欤?彼之史与彼之地,不必知欤?”⑨在此之后,张星烺先生分析了中国学者做学问方法上的缺点,即“多偏重书籍,辗转抄录”,“不注重实地探测,费力多而效果少”。他指出:“西洋人重试验,有各种学会辅助进行,各种杂志以便播布讨论。故攻读功夫,未必中国学者之劳,而所得结果,则精确过于中国也。”中国古代有一种说法,“六合之外,存而不议”,所以史书中的“外夷传”和野史中的外国著录也为士大夫所不齿,结果呢,张星烺先生指出:“迄于今日,古人所存而不议之史料,视为纰缪不经者,西人皆代吾一一证明。甚至中国版图以内多种问题,中国学者争论不定。西洋人代为调查探测,清理判决者,不一其事也。例如蒙古初起时之都城,喀拉和琳地址所在,张穆、何秋涛、李文田、丁谦等,引古证今,议论纷纷,考其究竟,终无结果。俄国之探险队,专往蒙古鄂尔坤河沿岸考查。和琳旧址即今额尔德尼昭之说,始确定矣(参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十六章注)。本国问题,且待他人为之解决。则本国之物,安足以抵制舶来品欤?外国所产者,固亦大有可学者也。中国史地,西洋人且来代吾清理。吾则安得不学他人,而急欲知彼对我研究之结果何如乎?昔契丹主谓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里云雾也。呜呼,是何今人,酷类于宋之人也!”在这里,张星烺先生道出了他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一个重要动机,即“急欲知彼对我研究之结果何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看做是早期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张星烺先生对《中西交通史》的写作,得到一中一西两位学人的帮助。一位中国学者是陈垣先生,在张之前,陈垣先生已经写了《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等关于中西交通史的重要专着。另一位西方学者是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担任《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主编的德国神父鲍润生博士(F.X.Biallas,1878~1936)。
张星烺先生对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另一贡献,是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翻译。当时译名《马哥孛罗游记》,1929年由北美印刷局印刷,燕京大学图书馆发行。在此之前,张星烺曾将英国亨利·玉尔(Henry Yule)英译本附注及法人考狄(Henri Cordier)修订补注本《游记》导言部分译出,以《马哥孛罗游记导言》书名于1924年由北京地学会发行。马可波罗是西方汉学的前驱人物,这部著作对其后“利玛窦时代”的汉学有着重要的引发作用。其中文译本的出版,使国人对“汉学”有了更多的认识。
除了张星烺之外,上文提到的冯承钧、方豪、向达、阎宗临等人,都通过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把西方汉学介绍给中国学界及大众。
冯承钧先生也是将中西交通史研究与汉学研究紧密结合的典型人物。其汉学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两个相关领域,一是法国汉学著作翻译,二是西域史研究。冯先生共翻译出版了法国汉学名著40余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达到空前的水平。翻译著作中包括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费琅等重要汉学家的著作和论文,这些作品至今仍是汉学研究的基础性文献。他除了在翻译中附加自己的大量考证以外,还写有《楼兰鄯善问题》、《鄯善事辑》、《高昌城镇与唐代蒲昌》、《高昌事辑》、《辽金北边部族考》等论文,成为中国西域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这些研究,在选题和方法上都受到汉学家的启发。
方豪先生的贡献,重点在16至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及与此密不可分的中国天主教史。这也是他的名著《中西交通史》之特色。明清之际,正是西方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时期,也就是上文提及的“利玛窦时代”。在《中西交通史》中,方豪先生用将近一半的篇幅讨论从利玛窦入华到清康雍年间传教士在华历史及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状况,开启了“传教士汉学研究”之先河。在对“传教士汉学”的研究中,方豪先生有一些独到的贡献。例如,他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携七千部书籍入中国的史实原委进行详细考订,写有《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指出金氏所携书籍,“其数量必在七千部左右殆无可疑”。并把当时北京北堂图书馆所存七千部图书的残遗,按书目一一举出,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考订七千部图书的同时,他又搜检出清朝同治(1862~1874)年间114位中国留欧学生的史料详加考订,写有《同治前欧洲留学史略》,为中西文化交流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史料。此外,他还写有《拉丁文传入中国考》、《明清间译著底本的发现和研究》、《伽利略与科学输入我国之关系》、《十七八世纪来华西人对我国经籍之研究》、《明末清初天主教适应儒家学说之研究》、《明末清初旅华西人与士大夫之晋接》、《徐霞客与西洋教士关系之探索》、《明清间西洋机械工程学物理学与火器入华考略》、《王征之事迹及其输入西洋学术之贡献》、《敦煌学发凡》等一系列涉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专论,至今仍不失为研究明清间的汉学及中西交流史的重要参考。台湾出版的《方豪六十自定稿》,收录了上述研究成果。⑩
向达先生的中西交通史研究,早年以论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及《中西交通史》为代表作,而在西域研究方面有独到的贡献。与前述张星烺、冯承钧、方豪一样,他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良好的外语背景,二是注重欧藏及域外文献。可以说,是他们这一批人,实践了明末徐光启所说“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理念。
向达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实际上是对西方汉学的介绍。在以上几位前辈的中西交通史著作中,都大量引用欧洲各国文献(亦包括少量日本文献)。张星烺说过:“书既为叙述古代中西交通而作,若仅指中国文字,而不有西国记载,则仍是片面考古,而非完全信书。中国记载,证以外国事实,或外国记载,证以中国事实。于是乃全信矣。”应该指出,这种对欧藏与中国相关文献的重视,正式欧洲汉学影响所致。在这种影响下,向达、方豪等人亲自到欧洲考察(11),以向达为例,他1935年秋赴欧洲,先在牛津大学鲍德里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抄录中西交通史资料。1936年秋转赴伦敦,在不列颠博物馆东方部检阅敦煌写卷、汉籍及俗文学等写卷,抄录了与来华耶稣会士和太平天国有关的重要文献。1937年末访问巴黎、柏林、慕尼黑等地科学院、博物馆,考察各处西方人用各种方法取自中国西北地区的壁画、写卷等藏品。在巴黎期间,着重研究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写卷,抄录了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有关文献等等。1938年秋,他携带数百万字资料返回中国。
除了文献资料的欧洲实地调查以外,向达先生还直接参与了中国西部的实地考察。他在1942年至1944年,两度作为国立中央研究院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和历史考古组长,经河西走廊至敦煌,考察石窟,写成多篇有关敦煌和西域考古方面的论文,如《敦煌藏经过眼录》、《西征小记》、《莫高榆林杂考》、《两关杂考》、《唐代俗讲考》等。实地考察本来一向为当时的中西交通史研究者所重视,而向达先生是我国在这方面第一个真正踏出书斋的学者。
向达先生由书斋走向实地考察,是受到了世界学术潮流的影响。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是欧洲实证科学重要发展的时期。这种实证科学在人文学科方面的特点之一,就是多学科的结合,如地理学与历史学、语言学的结合,引发了一系列新的学科,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方志学、考古学等等,还有在广义上的“东方学”——如印度学、埃及学、亚述学、蒙古学、突厥学、汉学等等。这些学科的出现,引导着科学家用实证方法进一步探寻未知领域,这种方法,深深影响到传统的人文学科。对这些新知识领域的探索者而言,中国西部地区乃至中亚(即亚洲腹地),是一个真正的神秘所在,同时也是让这些新学科得以施展的试验场。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概念在19世纪被接受和使用至今,不是偶然的。
用“西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问题,不仅使一些历史的疑难得到解惑,更开拓了中国学者的视野。19世纪中叶以来,以欧洲为主的外国“探险队”、“考察队”接踵而来,这种活动到20世纪初达到高潮。其活动范围,包括中国的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和四川的一部分。其考察内容,涉及民族、语言、考古、民俗、宗教、艺术等多学科领域。考察队员留下的大量考察报告、游记、日记、图录、专著等等,许多至今还在研究之中。
中国西部的探险考察,不仅在学术内容上有新的发现,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大大突破了以往的时代。以简牍学研究为例,20世纪最先发现和整理简帛材料的,是斯坦因(Marc Aural Stein 1862~1943)、伯希和等人,中国学者王国维、罗振玉等人,将汉学家发现和公布的材料,运用于历史研究并取得重要成就。王、罗两人于1914年在日本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书中对敦煌汉简中的文书作了重新分类,对法国汉学家沙畹的释文进行了新的考订。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结合传统文献,写出了一批研究汉代制度、西北史地的论文。内容涉及汉代边郡的组织系统、屯戍状况、烽燧制度、历史地理等等。其成就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其后劳斡利用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出土的汉简,作《居延汉简考释》、《居延汉简考释补证》。此外,贺昌群《汉简释文初稿》、《烽燧考》,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严耕望《西汉郡县属吏考》及补证等论著,都是利用简牍资料,对汉魏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社会文化、历史地理等各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极大地扩展了中国古代史学的视野。以上虽是举例而言,却说明了“汉学”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中国近代以来人文学科领域的拓宽和视角与方法的创新。
中国西部探险考察,开拓了中外学者的合作,促进了东西方学术上的沟通与会通。
以中国西部探险考察为媒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中西学者交往的重要阶段。这种交往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合作进行考察与探险,如1927年成立的中国和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1930年成立的“中法学术考察团”;另外一种形式,是中西学者在具体学科领域上的切磋与研究,除前文所提到简牍学研究以外,近代史有很多中外学者合作的例子。
关于第一种形式,中国学者1927年至1933年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从其创立之初经历种种磨难到最终取得丰硕成果的过程中,西方人了解了中国科学家的品格,中国人了解了西方科学的实证方法。
关于第二种形式,西方学者如沙畹、伯希和与中国学者的交往,是典型的例证。这两位法国学者,都努力学习中国历史与文化,或借助中国学者的帮助翻译汉籍。正如伯希和所说:“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而能实地接触当今代表中国之人,此种幸运,绝非倾慕埃及或希腊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运而能亲来享受者,以沙畹为第一人。”(12)在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如张元济、罗振玉、王国维、胡适、顾颉刚、梁启超、陈垣、陈寅恪、刘半农等一大批学者,受到西学风气的影响,开展了努力运用西洋研究法的新兴学问运动,今天当人们谈到一些专门学问大家,例如中外史地方面的沈曾植,甲骨文方面的罗振玉、王国维,法国汉学方面的冯承钧,中西交通史方面的张星烺、向达、张维华,敦煌学方面的王重民,传教史方面的方豪,历史地理方面的谭其骧,最早进行系统引得编纂的历史学家洪业,蒙元史方面的姚从吾、韩儒林,隋唐史方面的陈寅恪,宗教史方面的陈垣,语言学方面的赵元任,考古学方面的李济,等等,还深感肃然起敬,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受到中西学术交流的深刻影响而成就斐然的大方之家,才使得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学术,出现了蓬勃的景象。
由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到,20世纪以来的中国本土学术,是在与“汉学”的互动中发展起来的,而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也是在这种互动中完成的。
遗憾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大陆学者与汉学的互动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直到“改革开放”,人文社会学科才重新获得生机,域外汉学成果也被大量引进国内,汉学研究蓬勃地发展起来。包括专门的著作、译介“丛书”、专门期刊、专门讲座、专门学术会议、专门机构、大学里专门课程的开设及“汉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等等。这些学术现象,使“汉学研究”在20世纪末以来再度成为大陆的“显学”,一大批成果公之于世。(13)中国的学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再与汉学的互动中发展。
回顾百年的学术历程,我们看到,西方汉学与中国人对西方汉学的认识与研究,是一个互动过程;中国人通过“汉学家”(包括传教士与早期汉学家)这一中介,对本土对象进行“再认识”,不仅对本土对象的研究取得了新斩获,而且也对“汉学家”的视角和方法有所借鉴与批判;“汉学家”把从中国学者的借鉴与批判中得到的反馈,进一步运用到他们的研究中去。在这种双重互动往复中,推动了“汉学”与中国学术的共同发展,这也将是21世纪汉学与汉学研究发展的一个趋势。
注释:
①本文所说的“汉学研究”除特别指明外,是指对“汉学”所进行的研究,研究主体以中国人为主。
②“汉学”虽然在西方语言中有对应的词汇——Sinology,但在欧美的大学里,分别隶属于文学系、历史系或区域性研究部门(如东亚系)。西方的汉学在近代以后也形成比较关注现实问题的“中国学”(Chinese Studies),一般而言,“汉学”一词有更广的包容性,所以在汉语中,也用“汉学”一词指称包括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在内的研究。
③《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后改名《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收录《问题与主义》,第163页。
④《北大成立廿五周年纪念会开会词》,收录高平叔主编《蔡元培文集·卷三·教育(下)》。
⑤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遗书》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⑥中西交通史是一种旧提法,就其名称而言,受到日本学界提法的影响。现在称“中外关系史”或“中西文化交流史”。
⑦参见朱希祖(1879-1944)为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所作的《序》。中华书局,2003年6月重排本,第2页。
⑧沈曾植(1850~1922)是清末民初著名诗人和学者。字子培,号乙庵,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官至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研究南洋舆地和舆图,注重域外史料,努力吸取西方治史方法。
⑨参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自序》,中华书局,2003年6月重排本,第7页。
⑩《方豪六十自定稿》上下册,台北市,学生书局,1969年6月。
(11)作这样考察的还有王重民等。
(12)《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平》,《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
(13)参见拙著《汲古得修绠,开源引万流——关于新时期汉学的回顾与思考》,载《跨越东西方的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1月。
标签: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法国文化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汉学研究论文; 中西交通史论文; 国学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