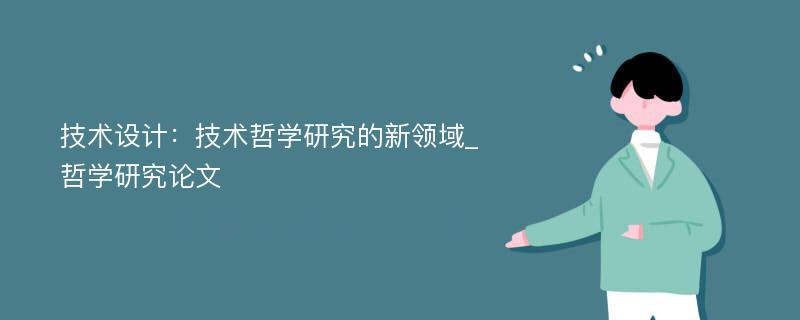
技术设计: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论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技术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8)08-0066-06
一 技术设计:当代技术哲学发展的内在意含
哲学历来被人们认为是追求智慧的学问,而智慧大体可分为理论活动的智慧和工程活动的智慧。最早的技术设计作为工程活动的智慧,伴随人类早期的造物行为就已经产生。古希腊一些著名哲学家曾对工匠、人造物活动进行过富有启发意义的探索,如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等。但自古希腊以降,在重理性轻实践的哲学理路影响下,“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①,而诸如技术人工物、技术设计的智慧等这些循着早期工匠实践传统而发展的领域并没有引起哲学家及哲学研究的应有重视,传统哲学在长期的演进中迷失了造物这一主题。②
伴随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技术这个概念作为时代的一个焦点,其象征和隐喻性意义不断凸显,技术活动日益被人们理解为问题之源。自1877年技术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的《技术哲学纲要》出版以来,在众多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技术哲学作为追求技术活动智慧的独立学科得以确立并迅速发展,成为一门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随着技术哲学的建制化发展,在现代哲学研究中产生了哲学的“技术转向”,诞生了一大批著名技术哲学家和经典技术哲学理论。在技术哲学研究中“尽管有大量的文献关注技术,但技术很少成为技术哲学家的主要主题。即使有众多著作关注技术对人的影响,但很少有关技术本身的”③,经典技术哲学理论基本上把技术作为既定事实存在加以考察,持久热切地关注技术大规模扩张的社会后果,而技术人工物、技术设计活动本身却被排斥在技术哲学关注的视域之外。人们对技术“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有用性这种外在关系来理解”④,由于忽略技术本身,经典技术哲学理论在赖以成形的一系列中心问题上缺乏一致性,没有形成集中于中心问题的内聚性理论(cohesive theory),技术哲学难以形成统一的范式,⑤ 人们对技术的探讨囿于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的对立、技术决定论与技术工具论的争论、技术人文主义与技术科学主义视野的对峙、技术乌托邦(utopia)与技术敌托邦(dystopia)的漩涡之中。
鉴于经典技术哲学研究传统的缺陷,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技术哲学研究形成了“经验转向”(empirical turn)。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转向是要使对技术的哲学分析建立在对技术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可靠的和经验方面的充分描述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对技术的预先设定基础上,使技术哲学研究更加关注那些与技术有关的技术人工物、技术设计、工程活动等问题。从现象学角度看,对技术的审视和批判“不是反驳,不是反证,而是去理解被批判的命题,理解这些命题的意义起源在哪里”⑥,探讨和分析技术就是去理解各种被批判的技术概念和命题,将其意义奠基在技术实事本身之上。人类技术系统发展到当代,技术已经成为一个复杂体系,技术概念很难用技巧、工艺、方法、知识或工具等语词来概括。美国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将技术现象分为四个层次:作为对象(object)的技术、作为知识(knowledge)的技术、作为活动(action)的技术和作为意志(volition)的技术⑦。从动态上看,技术设计的构思(基于社会需求和科学理论)相当于作为知识的技术和作为意志的技术,技术设计的实施、生产过程相当于作为活动的技术,技术设计的物化成果——人工物(artifacts)相当于作为对象的技术。可见,技术设计在复杂的技术体系中具有独立意义,技术设计就是要解决“做什么”、“怎么做”、“为谁做”的问题,它体现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变自在自然为人工自然的过程。
技术设计作为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所指涉的重要概念,是建构当代技术哲学的核心话语。对技术设计进行详细的经验描述和理解,是我们有价值地分析处理技术本身的哲学问题及其对我们生活世界影响后果的前提。因此,当代许多技术哲学家都将目光聚焦在技术设计上。卡尔·米切姆多篇论著如《作为生产活动的工程》、《思考工程》、《工程设计研究与社会责任》,从哲学角度阐述工程,展示了研究技术设计的重要性,技术设计作为一种工程活动,构成“一种崭新的哲学生活世界的模式”⑧。约瑟夫·C·皮特(Joseph C.Pitt)的《技术思考》、《工程与建筑中的成功设计——一种对于标准的呼求》、《设计中的失误:哈勃太空望远镜案例》等论著从技术行动论角度,对技术设计的分析思考建立于具体案例的经验实证研究之上,形成了以技术模型MT为基础的设计过程模型。⑨ 沃尔特·文森蒂(Walter G.Vincenti)在《工程师知道什么以及他们如何知道》中在分析飞机案例时,阐述了设计的层级性,认为:“设计过程可以在上下和水平层次上交互作用,工程是一个设计的过程”⑩。布西阿勒里(Louis Bucciarelli)在《设计工程师》中,将设计视为工程活动的核心,从社会建构论视角,讨论了技术设计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建构的社会过程。(11) 近年来,技术设计也开始进入了国内技术哲学探讨的视野中,李伯聪教授等将技术设计作为工程哲学的范畴加以讨论,(12) 陈凡教授等把技术设计纳入技术哲学研究中,对技术设计的讨论渗透在技术知识、技术认识论的研究之中,(13) 张华夏、张志林教授等将技术设计纳入技术解释研究体系之中。(14) 技术设计是一个有待技术哲学深入开辟的新领域,我们必须研究技术设计的历史,技术设计所体现的本体论承诺和认识论假设,技术设计的社会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对技术设计发生、发展的影响。
二 技术设计的哲学研究维度
技术设计的本体论研究维度。美国学者彼特·克罗斯(Peter Kroes)提出了“技术人工物的二元本性”研究纲领,认为,“技术人工制品一方面是物理客体或过程,具有特定的结构,它们的行为受到物理定律支配;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技术客体不可缺少的方面就是它的功能”(15),技术人工物的功能描述与结构描述在逻辑上彼此独立,特定功能通常可以用不同的物理学方式实现,同一个物理客体可以发挥不同功能。技术设计必须要在“一个客体的功能描述(即设计过程的输入)和结构描述(即设计过程的输出)两者之间的鸿沟上架设桥梁”(16),技术设计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功能被翻译或转换成一种结构”(17)。因此,技术设计是工程技术活动的中心环节,设计者基于对物理结构和人工物使用者的意图认知基础上,设计并制造具有专门功能的技术人工物,体现着一定的本体论承诺。设计者理解使用者意向性进行技术设计的过程则体现为一种社会建构过程,相关联的社会群体聚焦于技术设计,进行互动。在技术哲学家安德鲁·费恩伯格(Andrew Feenberg)看来,技术设计取决于形成这些设计的概念以及它们承载的社会价值。技术设计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它表现为“一个动态的、反复的设计过程,而不是一次性事件”(18)。技术设计可在不同方向发展,各种因素错综复杂地影响技术设计,只有经过相关力量的博弈,技术设计才固定下来。
技术设计的认识论研究维度。技术设计过程是一种认识活动,技术设计的认识论关注技术设计知识及技术设计过程中的认知结构问题。美国技术哲学家约瑟夫·C·皮特(Joseph C.Pitt)在《技术的反思:论技术哲学的基础》中提出“技术认识论”及其模型——“人类打算如何活动的模式”(简称为MT模式),他认为MT模式包括三个转换:第一个层次转换是我们面对某个问题所做出的决定;第二个层次转换是我们改变现有的物质状况并获得人造制品;第三个层次转换是对技术应用后果的评价。(19) 在他看来,技术设计认识活动模式是对技术设计作为技术发明、技术创新、技术应用的中心环节以及技术设计的物化成果即技术人工物的使用后果的哲学反思。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杰罗(J.Gero)提出技术设计行为的公式化、合成与评价“三阶段理论”和有关技术设计的“功能-行为-结构(FBC)”情境模式,阐释了支撑设计过程的技术知识和技术设计过程观问题。设计者与设计环境之间的强烈互动影响并决定着技术设计过程。技术设计的建构是一个逻辑-经验过程,贯穿着逻辑性的真理体系,也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折射着不同利益和不同价值观等的碰撞与交融,体现着解释-重建过程的互动。
技术设计的伦理学研究维度。美国技术哲学家P·杜尔宾(Paul Durbin)认为,技术哲学要阐释一个合理的技术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从哲学上讲,技术设计问题则具有伦理道德性质,对技术设计的伦理学分析理所当然应对其进行规范性的评价。从海德格尔的“座架(ge-stell)”到马尔库塞的“虚假需求”、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再从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福科(Michel Foucault)的“知识/权力(savoir/pouvoir)”谱系到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拟像/仿真(simulacra/simulations)”,对技术批判的解构性叙事中有着共同的理论要旨,即技术社会中技术问题的实质是伦理问题,(20) 人们比以往更加关注技术设计实施的目的、意义及伦理责任,关注人类如何按照自身的价值进行技术设计,思考如何有效控制技术工程活动。荷兰技术哲学家E·舒尔曼(E.Suhuurman)强调指出,技术设计的八个规范性原则如文化适宜性、生态可行性、和社会公正性等。(21) 技术哲学家汉斯·尤纳斯(Hans Jonas)的《责任原理——工业技术文明之伦理的一种尝试》,汉斯·萨克瑟(Hans Sachsse)的《技术与责任》的著作涉及技术设计的伦理标准和原则是什么,如何在这些伦理原则中进行协商、达成共识,技术设计伦理的地位,如何体现个人主义伦理学与制度伦理学的结合,将公众协商、合作伦理、职业角色伦理引入对技术设计的伦理分析中。技术设计活动作为社会技术事务,技术设计者肩负重大社会伦理道德责任,需要让设计对象的使用者参与设计过程,促进技术设计的人性化发展。
技术设计的方法论研究维度。技术设计方法论主要任务是探讨技术设计、工程设计及工业设计的一般规律与方法。近年来,技术设计的可控性、安全性、有效性、不确定性以及技术设计的组织空间、风险、可持续等问题引起技术哲学家的高度关注。美国技术哲学家保罗·汤姆森(Paul Thompson)分析了技术设计与排他性成本、让渡能力和竞争这三者的关系,荷兰哲学家格乌斯·伯克霍特(Guus Berkhout)提出了技术设计如何依据技术与社会因素之间平衡关系展开,体现怎样的社会—技术系统设计变迁的循环模式。(22) 技术设计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活动,工业革命以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技术设计的方法论流派,诸如包豪斯主义(Bauhaus)、流线型设计(streamlining)、商业性设计、现代主义和绿色设计等。技术设计活动与科学研究活动既相似又相区别,技术设计有着特定的方法,技术设计除了常规性设计方法之外,技术设计的方法还有系统性设计、功能性设计、工效学设计、最优化设计和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等。
三 哲学视域下技术设计的研究进路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使得我们时代的人类智慧定向在整体这块基石上,形成整体思维的时代特征。(23) 在技术化的社会中,随着技术设计越来越成为一个与周围环境相联系的整体系统,我们思考技术设计,也必须用一种整体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立足于技术实践,多层次、多角度地推进技术设计的研究。
多视角整体透视技术设计,把握技术设计研究的当代趋势。技术设计是历史地形成的复杂而多样的技术现象。对技术的整体不加批判地接受与对技术的极简单的拒绝都是不可取的,技术哲学要建立在对技术工程实践的经验描述基础上,对技术进行经验案例分析与规范评价。技术哲学家阿诺德·佩斯(Arnold Pacey)认为,经验是丰富的、多层次的,它既包括知识和实用技巧,也与政治、价值、信仰等相关联,经验既具有社会共享属性,也具有个体属性。(24) 技术设计作为经验性概念,从哲学维度看,既要坚持把技术设计活动视为整体进行描述和阐释,以思辨的方式思考技术设计相关联因素的“整体的方法”,又要坚持从本体论、认识论等角度对技术设计进行经验性的阐释和细节分析的“分析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影响,形成了技术的社会建构(SCOT)分析模型,将技术纳入社会学框架,阐释技术可以不只通过一种方式来进行,在各种不同技术可能性中存在多种选择,一种技术形成要塑造(shape)于特定环境。
将技术设计置于当代技术实践之中,生成技术设计研究的特定语境。我们正处于一个复杂的技术社会语境中,随着20世纪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卡尔·米切姆提出了元技术(metatechnology)这一概念,它是指相对于前现代技术与现代技术而言的后现代技术。(25) 在卡尔·米切姆看来,前现代技术是与农耕社会田园生活相匹配的一种建构性技术设计,现代技术作为单一的利益工具是通过机器、工具理性等对工业社会进行解构的技术设计,后现代技术是通过信息网络等具体技术形式压缩了时空,使不同国家地域、种族人群、文化传统、社会组织、经济形态整合重构的技术设计。显然,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种类型的技术设计旨趣存在巨大差异,对前现代以及现代技术设计的反思与批判,对后现代技术的建构性设计必须将其纳入到特定时空的技术形态语境中加以研究。人们对技术“在所谓后现代、现代、甚至前现代的体验、实践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和连续性”(26),我们必须去关注“跨现代”(transmodern)的技术语境中错综复杂的技术设计。
整合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式,形成技术设计研究的基本纲领。技术设计既“依赖于功能与用途观,包括范式引导,功能的解释”,又“依赖于概念和工程的模式,它们来自于不同的学术、职业和组织文化”(27)。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哲学研究受相应哲学传统和技术社会形态的影响,形成审视和反思技术设计的不同理论倾向和研究范式。技术哲学家伊德(Don Ihde)将西方技术哲学研究分为杜威学派(Deweyans)、埃吕尔学派(Ellulians)、马克思主义学派(Marxians)和海德格尔学派(Heideggerians)。(28) 在技术设计的研究中,需要去综合不同范式,如杜威学派的实用主义理论范式对技术设计发生演进研究的启示,埃吕尔学派的技术社会理论范式对技术设计自主性的探索,海德格尔学派如伊德的技术现象学理论范式对技术设计及其人工物的本体论追问,马克思主义学派如安德鲁·费恩伯格(Andrew Feenberg)的技术批判理论对技术设计的全方位透视,技术哲学家伯格曼(Albert Borgmann)的“器具范式论”(Device Paradigm)从后现代视角对技术设计的建构性分析,温纳(Langdon Winner)对技术设计的政治学解析。不同范式的整合,将实现对技术设计外部与内部、静态与动态的综合性研究,达到政治、社会、制度、文化等的“视域融合”。
推进相关学科领域的交叉研究,体现技术设计的综合性特征。工程师、设计师、技术人员都是技术设计的直接实施者,技术设计的组织研发者、工程科学、技术理论研究者们也都参与着技术设计活动。如C·P·斯诺在《两种文化》中所言,由于大多数人只属于一种文化,工程师在具体的工程实践过程中思考技术设计,工程科学研究者在理论建构中理解技术设计,都不免对技术的理解太狭隘,也就很难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并取得共识,必须解决技术设计研究者们对技术的“知识完备性(intellectual integrity)”问题。技术设计研究“包括多种学科的及各体系间相交叉的技术问题,需要社会学家和通晓数门知识的学者进行学科间的合作”(29),对技术设计的跨学科、跨领域研究,意味着学科背景、知识结构各不相同的研究者都可参与技术设计研究,从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中把握技术设计的相关问题。卡尔·米切姆指出:“工程变得越来越哲学化了,而哲学也变得越来越向工程思想和工程实践敞开”(30)。“在后现代世界中,工程师是未被承认的哲学家”(31),对技术设计的多学科研究使技术哲学突破工程主义、人类学的抽象层面,深入到技术内部,达到对技术的感性知觉与理性审视的有机统一。
四 技术设计视角对技术哲学研究的意义
对技术设计的哲学分析使技术哲学的追问基点建立于可靠的技术实事本身之上,有助于真正打开技术黑箱(opening the black box of technology)。F·拉普指出:“技术的第一特点就是它总是一种事实上给出的现象。不能无视具体的经验证据,只根据对技术的逻辑的和不变的本质的思考,演绎出技术的现实特点”(32)。约瑟夫·C·皮特认为,按照认知顺序来说,技术的“认识论问题比社会批判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33),技术哲学要集中于有关技术的经验性概念框架,阐述技术的经验性概念,从而对现代技术进行充分的经验描述,消除关于技术的种种神话和抽象虚构。更加关注技术的设计、实施与发展问题,理解技术本身提出的哲学问题,理解我们对于技术所知道的东西及其可靠性。从而区分“关于技术的学问”(question of technology)即对技术本质的描述和接近和“追问与技术有关的东西”(question of something related to technology),即谈论与技术有关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的话题。对技术设计的哲学研究并非仅是描述或支持已有的哲学理论或观点,更不是简单地将哲学分析应用于技术设计这一事实,而是要在技术设计实践中为“打开技术黑箱”提供一个稳固的经验基础。
对技术设计的哲学分析使技术哲学的提问方式发生巨大转变,使对技术的本质解读、价值分析和发展透视,建立在对技术设计实践的内在洞察和经验充分描述基础上。对技术设计的关注把技术哲学由研究抽象的、整体的技术及其后果,引向探索具体的技术设计形态如何影响人们的物质及精神生活。技术设计将技术本质理解现实地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之中,思考谁制造了技术设计,为什么制造技术设计,如何制造技术设计等问题,超越了对技术本质的非历史的(unhistorical)和超历史的(transhistorical)的概念建构和解释。“现代技术既不是人类的奴隶,也不是不可变异的铁笼,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框架,其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并且是可以改变的。”(34) 技术设计过程不仅是追求理性控制和功能效率,而且价值取向及复杂意义蕴涵在技术设计过程之中,内化在技术发明和成果之内,直接影响着技术使用产生的效果即外在价值。因此,技术不是“人类无法逃脱的天命”,不是“中性的工具”,也不是“具有绝对效率的方法总体”,而是与社会协同进化(co-evolution)的。(35)
对技术设计的哲学分析有助于人们更加自觉合理地进行技术控制,真正使技术实践朝着有利于人的方向发展。法国技术哲学家埃吕尔提出“适当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概念,英国学者罗宾·克拉克提出了“替代技术(alternative technology)”理论,对技术发展的未来方向进行展望。而“我们在从事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与发展或运用传统技术之前,必须反思我们的目的和价值,必须有效地控制技术。”(36) 要控制技术就要重视技术的设计。技术设计是一项牵涉众多因素的复杂活动,“不是一种命运而是一个斗争的舞台,它是一个社会的战场……在它上面的人们讨论并进行着文明的选择”(37)。安德鲁·费恩伯格提出“参与民主”的概念,即人们在特定的民主制度下参与那些影响他们自己的技术设计事务的决策,技术的设计过程是由不同的社会角色参与开发技术的过程。(38) 技术变革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technical change)要求对那些不占有任何资本的社会角色开放技术设计过程。民主化意味着增加了技术设计过程中社会角色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拓宽了技术设计的可能性,这也就形成了技术的可选择性,同时在更深层次体现了现代性的可选择性。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7页。
②(12) 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大象出版社,2002,第12~15页;第95页。
③ H.Achterhuis,Americ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1,p.56.
④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第88页。
⑤(13) 郭贵春、乔瑞金、陈凡:《多维视野中的技术》,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第25~33页;第48页。
⑥ 倪梁康:《现象学的效应》,三联书店,1994,第178页。
⑦ Carl Mitcham,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159.
⑧(30)(31) Carl Mitcham,“The Importance of Phiosophy to Engineering”,Tecnos,1998,p.17; p.45; p.21.
⑨(19)(33) J.C.Pitt,Thinking about Technology:Foundations of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New York:Cambridge Press,2000,p.12; p.42; p.33.
⑩ Vinceti,“The Experimental Assessment of Engineering Theory as a Tool for Design”,Techne,2001,p.5.
(11) Louis Bucciarelli,Designing Engineers,Cambridge,MA:MIT Press,1994,pp.18~21.
(14) 张华夏 张志林:《技术解释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第29页。
(15)(16)(17) Kroes,“Technical Functions as Dispositions:a Critical Assessment”,Techne5:3,Spring,2001,pp.1~16.
(18) Rothwell R,Reindustrialization and Technology Longman,1985,p.48.
(20) 冯俊:《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88页。
(21) E.Schuurman,Beyond the Empirical Turn:Responsible Technology[EB/OL].http://www.home.planet.nl/~srw/sch,2004~02~13.
(22) 陈凡、朱春艳、赵迎欢、田鹏颖、马会端:《技术与设计:‘经验转向’背景下的技术哲学研究——第14届国际技术哲学学会(SPT)会议述评》,《哲学动态》2006年第6期。
(23) 乔瑞金:《现代整体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第21页。
(24) Arnold Pacey,Meaning in Technology,Cambridge,MA:MIT press,1999,pp.6~9.
(25) Carl Mitcham,“Note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MetaTechnology”,Techne,Volume1,Number1,1995,p.32.
(26)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第78页。
(27) W·拉莫特:《技术的文化塑造与技术多样性的政治学》,《世界哲学》2005年第4期。
(28) Don Ihde,“Philosophy of Technology,1975~1995”,Techne,Volumel,Numbers1~2,Fall,1995,p.48.
(29) Paul Durbin,“Adances i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Techne,Society for Philosophy & Technology,Volume4,Number2,Fall,1998,p.62.
(32) 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刘武等译,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第19页。
(34) Andrew Feenberg,From Essentialism to Constructivism: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t the Crossroads,www-rohan.edu/faculty/feenberg/talk4./html.
(35)(38) Andrew Feenberg,Alternative Moderni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44; p.67.
(36) 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人民出版社,2002,第7页。
(37) Andrew Feenberg,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