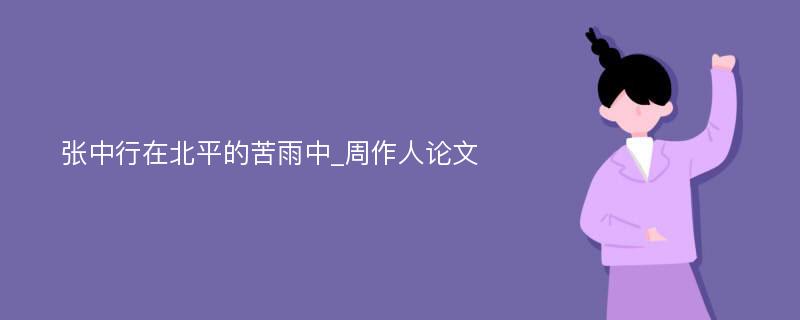
北平苦雨中的张中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平论文,雨中论文,张中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1936年,张中行从北大毕业,辗转来到南开中学任教,一年后与何其芳一同被学校辞退,后到保定的一个中学觅到教职。这一年暑期他和保定姑娘李芝銮结为百年之好,回到北平探亲。不料恰逢七七事变,日本人占领北平,竟不幸成了困城里的囚徒。
在张中行的记忆里,日伪时期的日子,可谓不堪回首。日本侵略者来了,国土沦陷,百姓的日子极为艰辛。他的自传对此有过描述,给我很深的印象。只是笔墨太少,没有细谈,对读者是个遗憾。我后来翻看《流年碎影》,心想,那个时代的风雨对其一生都是巨大的影响,可只留下了一点点印迹,也许是不愿意多费心思,也许有难言之隐。不论如何,非人的生活,回忆起来是苦楚的。国家的巨变,对他来说是无可奈何的事。他自己是个小民,无力于身边的世界,只能是个看客。后来连看客也做不成了,于是穷,无职业。当时不仅他这样的青年挨饿,连周作人这样的名教授也遇到了生计上的困难,为职业而苦苦找寻。那时一些有一点成就的学者,在气节上还是保持住了清白,比如钱玄同、顾随、马裕藻等。钱玄同在日本人进城后,闭门不出,更名钱夏,立志反日。顾随还差点因抗日被俘,及时逃脱掉了。也有抵抗住诱惑,坚持本色的人,比如俞平伯,三十年代末无奈出席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大会,还被任命为“华北文艺奖”诗歌方面主审委员,为了活命,不得不在《同声月刊》发表作品。其间沈启无主编的《文学集刊》也有他的作品。这引起了朱自清的注意,写信劝其不要和类似的杂志发生来往。最后只能靠在家辅导几个学生和在大学兼课聊度时光。在水深火热之中,读书人之苦可想而知。
比之上述诸人,张中行的状况更差,活下去的路就更少。开始听到周作人被日本人拉拢的事情,他曾写信劝其不要出山,那原因是有失人格的。可后来实在活不下去,竟也找赵荫堂等人帮忙,在北京大学找到了助教的席位。那时的北大被称为伪北大,声誉并不好,也只能不顾了。接着是物价攀升,境地似乎并未好转,反而越来越难了。与此同时他还在几个报刊上撰文养家糊口,署名疑堂等。文章不过社论时评、文化随笔之类。我问过此事,他不太愿意回答,以为是没有意义的。在《流年碎影》里,他很坦率地写到了这些,并不回避自己的困惑和无奈的选择,心里的隐痛是强烈的:
兼课的一条路不能再开辟了,因为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再加码。写可有可无的文章一样,因为还不愿意高明的任何熟人看见齿冷,产量就不能过大。剩下的一条路是各时代一些头面人物关系走的,是托靠一些社会关系,或者说有位者关照,闭门家中坐而也能分得些残茶剩饭。几年以来,由于涂涂抹抹,我与活动于所谓文化界的一些头面人物有些往来,而这些人,有的就同一些有位者有或远或近的关系。这种情况使不费力而分得一些残茶剩饭的机会成为不难得,如何对待呢?曾经退避,因为想到,上课吃粉笔面,卖文稿,总可以是在岸上,至多是临渊羡鱼,至于以器与名假人,以换取一点点可怜的伪币,就是跳下去了。可悲的是生活越来越困难,在活着与洁身自好之间,本诸“天命之谓性”,我还是只能不再思三思,现顾活命。具体说是,接受了友人的关照,先后两处,挂个闲散的职名,每月可领一些钱和粮食。这在当时,由生计方面考虑,也许竟是可行的。有时甚至想,生为小民,总会有大大(受侵略、战争、改朝换代、运动之类)小小(压榨、欺凌、抢劫、偷盗之类)的人祸送来各种苦难,抗,也许很难吧?那么,想想办法,在不吃别人肉,不喝别人血的情况下,求能活过来,就不应该吗?通常的答复是两歧的,农工商可以,士不可以。
不幸的是竟沦为知识分子!但既已有知,想退回去住伊甸园是不可能
这里埋藏了许多信息。只是点到为止,深层的内容读者只能自己思考了。当年他曾和刘德水谈过这个问题,说当时汪伪北平市党部有个委员运动到了南方某县长职位,出现空缺,只要填个表格,就能每月领到一袋洋面,一位朋友知道他家境困难,找到他,为了一家人能够活下去,他填了。而事实上是什么也没干——这个党部的存在,也只是表明这儿还有个基层组织而已。可是在内心深处,他也感到一种沉重的道德负担。这种道德负担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内心的自省——更多的是读书人不能摆脱外界的侵扰、尽享自己宁静的书斋生活的无奈。他对刘德水说:总结这一生,感觉活着很不容易,如果说有什么让自己感到惭愧的“污点”,那就是先后两次的“入党”(一次是通县师范北伐时期)了。我也曾和他探讨过一些附逆问题的往事。他的回答是,民活主义,只要活就可以,道德次之。西方人在战场上被俘,投降不属于气节问题,因为人活为首义。这是人道的考虑。关于这一点,他在晚年的一篇下了大力的一万五千字的长文里做过集中阐述,题目叫做《评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收于《散简集存》及《民贵文辑》)。日伪时期的北平,之所以有许多文人无奈呆在伪职里,不都是信仰的问题,没有活路是主要的原因的。袁熹先生在《从工资、物价看沦陷时期北平人民的生活》中说:“1939年北平发生粮荒,伪政权实行粮食的配给制度计口售粮。1942年1月1日,日伪华北政权宣布实行免分配给制度,5月份购买大米也开始实行配给制度。由于日伪政权加紧掠夺,粮荒日益严重,粮食配给日减。年底,公职人员亦停止供应大米,白面由每人一袋减至半袋。普通市民只供应粗粮,不仅数量少,质量低,而且价格昂贵。”如此凄惨的现状,文人在传统理念和现实生存间,有的选择的是活命。可是中国的文化心理是排斥这些的。这就遇到道德与生命价值的冲突,哪个更为重要呢?显然,在这一点上,他是儒家哲学的反对者,因为忠君、舍生取义,不合于人性。君是暴君、昏君,也要为之守节么?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可是几千年来,这个问题被完全颠倒了。在道德和人性的尺度里,后者的价值是该高于前者的。
此类观点,私下议论没有问题,但形诸文字,就难了,不免招来非议。启功回忆录里也曾讲到日伪时期自己的无奈,竟到伪北平政府里谋了职位,也是为了活命的。后因被自己的老师陈垣骂了回来,避免陷入更深的苦地。那时候的周作人、沈启无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文章只谈古文化,讲讲风俗,谈谈天气,玩玩文物。周作人、沈启无甚至还为共产党人提供了方便。人是复杂的,复杂的环境,也造就了复杂的人和文化。若是考察那时的文人写作,不能不感到精神的异样。日伪时期的报刊在风格上除了无耻的大东亚文化理念外,就是沉闷的古人气味。上海、南京、北平的几个杂志,都是一种调子。文中普遍讲学问气,儒雅而从容,从历史讲到国民性,从文字的理论说到版本目录之学。言论是受到限制的。当文人只能够在风月里绕的时候,精神是萎靡的,尤其在国破的时期,周作人、胡兰成的文字就是这样。虽然好,可是与真的人生是远的。
张中行和周作人不同的地方,是他对欧美的哲学有很深的兴趣,日本的文明对他是隔膜的,所以就有东亚以外的学术背景。在骨子里,是不愿走近日伪文化的圈子里的。写作时候也许会有应景的文字,可那并非自己真实的思想。文章成了啖饭的拐杖时,真的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欧美文化,不太容易让人在主奴的关系里存活,东亚的文明不幸的是,偏偏陷入主奴的关系里,怎么能不让人深恶痛绝?他晚年喜谈英国与德国的哲学,鲜及日本,是与早年的记忆有关呢,还是知识结构的问题,是大可探究的。
2
对一般的文人而言,故都是死去了,只要写到北平,都有忧伤的感觉。留守在故都的文人,在那时写下的,也不过风月、民俗、古董类的文字,文风整体是沉闷的,几乎看不到热血的篇章了。那时出版的《艺文杂志》、《中国文艺》、《新中国报》、《实报》、《庸报》、《中和月刊》等,都是些平淡、雅气的作品,被古风所袭,或附庸于日本人的躯体,肉麻的亲善之语,或静心谈学,与时风无涉。文章多书卷气,被日暮的沉闷所笼罩,久久地陷在雾霭里。俞平伯写着诗词、昆曲的研究文章,顾随讲古文与小说,沈启无谈诗,耽于趣味,沉于冥想,是非冲动的淡语,静谧的走笔里,将市井里的阳光、空气都隔开了。
与他交往的前辈,大凡深一点的,都能品出内心的沉重。周作人不用说了,他后来结识的顾随,就给他苍凉的感觉。还在张中行读北大之前,顾随的诗文就已很出名了。1927年印行的《无病词》,1928年编辑的《味辛词》,以及后来的《荒原词》、《留春词》、《积木词》等,在朋友间悄悄流传着。后来,当张中行读到这些作品时,是大为佩服的。有时也是心有戚戚然的。顾随的诗词有荒冷的意向,是旧体的与现代人的感受的杂糅,格调自创一路,全不落俗套,高而凄凉,绕人心肺,久不散去。作品多梦语,残阳、冷照、落花、秋水,苦吟愁唱,煞是感人。张中行后来也填词,境界却一直难及顾氏,所以晚年有人夸赞他的文字时,他是不敢欣喜的,因为有那么多前辈高手在,也只好自认平平了。
顾随的笔名叫苦水,文字常有凄楚的清音,有天人之象,是学不来的。他出语飘逸清寂,直指苍穹,有佛气与庄生气,还带着曹雪芹式的悲凉。那些诗文有对病痛的无奈,也多对生命无常的惊悸。却又没有消沉的下坠,总是有美的灵光闪动着,让人随着攀援智性的高峰。与顾随的作品相逢是他的快事,许多年后回忆这位老师的遗产,他的敬佩感是仅次于周作人的。
较之于顾随,俞平伯的作品则是古水里泡出的香木,自是一绝。就才情而言,均无法与废名、顾随相比。张中行对他的感觉是另类的,也许是儒者的风范更吸引自己吧。俞平伯是新旧参半的学人,他对古代诗词的研究,有不凡的见识,关于《红楼梦》的解读那是才学耀世的。俞平伯治学的方法和胡适不同,与顾随的才子式的独语也有别。他善体味古人情思,又能从史料里把握人生,谈论问题温文尔雅,从容而自信。就思想的高度和审美的深度而言,俞平伯都算不上高人,他的对现实的理解有时甚至还显得可笑。但他身上流动的文人的古风,在张中行看来是难得的。他的治学方法虽旧,但功夫不浅,比如谈古诗十九首,就九曲十折,从文献里找材料,在体悟中辨曲直,就心境的自如与坦然而言,是超然于世的。那么喜欢旧诗文,却又能发现前人读解时的问题,在一般学者是不易做到的。这样的功夫,张中行就欣赏不已。俞平伯的文字是寂寞的,在品读旧诗文的过程,也渗透着无量的悲哀,似乎也有排泄不去的苦恼。有苦恼,就有语言的真意在,在词语间流着爱意。那样的纯正而无邪的存在,在是非四起的地方,没有一丝的影响,还散出清幽的气息,总是让他如临清潭,心情是愉快的。
在他的老师里,赵荫棠的文字也很有特点,杂文的风格有峻急的一面。赵荫堂是周作人的朋友,思想是沉浸的地方居多。他有时也很幽默,在文章里说一点笑话。赵氏喜谈掌故,对历史的看法颇为深切,又无夫子气,见识是高的。看过他的一篇谈剪辫子的文章,散淡多致,韵律和鲁迅略有相似,对专制统治的看法是切齿的仇恨的,行文老到,出语深切,纠葛着历史的伤痛,却又有超脱的笔致。他的《奕齐记》、《述酒》、《艺术杂谈》、《穷之赏玩》都是好文章,不知为何却不为后人注意。他的思想在根本上与周作人是一路,或许是受到周作人的影响也未可知。比如都厌恶载道的文章,喜欢性灵的、有趣的、文不雅训的存在。《穷之赏玩》就说:
蒲松龄也有祭神文,大概受到杨韩的影响吧?朴实也是个想达而在上的人。但在他连考数次举人不中,便绝望了。此后,他的生活过得倒很潇洒,饮酒赋诗,骑驴逛山。在文艺的成就说起来,我觉得他比韩愈高。一部《聊斋志异》,可以抵十部《韩昌黎文集》。
此话似乎和周作人一样,是反伪道学的。他们都远离道貌岸然的艺术,沉浸在心灵的游戏和智力的探险里。京派文人的这一点,一直左右着北平的学术风气。张中行也是对此心以为然的。京派文人不都是贵族气,有许多是平民化的,赵荫堂就是这样的。他和张中行交往较深,一生多厄运,学术之外,人生可以说是失败的。张中行回忆道:
记得同一位老友说过不止一次,观照人生,就不由得想起孟德斯鸠辞世时的一句话:“帝力之大,如吾力之微。”人力,究竟能把命运扭转多少呢?这命运,或说定命,不是指神秘意义的,是指科学意义的,即天性加机遇。天性,大的如聪慧与愚钝,小的如近酒与远酒,机遇,大的如生在什么社会,小的如买的火车票,对号,碰到哪个座位,都很少是人力所能左右的。不能左右,也不能躲,剩下唯一的路,不管欢迎不欢迎,只有顺受。这所受,表现为顺成逆,更向身边贴近就成为得失,成为苦乐,成为荣辱(只世俗的)。言归正传,赵荫堂先生,用这两个条件衡量,情况怎么样呢?我的私见是逆多顺少,所以一生是颠簸(或只是心情的)时多而安定时少。分开说,天性,他是庄子说的“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所以积极不能走顾亭林的路,消极不能走邵潜夫的路,能走的只有李笠翁一条路,由旁观者看是不能洁身,不能乐道。机遇呢,他惯于没有遮拦,可是环境常常很需要有遮拦,因而就圆凿方枘,轻则成为不协调,重则会成为悲剧。
这样一个悲剧的人物,也能写一手好的文章,不能不使人感慨系之。满肚诗文的人,有时是命运坎坷的。京派学人,多是没有身份的普通读书人,知道人间的冷暖,也就能以平静的心态谈一些掌故和学识,文字闪着精神的张力,那是对苦楚的人生的慨叹吧?也由于此,这些京派作家和学人的自我的内觉丰富,思想是内敛的,自己和自己交流着,挺进灵魂的深处。他们学会了在乱世里的独处,能从静观里打量人生和世界,历史的眼光和审美的视野都是特别的。他们也玩玩古董,写写画画,但思想却不都沉浸在远古的过去,而是悄悄地与当下对话。作为一介书生,他们知道自己无力改变世界,但也不想污染这个世界,希望保持着精神的纯洁。且从历史的旧迹里觅出今人的参照,知道何路可行,何人可念。失落的闪光可以还原么?什么对世间更有意义?
在那样的乱世,这样的状态的人有许多,后来却渐渐稀少了。张中行在心里知道,世道浇漓,民乱不止,精神的美质渐难保存了。自己做不了英雄,也非坏人,那么就安于平淡,做个读书知礼之人吧。他身边的老师和朋友,多可成为人生参考。在这些人的光环下,生活庶几不会荒凉的。所以,理解张中行的世界,他周围那个世界里的人与事,不能不读的。对照起来一看,精神景观的逻辑线条,就清楚了。
3
张中行在三十年代开始写作,主要以杂文随笔为主。但其文晚年才被世人关注。其文章多以讲文坛旧事为主,那些关于学界的林林总总的掌故,大有《世说新语》之状。不过他讲了许多大人物,却放过了鲁迅。我问他为何如此,他说,不太好谈。讲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都容易,而说起鲁迅则是大难的。为什么呢?他的思想深,精神阔大,语言婉转多致。一般人与他的距离,总还是太大了。
当他到北大时,鲁迅已离开北京,能见到的只是周作人、钱玄同等五四的人物。所以鲁夫子的音容笑貌只是从别人的谈吐那里得到,再就是阅读作品感受其间的神韵了。张中行极为欣赏鲁迅的小说,尤对阿Q的形象感兴趣,以为那是了不得的创造。他教书时,讲到白话文,也推崇鲁迅的文章,用其作为例子启发学生。关于鲁迅,他从周作人那里得到的都是正面的信息,没有坏的评价。比如五十年代初他到苦雨斋去见周作人,谈到世风,周氏就有“鲁迅如活着,不会像郭沫若那样”的话。
在精神的深处,张中行是推崇这位思想者的。虽然没有系统地谈论鲁迅的文章,但在私下的言论里是很佩服鲁迅的文字的。在他看来,鲁迅的智慧太高,常人无法及之。他在《作文杂谈》里写到对鲁夫子的感受,是强烈的:
那还是《呐喊》刚出版之后,买来,先读《自序》……觉得意深刻而语沉重,也是爱不忍释,于是反复念了几遍,以后,偶尔也有寂寞甚至幻灭的悲伤,就找出这篇文章,一面沉思一面吟咏地念一两遍,这时候,心情完全渗入文字的意境中,觉得理解和收获比初读的时候多多了。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话,那就是鲁迅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大家跟他不上。就知识结构而言,鲁迅有哲人的一面,康德、尼采式的东西都有一些,现代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是颇为了解一些的,这和周作人、胡适这些人是不一样的。张中行其实也感到了彼此间的差异。鲁迅的那些东西,远远地看可以,学起来是大难的。鲁迅在日本读书时,就注意到摩罗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的作品,还系统地了解了科学思想史,像克尔凯郭尔、斯蒂纳、叔本华的著述,都是浏览过的。中年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也下过相当的功夫。他一生里,一是关注科学,一是思考人文主义,还有报国的热情,思维就别于他人,想的是人本的问题。这还不够,那时对国民性的思考也夹带其间,精神就呈现出多面性的特征。中国的读书人,一般满足于知识的获得和事功的体现。鲁迅没有这些。他将知识看成改良人生的存在,而且不断地向自己的有限性和国民的弱点挑战。这种复杂的心理和盘诘过程,一方面使他呈现出精神的创造性的一面,一方面具有浓烈的批判意识。在他的世界里,纯真与复杂相间,深切与平和交汇,精神结构是极其神异的。
鲁迅表现爱的时候,是在最悲愤的文字里,而幽默的语调里,也含有闪闪的泪水。熟读《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的人,都可嗅出他深广的情思。那种情感的表达方式,过去是很少有人拥有的。周作人、林语堂在表现悲欣的情感时,是常人的智慧,你一点不觉得奇怪。可是鲁迅的精神是腾越的,从泥土里生出,在高远的天地里翻转,那就表现出意识的高度和思想的高度。在描述人物形象时,是俯视的,看穿了灵魂里的一切。像阿Q那样的形象,其表现的态度里是爱恨交加,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者正是。鲁迅的表达方式有时不能用是与不是来解释,他的智慧是超出线性因果的联系的。你看“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多么反逻辑。“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类似的句子,我们用常理能够理解么?理解鲁迅,必须意识到表达的反世俗与切近世俗。这是个悖论,但他穿越了这个悖论。他同代的知识分子和后来的读书人觉得无法与其并驾齐驱的原因,是思想的构成不在一个层次里。
鲁迅的思想有表层的,也有隐层的。他文字里有许多暗功夫,不是一般人可以企及的。比如他读文字学的书很多,却很少谈及,那些都隐含到文字的背后了。他关注考古学,却不在作品里运用这些,但在随笔里,偶一论及旧文明,则是现代的眼光,科学理性的光暗自闪烁着。他藏的西方版画和各类美术品多矣,却从没有写过一篇研究的文章,但他作品里明暗相间的审美精神,都是汲取其精华的表现。他平时很关心自然科学知识,你看他藏书中有关天文、地理、医学、心理学的著作,都隐含着思想的波澜。那些看似不经意的东西,却形成了他精神的底色。总的说来,鲁迅有专的一面,比如文学的修养,更主要的是杂家的一面,对各类学说都知晓一点。他常说读书要随便翻翻,对自己的眼光大有好处,不是夸大的说法。先生在读书与写作里形成的气象,我们的确还总结得不够。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一直不能解决。鲁迅首先是消解自己的,对生命有种苛刻的一面,认为自身存有问题,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一面自戕着,一面求索着,渴望着新人的出现,向着虚无和黑暗宣战。可是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是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的,于是自恋和恋人纠缠着一生,久久地趴在地上。鲁迅是飞腾的,抖落了一切尘土,自由地飞动在精神的天空上。我们什么时候能像他那样不为俗物所累,坦然地思考和坦然地书写,就不会有离他很远的感觉了吧。
许多年来,张中行对鲁迅的传统敬而远之,自知自己不是那传统的一员。他喜欢周作人,乃是心灵相近的缘故。记得他对我说,周作人偏于疑,鲁迅偏于信。似乎是对前者更爱一些。但其实鲁迅也未必不是怀疑主义者。他有点像罗素所说的孤独地思考,且有人间的情怀的那类斗士,我们俗人是学不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张中行和那类超人式的智者比,终还是有距离的。远离尼采而亲近罗素的人,大概都有一点这类的特点的。
4
但是他对周作人则是另一种态度。有一段时间,他经常去看望周作人,这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苦雨斋的弟子里,就文采和智慧而言,废名第一,张中行当属第二。废名是周氏早期的学生,张氏则属后来的弟子。废名喜欢周作人,乃学问和智慧的非同寻常,从那清谈的路里,摸索出奇、险、怪谲的新途。而张中行把苦雨斋的高雅化变成布衣学者的东西,就和百姓的情感接近了。
张中行认识周作人是在三十年代初,我相信起初周氏对他的引力只是在文字上,因为他的课并不好,只是以文章名世。周作人与学生的交往没有胡适多,亲和力并不大,但周氏的文章实在好,就见识和文字的魅力而言,除鲁迅外,别人是不及的。周作人在那时是个清醒的思想者,古典文学的修养高,希腊文化的研究和日本文化的思考也深。这在北大是极其特别的。周作人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者,又带有儒家的中和之调。他对西方的人文学说有相当深的理解,在审美的范畴里,又深解东方艺术的要义。他的书那时在知识界风靡得很,博识与冷静让人动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的声名很大,虽没有领袖之风,可在一些具体话题表述里,见解常常在胡适、陈独秀之上。胡适、陈独秀的意识,有巨人的风采,别人是不及的。可是周作人的选择是个人的,就让一些青年觉得有可行的一面,是普通人的状态。从北大毕业的人,讲起自己的老师,文科的青年佩服的往往是周氏。张中行后来越来越感到这位老师的重要,他身上能汲取的东西,是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所不及的,所以内心深处,就自然亲近于周氏,也自称是他的学生。
日本人占领北平时,张中行听到老师要出任伪职的消息,还写信劝阻过,可见那时他们的交往已很多了。那时苦雨斋身边的友人,差不多也是张氏的心仪之人。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钱稻孙、废名、沈启无都在张氏那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有的后来也成了自己的忘年交。周作人身边的人都不太张狂,个性却是耀眼的。他们不随流俗,思想放达,有六朝的意味,在张中行看来都是可念可感的存在。闲暇之时,偶尔还到八道弯看望老师,成了自己的乐事。他对周作人的认识,也随之越来越深,甚至受到了很强烈的暗示,有时也影响了对一些事物的判断。到了五十年代,弟子皆散,只有张氏还经常去探望,周作人是一定感慨的吧。我想周氏绝不会料到,承传自己的文学风格的竟是这个弟子,不过他的诚实、勤勉、远离世风的态度,周作人是赞佩的吧?所以,赠送许多手稿给他,也是自然的了。
在苦雨斋弟子里,深入揣摸到老师的精神底蕴者,不是很多。有的只学到了形,毫无神采;有的只附庸风雅,连基本的要领也没有掌握。这样的例子可以找到许多。张中行得到的精神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一是怀疑的眼光,不轻信别人的思想;二是博学的视野,杂取诸种神色,形成一个独立的精神境界;三是拒绝一切八股和程式化的东西,本于心性,缘于慧能,自由地行坐在精神的天地。他在周氏那里找到了汉语的表达方式,这方式既有旧学的一套,也有西学的因素,不同于古人的老朽,也和西崽有别。这两方面恰恰符合了张氏的美学追求,他后来的写作就是由此而出发的。了解张中行,是不能不看到这个关键点的。
张中行不止一次地说过,周作人的精神大,能包容下什么,而且写文章举重若轻,神乎技艺,渺乎云烟,探乎学理,是大的哲人才有的气象。比如在对古希腊的认识上,就高于常人,知道非功利哲学的意义。思想上呢,也有路基阿诺斯的怀疑意识,像尼采般能从世俗的言语里走出,看清人间的混沌。不过他在后来的选择上也有周氏没有的新东西,那就是不满足于知识的积累,要向哲学的高地挺进,于是就多了苦雨斋里没有的东西,和形而上的存在纠葛在一起了,这是他超出老师的地方。而这超出的部分,正是他对文化的一个大贡献,也因为这个贡献,他的世界就与同代人区别开来,远远地走在了世人的前面。
苦雨斋主人在文体上给张中行的影响是巨大的。《负喧琐话》的风格明显是从《知堂回想录》那里流出来的。那组红楼的回忆文章分明有周氏的谈天说地的影子,话语的方式有连带的地方的。差别是前者是亲历的漫语,无关乎历史评价;后者则多了往昔的追忆,是感伤的文本,有大的无奈在里。在周作人一笔带过的平静里,张氏往往荡出波澜,似乎更有精神的冲击力。苦雨斋的文本是绝望后的冷观,而张氏的笔触却是冷中的热的喷发,不安的悲悯和伤感的低语更强烈吧。周作人看历史和人物,不动神色的地方多。张中行却情动于中,有诗人的忧郁。所以,我更倾向于把他的书看成是忧郁的独语,较之于自己的老师,肉身的体味更浓些罢了。
关于苦雨斋的主人,他写过许多文章,看法都是独到的。在我看来是真正懂得自己的老师的人。在鲁迅和周作人之间,他似乎更喜欢周氏,因为那种平和与学识是自己不及的。鲁迅难学,许多模仿鲁迅的人不幸成了流氓式的人物,而追随周氏的读书人,大多是本分的边缘化者。在那个历史年代,革命风云变幻,激进队伍成分复杂,鲁迅不幸也被复杂的烟云包围着。在张中行看来,只有苦雨斋主人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保持了读书人的本色,是大不易的。他在《苦雨斋一二》写到了两人的交往:
他多次说他不懂“道”,这大概是就熊十力先生的“唯识”和废名的“悟”之类说的。其实他也谈儒家的恕和躬行,并根据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理论而谈妇女解放。他多次说他不懂诗,对于散文略有所知。他讲六朝散文,推崇《颜氏家训》,由此可以推知他的“所知”是,文章要合乎人情物理的内容,而用朴实清谈的笔墨写出来。关于诗,我还记得三十年代初,一次在北京大学开诗的讨论会,参加的人不多,只记得周以外,还有郑振铎和谢冰心。别人多讲了不少话,到周,只说他不懂诗,所以不能说什么。我想,这大概因为,对于诗的看法,他同流行的意见有区别;流行的意见是诗要写某种柔情或豪情,他不写。他先是写白话诗,后来写旧诗,确是没有某种柔情和豪情,可是有他自己的意境。晚年写怀旧诗《往昔三十首》,用五古体,语淡而意厚,就不写某种柔情和豪情说,可算是跳出古人的藩篱之外了。
这文的方面的成就,与他的勤和认真有密切关系。从幼年起,他念了大量的书,可以说是古今中外。 比如他喜欢浏览中国笔记之类的书,我曾听他说,这方面的著作,他几乎都看过。有一次,巧遇,我从地摊上买到日本废性外骨的《私刑类纂》,内容丰富,插图幽默,很有趣,后来闲话中和他谈起,他立即举出其中的几幅插图,像是刚刚看过。还有一次,谈起我买到蔼理斯的自传,他说他还没见过,希望借给他看看。我送去,只几天就还我,说看完了。到他家串门的朋友和学生都知道,他永远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上放着一本书。写也是这样,几乎天天要动笔,说是没有别的事可做,不读不写闷得慌。
虽然老师最终落水,附逆于日本政权,可在精神的维度上,那种坚守思想的独思和寂静,确实使人看到了思想的另一种可能。至少他在文章的写法与精神的表达上,没有趋于泛道德化的思路,在张中行看来是极为稀少的清醒剂。作为一种遗产的继承者,他知道理解苦雨斋的主人仍需要时间。
从他所引的周氏的观点来看,周作人所保持的许多理念,都是张中行自己后来坚持恪守的。不陷于柔情,非豪情状,默默地对视世间的遗产。精神的冷,和内心的热,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在三四十年代,知识群落都卷入到社会的冲动里,情感的因素战胜了理性的力量。身处乱世,奇冤四起,血气冲天,怎么才能保持精神的安宁呢?安宁,就要不动,与火热的人间疏离。这是大难之事,浅的被说是落伍,深的要被视为无爱者。周作人、张中行都被同代人指为是自私的人。可在他们看来,彼时的中国已经发了疯,包括知识群落,差不多都远离思想的园地了。
经历几十年的动乱,周作人式的思考问题逻辑及表达逻辑,几乎消失殆尽。社会流行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已没有希腊式的风致了。怀疑与包容,从人们的视野里隐去,几乎没有温馨和蔼平淡如水的存在。如果不是张中行在八十年代坚持的这条写作与思考的路向,我们对五四的理解也许将少了些什么。他的文字仿佛五四文化的活化石,展示了艺术表达的另一种可能,而且重要的是,他把这样的一种路向扩大化了。
这都是远去的旧事,一个泯灭的文学生态,指示着智性的高度。而有段时间,我们是漠视了这个高度的。
标签:周作人论文; 鲁迅论文; 顾随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张中行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俞平伯论文; 鲁迅中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