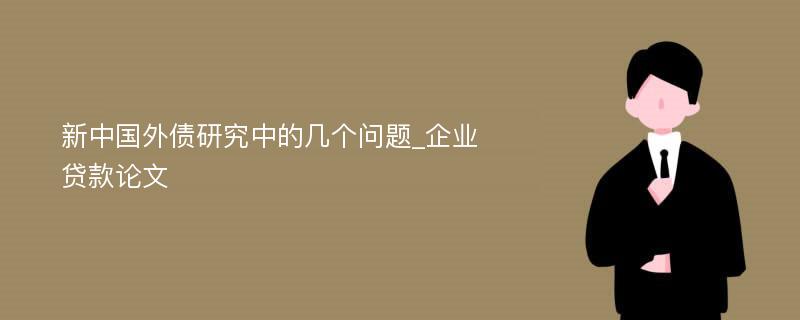
新中国外债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债论文,新中国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学界对中国近代外债资料的整理和外债史的研究已经花费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清代、北洋、国民政府几个时期的资料整理,并出版了相关的研究专著。经过多年的分析研究发现,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依靠传统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发展起来的,而是依靠特殊的原始积累形成的[1](p.9)。中国近代化的生产力、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可以说主要依靠外债。而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又来源于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通过没收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垄断资本而形成的。此外,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宣布冻结中国在境外的资产;我国政府针锋相对,宣布没收英美在华资产,也增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因此,在研究近代中国外债的基础上,对新中国外债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巨大的课题。本文拟对新中国外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乞就教于方家。
一、新中国外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研究任何课题,首先要弄清的是该课题前人已经做了些什么?提出过什么问题?怎样解答这些问题?因为任何研究的新成果或新发明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获得的。
自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决策和管理部门以及一些学者开始对我国外债问题进行了有选择的介绍、分析和研究,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和金融研究所编写的《关于中国外汇与外债问题的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黄苏等人编的《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情况与经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邓子基等人撰写的《公债经济学——公债历史、现状与理论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甄炳喜编著的《债务:第三世界的桎梏》(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陈同亮所著的《中国债务备忘录》(河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高坚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国债问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王建军等编著的《外债与发展中国家》(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年版),等等。但上述著作尚停留在理论层面或政府部门的决策性层面上。20世纪90年代初,国务院经贸办与共青团中央的李祥林、洛桑主持编撰了《走向国际市场》丛书,其中由彭建国编著的《利用外资与海外投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不仅论述了国外贷款、国际融资、直接利用外资、海外企业的建立与经营管理、保护国际投资的政策及法规,还介绍了22个国家和地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基本法规,它融理论性、知识性和实用性于一体,阐明了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法规,突出了最实用的内容,为处于第一线的对外经贸业务人员和管理工作者提供了最新的资料。董志凯在《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1950—2000)》(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省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以大量鲜为人知的档案资料为基础,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利用向前苏联举借18.5亿美元的长期低息外债来进行的156项重点工程建设进行了全面展示,客观分析了在那个特定时期的经济体制下,这些项目对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意义及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
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债研究,近十年来也陆续有文章发表,如常亮和张华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债状况分析》(载《财经理论与实践》1999年第20卷,第100期)、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撰写的《我国外债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建议》等文,从标题中即可看出其着眼于现状及相应的对策。
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结合的学术层面上研究新中国外债的当推隆武华的《外债两重性——引擎?桎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和王国华的《外债与社会经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两本专著都是他们在许毅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是研究近代中国外债和新中国外债的原创性著作。
《外债两重性——引擎?桎梏?》一书对中国外债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与分析,其中有三章专论新中国外债,即“中国外债规模的分析与外债结构的透视”、“亚洲金融危机、外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药方”、“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安全”。在“中国外债规模的分析与外债结构的透视”一章中,作者以大量的数据和事实为基础,指出了1985—1995年中国外债的基本情况及结构特点。该书指出:“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债的发展尚属健康,还不存在发生危机的条件。但存在的问题确实不少,一是多头对外借款导致外债规模迅速扩展,成为发展中国家第三大债务国;二是外债结构基本上是在自发的基础上形成的,缺乏整体的借款战略等。”[2](pp.6—7) 但该书对新中国成立至1985年的中国外债未能加以阐述与分析。
《外债与社会经济发展》一书则对新中国外债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积极争取和利用前苏联提供的贷款和援助,以加快经济建设、促进社会发展的情况;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外债利用的情况也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并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外债利用规模的迅速扩大有极强的相关度。书中具体分析了外债对我国交通、能源等基础性、瓶颈性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肯定利用外债的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存在着外债规模扩大过快、使用效益不高、管理散乱、风险较大等问题。
此外,财政部科研所与有关单位还组织了数十人,用了十几年时间,先后整理出版了大量近代中国外债的档案资料,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打下了基础。但是,目前学界尚无人对新中国外债的研究史料进行整理,研究成果寥若晨星。《党的文献》在1999年第5期上登载了《建国初期156项建设工程文献选载(1952年9月—1954年10月)》,首次公布了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前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决定,以及周恩来致李富春的信等档案文献,这些资料的公布,不仅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也为新中国外债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材料。
借用外债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如何进一步扩大外部资金的利用,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须回答的问题,因而有必要对新中国外债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有关新中国外债的政策、实施、作用、影响及我国外债规模和管理体制等问题,都需要我们来认真探讨,总结历史经验,以防范债务风险,提高外债使用效率。
二、新中国外债研究的对象与范围
债或债务,具有强制的责任与义务。1988年3月,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世界银行(IBRD)等四家国际权威机构联合出版了《外债:定义、统计范围与方法》一书,对外债作了统一的规定。该书对外债作了如下定义:“Gross external debt is the mount, at any given time, of disbursed and outstanding contractual liabilities of residents of a country to non-residents to repay principal, with or without interest, or to pay interest, with or without principal.”(即“外债是在任何给定的时刻,一国居民对非居民所欠的已用尚未清偿的有契约性偿还义务的全部债务。”)1987年8月27日,中国公布的《外债统计监测暂行规定》中,对外债定义以及外债的具体内容规定为:中国境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对中国境外的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金融机构、企业或者其他机构用外国货币承担的具有契约性偿还义务的全部债务。
有研究者认为:“(我国的外债定义)与国际通行的外债定义有细微差别,带有与我国国籍法一致的血统原则与属人原则,与西方通行的属地原则有些不同。如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外资企业所借入的外汇资金不视为中国外债,尽管这些外资企业是中国境内的法人(居民)。”[3](p.12) 也有学者提出:“对于外债的定义,应该从四个方面来把握,即最狭义的外债、狭义外债、广义外债、最广义外债。这四个概念,一个比一个范围大,前两者构成内涵外债,我们把它们称为外债;后两者构成外延外债,称为准外债。”[2](p.2) 最狭义的外债,即最核心意义上的外债,又称国家外债、国外公债或公共外债,是指政府通过借款、发行债券等形式或由政府予以担保而形成的对外国的债务,它直接构成一个国家的国债。狭义的外债是指一国居民欠非居民的债务,即中国境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金融机构或者其他机构对中国境外的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金融机构、企业或者其他机构用外国货币承担的具有契约性偿还义务的全部债务。广义的外债包括一个国家的外贸逆差,外贸逆差可以用扩大出口的办法来清偿,也可以通过经常项目上的非贸易往来或包括侨汇在内的资产转让来弥补,甚至于动用外汇储备;外贸逆差还可以在资本项目上用直接举借外债或利用直接投资的沉淀部分来偿还,这种偿还含有借债还债的性质,理所当然属于外债。最广义外债指外国对一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或一个国家银行的外国分行在国外吸收的存款等。
据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底,中国外债余额折合美元2 285.96亿,比上年末增加349.62亿美元,上升18.06%(注:相关数据参见《中国财经报》2005年4月19日第5版。)。目前,中国外债余额超过了历朝历届政府,但由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仍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出口增长迅猛,所以偿债率(注:偿债率为当年中长期还本付息额加上短期利息除以当年国际收支口径的外汇收入,一般情况下不超过25%即为安全。) 一直控制在15%的安全线以内(最高的1999年为11.3%);债务率(注:债务率为外债余额除以当年国际收支口径的外汇收入,一般情况下不超过200%即为安全。) 控制在100%的安全线以内(最高的1998年为70.4%);负债率(注:负债率为外债余额除以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一般情况下不超过25%即为安全。) 控制在25%的安全线以内(最高的1999年为15.3%);另外,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率也控制在100%的安全指标以内(最高的1996年仅为13.4%)。
新中国外债史既要研究内涵外债,也研究外延外债,但主要是研究内涵外债;既要研究举借外债的背景、债项债额,也要研究外债的用途、作用以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对债项、债额的研究则主要是针对登记外债而言。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政权,并统一了货币和金融机构。但是在香港1997年收回主权、澳门1999年恢复行使主权后,我国实行的是“一国两制”,货币上仍有港元和澳币的流通;而台湾至今未统一。因此,本文研究新中国外债,在外债数额的统计与分析中,不包括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的对外负债,只限于大陆地区。
三、新中国外债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向前苏联举借的外债以及国内发行的公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于有效利用了前苏联的贷款资金、技术设备和专家人才的支持与帮助,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发展迅速。1953—1956年,我国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9.6%,农业生产年均增长4.8%。在生产总量、增长速度上大大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任何时期,也是新中国头30年中建设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学者对此有过专门研究,并发表了研究文章,在此不再赘述(注:对这一问题,除王国华《外债与社会经济发展》一书中有专门论述外,其他文章主要有:蒋洪巽、周国华《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煤炭工业建设项目的由来和变化》(《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陈夕《156项工程与中国工业的现代化》(《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宿世芳《关于50年代我国从苏联进口技术和成套设备的回顾》(《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王奇《156项工程与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陈东林《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引进》(《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等等。)。
至1959年,前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1960年撤走专家,逼我国提前还债,给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宿世芳(注:宿世芳于1949年秋在中国贸易部国外贸易司工作,1952年调往莫斯科,1955年回北京后,在中国技术公司工作。) 在回顾从前苏联进口技术和成套设备及前苏联撕毁合同的情景时说:“回顾过去,既使我们愉快地想到在5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友好时,两国贸易大发展的情形。也使我们痛心地想到苏联专家的突然撤退,使我国40个部门的250个企业和事业单位陷入瘫痪的状况。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不仅破坏了我国这些部门的设计、设备的安装和生产,而且打乱了中国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带来了巨大损失。”[4] 从中可以了解到我国利用外债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历程。
但中国不仅还清了前苏联的外债,继而还清了国内公债,成为当时世界上惟一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虽然此时社会主义建设缺乏资金,困难重重,但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华民族还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无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上经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挫折、延误,说明利用内外债是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必要手段。
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资金,因此,改革开放后,一定要吸收外国资金,用资金来恢复和发展经济。“借外债并不可怕,但主要用于发展生产,如果用于解决财政赤字,那就不好。”[5](p.193) 因此,考察外债利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即从外债的使用方向和外债的使用效益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举借的外债重点投向交通、能源、化工、冶炼、机电产业等,如1979—1991年间,我国外债总额近一半投向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用以缓解这些“瓶颈”行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详见表1、表2):
表1 1979—1991年中国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的使用分布情况
序号贷款使用行业项目个数使用贷款额比重(%)
1交通运输52 28.58
2能源46 17.95
3石油化工49 13.16
4邮电通讯104 9.82
5轻工纺织416 8.91
6城市建设54 6.28
7钢铁冶炼28 5.13
8机电仪器52 4.60
9农林水利70 2.44
10
建筑材料37 2.19
11
科教卫生24 0.68
12
其他4
0.26
总计936 100
*资料来源:马洪《现代中国大事典第三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2197页。因为有些贷款项目是跨行业、跨地区的,所以贷款项目总数多于按贷款国计算的贷款数916个。
表2 2002年全国中长期登记外债投向表(金额单位:亿美元)
债务人外资
类型 国务院部委中资金融外商投资中资外资 非银行其他合计
贷款机构企业企业银行 金融
使用行业 机构
农牧渔业 58.28 3.483.640.440.13 0.23 66.2
采矿业24.27 59.39
24 5.220.04 0.41 113.33
制造业9.37
15.29
44.10
0.641.06 0.18 70.64
电力煤气及
水的生产和73.96 96.31
43.35
2.230.01215.86
建筑业17.52 2.4747.96
0.021.5369.50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10.19
25.67
35.86
信息技术服
务业 176.9 37.44
16.86
64.53 0.330.01 296.07
水利管理和
社会服务业10.24 1.9937.17
0.350.01 0.01 49.77
卫生、社会
保障和社会43.96 5.134.120.2453.45
其他 80.43 64.87
44.57
0.7843.87 1.320.01 235.85
合计 494.93 286.37 275.96 100.12 46.65 2.470.03 1206.53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2002年度我国外债基本情况报告》,2003年4月15日。
从表1、表2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借用外债投向社会经济急需的行业和部门,确实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利用借入的外债建成了上千个大中型项目,使长期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交通、能源“瓶颈”得到很大改善,并利用外债建设发展了一批农林、水利、饮水、卫生和教育科研项目,不但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改善了社会环境。
总之,我国利用外债外资投向经济急需的行业与部门,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成功的,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有效地调整了产业结构,在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上实现了飞跃,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03年,中国财政收入达到2万亿元人民币,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1.8万亿元人民币,全社会金融资产近36万亿元人民币,全国总资本流量则已超过30万亿元,经济总量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世界排名已跃升到第6位。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继续引进外资、举借外债来发展社会生产力。
四、新中国外债与近代中国外债的联系和区别
外债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使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产物,也是金融国际化的一种表现,最早产生于西方。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但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从此,中国走上由无债、借债到依赖外债的道路,此后历届政府均向外借款。据粗略统计,清政府举借了210项外债,总额相当于18亿银元[3](p.145);北洋政府(包括南京临时政府)举借外债约633项,债务总额达15.56亿银元[6](p.1);国民政府共举借外债85项,债务总额约28亿银元[3](p.145);新中国外债除20世纪50年代的债项与债额有统计外,新时期的外债尚无统一的统计数字。近代中国外债与新中国外债尽管举借的背景、目的不同,但是举借外债可以引进资本、技术、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则是一脉相承的。
外债是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形式。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要是通过外债这种形式形成的。清末举借的208笔外债中,实业借款有85笔,债额达374 560 965.7两,占清末外债总额的28.7%,相当于当时清政府近四年的财政收入。其中铁路借款37笔(318 147 297两),矿业借款26笔(36 050 927两),电讯借款7笔(8 738 344两),轮船招商局借款4笔(4 383 192两),河工借款4笔(3 330 515两),其他实业借款7笔(4 910 689两)[1](pp.356—541)。清政府主要用这些借款修铁路、开矿山、办电讯等。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近代化的大生产都与外债联系在一起。北洋政府时期举借的外债中,实业借款和教育借款达4.5亿银元,约占总数的29%[3](p.199)。实业借款虽也有被移做他用的,但绝大部分还是投入近代企业的创办与建设中。例如,1912—1927年,全国新增铁路4 264公里,除沪杭甬等少数铁路由股东集资或交通部拨款外,都是借外债修筑的;另外还借款兴建了电讯业、轮船航运业、航空业与金融业;一些大型的棉纺企业,如上海宝成厂、上海华丰纺织厂、天津裕大纱厂等,也都是靠借外债来更新设备、扩大生产或维持生产的。国民政府接收了北洋政府的官办企业后,又举借了63笔实业外债,债额为3.7亿银元,占总额的8.23%[7](p.16)。国民政府用这些外债款兴建了铁路、电讯、航空等事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通过对敌伪产业的没收和处理,又扩大了官僚资本企业。国民政府时期,还把1/4的实业借款投向了金融事业,把创建于晚清、成为北洋政府的两大金融支柱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通过参股、增股等形式加以控制;又创办了中央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简称“四行二局一库”。为加强对金融业的垄断,国民政府还改组了中国国货银行、新华信托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四明银行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在上海设立了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业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统一管理全国金融,形成了国民政府金融垄断的最高形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除运往台湾和存在海外的财产外,国民政府留在大陆的官僚资本财产全部被人民政府没收,转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除了运用国内资金发展经济外,又通过举借外债发展了社会化大生产。新中国外债与近代中国外债,正是在引进技术、发展生产力这一层面上联系在一起的。
新中国外债与近代中国外债又有着巨大的差异,或者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国情的变化。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政治上受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封建经济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经济已得到一定发展的社会。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从1840年入侵中国后,逐步操纵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和政治、军事力量。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借款给中国,成为他们从经济上、政治上控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本帝国主义不仅对中国进行了高利贷式的掠夺,中国的关税、盐税、厘金、田赋也被抵押殆尽,举借外债意味着丧失更多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也意味着丧失国家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近代中国外债史,就是一部资本帝国主义侵华史。新中国外债则不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不受制于任何外力。新中国举借外债,是出于强国富民的需求,是一种自觉的、主动的行为。新中国成立后,成功地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引进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及技术,建成了156项重点工程,为新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外债事业更是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外债的风风雨雨、举债的曲曲折折,与近代中国、当代中国的历史演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如前所述,一部近代中国外债史,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一部新中国外债史,同样是新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近代中国外债给中国社会经济起的更多的是“桎梏”作用,而新中国外债给新中国社会经济带来的更多的是“引擎”作用。当然,新中国引进外资、举借外债,要时刻区分与警惕国际间平等互惠互助的资本流动与霸权主义国家利用金融实力控制、欺压债务国的图谋。
第二,债项结构与债务投向的不同。近代中国举借的外债主要是军政借款,而非实业借款,而且各个时期也不完全相同。晚清政府时期主要是赔款借款,所赔借款额计79 388万两库平银,占当时外债总额的61%[8](p.41);北洋政府时期(包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主要是军政借款,计6.7亿银元,占当时外债总额的43.05%[3](p.196);国民政府时期主要是国防借款(大部分用于抗日战争),计325 172万银元,占当时外债总额的72.3%(注:根据许毅、潘国琪主编的《国民政府外债与官僚资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附表2计算得出。)。晚清、北洋与国民政府时期的外债中,也有数量不等的实业外债,且大部分投向铁路建设,这是它们的共同点。 而新中国所举借的外债基本上都是实业外债。从中长期债务投向看,1979—1991年,投向交通运输、能源、石油化工、邮电通讯、轻工纺织的占78.4%(注:根据前文表1计算得出。);2002年,按照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在1 206.53亿美元的中长期外债中,投向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占24.5%,投向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占17.89%,投向采矿业的占9.39%,投向制造业的占5.85%,投向建筑业的占5.76%,等等(注:根据前文表2计算得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在21世纪的头几年较之20世纪90年代又得到了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