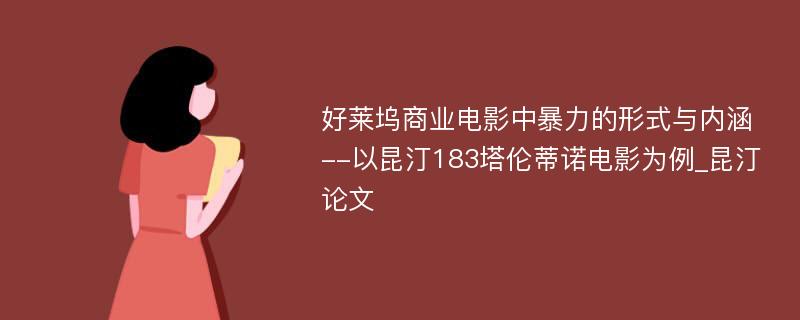
好莱坞商业电影中暴力元素的形式与内涵——以昆汀#183;塔伦蒂诺影片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好莱坞论文,为例论文,内涵论文,暴力论文,元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电影制作在投入成本与技术的同时依赖多人合作,这使得电影作品具有工业产品的特性,电影的生产与发展依赖市场的反馈,观众对一部电影的喜爱可以使投资者获得资金回收,“电影是群众性的娱乐。因此,它必然要去迎合一般群众的愿望和梦想。”①电影作品的商业属性使得电影必须依从观众的喜好,并且尽可能地迎合观众的心理,以便求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为了吸引观众心甘情愿走进电影院,也为了抗衡其他媒介的竞争,电影就必须更注重凸显其所要表现故事的题材类型和运用各种类型元素的强度。早在好莱坞电影业发展起步阶段,电影制作人就有普遍的共识,如果想要赚取利润,电影里就必须要展现现实生活中难登大雅之堂的元素,其结果即为“暴力”和“色情”,这两个人类永远感兴趣的话题成为商业影片的重要卖点,而市场的反馈也确实证明这一论断的正确。自此,“暴力”和“性”成为吸引观众眼球屡试不爽的法宝。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思想的解放,时至今日,好莱坞电影乃至全世界的商业电影仍无法摆脱“拳头加枕头”的套路。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工业社会已经发展到后工业社会阶段,随着社会财富日益丰富,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得到前所未有的极大满足,但传统的价值体系也逐渐走向崩溃。大众消费时代来临后,随着“受众本位”观念的崛起与发展,大众变成主动的、有选择能动性的信息使用者,“受众本位”观念与商业资本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完美契合于“人文关怀”的大旗下。大众文化乐于制造轻松的、激烈刺激的内容,而放弃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探索,极力迎合社会中大众的欣赏趣味,在满足消费欲望的同时,也不再着力推崇或认可某种世俗生活的观念。人们通过消费来持续保证感知上的刺激,继而证明自己的生存意义与价值,所有的东西都倾向成为消费品。这样的时代背景中,电影这种商业产品当然更不可能摆脱被大众消费的命运。 “消费文化使用的是影像、记号和符号商品,它们体现了梦想、欲望和离奇幻想;它暗示着,在自恋式地让自我而不是他人感到满足时,表现的是那份罗曼蒂克式的纯真和情感实现。当代消费文化,似乎就是要夸大这样的行为被确定无疑地接受、得体地表现的语境与情境之范围。”②在今天这样一个后工业时代,种种人类社会中的迷茫与无意义逐渐暴露,比如,人的精神被无形的权力意志过分束缚,现实生活中暴力行为普遍存在,种族群体和利益团体之间的权力冲突和茫然无序又残酷异常的生存竞争,等等,这些使得消费成为寻找生活意义与价值的手段,人们在感官刺激与消费中震撼自己、感知世界,以此证明自我的存在价值。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曾有着这样的论述:“作为封闭的日常生活,没有世界的幻影,没有参与世界的不在场证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它需要这种超越所产生的一些形象和符号。我们已经发现,它的宁静需要对现实和历史产生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他的宁静需要用永久性的被消费暴力来维持。这就是它自身的猥亵之处。它喜欢事件和暴力,条件是只要后者充当它的同室战友。夸张一点地说,就是在越南战争图像前感到轻松的电视观众。电视图像宛如一扇面向房间的反向窗口,世界残酷的外在性在这个房间里边的亲切、热烈、邪恶般的热烈。”③电影中的暴力泛滥,代表的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冲动或欣赏,只是因为电影作为一种商品,影片中的暴力元素必然存在于消费社会的消费逻辑中,这也是观众的消费欲望被点燃后所产生的一种必然结果。电影中的暴力往往一方面在曲折的反映人类真实生存状况的同时代表着电影创作者自发的、标新立异的艺术追求。消费社会中对暴力艺术的享受和认同,更是逐渐形成一种大众享虐心理,且这种心理越来越趋向成为一种令人震撼的集体无意识。以下将以昆汀·塔伦蒂诺的影片为例,详述好莱坞商业电影中的暴力元素是如何展现并负载着何种功能意义。 昆汀·塔伦蒂诺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独立电影革命中重要的年轻导演,他的影片以独特的个人风格风靡全球,擅长用非线性叙事方式讲述故事,其中夹杂大量血腥异常的暴力场面。昆汀·塔伦蒂诺出生于1963年的美国田纳西州的挪克斯维尔,父母都是狂热的影迷,昆汀这个名字来源于影片《枪之烟火》中的角色。他两岁时随家迁居洛杉矶,随后在这座电影气息浓厚的城市长大,1984年,高中毕业后的昆汀在曼哈顿海滩一家名为“录像档案馆”的录像租赁店工作,打工赚钱的同时,昆汀和好友罗杰·阿瓦里可以在那里整日地观看和讨论各种不同影片。他通过大量观看和仔细研究逐渐领会并掌握了众多电影知识和技法。在业余时间学习表演的同时,昆汀将更多的精力投向剧本创作。1991年,他凭出售《致命浪漫》剧本所得的5万美元,决定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三个剧本《落水狗》,在圣丹尼斯电影节首映后,这部集合暴力血腥、荒诞搞笑于一体的电影立即引起关注。1994年昆汀编导的了第二部影片《低俗小说》,这部电影继续发扬了他善于展现暴力血腥场景中的黑色幽默的风格,夺得戛纳影展金棕榈奖,次年获奥斯卡最佳原著剧本奖,从此奠定了昆汀在好莱坞电影界的地位。继1997年的《危险关系》遭遇滑铁卢后,昆汀于2003推出《杀死比尔》,由于影片过长,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分别在2003年和2004年公映,从此再次于全球范围内掀起“昆式暴力美学”的高潮。2007年与好友罗伯特·罗德里格兹合导《刑房》。《刑房》由两部电影组合而成,昆汀负责其中一部《死亡证据》的编导工作,2009年,昆汀邀请布拉德·皮特拍摄了电影《无耻混蛋》。该片在北美共上映119天,取得了120540719美元的佳绩,加上海外票房赚取的193059925美元,总票房高达313600644美元,可以说是口碑票房双丰收。如此丰厚的收入使得昆汀有了更多本钱去异想天开、再次颠覆历史,最终,2012年,《被解放的姜戈》上映。《被解放的姜戈》是昆汀向1966年由塞吉奥·考布西执导的经典意大利西部片《迪亚戈》的致敬之作,将是一部集合大量幽默元素、动作场面以及各种新奇有趣点子的意大利式通心粉西部片。《被解放的姜戈》获得2013年第8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摄影等多项提名,而昆汀本人也凭借此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 一、暴力元素的模仿再创造 昆汀成长的环境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那是一个消费文化与通俗文化飞速发展的时代,由于经济衰落加上越战后尴尬的国际地位,美国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人的思想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众文化逐渐取代精英文化成为社会主流,在对经典的各种解读与否定中人们获得解放般的快感。昆汀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听着摇滚流行乐,看着各种类型电影长大的年轻一代,他不可能再向前辈奥利弗·斯通那样于影片中深刻追问人性价值、思索社会问题,对他来说,电影只是娱乐人生、表达自我意识的一种手段。昆汀在采访中直言不讳,说自己“不像有些憋着和道德情感较劲的导演”,成天总拍些“老掉牙的如同便秘的影片”,④虽然有时候他也会借影片中的对白谈一些宗教、种族、社会问题,但这些都是暴力血腥场景开始前的调味剂,其作用与脱衣舞女挑逗的眼神、裸露的大腿相差无二。在涉及这些问题的冗长对白中,根本看不到导演赋予这些问题什么特别的观点或诉求,只不过是给将要开始的血腥杀戮“加点料”,所以,在昆汀的电影中,很难看到道德与精神层面的深刻思考,他追求的就是一种单纯的视觉快感和解构崇高中的无限乐趣。 由于昆汀的个人经历,他拍摄电影的技法基本上都是源于自学。法国的新浪潮电影,吴宇森的动作片,梅尔维尔的黑帮电影都成为他的教材,有意思的是,昆汀对这些经典作品并不采取嫁接或融汇贯通的方式,而是在自己的电影里直接再现经典影片的片段,对于曾看过大量类型片的昆汀来说,这根本是手到擒来。在他的电影《低俗小说》中,由黑社会大哥的手下陪大哥的女人出去用晚餐,但是不可以怀有不轨之心。这个故事在科波拉执导的《棉花俱乐部》里有类似的桥段,《棉花俱乐部》中的主人公也是在成为黑社会大哥的跟班后,与大哥的情妇产生了爱恨纠缠的感情。另外《落水狗》的主要故事情节基本上就是林岭东《龙虎风云》的翻版,昆汀坦言:“其实我每部戏都是这儿抄点,那儿抄点,然后把它们混在一起。如果不喜欢的话,观众大可不看,我就是到处抄袭桥段的。伟大的艺术家总要偷桥段,是偷,不是什么他妈的致敬。”⑤昆汀如此肆无忌的胆大妄言,是因为他的本领其实并不仅仅只是抄袭、拼贴其他导演的作品,因为如果仅仅这么做,根本不可能被观众和评论界接受。昆汀的独到之处在于,在借用经典类型片的桥段的同时,对其进行解构性的反讽处理。虽然故事框架和经典影片略有相似,但是故事内容却被他赋予全新的内涵。《低俗小说》中的杀手文森特和老板的女人米亚在餐厅里跳起摇摆舞(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风靡全美的一种爵士舞蹈),他穿着黑西装、白衬衣、系着领带,从服饰到所跳舞步,都明显包含着20世纪50年代好莱坞强盗片的影子,但是人物从对话到动作体现出的幽默,又将这种参照变得毫无严肃气氛。所以说,昆汀“对人物形象所进行的修改,不是一种没有内容的简单创造,而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极端化,这种极端化就是空洞的人物形象转变为导演的抽象动机”。⑥ 昆汀的电影作品包含大量暴力元素,称其为“暴力电影”的代表,不会有人产生异议。但是,他与其他导演在表现暴力情节、刻画暴力场面时最大的不同就是独具一格的影片形式的多变,这是昆汀电影中的创新,也是最被人津津乐道之处。可以说他所有的影片都是高度形式化的作品,是“形式主义的极端化”,通过千奇百怪的影片结构和各种各样的叙事手法,昆汀将典型的类型片叙事与当代都市中发生的种种传奇插曲融合在一起,使观众体验“复古”情调的同时又眼前一亮。昆汀推崇法国新浪潮电影代表导演戈达尔,他说:“戈达尔对电影所做的事情相当于鲍勃·迪伦对音乐所做的事:他们都进行了形式上的革命。读得懂电影和电影手法的爱好者一直都有,尤其是现在,借助录像技术,几乎谁都可以成为行家,即便只是一知半解。”⑦由于形式上的大胆创新,使得昆汀的电影虽然内容仍然是以反映暴力犯罪居多,但是却比之前的警匪片、强盗片、黑帮片都多了自己的特色,“1992年首映的塔伦蒂诺的《水库狗》,将被证明是美国独立制片史上的关键性的作品,因为它理顺了与好莱坞类型片的关系。塔伦蒂诺的新作《低俗小说》把他对美国20世纪40年代盛行起来的低俗传统的调和与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后波普艺术的特色风格统一起来了。”⑧ 二、暴力情节加强人物塑造 1.以层层堆砌的暴力元素推进情节发展 昆汀喜欢在电影中着力塑造匪徒、黑帮成员或者杀手的形象,他总是将自己的焦点集中在一些日常生活中不常见的、社会边缘的人物身上。但是他电影中的主人公却不像吴宇森镜头下的英雄那样有着光辉伟大的形象,同时也不承载任何重大的道德使命。无论是《杀死比尔》中的一帮职业杀手还是《落水狗》里的黑帮成员,这些人只是为了生存或者复仇而存在。虽然他的电影里也有代表正义和法律的警察出现,但是昆汀根本没有赋予他们任何高尚的情操或追求,比如《刑房——死亡证据》里出现的德州警察,明明已经推断出杀手残害四个花季少女的杀人动机与手法,但是却选择“我觉得还是回去看看棒球赛更有趣”般作壁上观。所以,在昆汀的电影里,人物没有明显的正反之分。他塑造的匪徒和杀手,既不像吴宇森影片中的英雄,使用暴力必须“师出有名”或为兄弟义气、或为匡扶正义,这些人更似是一群“乌合之众”,毫无理由的进行杀人越货、复仇抢劫等活动;也不像好莱坞电影里一贯对杀手冷酷嗜血的形象化描绘,比如《刑房——死亡证据》里的杀手,已经精心策划并丧心病狂地杀死四个少女,但是在遭遇另外一群女孩的报复时,却又吓得屁滚尿流。昆汀让演员夸张的表现身受小小创伤后撕心裂肺的痛哭疾呼,于幽默中更加增添影片荒诞、游戏的意味。由于法律和道德在暴力行为面前形同虚设,所以昆汀电影中对人物的设置,已放弃了符合伦常的预设和道德的追问,人物的出场就是为了情节的有趣,暴力活动更像一场游戏。 另外,昆汀的电影一般不会固守单一角色的视点,所以也就不存在唯一的主人公,在《杀死比尔整个血腥事件》中,复仇的新娘看似是片中唯一主人公,实则不然,她只是担负起串联各个篇章、介绍故事背景的叙事功能,就像谈话节目中的主持人一直在介绍到场嘉宾那样,由她的复仇行动引出每一个被复仇者自己的故事段落。在她介绍到第二个复仇对象石井尾莲时,叙事重心一下子转移到了对石井的身世介绍上,此时复仇新娘只是用画外音的方法来推进故事进展,而这一段真正的主人公是由动画片中的幼年石井和刘玉玲扮演的成年石井共同组成。接下来,导演通过用“幼年目睹父母被杀”“少年时代手刃仇人”“血腥镇压帮会反对势力”三个片段完成了对石井尾莲的性格塑造,使这个冷血、暴戾、包含双重性格的黑道大姐人物变得栩栩如生,其出彩程度甚至盖过复仇新娘,令观众过目不忘。这种多视点、多主人公的叙事呈现出影片故事包含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由于不再给观众一个清晰明显的认同对象,观众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或者故事去进行多角度的解读。 2.暴力元素负载对待死亡之游戏态度的内涵 昆汀的电影中,女性既不是被保护的对象,也不完全是被虐杀和受到伤害的弱者,在他的电影中,女性具有相当的自主性,比如在《低俗小说》中,米亚可以随心所欲支配男性手下陪自己吃饭跳舞、外加眉眼调情;在《杰基·布朗》里年过四十的黑人空姐,除了借警方之手干掉了对头、侵吞巨额黑钱以外,还收获了年轻帅哥的爱情。《杀死比尔整个血腥事件》则更是塑造出一个具有钢铁般意志和不死之躯的复仇新娘。新娘曾是一名职业杀手,代号毒蛇“黑曼巴”,欲隐退过平常人生活而遭遇杀手头子比尔的疯狂虐杀,捡回一条命的她在医院昏迷了四年,苏醒后不但先虐杀两个对昏迷中病人实行性侵犯的变态,还拖着半废般的身体逃出医院,后来凭着超人般的意志使躯体恢复正常功能。在实行复仇活动中,她屡屡深陷险境,但身负重伤仍然能反败为胜,最神奇的是胸口中枪且被活埋至地下棺材中的她,居然于狭小空间里数拳击碎棺木再次神奇复活。昆汀将复仇新娘塑造为一个“不死”的超人形象,她数次复活后的“满血再战”更像是只有电脑游戏里才会设计的游戏情节,所以这种被赋予了超现实意味的暴力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暴力的现实意义,使血腥场景变得更加游戏化。 这种游戏化般处理暴力行为的设计,早在《低俗小说》中就有体现:“我在编导《低俗小说》时就曾经设想过让大人来玩小孩的游戏,不过是用真刀真枪,这种想法在我的头脑里经常出现,我认为那实际上是可行的。”⑨所以《低俗小说》中的暴力行为与犯罪情节都更像是一种介乎成人与孩童之间的混合游戏,暴力元素的呈现不再承载任何特殊的意义,不过是为发展剧情、为讲故事而必须出现的一个载体。为了不让暴力行为负载过多的道德意义,在《杀死比尔整个血腥事件》中,他索性设置所有实施暴力的角色都是职业杀手,这样一来,无论角色使用何种非正常的暴力手段,都变得可以理解,也就弱化了有可能在观影时出现的道德伦理上的判断与追问。由于杀手杀人的行为和吃饭睡觉等行为一样的随便、正常,所以鲜血与死亡已经不会产生任何痛心疾首的心理伤害,带来的只有导演希望观众体会到的“视觉泄欲”,在《杀死比尔整个血腥事件》中,无论是动漫画的处理死亡的方式,还是各种断肢飞舞、鲜血激喷不止的夸张场景,昆汀对待死亡的态度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漫不经心。可以决定人物生死的是剧情的发展趋势,他们的死亡既不光辉伟大也不悲壮动人,除了展现暴力伤害所能到达的极致后果外,别无他用。 所以,死亡本身也就不再承载任何意义,这种对人物生死的随意处理很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昆汀在本身的生活中并不会遭受类似于战争这样的暴力袭击,他只是生活在影像暴力行为猖獗时代的一个旁观者。在他质疑奥利弗·斯通为什么要把《天生杀人狂》中轻松有趣的情节变成承载更多思考的暴力场面时,被前辈严肃地教育一番:“你才20多岁,你拍的是有关戏的戏,我拍的则是我40年的人生阅历。我见过的暴力比你多,我到过越南打仗,中过枪。你真的想谈暴力吗?好,那就扎扎实实地谈吧!”⑩当然,不羁的鬼才昆汀根本也不会把前辈导演的教训放在心上,后来在采访中他公然不承认《天生杀人狂》是自己的作品,而且一如既往的在自己的影片里用游戏化的表达方式肆意展示暴力打斗中的快乐和刺激。 另一个原因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无法得到确切答案的假设,那就是昆汀是一位SM性虐与享虐爱好者,昆汀受日本SM动漫影响颇深,且在影片中不止一次对女性的足部表现出近乎异常的迷恋展示。《刑房——死亡证据》中不论是被杀、还是参与施暴的两个女孩,都把脚伸出车窗外,昆汀特意给于这些女性足部足够长时间的特写。 在《杀死比尔整个血腥事件》中,复仇新娘通过活动脚趾来恢复下肢力量。如果说《刑房——死亡证据》中尚且是对女性美腿、美足的刻意展示,那么在《杀死比尔整个血腥事件》中对一双并不美丽的脚掌进行大幅的特写展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我们知道,恋足癖属于性倒错中的其中一种恋物癖。性倒错是一种性行为形态,“需要藉着不寻常的物体、仪式或情境,才能得到完全的性满足”。(11)部分恋足者会以别人践踏自己以获得快感,因此有些恋足者也有被虐或享虐的性心理,比如可以从被他人施加痛苦——鞭打、践踏、掌掴等方式获得性愉悦。昆汀在现实生活中的性心理究竟为何,研究其电影作品的学者们当然无从得知,但是创作活动可以满足心理欲望的释放已是学界公认的观点,那么在这里我也可以用不成熟的假设来推断,在进行电影剧本、影片拍摄等创作活动中,喷涌的鲜血和对身体的各种暴力伤害会使他得到身体本能欲望的最大发泄与满足。 在昆汀的影片里,女性角色除了充当男性视觉欲望的客体承受者,也是拥有超长意志力和特殊技能的丰满角色,而且与以往女性只是处于被保护的地位不同的是,昆汀影片中的女性角色,为了复仇或者为了金钱,她们站在了主动施暴的地位。《刑房——死亡证据》中,三个女孩原本在玩自己疯狂的飞车游戏“轮船桅杆”,这时候之前已经虐杀四位少女的杀人狂冲了出来,影片气氛瞬间紧张,女孩们命悬一线,好在危险过后三个女孩都毫发无伤,被吓坏了的她们泪水肆意,就在观众仍然担心变态杀人狂会再次返回虐杀女孩时,剧情出现了大反转,女孩们居然决定不顾危险去追逐杀人狂并且给他沉重的教训。接下来影片气氛相当高亢且令人热血沸腾,几个女孩驾车追逐杀人狂并一再对其冲撞,带枪的Kim甚至愤恨的射伤杀人狂,负伤后的杀人狂阴冷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在女孩们疯狂的暴力报复中鬼哭狼嚎般吓得屁滚尿流,最终也没能逃过一劫,正如对白中Kim表达的:“一瓶辣椒水或许也能让女人从强奸犯的魔爪下逃过,但只让那混蛋长些皮疹是不够的,活该用枪崩掉!”导演赋予女孩们复仇天使的任务,设计带枪的情节更重要的是体现女性角色将会以牙还牙的强硬态度。通过对杀人狂的报复,让其为之前所做的虐杀行为付出代价,正如片尾曲中唱的那样:“Hang is up,Daddy.A girl is not tonic or a pill,you’re just jumping for a spill!(别这样老爸,女孩不是补品也不是你的药,你正在去送死!)”当原本正义的化身警察选择对残忍的谋杀视而不见的时候,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另一伙意气奋发的女性复仇者将最终完成对男性施暴者的斩杀。 三、在团状叙事中反复展现的暴力场面 前面提过给于昆汀巨大影响的法国先锋电影导演戈达尔,昆汀沿着前辈的脚步,在叙事策略、视觉语言、电影的表现形式方面做出进一步的革新与尝试。“从《水库狗》到《低俗小说》,塔伦蒂诺半真半假地把犯罪片重新界定为艺术电影,通过介绍一种选择机制,让观众不得不面对平常难得一见的、一两句话难以说清的叙事结构。”(12)可以说,正是因为昆汀在影片中特意设定的、令人费解的同时又玩味有余的叙事结构,使他的电影在纯粹的类型片上取得成功。昆汀在讲述故事情节的时候,没有封闭的叙事和线性推进的时间,他更多的选用一种开玩笑的方式将跳跃的时间和片段连缀在一起,用叙事结构并以叙事角度的共同变化创造出一种复杂的、重合的影片结构。比如《杀死比尔整个血腥事件》,将整个影片分为十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是独立的一个故事,通过黑曼巴的复仇行动将所有段落串联、整合,其中既包括各种复仇活动,也有彼此独立的讲述不同人物背景故事的片段。在电影的时空构架上,昆汀将各个叙事元素打乱重组,从而建立起一个新的叙事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打乱了观众对类型片固有观影经验,获得新鲜的观影体验。例如在表现婚礼虐杀这一情节上,昆汀并没有完整的向观众做一次性的展示,而是将这场戏分为三个段落穿插于全篇。随着故事的不断推进,观众才逐渐了解了这一血腥屠杀的整个发生过程。这样的叙事方式使得原本类型化了的、老套的故事模式焕发出新的生机,重新具有挑动观众神经的悬念感。正是由于昆汀在叙事方式上进行的大胆革新,使得他在颠覆了传统类型片的叙事套路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类型电影的发展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起观众的积极性,使其在观影中更多的参与影片的故事建构,从而进行自主判断。 在暴力元素的呈现方面,昆汀对暴力场景的展现更接近西方传统的、力图真实的表达方法,这和吴宇森诗意、唯美的暴力表达有着本质的区别。昆汀的电影中,一旦出现暴力杀戮行为,必定是血红色浸染银幕,呈现出一片血色汪洋的夸张景象,而且在出现暴力场景之前,影片往往有很多与之并不相关的人物对白、心理描写、或者是细节展示。暴力场面往往是突如其来令人猝不及防,在《刊房一死亡证据》中,电影前二十分钟都在表现几个女孩的对话,冗长的对话与主题并不相关的各种情节糅杂其中,令人昏昏欲睡,但是就在这个时刻,暴力情节突然出现,两车相撞的瞬间,女孩们以各种夸张、血腥的死亡方式命丧黄泉,之前一直伸在车窗外的导演钟爱的美足,此时也变成烂肉一块。昆汀仿佛生怕观众一下忽略了这血腥的死亡瞬间,甚至用劣质广告才使用的重复手段将每个女孩不同的死法加以展现,她们有的是脑袋被削掉一半,有的身体直接被砸成肉泥。伴以暴力场景突然呈现的是暴力行为的实施往往根本没有明确动机,是一种“即兴式”的杀人:“在这个意义上,昆廷·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成为后现代社会泛暴力时代镜语风格的一种新的典范,因为当暴力失去了浪漫的神化之后,暴力电影要讲的无非是琐事和笑话,是一本后现代的‘低俗小说’。”(13)昆汀对暴力情节的偏爱和对暴力残酷的肆意展现,使得他影片中的暴力行为虚化成一种完全形式主义的镜头语言。 人物冗长的对白虽然有时候会让观众听得昏昏欲睡,但是这些饶舌的台词也成为构建人物性格、增添影片幽默喜剧色彩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人物似乎永远不会闭嘴,不管在做什么事,总是在不停地说话。在《杀死比尔整个血腥事件》中有一个场景,复仇新娘黑曼巴在茶室大战黑帮成员,整个段落充满血腥,惨叫声不绝于耳,当暴力场景从黑色的剪影状态重新转为正常光线时,黑曼巴发现她最后攻击的一个黑帮成员竟然是个未成年的男孩,男孩瑟瑟发抖的样子显得既滑稽又可笑,这时的黑曼巴一改刚才的暴戾斩杀,反而将男孩拉过来狠揍其屁股,同时说道:“让你不学好,加入黑社会,快回家找妈妈去!”突然出现的搞笑片段瞬间弱化了刚才的暴力行为,稀释了其浓度使之前的以一敌百的血腥厮杀场面如同一场不真实的闹剧。 在运用镜头方面上,昆汀所做的更是一种多方法、多元素的糅杂:“我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拍一部影片时把多种不同的风格混在一起,我从没有只用一种特写的电影语言来拍摄,我喜欢越多越好。”(14)昆汀的电影里会出现超长的镜头,比如《刑房——死亡证据》中,四个女孩坐在桌前谈话,摄影机只做圆周运动进行拍摄,即便是人物近景和人物表情,也不加剪切,也会出现定格,比如在《杀死比尔整个血腥事件》中,只要介绍人物出场,必用定格特写人物表情来展现。总体来看,昆汀电影的镜头表达花样繁多而且运用自由,不介意使用稳定传统的镜头语言,也会出现各种实验性质的拍摄手法。在影片剪辑方面,昆汀受香港武侠片、吴宇森的动作电影的影响比较大,尤其是在大幅展现暴力行为和暴力场景时,特别注意暴力动作的节奏。在影片《杀死比尔整个血腥事件》的茶室大战一场戏中,共计用7分23秒零7帧,327个镜头,平均每个镜头只有1.5秒的时间,黑曼巴刀起刀落从未停歇,伴随着她凌厉动作的是各种残肢飞散,在紧锣密鼓的厮杀中,观众体会到暴力血腥带来的心理紧张。然而,随着茶室后门打开,刘玉玲悄然伫立于白雪茫茫中,影片的节奏马上慢下来,这时多采用远景拍摄的方法,将提刀而立的人物置于雪落无声的安静暗夜中,决斗双方皆蓄而不发,等待攻击的最佳时刻,这种得益于日本武士片的处理手法,使影片节奏动静相宜,于安静的气氛中蕴藏着更大的杀机。 昆汀在展现影片中的暴力场景时,还有一大特色就是电影配乐常常被置于主体地位。他在运用音乐时,不管是什么民族、什么风格的音乐,只要符合自己影片段落的意境,就直接拿来使用;同时,还将这些民族、摇滚、说唱、爵士、流行歌曲等音乐元素糅杂粘合在一起,表现出另一番趣味。比如在黑曼巴与石井尾莲决斗的一场戏中,先是响起日本传统民歌的曲调;随着镜头移向复仇新娘黑曼巴,音乐又变幻为具有德州风情的乡村吉他;随着两个人的打斗开始,铺底的贝司又演奏出funk风格的曲调,由于funk音乐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注重节奏上,它的重拍落在每小节的第一和第三拍上,形成节奏为主、旋律为辅的特点,所以配合着这样的律动,人物的暴力动作也显得在动作上张弛有度,使观众在愉悦欢乐的试听节奏中感受暴力动作带给人的冲击。 昆汀·塔伦蒂诺是在影像世界的包围与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导演。从他感知电影中的暴力到在自己影片作品里重现各种暴力元素,昆汀始终是在用自己的想象构筑一个虚幻的暴力世界,在他的电影中,暴力与血腥被幽默的情节和游戏化的处理方式来展现,在消解暴力的现实意味的同时也从不给暴力行为附加道德诉求,暴力行为的展开往往是人物即兴的表演,在影片故事情节上,昆汀善于借鉴前人的经典桥段加以戏仿、解构,镜头运用和剪辑方面则糅杂各种形式技巧,同时配合各种自己喜欢的音乐类型来烘托暴力场面的气氛。在赋予女性角色施暴者身份的同时,往往用独特的叙事手法和使电影中的暴力趋向形式主义,进而用叛逆的手法将血腥的暴力场景虚化、打造成一场电子游戏。 ①[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著,邵牧君译:《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207页。 ②[英]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③[法]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3页。 ④[美]杰米·格拉汉姆:《我就是电影世界的肾上腺素——昆汀·塔伦蒂诺访谈录》,《电影世界》2012年第12期。 ⑤[美]爱斯特:《脱缰的野马——昆廷·塔伦蒂诺》,《电影双周刊》1995年3月9日。 ⑥[法]樊尚·阿米埃尔、帕斯卡尔·库泰著,徐晓媛译:《美国电影的形式与观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⑦⑧⑨(12)(14)[美]G.史密斯著,李小刚译:《昆廷·塔伦蒂诺访谈记》,《世界电影》1998年第2期。 ⑩转引自郝建:《叙事狂欢和怪笑的黑色——好莱坞怪才昆廷·塔伦蒂诺创作论》,《当代电影》2002年第1期。 (11)刘新民、李建明主编:《变态心理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 (13)郝建:《电影天才还是好莱坞的坏孩子》,《当代电影》1996年第4期。标签:昆汀论文; 低俗小说论文; 电影论文; 暴力电影论文; 美国独立电影论文; 暴力美学论文; 杀死比尔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落水狗论文; 影视论文; 暴力女孩论文; 犯罪电影论文; 恐怖电影论文; 剧情片论文; 美国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