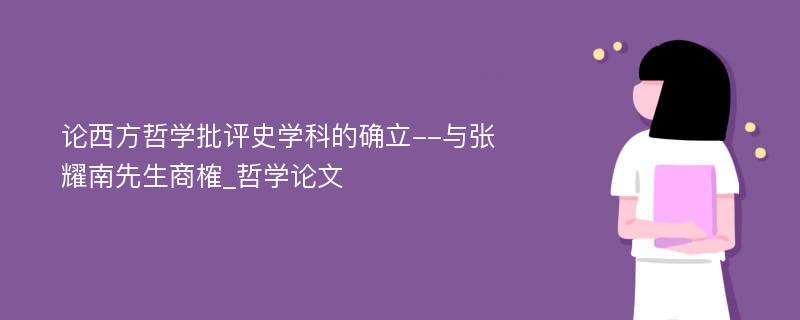
也谈“西方哲学批评史”学科的创建问题——兼与张耀南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也谈论文,学科论文,批评论文,西方哲学论文,张耀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698(2005)-03-0129-04
有幸看到张耀南博士《关于创建“西方哲学批评史”的初步设想》一文(注:张耀南:《关于创建“西方哲学批评史”的初步设想》,载《新视野》,2004年第3期;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2004年第7期。)(以下简称《创建》),被作者的大胆设想所吸引,遂仔细研读,再三玩味。阅后有若干疑问未能释解,故不揣冒昧,提出与张耀南博士共同研讨。
《创建》一文认为,创建“西方哲学批评史”学科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应该承认,文章对创建“西方哲学批评史”学科的可能性的分析是颇具说服力的(尽管文章将之置于“必要性”的框架内展开论述)。诚如作者所言,“‘西方哲学’中‘批评史’的材料,几乎是现成的”,从“柏拉图对话集”到“经院哲学”,再到“解释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都不乏“批评史”的材料,“若是详加整理,就可写成一部‘西方哲学批评史’”。不过依笔者的观点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可能创建“西方哲学批评史”,而在于是否有必要创建独立于西方哲学史的“西方哲学批评史”,而恰恰在后一点上,《创建》一文有所疏漏。
按《创建》陈述,创建独立于“西方哲学史”的“西方哲学批评史”的理由,实际上主要有两条:其一,是“学科建设方面迫切需要‘西方哲学批评史’”。其二,是“有许多‘西方哲学史’覆盖不到的地方,必以‘西方哲学批评史’研究之”。
首先看看第一条理由。我们发现,《创建》一文的陈述奠基于“西方文学”与“西方哲学”的类比。文章指出:“查‘西方文学’,其中‘西方文论’或‘西方文学批评史’学科,总是要占很大的比重。甚至可以说,它在‘西方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为什么哲学系就可以对‘西方哲学批评史’根本不提呢?”文章认定,“‘西方哲学批评史’在‘西方哲学’中之地位,等同于‘西方文论’或‘西方文学批评史’在‘西方文学’中的地位。”
这个理由真的像《创建》一文说的那样“几乎无需多论”吗?恐怕不那么轻巧。有一个问题似乎是不能不考虑的,这就是文学与哲学之间的根本性区别。
在广义的文学概念中,实际上包含了两个部分:作为艺术形式的狭义文学和由之衍生出来的文艺理论(包括文学批评)。前者主要由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和影视文学等诸多文学艺术形式构成,它借助于作者的创作活动来形成;而后者则表现为对文学艺术活动以及文学艺术作品本身的一种理论研究,它除了有创作者自身创作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外,大量的是哲学家或文艺理论家对文学艺术的理论思考和理论阐发,更加具有美学和哲学的意味。在广义的文学中,这两个部分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又相互独立,成为两个无法相互替代的独立元素。在某种极端的意义上,这两个部分之间的分离也是可能出现的:不懂文艺理论及其历史的人,也能写出某些文学作品,而许多文艺理论家却没有自己的文学作品。相应地,在广义的文学历史中,也就有了狭义的“文学史”和“文论史”或“文学批评史”的区分。换句话说,“西方文论史”或“西方文学批评史”与狭义的“文学史”比肩而立也就有了充分的依据。
然而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哲学时,情形却有了很大的不同。哲学并没有类似文学的那种广义和狭义之区分,也不存在哲学作品和哲学理论之间的二分现象,哲学作品就是哲学理论本身。一切哲学,无论是近代以前具有知识论倾向的传统哲学,还是现当代具有生存论倾向的新型哲学,都属于一定的理论形态,即便它以诗性的语言出现(如尼采的哲学著作);更为重要的是,在任何一种哲学理论形态中,批评和建构都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共同成为一种哲学理论形态赖以形成的支撑性要素。
由此看来,西方哲学史中内在地蕴涵了许多“西方哲学批评史”的材料,也就不足为奇了,它恰恰说明西方哲学的发展始终是与哲学的批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哲学研究除了现实性维度以外,还必然具有历史性维度。哲学研究的历史性维度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对哲学文本的解读和批评彰显出来的。借助于哲学家和传统哲学理论之间展开的超时空对话(通过解读和批评),后起的哲学理论与先前的哲学理论得以关联起来,哲学的传统渗透到当代哲学中,而当代的哲学又超越既有的哲学传统,由此哲学的传统得以不断地流动和更新。比如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Fundementalologie)的建立,就与其对既往西方哲学史的批评密切相关。海德格尔认为,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古希腊早期先哲开启的探寻“存在”的道路被遗忘了,大多数的哲学家都在探寻“存在者”的路上痴迷忘返,以对“存在者”的探讨替代了对“存在”本身的探讨,从而堕入了一种无根的本体论。他撰写《存在与时间》的目的,就在于重新提出并解决“存在”的意义问题,建立一种“有根的本体论”,将哲学重新导引到探寻“存在”之路。再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提出,也与他们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批评密切相关,无论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诞生地都大量地蕴涵着哲学批评的内容。伟大的哲学著作,伟大的哲学理论,必须要把自己的双脚同时植根于哲学传统和社会现实之中,在对传统哲学的批评和对现实的反思中实现哲学理论的建构。我们几乎无法找出不包含建构的纯批评性的著作,或不包含批评的纯建构性的著作。借助于批评,一种哲学理论得以置身于哲学的传统之流,借助于建构它又推进着哲学之流的奔涌。
西方哲学中的批评已经成为沟通不同时期的哲学理论以及同一时期不同的哲学理论的经纬线,离开了西方哲学中的批评,就很难理解西方哲学史中各种哲学理论之关联,很难理解西方哲学的历史和逻辑进程,西方哲学史也必将因此而变得支离破碎。难道我们有必要冒着肢解西方哲学史的危险,去创建一门独立于哲学史的“西方哲学批评史”学科吗?我们认为,“西方哲学批评史”最多只能作为一种专门史涵盖在西方哲学史当中,而不是独立于其外;“西方哲学批评史”与“西方哲学史”的关系,是不能与文学中“文学批评史”与“文学史”的关系相比附的。
其次,再看看第二条理由。《创建》一文强调,“有许多‘西方哲学史’覆盖不到的地方,必以‘西方哲学批评史’研究之”。就其论述来看,主要提到“经院哲学”与中国“经学”的比较、中西学者对哲学史的不同分期以及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解读等等。
作为学术研究的哲学史,与真实发生的哲学史相比,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重合的,这不仅是因为重现历史真实所面临的诠释学困难(注:关于这种困难,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有精辟的阐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而且还因为作为学术研究的哲学史要对真实发生的哲学史进行批评、精选、重构。德国哲学家、著名的《哲学史教程》的作者文德尔班曾经说过:“哲学史,像所有的历史一样,是一门批判的学科。它的职责不只是记录和阐述,而且还是,当我们认识和理解历史发展过程时,我们要估计什么可算作历史发展中的进步和成果。没有这种批判的观点,就没有历史。一个历史学家是否成熟,其根据就在于他是否明确这种批判观点;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在选材和描述细节时他就只能按照本能从事而无明确的标准。”(注: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8页。)依此而论,肯定有些真实发生的哲学史的内容在现有的哲学史研究框架中覆盖不到,因为哲学史家要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取舍,取舍标准的不同,哲学史覆盖的范围也会有所不同。当然,在通史中难以覆盖到的内容,在断代史、专门史中可能能够覆盖到,因为后者是对前者的某种补充。所以,创建“西方哲学批评史”学科来开拓“西方哲学通史”因学科局限而难以覆盖的某些学术领地,不能说不是一个合理且富于建设性的想法。但据此认为“西方哲学批评史”能够独立于“西方哲学史”学科,那未免就有点言过其实了。
至于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与中国古代“经学”之间的比较问题,中西学者对“西方哲学史”分期的不同见解问题,“西方哲学史”的确覆盖不到,但其实它也不应该去勉强覆盖,因为它们更多地属于“比较哲学”的研究范围,像《创建》一文主张的那样把它们纳入到“西方哲学批评史”中,实际上也是不合适的。
而“中国人的西方哲学观”或“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不同解读”,本来就属于中国哲学发展的轨迹,没有必要把它们强行纳入到西方哲学的范围里面。如果“西方哲学批评史”定位于西方哲学的话,应该考虑的倒是西方哲学在其发展进程中对不同哲学理论的批评,甚至包括他们对中国哲学的批评。所以,“西方人的中国哲学观”或“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不同解读”等方面的内容,比“中国人的西方哲学观”或“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不同解读”等更适合于纳入到“西方哲学批评史”中。
综合上述,我们认为即便可能创建“西方哲学批评史”学科,那它也只能归属于西方哲学史学科的范围,不可能独立于西方哲学史之外;创建独立于西方哲学史的“西方哲学批评史”的设想虽然大胆,但还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