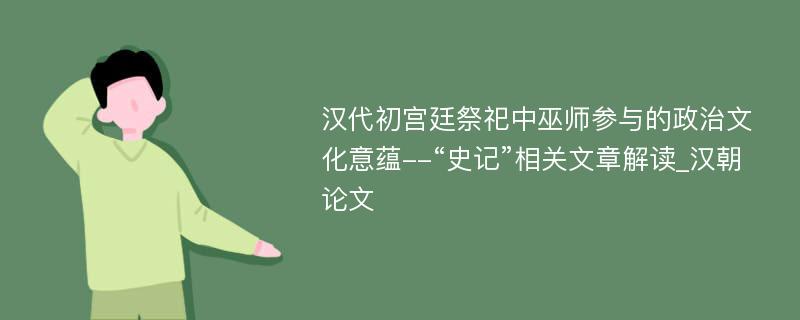
汉初异地群巫参与朝廷祭祀的政治文化意蕴——《史记》相关篇目的对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篇目论文,意蕴论文,朝廷论文,祭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12)05-0001-07
西汉初年,朝廷征用大批异地巫师到当时的都城长安,参与多种祭祀活动。这些巫师除秦地本土巫师之外,分别来自晋、梁、荆三地。征召大批外地巫师进京参与朝廷的祭祀,这在整个西汉时期是惟一的例外,在后代也很罕见。这些巫师来自多个地区,所祭祀的对象又有许多是前所未闻,因此,给人留下一系列悬念。
西汉初年是炎汉代秦的开始阶段,也是政治和文化转型的发轫期。把异地群巫参与朝廷祭祀这一事象,放到当时整个政治、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才有可能梳理出事情的来龙去脉及原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把《史记·封禅书》有关异地群巫参祭的记载,与《史记》的相关传记及《天官书》对读互证,似乎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操作方式。
一、汉初杂用异地群巫引发的学术议题
《史记·封禅书》叙述两汉初年朝廷主持的祭祀,有以下大段文字:
后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枌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于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时日。[1]1378-1379
司马迁对于西汉初年的祭祀状况作了详细记载,除了沿袭秦代已有的一些祭祀外,朝廷主持的祭祀又增加枌榆社至南山、秦中等一系列内容。其中朝廷主持的祭祀提到梁巫、晋巫、秦巫、荆巫,在古今学界引起多种猜测,是解读上述文字的难点。裴骃《集解》援引文颖如下解释:
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于晋,故祠祝有晋巫。范会支庶留秦为刘氏,故有秦巫。刘氏随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后徙丰,丰属荆,故有荆巫。[1]1379
文颖提到的“范会支庶留秦为刘氏”,其事见于《左传·文公十三年》。晋国大夫范会流亡到秦国,后来晋国又设计将他引回,留在秦国的家族成员姓氏为刘。相传范会是尧的后裔,汉代天子姓刘,亦称是尧的后裔,对此,杨伯峻先生已有详细的考证和说明[2]。按照文颖的说法,汉高祖所用的晋巫、秦巫、梁巫、荆巫,均是范氏的后裔,是刘姓成员,汉高祖是选择属于刘姓血脉的成员充当巫师。可是,文颖所说的刘氏随魏都大梁,后又迁徙到丰地的说法,无法从历史上找到线索,因此,文颖的说法在古代很少有人响应。
西汉初年的宫廷祭祀有晋巫、梁巫、秦巫,均非出自楚地。而晋巫所祭祀的东君、云中君、司命,又见于《楚辞·九歌》。这个现象又引出当代学者的另一种猜测,认为《九歌》中提到的神灵,多数不是楚地原有的祭祀对象,是楚地以外的神灵。有的学者作了如下论断:
《史记·封禅书》上说是晋巫祭祀东君、云中,河巫祀河,也就说明东君、云中君是晋地之神,河伯是北方的神祇。《九歌》中的东君、云中君和河伯都不是楚地原有的神祇,不该由楚人来祭祀。[3]32
那么,《九歌》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神灵呢?书中作了如下解释:
屈原之所以能够接触这些题材,途径很多。他在出使他国时可能耳闻过北方神祇的故事,或目睹过有关的祀典;任左徒而接待宾客时,可能了解到有关各地神祇的传说;南方保留着记载各种神话传说的书籍,屈原也有可能通过学习而知悉一切。[3]157这种推测具有合理性,所说的几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按照这种说法观照楚文化,必须承认它的开放性,它对其他地域文化的吸纳。按照这种说法审视西汉初年朝廷主持的祭祀,必然得出晋巫、梁巫、秦巫祭祀的均是本地神灵,而不是把楚地神灵作为祭祀对象,东君、云中君原本是晋地之神,到了西汉初年又由晋巫负责祭祀。由此得出的结论,关乎对西汉祭祀文化的考量和评价,涉及西汉初年楚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关联。
二、汉初杂用异地群巫与分封诸侯王的关联
汉初朝廷的祭祀兼用晋、梁、秦、荆四地的巫师,其中任用秦巫比较容易理解。兼用群巫是在刘邦都定长安之初,那里本是秦地,必然有一批秦地巫师生活在那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朝下达焚书令,“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1]255,巫书因为其特殊属性,在焚书时得以幸免。巫师作为特殊的社会角色,也往往与政治有所疏离,自身的命运有时能够不受朝代更替的影响。刘邦取代秦王朝而继续任用秦地巫师,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可以为当时的舆论所接受。至于任用荆巫,更是合情合理,刘邦是楚人,当然要选用楚地巫师在朝廷供职。
仔细阅读《史记·封禅书》有关西汉朝廷兼用各地巫师的记载,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晋地包括赵、魏、韩,可是,既然有梁巫,何以又出现晋巫?按照传统的区划来看,二者在地域上有重合,晋地应该包括梁。梁指大梁,即今河南开封,是战国中后期魏国的都城。大梁在魏地,那里的巫师为什么不称魏巫,而是称梁巫?荆巫是楚地的巫师,为什么不称楚巫而称荆巫?要破解这些难题,还需要从汉初政治格局切入,那个特定历史阶段分封诸侯王的举措,提供了破解难题的线索。
《史记·封禅书》提到朝廷主持祭祀所用的各地巫师,首列梁巫。刘邦兼用各地群巫是在平定天下、定都长安之后,时当高祖六年(前201),这个时期所封之王确实有梁王。《史记·魏豹彭越列传》记载,垓下之战结束,“春,立彭越为梁王,都定陶。”[1]2593照此说法,彭越被封为梁王是在汉高祖六年(前201)。而《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称“五年,封彭越。”[1]804两相对比,《年表》的记载似乎更接近历史实际。不管是根据哪种记载推断,彭越是在刘邦兼用各地巫师之前被封为梁王。彭越之所以被封为梁王,与他在楚汉之争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密不可分。《史记·高祖本纪》叙述楚汉相争的形势时写道:“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秦兵,绝其粮食。”[1]377彭越此举对于扭转战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梁地是他所平定,论功行赏,封他为梁王。西汉朝廷所用的梁巫,就是从彭越的领地所选出的。称作梁巫,而不称魏巫,乃是彭越封为梁王的缘故。
《封禅书》继梁巫之后提到的是晋巫。晋巫出自晋地,这与韩王信的封地直接相关。《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记载,韩王信是战国时期韩襄王之孙,随从刘邦率军入武关、汉中,后平定韩地,协助刘邦战败项羽。“五年春,遂与剖符为韩王,王颍川。”[1]2632韩王信是韩国贵族的后裔,平定韩地有功,所以封王之初居于韩地。后来,他的封地发生了变化,传记作了如下的叙述:
明年春,上以韩信材武,所王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乃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信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上许之,信乃徙治马邑。[1]2633刘邦为加强北部的边防,将韩信的封地改为晋地,其中所说的晋阳,在今山西太原以南,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北方重地,三家分晋局面的确立,关键是晋阳之战。韩王信最初被定为以晋阳为都城,后来他主动要求定都马邑,即今山西朔县,但晋阳依旧是他的领地。韩王信是在汉高祖六年(前201)春天迁入晋地,《封禅书》所载朝廷兼用各地巫师也始于此年。所谓的晋巫,就是从韩王信所辖领地选拔出来的。西汉王朝开始是定都洛阳,高祖六年六月迁到长安,征召群巫是定都长安之后的举措,韩王信领地的晋巫有充裕的时间在当年到达长安。
《封禅书》还提到荆巫,顾名思义,必然是出自荆地。西汉初年确实有荆王,他就是刘贾。《史记·荆燕世家》称:“荆王刘贾者,诸刘,不知何属。”[1]1993司马迁知道刘贾是刘邦的族人,但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血缘关系。《汉书·荆燕吴传》则称:“荆王刘贾,高祖从父兄也。”[4]1899班固认定刘贾是刘邦的堂兄,当是有所本。刘贾与刘邦的血缘关系很近,又跟随刘邦出汉中,定三秦,并在刘邦与项羽的争夺战中屡立战功。《史记·荆燕世家》写道:
汉六年春,会诸侯于陈,废楚王信,囚之,分其地为二国。当是时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贤,欲王同姓以镇天下,乃诏曰:“将军刘贾有功,及择子弟可以为王者。”群臣皆曰:“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二域……”[1]1994刘贾因战功及亲缘关系而被封为荆王,具体领地在今江苏东部泗洪一带,后来成为汉代的临淮郡。《封禅书》所说的荆巫,就是从荆王刘贾领地选拔出来的巫师。《史记·货殖列传》称:“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1]3267彭城指今江苏徐州。荆王刘贾的封地在徐州东南,汉代称为东楚文化。所谓的荆巫,乃是东楚之地所出。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封禅书》所记载的西汉初年朝廷所征用的异地巫师,除了秦巫之外,其余的梁巫、晋巫、荆巫,均来自京城以外地区,出自三个诸侯王所管辖的领地。西汉初年的朝廷祭祀之所以选用这些地区的巫师,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封禅书》所载朝廷祭祀杂用异地巫师之事,是在天下初定之际,当时百废待兴,朝廷现有的人员不足以应付文化建设的需要,因此,有时要从外地征召相关的人员。《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为了演练朝拜礼,“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1]2722鲁地是礼乐之邦,熟悉礼仪的儒生较多,叔孙通从那里征召演练朝仪的人员,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以此弥补朝廷在这方面的不足。汉初祭祀杂用异地巫师,是由于朝廷原有的巫师数量有限,难以承担新增的祭祀项目。
第二,朝廷征用的异地群巫来自晋、梁、荆三地,而这三地的诸侯王均是与刘邦一道平定天下的开国元勋,所处的地理位置又极其重要。朝廷选用这三地的巫师是在分封诸侯王之后进行的,是加强朝廷与诸侯王关系的重要举措。文化建设方面的人员选用与巩固新生政权密切相关,体现出朝廷对这三位诸侯王的信任和倚重。
三、异地群巫参祭所体现的文化趋势
西汉初年朝廷的祭祀杂用晋、梁、楚、秦诸地的巫师,从这些巫师的祭祀对象及地点来考察,可以看出朝廷这些祭祀的文化趋势。
第一,有些祭祀反映了西汉王朝对楚文化的继承,把楚文化带进了中央朝廷和关中地区。晋巫祭祀的对象有东君、云中君、司命,荆巫祭祀的对象也有司命,这几位祭祀对象均见于《九歌》,指的是太阳神、云神、司命神。显然,这是把楚地原有的祭祀带进西汉朝廷,分别由来自晋地和荆地的巫师加以承担。至于晋巫和荆巫的祭祀对象都有司命,那是因为《九歌》的司命神有两位,即大司命和少司命,所以要由晋、荆两地的巫师分别承担祭祀。
《史记·封禅书》所列举的祭祀对象,有多个名称冠以巫字。晋巫祭祀的有巫社、巫祠,秦巫祭祀的有巫保,荆王祭祀的有巫先。从这些名称来看,祭祀对象均与巫有关。关于巫先,司马贞《索隐》称:“巫先谓古巫之先有灵者,盖巫咸之类也。”[1]1379这种解说是正确的,传说巫咸是巫术之祖,《世本·作篇》称:“巫咸作筮”[5]。所谓的作,指的是首创。巫咸是传说中的巫术之祖,与楚文化的关联最为密切,屈原的《离骚》就用了大段文字描写巫咸夕降的场面[6]37-42。巫先指巫咸,这位与楚文化关系极为密切的神灵由荆巫承担祭祀,是楚巫祭祀楚地神灵,可谓恰如其分。晋巫祭祀的巫社、巫祠是由祭祀场所而得名。巫社,指祭祀巫神之社,亦即土地庙。这种建筑没有屋顶。巫祠,谓祭祀巫神的庙宇,这种神庙有屋顶。至于秦巫祭祀的巫保,指的也是巫神。《诗经·小雅·楚茨》提到神保,克鼎铭文提到圣保,对此,王国维先生指出:“是‘神保’、‘圣保’皆祖考之异名。”[7]除此之外,《诗经·小雅·天保》、《楚辞·九歌·东皇太一》有灵保,这些缀以保字的称谓,指的都是神灵,天保即天神,灵保即神灵。由此推断,秦巫所祭祀的巫保,指的是巫神。《封禅书》列举四种祭祀都是以巫神为供奉对象,体现出楚文化尚巫的传统。
《封禅书》记载梁巫的祭祀有房中、堂上,这是就祭祀场所而言,司马贞《索隐》称:“《礼乐志》有《安世房中歌》,皆谓祭时室中堂上歌先祖功德也。”[1]1379司马贞所说的《礼乐志》,指《汉书·礼乐志》,其中对房中乐有如下记载:“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4]1043由梁巫主持的祭祀,用的乐曲是楚声,而不是梁地曲调,带有鲜明的楚文化特点。这个事实也可进一步说明晋巫祭祀的东君、云中君、司命都是楚地神灵,而不是出自晋地。
《括地志》卷一记载,刘邦因为其父对长安的环境不适应,“高祖乃作新丰,徙诸故人实之。”[8]刘邦的故乡是沛县丰邑,在今江苏濉溪附近。他为了使父亲能在长安生活愉快,竟然模仿家乡的样态再造一个丰邑,并且连其中的成员都是由家乡迁入。刘邦对楚文化情有独钟,他当上天子之后对于楚文化的继承更是不遗余力。朝廷选用异地巫师所进行的祭祀,带有鲜明的楚文化特点。
第二,异地巫师所进行的祭祀,反映出对社神的高度重视,使社神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对于社神的祭祀,先秦时期就已有之,并且比较普遍。但是,在朝廷主持的祭祀中,把众多的社神作为供奉对象,汉初朝廷却是开风气之先。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高祖二年(前205)“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汉社稷”[1]370,这是以社稷的废立显示改朝换代。《史记·封禅书》记载,同一年,“因令县为公社”[1]1378。所谓的公社,指官社,即由官方主持祭祀土地神的场所。《封禅书》所记载的祭祀对象,多次提到社。丰邑有枌榆社,梁巫祭天社,晋巫祭巫社,秦巫祠社主。由朝廷主持的祭祀所涉及的社如此之多,确实是史无前例,开创了汉代重视社神之风。陈直先生对居延汉简所载祭社文献作了梳理,并且指出:“两汉人最重祭社”[9]。这种传统是由汉初朝廷奠定的。
第三,异地巫师所进行的祭祀,有的是对初建的西汉王朝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带有歌功颂德的性质。如前所述,梁巫主持的堂上、房中祭祀,演唱的乐曲是出自高祖唐山夫人之手的《安世房中歌》。这组歌共十七章,歌辞除少量用以娱神的句子外,其余绝大多数文字都是歌颂西汉王朝的功德。由此可以设想,由梁巫主持的堂上、房中之祭,其场面、气氛都体现出对西汉朝廷的歌颂赞美,娱神反倒居于次要地位。
《封禅书》所载梁巫的祭祀对象有天水,何谓天水?《史记》及《汉书》的古代主要注家均未解释。这里的天水,指的当是水位星。《史记·天官书》称:“东井为水事。”司马贞《索隐》引《元命苞》:“东井八星,主水衡也。”[1]1302东井,属二十八宿南方朱雀宿的星座,主水之星就在东井。《史记·天官书》提到战国时期的星象家主要有如下几位:“在齐,甘公;楚,唐眛;赵,尹皋;魏,石申。”[1]1343张守节《正义》:“《七录》云:石申,魏人,战国时作《天文》八卷也。”[1]1344石申是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家,据石申所言,“水位四星在东井东,南北列。”[10]468这段话当出自他所著的《天文》一书。水位四星位于东井星宿的东部,按南北方向排列,因此之故,东井又称主水衡之星,他的名称包含这种含义。
对于西汉王朝来说,水位四星所在的东井,亦称天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星宿。《史记·天官书》称:“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1]1348关于这句话的具体所指,《史记·张耳陈馀列传》所载甘公的一段话所言甚明:“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虽强,后必属汉。”[1]2581这里的甘公,指《天官书》提到的齐地天文学家甘德。汉高祖率兵入武关那年,正值五星聚于东井。按照当时划分的地望与星辰的对应关系,东井与秦地相对应。五星聚于东井是大军压境之象,甘德预言刘邦一方必胜。对于刘邦一方而言,东井,亦即天水,是吉祥之星。正因为如此,汉代典籍反复提及这一事象。班彪的《王命论》称:“始受命则白蛇分,西入关则五星聚。”[4]4212这里指的是汉高祖斩白蛇起义的传说,以及他率兵入武关直捣咸阳一事,五星聚于东井作为吉兆看待。既然天水指的是水位四星所在的东井,对于西汉王朝来说是吉祥之星,又是反秦胜利的见证之星,从那里可以品尝胜利者的自豪和喜悦。梁巫祭天水,反映的是西汉王朝对历史的追忆和纪念,起到昭示汉高祖刘邦历史功绩的作用,当然也包括对天水星的感恩心理。
梁巫祭祀的星宿称为天水,《汉书·地理志》所列行政区有天水郡。颜师古注:“《秦州地记》云:郡前湖水冬夏无增减,因以名焉。”[4]1612按照这种说法,天水是因为本地的湖水而得名。天水属秦地,与之对应的星宿有东井,即水位星。天水的得名,当是取自星宿。
四、巫师所出地望、所祭对象与星宿配置的对应关系
汉初朝廷主持对天水星、亦即对东井星宿的祭祀,已经涉及人间祭祀与天上星宿之间的关联。深入加以考察还会进一步发现,巫师所出的地望、所祭祀的对象,往往与该地所属的星宿存在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有的比较明显,容易发现;有的则非常隐晦、需要深入发掘才能显示出来。本着先易后难的次序,择其要者依次梳理如下:
第一,梁巫祠天社与参宿的对应。《史记·天官书》提到梁巫的祭祀对象包括天社。天社,实有其星。“甘氏曰:‘天社六星在弧南。’”“甘氏赞曰:‘老人天社,理落祷祀。’”[10]509按照甘德的说法,天社星在弧星的南部,是祭祀的对象。如前所述,《史记·张耳陈馀列传》提到的这位甘公,秦末到楚汉相争之际仍然健在。由此看来,汉初朝廷主持祭祀天社,在星象上是有依据的。天社由梁巫祭祀,天社星与弧星相邻。《史记·天官书》提到参宿时列举的星宿有弧:“下有四星曰弧,直狼。”[1]1306弧星属于参星系列,与狼星相对。《汉书·地理志》写道:“魏地,觜觿、参之分野也。”[4]1646魏地亦即梁地,它所对应的星宿就包括参星,而梁巫所祭祀的天社星正属于参宿系列。梁巫所出的魏地,他所祭祀天社星所在的参宿,在古人的观念中正好形成上下对应的关系。
第二,晋巫祠先炊、荆巫祠施糜,与张、翼星宿的对应。《史记·封禅书》记载晋巫的祭祀对象有先炊,张守节《正义》称:“先炊,古炊母神也。”[1]1379所谓先炊,指最早发明炊事者,在后代被奉为神灵而加以祭祀。天上的星宿也有与炊事存在关联者,《史记·天官书》称:“张素,为厨,主觞客。”对此,古代注家作了详细的解释:
《索隐》:“素,嗉也。《尔雅》云:‘鸟张嗉。’郭璞云:‘嗉,鸟受食之处也。’”《正义》:“张六星,六为嗉,主天厨食饮赏贲觞客。”[1]1303
鸟宿与炊事、招待客人联系在一起。嗉,指鸟的胃,承受食物的器官。张宿与炊事相关,《史记·天官书》称:“柳、七星、张,三河。”[1]1330与张宿相对应的地望包括三河。所谓的三河,是汉代人对河东、河内、河南三郡的称呼。其中河东郡位于今山西南部,是春秋时期晋国的腹地。晋国腹地与鸟宿存在对应关系,鸟宿被视为主持饮食之星,由晋巫祭祀先炊,与其所出地域及天上的鸟宿,存在着意义上的关联。
《史记·封禅书》记载荆巫祭祀的对象包括施糜粥,《索隐》引郑氏说:“主施糜粥之神。”[1]1379荆巫所祭祀的是主管施舍之神。如前所述,汉初荆王刘贾所辖领地位于西汉临淮郡一带,古属吴地。《汉书·地理志》写道:“吴地,斗分野也。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尽吴分也。”[4]1666荆王刘贾所在的临淮郡一带,与之相对应的星宿是南斗。在古人观念中,南斗是主持赏赐施舍之星,对此,战国时期的星象家已经作了解说。甘德云:“南斗星明,大爵禄行,天下安宁,将相同心。”[10]425魏国石申称:“斗主爵禄,褒贤达士。”[10]425南斗在古人观念中是主持赏赐施舍之神,与之相对应的地望包括荆王所辖的领地,荆巫所祭祀的是施舍之神,与南斗的属性正相符合。
晋巫祠先炊,荆巫祠施糜,这两处巫师祭祀的对象均与炊食、施舍相关。而晋、荆两地所对应的星宿,或主饮食,或主赏赐。巫师所出的地望,所祭祀的神灵,与其相对应的星宿,同样具有内在的关联。
第三,秦巫祭族纍与舆鬼星宿的对应。《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巫的祭祀对象包括族纍。关于族纍和巫保,司马贞《索隐》称:“二神名。纍,力追反。”[1]1379颜师古注《汉书·郊祀志》亦称:“巫保,族纍,二神名。”[4]1211把族纍释为神灵名称,与这个称号的含义难以相契。族,家族、宗族之义。《说文解字·系部》:“纍,缀得理也,一曰大索也。”段玉裁注:“引申之,不以罪死曰纍,见扬雄《反离骚》注。”[11]扬雄的《反离骚》见于《汉书·扬雄传》,其中有“钦吊楚之湘纍”的句子,颜师古注引李奇的解释如下:“诸不以罪死曰纍,荀息、仇牧皆是也。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也。”[4]3516李奇对于纍字的解释与《说文解字》段注相一致,是汉代对于无辜而死之人的称呼。他所提到的荀息和仇牧,分别死于晋国和宋国的内乱,都是无辜的牺牲者,具体记载见于《左传》的僖公九年、庄公十二年。秦朝严刑峻法,死于无辜的人数极其众多,因此,汉初朝廷安排秦巫祭祀无辜而死的家族成员,带有安慰亡灵之意,同时又是对亡秦暴政的揭露。《史记·天官书》写道:“东井、舆鬼,雍州。”[1]1330秦国地处雍州,即关中地区。与秦地相对应的星宿是东井、舆鬼。东井即天水星,它与秦王朝的关联前面已经提及。战国时期魏国石申对舆鬼星有如下解说:“中央色如白粉絮者,所谓积尸气也。一曰天尸,故主死丧,主祠事也。”[10]438舆鬼,顾名思义,就是承载死鬼。古人把它视为死尸堆积、阴气充溢之象,和死丧密切关联。秦巫祭祀无辜而死的族人,与秦地相对应的舆鬼星被先民视为死丧之象,由此而来,秦地祭祀的对象就与舆鬼星构成意义上的关联,具有相通的内涵。
第四,晋巫、荆巫祭司命与北斗、南斗的对应。《楚辞·九歌》有《大司命》和《少司命》,二司命所指究竟是哪两位神灵?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悬案。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为《大司命》解题时写道:
《周礼·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传》云:“三台,上台司命,为太尉。又文昌宫第四曰司命。”按《史记·天官书》“文昌六星,四曰司命。”《晋书·天文志》:“三台六星,两两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为司命,主寿。”然则有两司命也。[6]71
洪兴祖是宋代人,他援引唐人贾公彥在《周礼注疏》中所述《星传》之语,把三台星说成是司命神。再加上《史记·天官书》所标示的文昌第四星为司命,推断这两个星宿是《九歌》所写的两位司命神。
朱熹的《楚辞集注》也是用三台星和文昌星来解说两位司命神,并且指出彼此之间的对应关系。他在《少司命》解题中写道:“按前篇注说有两司命,则彼固为上台,而此则文昌第四星欤?”[12]按照朱熹的说法,大司命指三台星宿的上台星,少司命指文昌第四星,它们都属于北斗星宿。
北斗星宿所属文昌宫有司命星,《史记·天官书》有明确记载:“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1]1293这段叙述非常清晰,文昌宫第四星是司命星。与司命并列的都是以朝廷显贵官职命名的星,有将有相,显然,文昌宫被作为了天界的朝廷看待,因为它居于“斗魁”,与北斗七星相邻,所以在星界的地位甚高。《九歌·大司命》开篇云:“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王逸引《淮南子》注:“天门,上帝所居紫微宫门也。”[6]68大司命是从天门乘云而下,古人传说的天门位于北部天界,大司命所乘的是“玄云”,按照五行说的划分,北方为玄,正与北斗星所处的方位一致。由此看来,大司命应是指文昌宫第四星,合乎人们对这颗星所作的定位,是司命神。
洪兴祖、朱熹都根据贾公彦《周礼注疏》的说法,认为三台六星中有司命星。《史记·天官书》在叙述文昌六星之后写道:“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齐,君臣和;不齐,为乖戾。”司马贞《索隐》:“魁下六星,两两相比,曰三台。”[1]1294司马迁在《天官书》中所说的三能,后来又称为三台。无论是司马迁,还是在他之前的战国天文学家,都没有说过三台星中有司命星。贾公彦所引的《星传》当是出于后人之手,把三台星说成是司命星所居之处,是汉代纬书始肇其端。《晋书》成书于唐初,也是沿袭后来的说法,以三台解释司命星,那里有两颗司命星,这样一来,文昌宫的司命星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所以,断定三台星中有司命星是后人的附会,不是先秦时期的古说,可以把这种可能性排除。
先秦时期形成的星相术还有一种说法,把南斗说成是具有司命职能的星神。《史记·天官书》称:“南斗为庙。”[1]1310大司命所居的文昌宫是先民想象中的天宫朝廷,亦称天府,南斗则被定位为天庙,天府与天庙之称,取自人间的朝廷和宗庙,南斗在星界的地位很高,仅次于北斗和中宫天极星。战国星相家甘德云:“南斗,天子寿命之期也。故曰,将有天下之事,占于南斗也。”[10]425甘德把南斗说成是司命之星,不过,它的职责与文昌宫的司命星稍有区别,文昌宫的第四星是统领司命之职,南斗的司命职责则仅是针对天子。《圣洽符》亦有类似说法:“南斗者,天子之庙主,主纪天子寿命之期。”[10]425南斗被视为天庙,是供奉祖先神之处,因此把它说成是司命之星,天子寿命的长短由南斗掌握。《史记·天官书》叙述北斗七星的职能云:“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1]1291这样看来,南斗也在北斗统辖之下。作为司命之星,文昌宫的司命星统辖南斗,文昌宫的司命星为大司命,南斗为少司命。所谓的大、少,乃是古代对正、副职的称呼。
《史记·封禅书》记载,晋巫、荆巫均祭祀司命,那么,具体分工如何呢?这从他们所出地望与星宿的对应关系中可以找到答案。《史记·天官书》叙述地望与星宿的对应关系写道:“柳、七星、张,三河。”[1]1330这里所说的七星,指北斗七星,司命神所在的文昌宫属于这个星系。与北斗七星系列相对应的地望包括三河,而属于晋地的河东郡就是三河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样看来,晋巫所祭祀的司命神,具体是指文昌宫第四星,属于北斗星系。如前所述,西汉初年荆王刘贾的领地在临淮郡一带,古代属于吴地,与之相对应的星宿是南斗。荆巫祭祀的司命神,指的是南斗。荆巫和晋巫所祭祀的司命之星分别属于南斗和北斗,南北各一,相互辉映。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封禅书》所载异地群巫所出之地与他们祭祀对象及星宿配置所形成的对应关系,可划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巫师所出地望与所配置的星宿相对应,而祭祀的对象就是所配置的星宿本身,梁巫祠天社,晋巫和荆巫祠司命,属于这种类型;第二种类型是,巫师所出地望和所配置的星宿构成对应关系,祭祀的对象虽然不是所配置的星宿本身,但是,所配置星宿的文化内涵,与巫师的祭祀对象密切相关,晋巫祠先炊,荆巫祠施糜,秦巫祠族纍,属于这种类型。巫师所出地望与祭祀对象、星宿所形成的对应关系,在《封禅书》中出现了多个案例,这种情况表明,西汉朝廷当时从多个地域征召巫师,除了政治方面的因素起作用,还有文化方面的考量。关注祭祀对象与星宿配置的关联,以此为根据征召相关地区的巫师。
《封禅书》记载祭祀事象,《天官书》记载星象,二者均具有深奥神秘的属性。先民所持的是天地人三才相通的理念,因此,通过《封禅书》与《天官书》的对读,以《天官书》来解读《封禅书》,异地群巫的许多祭祀就可以得到合理的阐释。当然,仅靠《天官书》的记载来解读《封禅书》,还显得材料单薄,有些问题无法下定论,这就要借助于司马迁之前的战国天文学家的相关论述。而对于《史记》成书之后生成的文献,则要采取谨慎的态度,斟酌取舍。
《史记·封禅书》所载西汉初年杂用异地群巫参与朝廷祭祀之事,发生在天下初定之际,是在特定历史阶段采取的应急措施。随着西汉王朝的日益稳固,礼乐制度愈来愈健全,大批征召外地巫师的事情未再出现。尽管如此,异地群巫进入朝廷参与祭祀,毕竟使西汉王朝在前代的祭祀对象之外,又增加了一系列加以供奉的神灵,使得西汉朝廷的祭祀文化,在继承秦制的同时,又有别于秦朝,并且超越秦朝。从异地群巫所承担的祭祀也可以看出,这些新增祭祀项目的设计者,具有清醒的政治意识和良好的文化素养。所征召巫师的所出之处,均是当时政治格局的关键之地。而祭祀所体现的巫师所出之处与所供奉的神灵、所配置的星宿形成对应关系,表明祭祀设计者具有广博的知识、渊深的学问,是对祭祀文化所进行的成体系的建构。
标签:汉朝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史记论文; 祭祀论文; 南斗六星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九歌论文; 封禅书论文; 天官书论文; 司命论文; 楚文化论文; 北斗七星论文; 二十八星宿论文; 远古论文; 西汉论文; 东汉论文; 秦朝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汉书论文; 后汉书论文; 离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