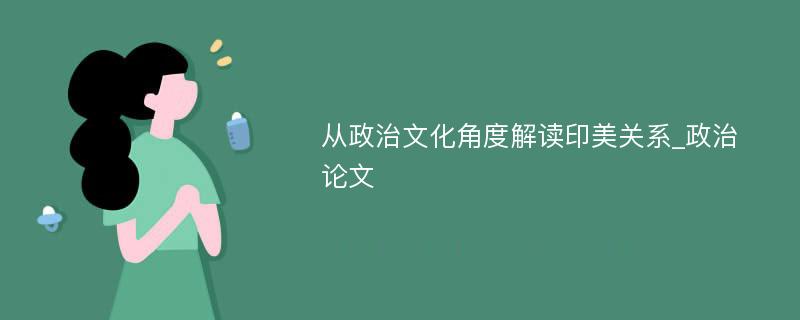
印美关系的政治文化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关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后,美国确立了其世界霸主地位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角色。在二战后的世界历史、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中,美国一直是独占鳌头和备受瞩目的国家,与美国的关系成为众多国家外交的重点。本来同属西式民主政治体制国家的印美两国,应具备更多发展双边友好关系的有利条件,但实际情况却是,印美关系的发展艰难坎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总有不尽完善、难以令人信服的方面,国际关系问题的变化与复杂性要求理论的不断跟进和研究视角的不断调整。
国际关系维度的政治文化
随着国家间因文化差异引发的冲突与矛盾的加剧,学者们在关注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结构转型与变迁的同时,也认识到民族文化的差异逐渐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矛盾与冲突的根源之一,而且,文化的差异已成为影响或制约各国外交决策与实践的重要因素之一。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到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等,都是学者们从文化视角分析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问题的积极尝试。
虽然文化是分析国际关系问题时不可或缺的考虑因素,但文化概念本身的宽泛性和内涵外延的模糊性也给我们提出了难题。在分析各国的外交时,哪些方面更需要我们特别关注呢?随着近年来文化与国际关系讨论的深入,理论范式的创新,更具特色的政治文化逐渐适应了这一需要并成为人们透视国际关系问题的新视野和新方法。学者们普遍认为,从文化学与政治学交叉的政治文化视角来探讨国际关系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政治文化是一个带有特定和特殊意义的政治学术语。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lmond)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①美国著名学者杰里尔·A·罗赛蒂先生对政治文化与对外关系之内在联系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他在《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一书中,把政治文化直接定义为,人们看待自己的国家以及其与世界上其他地区和国家关系的态度和方法,并强调政治文化包含着各种各样的重要价值观,如美国的政治文化就包含民主、个人主义等。他认为,政治文化不是以立即的或直接的方式,而是通过渲染人们对自己的国家及其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的看法来影响国内政治和政策制定的过程②。
总之,政治文化是指与政治有关的文化现象,它探讨的不是政治行为本身而是影响政治行为的文化因素。本文侧重于对一国政治的对外方面的政治文化分析,或者说是对一国外交的政治文化解读,因此本文所指的政治文化主要包含属于一国看待自己国际地位,与他国关系,影响外交政策制定和实践的比较稳定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观等。就印度来说,“大国主义”精神、“印度中心论”就属于这一范畴;对美国而言,“山巅之城”、“上帝选民”等思想熏陶下的政治文化也是自有其独特畛域的。
显然,由于印美两国历史进程的迥异、地理位置与环境的悬殊、政治经济发展的差异及国际交往程度的不同,美国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与印度大国主义政治文化的精神诉求明显存在着差别。不过,近代以来两国追求西式民主政治的不懈努力,又培育出了一些相同或相近的政治文化因素,成为双方相互靠近的动力。印度对自己国际地位的设定与美国对这一定位的认同程度,以及相互间对发展彼此关系的看法与愿望,直接影响着双方关系的微妙变化。
冷战时期印美关系的政治文化思考
美国对印度“有声有色的大国”地位的不认同甚至反对是印美两国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印度自独立以来遵循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政治理念即像印度这样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并且具有极大发展潜力的国家,不能作为任何意识形态或权力集团的附属,而应该充当与美苏平起平坐的角色,至少也应获得同中、法、英相同的政治地位。因此,印度的大国主义精神决定了印度确立的对美关系的基本原则及目标主要有:在国际事务中,获得与美国同等的尊重;寻求与美国建立积极而平等的关系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联盟或依附关系;至少取得美国对其大国地位追求的支持。因此,印度除了在冷战时期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外,一直遵循着独立的道路,并且力求避免与别国的密切结盟关系③。因此,印度领导人在处理同美国的关系上,时时表现出强烈的大国自尊和自傲感,处处希望美国把印度当作大国对待。但是,“粗心”的美国并没有注意到“敏感而细心”的印度的心思。
1949年10~11月间,尼赫鲁首次访美,给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留下世界上“最难对付的人物之一”的印象。尼赫鲁则认为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对印度持有“优越感和恩赐态度”。数月后,尼赫鲁总理看到美国热情接待巴基斯坦总理阿里汗时很是生气,遂得出美国企图“抬高巴、压低印”的结论,并批评美国在“政治上极不成熟”。被伤及自尊的印度对美国实行了报复。1953年12月初,尼克松副总统访印后说,尼赫鲁是他那次出访的17国中对美国“最不友善的领导人”。这种相互间的不友好气氛并不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恩怨,而是国家地位认同的差异导致的外交报复。其实,尼克松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心思,“尼赫鲁反对美供巴武器,如果不是出于他个人渴望控制也是出于渴望影响南亚、中东和非洲。”④“他自诩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不结盟运动的缔造者,但是他的一举一动表明,他希望世界真正把印度作为大国对待。”⑤但是,美国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对待印度的态度。
后尼赫鲁时代印度领导人强烈的大国意识丝毫未减。英·甘地执政后想使印度不仅作为印度古代文明的继承者、主宰南亚的强国和不结盟运动的领袖,而且希望使印度成为受人尊敬的重要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重要角色⑥,实现“穷国也能发挥大国作用”的愿望,保持住印度的大国自尊和身份。可是,美国的做法重重创伤了印度的“死穴”。比如,60年代印度由于遭受连年粮荒向美国请求援助,美国政府自称是为了促使印度政府改革农业以实现自力更生,就警告印度政府,在印度未能整顿好本国粮食生产之前不会再与印度签订长期粮援协议。在这一事件的交涉中,印度感觉自己处于受屈辱的乞援地位。当印度面临断粮的危急关头,英·甘地只得忍气吞声地亲自打电话向约翰逊恳求美国发放480号公法剩余农产品援助,据当时在场的她的新闻顾问夏拉德·普拉萨德回忆,当英·甘地放下话筒时,便恼怒地发誓:“我再也不会去乞求粮食了”。美国虽然是印度最大的经济援助国,但其对印度的援助常使印度人感到双方间是一种“施与者”与“受赠者”的关系,美国的傲慢自大及对印度大国自尊的漠视使印度觉得受到了轻视而倍感屈辱。
同样,1971年底,英·甘地访美时在白宫草坪欢迎仪式上致答谢词中顶撞了尼克松总统,次日尼克松就在白宫会见英·甘地时进行了报复,故意让她空候了45分钟。基辛格称这是他参加过的首脑会见中“最糟糕、最令人痛心的一次”。随后的晚宴上,两人也是话不投机,谈话不多。英·甘地随行的新闻顾问回忆说:“这是他参加过的百次类似宴会上气氛最为紧张的一次。”⑦暂不说美国出于何种考虑,仅从印度方面来说,印度认为,美国处处阻挠其实现称霸南亚的梦想,总是想变印度于仆从国的地位,希望印度为其火中取栗。印度人认为,美国插手南亚地区事务的目的就是要扮演当年英国撤离时的角色,印度抵制美国在印度的各种企图,就是避免成为美国的附庸国⑧。这是印度从此疏远美国的重要原因,因为,美国不能以平等身份对待印度,从不认同印度的大国地位并给与相应的支持,愤怒的印度转而投向美国的对手但给印度大国自尊的苏联的怀抱。总之,印度人被美国长期严重伤害的民族自尊心渐渐内化为印度人的反美情绪。
冷战后印美关系的政治文化解读
印度追求“有声有色的大国”地位的独立外交政策的内在逻辑,不仅主导了印度在冷战时期的对外关系,而且仍适用于冷战后。在当今的“单极”秩序下,印度既不打算与美国永久结盟,也不打算永远反对结盟,而是设法开创必要的政治空间,在此空间内,其国力能够得到提高,其地位可得到广泛承认。
冷战后美国虽然屡屡提及印美关系的重要性,但总是说得多,做得少。从目前看,美国仍未视印度为平等的盟友和大国,这是制约双方关系发展的重要不利因素。从双方关系的现实看,冷战后美国看待印度的视角并没有多大变化,美国仍认为“印度现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和印度的关系为美国提供了可以直接影响印度对涉及美国重要利益的世界事务的看法的机会,同时,也将为美国及时获得潜在的危害性政策的早期预警提供保障”⑨。美国一直将印度的地缘地位及民主制作为发展同印度关系的理由,正如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所说:“印度是拥有关键的地缘战略位置、庞大中产阶级的民主国家”,是其所在地区的“稳定之锚”⑩。美国南亚问题专家丹尼斯·库克斯认为,“如果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发展不顺的话,美印更为密切的关系就会切实有用。”(11)印度仍只是美国手中的一颗棋子而已。
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不知道印度的心思,而是故意漠视。虽然印度实行的是西式的政治制度,但印度的印度教文明和美国的基督教文明毕竟分属不同的文明体系,美国害怕受到来自异文明的威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便是代表。在美国人看来,作为“山巅之城”和“希望之乡”的美国的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最高体现,也是最值得推广的。他们赞赏印度文明,只是从文物古迹的角度来欣赏而已。美国人认为,东方文明的价值体现在过去,西方文明才属于当代,而一种在他们看来落后的文明想要与他们的文明平起平坐,这是难以接受的。这种潜在的、深层的认知差异是难以在短期内消弭的,因而成为导致美国在承认印度大国地位时有所保留的深层政治心理和情感因素。特别是,美国虽然常宣示自己的对外扩张行为是“天赋使命”和仁心善举,以掩饰其现实的利益追求及战略图谋,为其插手世界事务寻找道义支持,真正的目的是充当“世界领袖”。美国不允许其他国家挑战其霸主地位,就是对美国在世界某一地区的优势构成潜在威胁都不允许。因此,美国不愿印度在南亚—印度洋地区坐大,以避免使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受到威胁。出于此心的美国,在承认印度大国乃至地区大国地位时是有保留的,认为印度虽是可用以遏制中国的力量,却是一个“任性的国家”,要把印度绑定于自己的战略车轮上是不可能的,美国在对印度的大国追求表示担心的同时需对其加以防范。兰德公司的报告把印美关系说成是“仍然处于冷战后解冻的早期阶段,尚未克服过去遗留下来的分歧疑虑”。2001年 8月21日,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彼德·罗德曼表示,美印关系是有限的,“印度不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友”(12)。印度以及南亚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只是“处在美国对外优先考虑问题表上的中高偏上的位置”(13)。
总之,美国的南亚利益是冷战和其他全球事务的派生物,是美国全球利益在南亚的一种标志。印美间实力的不对称性使美国实际上并不把印度当大国看待,对于印度的地位和重要性,美国从来都是有选择的重视。事实上,美国既不愿把印度看作大国,也不愿把印度看作盟国,更不愿考虑印度的谋求大国的观点和感受,印度实际上连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地位也没取得,这让印度有强烈的失落感。美国为完成其世界领袖目标主张“单极”世界,而印度向来坚决反对美国的这一主张和行动,正如美国前驻印大使特雷西塔·谢弗所言,“印度不喜欢一个两极的世界,也不喜欢一个单极的世界,它喜欢一个多极的世界”。印度倡导多极化的目的是谋求成为“世界一极”并进而实现其大国梦想;而美国所倡导的单极领导理论是为了保持其全球霸主的地位并能主导国际事务,双方的战略利益明显发生冲突,长期合作的目标意图相左,美国的颐指气使和印度的勃勃雄心必然在建立新秩序问题上迎头相撞,美国不会轻易示弱,印度也不会轻易放下自尊,甘愿充当美国的战略棋子。而且,印美在印度洋的竞争会大大加强,双方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印度大国思想的延伸便是,在其内心深处一直存有将印度洋看作自己的“内湖”或“印度的印度洋”的观念,十分反对其他国家染指这一地区,因此不断加强其远洋进攻和控制能力。而美国出于其全球利益的考虑以及在南亚、中东、中亚的战略筹谋,必然深入涉足印度洋,这样,稍有不慎双方就会发生利益冲撞。在印度看来,美国在印度洋控制力的加强势必对其实现大国目标存在制约,双方争夺海权的问题将凸显(14)。因此,美国不愿印度在印度洋地区坐大,以避免对其在这一地区利益的威胁,它在承认印度地区大国地位时是有保留的,相应的政策措施必然波及到印美关系。
结语
印美关系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若即若离、不冷不热,彼此间有着很强的不信任感。美国视印度为桀骜不驯的地区大国,与巴基斯坦相比,印度是一个不容易相处的国家。美国人对印度的印象是:支持苏联搞霸权、在邻国关系上实行黩武政策、无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核禁试条约、无视人权、在世贸组织谈判中吵吵闹闹。印度对美国的记忆也是苦涩的:与巴基斯坦结盟,特别是在印巴战争中支持巴基斯坦;经济援助常与政治挂钩;在印度洋对印度利益存有直接或间接的威胁;在中东和亚太实行新殖民主义;等等。这激发了印度人潜意识中的历史受害者心理和使国家强大的政治情感与价值取向。尽管印度想同美国建立一种新的、切实可行的政治和军事关系,以提高印度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但反美在印度仍相当有市场。加之,印美在建立世界新秩序以及人权、主权等基本国际政治理念的理解上存有的严重分歧,美国政治文化中“天赋使命”观指导的霸权外交的无限放大,越来越与印度大国主义政治文化中的权力追求与大国目标相忤逆,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利益认同的相异,是导致印美双边关系难以实现根本性改善的重要原因。总之,美国对印度“有声有色的大国”地位的不认同甚至反对,已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
但是,美国的强大又使印度时时有求于美国。对印度来说,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影响都是举足轻重的:在经济方面,美国是向印度提供双边援助较多的国家,也是印度重要的贸易伙伴、投资者及技术提供者;在政治与外交方面,需要同美国维持工作关系以免自己沉寂于西方社会。美国已成为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其经济、技术和军事优势以及在当今国际政治中的霸主地位使印度认识到,印度的国家利益将通过全方位提升与美国的关系而得到满足(15)。冷战后伊始,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不升反降,甚至有边缘化的危险,印度亟需在国际社会中谋取到一个有利的地位。印度精英的共识是,在失去苏联的强力支持后,与美国建立起密切关系,借助美国的支持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显然十分必要,即便是在南亚坐大,在南亚区域内问题上享有较大的代表权,获得美国的支持也极为重要,况且印度经济改革迫切需要的技术、资金等都有求于美国。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南亚部主任特雷西塔·C·谢韦认为,印美这两个民主大国都认为加强合作对双方有好处。对印度来说,倚赖与美国的良好关系来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以实现其在世界上发挥重要领导作用的雄心(16)。因此,印度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时,常常陷入外交困境,一方面对美国的强权政治十分敏感,以反对美国的做法保持印度的大国自尊与身份;另一方面又强调两个民主国家的共通性讨好美国,对美国的一些要求常常不得不做出让步。而美国在发展对印关系上从来不顾及印度的心理感受,不仅不给印度应有的大国尊重,很多情况下还恩威并施,使印度有种挫折感。寻求心理平衡的印度,常常在对美关系中会制造出一些针对美国的“花絮”来。
因此,美国要做全球性超级大国,印度不但要做南亚次大陆上的超级大国,而且要取得与美国同等的地位。印度副总理阿德瓦尼说:“如果说20世纪属于西方,那么21世纪将属于印度。我们的短期目标是成为新加坡那样的发达国家。我们的长远目标是要与美国平起平坐。”新德里尼赫鲁大学南亚问题专家拉贾·莫汉说:“一些印度人敢做超级大国梦,体现了这个国家出现了一种新情绪。45年来,我们第一次从说‘我们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改口说‘我们将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和强国’。这使我们在认识自己是谁和自己能做什么方面发生了根本的改变。”(17)这必然导致与美国的利益冲突,在南亚地区更是有“一山不容二虎”的特点。只要印美关系的互信度达不到冰释猜疑的程度,来自于争霸精神诉求的矛盾必然导致双方关系的复杂化。虽然印美迫于政治、经济和安全等现实利益,会尽量弥合彼此间的分歧,但是,源于心灵深处的政治文化分歧要在短期内消释则要困难得多。
印美两国在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具有共性,但两国关系一直起伏不定,在更多的情况下,常常是相互疏远的。这并非由于印美两国在国家利益和军事安全等根本问题上要奉行相互冲突的政策,而主要是由于相互间缺乏真正的沟通,对各自民众的精神诉求不了解而没有协调好相互间的立场。印苏间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有异,但苏联迎合了印度的大国主义心理并给予适当支持,因此相互关系总的来说发展比较顺利。可见,印美间分歧多于共同点的重要原因就是双方政治文化认同上的分歧,即是否承认印度的大国地位。
当然,印度为了通过“美国效应”加快实现自己大国战略的步伐,在有些方面有讨好美国之举,如在导弹防御系统等问题上对美国的曲意迎合等,引起了其他大国的警觉,也引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满,无形中削弱了印度外交的效果。印度为降低其负面影响,会通过大国平衡外交避免因小失大的事情发生,印度的大国外交会有些摇摆,但不会偏离太大。从印美关系的现状看,未来一段时期内,双方仍需时日以冰释前嫌和弥合政治文化诉求差异造成的伤痕。
注释:
①〔美国〕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②〔美国〕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72页。
③〔美国〕扎勒米·哈利勒扎德等:《美国与亚洲》,中译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第24页。
④孙士海主编:《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1~352页。
⑤〔美国〕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312页。
⑥Surjit Mansingh,Indira's Search for Power:Indira Gandhi's Foreign Policy,1966-1982,Sage Publications,New Delhi,1984,p.70.
⑦孙士海主编:《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第350页。
⑧V.B.Singh,ed.,Indo-Soviet Relations:1947-1977,New Dehli,1978,p.10.
⑨Stephen Philip Cohen,India:Emerging Power,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Washington D.C.,2001,p.312.
⑩Teresita C.Schaffer,"Building a New Partnership with Indi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5,No.2,Spring 2002,pp.31-32.
(11)Dennis Kux,"India' s Fine Balance",Foreign Affairs,Vol.81,No.3,May/June 2002,p.95.
(12)张文木:《印度的大国战略与南亚地缘政治格局》,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第89页。
(13)参见《美国学者谈南亚有关问题》,载《南亚研究季刊》1993年第4期。
(14)马加力:《关注印度——崛起的大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15)S.S.Mehta,Lauching India into the 21st Century ,Minerva Press,New Delhi,1999,p.115.
(16)Teresita C.Schaffer,"Building a New Partnership wtth Indi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5,No.2,Spring 2002,pp.31-32.
(17)王新刚:《“费尔康”欲圆印度制空梦》,载《参考消息》2004年3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