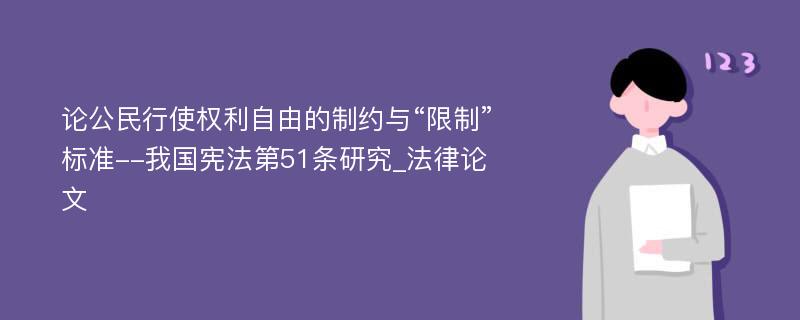
论公民行使权利和自由的限制与“限制”的规范——对我国《宪法》第51条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法论文,公民论文,我国论文,自由论文,行使权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512(2013)07-0067-11
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1982年宪法第一次规定了这一条款,新中国建立后的其他三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与1978年宪法都没有规定这一内容。那么,现行宪法为什么要规定这一条文呢?《宪法》第51条的立法背景是什么?如何认识《宪法》第51条的内涵及其在宪法中的地位与作用等?这些都是《宪法》第51条的基础问题,意义重大,本文为此展开分析。
一、《宪法》第51条的形成与发展
(一)《宪法》第51条的由来
《宪法》第51条的立法背景是对法条进行专门研究的前提条件。《宪法》第51条的由来与苏联宪法的相关规定有一定的关系,该条的出台是对1975年宪法与1978年宪法的反思,也是对十年“文革”的总结与反思。
1.苏联宪法的相关规定
研究《宪法》第51条的由来,需要分析大致上“同一时期”①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宪法的相关规定。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横跨欧亚大陆、起初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一阵营后来扩展到17个国家,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长期对峙,是冷战时期的主要内容。在中苏两国关系方面,“20世纪60、70年代中苏关系的全面激烈对抗,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促使中苏关系解冻的气候已逐步形成。从1979年开始走出对抗到1989年实现关系正常化,经历了10年过渡阶段。中苏关系第一轮谈判于1979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标志着对抗了20多年的两国关系发生转折”。②
1977年10月7日苏联第九届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第七章规定了苏联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由和义务。其中第39条第2款的规定与我国宪法第51条有相似之处,该条的完整内容为:“苏联公民享有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宣布并保证的全部社会经济、政治及个人权利和自由。社会主义制度保证扩大权利和自由,保证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计划的执行不断改善公民的生活条件。公民行使权利和自由不得损害社会和国家利益以及其他公民的权利。”另外,苏联1977年宪法义务条款中的第65条值得注意,该条规定:“苏联公民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合法利益,对反社会行为毫不妥协,全力协助维护社会秩序。”
对于上述规定,我国学者的看法是:“早期的社会主义宪法一般说来没有这样的规定,如苏联一九一八年、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三六年宪法。后来,情况有所变化。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有了这方面的内容,如南斯拉夫宪法的第二百零三条,罗马尼亚宪法的第二十九条。苏联自己的情况也有了变化。例如一九七七年宪法就有了这方面的内容,如该宪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权利和自由的实施同公民履行自己的义务是不可分的。苏联公民必须遵守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尊重社会主义公共生活规则,无愧于苏联公民的崇高称号。’”③对于早期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没有此类规定的原因,我国学者认为,“可能和这样一种情况有联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多次揭露过,资产阶级宪法一方面详细规定有公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另一方面又以‘但书’等形式对公民行使自由和权利作出各种限制,以此揭露资产阶级民主与自由的虚伪性和局限性。……此外,也同缺少实践经验密切相关”。④
比较两国的相关规定,可以发现两部宪法的区别具体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形式上的不同。从形式来看,两国宪法的相关条文在宪法中的位置不同。苏联宪法将该条款放在宪法第七章“苏联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由和义务”的篇首,作为基本权利、自由和义务的第一个条文,我国则规定在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中间位置,在权利篇与义务篇的中间,即在权利篇(含劳动权、受教育权)之后,义务篇之前。这一不同位置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对权利义务认识水平的提升,说明我国1982年宪法更加突出公民权利在宪法中的地位,更加强调公民权利的重要性,而与1977年的苏联宪法几乎“同一时期”的我国1978年宪法,其“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列在宪法第三章,安排在第二章“国家机构”之后。
其次,内容上的不同。这集中体现为不得损害的具体内容不同。在表述上,我国宪法中不得损害的内容为“国家的、社会的”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而苏联宪法不得损害的内容为“社会和国家利益”及“其他公民的权利”。可见,与苏联宪法相比,我国宪法不得损害的内容有少许不同。第一,在形式上包括了集体的利益。当然,这并不是说苏联宪法不保护“集体的利益”,笔者不排除苏联宪法已经将“集体的利益”归入“社会和国家利益”之中。因为集体经济也是苏联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苏联宪法第二章规定了经济制度,其中第10条规定:“苏联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包括:国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第二,我国宪法将“其他公民的权利”限定为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因此,我国宪法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权利”的范围要明显地小于苏联宪法。
2.《宪法》第51条是对十年“文革”的总结与反思
该条的出台是对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的总结与反思。1975年宪法在第一章总纲中确认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1975宪法第13条规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1978年宪法在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规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1978年宪法第4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产物,是与“大民主”相适应的权利观,当然也是错误的理论之一。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两处提到“大鸣大放”,并两次予以彻底的否定。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未经限制的“野性的”权利,需加以规范。如同权力需要规范一样,权利也需要规范,《宪法》第51条正是基于历史的总结之后对公民权利行使的规范。事实表明,不受控制、限制的权利就是“洪水猛兽”。我们平常所说的“言论自由不是洪水猛兽”,那是在权利经过“合理限制”之后,在良好的法制环境中所呈现的理想状态。生活中除了有正确与正常的错误言论外,还有极端的言论、夸大的言论、虚假的言论等各式言论,解决的关键是对言论自由的合理限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对权利的制度设计与有效管理。在这一方面,“文革”的教训是很深刻的,因此,我国有学者结合《宪法》第51条提出:“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并运用这一条,来有效地同滥用公民的自由与权利的行为作斗争。”⑤
因此,合理地规范权利,对权利的合理限制对于法治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而且“规范权利”也是宪政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宪法》第51条的立法原意与变迁
制定1982年宪法时,我国的经济体制属于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的生产安排、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各方面,都是由政府事先进行计划,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政府决定。因此,计划经济也被称为“指令性经济”,政府被称为企业的“婆婆”。个人也是“单位人”,个人的住房、医疗等由单位解决。这一状况也明显地反映到立法精神中。
《宪法》第51条的立法精神历经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不同的阶段,1982年宪法第四次修订反映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当然,立法精神的变迁并不是与时代发展绝对同步的,其变迁要略微滞后于时代的发展。
第一个阶段是1982年至1999年。该阶段强调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强调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这一时期,主流的宪法理论不认为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之间存在冲突,而认为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是统一的。这具体表现在宪法学教材对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主要特点的理论总结上。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主要特点是,公民权利与义务具有广泛性、真实性、平等性、一致性。因此,学者一般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决定着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高度统一。因为在这里,公民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之间,反映着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不可分离……国家为人民,人民爱国家;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与人民是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⑥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时代,处理国家、集体、个人的行为准则是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这一思想的形成与计划经济有关,并且在计划经济时代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作用。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差别不大,利益冲突没有呈现出显性的状态。
对于这一情况,参与了1954年宪法的起草工作的许崇德教授完整记录我国宪法产生、变迁过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中没有记录该条的起草过程。有学者当面请教许先生,他的回答是该条几乎没有发生过讨论。⑦
第二个阶段强调合法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国家利益之间的“协调”。在该阶段,《宪法》第51条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标志之一就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再是纯粹的公有制经济。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宪法原来的第15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宪法第6条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内容作为第3款,即“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时将宪法第11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对多种所有制经济与多种分配方式的确立,以及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不仅意味着国家承认与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而且意味着国家承认与保护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因此,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个人利益也不再简单地服从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冲突,就需要进行新的思考。随着社会的转型、法治的发展、人权观念的深入,个人、集体、国家之间的关系,个人利益与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集中表现为个人利益在法律地位上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合法的个人利益成为法律承认并予以保护的重要利益。这一个人利益在地位上的变化,使得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之间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2)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由单向的服从向“兼顾”转变。在指导思想上由过去的重点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发展到了兼顾个人利益,现行宪法确立了这一原则。(3)表现形式上的相应变化。在社会生活中,过去强调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奖励形式在很多场合已经转变成了以“物质奖励”为主的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个人利益在法律地位上有了变化,但这不等于说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在实质上具有平等性。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情况下,在形式上个人利益可以“对抗”国家利益。例如个人可以对政府提起行政诉讼等,并且在诉讼中双方的法律地位平等,这只是反映了形式上的平等或者说诉讼中的平等。国家利益依然具有适度的优先性,但是这一优先性同样有一个合理的“度”,不能绝对化。
上述变化直接导致合法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之间可能会存在冲突。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保障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适度的优先性,从而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合法的个人利益之间也会产生冲突,因此需要建立对基本权利限制的相关制度以协调各方利益。公共利益在我国逐渐成为本世纪以来的一个研究热点,正是为了明确利益各方之间的权利界限。如何认识与运用《宪法》第51条就需要新的理论与制度,包括对《宪法》第51条进行适时的解释等。
二、《宪法》第51条的基本内涵与规范结构
对《宪法》第51条涵义的正确把握是分析《宪法》第51条的前提,《宪法》第51条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其时代内涵如何把握,如何有效地概括与提炼《宪法》第51条的时代精神,这对于研究与发展《宪法》第51条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学者对《宪法》第51条涵义的主要观点与评价
纵观我国学者对《宪法》第51条理解,主要有如下五种观点,这五种观点反映了中国学界对于《宪法》第51条认识的深化过程。
其一,权利论。这种观点将该条与《宪法》的第33条至第50条视为同样性质的权利条款。有学者认为:“我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33条至51条规定了若干我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2004年颁布的宪法修正案第22条也通常被认为确立了我国宪法中的‘财产权’制度。”⑧不少论著将我国宪法的第33条至第51条全部视为权利条款。
其二,义务论。有些学者认为该条事实上增加了公民的义务。有著作将该条的内容作为单独的一个义务列入公民的基本义务中,将之命名为“尊重公有和他人所有利益的义务”。⑨该著作的作者在下文中继续阐述道:“宪法第五十一条,对公民尊重公有利益和他人所有利益的义务作出了规定。”俞德鹏教授在引用该条后直接认为:“这种限制不是说国家可以随时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范围或内容,而是表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必须与多数人的利益相平衡。也就是说,行使权利就负有义务。这种义务是与权利的享有相一致的,根本上就是遵守国家法律,这是公民最基本的义务。”⑩
其三,权利与义务的一致论。有学者提出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是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1954年宪法就有这一原则,1982年宪法更加突出地体现这一原则,并且比1954年宪法有了新的发展。这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中第三个方面就是“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别人的自由和权利。这是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的又一体现”。(11)随后该学者列举了宪法第51条的规定,并作了分析:“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没有根本对立的矛盾和利益。因此,广大人民经常能维护国家的利益,新宪法的这一规定反映了我国的本质和实际情况……”(12)
其四,禁止权利滥用论。有学者对该条由来所发表的观点是:“我国宪法在充分保障公民享有广泛的自由和权利的同时,又要防止少数公民滥用权利和自由,因此在宪法第二章中新增加了第51条。这是我国前3部宪法所没有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现行宪法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该条“是防止权利滥用的一条规范,也是公民正确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指导原则”。(13)同时,他还提出:“在我国宪法中,防止权利滥用的限制性条款,并不只有第51条。如宪法第36条,宪法在保障公民享用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还规定了三个‘不得’。不过,第51条是防止公民滥用权利的总规定,所以称为指导原则。”(14)这里,他还将宪法第51条作为公民正确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指导原则。也有学者将宪法第51条的内涵归结为“不得滥用原则”。(15)
其五,限制论。有学者认为:“本条是对公民行使基本权利总的限制性规定。这是1982年修宪新增加的内容。八二宪法被总结为有公民权利与义务一致性的特点,这一条就是集中的体现。这一条也是以下几条公民义务的总的原则。宪法基本权利的行使都必须与这一条联系起来。”(16)另有学者认为:“这里对限制基本权利作了总的要求,即只能基于维护公共利益和其他人的基本权利的目的而限制基本权利。”(17)
笔者对上述观点作出如下几点评价。
其一,权利论、义务论、权利与义务一致论三种观点值得商榷。其实,宪法第51条既不是权利条款,也不是义务条款,当然也不是权利与义务一致论中的相关条款。随着对宪法认识的深入,学者们对《宪法》第51条的认识也在转变。第一,尽管有学者将该条归入权利篇,但是由胡锦光教授主编的同一本教材在具体解读《宪法》第51条时,认为:“这一规定与当代宪法理论关于基本权利的限制理由表面看来有一致之处。但是此条规定的内涵还需要进一步的界定,否则容易造成任意以公共利益为借口限制基本权利的问题。中国宪法对于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界定,还需要深入研究基本权利限制的形式、限制的界限、限制的方法和宪法的表述等方面。”(18)该教材提出:“《中华民国宪法》第23条对于基本权利的限制作了较好的规定:‘以上各条列举之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这种规范对于宪法处理基本权利的限制问题可以是一个示范。”第二,将该条解读为“义务”的观点在我国还是极为少见的。其中,上述俞德鹏教授的论述事实上包含了三种观点。虽然他认为《宪法》第51条是一种义务,但是该观点是将限制等于义务,同时也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事实上义务论反映了特定时代的历史局限性,在国内不占主流。第三,主张权利与义务一致论者,主要是部分老一辈宪法学者的观点。目前,上述权利论、义务论、权利与义务一致论等观点尽管还时常出现,但是这三种观点在学界并不占主流。
其二,禁止权利滥用论不能反映《宪法》第51条的全貌,理由是:第一,禁止权利滥用只是限制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不是限制理论的全部内容。第二,主张禁止权利滥用论的部分学者事实上在有些场合也主张权利限制论。如许崇德先生在其他的宪法学教材中论及《宪法》第51条时,明确地认为:“这一条是确定公民基本权利合理界限的依据。在我国公共利益和基本权利的价值是并重的,离开了基本权利主体的利益,公共利益就成为无源之水,而如果公共利益价值得不到维护,那么基本权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19)
其三,上述“五种观点”事实上已经出现了趋同的现象。这些观点反映了对于《宪法》第51条的认识过程,而这些观点是不断发展的,它们已经出现了趋同的现象,即基本上已经趋同于“限制论”。
(二)“为保障而限制”是《宪法》第51条的基本内涵
1.“为保障而限制”的涵义
如上所言,尽管对《宪法》第51条曾经存在着诸多观点,但这些基本上已经趋同于“限制论”。目前国内主流的观点是“限制论”,这不仅表现在近年来出版的各类教材中,更反映在近年来发表的相关论文中。尽管具体表述存在差别,通行的说法为该条是对公民行使基本权利“总的限制”或者“合理限制”。“总的限制”与“合理限制”这两种观点都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为推进权利限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鉴于我国的社会现实,结合法治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笔者主张以“为保障而限制”这一关键词来提炼、概括该条的基本内涵,其完整表述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而限制基本权利的行使。其内涵包含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限制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该条的首要任务是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通过限制保障每个公民最大限度地享有权利,防止公民在行使权利的时候对其他公民合法权利的毁损,包括公民对此权利的行使毁损了他人彼权利的实现,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正如霍尔姆斯法官在1919年“申克诉合众国”(Schenck v.U.S.)一案的判决意见中所说:“对表达自由做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容忍一个人在戏院中妄呼起火,引起恐慌。”(20)美国最高法院正是在该案中首次确定了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的“明显且即刻的危险”标准。
第二,在权利限制中要建立权利保障的基本理念与相关制度。尽管上文提及部分限制条款中“内含”或者“内嵌”着保护的内容,但是还必须强调权利保障的价值。限制之中强调保障,其意义在于以下方面:首先,《宪法》第51条立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充分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因此限制应当适度,并且限制始终要贯彻对于基本权利的保护。限制又可分为合理的限制与不合理的限制。某些合理的限制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保护,是“内含式”或者“内嵌式”的保护。如西方古代法律制度中的“禁止卖身为奴”(21),中国战国时代秦献公“废除人殉”的规定。再如《刑法》第243条第3款关于诬告陷害罪规定了“不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的,不适用前两款的规定”,也体现了“限制中的保护”这一精神。必须注意的是,并不是全部的限制性条款都具有这一功能。不合理的限制常常表现为违背权利限制的正当目的,使得权利限制超出了一定的范围,因此又称为限制过当。关于限制范围的确定问题,需要用到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与个案衡量等方法。其次,通过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能够生成基本权利限制的一系列制度。限制中的保护需要通过专门的制度予以落实,例如对限制的限制制度、“核心权利”制度(限制不能影响公民的“核心权利”或“实质权利”)、权利救济制度等;总之,要遵循“最小限制”原则。最后,除了法律特别规定外,不能通过限制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
第三,把握《宪法》第51条必须正确处理好限制与保障的关系。现实法治的发展要求我们在权利限制中强调权利保障。正如张友渔在《对“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的意见》中所说,限制与保障“两者须分主次,保障是主要的,限制是次要的”;“限制也是为了保障,限制与保障是辩证的统一”。(22)权利限制与权利保障的统一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权利限制是《宪法》第51条的首要任务,但是并不是唯一任务,该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权利的充分实现。因此,在权利限制中要做到限制与保障的两者的平衡。其二,在基本理念上,要树立限制中有保障,保障中有限制,反对机械地割裂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权利限制理论的构建中真正地做到限制与保障的统一。其三,为了贯彻“为保障而限制”这一精神,必须建立相关的制度予以落实。例如,建立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等制度以完善对限制的宪法控制,落实权利限制的救济措施等。
2.“为保障而限制”提出的必要性
在限制之前加上“为保障”不只是文字上的安排,而是出于宪法理论的发展与我国现实法制发展的状况的需要,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以“为保障而限制”来概括《宪法》第51条的内涵是吸收西方法治文明成果的要求。考察发达国家的宪法,其关于权利限制的条文值得我国借鉴,例如《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9条对于权利限制的规定是非常详细的,(23)其包括了如下重要内容。首先,法律保留原则。德国宪法第19条第1款属于法律保留的内容,该款承认了基本权利可以依法限制,但是对权利限制中的“法律”的要求为:一是“须具有普遍适用效力,不得只适用个别情况”;二是“该法律须指明引用有关基本权利的具体条款”。因此,德国宪法严格地贯彻了法律保留原则的内容。其次,限制的限制。权利限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权利,因此,限制并不是无限度的限制,基本权利的限制存在“底线”。在德国宪法中,这一“底线”就是第19条第2款规定的“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侵害基本权利的实质内容”。再次,权利限制的法律救济。所谓“无救济即无权利”,德国宪法第19条第4款规定的就是救济。最后,第19条第3款还规定了此条的适用范围。
在最新的人权理论方面,西方已经发展出了“最低限度的人权”理论,又称为“低线人权”理论。这一理论是由英国达勒姆大学教授米尔恩在其著作《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中提出的。“作者从道德、政治和法律哲学的角度对人权观念进行了全面深刻地探讨。他认为,人权是一种道德权利,而不是政治权利,作为最低限度的人权应包括生命权、公平对待的公正权、获得帮助权、不受专横干涉的自由权、诚实对待权、礼貌权、儿童受照顾权等7项基本权利。”(24)米尔恩认为有九项道德原则为社会生活本身所必需,包括行善原则、尊重人的生命原则、公正原则、伙伴关系原则、社会责任原则、不受专横干涉原则、诚实行为原则、礼貌原则、儿童福利原则。(25)“低线人权”的理论价值不仅仅是如该书简介所说的为“我们了解人权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而且,就权利限制而言,“低线人权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检验现行法律制度正当与否的评价标准”。(26)结合低线人权这一概念,我国学者发展出了“底线权利”(27)以及“人权底线”(28)的概念,这些概念对于丰富与发展我国的权利限制理论与制度具有一定的积极的意义。
第二,以“为保障而限制”来概括《宪法》第51条的内涵是我国法治发展的内在需要。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这就是我国现行宪法第33条第3款的内容。这一条被学者认为是权利的“概括条款”,其效力当然及于整个宪法,包括《宪法》第51条。因此,“人权入宪”对于《宪法》第51条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作为宪法学人更应理所当然地将这一精神补充到《宪法》第51条中去。权利限制理论除了包括限制的目的、限制的理由、限制的方式、限制的范围等问题,还有限制的“度”的要求,即限制的“限度”,在宪法理论上称之为“限制的限制”。限制表述的是一种手段与方法,限度表示的是一定的范围与边界。两者的关系为:限度表示的是通过限制所能达到的最大范围。为此,在权利限制理论中,产生了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等制度,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权利”。
第三,以“为保障而限制”来概括《宪法》宪法第51条的内涵是法律科学性的要求。首先,在有些情况下,权利限制本身就内含着权利保护的内容。这一形式上的限制常常也是一个保护条款。诸如“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等规则也体现为一种保护。故有学者从这一视角上将权利限制称之为法律的“父爱主义”或者“家长主义”,认为这是一种“强制的爱”。“法律父爱主义对个人自由或权利的限制,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由权利。它不是对人性尊严的侵犯,相反,限制是为了更好地肯定和保护人性尊严。当然,限制也要有限度,‘父爱’也要适度,‘超父爱主义’会沦为对个人的压制和压迫。在中国的场景下,法律父爱主义尤其值得和需要‘认真对待’”。(29)其次,宪法上“不受侵犯”的权利条款需要得到客观、理性的对待。我国宪法上“不受侵犯”的条款很多,如《宪法》第13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些条款的形成受制于当时的历史、环境等因素。事实上,不受限制的条款尽管在形式上是“只见保护,不见限制”,反而增加了权利实现的难度。与其陶醉在浪漫的“权利真空”里,还不如在私权利与公权力以及私权利相互之间明确各自的范围、界限,以期能够真正地实现权利。最后,就为什么要求限制,即权利限制的目的问题,可以提出权利行使中的“安全阀”或者“制动闸”理论与“马鞍理论”。权利限制就是对权利的行使进行规范,这一规范是权利行使中的“安全阀”或者“制动闸”,其目的在于过滤权利行使中的“不合理”、“不理性”等因素。同时,权利限制中存在着“马鞍现象”,就如同给马套上马鞍一样。给马套上马鞍是为了让马儿跑得更好,权利也需要“套上马鞍”,使得野性的、无拘无束的权利成为文明社会可以控制的法律上的权利,即“可控权利”。当然,一旦谈及给权利“套上马鞍”特别容易使人“谈虎色变”。但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给权利“套上马鞍”,而是如何给权利“套上马鞍”,包括由谁决定、决定的程序、决定的依据等等。因此,这就特别需要对权利限制进行反限制,以保证权利的真正享有与有效行使。
三、《宪法》第51条的规范结构以及在我国宪法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宪法》第51条的规范结构
“为保障而限制”反映了《宪法》第51条的基本内涵,“为保障而限制”涵义也应有规范的界定。
首先,限制的目的解决的是为什么要限制公民基本权利。这是理解《宪法》第51条的前提。在此,笔者重申权利限制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即为了保障权利的充分实现而限制权利。在这一前提之下,才会存在限制的限制,即限制的限度等重要问题。有学者将限制基本权利的目的归纳为: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国家安全;紧急状态;他人权利和自由。(30)本文将这些内容归类于限制的理由。
其次,从大的方面来说,《宪法》第51条限制的理由包括两大块内容:一是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二是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限制的理由不同于限制的目的,目的与理由的区别表现如下:第一,理由是具体的,一般是在条文中予以明示的;目的是抽象的,是需要解释与提炼的。例如该条中“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作为限制的理由,是条文本身所明示的,限制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权利,这是该条所“暗含的”,是根据宪法的精神进行的“解释”与提炼。第二,目的往往表现为人们通过行为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理由是当前行为的动因,是之所以进行该行为的依据、出发点。简言之,限制的目的就是人们通过限制行为达到的结果,限制的理由是当前行动的行为依据。第三,在文本的表述中,目的与理由有时存在着相同的表达,如《宪法》第10条第3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与《宪法》第13条第3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严格地说,这里的公共利益是限制的理由,目的是为社会更好的发展,从而使得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能够得到更好的实现。尽管文本中使用的语言都是目的性很强的“为了”。
需要强调的是,在某些情况下,目的与理由的界限较为模糊,如上述《宪法》第10条第3款和《宪法》第13条第3款。故此,在其他场合不必刻意区分,但是在权利限制领域,包括在《宪法》第51条中,这一区分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这就如同在法理学领域对“法”与“法律”的区分一样。
再次,限制的主体解决的是谁有权限制基本权利的问题。这是限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基本权利是由宪法予以确认与保障的,基本权利的限制往往要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予以保障,因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权利限制的基本主体。
再其次,限制的限度强调的是对基本权利限制的限制。宪法确认基本权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基本权利,因此,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不是取消基本权利本身。尽管在法律上存在基本权利的“剥夺”一说,如我国《刑法》中的“剥夺”政治权利制度,但是,基本权利的“剥夺”只能由法律予以专门性的规定,而且事实上仅仅限于极个别的例外情况。
最后,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否适当,是否存在着违背宪法精神的限制,这就是权利限制的合宪性问题。我国宪法上有宪法监督等制度,可以通过这样的制度来保障权利限制的合宪性。
(二)《宪法》第51条在我国宪法中的地位
《宪法》第51条在我国宪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其一,就条文在宪法文本中所处的位置而言,该条主要是权利条款与义务条款之间的“过渡性条款”。《宪法》第33条至第50条属于权利条款,其中还有国家义务的规定,之后第52条至第56条五个条款属于义务条款。其二,就具体内容而言,该条是关于权利限制的“兜底性条款”,即所谓“总的原则性限制”。其三,就权利种类而言,该条是唯一的一条关于权利行使的具体规定,需要其他法律、法规予以贯彻落实。
(三)《宪法》第51条的作用
对《宪法》第51条在宪法中地位的把握,对深入理解该条的意义重大。该条是在寻求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陈云生教授认为这一规定“明确地告诫了公民要准确地处理个人权利与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以及他人的合法权利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求公民准确地处理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31)该条是在寻求私权利与私权利之间的平衡。笔者注意到,在知识产权领域,已经有学者提出了利益平衡论这一学说。该条是在寻求整体权利,而不是个体利益。《宪法》第51条追求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处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国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当然,理想目标还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身关系的和谐。可见,环境权同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权利。
注释:
①这里的“同一时期”是相对的概念,苏联宪法1977通过,我国“同一时期”的宪法就有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两部。本文以我国1982年宪法与苏联1977宪法进行比较,兼及我国1978年宪法。
②马叙生:《结盟对抗均不可取——忆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1年第2期。
③④⑤⑥李步云:《新宪法简论》,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页,第158-159页,第158-159页,第137页。
⑦参见刘连泰:《我国宪法文本中作为人权限制理由的四个利益范畴之关系》,《法律科学》2006年第4期。
⑧胡锦光主编:《宪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7页。该段文字出现在该页第一段的开头部分。在该页的第二段文字中(共2段),作者再次重复了这一观点。
⑨李伯钧:《中国宪法新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⑩俞德鹏:《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101页。
(11)(12)肖蔚云:《论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页、第246页,第246页。
(13)(14)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5-336页,第336页。
(15)杨海坤主编:《宪法基本权利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3页。
(16)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页。
(17)周叶中、韩大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页。
(18)胡锦光主编:《宪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页。
(19)许崇德:《宪法学》,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页。
(20)Geoffery R.Stone and others,Constitutional Law,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86,p.944.
(21)Anthony T.Kronman,Paternalism and the Law of Contracts.[J].92 Yale L.J.April,1983.转引自孙笑侠、郭春镇:《美国的法律家长主义理论与实践》,《法律科学》2005年第6期。
(22)参见郭道晖:《法的时代挑战》,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351页。
(23)《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9条(本权利的限制,诉讼权的保证)规定:“(1)依据本基本法规定,某项基本权利可通过法律或依据法律予以限制的,该法律须具有普遍适用效力,不得只适用个别情况。此外,该法律须指明引用有关基本权利的具体条款。(2)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侵害基本权利的实质内容。(3)基本权利依其性质也可适用法人的,即适用于国内法人机构。(4)无论何人,其权利受到公共权力侵害的,均可提起诉讼。如无其他主管法院的,可向普通法院提起诉讼。第10条第2款第2句的规定不受影响。”
(24)(25)[美]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简介部分,第10页。
(26)林喆:《公民基本权利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6页。
(27)秦强:《论底线人权》,《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5期。
(28)张勇:《反恐“裸检”触碰人权底线》,《法制日报》2010年1月19日。
(29)郭春镇:《法律父爱主义及其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内容简介部分。
(30)参见郑贤君:《基本权利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31)陈云生:《现代宪法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页。
标签:法律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宪法论文; 宪法修改论文; 宪法监督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