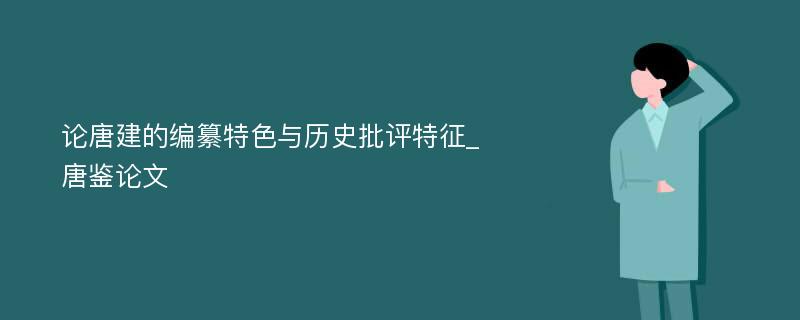
论《唐鉴》的编纂特点及其历史评论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色论文,历史论文,唐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4)02-0073-06
《唐鉴》是北宋时期史家范祖禹参修《通鉴》时“于紬次之余”写成的一部史著[1],其史实部分基本上不出《通鉴》。但因其著述宗旨是欲“稽其成败之迹,折以义理”[1],而《通鉴》特有的编纂模式又无法满足范祖禹阐发自己对唐代历史之看法的需要,因此,他在历史编纂上锐意创新,采用历史评论体裁,借用唐代的历史事实作为引发议论的依据,因史而发论,对君主建德、修政以及政权建设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看法,为我国古代的行政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一、编纂特点
体裁、体例虽然是史书外在的编纂形式,但它与史家著史的目的、史识却密切相关,反映的是史书内容特有的规定性,因此也是我们考察史家的历史与史学思想及其时代精神的重要途径。
1.合编年与史书论赞为一体
从历史编纂的角度来考察,《唐鉴》这种历史评论体裁,实际上是对编年体和史书中的论赞形式进行综合改造和创新的结果。其体例是先记史,继而以“臣祖禹曰”的形式阐明史家之意。记史部分,吸收了编年体史书按年书事的特点,以唐代14世20位君主的在位次序作为记史的时间顺序,在此次序之下,又以事件发生的自然顺序相次,跳跃式地抓取那些影响唐代历史发展,并对当时具有某种启示作用的关键事件进行简略叙述。正如他本人所说:“臣谨采唐得失之迹,善恶之效……唐之事虽不能遍举,而大略可睹矣。”[2]体现出其对编年体的吸收与合理的改造。如对唐太宗下诏讨论如何处置突厥降唐者问题,《通鉴》于贞观四年夏四月戊午条下,按照事件的先后顺序从突厥可汗到长安请降,太宗下诏讨论处置降虏,朝士及颜师古、李百药、窦静、温彦博和魏徵五位名臣的对策,一直记到太宗采纳温彦博、魏徵之议,将突利所统地区分为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颉利之地分为六州,并设置定襄、云中二都督府以统领其众等,共用了大约八百余字来叙述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唐鉴》则对这一事件的详情细节统统省去,只用了237字,就提纲挈领地将这一事件的简要过程提炼了出来。同样,对于玄武门之变的记述,《通鉴》用了数万字,而《唐鉴》却将它浓缩为区区25个字:“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立世民为皇太子”[2](《高祖下》卷一)。从这二例的叙事方法上看,编年体的《通鉴》显然是以保存历史、反映历史发展趋势为目的,故主详,而且将记事系于确切的时间之下,十分强调时间、地点对于历史事件产生的特定意义,体现了编年体史书的编纂特色;而《唐鉴》则不以保存史料、梳理历史发展脉络和反映历史发展趋势为著述旨趣,而是把记史作为产生评论的背景资料,并进而阐述这些历史现象发生的抽象原则。因此,其史料虽与《通鉴》同出于一源,但它多是对《通鉴》内容的节录或改写,旨在摄取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片段作为发论的依据,因而显示出略而得其要的特点,仅在记史的格式上保留了编年体的体例形态。
史书中的史论形式是指史家对自己或他人记载的历史所发表的评论,它始见于编年体《左传》的“君子曰”。汉代以后史家对史论的重视越来越突出,纪传体《史记》、《汉书》等都相继运用这种形式,以“太史公曰”、“赞曰”等形式,于记史之后,阐发自己的历史观念、政治见解。还有部分史论或是以序文的形式出现在书志、表及类传之中,或是夹杂在历史叙事之中,与史事融为一体。此后出现的大量历史著作,也都比较重视史论的作用,并把它放在历史撰述中的重要位置,使其成为史家表述历史见识的主要形式之一,这些都反映出史家历史评论意识之自觉程度的不断加强。《唐鉴》与以往的史论形式相比,它不再仅仅是作为史书中的非主体部分而存在,而是直接以专门的历史评论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从形式上看,前者是附于记事之史或系年之书,通常是于卷内发论,而且位置不定。从文字的份量上说,它与历史记载的文字之比相差悬殊,而且也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史学品格。《唐鉴》则反其道而行之,它不仅把“论”从附属于其他史书体裁的地位提升到历史著作的主体地位,而且其编纂体例是先史后论,“摄取大纲,系以论断”[3],基本上保持了一事一议[4],而且其评论性的文字笔锋犀利,文字简捷,呈现出以史说理的趋向。另外,从“史”与“论”的文字数量之比上看,二者的数量也大致相当[5],凸现出其议论与记事并重的编纂特色,反映出史家的著述目的和撰述思想与史书的体裁、体例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史书的外在形式为内容规定性的必然反映这个辩证的道理。同时,也体现出我国古代史家在历史编纂领域善于吸收和综合创新的能力,为后世的历史编纂指出一条体裁创新的新思路。
2.仿《春秋》书法记事
“正统论”是北宋时期史学领域讨论十分激烈的一个问题,范祖禹虽然没有撰写专文参与这场大讨论,但他实际上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即通过历史编纂的纪年和书法表明了自己对于正统问题的看法。
一般说来,历史上的“正统论”就统系来说有二层含义:一是指历史纵向发展过程中的各不同政权间的统系继承问题,体现为史家对其政权在纵向的政治序列中合法性的认同;二是指同一个政权中不同的统治者间的统系继承问题,反映了史家对不同君主在其政权内部政治序列中合法性的认同。《唐鉴》涉及的是后一层含义。按照唐朝历史的客观情况来看,武则天于光宅元年(684年)开始听政,并于天授元年(690年)建立“周”政权,正式行使帝王的权力。但范祖禹是尊奉儒家,特别是《春秋》的价值判断标准来著史的。因此,他把武则天当政时期的历史系于中宗之下,以中宗的年号编年记事,目的是将武则天排斥出“正统”之外。
《唐鉴》作为以记史与议论并重为基本特征的史书,它的基本体例结构是先叙史后议论,借史明义,以阐发历史经验和史家的政治见解,并不以追求历史记载的连续性为著述旨归。但范祖禹为表达其对唐王朝统绪的看法,抨击武则天专权,却不惜自破体例,对武则天听政时期的历史,完全按照编年体的传统,逐年连续记载了她在21年当中(嗣盛元年中宗被幽禁~神龙元年正月迎睿宗于东宫)对中宗、睿宗任权废立的情况。并仿照《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公在乾侯”的书法,从嗣圣三年(687年)起,于每年记事之前先书“春正月,帝在房州”(即使是无事可记,如八年、十年,也同样只书“帝在房州”一语;四年,因载有杨初成招集人马迎接睿宗一事,故不书此语)[2](《中宗》卷四)。从十六年起,睿宗被迁往东宫,范祖禹于记事之前则先作“春正月,帝在东宫”[2](《中宗》卷四),然后编年书事,表明武则天虽在君位,但其并非在合法的政治序列之中,而是僭伪之君,真正的君主实屈居于东宫。十五年,武则天又以睿宗为相王,迁其出房州,范祖禹又仿照《春秋》“公至自乾侯”之例,书曰“帝自至房州”[2](《中宗》卷四)。“自至”一语,源自《春秋》鲁昭公二十六年春的记事。当时鲁国季孙氏已将昭公驱逐出境,齐景公攻克了鲁国的郓城(位于齐鲁间边境),使昭公暂居于此。按照经书之例,“自至”应为告庙之辞,昭公没有回到国都本不应用此语。但《春秋》却破例用此法记事,其意在于只承认昭公的鲁国国君地位,而以季孙氏为僭伪。范祖禹仿效此书法记事,其目的也不过要以此来表明这层意思。
在这部分的“论”中,范祖禹也打破惯例,专意于说明此书法的来历及其用意:“昔季氏出其君,鲁无君者八年,《春秋》每岁必书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书曰‘公在乾侯’,不与季氏之专国也。”[2](《中宗》卷四)并对《唐书》为武则天立本纪的做法进行了分析,指出:“唐史亦列武后于‘本纪’。其于记事之体则实矣,《春秋》之法未用也。”[2](《中宗》卷四)如果从史学求实的角度看问题,为则天立本纪本无可厚非,这是史学在事实层面上求真的体现。但从道德层面上看,“中宗之有天下,受之于高宗也。武后以无罪而废其子,是绝先君之世也”[2](《中宗》卷四)。故而范祖禹要仿“《春秋》吴楚之君不称王,所以存周室也”的做法[2](《中宗》卷四),黜武氏之号,将其系于嗣圣之年,以此来抨击武则天的越礼行为,并把它作为“母后祸乱之戒”[2](《中宗卷四》)。究其实质,范祖禹采用《春秋》书法的目的是要实现史学的社会教育功能,这是史家及其史学与社会结合的具体体现。但客观求实是史学的第一要义,范祖禹无疑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为此,他在对“太宗观史”一事的议论中,借司马迁之言:“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盖止于执简记事,直书其实而已,非如《春秋》有褒贬赏罚之文也。”[2](《太宗下》卷三,文渊阁本无“如”字)“后之为史者务褒贬而忘事实,失其职矣。”[2](《太宗下》卷三)从表面上看,其言与行似乎是一个悖论,但如果我们把《唐鉴》一书的编纂体例整合起来加以考察,就不难看出他既要完成史学与社会、政治结合的任务,同时又要体现史学求真这个本质属性的深意。他于卷首以《唐历代传世之图》和《历代纪元之图》提示唐朝诸帝世系所出及其继位顺序,是在事实层面上对其以《春秋》书法处理则天后纪年问题的修正。由此看来,范祖禹并不是质疑《春秋》书法本身,他反对的仅仅是因《春秋》书法而损害历史之真的做法,他所追求的是史学的褒贬劝世功能同历史之真的并存不悖,体现出史家唯真理是从的理性精神和客观求实的治史态度。
二、历史评论的特色
《唐鉴》作为较早的一部历史评论专著,其撰述旨趣是“稽其成败之迹,折以义理”[1]。也就是要通过唐朝的历史,探讨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它与记史之书相比,其著述的最主要任务并不在于记载历史,而是要阐释历史,直接把史学的本质定位在究明义理上,主张要在论史中体现和贯穿义理,体现了宋代史家注重发挥义理的著述精神。而他对历史的阐释主要是通过历史批评和理论的方式,以君德、臣宜和君臣关系等为基本着眼点,总结唐政权的盛衰规律,因此,宋高宗称“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6]。
1.以道德为本位展开历史批评
礼,是儒家政治伦理中的一项基本内容,也是古代史家衡量君臣道德标准的一个重要尺度,其基本内涵是指等级名分。具体地讲,对臣而言就是要遵守等级制度,忠于君主;对君而言,则是要最大限度地实现道德自律,并把这种自律外化为正确的统治策略。这也正是范祖禹在《唐鉴》中对唐代兴亡原因进行探索和总结时所尊奉的一条重要原则。因此,《唐鉴》通篇主要是围绕君德和臣宜两个方面展开批评,以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标准来阐释如何做明君、贤臣,臧否他们的所作所为,展现出其历史评价的道德论特色。
总结帝王为君之道是《唐鉴》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强调的君道主要有二层含义:一是指君主自身的道德修养,即要求君主重视以礼法为行为操守之准则;二是指施行仁政。范祖禹把君道放在首位,是源于他对帝王表率作用的重视,他说:“然三纲不立,无父子君臣之义。见利而动,不顾其亲。是以上无教化,下无廉耻。古之王者,必正身齐家以率天下。”[2](《肃宗》卷六)“人君唯恭俭寡欲,清虚以居上,则邪谄无自而入矣。”[2](《玄宗下》卷五)这显然是对孟子“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思想的继承和发扬[2](《代宗》卷六转引),而他对君主无“礼”行为所作的批评,则同样可以看作是对君道的重视。
太宗是范祖禹最为关注和欣赏的唐代少数帝王之一,但他还是用道德论的标准,在开篇对其劝父联合突厥起兵的行为大加挞伐,认为太宗“胁父臣虏以得天下”的行为是“陷父于罪”[2](《高祖》卷一),既违背了臣节,又为家庭伦理所不容。因此,范祖禹对他的评价是“太宗有济世之志、拨乱之才,而不知义也”[2](《高祖》卷二)。在肯定其才能的同时,又因其不知臣、子之宜而责难其过失。同样,按照礼法的要求,范祖禹把太宗弑兄自代的行径也视作僭礼行为,认为“立子以长,不以功;以德,不以有众,古之道也”[2](《高祖》卷一)。“建成虽无功,太子也;太宗虽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贰,父之统也,而杀之是无君父也。”[2](《高祖》卷一)如果说范祖禹在其前还对太宗的才能有所肯定的话,那么他对太宗为帝的看法,则完全是从道德原则出发的,为此,他对太宗自比弑建成、元吉为周公诛管、蔡的言论提出了辩难:“管蔡启商以叛周,周公为相也,则诛之。……管、蔡流言于国,将危周公,以间王室,得罪于天下,故诛之。非周公诛之,天下之所当诛也,周公岂得而私之哉!”[2](《高祖》卷一)
要之,他是以“臣宜”的立场,对这场看似相同而实际相异的两个问题做出了区分,其结论就是周公所为是以臣职身份,在“处其变”的情况下替君行使诛乱大权,而非出于私欲。这里所说的“变”,就是管、蔡危害到了君权,而建成、元吉则不同。因此,他的结论是太宗“悖天理,灭人伦,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2](《高祖》卷一),体现出明显的以道德为本位的理学意味。
此外,范祖禹对肃宗自立为帝的行为也提出了批评。肃宗曾以皇太子的身份征讨安禄山,后于灵武自立为帝,他虽然在玄宗回咸阳之时,备法驾欲归位于父,但范祖禹还是把他的行为归结为“临危则取大利,居安则谨小节”[2](《唐鉴·高祖》卷一),“是以不孝令也”[2](《唐鉴·肃宗》卷六),认为他有悖于道德原则。而他在咸阳的举动不过是“屑屑焉为末礼,以眩耀于众”罢了[2](《唐鉴·肃宗》卷六),不可为后世法。这些认识都无不体现出范祖禹以道德为本位评价君主的方法论原则。
从道德论出发,范祖禹对臣宜的看法则反映在他对臣节问题的认识上。尽管太宗为一代明君,王珪、魏徵也在历史上极有作为,但范祖禹并不因此而放弃对他们的谴 责,而是以“责以备”的原则,认为他们“食君之禄,不死其难,朝以为仇,暮以为 君 ,于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2](《唐鉴·肃宗》卷六)。其中所寓的道理就是 “ 臣之事君如妇之从夫”这套家国同构的礼法标准[2](《高祖》卷一)。而李勣身 为 大臣,不仅不能规避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而且还劝成之,被认为是没有完成太宗托孤 的 任务,以其为失节之佞臣而遭到范祖禹的抨击,认为“唐室中绝,皆勣之由也,其 祸 岂不博哉!”[2](《高宗》卷三)同样,德宗时期朱泚为乱,僭号大秦皇帝,礼部侍 郎樊系为其撰写册文后服药身亡,范祖禹借用司马迁“知死必勇”这句话,对其行为作 了诚恳而合乎情理的评论,即“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2](《唐鉴·德宗中》卷 七) 。但合情的未必合理,在他看来忠与逆的区别只在于“作与不作而已”[2](《唐鉴 ·德 宗中》卷七),“理”也就自然只有一个,那就是“节”。樊系虽因不愿与朱泚为 伍而亡,但他毕竟为朱泚写过册文,曾有过卓然无节之行,而且这正是其为臣失大 节之处。因此,范祖禹仍然按照“责以备”的原则,把他排除在忠臣死节的行列之外, 将其归入“死事”一类。其历史批评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是欧阳修直接运用史书编纂体 例彰显臣节思想的一种转换形式,但却比欧阳修更加直接、通俗地传达出了史家的著述 旨趣和对历史的评价标准。
由此可见,《唐鉴》是以“礼”为核心的社会道德伦理原则作为历史批评标准的,反映了他重视道德力量和人之精神修养的意识,其中寄寓了他对现实的政治理想和恢复儒学地位的愿望。但由于他过分地拘泥于道德,其中又不免出现牵强和偏解历史的成分,以至于公主嫁与节度使之子,也被视作有悖于礼[2](《代宗》卷六),使本来很有思辨色彩的思想渗透出些许的保守、陈腐之气,反而有损于其思想的进一步升华,也会对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但从其主要内容来看,其中的许多议论又都体现出史家范祖禹对唐代历史的深刻反思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而且也确实对其所处的时代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与道德原则相联系的,是他对太宗所言“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的批评[2](《太宗上》卷二)。“逆取顺守”之说源于汉代政治家、思想家贾谊的《过秦论》,是他在总结秦朝为政得失时提出来的见解,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唐太宗的认识就直接来源于此。所不同的是太宗采用了或然判断的形式来说明“逆”与“取”的关系,范祖禹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依据具体的历史事实对此作出了全新的解读。他以《易》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作为立论的依据[2](《太宗上》卷二),对唐太宗之论作出了“于是失言矣”的批评,并得出了“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秦也”的认识[2](《太宗上》卷二)。他从根本上否定了唐臣萧瑀关于周、秦“得天下虽同,人心则异”的观点[2](《太宗上》卷二)。他认为周是以“顺”取方式取得的,而秦则恰恰相反。从其“强有力者贵其敢行礼义也”[2](《太宗上》卷三),及“后世或以汤武征伐为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顺天应人,所以为仁义也”的论述来分析[2](《太宗上》卷二),范祖禹所说的“顺”,有“顺取”与“顺治”之别。“顺取”并非是否定使用暴力,而是强调在建德、修政、顺应民心和历史大势的前提下用暴力夺取政权。范祖禹显然是把贾谊“逆取顺守”思想中的二大元素融入到了其“顺取”的理论当中,为武力夺取政权增加了一个道德和符合历史之“势”的大前提,这也正是其理论的耀眼之处,从而也更加丰富了我国古代儒家以道德论为依据的政权建设理论,为我国的政治思想宝库增添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2.以理论思维的方式阐发对于政权建设的认识
强调建德是范祖禹论史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内容,但他并未停滞在理想化的道德说教当中,而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评议,从整体认识的高度,在理论上解决了建德与修政的关系问题。他说:君主“是以虽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泽,天下愈受其弊”[2](《代宗》卷六)。相反“人君苟行仁政,使民亲其长,爱其上,驱之为乱,莫肯从也”[2](《德宗上》卷六)。而他在另一处又指出:“自古治少而乱多,由上失其道而民不知所从,故奸雄得以诡其众而用之也。”[2](《德宗上》卷六)以上三段议论大致包含了二层含义:建德是修政的基础,君主的道德修养是施行仁政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前提条件,道德修养是礼的内化,而修政则是礼之外化的必然结果;修政是政权得以长久巩固的基本保障。这不仅在理论上阐明了君主建德与修政的关系,以及君主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将这种修养外化为正确的政治实践的重要性,也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进一步具象化和理论的进一步升华。
修政是君主道德修养的外化和进一步延伸,也是稳定统治秩序的重要保障,因此如何修政则必然是范祖禹接下来要进一步讨论的重要内容。修政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应该包括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里我们仅选择了君臣关系和他对民心、民意的认识问题来做一番探讨。
关于君臣关系,范祖禹认为它的第一要义是“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2](《德宗下》卷八)。具体地说,它应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君臣应有属于其各自不同等级所应该具有的道德自律,这一点前已论及。二是君臣在行政上应各有分工,不能超越职分。关于这一点,他的经典论述是:“君人者如天运之于上,而四时寒暑各司其序,则不劳而万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劳也,所治者寡,所职者详也。……是以隋文勤而无功,太宗逸而有成。”[2](《太宗上》卷二)又说:“夫君以知人为明,臣以任职为良。君知人,则贤者得行其所学;臣任职,则不贤者不得苟容于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职则丛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则惰矣。此万事所以堕也。”[2](《太宗上》卷二)从行政角色上理清了君臣的分工关系:君主所司应大而要,即知人善任;臣下所职则应寡而详,即任君之职。概而言之,也就是君逸而臣劳。强调君臣于行政上各有所司,把君主知人善任作为实现其无为而治理想境界的必要途径。三是在行政实践层面上,具体地体现为君与相的关系。他说:“古之王者,唯任一相以治天下。……是以政治出于一,政有所统,相得其职,君得其道,恭己无为而治,盖以此也。”[2](《德宗中》卷七)他在这里虽然是从反对分割相权的角度来立论的,但确也道出了宰相在行政实践中统领百官的重要职能。“夫人主任一相,一相举贤才,贤者各引其类,岂不易而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伐其下,下不可勤其上,为上而行有司之事,岂独治天下不可为也?”[2](《宪宗》卷九)又曰:“夫天子者,择一相而任之,一相者择十使而使之,十使者择刺史、县令而置之,贤者举之,不肖者去之,则君不劳而天下治矣。……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选使者相之职也,察吏择使之责也。……苟相得其人,则委之择大吏而已矣。”[2](《玄宗上》卷四)这就把笼统的君臣等级关系明确地具象化为君相关系,并从提高行政效率的角度规定了二者间的权力分工,从而也使等级关系由礼法层面转化为行政制度层面的权利等级关系。
由以上议论可见,范祖禹是把君相关系和任相问题提升到政权安危存亡和统治策略的高度来认识的,这是他对政治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性认识的高度概括。除此以外,范祖禹还从历史经验出发,对君主任相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置相者当择之于未用之前,而不当疑之于既用之后。”[2](《宪宗》卷九)目的是要避免“既用也,过防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政愈乱也”的弊端[2](《宪宗》卷九)。
范祖禹以上所论的君臣关系,显然也是在等级关系的框架内进行的。但与其他史家所理解的君臣关系相比,范祖禹的夺目之处在于他于等级关系之外,又为君臣关系增添了新的内涵,即“君臣以道相与,以义相正者也。故先王以群臣为友,有朋友之义,非徒以上下分相使而已”[2](《太宗上》卷三)。他主张君臣间的等级名分要以“道”和“义”的存在为前提,君臣之间在名分等级关系之上还应建立起一种以“义”相扶持的“朋友”关系。朋友是“五伦”之一,按照家国同构的原则,君臣关系可以下推及父子。而范祖禹却把君臣关系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为传统的君臣关系增添了一层情感色彩,这是以等级制度为建立秩序依据的封建时代少有的见解,由此也反映出他非凡的政治洞察力和超越前人的历史见识,无疑为调整、改善君臣关系和统治策略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是历代有识之士都十分重视的问题,从先秦孟子的民本思想到西汉时期贾谊的《过秦论》,以及唐朝名臣魏徵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7],都无不反映了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对它的关注和思考。范祖禹的著述目的是要以唐朝的历史作为鉴戒的对象,从中“稽其成败之理”,以为后世之参考,而政治成败之理则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民心、民意。为此,他的认识是:“臣民之位,上下之等,以势相扶而已矣。天子者,以一身寄天下之上,所恃者,众心之所载也。合而从之则为君,离而去之则为匹夫。天下常治则能保其人君之尊,乱则众散,众散则与匹夫何异哉!……天子之贵,四海之富,岂可恃乎?”[2](《玄宗下》卷五)这里讲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承认统治者与民众间等级关系的同时,又提出了“以势相扶”的问题,“势”指的是什么?我们从范祖禹评议朱滔劫民叛乱未遂事件所说的“民皆有常性,饥食渴饮以养其父母妻子,而终其天年。此人情之所欲也”的言论看[2](《德宗上》卷六),“势”中包含了民生的含义。因此,满足下层民众的生存需要就是顺“势”而治,其中蕴涵着他对民众生计的重视。二是君主权威的树立同民心的关系是“恃”与“载”的关系,在逻辑关系上把民众、民心放在了君主权利存在的奠基位置上,与魏徵“载舟覆舟”的看法有着相通之处。
总之,《唐鉴》围绕君德、臣宜和君与臣、民关系所展开的议论,从编纂形式上说,虽然并不是以直接连贯的理论论述形式阐述出来的,但由于它是以“义理”为著述旨归,这就使他能以纵放之笔从唐朝日常的政治生活入手,将其所记零散的历史事实提升到政治规律的认识高度,体现出历史智慧与理论思维相交融的特点,将著史与论政紧密地结合起来,具有独特的思想魅力和普遍意义,这是纯理论著作或单纯的记史著作都无法企及的。
史家的历史见识不仅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有着系统而深刻的认识上。而且也体现在他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独立历史事件的理性认识上。范祖禹对唐代一些看似细琐但却直接关乎治道的历史事件的评论,就往往出人意料,他极善于从人们习以为常的政治生活的细微之处入手,深入浅出,不拘泥于就事论事,而是以事件为切入点,用与众不同的眼光,把它投射到政治层面上加以考察,展示出史家卓越的见识和智慧。他往往是所言之事极小,但所蕴涵的旨意却极大,于小事的评论中包含了深刻而重大的政治主题,闪烁着智慧和思想的光芒,实为一部史料丰富、论议比较全面系统的政治文化史专著。而从其所议论的内容看,可谓是非得失两存之,而且是得多失少。他论君主之道是政权安危的关键,这是对的,但他把君主的道德修养与政权安危的关系绝对化,以夷狄为殊俗丑类,以为嫁公主与四夷是“变华为夷”的思想,以及把女人与小人并举等,又显然是不足取的。而对于这种评论,我们都应做出科学合理的分析,才能判定其价值。
收稿日期:2003-1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