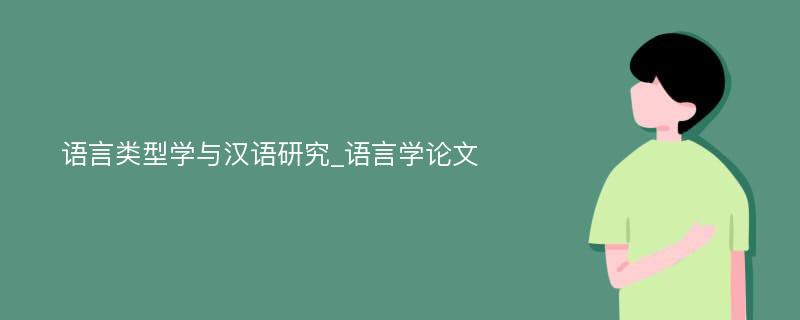
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语言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类型学是当代语言学的一门“显学”,但目前还不能说已是汉语语言学中的“显学”。这部文集可能是汉语语言学第一部以类型学为专题的论文集,催生这部文集的第一届肯特岗圆桌会议也是第一次以类型学为主题的汉语语言学国际研讨会。这本身说明了类型学研究在汉语学界尚处开发阶段,同时也说明此次会议和这部文集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意义,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及有关同仁办会和编集的功绩也将被学界铭记。
语言类型学有广狭松严不同的种种含义,但都离不开一个“跨”字,即它必须有一种跨语言(及跨方言、跨时代)的研究视角,才能称其为类型学研究。而严格意义上的类型学,是具有自己研究范式的“语言共性与语言类型研究”。
从当代语言学的学术构成看,语言类型学既是语言学的一种分支,也是语言学的一种学派。说它是分支,因为它和其他研究领域构成了某种分工:承担了跨语言比较和在比较中总结人类语言共性的任务,从而与注重语言结构内部深入研究的工作形成学科上的互补合作。
说它是学派,是因为语言类型学有自己的语言学理念、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从而区别于其他主要的语言学流派,例如形式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其根本的理念,就是不相信仅靠单一语言的深入发掘,就能洞悉人类语言的共性、本质或者说“普遍语法”,因此致力于通过跨语言的观察比较来获得对人类语言共性的认识。语言类型学家相信,对人类语言机制和规则的任何总结概括都必须得到跨语言的验证,而对任何具体语言的“特点”之研究也必须建立在跨语言比较而得到的语言共性和类型分类的基础上(而不仅是基于一两种语言间的比较)。类型学特有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类语言间的共同点和差异点,差异的不可逾越之极限也就是语言共性之所在。其特有的研究方法,包括语种库(language sample)的建立及语种均衡性的追求、参项的选择、相关语言要素或语言特征间的四分表分析及其空格的发现、绝对共性和蕴涵性共性的建立、对跨语言的优势现象(prominence或priority)和标记性(markedness)的总结、将蕴涵性共性串成系列的等级序列的建立、基于大规模语种库统计的和谐性(harmony)的总结,对共性或倾向的解释,等等(参阅刘丹青,2003)。
关于学派,有学者将语言类型学归为功能语言学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学派,文献中也能看到“功能—类型倾向/方法”(functional-typological approach)这一类表述。这的确反映了部分的现实:类型学家中的多数学者在语言哲学上倾向于功能主义而不是形式主义,而功能派学者中也有不少人乐于做类型学研究。但这只表明类型学和功能语法的交叉,并不体现两者的等同。类型学的“区别性特征”是它在理念上对跨语言研究必要性、重要性的坚持和上面所述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特色,而不是功能主义的那些基本信念。不少功能派学者主要从事单一语言的内部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自己的理论,并不重视跨语言研究,如一些话语分析的学者和认知语法的学者。虽然部分(哪怕是大部分)类型学者像功能学派一样相信,语言共性的存在,不是因为天生得来的普遍语法,而是为了满足人类语言交际或认知等功能的需要(参看科姆里(1981;沈家煊译,1989:28),但也有一些类型学家,包括最专业的类型学家,却很乐意采纳形式语言学的观点。例如,Hawkins在用处理机制(processing)解释语序共性的同时,就很强调句法的独立性,他不但乐意采纳X杠杆的理论来分析句法结构(Hawkins,1983:184),而且强调语序共性或倾向是为了便于处理纯句法结构而不是处理语义关系或语用功能(Hawkins,1994:425),这明显有悖于功能学派的基本信念,并且在成果的表达上也尽量地追求严格的形式化。此外,也有不少形式派学者,包括像来自生成语法大本营麻省理工学院的Ken Hale这样的学者,非常热心于类型学的研究,愿意让生成语法的理论解释去接受更多人类语言的验证。将语言分为结构定型语言(configurational languages)与非结构定型语言(non-configurational languages),被视为类型学中的一项重要分类,而这项类型划分正是由Hale等生成学派类型学家所作出的,而关于话题结构化语言、焦点结构化语言等的类型划分,也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参看本书徐烈炯文)。这些学者构成了类型学中一个分支——“原则与参项”类型学派(Fukui,1995),他们虽然从形式学派出发,但在相信跨语言验证的必要性和致力于从事跨语言比较方面跟其他类型学家是一致的,体现了类型学和形式学派的交叉。形式学派的最新分支之一优选理论更是大量吸收了类型学的观念和成果,如它对某个特征有无标记的判断就主要基于跨语言的分布情况。因此,将语言类型学简单地归入功能学派的分支,难以反映当代语言学学术分野的大势。
类型学作为一个学派,还在于它有自己的一套成熟并不断发展的科学研究范式,并据此获得了相应的重要成果。功能学者或形式学者从事的跨语言类型研究往往带有举例说明的性质,而不太讲究类型学特有的那套工作程序。“职业”类型学家的成果特别是经典性成果,则遵循Greenberg(1963)所奠定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这些著述首先追求语种库的覆盖面和均衡代表性,一方面是逐步扩大语种库的数量,从Greenberg(1963)的30种语言,到Keenan & Comrie(1977)的50多种语言,到Hawkins(1983)的200多种语言;再到Dryer(1992、1999)的600多种语言和900多种语言,另一方面是通过改进统计程序来减少谱系、地域方面的不平衡(如Dryer,1992)。此外,这些成果在大型均衡语种库的基础上,或者寻求无例外的蕴涵性共性,如Greenberg(1963)和Hawkins(1983)关于语序的共性,或者寻求严格的等级序列,如Keenan & Comrie(1977)关于制约名词短语关系化的可及性等级序列(Accessibility Hierarchy),或者追求大规模的统计结果,如Dryer(1992)通过625种语言的调查来确立各种句法结构与动宾结构是否和谐,或者追求全面覆盖的分类系统,如Grinevald(2000)关于类别词(classifier,包括汉语所谓“量词”)的分类系统。在这种范式下所获得的研究成果,能够在语言普遍性方面获得最大的说服力。而功能主义学者或形式主义学者所从事的类型学研究,尽管在理论追求和洞察力方面也许有其不俗的表现,但其类型学的充分性(typolosical adequacy)(注:这是Dik(1997)所提倡的语言研究的三个充分性之一,其他两个充分性是交际的充分性和心理的充分性。显然这是针对Chomsky的观察、描写、解释三个充分性而提出来的。)却无法与狭义的类型学成果相比,多多少少带有“客串”的性质。凭着自身特有的范式,语言类型学业已成为当代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学派,是一个与形式学派和功能学派都有交叉、都能沟通的学派。
单从语言学理念来看,类型学应当比形式学派甚至功能学派更具有与汉语语言学的亲和力。形式学派从语法能力的先天性假说出发,通过假设、演绎和母语者的语感测试来寻求与生俱来的普遍语法。功能学派则抱有与之对立的基本信念,认为语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要满足交际或认知功能的需要,于是以此为出发点,致力于从语言的使用或理解规则中去解释语言的结构及其演变。两者不同程度地带有从假设出发、“主题先行”的特点。语言类型学则更多保留了语言学作为一门经验性学科的特性,注重材料,讲究实证,主张旁征博引,提倡归纳推理,力求以事实说话,在调查之前不假设任何东西。这本是最容易为中国的语言学家认可的研究方法。然而事实上,在形式、功能、类型三大当代“显学”中,偏偏是类型学在中国国内最少为人了解。怪也不怪,这与中国学术界的另一些“国情”有深刻的关系。
中国的传统学术包括语言文字之学,素有尊夏贬夷、厚古薄今、重文轻语的传统。虽然华夏—汉民族数千年来就在众多民族部族的大交融中产生发展,中国也一直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但在汗牛充栋的传统中文典籍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对汉语以外语言文字的记述,更遑论研究了。不要说非汉族语言,即使是各地的方言,除了作为“匡谬正俗”的对象偶尔一现,也很难引起历朝历代学者们的关注。也就是说,正统的学术向来缺少对异族语言的兴趣,更没有进行语言比较的传统。进入现代以来,外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都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这本是孕育跨语言比较的很好时机。可是,20世纪50年代过于追求专业分工的前苏联式教育科研体系,以及语言研究队伍和学术兴趣向普通话的高度集中,又强化固化了不同语种研究队伍间的壁垒,形成了纯粹语种导向的语言研究体系。不要说汉语、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三大队伍很少有切实的交流,即使在古今汉语之间、普通话和方言之间也缺少实质性的沟通,更谈不上在跨语言基础上对语言共性的追求了。这种学术格局下,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甚至生成语法都有一定的机会被引进来成为汉语研究的利器,甚至发展成主流,唯独语言类型学很难获得发展的空间,因为这株树苗是无法在单一语言的土壤中生长的。(注:在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相关的领域,如方言、音韵、民族语言等,还是有不少跨语言跨方言语音及词汇方面的研究成果,但这多出于历史比较的研究目的,与语言类型学的学术目标大异其趣,而且也较少涉及语言类型学最关心的语法问题。)而缺少了类型学视野的汉语语言学,也很难用汉语研究的成果去贡献于普通语言学理论。
当然,跨语言、跨方言、跨时代的兴趣和研究实践在现代中国并非完全没有,它主要表现为少数学者、特别是一些视野开阔的语言学大家的个人行为,未成风尚,更不成学派。赵元任先生公开发表的首篇语法论文就是《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1926),论文不但从语法和语义功能的角度比较了三地方言的许多虚词,而且不时穿插与英语、德语等的比较。黎锦熙先生在他开创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先河的《新著国语文法》之后又撰《比较文法》一书,进行古今汉语和英汉之间的语法比较。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以《红楼梦》为主要语料研究普通话的语法,但在各章之后设有与吴、粤等主要方言的比较。吕叔湘先生《中国文法要略》首创将古今汉语合为一书的体例,便于读者在古今比较中体味汉语的内在联系和演变。陆志韦先生在给萨丕尔(Sapir)《语言论》中译本所作的序和译注中,不时流露出他在汉语和其他语言比较中获得的一些真知灼见。朱德熙先生则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写出了数篇方言比较和古今比较的语法论文,涉及结构助词、名词化标记、疑问句类型等。语言学大家对跨语言跨方言跨时代研究的兴趣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他们的学术成就互为因果的。因为他们有超越汉语本身的更广阔的语言学兴趣,才会注意其他方言语言的情况;也正因为他们视野开阔,才会在汉语语法的研究上取得更加杰出的成就。这些研究虽没有同当代类型学的学术范式直接挂钩,但其精神仍与类型学有相通之处。遗憾的是,中国大陆分工过细、语种导向的语言学学术体系,以及结构主义学派对纯共时状态和语种“特色”的过分追求,使跨语言研究在很长时间里难以发扬光大。有一些著作出于语言教学的需要进行一些中外语言的语法对比,这种基于应用的对比距语言类型学所关心的理论问题还是相当遥远的。
20世纪80年代起,在介绍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过程中,当代语言类型学开始为中国大陆的语言学界逐步有所了解,其中数陆丙甫、陆致极翻译的Greenberg的经典论文(1963;陆译,1984)和沈家煊翻译的科姆里(Comrie,1981;沈译,1989)最为重要。但比起其他学派来,语言类型学的介绍仍是最为薄弱的,对汉语语法的直接影响仍然相当有限。主要的积极影响在于,一些功能倾向的学者在研究汉语时有意识地以类型研究所得的语言普遍现象为背景,从而使汉语语法研究与人类语言共性的研究发生更加密切的联系,如陆丙甫(1993)关于语序的讨论、沈家煊(1999)关于语法单位和语法范畴的标记模式和关联模式的论述、张伯江(1997)关于汉语形容词词类地位和范围的研究等。直接关注汉语的类型学地位的则有徐烈炯、刘丹青(1998)、刘丹青(2003)关于话题、语序类型和介词类型的研究等。当代类型学对海外汉语学界的影响要早一些,如上个世纪70~80年代关于汉语是SVO还是SOV的热烈讨论(参阅屈承熹(1984)和徐、刘(1998)对此的综述)、桥本万太郎(1978;余志鸿译,1985)的语言地理类型学,都是在Greenberg(1963)所开创的语序类型学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成果。不过海外的这些类型学讨论也并未延续为某种类型学派,参与讨论的多数学者后来仍分别主要从事形式语言学、功能—认知语言学或历史句法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传统语法和结构主义二分天下的格局逐步消解,语言研究出现了多样化的取向,人们不再满足于单一语言纯粹共时的描写,跨方言、跨时代乃至与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比较逐渐兴盛起来。这些研究有的有类型学理论的背景,有的(主要是历时研究)与语法化理论有关,更多的则是在结构主义范式描写基础上的朴素的比较、提炼和概括,可以认为是一种宽松意义上的类型学研究,它们无疑为类型学在汉语语言学界的下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气候、土壤、地基和环境。肯特岗圆桌会议的第一届就以类型学为主题,真可谓得其时也。
语言类型学以跨语言研究为本,而汉语语言学以研究作为单一语言的汉语为本,在汉语语言学界提倡语言类型学,看似有点方枘圆凿,其实不然。语言类型学和汉语语言学的结合,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且将给普通语言学和汉语研究两方面都带来巨大的促进。
典型的类型学研究,当然不能单研究汉语,汉语只是类型学所面向的大量语种之一。不过,语言类型学虽然面向众多语言,但不同语言的研究深度不可能完全一致。某些语言使用人口多、研究队伍雄厚、在类型学上有一定的代表性,就有条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更加详尽的研究成果,这样的语言能成为类型学比较中的主干支撑语种。在这方面,汉语无疑是很有资格成为主干支撑语种的,汉语语言学界也有条件为语言类型学作出特殊的贡献。但是,由于汉语研究有自己特有的一些传统,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语法描写和研究所依据的工作框架与世界上通行的框架特别是类型学比较的框架还有诸多出入,许多基本的普遍性概念在汉语语言学中还不为人所熟悉,如非受格(non-accusative)动词、标句词(complimentizer)、关系化和关系从句、核心标注—从属语标注(head-marking vs.dependent-marking,参本书刘丹青文)等。而汉语学界习惯使用的一些概念,如补语、存现宾语、量词等等,又不能简单地转换为普遍性的语法范畴。这使得汉语研究的大量成果还无法直接转化为类型学上的可比性材料。随着汉语本土和海外研究队伍日益密切的交流和合作,这一情况正在得到改善,而对类型学的关注将促使学界加速汉语描写现代化、通用化的进程。这一进程反过来将帮助汉语语法学发现更多描写研究中的死角,从而揭示出更多的汉语事实,而“汉语事实”正是汉语语言学界历来呼声最高的追求目标。
当代语言类型学远远不满足于对语言的分类,而将语言共性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面对表现各异的众多人类语言,需要特别重视的就是如何判断某种现象属于个性(差异)还是共性。有了这种类型学的视角,我们才能在汉语研究中较好地把握有关汉语现象的本质和语言学价值,从而使汉语研究的成果可以直接服务于语言学理论的建设。例如本书徐杰的论文,借助于跨语言比较和理论概括,一方面注意到,话题的语用属性是在所有语言中都有的,属于共性;另一方面又注意到话题作为一个“句法特征”(而非“句法成分”)在不同语言中可以有不同的句法实现手段,其中有些语言有更丰富、更固定的实现话题(话题化)的句法手段,从而形成语言类型的差异。虽然他的构想尚有讨论的余地,试比较本书徐烈炯文对汉语话题的句法性的论述,但两篇“徐文”共有的结合了形式语言学和类型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的研究,无疑有力提升了汉语“话题”研究的理论高度,这是单纯汉语内部的研究所难以达到的。
汉语的“特点”、“特色”向来是汉语学界的热门话题。但是有一些人所谈的特点,仅仅基于同英语等少数印欧语的一点印象式的比较,面对数千种类型各异的人类语言,这种印象式比较得出的结论难免片面。有人再把这种印象式结论拿来作为抵挡现代语言学的盾牌,声称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全都是在印欧语基础上得出的,不适合汉语,等等,那又从片面走向了偏激,无益于汉语语言学的发展。假如了解几十年来语言类型学的丰硕成果及由此带来的语种视野的空前开阔,了解形式语言学、功能语言学从类型学成果中吸取的营养和它们自己所从事的大量跨语言比较,就不会轻率地发表这样的议论。我们要真正了解汉语的特点,应当了解语言类型学在这方面已经作出的类型概括,或者自己去从事具有一定的类型覆盖面的跨语言比较。而从事跨语言的类型比较,经常采用的一个策略是从语义范畴出发而不是从形态—句法范畴出发,因为许多语义范畴是人类语言的表达所普遍需要的,因而具有可比性,从中可以看出不同语言表达同一范畴时在形态—句法方面的类型差异;而特定的形态—句法范畴却可能只存在于部分语言,无法有效进行比较。本书崔希亮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他从空间范畴这个语义范畴出发,考察了近10种语言的相关表达,并结合认知语法探讨了古今汉语在空间表达方面的特点。他考察的语种数量虽然不算很大,但是类型上已有相当大的覆盖面和代表性,代表了语序和形态方面相当不同甚至对立的类型,如高度屈折的俄语、典型的粘着语日语和芬兰语、高度孤立的越南语、典型的SVO语言泰语、典型的SOV语言日语和韩国语、语序类型介于两者之间的汉语等。这样的比较才能让人对汉语在空间范畴表达方面的句法特点有较为客观的认识。跨语言考察对“特点”、“特色”的另一大冲击在于,许多被认为是汉语特色的东西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特殊。《马氏文通》在“泰西葛朗玛”常见词类之外为汉语加设一类“助词”,指的是语气助词。这一做法引来一片叫好,连批评马建忠过于“模仿”的学者也对“助词”之设不吝称赞。但由此便认为语气助词是汉语(或汉语的亲属语言)特有的“特色”,却在跨语言比较面前经不起推敲。陆镜光(2001,手稿)的跨语言考察显示,语气词之属,遍及亚、欧、美几大洲的许多种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中。中间不带连接性虚词的连动式也被认为是汉语区别于印欧语的一大特点。不过类型学的调查显示,这类结构广泛存在于西非、东南亚、大洋洲等许多语言中(参看高增霞(2003)第一章所引文献)。随着类型学愈益为人了解,随着人们的语种视野愈益开阔,那种拿汉语“特色”来抵挡现代语言学的努力恐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越来越多的汉语“特色”现象将被跨语言考察证明,原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注:当然,汉语确实存在一些真正的特点甚至很突出的特点,只是这些特点要放在人类语言共性和类型分类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和研究,例如,汉语是世界上众多VO语言中几乎仅有的关系从句在核心名词之前、比较基准在形容词之后的语言。像这样的真正的特点,汉语学界还很少关注,因为缺少类型学的视野。)
带着类型学的意识来研究汉语,也并不是每一项课题都必须涉及众多语言。重要的是要有语言共性和类型的意识。有了这种意识,再借助于合适的理论框架,那么即使是与少量语言方言的比较也会获得可喜的收益。例如本书蔡维天文,讨论的是“一、二、三”三个基本数词的语义和句法。对这几个汉语数词,特别其语义,从传统的训诂学到现在的词义学和词典释义,探讨得不可谓少、不可谓浅。但蔡文以形式语法为理论背景,通过相关表达与英语等的对比,揭示了很多前人所未见的特点和规则。要是限于在汉语内部研究,我们是很难获得这些可贵的认识的。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有本书中方梅的论文。她所讨论的北京话“这、那”向来只被看成指示词或曰指示代词。方文运用功能语法的视角,揭示口语中很多“这、那”已不起指别或代替作用,而发挥着某种指称标记或语篇标记的作用。她进一步借助功能语法关于冠词和指示词的理论及英语相关现象的比较,用可操作的标准判定某些“这、那”已从指示词发展为冠词。方文还比较了福州话等方言材料,更进一步显示从指示词到冠词并不是北京话特有的发展,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常见机制。方文整体上比较的语言方言并不多,比较所占的篇幅比例也不大,但这些跨语言跨方言比较对论文的研究成果起到了至关紧要的作用。
中国虽然在学术方面存在着某些不利于类型学发展的传统,但同时也存在着类型学发展的有利条件,除了前面提到的中国语言学界和类型学对材料优先的共同注重外,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是类型学所需的跨语言研究的绝佳条件。中国境内的上百种民族语言,汉语自身丰富多变的方言,还有汉语数千年有记载的演变历史,都为类型学的展开准备了充足的语言食粮。当然,为了面向人类语言共性的类型学比较,我们需要拓宽眼光,善于将国内的语言资源同世界上其他语种材料结合起来研究,以取得更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只要以语言共性和类型研究的已有成果为背景,只要遵循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那么,即使是同一类型或同一谱系内的跨语言比较、甚至同一语言(如汉语)内部的跨方言或跨时代比较,也能获得富有价值的发现。由此得到的一些局部性的共性,包括蕴涵性共性或等级序列等,有时反映的就是人类语言的普遍性,在今后更大范围的跨语言比较中就会获得验证,有时反映的则是某一类型或谱系内部的特点,这同样具有类型学的意义。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海内外同行的共同努力下,汉语和中国境内的语言方言的研究队伍,将逐步发展出类型学研究的新兴有生力量。汉语语言学家不会永远满足于关起门来做自己的汉语专家而置身于世界语言学之外,不会永远满足于只见树木(哪怕是汉语这棵大树)而不见森林的视线限制。随着学术的发展和交流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学者会从汉语出发进而产生对人类语言普遍性的关怀,从而在不同程度上介入类型学的研究,在世界的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探求人类语言共同的奥秘做出自己特有的贡献。
蒙本书编者相邀,写下以上个人的感想。本文主要是对语言类型学及其与汉语研究的关系做简要探讨,所提到本书中的论文,仅仅为了说明某个问题而举的例子,而不是对本书内容做全面或重点介绍,大部分论文包括一些重要的论文并没有在此提及。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本文难以担当真正“前言”的使命,权且作为一个“代前言”供读者参考、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