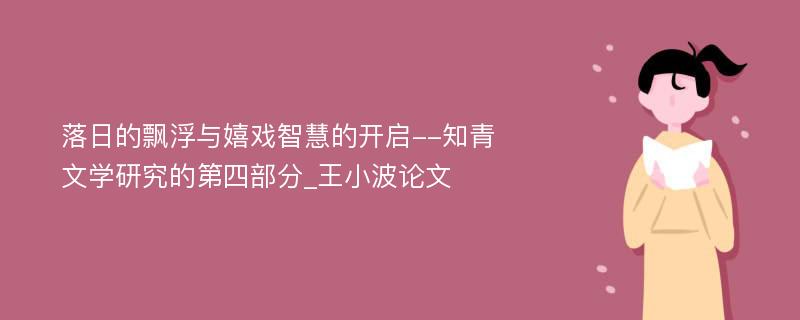
落日情节的漂浮与戏谑智性的敞开——知青文学研究之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青论文,落日论文,之四论文,情节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2)01-0001-06
我曾在自己的知青文学研究之三中,分析了新时期知青主体在90年代中期的最后坍塌 。[1]虽然进入九十年代后,除了“老三届”文化热的喧嚣,更具个人化的知青题材的 文学写作也零星存在,不过已没有什么评论者将它们刻意集中起来作为知青文学的延续 来进行评论,而且它们也的确与过去的知青文学写作有了极大的差异。但正是这种差异 ,又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知青文学的新视角,所以有必要进行一些研究。
一、落日情节的漂浮
(一)
新时期知青文学在作八十年代表现出永恒空间的建构意向,[2]但是大约从九十年代开 始,蒋韵、李锐、林白等人的一些知青题材作品,却呈现出了强烈的时间意识,或可名 之为“落日情节”的飘浮性伤感。(注:这里所说的主要是以下这些作品:蒋韵的《落 日情节》、《旧盟》、《相望江湖》、(《上海文学》1990年11期,1992年1期,1993年 10期)、《旧街》(《花城》1991年1期)、《古典情节》(《山西文学》1991年12期)、《 裸燕麦》(《当代》1991年6期),李锐的《北京有个金太阳》(《收获》1993年2期)、《 黑白》(《上海文学》1993年3期),林白的《一路红绸》(《中国作家》1992年2期)、《 英雄》(《青年文学》1991年12期)。还存在其他一些较为接近的作品,如柳岩的《鱼知 青的岁岁年年》(《清明》1990年1期),储福金的《情之轮》(《小说月报》1993年2期) 等。另外上述所列作品的意蕴是多方面的,像林白的两部作品或许就要作为朦胧的同性 恋故事来解读。而在此,只是从知青文学这个角度去进行解读的。)当然,这里所说的 并非那种八十年代初的知青作家们共有的人生易老的感慨,而是某种具有了哲学意蕴的 存在性时间意识。首先在这些文本中,空间的形式已不再或不很重要,刻意而为的时间 因子弥漫文本空间。第二,其中的时间不是凝固化、单向性的,而是弥漫性的具有强烈 漂浮感的时间。第三,飘浮的无定向性的时间粒子随意穿越每一个出场的或不直接出场 的人物和叙述者,将他们变为破碎的所在。而且这里又不是萨特式的从一开始就被抛入 空无的完全无定向性的要去进行自我意义建构的个体;相反,过去的时间已给他烙下了 永难消失的时间印痕,将其一次性地永远定性,可是转瞬间时间又将他抛弃,让他独自 承担过去时间的重负。因为这过去的时间已不再是构成公共历史的过去,而是已被抽象 的时间和在场的历史时间双重遗弃的时间,(注:“抽象的时间”即以记年日历形式展 开的时间,而“在场的历史时间”指具体的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时间。)所以在根本上这 种承担就成了无社会意义的、无观众的纯粹的个人化的行为,是一种被历史放逐了的时 刻的个体化消蚀的承担。第四,当这种个人化的行为被给予哲学意蕴的时间意识加以体 验、咀嚼、叙述时,一种特有的既具哀婉悠长的古典意蕴,又是破碎而无主体化的弥漫 性感伤就萦然而现。第五,正是通过这种时间对时间的放逐的观照,时间就同时具有了 此在和存在的双重性。第六,这种双重性的时间尽管相当疏远了“新时期”的主流意识 形态时间意识,但却未必逃离了意识形态的捕获,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这种无可逃离 正构成了所有这类作品的哲学意蕴与文学意蕴。
(二)
前面概括性地点出了隐含于蒋韵、李锐等人90年代知青题材写作的时间性特点,换言 之就是说,他们对作品的时间形式的建构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里所说的形式,不是传 统文学理论所说的内容载体,而是被讲述者,讲述者,讲述、关于讲述的讲述相互作用 ,相互转换的共构的时间形式。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对时间形式感构建的“技术性”分析。这一方面最外露的手段是外在性时间标 度的刻意重复。如蒋韵的《落日情节》一开始的前三节就极力营造某种特殊的时间意味 ,尤其是第二节反复以“九月九日”这一时间标度开启每一个自然段。通过对“九月九 日”或“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的反复书写,于是主人公郗童再也逃不出“一九六七年 九月九日”这一劫数。与时间标度的刻意重复相较,此处所涉作品的更具共性化的艺术 表征是某种肖像化的时间片断不可遏制地穿越文本的时空反复呈现。所谓肖像化的时间 片断是指某种特殊的叙事片断,它既具有肖像特性,好似一个被凝固的瞬间形象,又含 有浓郁的时间意味。这种时间意味不仅由叙述的字、词、句所传达,而且这一肖像化片 断本身就是某一特定时间的曝光之结果。它被某一特定的历史时刻所定格,却仿佛又具 有某种时间的神奇穿透性。单向时间的流逝将其冷漠无情地抛在身后,欲使它成为过去 、成为遗忘,可它却不可遏制地击穿时光流逝的屏障,反复地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 空领域浮现。它就像是一个时间的蒙太奇镜头,在时间的波海里,反复凸现于我们的眼 前。例如蒋韵的《裸燕麦》里有这样一幅肖像的描写:
“她们(姐姐的知青战友们——引注)还互赠照片,有一张照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照片中的女孩儿骑在一匹肮脏的老马身上,双手抓缰,两眼遥视前方,后面题辞曰: ‘塞外风光好,战友向阳笑。’我姐姐就把这些照片一张张贴在照相薄上,然后流涟其 中,从此再也没从里面走出来。”
常常这种漂浮的时间片断本身就是好几个时空的融会,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意象, 穿过时空的幕障在一瞬间凝结:
“她朗诵卢森堡《狱中书简》的声音,就像一条宽阔的大河波涌平静,在满天星光下 流向远方。一九六九年的夏夜在永隆、在沙街、在狭小的阁楼上,河风从高空中灌进, 将蚊帐高高掀起,十七岁的女学生在为七岁的女孩朗诵罗沙·卢森堡半个世纪前在德国 监狱里写的信,她全神贯注,在声音中注入了一种热烈而永恒的情感,仿佛这封一九一 七年的信就是写给她的。”
“革命者丹娅头发湿漉漉地站在我家天井里的形象永远停在那里。多年以后发胖的丹 娅抱着儿子喂奶的情景,总是被我叠印在这个画面上,像是一部陈年的电影。这电影用 了一种奇怪的剪辑手法,跳跃很大,毫不连贯,而且匆匆忙忙难以停留。”(《英雄》)
时间形式建构的技术性方面的第三点是叙述语句时间感的传达。这一点实际与前两点 有关,不过它所强调的是,时间意识的传达不只局限于单个性的时间标度和时间片断, 而是弥漫于整个文本的叙述语言中,既是叙述语言所表达的形式意蕴,又是叙述者语言 形式的具体建构材料。且看:
“千里皓月。/万里荒原。/千里皓月和万里荒原之中紧紧拉着一双滚烫的手。有一双 乌幽幽的眼睛一往情深地看着这双手。”(《黑白》)
其次是多种时间意识交叠的问题。对所涉及的有关文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时间既不 是单一性的,也不是完全碎散而无任何定向性的,大致可划分为这样三类:过去时间、 个体时间、永恒时间。所谓过去时间是指与过去某一特定时刻(“文革”或知青岁月)或 时期相关的时间;个体时间是个人生命岁月(往往是青春岁月)的消逝流程;永恒时间或 可称为自然时间,它与前两种时间似乎是无关涉的,或像永远流淌不息的大河,或像凝 然不变的亘古荒原,衬映出前两种时间的短暂、有限。重要的不是这种三种时间的存在 ,而是它们存在的相关性、共生性、交叠穿插性。
按我们习惯的线性历史发展观来看,“文革”或知青岁月是一个客观的历史阶段,不 论它给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具体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它的特征在根本上却是超然于具 体存在者的;而且作为一个历史的发展阶段,不管个人对它持有怎样的态度,也不管它 对现在还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它终究是一个已被不断展开的历史所Pass了的过去的历史 。与这种观点不同,此处所涉及的作品恰恰强调的是它与个人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就个人而言,历史表现了无可商量的外在强力,它将所捕获的猎物牢牢地抓住不放,将 其染色定格,变为历史的标本。其魔力就如《落日情节》中的那个“一九六七年的九月 九日”,《黑白》中的火红的知青岁月。然而,这历史的时间绝对不是可以超然于个人 而存在。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从这些文本中并不容易发现关于某种类型化的时代特征的 书写。这里,过去时间给个人的时代染色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一种偶然性的个别行为,不 仅所染的色调深浅与个人有很大关系,就是染色本身往往也是建立在个人体认之基础上 的,无此,染色就不可能发生。《落日情节》中,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那天,少年郗童 由于经不住哥哥的哀求打开锁放走了哥哥,恰巧哥哥死于那天的武斗,母亲认定是她杀 死了哥哥,她接受了这一“宣判”,从此就再也逃不出这“历史性”的审判的那一刻, 或者说是开始了她的成人史。这种审判无疑是蛮横的,但是它并无什么有形的不可冲破 的外在强力的支持,如果被束缚者不接受它,它也就失去了魔力。就如对“黑”而言, 没有那火红的年代就不会有他这个扎根楷模,而无他对这一楷模的一厢情意地执守,也 不会有那最后不幸的结局。如果说上两篇倒还更多地包含了过去历史的强制性外力(“ 文革”年代、传统伦理母爱),那么隋小安所落入的历史之网,就更纯粹只是由“几点 了”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搭讪所张开的。(《旧盟》)我们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双向作用 下,历史——既是与特定时代相关的,更是个人的历史——才可能生成。
很显然,这样的历史不可能通过一次曝光、一次定格形成;这曝光、定格之所以能成 为历史,还有赖于在时间的绵延中被有关者所持有。请看:
“陈叔叔想,谢萤死了,我为什么还活着?/但是陈叔叔一天天活下去了……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陈叔叔拒绝了所有说媒的人,拒绝了所有温情女人名字……陈叔叔走在吕 梁山区没有星月的山路上,于自虐中一点一点去亲近谢萤的世界。(《旧盟》,着重号 为引者所知)
正是这种自虐性的持有,才得以使陈叔叔的活和谢萤的死所共构的历史时刻得以延展 ,成为历史。同样姐姐英雄丹娅的幻象,如果不始终萦绕于妹妹的心头,不被她(作为 妹妹的她和叙述人的我)找回的欲望所反复呈现,也就不可能构成关于寻找或虚构英雄 丹娅的故事。(《英雄》)更为显豁的例证是《黑白》,黑与白的非知青岁月的最后的知 青岁月,就是黑的那种一厢情愿所致:“我不还是个知青代表吗?只要全中国还有一个 人在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件事情,就还存在,就还有。”
然而把这一切称之为相关者的持有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所谓的持有者和被持有者在此 是同时作为一种时间历史被展开的,正是在这种展开中,个体时间才得以呈现。不过, 既然已经排除了外在性的线型历史框架,那么这种展开是在什么意义下的展开?它能够 自我展开吗?当然不可能,还需要永恒的时间。在李锐那里,永恒时间更接近天荒地老 的那种意蕴,它的直接表征就是几乎恒定不变的黄土高原、吕梁山脉。曾经有那么几个 知青闯入其间,搅起了几汶涟漪,但是很快一切都归复平静;知青、知青的历史都烟消 云散,而一两个被遗落在这里的当年的知青,却在凝固时空的包围中独自咀嚼着早已消 逝的过去,将自己的生命时光的延续化为对虚幻空无的历史的承载。与李锐不同,蒋韵 、林白那里的时间的永恒性更多地以生命岁月的流逝来呈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呈 现不仅是以主要人物的变化来实现,而且也穿插于应属于“同时代”的他人的不同生活 形式的对照性表现。不同的个人时间不时地交汇、错位,没有谁能为你分担你自己的命 运,当你选择了历史和被历史所选择,就意味着这根本上只能属于你自己的历史,历史 只能通过不同的个体生命来展开,也注定要溃散于个体时间的消逝之中。另一方面,蒋 韵、林白的永恒时间比李锐的更富流动性、换位性。因为它不仅没有凝定直接的象征物 ,而且似乎本应是它所具有的悠远的意蕴,也是由个人生命历史的“不变性”来传达的 。前面所说过的那种肖像化了的凝固瞬间,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一次次地在任 意的时间方位中闪现,将本应消逝了的“旧事”、“旧街”、“旧式公寓”、“旧时代 ”不断地拉回到当下的时间中,“不知觉之中我们就看到或说拥有了一双隔世的眼睛, 以这“隔世的眼睛看待此生此世,渐渐觉到了一种悠远的苍凉。”
上述时间形式要作为文本形式呈现,就不能只是被讲述的时间的形式,而同时一定是 讲述的时间形式。这样,我们显然不能想象一个存在于固定时空方位的超文本的讲述者 存在,它一定是与其所讲述共生的、同样具有非主体化的漂移不定性。这就是此部分要 分析的第二个方面。我想通过讲述与被讲述所共有的间距共生化关系进行分析。
直截了当地说,间距共生化意味着一套讲述与被讲述的可换位机制的存在。为了分析 之便,我们区分出了讲述与被讲述两者,但是实际上并不存在可独立存在的任何一方, 不论何时提到一方就意味着另一方的存在,说某一讲述在进行讲述时,就同时包含了讲 述向被讲述的转换之意。这与拉康化了的看与被看的无意识转换机制是相同的。不过在 此,这种关系并不是一个深层文本心理分析的问题,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呈现为文本 的形式本身。这点可以某种特殊的观照性叙述视角的设置来体悟。
将《裸燕麦》、《英雄》、《一路红尘》以及《黑白》、《北京有个金太阳》联系起 来分析,我们会发现,其中都存在一个不完全的相对独立的重要叙述视点。前两篇以妹 妹的身份出现,第三篇是以同学的身份,第四篇是北京的两个知青,最后一篇是“白” 。他们含有这样的共同特点:在相当程度上,文本是通过他们来观望“主人公”的(注 :这里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使用了“主人公”这一传统词语,其实严格地说,在这些作 品中是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主人公”的。他们一方面已没有传统作品中的中心化结构 地位,具有相当的漂浮性;但是另一方面又未走到先锋小说人物彻底散化的地步,还可 以作为人物、作为有一定突出性(在文本世界里)的角色来理解。),与“主人公”直接 相关的历史肖像实际上就是由他们的观望所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观望者 主体。但是文本又明明白白地交待出,那由他们所看出的肖像又以其特有的时间穿透性 ,将所观望者牢牢地缚住,将被观望的命运的展示变为观望作为被观望的观望的命运展 示。《英雄》中的妹妹很早就与姐姐丹娅分开了,留在她脑海中的是一个留着短发的刘 胡兰式的女英雄的形象。在文本的第一层空间中似乎是她要给我们讲述姐姐的故事;可 是随着不同的叙述视点的转移,随着文本的不断展开,我们却发现原来关于姐姐们故事 转变成了关于讲述姐姐故事的故事。正是姐妹两者之间存在的时间距离造成了讲述的共 生性张力,整个文本在相当意义上就是关于这种距离的克服与不可克服。
在《裸燕麦》中,也通过妹妹“我”与姐姐昔日的恋人彭高(这是一个梁晓声、张承志 式的知青形象)的关系更直接地表现出同样的意蕴:
“怨怼之情烟消云散,那一会儿我知道,我终于走出了彭高的笼罩……我寻根溯源, 告别了最后一次感伤的回味……我终于拥有了适于谈话的阅历和平等心境。因为彭高已 不复存在,一旦走出那幅历史画卷就没有了彭高。”
相较而言,《黑白》中的这层讲述与被讲述观望与被观望的转换性关系似乎不象前几 篇那样明显,但黑白难辨的含义(注:该作是这样描写他俩死时的情景:“两个人是抱 在一起死的。两个人身上都没有穿衣服,黑白相绕,怎么也分不开。队长说,算了,别 分了,给两人打一口棺材吧……”。)的人格化存在,就更浓聚了这层关系。
二、“黄金时代”的重写与敞开
(一)
以《黄金时代》所涉及的生活面来看,它无疑应该纳入知青文学的范围,尤其是集子( 注:这里指的是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的《黄金时代》。它共收入了三部作品,《黄金时 代》中篇三部曲只是其中的一部。)中的《黄金时代》三部曲中的第一部《黄金时代》 更是在背景与结构上同《血色黄昏》非常接近。(为了便于区分,下面以<黄金时代>指 称集中的<黄金时代>三部曲,以<时代>代指三部曲中的第一个中篇,而带双书名号的《 黄金时代》则是指整本集子)然而《黄金时代》不仅与各种知青小说相去甚远,而且与 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各种风格样式都极为不同。在王小波那里,文学的叙述向日常 生活和理性思维、向肉体和精神、向荒唐和严肃、向嬉戏和反思、向过去、现实和未来 无限地敞开;他以其拉伯雷式的狂欢文体、《十日谈》式的无拘无束、汪洋恣肆的性爱 描写、经验理性式的冷静,把我们带入到了一个相当新异的生命境界中,给中国人的存 在提供了新颖的开放性结构之参照。
《时代》是这样开篇的。有一天漂亮的医生陈清扬专门来找王二“讨论她是不是破鞋 的问题”,王二说“如果我要安慰她,并不困难。我可以从逻辑上证明她不是破鞋。如 果陈清扬是破鞋……则起码有一个某人为其所偷。如今不能指出某人,所以陈清扬偷汉 不能成立。”如果按照这样的证明逻辑去展开故事的话,那么《时代》就将完全落入《 血色黄昏》的窠臼,去展示“判定有罪—证实清白”的游戏。王二可不想玩这套游戏, 他“偏说陈清扬就是破鞋”。这话颇像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痞子无赖言语。 但是我们决不能把王小波等同于王朔。王朔写作表现的是一种犬儒主义的生存智慧,而 王小波所凭借的则不仅是这种直接的经验智慧,而是将其提升到了经验哲学的高度。这 里的问题实质是这样的,当你被宣判为搞破鞋而你又要千方百计证明自己不是破鞋时, 实际上已经承认了那个原初判定的合法性,承认了搞破鞋是一种罪,并把自己置于它的 控制之下,使自己处于一种被审判的位置;使得这种审判和被审判的游戏得以展开,成 为现实。因为这套游戏并不在乎被审的一方是否犯罪,在这套游戏逻辑中,根本不存在 某种能够证明被审者是否犯罪的客观标准。以王二前面所做的逻辑证明来说,即便如今 不能指出某人为陈清扬所偷,也不能排除今后能够指出某人为其所偷的可能性,所以仍 然不能排除陈清扬是破鞋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无法证伪的问题。正是利用了这种潜在的 无法证伪性与被审者竭力想证明自己无罪的心理冲动,包括“文革”中发生的无数控制 和被控制的政治游戏才能够长久持续。而王小波的智慧就在于看透了这套把戏,不去证 明陈清扬和王二无辜,“倒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要“偏说,陈清扬就是破鞋”。 这样一来,王二们就占有了现代文学史上从未有人占领过的双重制高点:既可以摆脱社 会意识形态牢笼的束缚,给自由欢娱的生活敞开想象的天地,又可以反思、颠覆传统意 识形态;简言之求得一种嬉戏的生活和智性反思的平衡。正是理解了这一点,我认为不 能再说“王二和陈清扬的恋爱故事整个地包括在一个罪恶与情欲的冲突形式中”[2]因 为这属于对传统情感文化结构的概括,它所寄含的意蕴是对性的窥视、觊觎和性禁忌的 抑制性对立矛盾冲突,我们在章永璘和马缨花(《绿化树》)、“周兆路和华乃 倩(《白涡》)、菊豆和扬青天(《伏羲》)的关系中已早为熟知了。反之在王二和他的情 人那里,性爱关系完全没有了那种压抑性情欲色彩,完全是一种自然的生命现象,一如 《十日谈》中的那一个个性爱故事一样被毫不造作却精彩悦目地展示在人们的眼前。正 如前述所引的同一个评论者所概括的:“男女欢爱在性禁忌年代成为罪恶、罪名,这不 稀罕,罕见的是还从来没有人如此理直气壮,如此汪洋恣肆地写其出于生理本性的自然 、单纯。王二与陈清扬多次做爱(作案),只是因为他们年青,他们乐意。王小波还原性 爱的单纯性,正好戳穿了逼供者的潜意识。夸张、张扬、恬不知耻的叙述姿态,调戏了 那时代(其实也包括现时代——引者按)集体性的窥春癖”。[2]
然而仅从性爱描写的自然还原这一点还不足以充分说明王小波所达致的嬉戏生活和智 性艺术平衡。我们还有必要对王小波文本中存在的不同游戏关系再做些分析。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时代》一开始就推出了一个传统常规的审罪的游戏,但是王二认 清了这套游戏戏耍被审者的要害所在,以一种戏谑的自供瓦解或说跳出了这套游戏,开 始了他们自我选择的游戏——欢悦的性爱游戏。这两套游戏可说是《时代》最基本的两 种游戏方式。由于第一种游戏是作为社会规则而先在的强制性游戏,第二套游戏是受到 强制的个人为摆脱强制而做出的第二级反应,(这是就王二、陈清扬两人性爱关系的具 体展开而言的)因此,一,两者必然是关系性的;二,第二套游戏要想摆脱被动的反应 保证其真正是自己的游戏,就必须创造出第三套游戏——能够自由跨跃第一、第二套游 戏的游戏;只有如此,非抑制性平衡才能获得。这第三套游戏就是叙述人兼主人公王二 所玩的经验哲学的推理演绎游戏。
熟悉王小波“随笔”的人对此可能都不陌生,那本《我的精神家园》可以说是这种经 验哲学推理性游戏的结晶。然而在此,同样性质的游戏却必须具有不同的玩法,才有可 能具有自由、穿插的功能。王小波的高明之处在于充分利用了经验哲学接近日常生活的 特点,把一般性的严肃的哲学逻辑思考转化成戏谑性智性推理游戏。它遍布全篇,既随 心所欲地肢解着传统审罪游戏,又为情爱的欢悦游戏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注:这 点似乎与王小波性爱描写的自然勃发相冲突。但是需要注意,经验哲学本身就是建立在 经验基础上的,是经验的理论提升,所以与自发的生命经验是相通的,这是其一。其二 ,如果没有这套经验哲学的智性支持,王二们就难以摆脱审罪游戏的罪感心理的控制, 也就不可能进入到无拘无束的性爱状态。(与那些以佛洛伊德学说为基础的文学文本相 对照,更容易理解这一点)。所以这里的智慧是生命娱悦的不可缺少的基础。)在第一、 第二套游戏之间架起了自由穿行的桥梁,形成了王小波独特的文本世界。
(二)
创造新的生命游戏这只是颠覆传统情感结构的重要方面,另一相关的方面是新的游戏 世界的丰富多彩性。仅从王小波文本所涉及的关于“文革”的素材就具有前所未有的丰 富性,我们从中几乎可以找到所有的他人已涉及过的素材或角度。有关于知识分子受迫 害的大墙文学:贺先生、刘先生的故事;有章永璘式的知识分子改造、饥饿、 艳遇的:龟头血肿李先生的故事、刘先生的故事;有关于大批判、红卫兵武斗及其他行 为的;《啊》式的“文革”荒诞:关于李先生龟头血肿的论辩;有谢惠敏式的革命青年 的故事:X海鹰;有王朔式的游戏弋于运动边缘或革命空隙间的游荡少年的:小王二的 造式器、热衷于小发明制作、恶作剧、打群架、交异性朋友、逃学……当然还包括其他 人没有写或不屑于写的东西,如“屎”。所有这些杂乱的、不无矛盾的素材或角度之所 以能被容纳在一起,是与一种特殊的少年视角有直接关系的。关于此,一位评论者做过 专门分析。它被称之为儿童情结,被放到了“官方/民间、有权/无权、上层/下层”这 样的对立性社会结构框架上审视,从而揭示它对前一半权力的戏弄,僭越颠覆性功能。 换句话就是通过对原来被抑制了的少年情结的释放,关于过去、关于被压抑到了心里深 层的过去的经验和感受才无所顾忌的喷薄而出。[3]的确,读王小波的作品,尤其是读 《逝水流年》和《革命时期的爱情》,唤醒了我少年时代的许多印象,感到无比的亲切 。然而把这一切归为儿童、儿童情结显然是过于简单了。因为,作为一种经验的记忆不 可能有本真的状态,不可能完全摆脱折射。所以更确切地说王二的少年叙述是一种“拟 少年”的姿态。它巧妙地将儿童眼光所具有的好奇、开放性,同经验理性的冷静、宽容 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极为独特的叙述视野:即一种儿童的顽皮率真和成人的理智思考 相融合,文艺复兴时期式的对革命的欢悦和对“文革”摧残生命现象的反思相交织,冷 静的审视和所展示的人物自身的语义相交错。总之,由此叙述视点所展示的世界,在相 当大的程度上接近于巴赫金所谓的众声喧哗式的文本。它所具有的拉伯雷式的文体已有 评论家做出了精彩的描述,在此我想对这个文本世界的多义性语义相互对话性特点的稍 做一点补充。就此而言,关于红卫兵—知青理想主义的思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 入点。无疑王小波对狂热的理想主义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在多处借王二之口对其进行了 讥讽,甚至把其与粪便沤出的蓝光相类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叙述人直接站在这种理 想主义的截然对立面,对其进行全然的批判和否定,不给其以任何发言权和审辨权。相 反,由于王二所具有的拟少年视点,理想主义在《黄金时代》那里具有某种有意味的混 沌半透明性,构成了叙述人视野要素的一部分。一方面它往往以某种主动者的角色去观 察、去拟想对象世界,把一些看去无联系的散乱的现象聚合在一起,想给它们定性。可 另一方面,它的混沌、暖味的观察又显得幼稚、荒唐,变成其对象的和自我的否定性对 象。这里各种形式的存在都没有被剥夺发言权,各种声音彼此交汇、挤撞,但某种善、 某种正义之音仍然依稀可辨。
例如在《逝水流年》里,叙述人的对象性故事有三个,一是贺先生的自杀,二是李先 生与线条的爱情故事,三是刘先生的饥馋故事。它们之间本身并没有什么逻辑联系,而 是由直接出场的叙述人将其串接在一起:无所事事的王二,在各种不同的人物命运间游 荡穿梭,以某种顽皮儿童的生存方式将关于他人的故事与自己的生活一起呈现。但是王 二是一个深受革命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熏陶的顽皮少年,对英勇就义的行为具有狂热的 执着,这种执着使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贺先生就这样一声不吭地跳楼自杀,他想要弄 清贺先生临死前究竟想过什么,说过什么。于是他要千方百计地去弄清贺先生临死前究 竟有何遗言。正是这种不可理喻的冲动,在文本中赋予了贺先生之死以历史的延展性, 那一个瞬间性的行为,才反复地被拉入到后来发生的事件场景中,反复冲击着读者的视 野。这也就是说,狂热的理想主义在这里具有了结构的功能。另一方面王小波又设下了 一个毫无痕迹的机扣,它绽裂了狂热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一个荒谬所在:过分强调牺 牲的意义,或说牺牲本身,而放逐了生命这第一性的东西,宝贵的、每人只有一次的生 命、被外在的虚假的各种形式的英勇就义的表演所吞没。这一效果所达到的重要前提在 于混沌的少年理想主义的开放性,正是因为此,生命已结束但依然直直挺立的贺先生的 生殖器,才能被容纳于关于贺先生死之意义的思考中,并对其中的传统意识形态的执谬 构成无言的挑衅,最终与其他一些让人日夜不安的事情一起促使王二明白了人的死法各 异,“但每个人身上都有足以让他们再活下去的能量。我真希望他们得到延长生命的机 会,继续活下去。我自己也再不想掏出肠子挂在别人脖子上。”
上面我主要只是围绕着有限的几位作家进行讨论的,也许会给人造成一种误解,以为 这里所涉及现象是90年代文坛比较孤立和独特的表现,其实并非如此。若套用90年代文 学批评的一个时髦词语的话,可以说这些作品都属于“历史颓败期”的产物或表征。“ 历史颓败期”的写作是对80年代末、9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种总体精神特质的概括,揭示 了传统意识形态整合魅力消解之后的文化精神的无定向性、散淡性、衰败性。本节所讨 论的作品并不是最为典型的,在所谓的先锋—新写实的南方写作(注:我这里主要指苏 童、格非、孙甘露、余华、叶兆言等作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在八十年代后期被人们视 为先锋小说作家,后来又逐渐转向“新写实”。)那里要表现得更为突出。先锋写作以 语言实验和叙述革命的名义,书写了一个个家族的、个人的高度虚构化了的历史,呈现 出了一幅幅不同于以往的零散、破败的历史画面和生存景观,从语言的碎砖断瓦的缝隙 中散发出一股股腐烂发霉的江南气息。也许起初叙述革命的外表还多少掩盖了生存于失 范的的文化意识形态情境中的南方写作的匮乏和衰朽,当它被人们更多地标榜为新写实 时,就更为直接地流露出无可奈何的伤感,弥漫着世纪末且又是古老的古典情致。应该 说这破碎的时间、溃散的历史、忧郁的抒情,在总体上与本节所分析过的作品是非常接 近的。不过前者南方写作是通过走进重新虚构的“历史”来呈现传统意识形态的历史的 溃败,而后者则是把历史意识形态溃败的现实对相关个体生存影响的当下状态进行文学 化、哲理化的观照。而且前者不论是结构、故事、人物,意味都要比后者显得更为破碎 支离,而后者则相应更具完整性和形象性。所以单从作品的发表先后顺序来看,可以说 是后者对前者过于实验化叙述的改造,而若以两者所传达的历史颓败意识的强度来说, 后者则似乎又成了前者的过渡。
与《古典情节》、《裸燕麦》、《黑白》等相近的另一类文本是高红十的《哥哥你不 成材》和《上路》等。它们虽然没有直接呈现出文本化的时间存在形式,但其所采用的 片断式的、意绪式的漂忽不定的叙述,也传达出了对传统意识形态历史完整性破碎的恍 忽与焦灼。而且可能由于高红十个人典型的生活经历,(注:高红十,北京67届初中生 ,1969年赴江西插队,1972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入北大中文系读书,1975年毕业,重返 陕北农村,轰动全国,完整地经历了所谓“老三届人”的全过程。参见《劫后辉煌》中 的《延河在这里拐弯》。)她的这两篇作品所寄寓的知青情结与李锐的那两篇更为接近 。但是李锐本人已基本放弃了对所谓知青情结的执着,相当冷静地观照个体对虚幻历史 的执迷和这种执迷所体现的历史溃败的个人化承担,使文本含韵了复杂的意蕴。而高红 十则是想试图通过把以往的公共性的历史(知青历史)转变成个人的私有财产,来想象性 地逃避历史的失落。所以读《哥哥你不成材》不难感受到贯穿作品的中心情感就是这样 一个呼吁:不要用现在人的苛责来追问“我们这一代”。当然,正如我已分析过的那样 ,对传统意识形态直接产物的知青情结的执迷,绝不可能仅止于个人化的私人持有,潜 藏其深处的意识形态整合性功能冲动才是表面的个人持有的内在动力。所以当我们在《 上路》中发现,高红十用“起、承、转、合”的时间结构,试图重新将溃散的历史整合 在一起也就不奇怪了。(注:《上路》这个中篇共有4部分,分别以“起、承、转、合” 为名,每部分为3节,共12节。穿插叙述这样几大块故事:一,当年地下革命者的故事 和老革命者重返故地去为自己战友纪念馆剪彩的故事;二,“你”“他”两个当年的知 青彼此由聚到分的当年故事(主要是男“他”的)和眼下两人结伴旅行的关系故事;三, 当下的私人个体运输汽车司机和红衣女子的故事。这几大块故事,分别代表了传统主流 意识形态历史所界分的三大历史段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国后头二十多年的历史 ——当下的改革开放阶段。作者一方面似乎在淡化传统历史教义的刚性一体化解释,把 其抽象为“上路”这样一个隐喻,并且强调不同的人生经历只不过是走在路上的一个区 间:可另一方面,无论作品本身的结构安排,还是直接的思想表达,又明显地传达出想 将它们整合在一起的意欲。当然这种意欲并非高红十一人所有,我们在张承志的《金牧 场》那里已遭遇过。)
收稿日期:2001-11-01
标签:王小波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黄金时代论文; 读书论文; 英雄论文; 黑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