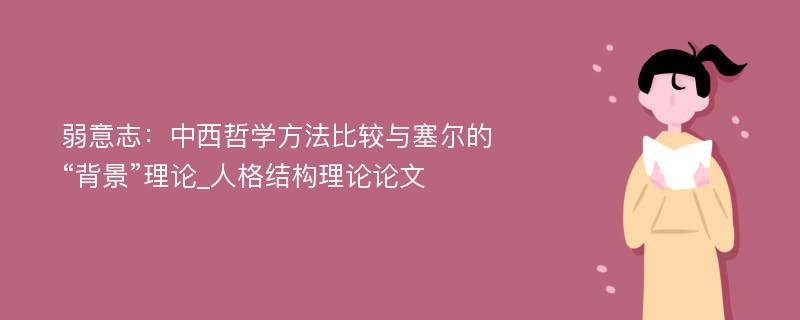
意志不坚:中西哲学进路比较及塞尔的“背景”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路论文,中西论文,塞尔论文,意志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06)05-0083-07
1.前言
下述行为司空见惯,我们差不多每天都会碰到:在作出了“X会是最好的做法”的判断后,形成了坚定而无条件的去做X的意向,最后却做了与之背离的Y。我们都得同意,人们常常故意做一些不符合他们的道德理性或计策(prudential)理性的最优判断(best judgment)的行为。此现象通常称为“意志不坚”或“akrasia”,而有关的行为则可描述为“意志不坚的”(weak-willed)、“缺乏自制的”(incontinent)或“akratic”①。传统将意志不坚看成是一种实践上的非理性(practical irrationality),因而认为意志不坚的本质和可能性构成哲学的课题,并须给予哲学上的解释。但最近,塞尔(John Searle)和阿帕丽(Nomy Arpaly)论证了意志不坚的行为不必具有非理性的特征②。塞尔的论证是简单而直截的否定,他认为“如果我们认为意志不坚的人都是非理性的,那么在世上就找不到有实践理性的人”。塞尔又认为,“意志不坚不是理性行为”这个传统观点,实源于一种关于理性和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的错误观念。另一方面,根据阿帕丽的看法,如果我们的最优判断(即对于“我做什么才是最合乎理性的”的判断)要有规范力量,那么这些判断必须为我们持有的某些信念和欲望所支持,而这些信念和欲望又应该是有一定根据的;所以“一个人的行为若背离了他的判断就必然是非理性的”的看法是很有问题的。按阿帕丽的分析,这看法源自“理性行为必须通过慎思(deliberation)才能产生”的观点;而后者是错误的,因为不基于慎思的理性行为明显存在。
当代西方哲学对意志不坚问题的主流见解,假定了“意志不坚的可能性需要哲学上的证明”。这个为塞尔和阿帕丽所质疑的假定,引出过许多精辟的论证,企图证明所有背离个人的无条件意向(unconditional intention)的行为都算不上是真正的意志不坚。然而,在传统中国关于意志不坚行为的论述中,却找不到类似观点。本文的一个目的在于阐明这一点,以及比较当代西方与先秦中国哲学对有关问题的进路的差异。我们认为,塞尔和阿帕丽(尤其是前者)的观点在某些方面与中国哲学的进路吻合,因而他们对西方的主流看法的批评,有助于理解中西进路的差别。
塞尔对有关问题的讨论,着眼点是晚近某些对意志不坚现象的解释,因而他很少论及“如何能够克服或避免意志不坚”这个实践上的问题。但他对主流观念的抨击,间接地鼓励了一种转向,即把问题的重心由“如何作哲学上的解释”转移到“如何克服意志不坚”的问题,由是转向一种接近中国式的进路来探讨意志不坚的现象。这个问题,正如尼维森(David Nivison)所认为,是传统中国道德心理学的中心课题。③但是,尼维森在诠释古典中国道德心理学时,却把塞尔所批评的(关于理性及实践推理的)“经典模式”(classical model of rationality and practical reasoning)视为理所当然。他假定了意志不坚的行为属动机(motivation)方面的缺陷。因而,他认为避免意志不坚的关键在于用伦理教养来重构情感状态(affective states)。下文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凸显尼维森的理论所碰到的困难。
通过对尼维森的批评,我们提出另一种看法来说明中国哲学里的行动观。我们又认为,此看法跟塞尔的行动理论,尤其是他的“背景”(Background)观念,有不少契合之处。本文的最后部分会论证:自我在执行意向时的不坚定,可以通过提升“背景”中的能力而得到改善。
2.关于理性的经典模式
让我们先看看塞尔对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批评④,藉此说明塞尔对意志不坚的分析。按照戴维森的解释,akratic或意志不坚的行为的特征是:
(A)行动者作出“做X的行为比做Y好”的判断,并且认为可以随己意做任一行为,但却选择去做Y。
所以,意志不坚的问题就在于:(A)似乎跟我们熟识的某些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ing)的原则相背离。
如果我们把(A)看成为对纯粹的意志不坚的行为的描述,那么在二十世纪的分析哲学,处理意志不坚问题的通常策略,就是企图证明根本没有纯粹的意志不坚行为。戴维森的理论就是一例。按此理论,我们一般认为是意志不坚的行为其实并不如(A)那样,因为行动者的最优判断(即做某个行为对他而言是最好的)只是有条件的(conditional),而不是绝对的或五条件的。因此,为了恰当地描述各种实际上经常出现的意志不坚的行为,(A)中的“判断”就必须用“附带条件的”或“初步印象的”来限定。如此,(A)和任何为人熟知的实践理性原则就不再矛盾了。
塞尔认为,戴维森这个分析的背后有一套关于动机和行为的因果关系的看法,但此看法却是站不住脚的。理由是戴维森假定了这样的观点:“就因果关系而言,信念、欲望等意向状态(intentional states)可以为理性的行为提供充分条件”。塞尔又认为,西方哲学对理性和实践推理之分析,有所谓“经典模式”(classical model of rationality and practical reasoning);而上述观点就正是此模式的核心原则之一。受这个观念所限,戴维森不能不认为,当某人的行为和他的意向与最优判断背离时,他不是真的持有相应的五条件的意向或价值判断。塞尔认为戴维森对意志不坚问题的处理,正显示出经典模式是错误的⑤。若此模式或戴维森的进路是正确的,行为的履行跟相关的心理先导状态(psychological antecedents,即先于行为的相关意向状态)之间就不可能有任何因果间隙(causal gap)。但塞尔却认为,这种间隙的存在是理性决策和理性行为所必不可少的:由于在思虑和行为的不同阶段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因果间隙,所以,对自愿而非强迫的行为来说,仅仅是行为的动机或意向,并不能促使我们去行动(2001:50.)。因此,我们必须作用于相关的理由或者意向(to act on the reason or intention),使其更有效地成为行动的原因。这种“作用于理由或者意向”,实际上相当于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努力去做下了决心要做的事。
塞尔强调行动或行为是为我们所执行或践履的,而不是以一种因果上必然的方式从某种心理先导状态产生出来的事件。所以,他认为意志不坚不过是心理先导和行为的执行之间的“间隙”的正常结果,是自由意志的一个标志,因此实在没有什么好令人困惑的。接着我们就要说明一下这个“间隙”的概念。
3.间隙
过往对意志不坚问题的讨论,着眼点都是在行动者能否按最优判断而作相应的意向性行动。但塞尔指出,在慎思和行为的结构中,还有其它可以出现意志不坚的地方。他认为,我们通常不会以一环必然地套一环的方式来经历“慎思——决定——行动”的过程。恰当地说,我们所经历的应是个连续的因果间隙(continuous causal gap)。这些间隙在不同的阶段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使得每一个阶段不能必然地引致下一阶段的出现。塞尔认为这些因果间隙出现于三处:
(1)第一个间隙存在于我们对决定如何行动的理由之慎思跟我们对如何行动所作的最终决定之间。作出这个最终决定即是形成一个行动的意向,塞尔称之为“先在意向”(prior intention)。
(2)第二个间隙存在于先在意向和行为中的意向(intention-in-action)之间,亦即存在于决定去做某事和实际试图去做之间。
(3)第三个间隙存在于开始行动与持续到其完成之间。所以,这一间隙可出现在执行一个须经历一段时间的“行为中的意向”的每一阶段。
传统观点认为,意志不坚的问题主要与第二个间隙有关,即不能执行先在意向。如果塞尔对间隙的想法正确的话,那么意志不坚问题就不必局限于这种执行上的失败。我们也可以由于不能形成某种先在意向而表现出意志不坚,或者由于不能执行一个复杂的行为直至其完成而表现出来。传统的行为失败问题之所以关注第二个间隙,只是过份强调理由的内在论(internalism about reason)的结果。塞尔的间隙概念提供了几个有用的区分来描述意志不坚的不同方面或阶段,这从来被传统观点忽略。
这“三种间隙”的观点还开启了一些理论上的可能,即是说,一个关于意志不坚的理论是否合理,可能有赖于所讨论的是哪一个间隙。也许不同的情形中的意志不坚需以不同方式来处理;因为不能完成复杂持续的行为与不能按实践理性慎思而形成合理的先在意向,应是颇不同的问题,其解决方法可能很不一样。
在下面,我们会讨论“间隙论”如何有助于理解中西传统在意志不坚的问题的差别。下节先勾勒出中国传统如何理解意志不坚的问题,然后将之与塞尔的观点联系起来。
4.意志不坚:中国式问题
古典或早期中国哲学(即先秦或战国时代的思想)⑥的中心主题之一是道德不牢(moral weakness)的问题,这与传统西方意志不坚问题同中有异。两者有两个主要的差别:
第一,传统西方哲学着重说明意志不坚如何可能;中国哲学关心的则是如何克服及避免意志不坚。所以,西方主要关注的是理论问题,而中国关注的是实践问题。而且,西方哲学家通常将问题理解为“行动者为何不能按照他的最优判断而行”,亦即一个涉及实践理性的问题;中国式问题则是:行为者怎样才能克服道德不牢或人格不稳,以使他可以坚持正确的道德道路。所以,将中国式的问题标示为道德不牢(moral weakness)或人格不稳(character weakness),似乎更为恰当。
中国哲学所讨论的行为单位是伦理道路或成德之途,而不是个别行为,而且问题是人格的缺失,而不是没法按实践理性的最优判断去执行意向。西方哲学家倾向于强调个人行为的是否合乎理性,并将意志不坚看成是实践理性和行为的逻辑关系,因此他们认为,意志不坚暴露了执行意向的失败,而不是为了追求伦理目标而坚持正确路径的失败。相反,在先秦关于行为缺失的讨论,所关注的问题是:人们往往知道正确的成德道路并希望循道而行,但由于缺乏决心、勇气、道德韧性而失败了。《论语》的这段对话概括了这个中心问题: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这里所讨论的行为单位是伦理路径或道的实践,是一整套实践、习惯和各种操行,而不是个别行为或意向的执行。第二,讨论的问题是冉求相信自己缺乏必需的能力或“力气”而不能践行道。为此,孔子巧妙地指责他事先就放弃了:这听起来熟悉得像体育教练所说:尝试了而失败是一件事,但在实实在在地尝试之前就为自己的能力划界,则是进取心不足。
这段话阐明,在中国传统中,道德不牢是不能守道,不能持续而可靠地做各种自知该做的事。先秦思想家多认为这类失败能通过练习和养成习惯来矫正。所以当讨论道德不牢的实践问题时,他们倾向于谈论怎样扩充德性来引导人们正确而可靠地行动,坚持正确的道路。循道而行的内容是提升某些能力和矫正行为的习惯模式;这些积累起来,就能培养成某种德性人格。因而,中国的思想家主要关注道德技能和习惯的成功运用和养成,以及旨在改善技能、习惯和德性的实践训练问题。
我们可用塞尔的“间隙”去刻画中西方对意志不坚问题的不同构思。西方传统问题关心第二个间隙,即未能按先在意向作相应的行动;中国思想家关注的是近乎第三个间隙,即“做某个行为的意向”跟“实际按该意向持续地践履相应行为”这两者之间的间隙。由此,早期中国哲学关注两个交错的实践问题,一是如何始终坚持对道的具体践履,另一是如何持续作人格提升和训练。这种提升和训练既是行道的一部分,又可强化行道的能力。
塞尔的理论也有助于凸显中国式问题的重要性。按他的说法,意志不坚的现象是间隙的自然结果;没有意志不坚,行为就谈不上是自由、自主或理性的。所以,只要我们认为意志自由是不容置疑的,就不用担心怎样去说明意志不坚如何可能。而且,间隙和自由的存在,其自然结果就是:无论行为有什么样的心理先导状态,意志不坚总是可能的。(这一点是塞尔反复提醒我们的。)那样的话,需要加以解决的就不是如何去说明意志不坚,而是“怎样应付或克服它”。所以,早期中国思想家将道德不牢理解成实践问题,可以说是将注意力放到了恰当的地方。
5.尼维森论意志不坚
尼维森在The Ways of Confucianism⑦一书所收录的几篇文章提出,《论语》、《孟子》、《墨子》等一些先秦哲学经典都曾尝试处理如何克服意志不坚的问题。尼维森认为,中国哲学家所关注的与其说是意志不坚akrasia,不如说是acedia(动机缺欠),即冷漠或缺少动机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1996:93)。这个主张已隐约显示出,尼维森诠译先秦哲学对意志不坚的处理时,其实已经预先设定了西方经典理性模式。他把acedia看成是这样一种状况:对事情不够关切,以至没有足够动机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1996:92)。所以尼维森说中国哲学家所关注的现象是:行动者由于动机不足,或者没有正确地致力于现有的动机,所以他虽然对应该怎样做作了正确的判断,但未能去做。恰当的解决方法是增强和重建情感和欲望,使得情感和欲望能与个人的规范判断一致(1996:99、102、144)。这样,我们就能充分关切应做之事,正确的行为就随之而成。很明显,这样的分析假设了动机(或至少是道德上有价值的动机)只能从欲望和情感中产生,亦即是假设了一种关于道德动机的内在论(internalism)及西方传统的“信念—欲望”式行动理论(the classical belief-desire model of action)。所以,尼维森实际上是将道德不牢看成是无法执行一项实践推理的结论的情况。他提议的解决方法是强化个人对情境的情感反应,使得我们能通过将道德反应从范例情形类推扩展到其它相似的情形中,将必需的动机转移到适当的地方。
至于如何加强或修正动机,尼维森认为有“共时的”和“历时的”两种情形。在前者,我们知道做什么,并且有被鼓动去那样做的倾向(disposition),但不能或不愿去落实这个倾向(1996:89)。解决方法就是学会执行“思想的内在行动”(inner act of thought)(1996:85),使这种倾向发生作用。至于历时的情形则是,要使我们的动机和规范知识相称,需要一个长期的,甚至是终生的自我培养过程(1996:85)。尼维森的论述主要是关于后一种情况。
尼维森认为墨家的后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没法处理对道德动机的问题;因为墨家没有将情感倾向的培养置于道德心理学之中。相反,他们相信,规范要求、社会的鼓励等足以驱使大部分人遵守道德规范,并最终成善。尼维森选取了一个名叫夷之的墨者和孟子的对话,以阐明墨家道德培养学说的缺陷。按尼维森的诠释,夷之认为,通过引导和扩充他们对亲属自然的关爱,可使行为者践行墨家兼爱的信条(1996:102ff.)。但尼维森认为这种进路是注定失败的,因为它以规范伦理的理由来推动人去执行自身的情感倾向所不能引导他们去履行的行为;相比而言,孟子的内在论进路则更有效。因为尼维森认为,按此进路,行为源自于适度培养的情感反应,而这正是防止道德不牢的唯一可靠的方法。
塞尔对传统模式的抨击和关于意志不坚的论述可以突显尼维森的观点所面对的困难。塞尔提出的论证不但提醒我们,中国哲学家的理论框架可能不同于西方的经典模式,而且还可以用来质疑尼维森对道德不牢所提的解决方法。因为按照塞尔的看法,无论我们怎样刻意强化行为动机的情感因素,意志不坚依然有存在的可能性。至于怎样才是一个可接受的实践解决方法,塞尔所提出的“背景”是一个密切相关的概念。
6.道德不牢问题的解决
尼维森曲解了中国思想家对道德不牢的处理方式。我们的看法是:他们不关注个别的行动,也不认为问题的解决在于培养和重新调整情感和欲望,并使它们和判断一致。相反,他们强调人都有能力或才能去发展德性人格,就像人人都有学会读书、说外语、游泳或骑马的能力一样。但要培养和应用我们的能力,我们需要养成习惯和训练。习惯的养成和训练不仅是修道的重要一环,而且能强化我们的道德修行。
在修道的过程,我们可能经历两种不同的道德不牢:个别行为上的缺失及非常严重的全面失败。前者类似于技能操作上的差错。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置身于塞尔所说的“不知怎样去做事”(a failure in how to do things),这是“意向状态的前意向能力(preintentional capacities)的运作出现障碍”(1983:155)。解决之道应在于持续地训练,以发展和完善个人的道德倾向和技术。全面的道德不牢则好象放弃训练计划,放弃学习课程、业余爱好、事业道路等。所缺失的可说是一种坚韧、献身或者决心,即任何能激励我们越过从行为的意向、心理先导到行为的完成之间的间隙的品质。这类道德不牢的解决方法,也在于通过养成习惯和训练,从而培养或增强相关方面的品格。
因此,先秦哲学对道德不牢问题的解决方法就在于持续进行道德训练和实践,达到既发展特殊美德,如仁,又发展一般的人格品质特征,如坚毅或决心等。这类训练的直接目标不是修正人对事物的情感反应,而是培养在道德上可靠的习惯和倾向(这些习惯和倾向很可能包含了一定的情感反应,但情感反应不是核心特征)。这种训练的成败,主要不取决于在任一阶段的意欲或情感状况,而在于有没有坚持训练的决心。
如果上述所言无大谬,那么类似以下的说法,应见于先秦哲学经典中:我们都有能力成为有德性的人,问题只在于能否“坐言起行”;尽管有时会不免失败,但当我们做错了,就必须重返正途,并坚持实践,直到道成为我们的第二本性为止。事实上,上述的看法常常被人用作表达孔子、墨子和孟子的观点,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就是一例。
7.“背景”的修改与自我的强化⑧
“背景”是塞尔的行动理论的中心论题,用来说明非意向能力或前意向能力或诀窍(knowhow)在意向性中的角色和作用。⑨“背景”包括各类令意向状态起作用的非意向的能力。“背景”这个论题可概述为:意义、理解、信念、欲望、经验、行动等等所有意向现象,只有在一套对意向内容起着必不可少的决定作用的非意向能力之内才能起作用。比如,一句话原只是声波,并不意谓什么;只有在某些使用语境中,该话语才会有意义。但语境之构成,就涉及说者和听者的一系列非意向的能力(从感官的知觉能力以至使得我们能参与复杂的社会活动的各种基本能力)。这些“能力”构成“背景”,也是意向状态和话语能够具有意义或内容所必需的。
塞尔的理论能够为如何防止道德不牢及意志不坚的问题作出很有意思的补充:“背景”包括的能力是构成人格或自我的部分基础,上面所谈到的习惯培养和训练能修改及强化我们的“背景”,从而防止道德不牢及意志不坚。这是因为这些训练有助培养德性倾向,令这些倾向和习惯随意向行为的发生而自动起作用,不需要意向的控制或引导。尽管由这些倾向和习惯产生的行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受有意识的推理和判断的监视和控制,但通常不必如此。相反,德性倾向和习惯能够直接地、本能地运作。这些倾向包括了对规则作出反应的倾向,使我们能以与社会制度规范相协调的方式行动,而不需要实际上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以规则引导行为。
我们因此认为修改和强化“背景”应有助于说明克服道德不牢所需的人格训练,因为“背景”就是前意向和非意向能力的潜藏部分,这些能力使行为跟其它意向现象发生作用。而德行就正是源自德性人格的意向性行为。长期的道德“训练计划”可培养出各种可靠倾向,于是德行便可理解为对特定境遇的道德上恰当和“熟练”的反应。我们认为,这些倾向之所以能产生这些反应,恰恰是因为他们是前意向的或非意向“背景”的一部分。而“背景”主要是自发起作用的,不需要意向的引导或控制。
按上述的说法,有德者是受良好训练而能持久可靠地循道的人。诚以修道,即持续的道德训练与培养,就是他的人格的核心,所以,“离道而行”对他来说,并不构成一种真正的选择。据此,我们的道德训练越提升,面对的可能性和选择就越受限制,而我们对行为的控制程度就越高,因而在道德上可以说更自由。这不是有点吊诡吗?“真正”的选择越受限,但却有更大的道德自主?“背景”的概念正好帮助澄清此点。我们都有自由作为的能力,习惯于认为自己的行为有大范围的可能性。不过,这个范围往往受环境、生理功能和“背景”等各种因素所限制。我们的生理的功能有一定限度,因而限制了我们的行动;同理,“背景”对我们能自由做的事情设置了限制。但我们也可以说,“背景”没有缩减我们的自由。首先,“背景”是使我们能够执行意向行动的因素。没有“背景”,根本就不可能有意向行为,更遑论道德实践。因此,“背景”是开启而不是禁闭行为的可能性。将一个业余篮球手训练成专业球员,并不会将他变成机器。相反,训练使他的“背景”能力的可靠性和娴熟度提高,令他可以做出以前做不到的,使他被培养成专业球员。同样,求道者以训练和习惯培养来修改“背景”能力,强化其人格,可能会缩窄他行事上的选择范围,但不会使他成为机械人。他不会把“离道而行不是真正的选择”视作自由的减损,反视之为人格的强化。
篮球运动员的例子还能带出另一要点,即道德训练在培养道德坚韧性的作用,正如专业运动员需要坚持训练。有德者之为有德者,其中一项特征就是坚持进行持续的道德“实践”。我们可能已经与道同游了很久,但无法避免的间隙总在当下。循道而行需要训练;长久循道则需要坚持深入的训练。道德不牢,不仅表现为对道的偏离,或者无法将我们做正确事情的天赋能力发展为一种德性人格,而且还表现为没法致力于循道而行所必需的训练。提升我们的“背景”的能力,是克服个别的行为缺失的关键;持续用力于训练和实践,是防止我们完全背离成德之途的关键。
此外,塞尔认为“背景”能够和制度规则产生因果作用而又不用“实际上包含对制度规则的任何信念、欲望和表象(representations)”(1995:141)。我们可以再看看篮球运动员的例子。初学的球员都需要学习一套外在规则、策略,并刻意地以这些规则和策略来引导自己。但技巧娴熟后,他就有了种种行为上的倾向,常常能对各种情况作出顺畅和直接的反应;所以他会恰当而自动地打球,不需要实际思考规则和策略。塞尔指出,如果说这个运动员已经学会非常熟练地应用规则和策略,那是错误的描述。因为他根本不再应用这些规则和策略。相反,他发展出了一些“背景”能力,而这些能力“在功能上相当于规则体系,但实际上并不包括这些规则的表象和内化”(1995:142)。这里,“背景”在解释规则反应(rule-responsive)行为中的作用,能帮助阐明有德性的人的道德力量的一些特性,即他们都能够以道德上“熟练”的方式来应对特殊境遇的道德要求,作出可靠的反应。正如上佳的技能,往往是把规则的遵循发展成为一组“背景”能力,伦理规范的活动一旦被整合到“背景”中,就会达到最高的可靠性和可控性,转变成不需要有意识地思考也能自动执行的行为。所以,我们认为,塞尔的理论不但适用于语言、游戏和社会实践,也同样适用于道德生活。
总括而言,“背景”——据此,性格和道德韧性——能够通过适当的方式来训练和修正,使得求道者愈来愈能可靠地贯彻他的意向,从而合乎道德地行动。塞尔的“背景”概念包括了很多倾向、能力和其它构成德性人格的要素。“背景”的理论能够凸显中国哲学家对意志不坚行为的一些观点。更根本的是,所讨论的不坚,不仅仅是理性的失败或执行意向的失败,而更是“背景”机制的失败。
注释:
①akrasia、akratic均为希腊词,意思分别为无自制力现象、无自制力的,英美学界分别译为weakness of will、weak-willed。在本文中,结合行文,分别将“weakness of will”、“moral weakness”、“character weakness”译为意志不坚、道德不牢、人格不稳。另,为方便查证,文中关于书名等基本信息的注释,采用原注。——译者注(以下未标明译者注的,为原文注释。)
②John Searle,Rationality in Action(Cambridge,Ma.:MIT Press,2001)及Nomy Arpaly,Unprincipled Virtu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③David S.Nivison(1996),The Ways of Confucianism,La Salle,Ill:Open Court。
④见Donald Davidson,"How is Weakness of Will Possible?",Davidson(2001),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页23。戴维森的论文初版于1969年。
⑤即使认可塞尔对戴维森的观点的批评是对的(塞尔还连带批评了黑尔(Richard Hare)的类似观点),我们仍可追问: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戴维森和黑尔这种对于“意志不坚的难题”的见解究竟可回溯到多远。但我们在本文不讨论这个问题。
⑥在本文,“古典”、“早期”、“先秦”和“战国时代”四词相通。
⑦见David Nivison(1996),The Ways of Confucianism,La Salle,Ill:Open Court。特别是“Weakness of Will i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Motivation and Moral Action in Mencius","Philosophical Voluntarism in Fourth-Century China”和“Two Roots or One?”等文。
⑧塞尔将“Background”作为专门术语使用,以大写表示。本文将其译为“背景”,并加双引号以示区分——译者注。
⑨塞尔将“背景”论题表述为:“所有意识的意向性,包括所有思想、感知、理解等等,只有和不是也不可能成为这个意识状态的部分的能力相联系,才能决定满足条件(conditions of satisfaction)。实际内容本身是不足以决定满足条件的。”见John R.Searle(1992),The Rediscovery of the Mind,Cambridge,Ma.:M.I.T.Press,第189页。早期的版本可见Searle(1983),Intention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第143页。塞尔在他1992出版的The Rediscovery of the Mind和1995出版的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中对“背景”有深入的论述。
标签:人格结构理论论文; 理性行为理论论文; 动机理论论文; 培养理论论文; 意志品质论文; 观点讨论论文; 道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