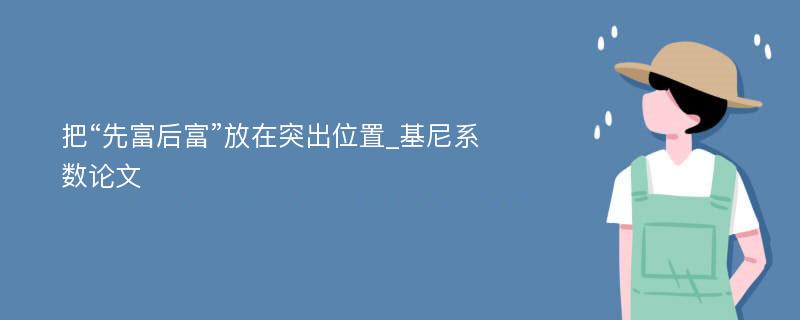
把“先富帮后富”提到突出位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富论文,位置论文,帮后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478(2003)02-0063-03
一
改革开放23年来,在“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个大政策的指引下,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已经变成现实。据统计,到2001年末,我国GDP达到95933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8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366元。部分地区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中,深圳、广州、上海、宁波、厦门、北京等地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已超过万元,其中居首位的深圳达到23500元。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上海(12883元)、北京(11577元)、浙江(10465元)、广东(10415.19)、福建(8313.08元)、江苏(7375元)、山东(7101元)。
在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出现了差距全面扩大的现象,为帮后富提供了对象。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由1999年的0.295扩大到2000年的0.32,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城镇10%最高收入户与10%最低收入户差距由1995年的3.79倍扩大到2000年的5.02倍。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上海为5850元,最低的贵州为1411.7元,高低相差4.14倍。城乡差距由2000年的2.79倍扩大到2001年的2.90倍,绝对差距由4027元扩大到4494元。如果加上城市补贴,城乡实际差距在4-6倍之间。
行业差距由1994年的2.38倍扩大到1999年的2.49倍,绝对差距由3893元扩大到7214元。2001年垄断行业的平均工资又得到了较快增长。其中,金融保险业由2000年的13178元增加到2001年的15628元,增长18.59%;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由12801元增加到14471元,增长13.05%;房地产业由12551元增加到14074元,增长12.13%;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由12170元增加到13987元,增长14.93%。2001年电信行业人均年收入57208元,居全行业之首,而排在行业之末的政府和公共事业人均年收入17993元,高低相差3.18倍。就体制内而言,同是公有制单位由于所在的层次、地域和行业的不同,收入差距悬殊;同是国家公务员,层次越高,收入越有保障;层次越低收入越少且无保障。
另一方面,靠“吃皇粮”的党政机关、全额拨款和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这些平均主义长期盛行的单位近几年差距也明显扩大。机关单位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相差4.28倍,事业单位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标准相差2.81倍。这是就统计数据而言,实际上单位内部负责人的收入比职工的收入高得多。他们分管的“面”越大、“摊”越多,其所取得的收入份额也就越多。而且,他们拥有的社会资源又比较多,可以在体制外利用市场“交换”到更多的收入。
二
一方面,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先富帮后富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主要是下列思想障碍所致。
一是怕走平均主义老路。现在仍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改革最大的威胁来自平均主义。这是需要澄清的一个模糊认识。事实上,中国改革以前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并不是导致普遍贫穷的根源,说平均主义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决定分配的原理和当时的实际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1](P306)所以,对平均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收入分配形式上的“平均”,更重要的是要看平均主义形成的原因——生产条件的分配及其运行方式。改革开放以前,在物质的生产条件的分配上的特征是“一大二公三纯”,是用计划的方法把资源分配于各个行业。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1](P306)以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为例,物质的生产条件为劳动者的集体财产,在经营方式上采取了集体集中劳动的形式。这种生产经营方式(或者说资源配置方式)且不说它违背了农业生产的自然规律,仅就其生产过程而言,也难以解决“不完全信息”和“搭便车”问题。也就是说这样的生产条件下其分配无法准确计量人们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干多干少都一样或稍有差别实在是无奈的选择。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就打破了平均主义分配方式。
现在经过20多年的改革探索,从农村到城市,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基础已经不存在,改革过程中的不公正现象以及过大的贫富差距造成的经济发展和人们心理的失衡才是当前改革的主要问题。
二是认为拉大差距可以提高效率。在一定条件下,适当的差距可以使人们努力工作、积极上进,从而可以提高生产和经营效率。但目前理论和实践都没有证明“差距越大,效率越高”命题的成立;相反过大的差距,不仅不能引起经济效率的提高,反而会导致下降。这是因为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容易造成高低收入者之间的对立情绪,增加低收入者的不公平感。这种不公平感造成的心理障碍会对低收入者劳动积极性产生不利影响,使其对提高效率采取消极态度。
此外,我国差距的拉大并不都是效率提高的结果,而是有效率的转移或损失存在。一些人的高收入是凭借其特殊的地位和关系而获得的,尤其是建立在以权谋私、卖官鬻爵、大量侵吞公有资产等腐败行为基础上的。而由此形成的差距不仅不会提高效率而且还会破坏社会风气和损失效率。这种基于机会不均等和特权基础上形成的收入差距既违反了公平原则,又严重违背了效率原则,更不符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可见,拉开差距并不等于提高了效率。
三是对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怎样才算处于合理范围没有一致的看法。主要的分歧在于:我国贫富差距比私有制国家应该是大还是小?就基尼系数而言,0.4的警戒线是高还是低?其实,我国的贫富差距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比都不可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不同的两个国家进行比较时,即使基尼系数相同,也并不表明下层人群具有相同的生活水平。比如,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与美国相当,但中美在贫困的含义上是不同的。1995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50,当年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为15569美元;我国1995年的基尼系数为0.445,当年农村的贫困线为人均530元,1996年城镇的贫困线为人均1671元。如果用我国的贫困标准去衡量美国的贫困,其结果可能是美国没有贫困人口;如果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我国的贫困程度,那么我国的贫困率会大大上升。因此,国际比较并不能对认识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多少帮助。
三
要统一认识和行动,把“先富帮后富”提到突出位置。先富相对于共同富裕目标而言,只是手段;而手段不能孤立存在,它必然要和一定的目的相联系。因此,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先富帮后富取得实质性进展。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情况,无论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还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看,都是不理想的。如果改变收入分配不平等现状,整个国民经济的福利水平都会提高,内需不足的局面也可以得到改善。
首先,要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现行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以往20多年收入分配方式和政策运行的必然结果。这个格局的调整可以有三种思路和结果:一是穷的状况有所改善,但不会富起来。比如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大扶贫力度等。二是穷人小富,富人大富,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三是穷人小富,富人处于零增长或变“穷”的状态。
第一种思路较易实行,但将继续加剧贫富分化。第二种思路当然很好,但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不容易行得通,并且由国内外经济环境所制约已经没有这种机会。第三种思路是目前可行的思路,但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会使现有的分配格局被“锁定”在既定的状态,并在今后的运行中得到强化。这不仅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使然,而且既得利益集团也要固守现行的利益格局。尽管如此,作为一个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打破“路径依赖”和体制“锁定”的格局。其中,由改革的受益者对受损者进行补偿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措施。当然这种补偿的原则是获益者(先富者)在补偿受损者(后富者)后还有剩余,从而构成了一个潜在的帕累托改善,使双方都获益。贫困者获益,是因为他们的收入有了提高;先富者的状况也有了改善,是因为他们有了一个安全发展的环境,因而这也是一种社会进步。当前进行补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税收上规范先富者的行为。
其次,充分就业。这是广大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形式。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成功地取得就业比任何其他方案都更有助于消除经济匮乏和缩小贫富差距。对于绝大多数靠劳动要素取得收入的人来说,失业和失业时间的长短一向是造成经济差别的重要因素。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命题固然不错,但其前提必须有劳动的机会和劳动的岗位。因此,与我们的目标相联系,我们有道德义务来保证充分就业。
我国经济改革的许多方面走的是一条资本密集型道路,也就是一条机器排斥劳动力的发展道路。从共同富裕的目标考虑,应该寻找一条资本与劳动力互补的发展道路。对于就业创造,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寻找与劳动力互补的投资,而不是替代劳动力的投资。例如在农业中,种植和收割的机械化可以替代大量的劳动力,而投在水利方面的投资却由于能够在同样土地上精耕细作,并且每年可以有更长的劳动时间,从而在事实上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再次,实现教育机会平等。教育机会分配的改善能够成为实现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的主要力量,是减少不平等的可靠而又有效的手段。国家投资于义务教育可以实现教育机会的均等,这比实行转移支付或累进所得税更具有积极的作用,它可以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
但是,改革以来政府实施了许多旨在把教育推向市场的措施,使教育资源的配置越来越不利于城镇低收入阶层和农村居民。如果受教育的机会只限于高收入阶层和特定的集团,那么,将会成为对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手段。所以,政府改变行为方式使教育机会均等,对改善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从而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加大对教育投资的力度。2001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在比前几年有较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也只占GDP的3.19%。不仅低于世界1995年5.5%的水平,而且也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我国属下中等收入国家)1995年4.4%的水平。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当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候,要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办教育。[2]因此,政府必须加大对教育投入的力度,为共同富裕创造有利条件。
